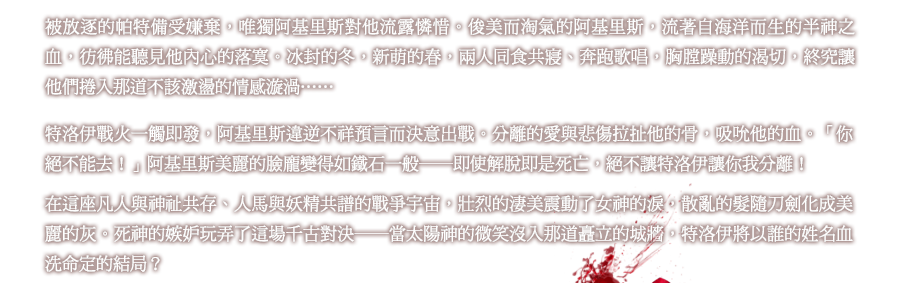我的父親是國王,他從列祖列宗繼承了尊貴的稱號。父親的身材矮小,與眾人相比並無特殊之處,然而他的體格如同公牛般強壯,足以承擔一切重任。父親迎娶母親時,母親只有十四歲,祭司祝福他們多子多孫。這是一門好親事:女方是獨生女,她父親的遺產最後將歸給她的丈夫。
父親直到婚禮當天,才發現母親生性愚癡。在此之前,外祖父一直想盡辦法遮住她的臉龐,希望能將此事隱瞞到婚禮之後,而父親不知內情,也就順從他的安排。如果她的容貌醜陋,那麼旁邊總還有女奴與侍奉的男孩。最後,當大家揭開面紗,他們說,我的母親笑了。眾人這才知曉我的母親是傻子,因為新娘一般是不笑的。
當我出生時──是個男孩──父親將我從母親懷裡抱走,轉交給奶媽撫養。可憐的母親,接生婆塞了枕頭到她懷裡,她竟以為那是我,緊緊摟著不放。她完全分不清枕頭與嬰孩的不同。
不久,眾人對我的期望轉為失望:我長得瘦弱矮小。我跑得很慢,不夠強壯。唯一可稱述的是我很少生病。同齡的孩子經常罹患的感冒與痙攣,在我身上從未出現。然而這反而讓父親起了疑心。莫非我是低能兒,還是我根本不是人?他總是垮著一張臉看著我。我的手似乎也感覺到他的不悅,一股勁兒的顫抖著。此時我的母親卻只是一臉癡呆,任由嘴裡的酒流淌下來。
我五歲那年,輪到父親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競技者從各地聚集而來,其中有遠從色薩利(Thessaly)與斯巴達來的,他們帶來的黃金讓我們的府庫為之充盈。一百名僕役花了二十天的時間努力錘打出平整的跑道,並且清除所有的石頭。充滿雄心的父親,矢志舉辦一場當代最盛大的運動會。
我對賽跑選手的記憶最深刻,他們在深棕色的皮膚上抹油,整個身體看起來光滑晶亮。陽光下,他們在跑道上伸展身子,進行賽前熱身。各年齡層的選手混雜在一起,有肩膀寬闊的成年已婚男性,也有臉上白淨尚未長出鬍子的少年與男孩,他們的小腿肌肉賁張,一副蓄勢待發的樣子。
公牛已被宰殺,血液緩漫流入帶著塵土的深色銅碗中。公牛並不掙扎,平靜等待著自己的死亡,對即將來臨的運動會來說,這是個好兆頭。
選手齊聚在高臺前,父親與我坐在上頭,四周擺滿準備頒給優勝者的獎品。有黃金的調酒器,精心打製的銅鼎,以及用梣樹葉子裝飾的貴金屬。不過真正的獎賞其實在我手裡:這是剛用灰綠色葉子製成的花環,在我的拇指撫磨下泛著光亮。父親把花環交給我,但他似乎不太放心,他不斷叮嚀我:我只要專心做一件事,就是好好拿著花環。
年紀最小的男孩先跑,他們的雙腳不安地踩踏沙土,等待祭司點頭起跑。這些男孩正值成長發育的時期,尖銳細長的骨骼,在緊實的肌膚下特別凸顯。數十顆深色蓬亂的人頭攢動著,唯獨一名金髮男孩吸引我的目光。我忍不住向前想瞧個仔細。他的頭髮在陽光下閃耀著蜂蜜的顏色,當中閃爍著金光──那是王子才能佩戴的飾環。
他比其他男孩來得矮小,氣宇間仍不脫幼兒的圓潤與稚氣。他用皮革從後面繫住長髮,對比著背部古銅色的肌膚,他的金髮顯得更為光亮。當他轉頭時,可以看到他臉上的神情跟成人一樣認真專注。
當祭司敲打地面時。他很快就從其他男孩的厚實身軀當中脫穎而出。他的腳步輕盈,粉紅色的腳跟就像舔舐的舌頭一樣。他贏了。
我看著父親從我膝上拿起花環,為他加冕;在他的金髮映襯下,花環的葉子似乎暗沉了不少。他的父親佩琉斯(Peleus)走到他身邊,微笑著,露出自豪的神情。佩琉斯的王國比我們小,但據說他的妻子是女神,而他也深受人民的愛戴。我的父親看著他們,眼神中充滿欣羨之情。他的妻子是蠢貨,而他的兒子跑不過比自己年幼的孩子。他轉頭對我說。
「看到沒有,這才是一個兒子該有的樣子。」
少了花環,我的雙手空虛無比。我看著佩琉斯國王擁抱他的兒子。我看著男孩將花環擲向空中,又接住了它。他笑著,臉龐因為勝利而熠熠生輝。
回想當時的自己,除了這件事以外,似乎只剩片段的影像:父親眉頭深鎖地坐在寶座上,我喜愛的一個小巧玲瓏的玩具馬,我的母親在沙灘上看著愛琴海。在最後的記憶中,我為她打水漂,石頭在海面上跳了三下,發出輕巧的聲音。母親似乎喜歡看著漣漪來回散布,最後恢復平靜的樣子。或許,她喜愛的是海本身。她的太陽穴有一塊星形的白色疤痕,看起來像骨頭一樣,那是外祖父用劍柄打她所留下的。她把腳趾頭埋進沙裡,然後又攪動沙子,我在尋找石頭時特別留意不去打擾到她。我找到一顆石頭,用力將它擲出去,我很高興自己還擅長打水漂。這是我對母親的唯一記憶,但似乎太過美好,我已經無法確定這是否出自我的想像。畢竟我的父親不可能允許我和母親單獨相處,一個愚蠢的兒子,一個更加愚蠢的妻子。而且,我們在什麼地方呢?我無法認出那片沙灘,以及海岸線的景觀。因為在那之後發生了好多事。
§
我站在原野中。手裡拿著兩對骰子,這是禮物。不是父親送的,他從來不會想到送我禮物。也不是母親送的,她有時並不了解我。我想不起來是誰送我這種東西。是來訪的國王?還是邀寵的貴族?
骰子是象牙雕成的,上面鑲嵌著縞瑪瑙,在我的拇指撫摩下,感覺光滑無比。當時正值夏末,我氣喘吁吁地從王宮跑了出來。自從賽跑那一天起,父親開始派人訓練我從事各項體育競技:拳擊,劍與矛,鐵餅。但我擺脫了那個人,獨自一人反而讓我更加精神抖擻。這是第一次,我一個人獨處了數個星期。
然後,那個男孩出現了。他名叫克里索尼穆斯(Clysonymus),是貴族之子,經常出入宮中。他比我年長,個子也比我高,但肥胖的樣子著實令人不悅。他的目光被我掌中骰子發出的亮光所吸引。他斜眼看著我,隨即伸出手來。「讓我看看。」
「不。」我不想讓他又髒又粗的手指碰我的骰子。況且無論我再怎麼年幼,我好歹是個王子。難道我沒有這等權利?但這些貴族小孩已習慣對我予取予求。他們知道我的父親不會干預。
「我要這些骰子。」他連威脅都省了,劈頭就向我索討。我討厭他這麼做。難不成我有那麼好欺負。
「不。」
他走向前。「把東西給我。」
「這是我的。」我咬牙切齒,就像狗一樣,準備為了桌旁的殘羹剩飯扭打一頓。
他開始動手搶奪,我一把推開他。他跌倒在地,我很高興。他不可能拿走屬於我的東西。
「嘿!」他生氣了。我的體格瘦小;人們都說我很容易打倒。如果他就此退縮,那將會是件丟臉的事。他走近我,漲紅了臉。不自覺地,我退後了幾步。
他得意地笑。「膽小鬼。」
「我不是。」我大聲回道,我的皮膚開始發燙。
「你父親覺得你是。」他從容不迫地說著,彷彿一邊說一邊品味著。「我聽見他對我父親這麼說。」
「他才沒有。」但我知道一定有這麼一回事。
他越走越近,舉起了拳頭。「你的意思是我在說謊?」我知道他要出手打我了。他只是需要一個理由。我可以想像父親是怎麼說這句話的。懦夫。我使足了全力朝他的胸膛打下去,推開他。我們腳下踩著青草與小麥,就算摔倒也不會受傷。
我也有了理由。而這裡也有一片岩石地。
他的頭砸在石頭上,發出沉悶的聲響,我看到他驚訝地瞪大了雙眼。他周圍的地面開始流出血來。
我呆望著,對於自己闖下的大禍害怕得喘不過氣來。我從未看過人的死亡。我看過牛、羊,還有無血的魚喘氣的樣子。我在畫裡、掛毯上看過,還有燒製在大淺盤上的黑色人像。但我從未看過這種情景:咯咯的聲響,窒息與掙扎。我聞到了血腥味。我逃走了。
不久,他們在長著瘤節的橄欖樹旁找到我。我站不起身子,臉色蒼白,身旁全是我的嘔吐物。骰子已經不見了,八成是在逃跑的過程中遺失了。父親憤怒地看著我,他的嘴唇緊繃,露出一口黃牙。他示意僕人把我抬起來,扶到屋內。
男孩的家人要求立即將我流放或處死。他們的勢力龐大,而死者是他們的長子。他們也許允許國王焚燒他們的田野或強姦他們的女兒,只要國王願意付錢賠償。但你絕不能動他們的兒子一根寒毛。否則的話,貴族會掀起暴動。我們都知道規則;我們遵守規則以避免天下大亂,因為混亂總是間不容髮。血仇。僕人做了去邪的記號。
我的父親一輩子費盡心力保全他的王國,他不可能為了我這樣的兒子而捨棄國王的寶座,畢竟兒子可以再生,而要找到能生育繼承人的女人亦非難事。於是他同意將我流放,我將在另一個人的王國長大。父親以與我等重的黃金為代價,讓對方養育我直到成人。我將沒有父母,沒有家族姓名,沒有遺產。在我們這個時代,處死是較佳的選擇。但我的父親是個實際的人。支付與我等重的黃金要比為我辦個隆重的喪禮來得划算。
這是我十歲時發生的事,我成了孤兒。我因此來到了普提亞(Phth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