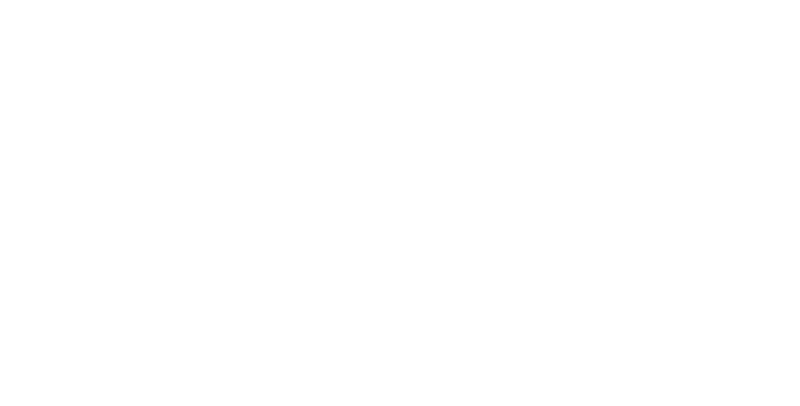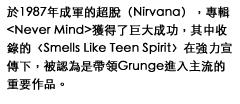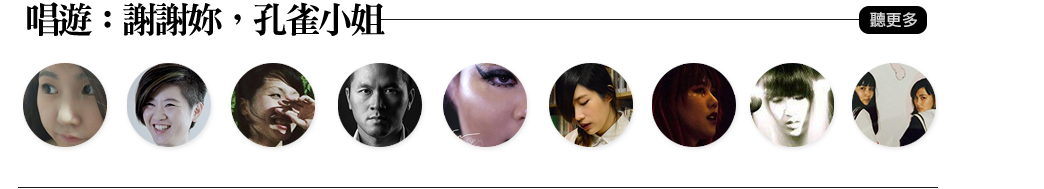「惡女」,「惡」在哪?看到時代雜誌上「她可以引領華人民主」,還要開玩笑 「尤達大師」,台灣已經要迎來第一位女性總統,我們準備好正視女人當家,而不只是宅男女神佔據電腦螢幕?先不管性別是否已經平等,性自主是否已經獲得真正話語權,對於特立獨行的且具有主張的女性,人們是愛多,還是恨?傾國傾城的獨裁,是迷人,或是毒狠?同樣的標準,放在男性身上呢? 這世界長期習慣男性為權力中心,女性的角色,在「強人」的定義上,是否負面多過肯定,其實單純只是習慣污名化強勢爭議女子? 「惡女」的惡,很特別,很廣泛,很隱晦,在這次「惡女」書展與講座中,我們試著不去直接定義,而嘗試從時代與文化意涵上,檢視「惡女」的形成與特徵,拉出一條「惡女警戒線」,別誤會,命案現場需要拉出警戒線,是為了細看發生的一切。 行文至此,我還是沒有拿掉引號,唯恐讀者認定我們輕易的「惡」,輕易的「女」,儘管難以一言蔽之。歷史會發明「鐵娘子」這類字眼,卻不會去說「鐵男子」,為什麼?男人與女人爭取認同與企圖,何以故事的原型從頭開始就不同? 避免粗略刻板(男/女,強/弱)的歸納,在女性主義和性別平等的旗幟下,關於女性的魅力與實力,誤會不曾少過,解讀仍待開發。這是我們探究的原因,在翻案與重現裡,還有太多細節。跳脫認知的輪廓,新的說法從各類文本的研究中,「惡女」是一個十年前看跟十年後看都會截然不同的議題。 見樹不見林,然而林的本質豈能跳過,「惡女」是一個概念,但不看案例,無法知其所以。繼往開來,我們找尋幾項範圍,請文化達人們從地域差異,流行語彙,各式社會/文本/藝術/政治人文方式解讀開講,把這「惡女警戒線」漸漸拉廣,景深也漸顯立體。 女權當道,並不等於「惡女」時代到來,一如前述,不久後當我們回頭看此題,會有截然不同的角度。一種嶄新文明論述來臨前,先讓我們回到當下,細讀惡女,端詳,靠近,理解。因為很多時候,理解惡女是理解自己所逃避的那些自卑,那些恨。權力優越中,敗給女性的自己,怎麼面對世俗的理解? 容我在此先把引號拿去。讓「惡女」,來到惡女。? |
 |
||
|
1.「如果我們嫉妒某人,我認為那是因為她備受稱讚。也許她們有些肢體特徵是我們喜歡的,我們只是不想讓其他人覺得,我們無法接受自己。」(《怪女孩出列》,P.133) 如果,女生這樣看待性徵或能力上特別出色的同性,那麼便不難想見,在職場為準的文化中,男性為本的陽剛,遇上惡女,會有多麼挫敗。在許多層面,惡女像一面鏡子,讓人們坐立難安。她們或許無畏世俗,叛逆果敢,但也可能溫文恬靜,細膩肢解周遭對自己的誤解,默默的刃不見血。很難說何種較為俐落驚世,但都是巨大無比的能量,永遠超出分析。這股能量的匯聚,包含了許多因素。至於惡女的外顯型態與刻板,相較都算容易理解了。你知道流行小天后泰勒斯(Taylor Swift)把她人生中愛戀的懦弱男子寫進歌,覺得這樣很帥或很賤,但有想過她何以要這麼做,這麼做需要正當性嗎?能不能,只要她喜歡就好?那不只是一個流行議題,那是一種自由。Lana Del Ray在歌曲裡唱「高談闊論以為自己是神的男人,自由還得你來給?這才不是我這賤貨要的,我要你的錢你的權你的榮耀,哈里路雅,我全都要」,管她用什麼換來,她的確成功了,這事情難道有辦法一廂情願?當不成《春琴抄》裡的佐助犧牲奉獻,當不成去小七幫前女友買東西的痴心男,眾人會同情你是一時,但仔細想想,憑著不平等心態嘆息的自尊,來日無多。 |
|
||
|
2.污名化不可怕,「女巫化」,很可怕。 從小野洋子與約翰藍儂之間,我們看見一種細微的特質:惡女的出現時常伴隨著一個鮮明的男性。在這裏,我們必須先理解故事原型:許多人認為披頭四的解散來自約翰藍儂的改變,而這樣的改變來自於他一見邂逅的小野洋子。小野洋子本身的特質也夠鮮明,作為一個前衛藝術家,她吸引了原本「乖」的約翰藍儂(披頭四後期作品雖然已經進入另一狀態,但整個團的形象有很大部分仍停留在乖巧伶俐的男孩搖滾中),人們很少去思考藍儂「為什麼」會被小野洋子吸引,卻會指出「小野洋子改變了約翰藍儂」。約翰藍儂的內心世界,便就此被他身邊的惡女形象簡化了。這是公眾「找尋女巫」的過程。當約翰藍儂去世,人們尤其需要一個攻擊的理由與對象,小野洋子在此簡直是完美的女巫。 即使你情我願,歌迷依然難以接受小野洋子「改變」了藍儂。在後來出版的滾石雜誌專訪內容《藍儂回憶》(《Lennon Remembers》,2001)中,讀者與歌迷可以輕易覺察到,對約翰藍儂而言,小野洋子的才華與魅力是一種信仰,使他自由的心發光。但是,歌迷怎麼可能這麼容易接受偶像的變異只是因為愛戀的神秘呢?他們得找出一個惡女。來追討偶像之死的原因。 1990年代極盛的搖滾巨星樂團「超脫」(Nirvana),主唱柯特寇班(Kurt Cobain)英年早逝,關於他的死亡眾說紛紜,一個始終沒有消失的理由是,彼時他的妻子寇妮拉芙(Courtney Love),如何讓寇班傷透心,玩弄,甚至一說是寇妮殺了(實際上的「殺死」)寇班。當英雄的死成謎,獵殺女巫的情況就出現了。而唱片工業如何繼續透過緬懷來榨乾偶像死後的價值,自然也需要投射「代言人」,每一次當小野洋子或寇妮談論他們的亡夫,很大一部分的樂迷是恨透了。怎麼可以你們還好端端的,在這大放厥詞,而偶像已死? 神祇偶像,必須是男性。總是如此。 中世紀的「獵殺女巫」,是一種廣泛的「運動」。看看當時奉行於世的「女巫之鎚」吧,「如果被告過著不道德的生活,那麼這當然證明她同魔鬼有來往;而如果她虔誠而舉止端莊,那麼她顯然是在偽裝,以便用自己的虔誠來轉移人們對她魔鬼來往和晚上參加巫魔會的懷疑。如果她在審問時顯得害怕,那麼她顯然是有罪的,良心使她露出馬腳。如果她相信自己無罪,保持鎮靜,那麼她無疑是有罪的:因為女巫們慣於恬不知恥地撒謊。如果她對向她提出的控告辯白,這證明她有罪;如果她由於對她提出的誣告極端可怕而恐懼絕望、垂頭喪氣,緘默不語,這已經是她有罪的直接證據。」 小野洋子怎麼可能不是女巫?寇妮拉芙怎麼可能不是惡女?只要把「宗教」概念換成「搖滾英雄」或「文化偶像」,惡女怎麼樣都是有罪而被需要的。 在人類文明中,有罪但又被需要,是一件聽似詭異,卻一直存在的事情。但我們始終沒有戒除這個習性。在影視與音樂流行文化中,甚至是各類次文化,陰性書寫等領域,女巫陰魂不散,一個男子性形象的對照,有時比惡女之所以是惡女,來得更強大。 |
|
||
|
3.抱持著自以為已經「開放」的心態,理解惡女之中的誤解,又是另一個題目。 武則天成了武媚娘,透過戲劇中的人味,翻轉了詮釋的角度,哪怕不是全面,也不再刻板。這是很基本的需要,當「開放」從相對(相對,多麼憐憫的詞彙),來到絕對,認識惡女的必要就不再針對性的包容或攻擊,身處在這個社會,尤其透過網路媒體,太容易被告知平等與出色的意義,悍婦,鐵娘子......「讓強者變弱並不會使弱者變強」(柴契爾語),那麼甘於自己是較為弱的一方,意識到所謂的強者嗎?因為,恐怕有太多惡女都需要被超譯,不是超渡。 於是這一次,我們從流行音樂的惡女獻祭,一直到行為藝術中的惡女豔遇,惡女,豈止是一個酷炫的潮流題目,裡面多少血肉痛交織,又有多少虐戀痛爽,是「巧婦常伴拙夫眠」,還是「烈女怕纏郎」,2016春季,一起來讀冊尋找惡女現場。 「不用你來說我們很正 不用你說我們普妹 不用你這態他媽度差的男孩 不用你跟我晚安吻別 我們才不需要你,才不需要你 身為女孩我們才不鳥你 不用你來說我們很乖 不用你來說我們很遜 不用你來保護我 不用你的屌來肏 嚇到你了嗎?我們不需要 嚇到你了嗎男孩?不需要 我們不需要,不需要 我們龐克馬子,才不需要你們」 這團叫比基尼殺很大(Bikini Kill),兇狠嗎?這還只是九零年代的歌曲呢。來吧,惡女精神正在召喚你,我們把鏡子抬出來,看看恐怖的是女,是惡,還是你。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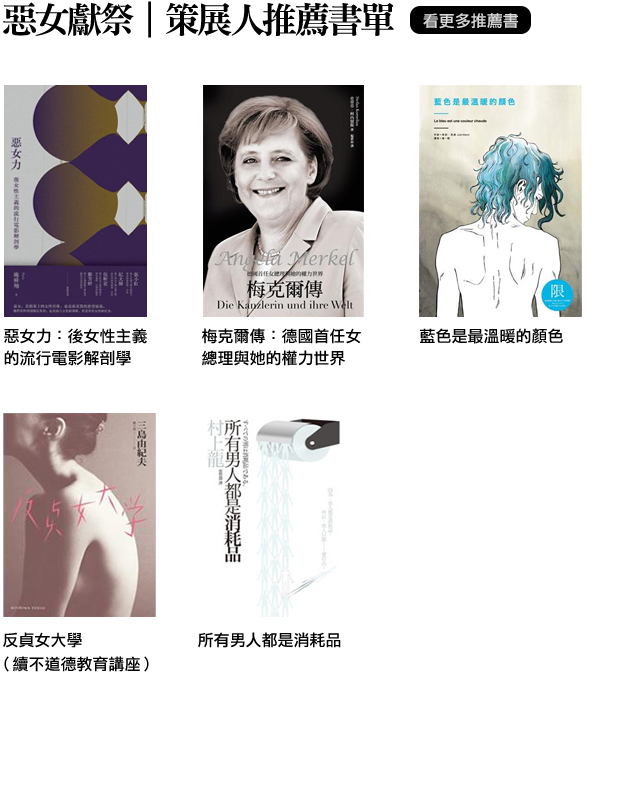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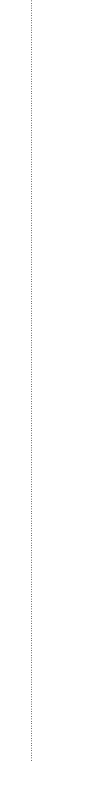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