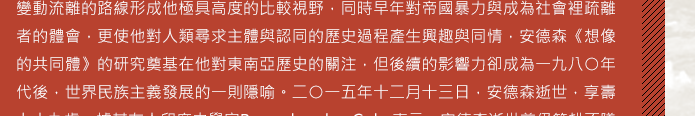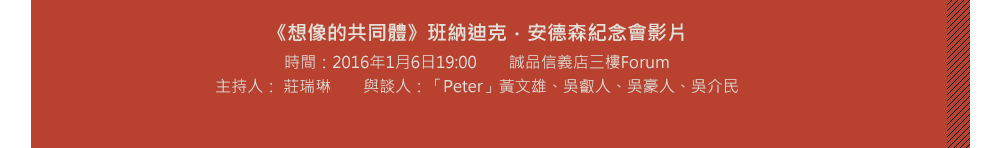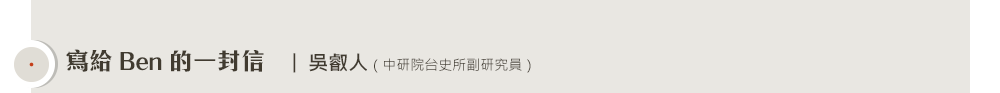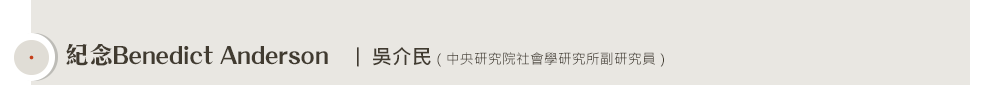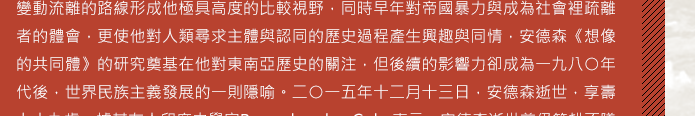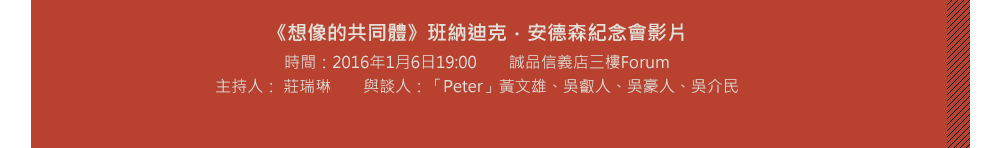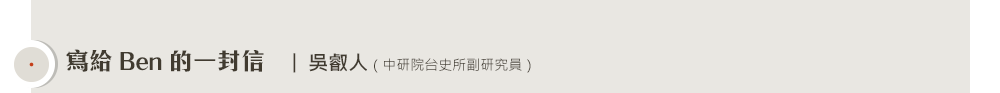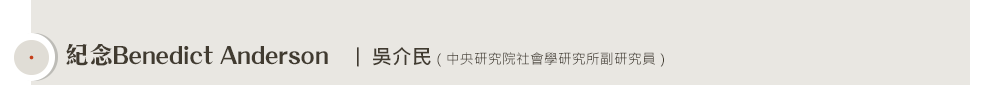Dear Ben,
很久很久沒有寫信給你了—自從五年前冬天母親開始生病以後,就停止了吧。這五年中我自己經歷了不少事情,臺灣也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還發生了一場號稱「太陽花」的準革命呢。去年十一月在Johns Hopkins 見面,時間太短,你身邊又總是圍繞著仰慕的後輩們,我除了幫你撐傘拿書包之外,什麼也來不及說。前些日子把今年春天寫的〈黑潮論〉翻成英文,才想到說應該寄給你看看,讓你知道我從寫了那篇〈賤民宣言〉以後的思想發展,順便跟你報告一下這幾年來的一些事情,結果卻聽說你又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Ben,你現在到底在哪裡呢?一個人悄悄從印尼回到曼谷了嗎?還是又跑到你泰柬邊境的那個村子裡,和當地的小孩們一起悠閒地過年了呢?唉,到哪裡都好,只要平平安安就好,你膝蓋痛,別再四處亂跑了。
兩個禮拜以來都在整理以前和你的通信,印起來厚厚一疊,一封一封讀,很多往事浮上心頭,自己十多年來的精神歷程彷彿也清晰地重現了。然後,這幾天和東京的白石隆學長通信,他寄了幾篇最近寫的文章給我,都是從東南亞研究,特別是印尼研究的脈絡裡討論你的學問的。讀了他的文章,我突然驚覺到我接觸你,認識你,乃至受你影響的過程,和他這樣正統康乃爾現代印尼研究計畫(Cornell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出身的門生比起來,是多麼的「體制外」,但同時也是多麼的個人啊。我們不僅是在「你的印尼」之外認識的,我們的交談內容也總是會逸出學院界線之外,遠遠地擴散到了政治、電影、人生、海涅的詩,甚至愛情。Dear Ben,回想起來,這些年來我一直在信中不停地向你發問呢,但我的發問總是會忍不住從知識的困惑延伸到臺灣的困境和個人的困境—包括我那微不足道、痛不欲生的,tragic-comic的失戀,而臺灣與我個人的困境最後總會重合在一起,於是在這些書簡當中,一個渺小個人的存在苦惱變成了臺灣的世界史處境的縮影或隱喻。信中的我讀起來像一個受詛咒的薛西弗斯,悲情地仰望崇高的奧林帕斯山。然而你從不厭煩,有問必答,不僅親切地啟迪我以知識,給我許多溫暖的安慰和鼓勵,還會講很多很多笑話給我聽,教我用戲謔與自嘲,化解世間這一切不可忍受的荒謬,和我可笑過剩的自我意識。所以每次讀你的信,總是一邊戰戰兢兢地反覆深思,但一邊又要忍不住捧腹大笑,於是悲情完全消散,大我小我紛紛讓位,只剩下某種對大寫的「歷史」澄澈的釋然。然而笑聲方才收斂,你又會突然正襟危坐地指著我那篇憂傷的〈賤民宣言〉說:「把臺灣變成一個像樣的好國家不是烏托邦,只是需要持續不懈的工作。」於是薛西弗斯只好再度起身推動那塊巨石,只是這次臉上帶著一絲自嘲的、戲謔的、體悟的笑容。
Dear Ben,在認識你之前,我在芝加哥大學就先認識了許多了不起的老師,他們大體上塑造了我日後的知識傾向,然而這間經院實在太嚴肅,老師們可敬而不可親,或者親切而不親近,我被包裹在一個巨大而疏離的古典精神氛圍中,過著敬畏、孤獨的求道生活。開始翻譯《想像的共同體》是我解放的第一步。你那恣意而自制的美麗文字釋放了我被芝加哥學派的社會科學與哲學深深壓抑的,詩的感性。然後我認識了你這個人,這個為我傳道授業的經師,為我解惑的人師,關愛我的父兄,與我長夜把酒傾談的摯友,甚至與我一同為臺灣,為弱者戰鬥的同志—認識了你,dear Ben,這個超越經院成規,以詩丈量世界的,奇妙的越界者和說書人,讓我體內長期被壓抑的所有浪漫主義能量,所有歷史熱情一齊爆發,衝決了一切學術體制的規訓,和我多年在經院禁錮中習得的教養全面交融,於是在最後那段經院歲月裡,我才終於能夠寫出我的《The FormosanIdeology》,和芝加哥和解,和自己和解。Dear Ben,偶爾我會遺憾自己「血統不純」,不是你在康乃爾的門下生,像白石隆學長一樣,但其實更多時候我慶幸自己不純的血統,慶幸自己是這樣帶著芝加哥的美麗與哀愁,風暴般地碰撞到你的─碰撞到你,然後我就有如歌德筆下漂泊的Wilhelm Meister一般,終於在你的星空下完成了修業時代。
不知不覺又失控了,dear Ben,這說明我的文字修為實在太淺,然而你說除此之外,我又該如何描述你之於我的巨大意義呢?你一定會說,我們就只是好朋友啊。不過當然不只是這樣而已。我手中這一大疊累積了十六年的通信,讀起來簡直像是一段段蘇格拉底和弟子的對話啊—當然,我們的對話要更熱鬧,更好笑,而且也更有人情味,因為你幾時聽見蘇格拉底會安慰失戀的弟子說「可是只有患相思病的牡蠣才會孕育珍珠啊」呢?Ben,我把這些信再印一份,寄給你吧。你讀讀這些珠玉般的話語,就會知道自己身上畢竟留著Jonathan Swift和葉慈的愛爾蘭血液了。
這次重讀我們的通信,我驚訝地發現我竟然早在一九九九年就向你表達一種身為臺灣人的「受困」焦慮,並且向你求救了。以後幾年間,這個主題好幾次出現在我寫給你的信中,並且成為我們之間兩次在日本公開對談的主題。事後看來,「受困感」(sense of being besieged)竟構成了我們這些年對話中反覆出現的主要動機(leitmotif)之一。最初,我是在試圖掙脫北美學界無所不在的中國意識型態羅網,並且回應後現代主義思潮對主體形成的攻擊,想為臺灣在世界知識地圖上找一個獨立位置的苦鬥中,體會到這種受困感的。那時候,你教我用一種「奧林帕斯山頂上的思考」,站在世界史與比較史的高度觀看臺灣,我也確實因此找到了臺灣獨特的歷史軌跡,並且寫出了一篇「奧林帕斯式的」博士論文,擺脫了中國民族主義史學幽靈的糾纏。然後,隨著中國在二○○○年代初期崛起,乘著資本全球化的浪潮進逼臺灣,我的受困意識再度浮現,而且更強烈,強烈到了要問你「hownot to become a cynic」的地步,因為一百多年前馬克思經驗過的那種巨大的、非人性的結構力量,以一種更凶猛、辯證的方式重新現身在這個時代。更糟的是,我在這時候讀了芝大老師John Mearsheimer的現實主義名作《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第一次深切體會到地緣政治位置如何像一個牢籠,緊緊地禁錮著處在帝國夾縫中的福爾摩沙。此後幾年,我的受困感與悲觀主義日益加深,因為我想不出在資本與帝國夾擊下,我們能有什麼出路。〈賤民宣言〉就是這段悲觀主義時期受困意識的結晶。二○一一年春天,我在親歷東日本大震災和福島核災,驚魂甫定之時,藉由在日本臺灣學會年會回應你的基調演講之際,總結了我這段奧林帕斯山頂的精神歷程,並向你提出最尖銳的質問:
「山頂上的比較史視野將臺灣從中國史解放出來,然而又把它關進另一個地緣政治的囚籠之中。Quo Vadis Formosa? 」
對於這個問題,其實連上帝也只能保持沈默吧。Dear Ben,然而對於我這無理而無禮的質問,對於我因天生感傷、容易陷溺的性格而日益加深的受困與悲觀意識,你卻慷慨地、溫暖地,而且智慧地做了回覆。你的回應是兩重的。一方面,你依然站在奧林帕斯山頂,提醒我不要就急著下山,要站久一點,要冷靜觀察,就會看到一個毫無疑問的歷史趨勢,也就是古老帝國的裂解。現實主義者眼中不可動搖的結構,從長期歷史的角度看,其實是只是持續移動、正在裂解的冰河,被禁錮的靈魂,終究會一一突圍而出。所以,奧林帕斯山頂的視野是辯證的:解放、受困、然後再解放。所以〈賤民宣言〉的經驗論證是站不住腳的,你說。
另一方面,你又給了我一個個人的,存在主義式的回應:現實主義無法改變現實,只有政治的道德主義才能改變現實。然後你還不忘提醒我Gramsci 的那句話:optimism of the will!
老實說,我不確定這回我有沒有被你說服—大概只有一半吧。古老帝國內部或許充滿矛盾,危機重重,然而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浪潮卻創造了外部擴張與帝國重生的契機;老式的、粗暴的領土兼併固然已經失去正當性,但是Ronald Robinson和John Gallagher所描述的那種以自由貿易和經濟力進行支配的「非正式帝國」(informal empire)卻又再度成為新帝國主義的擴張典範。當然,邊陲的抵抗動能依然存在,而且日益增強。如同Dani Rodrik所說,資本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結構性矛盾為新一波邊陲民族主義創造了動員條件。所以,做為抵抗的民族主義會繼續存在,但帝國也不會輕易消亡—而且,帝國的數目正在悄悄增加,我覺得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帝國主義年代了。
Ben,這是我最近的一點讀書心得。我知道你從來不是要給我簡單的,有如天啟般的答案,而是要逼我思考,找出自己的答案,這就是我最近的想法。還是很悲觀,但卻不再那麼悲愴了。奧林帕斯山頂上冷冽的風,讓我發熱的頭腦稍稍降溫,我的心情也沈靜下來了。我不知道自己還剩下多少意志的樂觀主義,但我的悲觀,變得比較理性了。
Ben,其實我的受困感在這些年當中已經不知不覺地發展,或者演化成一種多重受困的感受與認知,變得有點複雜了。如果仔細整理一下,大概可以區分為三個層次吧。我所感受的第一重受困,是歷史的,結構的:臺灣所處的「帝國夾縫」的地緣政治位置,使它的行動自主性受到很大的限制,而資本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則加深或惡化這個地緣政治的困境。這是我最「古典」的受困感。第二重的受困感則是知識的,個人的:面對如此複雜的歷史情境,我深深感到自己知識能力的嚴重不足—不要說提出「突圍」或「出路」的行動方案,我連正確分析當代歷史情境的能力都付之闕如。照理說,這應該是要結合幾個世代,不同學科的知識人共同思考的課題,然而新自由主義的另一項輝煌戰果是,它使學術生產徹底功利化與瑣碎化,因而瓦解了學院知識分子的歷史意識與宏觀思考的格局、能力,甚至興趣。這個情況在臺灣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界尤為嚴重。你知道我在知識上的專業訓練主要在比較政治、歷史分析與思想史,這些知識協助我理解了一點十九、二十世紀的民族國家與帝國型態,但卻無力透視這個新的資本與帝國的年代。Dear Ben,我意識到,或者感知道問題之所在,但卻無力分析或解釋它,也得不到多少協助,只能在黑暗之中,孤立無援,笨拙地、凌亂地到處越界,搜尋答案。或許我可以把這一層的受困,稱為「困而知之」吧,儘管我離「知」還如此遙遠。
我的第三重受困感也和知識有關,但比較不是知識本身,而涉及知識的政治—一種所謂「進步意識型態結構」的受困,而支撐這個結構的,則是中國革命創造的歷史意識與世界觀。Dear Ben,你當然知道我有很強的臺灣認同,也主張臺灣應該獨立自主,不受任何強權宰制。這些年來,我儘管能力微薄,也一直努力嘗試發展一個符合普世進步價值立場的臺灣主體論述—一種接近於薩伊德所說的「自我批判的民族主義」,或者法農所說的「具有社會內容與國際精神的民族意識」的想法。我不認為這種後殖民的進步民族主義論述有多特別,但它至少有理論根據,邏輯上說得通,並且也頗能呼應臺灣社會二十年來本土化、民主深化與公民社會成熟的發展趨勢。不過,一旦這樣的想法被放到某種特定的國際脈絡中—主要是國際的進步左翼體制的觀點中,似乎就會突然出問題,被打成「右派」論述,因為這個體制的主流見解似乎認為,不管你社會政策多左,族群政策多進步,性別政策多多元,反正只要主張臺灣獨立,就是右派,就是反動。在這個僵硬的觀點之中,「進步臺獨」、「左翼臺獨」的選項是一種oxymoron,不可能存在。這些年來,我在東亞、北美,以及歐洲,接觸過不少抱持這種想法的各國進步左翼知識人,也讀過不少這樣的作品,這些經驗,讓我意識到除了地緣政治和資本主義之外,臺灣同時也被一個可以稱為「進步意識型態結構」的圍堵。
My dear Ben,你應該很清楚其實我根本不在意是否被歸類為「左」或者「進步」之類的。就如Steven Lukes那句著名的雙關語:「what is left?」(什麼是左派?/還剩下什麼?)所提示的,在我們這個時代,連「左」這個名詞自身都需要進行廣泛、深刻的檢討、釐清與重構了,貼標籤的意義實在不大。我比較遺憾的,是這個「進步左翼」(加括弧的)偏見結構一筆抹煞了臺灣人民百年來追求掌握自身命運,追求自由、平等與多元價值的高貴的歷史努力,並且否定了臺灣人民與世界連結,將這段追求與實現普世進步價值的珍貴經驗貢獻給這個世界的可能性。這個偏見不僅抹煞了應為人類共有的珍貴進步遺產,同時也妨礙了一個可能貢獻於人類共同未來的進步連結的形成。用鄂蘭的話來說,這個偏見不公平地剝奪了臺灣人屬於、參與這個共同世界的權利。
最初,我以為這主要是一個知識問題—只要好好講清楚,誤解就會自然冰釋。然而在經驗了很多次溝通挫折之後,我開始覺得這其實是政治問題—中國的強大實力壓倒了一切關於臺灣正當性的論述與實踐。但是這幾年的反省,讓我體認到權力政治背後,還有一個強大的,根深蒂固的意識型態—用你的話說,impervious to argument2的意識型態存在,扭曲或掩蔽現實,並且干擾人們的溝通與連結。Ben,然後我讀了霍布斯邦的那本精采的自傳《趣味橫生的時光》(Interesting Times),對這個問題有了更深的理解。在自傳中,他說明自己在一九五六年赫魯雪夫聯共二十大演講公開史達林罪狀後,雖然轉向了義共的歐共主義路線,但仍然保有英國共產黨籍的原因:他少年時代在維也納所受到的社會主義啟蒙,是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所激發的偉大夢想的餘波,這份初衷之情使他即使喪失了共產主義信念,依然終生沒有放棄共產黨員身分。於是我恍然大悟,理解到歷史上的偉大革命會如何形塑一整個,甚至好幾個世代知識分子的道德情感、政治想像與觀看世界的方式,並且形成一個穩定結構,制約後來者的道路與選擇,不管這個結構如何日益偏離歷史發展的軌跡。如果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形塑了戰中與戰後初期世代歐洲知識分子的世界觀,一九四九年的中國革命則深刻影響了整個冷戰,乃至後冷戰時期國際進步左翼知識人對中國與世界的理解方式。時至今日,關於東北亞,關於臺灣海峽,中國革命所創造的歷史意識依然對這些知識人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革命早已被背叛,然而革命卻尚未過去。
(Dear Ben,你屬於歐洲新左翼的世代,然而你生命中那場偉大的革命,不是一九六八,而是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蘇卡諾的印尼獨立革命吧。)
Dear Ben,以上就是我的受困精神史。(你大概會想說,別活得那麼辛苦吧……)對我而言,每一個層次的受困都是一道險峻的高牆,然而最終極的障礙,不是地緣政治與資本主義,因為帝國間的矛盾是我們求生的縫隙,資本會滋生它的對立面,不是知識的不足,因為我們可以越界求索、假借與創造,甚至隨機應變地improvise3,也不是革命的幽靈,因為我們已在用自己的革命來驅魔;最終極的障礙,Ben,是歷史本身—或者應該說,是時間本身,因為如同艾略特所說,「唯有經過時間始能克服時間」,而我們身在歷史之中,時間之中,我們經驗時間點滴的過去,但是我們永遠來不及克服時間。DearBen,巨大的冰河正在緩慢崩解,然而在解放之日到來以前,我們需要仰賴意志,仰賴信念,行走一段漫長的艱辛,因為我們已經沒有彌賽亞,然而沒有了彌賽亞,信念的根據是什麼呢?
我猜想,dear Ben,這就是為什麼這麼多年來你在信裡寫了那麼多次和「勇氣」有關的字眼給我的原因吧:bravery、fortitude and courage,還有這句讓我落淚的話:
As the French comrades say, “de courage, mon vieux, et encore de courage.”
你明白,正如同你的好朋友和無政府主義同志,我的另一位知識英雄James Scott 也明白,對弱者而言一切都是困難的,抵抗不是一種美學姿勢,而是生存的必要,你明白,正如同James Scott 也明白,弱者抵抗是一種歷史的伏流,在這次和下一次的爆發之間,是漫長的羞辱、征服、忍耐、蓄勢與等待,而這一切都歸結到存在的問題。所以你才會送給我們臺灣人那句美麗的Samuel Beckett吧:
I cannot go on; I will go on.
然而你知道嗎?在去年雨傘革命爆發前夜,我把你這句話鄭重地轉送給勇敢的香港人民了呢。在那場傾城之戰,有一群熱情的年輕人借用了你的《想像的共同體》,為難產中的香港政治主體命名,召喚它的現身。你看,my dear Ben,偉大的天朝帝國邊陲,福爾摩沙西南海岸的彼方,如今又降生了一個imagined community了—不是複製,而是平行的原創!所以我們縱使依然孤獨,卻已經不再孤立無援。WE cannot go on, and yet WE will go on. Ben,我們這個時代的革命已經沒有先知,沒有神祇,沒有英雄,更沒有黨中央,we arebut a bunch of losers holding out hands for each other,然而我們有笑容,懂得嘲諷與自嘲—我們幾乎和Ben Anderson一樣愛開有水準的玩笑。而且,而且我們讀過The Imagined Communities,他X的沒有刪節過的,最美麗的完整版!My dearest Ben,請容我敬你一杯熱清酒,並且誠摯地邀請你加入我們這場克服時間,裂解冰河的,偉大的革命。
如果已經沒有彌賽亞,So be it!
“Before revolution this is happiness,” says Adrienne Rich, but revolution IS happiness.
跟你一開講,就停不下來,而且必定失控,從散文寫成詩,從嚴肅變成瘋狂,從政治經濟學變成無政府主義。這當然是我們向來聊天的模式,因為我們可以從臺北開車一路聊到東北角,再經過九份淡水聊回臺北,或者從臺南成大一路聊到高雄八五大樓,和陳菊市長那面美麗的大看板合照後再搭高鐵一路聊回臺大旁的福華會館。反正你的好奇心永無止境,看到什麼就問,我也太過嚴肅,滿腹沒完沒了的「公共知識分子」問題要請教大師。不過,也是因為我實在很久很久沒跟你說話,所以變得太想念你了吧。我知道你一定不會生我的氣,但我還是決定就此擱筆。對了,最後跟你說一件事:這幾天整理以前的舊照片,找到一張你以前在十八王公橋畔那尊黑狗銅雕前拍的照片,看起來很神氣,很像你信中說的那群lumpenproletariat6—那群信仰「dog temple」的「乞丐、娼妓、小偷和流氓」—的老大。我準備把照片放大裱起來,掛在我的研究室牆上,沾你一點福氣。我會加洗一張給你,另外也會把我的這張一起寄過去,請你記得要先簽了名再寄回來給我啊。這回就寄到南港的Cynical Academy 吧,他們都認得我這個悲傷的犬儒。
寫著寫著,竟然從二○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的深夜寫到了二○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凌晨一點了,算一算時間,我已經整整認識你十六年六個月又八天了呢,真是光陰似箭啊。親愛的Ben,另一個歷史變局前夜的臺灣正在寒冬裡沸騰,然而此刻你已經在邊境那個「收養你的村落」裡舒舒服服地準備就寢了吧。你就好好躲在這裡休息一陣子,喘口氣,等明年春天潑水節的時候我再到曼谷找你,到時我再帶一張(有版權的)《賽德克.巴萊》給你,不過你可別看了又說要學賽德克語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