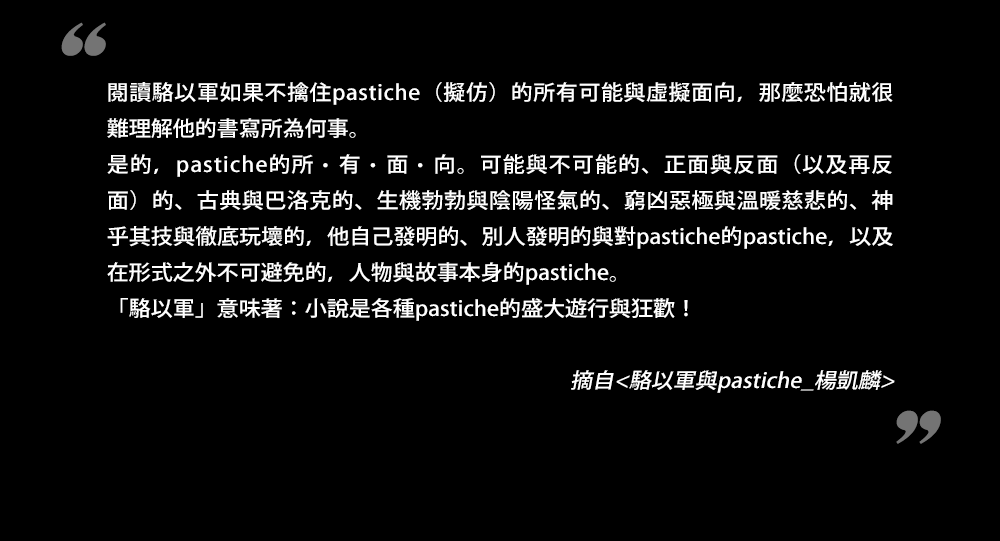絕對的存在者
這本《女兒》,我讀了幾次,每次都隨著那樣綿密濃重卻又繁花似錦的思想發展,踏上了不同道路,每次經過的風景皆不相同,出口也令我驚奇。
站在第一個岔路徬徨思考的,是〈藍天使〉中,那個德國一九三○年代黑白電影《藍天使》的片段:醜陋的、讓人感覺悲哀的(老)男人,與讓男人無來由迷戀不已的小女人,在末日老朽與青春之間的對立又吸引的關係。這是個二元論世界,我做為觀看的男人,「女兒」不管再如何不具吸引力,對於如此平淡的腐朽之我,還是完美的不可思議的女子;或者並不是任何特定的女人,而是做為女性的存在,本身就不能是我的世界的一種特質。在本書開始的幾章裡,都能看到這樣的意象,不管如何醜陋平凡,都是存在於如同「電影場景裡的超現實的美」,那不是這個敘事者置身其中的世界之一環。
我不能不想起柯尼斯堡的哲學家康德對世界的思考。在那個人類才告別僅以宗教角度探索世界的時刻不久的時代,康德切開了現象與物自身的範疇,為人類的認識能力劃下界限,告訴我們,有些絕對性的存在物,既決定了這個世界卻又不是這個世界可以企及的,對於那些東西(「物自身」),超出了一切自然法則或因果律,人類不可知,無法認識,只能想像。「女兒」也是這樣的超出「我」能理解的、擁有「女兒性」的存在――不管是《藍天使》中那個肥胖的德國女星、平凡的鄰家女路邊停車管理員、向病人求索便利超商集點貼紙的護士、像搪瓷娃娃般的「如清晨玫瑰般鮮豔的」微若表妹……。駱以軍甚至稱之為「少女神」。這些絕美的神般的存在,超乎了我們的知識能力,不在我們的經驗中,但我們只能確知有這樣的存在。
直到「女兒」們被這個世界弄壞為止。
這是絕美的存在者vs世界的二元對立之不可避宿命,「女兒」們終究要被弄壞,終究要被收入這個混雜各種惡意的世界中。所有女兒最後都必須進入如《藍天使》裡面那位男性教授的老朽狀態,這是這個世界正常化的做法。那些柔軟鮮美純粹的存在――不能不再想起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中接近偏執地重複使用那些「先於經驗的」(a priori)、「純粹的」(rein)、「未參雜任何東西的」(unvermischt)等形容詞――最後都必須被介入、被置放在認識範疇中、被參雜進一些什麼東西、被「父之惡」的暴力轉化。
女兒們的悲劇早已被寫好,如康德《判斷力批判》的美學論,自然界的崇高壯美必然需要人類的理解才能成立,超越我們的偉大與無限必然需要我們這些有限存在者才能被建立,女兒神還是必得從那個次元來到這個肉欲朽敗的世界裡,如同〈阿達〉一章裡原來美得不可方物的臺南家專的表姐,大一讀了半學期便被一個極為平庸的痞子把走了,三十多歲時成為一個「肥胖巨大、海獅般的婦人」……。「幾乎可以說她這個『絕美女人』的一生,就在二十多歲做出決定的那時,便像保險絲那樣燒斷了。」「被偷走的人生啊。」
妳被這世界弄壞了,駱以軍寫著。或者該說,妳終究成為了這世界的一部分,最終被摒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