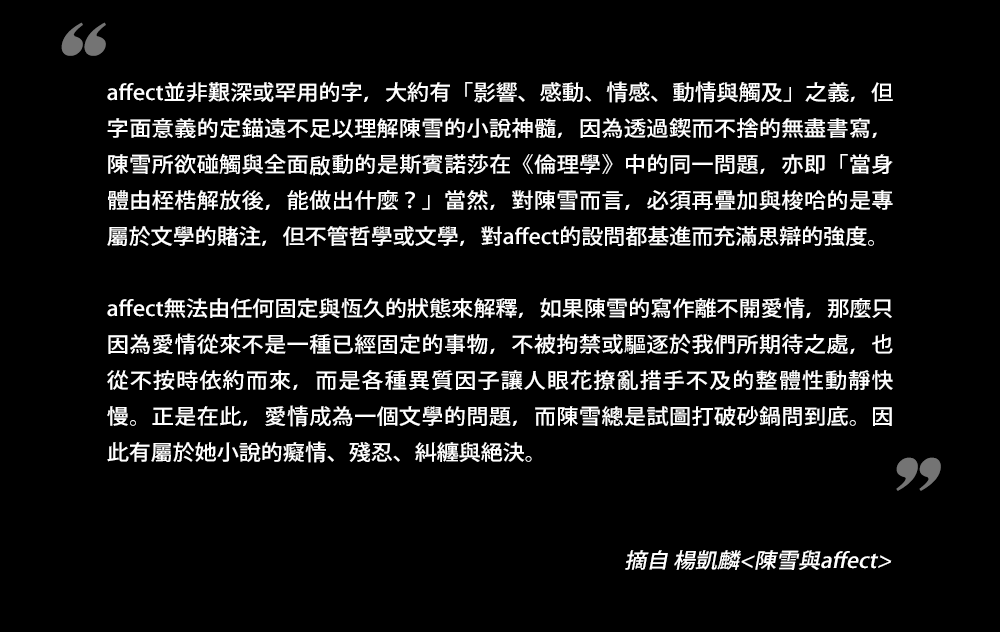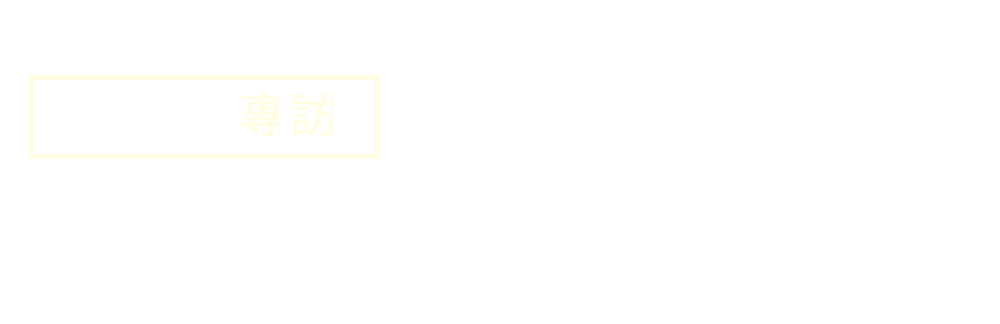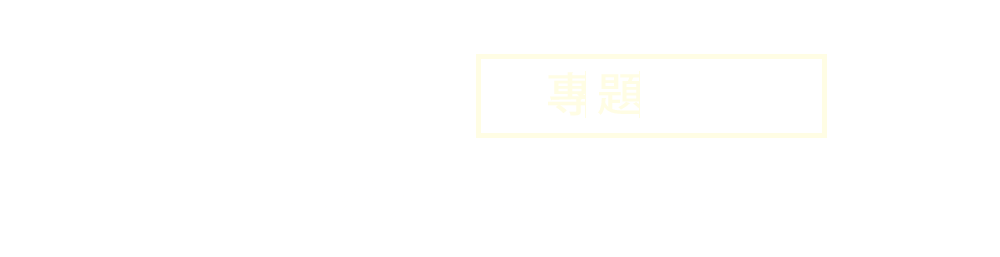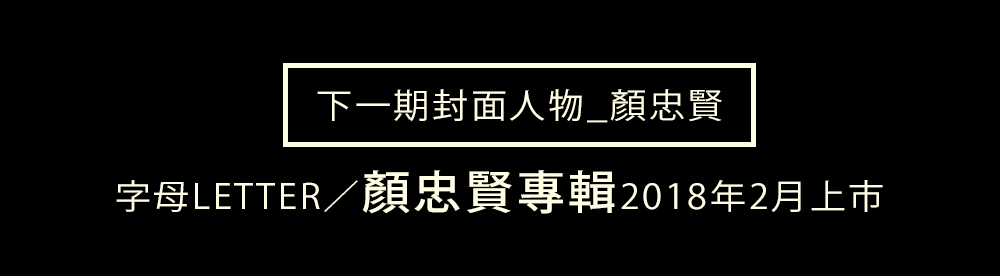日期:2017.10.27 14:30~18:00
地點:永和 小小書房
現場記錄:李映昕
莊瑞琳
對於作家身分的認同,在妳心中是怎麼慢慢形成的?妳的成長環境是非常普通,甚至不好的,作家這個行業又跟錢背道而馳。妳本來是一個「生意子」,而且妳很有天分,很會賣東西,那是怎麼變成作家陳雪的?是什麼過程,讓妳堅定要成為一個作家?而且要以寫作維生?
陳 雪
我二十五歲出第一本書,二十六歲出第二本,到二十九歲時已經出了四本小說,但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是作家。因為我一邊賣衣服、一邊送貨,一邊還債,家人也很反對我寫作,寫作變成我個人的祕密。我的生活裡面,因為常常要去送貨,如果提到我是作家,很怪,而且我覺得我不是作家,我只是一個小販,一個業務員。我年輕時也很叛逆,覺得說自己是作家好像很做作。我當然熱愛創作,寫作是我終身要做的事,但我覺得那比較像是我自己的祕密。那時候我也很少跟外界接觸,我想保護我的寫作,因為我寫的東西很禁忌,也很大膽,我不想要別人來干擾我,來提問為什麼要這樣寫。我骨子裡很怪,有一部分是個好孩子,我不想要好孩子這個身分影響我的創作,我就特別低調不讓人家知道。
我看問題裡有提到舞鶴,舞鶴對我有蠻大的影響。我記得第一次看到他,是去評東海文學獎,也是我第一次評文學獎,大概就是二十七、二十八歲,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駱以軍。我本來覺得自己就是一個擺地攤的,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人打電話邀請我去評文學獎,當時我沒有得過文學獎,至今也沒有。我跟舞鶴同場,那時候很幼稚,也不太會評審。最好笑的是,我穿一件很怪的衣服,舞鶴還問我為什麼穿這樣,反正就是很俗豔、露肩,想刻意展現性感。我記得他問我在幹嘛,我就說我在賣手錶,他說,妳幹嘛還賣手錶,妳應該寫小說。我說,可以只有寫小說嗎?他說可以啊,妳應該什麼都不要做,就是寫小說。對我來說,這就像是一個咒語,有一個人跟妳說,妳可以這樣做。我心裡還想說,難道他很肯定我嗎,其實他不認識我,當然我就送了他一本《惡女書》。我們兩個有點小小的緣分,後來我去訪問過他。那時他又再次跟我說,妳不應該再做那些工作了,妳應該寫小說。第一次讓我想到,我可以做一個小說家,可能就是舞鶴吧。而且他真的就是沒在做什麼,就是寫小說。我看到他的時候,我還蠻震驚的,他住在一個什麼都沒有的房子,我永遠都不會忘記,就是一棟透天厝,所有家具都是房東給的。我認識他本人之前,就有人跟我說,他是一個有精神病的原住民作家。我就很興奮,馬上去找了《悲傷》來看。我見到他的時候,是帶著一種很景仰的心情,因為我非常喜歡他那本《悲傷》。採訪他的時候本來只是在樓下,我就說可不可以參觀你的書房,那其實是一個房間,什麼都沒有,只有兩三本很奇怪的書,一張學生書桌,讓人印象很深的是,那房間非常乾淨,地上卻有非常多頭髮,桌上有稿子。說真的,他對我影響很大,妳可以什麼都沒有,滿地的頭髮就可以成為作家。人家可能是滿屋子藏書,但他沒有。我還問他,你都吃什麼,他就給我看電鍋,裡面就是紅豆薏仁飯。作家就是這樣,作品、米跟一張桌子就好。但他跟我說了蠻多竅門,他說他會鍛鍊身體,做伏地挺身之類。
採訪他已經是一九九九年的事情,我還沒成為專業作家。但他已經在我心裡種下,專業作家就是這樣。但我那時候要還家裡的債,還有很多心裡的負擔。精神科醫師一直鼓勵我,我那時憂鬱症很重,但他覺得我沒有憂鬱症,是因為環境造成的,他說我想要寫作但一直沒辦法,當然會憂鬱。滿地頭髮的舞鶴也一直鼓勵我要專業寫作,這兩個驅力一直讓我覺得要排除一切,去某個地方寫小說。到二○○二年,我終於到臺北了,沒有工作,開始寫小說。實際上我還不覺得自己是作家,只是躲在一個祕密的地方偷偷寫東西。寫《陳春天》的時候,我還有回去打工,每個月會去送貨好幾天,有一次我們送貨到花蓮,因為《陳春天》中國時報有採訪我,我以前不喜歡讓人家登照片,但那次照片放很大。我去送貨時,文具店老闆娘叫我簽貨單,她一直看著我,說陳小姐我看過妳,在報紙上看過妳,妳是不是作家。我就說,妳覺得我像作家嗎?她說像又不像,但那個(照片)真的很像妳。我說我就大眾臉啊,簽完我就走了。直到那一刻我還是沒辦法說我是作家,但我心裡知道,這可能是將來要去面對的問題。我真的很自然覺得自己是作家,是到寫《附魔者》的時候,那時都已經認識駱以軍他們了。我打從心裡覺得自己是作家,已經職業寫作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