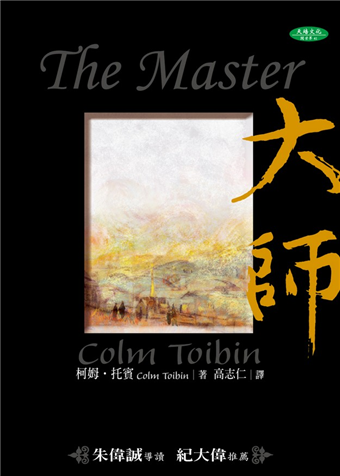得獎紀錄:
◆2006年國際IMPAC都柏林文學獎。◆2005年法國最佳翻譯小說獎。◆2004年英國布克獎最後決審名單。◆2004年《紐約時報》年度十大最佳小說。◆2004年《洛杉磯時報》年度最佳小說。◆美國最有名的同志刊物advocate大力叫好。
名人推薦:
◆名作家紀大偉專文推薦。
得獎紀錄:◆2006年國際IMPAC都柏林文學獎。◆2005年法國最佳翻譯小說獎。◆2004年英國布克獎最後決審名單。◆2004年《紐約時報》年度十大最佳小說。◆2004年《洛杉磯時報》年度最佳小說。◆美國最有名的同志刊物advocate大力叫好。名人推薦:◆名作家紀大偉專文推薦。
章節試閱
第一章
一八九五年一月
他曾經在夜裡夢見去世的人,有的臉孔很熟悉,有的已經有點模糊,無由來去,即起即滅。他醒來,以為再一個多小時就要天亮;過了幾個小時,沒聲音也沒動靜。他摸摸脖子上僵硬的肌肉,觸感十分堅實,卻也不痛。他轉頭時,聽得到肌肉吱吱叫。我就像一扇老舊的門,他心想。
他知道自己必須再睡點覺,不可能幾個小時一直醒著。他想睡覺,想念那美好的黑暗境域,有點暗又不會太暗的歇息所,沒有魂魅糾纏,沒有生人侵擾,沒有事情此起彼落悠悠忽忽的。
他又醒來,頗為心驚,不清楚自己身在何方。他經常這樣醒來,心裡七上八下,夢已忘了大半,恨不得馬上破曉。有時他打個盹,便沐浴在貝洛嘉多早春迷濛的柔光中,遠方盡付茫霧,陽光照在臉上多快樂,坐在椅子上,靠近老房子的牆,有紫藤、早春玫瑰、茉莉的氣味。他希望醒來後也能像這夢境一般,讓那閑適、顏色、光影的調調縈迴於世事之間,直到夜晚再臨。
但這個夢不同。那地方很暗,愈來愈暗,是座城市,義大利的一座古城,像歐維托或希耶那,但說不準是哪裡,那夢中的城市街道狹窄,他匆匆忙忙的,不確定是自己一個人,或是和哪個人在一起。他腳步急促,也有學生正緩緩上坡,經過亮了燈的商店、咖啡館、餐廳,他很想趕上他們,想辦法超越他們,無論他多麼努力回憶,還是不確定他是不是有個伴?可能有,也可能只是某個人走在他後面。他記不清那一團似散若聚的陰影,但隱隱約約就是有個人或聲音在他身邊,比他自己還清楚為什麼如此匆忙,不停在他耳邊叨唸著,哄著他走快點,幫忙不讓那些學生擋了路。
為什麼夢見這些?他記得只要一到進入廣場長而微亮的通道,他就想離開繁忙的大街,但仍被催促著繼續走下去。是不是那鬼魅般的同伴在催促他?他終於慢慢走進開闊的義大利廣場,有塔樓和城堡似的屋頂,天空顏色是渲染般的深藍色,平勻悠長。他站在那裡觀賞,像是比例與質地皆有可觀的畫作。這一次,他看見中心處有人,背對他,站成一個圓圈,看不到任何一張臉,他想起這一幕就不禁打哆嗦。他準備走上前去,這時那些背對他的人轉身。其中一位是晚年的母親,他最後看到的母親。旁邊還有一位是凱特姨媽。她們倆人都已去世好幾年了,現在正笑著慢慢朝他走來。她們的臉像是繪畫效果一樣明亮。他夢到的字是「懇求」,他對這個字的印象和這一景象一樣清晰。他們在請求他或旁人,要求著,渴求著,伸出手哀求著;她們走向他時,他一身冷汗醒來,他希望她們能說些話,希望他能為此生最愛的兩個人提供些許慰藉。夢醒之後,他只感到心力交瘁的噬心與悲傷,而他既然不能再睡覺,只好開始寫作,好痲痺自己,讓自己分心,不去想那兩位已離他遠去的女人。
他埋著臉好一會,記起了他猝醒前那一幕。他無法忘掉,記憶在這白日裡如此鮮明,他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在那廣場上他和母親目光交接,她眼裡盡是痛楚,隨時張口大叫。她渴求的東西拿不到、構不著,而他什麼忙也幫不上。
新年前這段日子,他回絕了所有邀請。他寫信給渥佘里夫人,說自己坐一整天彩排,陪伴他的是製作戲服的幾個胖女人。他緊張不安,心裡很不平靜,但有時也為舞台上的劇情所吸引,好像之前從沒看過似的,心中甚是感動。他的劇作上演之日已經不遠,他請求渥佘里夫人伉儷於開演之夜為他祈禱。
晚上,他什麼事也不能做,老是睡一會醒一會的。只有僕人能見到他,而僕人也知道別和他說話,別驚擾他,除非絕對必要。
他的劇作「蓋東維爾」(Guy Domville)描寫富有的天主教家庭繼承人,必須選擇是否繼承家庭事業,或者投身修道院。這齣戲將於一月五日首演。首演之夜邀請函已全數送出,他已收到許多回函接受邀請和表示謝意。製作人與男主角阿歷山大擁有一票戲迷,戲裡十八世紀的服裝美不勝收。然而,雖然他近來很喜歡和演員在一起,五光十色的戲劇呈現逐日臻於完善,也讓他欣喜不已,但他說過自己並不是劇場人。他坐在桌前嘆了口氣。他多希望這是平常的一天,可以把昨天寫的字句讀過一遍,花一個早上的時間慢慢修改,下午再好好開始做一些日常工作。不過他知道自己的心情變化很快,像是房裡的光線一下子就會暗下來,這時他又會止不住雀躍於自己的劇場生活,看到空白的稿紙就生厭。人到中年,變得顛顛倒倒的,他心想。
他的訪客準時於十一點到達。她寫來的信頗為堅持,他無法拒絕見她。她說她即將離開巴黎,不再回來,這是她最後一次來倫敦。那是種一了百了的奇怪語氣,和她平常的個性大不相同,他立刻警覺到她情況不妙。他很多年沒見過她了,但這些年來,他收過幾封她寫來的信,也從別人那裡聽到她的消息。但那天早上,他似乎沒有完全從夢中甦醒,而且滿腦子都是他的劇作,於是她就像他日記裡的一個名字,在喚起的記憶中輪廓雖清晰,但內容卻模糊。
她進房間時,一張老臉親切笑著,大骨架的體格走來緩慢而謹慎;她的招呼如此欣然、大方、和藹,她的聲音如此美麗、輕柔,如款款低語,他不知不覺就把他操心的戲劇擱在一邊,也不覺得不去劇院是浪費時間了。他已經忘掉他有多喜歡她,也沒想到如此輕易就回到了二十歲在巴黎流連於法俄作家之間的日子。
後來,他對沒沒無聞的人和對有名的人同樣關心,那些名聲不顯的人,失敗的人,不打算出人頭地的人。他的訪客嫁給歐里斯基王爵。這位自我放逐的王爵素來拘謹淡漠,俄羅斯的命運比夜間歡宴與名流交際讓他更感興趣。王爵夫人也是俄羅斯人,但大半輩子都在法國渡過。環繞著她和丈夫總是蜚短流長不歇。這是時代和環境使然,他想。他認識的每一個人似乎總還有另一個人生,那半秘密、半公開的生命史為人所知,卻不足為人所道。那些年裡,你在每張臉上搜尋無意間透露了什麼的表情,細心聽聞蛛絲馬跡。紐約和波士頓可不是這個樣子,而在倫敦,當他終於移居當地時,除非你大聲公告周知,那裡的人不會認為你藏有什麼秘密的。
他還記得初識巴黎甚感驚嚇,那習慣造假的文化,男男女女給他的印象,小說家旁觀這些人,對有關自己至為重要的事情表現出無所謂的態度。
他從不喜歡什麼內幕,卻喜歡知道些秘密,因為不知道是會完全狀況外的。他已學會不透露任何消息,或有耳聞也不當場點破,只當是彼此說笑。巴黎文藝圈各色男女玩著知己知彼、爾虞我詐的遊戲。他從他們身上學到太多。
他請王爵夫人入座,並添加靠墊,另外又找來座椅,可以算是躺椅了,好讓她舒服些。
「我這年紀,」她笑說,「哪有什麼舒服的。」
他停下走動的腳步,轉身看她。他知道,當他用那平和的灰色眼睛定定看著某人時,那人也會平和起來,接下來的談話會比較認真,閒聊扯淡的時間已經過去,至少他自己是這麼想的。
「我得回去俄羅斯,」她以緩慢清晰的法語說道。「不去不行。我說回去,好像我之前住過那裡似的,沒錯,我是住過那裡,但對我而言是不算數的。我不想念俄羅斯,但他一定要我待在那裡,不要再回法國。」
她說話時一如平常面帶微笑,此刻卻夾雜痛楚和幾許茫然。她和她的過去一起走進這房間,而如今他的父母和妹妹既已相繼離世,任何讓他想起時光俱往矣的提示,都是駭人的沉鬱。時間無情,年輕時他沒想過失去的痛苦,如今唯有工作和睡眠可以舒緩。
她聲音輕柔,儀態隨和,多年來她並沒有改變。她的丈夫據說對她不好。他有地產上的問題。她談起自己即將流放的某個偏遠的土地。
一月的光線如絲綢般在房裡流動。他坐著聽她說話。他知道歐里斯基王爵首次婚姻裡有個兒子留在俄羅斯,自己則不甘願去到法國。關於他,總有些政治傳言,說他將在未來的俄羅斯佔一席之地,他正等待飛黃騰達。
「我的丈夫說,是我們回到故鄉俄羅斯的時候了。他成了改革派,說俄羅斯不改革會垮。我告訴他,俄羅斯早垮了,我沒說的是,他在負債之前對改革似乎沒什麼興趣。他前妻的家人把小孩帶大,不想和他往來。」
「妳住哪裡?」他問她。
「住一間搖搖欲墜的宅邸,鄉野小農會頂著鼻子貼在我家玻璃窗上,假設窗子上還有玻璃的話。我就住那裡。」
「巴黎呢?」
「什麼都不能留,包括房子、僕人、朋友,以及我的人生。我不凍死也會無聊死,大概就是這兩種下場。」
「怎麼會這樣?」他輕聲問道。
「他說我把他的錢揮霍光了。我賣了房子,燒了幾天信,邊燒邊哭,也丟了幾天衣服。現在我正向每個人道別。我明天離開倫敦,在威尼斯待一個月,接著前往俄羅斯。他說其他人也會回去,但他們去的是聖彼得堡。那不是他要我去的地方。」
她話說得很投入,但他看著她,彷彿她是在他戲裡演出且頗為自得的演員。有時候,她的語氣聽來像在講別人有趣的八卦。
「我認識的人活著的我都拜訪過了,已經去世的也讀遍了他們的信。有些人我兩樣事都做了。我燒了保羅.周科斯基的信之後和他碰面。我沒想到會見到他。他老多了,這點我也沒想到。」
她和他短暫目光交接,房裡彷彿夏日晴光一閃。保羅.周科斯基快五十歲了,他心裡算著。他們已經多年不見,從來沒有人像這樣提起他的名字。
亨利專心應答、問問題、改變話題。或許信裡提到了什麼,說溜了什麼,談到某些對話或聚會什麼的。但他不這麼想。或許他的客人出於懷舊之情,想讓他知道他在當年所代表的風格,還有他自己營造的自我。他想表現得真心、細膩、守禮,卻逃不過女人如她的眼睛,只要她看了他的嘴形和眼神,一切立刻無所遁形。大家心照不宣,像現在她也沒說什麼,那只是個名字,繚繞他耳際的名字。那名字曾是他的全部。
「妳應該會回來吧?」
「他不給我承諾。我不會回來,會一直待在俄羅斯。」
像是一句台詞,他突然看見她在舞台上,走著悠閒的台步,說話像是不經意脫口而出,然後反將一軍,正中要害。他聽她說了這些話,開始理出頭緒。她想必是犯下大錯,只得讓自己任他擺佈。她在社交圈子裡一定有些議論。有人知道內情,不知道的也不妨猜猜,就像現在她說給他猜一樣。
他這麼想著,一邊觀察王爵夫人,細細思量她說的話,考慮如何為己所用。她一離開他就得記下來。他不想再聽其他細節,但她不停歇,顯然十分恐慌,他又感到同情。
「嗯,其他回去的人傳來好消息。聖彼得堡是新生活的開始,但我說過那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我曾在宴會上碰到多德,他對我說的話還真蠢,也許他是想安慰我。他說我擁有回憶。但我要回憶做什麼呢?我告訴他,我對回憶一點興趣也沒有。我喜歡今天和明天,狀況好的話也喜歡後天。去年已經過去了,誰還想著去年?」
「多德吧。」
「沒錯,他想太多了。」
她起身告辭,他陪她到前門。他看見有車子在等她,心裡想不知道是誰付的錢。
「保羅呢?你想不想要那幾封信?」
亨利伸出手,當她沒問過問題似的。他雙唇微啟,欲言又止。他牽住她的手,半晌,她淚眼婆娑上了車。
他住在德維爾園區這裡快十年了,從沒聽人提起保羅這名字。他的存在已淹沒於每天寫作、回憶、想像的工作當中。即使在夢裡,保羅也好幾年沒出現了。
王爵夫人的故事大概已深植心中,毋須寫下。他不知道如何處理這題材,無論是她在巴黎最後幾天燒那些信,或是處理那些要送人或者帶不走的東西,還是她最後一次文藝聚會,或是她和丈夫懇談,以及她獲知自己命運的那一刻。
他會記得她來訪,但有些別的事情他想馬上寫下來。那是他以前寫過的東西,後來又予以銷毀。說來奇怪,甚至覺得悲傷,他已經寫過、發表過那麼多作品,其中包含許多私密之事,然而他最需要寫下來的東西卻不可能公開或出版,不可能為人所知或理解。
他提起筆開始寫。他大可以使用密碼或速寫,只有他自己看得懂。但他寫得明明白白,字字婉轉柔美。他不知道為什麼要寫這些,何不就付諸回憶。然而,王爵夫人來訪談到流放與回憶,那些一去不復返的東西,他停筆嘆息;她提起那名字,彷彿那名字仍在附近某處活躍似的,這一切形成他運筆的基調。
他寫下他收到保羅的短箴後回去巴黎所發生的事情,那是近二十年前的夏天。他站在那美麗城市的小街上,在暮色中抬頭上望,等待三樓窗戶燈亮。燈開亮時,他努力想看見窗邊保羅.周科斯基的臉,他的黑髮、銳眼、緊繃的隨時會笑開的臉、窄鼻子、寬下巴、蒼白的嘴唇。天色已暗,他知道自己在漆黑的街上沒人看得到,他也知道自己不能走開,既不能打道回府,也進不得保羅房裡。進保羅房?光這麼想就要讓他停止呼吸了。
保羅捎來的訊息很清楚,他會一個人在家。無人出入,窗邊不見保羅的臉。他想,現在這時刻不知道是不是他最真實的人生。他能想到最適切的比喻是一趟平順、充滿希望、安靜的海上旅程,懸盪於兩個國度之間的插曲,站得飄浮,心裡曉得踏出一步就是踏進難以想像未知的世界。他總想再等一下,想看看那張遙隔的臉。他站著不動淋了幾個小時的雨,不時被路過的人推著,那張臉卻不曾在燈光中出現。
他寫下那一晚的經過,然後想像接下來的故事,這部分不會形諸文字,無論可以多麼保密,無論多快可以燒掉或銷毀。接下來的故事純屬虛構,他不可能白紙黑字寫下來。故事裡,保羅看到了他,走下來,他過馬路和保羅會合,兩人一語不發一起上樓,保羅知道,他也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他發現自己的手在顫抖。他從不敢再往下想。他只能想這麼多,然而多想無益。那一晚他在雨中站崗,直到窗內燈滅。他又等了一會碰運氣,但窗暗寂寂。於是他慢慢走回家。他靠了岸,衣服濕透,雨水毀了他的鞋子。
第一章一八九五年一月他曾經在夜裡夢見去世的人,有的臉孔很熟悉,有的已經有點模糊,無由來去,即起即滅。他醒來,以為再一個多小時就要天亮;過了幾個小時,沒聲音也沒動靜。他摸摸脖子上僵硬的肌肉,觸感十分堅實,卻也不痛。他轉頭時,聽得到肌肉吱吱叫。我就像一扇老舊的門,他心想。他知道自己必須再睡點覺,不可能幾個小時一直醒著。他想睡覺,想念那美好的黑暗境域,有點暗又不會太暗的歇息所,沒有魂魅糾纏,沒有生人侵擾,沒有事情此起彼落悠悠忽忽的。他又醒來,頗為心驚,不清楚自己身在何方。他經常這樣醒來,心裡七上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