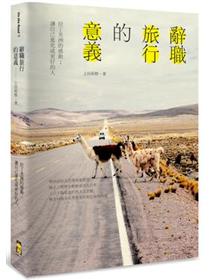中國新詩史上不容遺忘的經典詩作!
歷經八十年,經典重現!
中國現代新詩發展史上,有一顆璀璨明星曾短暫閃耀過文壇天際,那就是《小雅詩刊》(1936-1937)。
《小雅》詩刊是一九三○年代重要的新詩刊物,也是現代派詩歌的重要發表園地;詩刊主編吳奔星,不僅是位詩人,也是詩歌理論的研究者,而詩刊作者均為當時詩壇首屈一指的人物,如:戴望舒、李長之、李金髮、柳無忌、斫冰、錫金、路易士、李白鳳、侯汝華、林丁、常白、陳殘雲、吳興華等,因此《小雅》詩刊的詩歌品質均是名動文壇的篇章。
由於詩刊發行的時期,正是中日局勢緊張的抗戰前夕,在地域與時代性的影響下,《小雅詩刊》也是較早提出「國防詩歌」的口號,將國族情懷融寫入詩文的特殊風格,表明了抗日救亡的愛國主義,最終在戰火波及下,《小雅》只刊印了六期便遭查禁停刊。由於存世量少,又經戰火波及,使得《小雅》詩刊雖然受到重視,但就像詩文界的「神話傳說」,至今仍然難以被充分研究,也未難以獲得明確的歷史定位。
《小雅》歷經短暫卻光榮,漫長而顛沛的刊行時光,至今也已經八十年了!在詩刊故人與文人新血的合作下,得以重刊再版,真實地還原這一段珍貴的歷史,再現當時的璀燦光華,不僅是在詩學上有其指標性意義,於文學、史學、美學等各方面,都是時代意義的延續!
作者簡介:
吳心海
1963年生。現居南京。曾任職於《新華日報》,現為中國江蘇網多語種部主任。從事現代文學史料(偏重新詩)研究,在《萬象》、《現代中文學刊》、《南方都市報》、《文匯報》、《香港文學》、《文訊》等兩岸三地報章雜誌發表百餘篇探討現代文學史料文章,釐清諸多現代文學史上的所謂定論或訛傳。編著《別:紀念詩人學者吳奔星》、《落花生船》(沈聖時散文選)、《從「土改」到「反右」─吳奔星1950年代日記》、《待漏軒文存》(吳奔星散文選)、《斷環》(胡金人作品選)。亦著有《文壇遺蹤尋訪錄》、《故紙求真》等書。
章節試閱
特載:爛縵胡同之戀/吳奔星
北京是一座以胡同著名的古城。胡同最集中的地方,是城南的宣武門和前門之外。在明、清等朝代,北京城南是平民區。胡同之所以著名,與那些胡同裡的會館,為全國各省舉人赴京會試,提供無償住宿有關。特別是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要求光緒皇帝變法維新,曾七次上書。在一八九五年第二次上書時,住在會館的一千三百多名舉人,幾乎一呼百應,都簽了名。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車上書」,一次轟轟烈烈的知識分子企圖參政的運動。科舉制度廢除以後,進入民國,北京的會館仍是各省知識分子赴京工作或求學的免費住宅。凡公教人員與青年學子,不用介紹信,憑一口鄉音,便可在所屬會館各得其所。如魯迅在民國初年曾住宣外的紹興山邑會館;沈從文、丁玲二十年代初到北京,都曾住過湖南的會館;我和我的兩位家兄,在二十至三十年代,為了上大學,先後住過前門外草廠十條胡同的長沙郡館。但是給我印象最深而又最難忘懷的,卻是宣外菜市口附近,爛縵胡同內的湖南會館。
我是一九三二年冬從長沙到北平的,住在長沙郡館。因家兄吳蘭階畢業於北師大英語系,他要我報考該校國文學系。其時適逢魯迅即將在北師大講演,我算是躬逢其盛,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北師大風雨操場見到了魯迅。可惜少不更事,雖讀過他的《吶喊》、《彷徨》,畢竟所知太少,卻也強化了要考上北師大的信心。我複習了半年功課,真的考上了北平師範大學,得以從大雜院的會館喬遷高等學府的宿舍,地址在和平門外的南新華街,門外便是廠甸,琉璃廠的舊書店,烘托著最高學府的文化氛圍。
我之所以經常懷念爛縵胡同裡的湖南會館,那是因為其一,三十年代中後期,我與詩人李章伯借湖南會館為社址,創辦過北平《小雅》詩刊。其二,一九四九年開國大典之際,我又回到北京,任北京市文教局編審。適逢恩師黎劭西(錦熙)先生任北師大校委會主席(即校長),他和齊白石大師應北京市民政局之請,組成「湖南會館財產管理委員會」,我也參與其事。黎師因工作頭緒較多,囑託我以「委員」身分,代行「主委」之職。這就是說,爛縵胡同的湖南會館,我曾利用過它,又曾管理過它。而今進入晚年,難免懷舊,回顧青年時代的所作所為,眷戀之情,自然油然而生。
當年我們創辦北平《小雅》詩刊,正處於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和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學生運動的時代背景之下。以北平為中心的華北五省,正被漢奸和準漢奸組織所控制。國難當頭,各大學青年奮起吶喊,發動了一系列的青年學生示威遊行。但是在憲兵、敵偽、特務、日本「浪人」穿梭橫行的北平,青年學生徒有愛國熱情,是難於持久堅持示威遊行的。當時上海文藝界正開展兩個口號之爭,北平文藝界只有個別作家簽名響應,尚無統一的集體行動。偌大的華北五省,連一個呼應「國防文學」的口號,宣導國防詩歌的刊物也沒有,與時代氣氛太不協調。不少青年深感精神壓抑,思想彷徨,面對政治黑暗,社會混亂,無所適從。為了反映錯綜複雜的社會現實,我們萌生了創辦詩刊的念頭。縱使不能形成一支「國防詩歌」的隊伍,也想顯示一批絕不渾水摸魚的愛國詩人。但是,當時的北平,敵特橫行,各大學組織的學聯,被分裂為新舊兩派,嚴重對立。要辦一個詩刊,連找一個不受干擾的社址也很困難。幸而有人點化:我們是湖南人,住在和平門外的師大宿舍,離開宣外爛縵胡同的湖南會館,不過幾分鐘的路程,照顧比較方便。於是商請湖南會館的長班(北京看守會館的人叫長班)李子仲,代替《小雅》詩刊收管郵件。這樣一來,詩刊社址問題順利解決。我們對外不寫「湖南會館」,只寫爛縵胡同四十一號,也不公開作為主編的我們的真實位址。這是迫於當時的形勢。
此事雖已過去半個多世紀,詩友李章伯也已於一九九三年四月病逝於臺北,我卻仍然像當年一樣,要感謝老資格的北平《京報》,於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及時編發了長達千餘言的〈小雅詩刊徵稿啟事〉。我們曾表達四點意見:一是縱覽二十年來的新詩運動,較之其它文學部門,並不遜色,尤其是詩的寫作技巧,更有驚人的進展。本刊旨在促使新詩運動更加活躍、繁榮。二是希望從事新詩的朋友,把寫詩看成事業,不可視同「業餘消遣」,更不可借此沽名釣譽,逞一時的「鋒頭熱」。三是希望那些寫了詩苦於無處發表的青年,把詩稿寄來,共圖詩運的推進。四是我們對於任何流派的新詩,一律平等看待,自由競爭。共看他日的詩壇,竟是誰家之天下。啟事發表之後,出乎我們的意料,不過半個月之久,竟承不少前輩和平輩詩人紛紛賜稿。李章伯每天騎自行車去取郵件,都感受滿載而歸的喜悅。
令人感動的是,教過我們「十九世紀英詩選」的師輩詩人吳雨僧(宓)先生,不知我們是他的學生,首先寄來〈懺情詩〉(絕句)二十首和《吳宓詩集》一厚冊。吳宓先生中年喪偶,特感孤寂,經常資助留美女生,似有情意,但最後只收到學生的婚禮請柬。他為此寫了一百多首「懺情詩」,發表於北平《晨報》副刊,為人所記取的警句是「釣得金鼇又脫鉤」,一時傳為佳話。新詩方面先後收到李金髮、柳無忌、戴望舒、施蟄存、路易士(紀弦)、林庚、李長之、陳蘆荻、陳殘雲、李白鳳、甘運衡、吳興華、蔣錫金、陳雨門、韓北屏、羅念生、張天授、黑尼、史衛斯、水天同、梁之盤、常白、李心若、侯汝華等五十多位詩人的來信、來稿。由於他們的熱情支持,《小雅》不僅得以於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如期創刊,而且得以保證每期刊物的品質。只是對不起吳雨僧先生,他的〈懺情詩〉二十首,不是新詩,只好割愛,我們為他的《吳宓詩集》登了一則醒目的廣告。《小雅》在許多著名詩人的支持下,成為古城北平唯一的頗有影響的詩刊,與稍後問世的路易士和韓北屏主編的蘇州《詩志》、戴望舒主編的上海《新詩》,互登廣告,交換稿件。這樣,便豐富了刊物的信息量,保存了一些新詩史料。近幾年來,遠在美國加州的紀弦,回憶當年辦詩刊的情景。還欣然地指出:《新詩》、《詩志》和《小雅》,鼎足而三,對中國新詩的現代化,做出過一定的貢獻;而且強調地說,他始終是中國的現代主義者。的確,我們的現代派新詩,是不擺脫中國詩的悠久傳統的。遺憾的是,《小雅》詩刊剛剛嶄露頭角,因提出「國防詩歌」的口號,遭到憲兵、敵特的威脅。到一九三七年三月,承印《小雅》的印刷廠被查封,不久便是七七事變。我們被迫依依不捨地告別了爛縵胡同。
半個多世紀過去之後,緬懷當年為《小雅》執筆的詩人,有的已先後作古;有的年達耄耋,遠在海外;還有的雖都在國內,卻散居東西南北,天各一方;其它詩人,不是生死未卜,就是下落不明。他們對我們所「利用」的湖南會館,幾乎毫不知情。有的詩友今天偶爾提起《小雅》詩刊,也只曉得它是從北平宣外的爛縵胡同四十一號冒出來的。最最深感遺憾的是,當我們於七七事變後倉皇撤退時,連同《小雅》詩刊的合訂本,詩友們的原稿、信件以及他們贈送的詩集、詩刊,還有我的詩集《暮靄》與《春焰》的手稿,都捆紮於兩個木箱內,寄存在湖南會館長班李子仲處。諄諄叮囑他妥善保存。誰知世事滄桑,人心叵測,我於一九四九年九月回到北京,首先跑到爛縵胡同湖南會館,李子仲還在。他說所有寄存的書物,北平淪陷時都被日本鬼子搶光、燒光了。我聽了有如冷水潑頭,心也涼了。我朝思暮想的那些著名詩人的不可復得的手稿、信件等,竟然全部毀滅了。我雖一向以樂觀處世,卻也沒有過分寬廣的胸懷,能容忍這無可彌補的損失!我飽含淚水,離開湖南會館。走到菜市口,回過頭來,目不轉睛地望著爛縵胡同北口,向我噴吐冰冷的空氣!我的悲憤和遺憾,誰能理解呢?
大概過了半年多,北京市民政局有感於北京會館之多,年久失修,首先成立湖南會館財產管理委員會,作為試點,清理會館財產。我奉旨遷入爛縵胡同湖南會館。長班李子仲,神色倉皇,每天打罵老婆孩子,勸阻無效。不多久,他藉口老家有事,離開他住了二十多年的湖南會館。其後,從街坊獲悉了日寇進入北平的一些真實情況。他們說,日軍進入北平,注意力不在城南的貧民窟。這裡的老百姓因害怕抄家,預先把可以賣錢的東西「打估」。據說李子仲曾分批「打估」書刊,並且燒毀稿件、信件。我這才恍然大悟:我所珍惜的詩友的手稿、信件,早已灰飛煙滅,無可追蹤了。這是,日寇入侵導致的一筆「國難」帳,李子仲可以一走了之,我呢?只好長留遺恨在心頭。
特載:爛縵胡同之戀/吳奔星
北京是一座以胡同著名的古城。胡同最集中的地方,是城南的宣武門和前門之外。在明、清等朝代,北京城南是平民區。胡同之所以著名,與那些胡同裡的會館,為全國各省舉人赴京會試,提供無償住宿有關。特別是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要求光緒皇帝變法維新,曾七次上書。在一八九五年第二次上書時,住在會館的一千三百多名舉人,幾乎一呼百應,都簽了名。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車上書」,一次轟轟烈烈的知識分子企圖參政的運動。科舉制度廢除以後,進入民國,北京的會館仍是各省知識分子赴京工作或求學的免費住宅。...
推薦序
《小雅》復刻本序/陳子善
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是從白話小說和白話詩揭開序幕的,白話小說以魯迅《狂人日記》的發表為標誌,白話詩也即新詩則以胡適《嘗試集》的出版為標誌。一九二二年一月,署「中國新詩社」編輯的《詩》月刊創刊,這是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新詩雜誌,實由葉聖陶、劉延陵主編,為「文學研究會定期刊物之一」。然而,整個一九二○年代,專門的新詩雜誌寥寥無幾,徐志摩主編的《晨報副刊•詩鐫》當然是專門的新詩刊物,但是《詩鐫》是副刊的專版而並非雜誌。
進入一九三○年代以後,新詩雜誌開始爭奇鬥豔,徐志摩主編的《詩刊》先聲奪人,朱維基主編的《詩篇》和左翼的中國詩歌會主編的《新詩歌》隨後跟上,接著還有土星筆會的《詩帆》和戴望舒主編的《現代詩風》,後者創刊即終刊。 直到三○年代中期,新詩雜誌才迎來令人欣喜的繁榮期,中國新詩壇形成了戴望舒等主編的《新詩》、路易士與韓北屏主編的《詩志》和吳奔星與李章伯主編的《小雅》三足鼎立的新局面。
這三種新詩雜誌中,《小雅》問世最早,一九三六年六月創刊于北平,次年三月出至第五、六期合刊後終刊。四個月後,《新詩》在上海誕生,堅持出版了十期。又過了一個月,《詩志》也在蘇州呱呱墜地,但僅出三期就無以為繼。 《新詩》名家薈萃,壽命最長,自然影響也最大,研究中國新詩史的大都會提到它。《詩志》因路易士去臺灣後不斷憶及,也不能說毫無聲響。唯獨《小雅》,儘管詩人陣容強大,因流傳甚少, 反而最不為人注意。而且,儘管從文學期刊史角度視之,一九三六和一九三七兩年對中國新詩進程頗為重要,文學史家卻一直未引起應有的重視。再加上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裡,對非主流的新詩創作和刊物幾乎棄之不理。由於這些原因,半個多世紀以來,《小雅》差不多湮沒了,不要說一般的新詩愛好者,就是專業的新詩研究者,也幾乎都不知道新詩史上有這麼一個《小雅》詩刊的存在。
從這個意義講,復刻全套《小雅》實在是太有必要了。《小雅》的重見天日,將會為我們重新審視新詩史提供一個嶄新的視角。綜觀六期五冊《小雅》,至少有以下數點值得我們注意:
首先,這是編者十分用心的一個專門的新詩雜誌,雖小卻頗具特色。它以發表成名或無名新詩作者的原創詩作為主,輔以戴望舒、李長之、柳無忌諸家的譯詩,也有關於新詩的理論探討,包括對新詩的內容和本質、「明白話」與「真感情」的關係,以及新詩可否有「白話化的文言句子」等問題展開爭鳴,在當時的新詩刊物中自樹一幟。
其次,編者在創刊號《社中人語》中明確宣告「反對」當時「詩壇上多派相互攻訐」,強調「我們的編輯方針,對於任何一派的作品,都一律看待,予以榮發的機會。」顯然,《小雅》從一開始就顯示一種開放的姿態,只重「質的精選」而不問其他。儘管如此,刊物在成長過程中還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自己的風格,或者換言之,成為了編者後來自己所揭櫫的「作風為縹緲」的「法國詩風派」 的發表園地。
何謂「作風縹緲」?可以見仁見智。發表在《小雅》上的長短新詩,儘管也有《北洋軍閥》(斵冰作)這樣觸及時政的作品,但絕大部分是寫平民的日常生活,寫遊子的喜怒哀樂,古城洋場,晨曦月色,春殤冬暮,歎時光之流逝,抒失戀之傷感,這是《小雅》眾多詩作的基調,像吳奔星的組詩《秋天》,就有〈秋午〉、〈秋山〉、〈秋葉〉、〈秋雨〉四首,觀察之細緻,詩句之清新,可謂另有一功。這是不同於所謂激進的新詩主流的另一種新詩,以前往往被人視為小資情調、無病呻吟而詬病,現在看來仍不失為一群年輕的對未來生活充滿憧憬的新詩愛好者發自內心真情實感的流露。更何況這些詩作大部分是自由詩,大都注重古典資源的汲取,注重詩句的錘煉和獨特意境的營造。所以,《小雅》上的詩是新詩寫作的又一種有益的嘗試,理應得到積極的評價。
還有必要指出的是,《小雅》的作者,除了當時已經成名的新詩人,如李金髮、施蟄存、林庚、路易士等,更多的是詩壇新秀。有的在《小雅》上亮相後,逐漸走向成熟,已在新詩史上留下或深或淺的印記,如侯汝華、林英強、吳興華、陳雨門、甘運衡等。還有一些,或英年早逝,如沈聖時、史衛斯;或後來很少甚至不再寫詩,如錫金、陳殘雲、韓北屏等;或因多種原因淡出文壇,如李章伯、林丁、吳士星(吳仕醒)、常白等,他們的名字,有些我們熟悉,更多的是感到陌生,但有趣的是,他們共同組成了《小雅》作者群。這個新詩創作群體的功過得失,正待文學史家重新考量。
後來者研究前輩作家的文學成就,採取的方法通常是閱讀分析他們的作品,從單行本到文集到全集,還蒐集他們的集外文,以求更完整更全面地進行評估。也有更進一步從研究對象的文學活動切入,包括探尋他們的編輯生涯和文壇交遊,等等。吳心海兄從研究乃父吳奔星先生的文學道路起步,擴大到對奔星先生主編的《小雅》的關注,對《小雅》作者群的追蹤,正是循著這一路徑不斷深入的。《小雅》的五十多位作者中, 心海兄考證了三十餘位詩人或詩作者的生平、創作歷程及其與《小雅》的關係,已超過總數的二分之一以上,幾乎每期都有作品發表的《小雅》主要作者,都被他一網打盡了。這是一個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艱鉅而又漫長的發掘文墓之旅,心海兄這些年來堅定不移地努力著,查明了侯汝華、沈聖時、林丁的下落,考定了史密斯即後來的戲劇家方瀅,糾正了關於李白鳳的種種誤傳,還厘清了路易士和路曼士、吳士星和吳奔星、蔣錫金和蔣有林三對兄弟的《小雅》詩緣……。這一切,他都做得可圈可點,令人信服。新詩史上的這一段以前鮮有人關注的空白,由於有了心海兄這位有心人,終於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填補。
今年是《小雅》終刊八十週年,更是中國新詩誕生一百年,這是兩個很值得紀念的時間節點。因此,我完全有理由為《小雅》在今年重印鼓掌,為吳心海兄對《小雅》作者群卓有成效的考證工作叫好,也期待中國新詩研究界能夠以此為契機,進一步揭示中國新詩史的多種面向。
《小雅》復刻本序/陳子善
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是從白話小說和白話詩揭開序幕的,白話小說以魯迅《狂人日記》的發表為標誌,白話詩也即新詩則以胡適《嘗試集》的出版為標誌。一九二二年一月,署「中國新詩社」編輯的《詩》月刊創刊,這是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新詩雜誌,實由葉聖陶、劉延陵主編,為「文學研究會定期刊物之一」。然而,整個一九二○年代,專門的新詩雜誌寥寥無幾,徐志摩主編的《晨報副刊•詩鐫》當然是專門的新詩刊物,但是《詩鐫》是副刊的專版而並非雜誌。
進入一九三○年代以後,新詩雜誌開始爭奇鬥豔,徐志摩主編的《詩刊...
目錄
《小雅》(一九三六─一九三七)詩刊重印前言/藍棣之
《小雅》復刻本序/陳子善
特載:爛縵胡同之戀/吳奔星
《小雅》復刻文本
(創刊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六期)
【詩人篇】
沒有人知道你心中的大海─象徵派詩人侯汝華生平五題
翻譯家水天同的新詩及詩論
《小雅》主編之一 李章伯其人其詩
「神筆馬良」點津詩人史衛斯下落
英年早逝的現代作家沈聖時
喚醒「睡着了」的詩人林丁
錫金、蔣有林:《小雅》上的詩壇雙子星─兼談《中國新詩》雜誌
英語教學專家吳仕醒的早期新詩
生平鮮為人知的現代派詩人常白
一枚售價三分的明信片─詩人施蟄存伯伯印象記
林英強、李心若:《小雅》上的兩個女詩人?
黎敏子:時代讓他從詩人轉變為戰士、教師
王復周:少年情懷總是詩
詩人鄭康伯三題
沒有主編過《小雅》的《小雅》詩人韓北屏
他也是一位詩人─路曼士與新詩
來自揚州的無名詩人沈綠蒂
【史料篇】
李金髮與《小雅》詩刊
吳奔星致柳無忌詩簡裡的新詩史料
張愛玲激賞路易士的詩作初載《小雅》
關於詩人李白鳳生平的幾個史實
羅念生的筆和拳頭
吳興華最早的新詩作品─兼談《森林的沉默》轟動與否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戴望舒給李白鳳的題詩
甘運衡:「詩神捉住了我的靈魂」
小說家陳殘雲的新詩「習作」及筆名
李長之的新詩標準:兩類詩人不可原諒
《小雅》上林庚的「節奏自由詩」
陳雨門被遮蔽的閃亮詩句
《小雅》上「跛足」的詩壇兄弟─宋衡心及其主編的「詩之葉」
一樁美麗的誤會:石揮辨詩香
《小雅》上的卞之琳和徐芳去哪兒了?
《小雅》編外詩人曾今可
《小雅》上《吳宓詩集》的廣告
主要參考書刊
後記
《小雅》(一九三六─一九三七)詩刊重印前言/藍棣之
《小雅》復刻本序/陳子善
特載:爛縵胡同之戀/吳奔星
《小雅》復刻文本
(創刊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六期)
【詩人篇】
沒有人知道你心中的大海─象徵派詩人侯汝華生平五題
翻譯家水天同的新詩及詩論
《小雅》主編之一 李章伯其人其詩
「神筆馬良」點津詩人史衛斯下落
英年早逝的現代作家沈聖時
喚醒「睡着了」的詩人林丁
...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收藏
1收藏

 1二手徵求有驚喜
1二手徵求有驚喜



 1收藏
1收藏

 1二手徵求有驚喜
1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