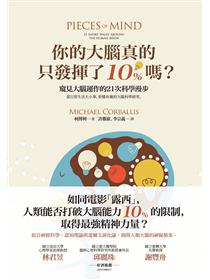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上海─台北兩岸文學營!童偉格、劉梓潔陪您逛上海書展。王聰威/文
四十年前,爸爸買的第一間房子,是蓋來賣給公教人員的四樓公寓的二樓,在高雄一處荒涼郊區。
我住的那一棟前後十六戶人家,大概都知道每一家是住什麼樣的人,做什麼工作、有多少成員,何時娶媳婦嫁女兒都掌握的相當清楚。朋友會直接在樓下叫我的名字,要我下去玩,中秋節時跟隔壁棟公寓小孩用沖天炮互射,一隻三色野貓則會沿著樓梯、鐵窗爬上陽台,把我家吊在外面三個鳥籠裡的鳥,大約五隻,全部用爪子割裂殺死。
貓抓死鳥沒什麼了不起的,三樓的狹窄陽台養了一隻比人還高大的大麥町,但才養一個星期而已,某天主人早晨起來一看,喉嚨一道貓爪痕,血流滿了陽台地板,大麥町已經死的僵硬了。那家小孩是我練習跆拳道的朋友,家裡曾經相當有錢,爸爸生意失敗之後不得已搬到這裡來,據說媽媽有段時間拋下家庭去日本「做代誌」,當鄰居說起「聽說伊去日本做代誌」時,總是壓低了聲音,好像怕早就知道其實是怎麼回事的人又知道一次。他們家空空如也,客廳只有一組紫褐色的古董木傢俱,地板跟所有人家一樣是綠白色塑膠貼皮。他媽媽是個清秀嬌小的女人,有次切了盤哈密瓜給我吃,好像很高興兒子有我這個朋友,卻又不好意思跟我說話,可能因為我是非常有名的好學生,而我那朋友其實是個小混混,打躲避球和打架的身手都很了得,附近小孩常常被他扁得慘兮兮的,不知道為什麼對我特別好。
現在想起來,那隻大麥町好像是他家的象徵,看起來那麼強壯氣派,卻得委屈於狹小不得志的偏
遠之地,而且事實上極為脆弱,只要一道貓爪痕便足以致命。我實在搞不懂為什麼一個空空如也,
已經沒有金錢沒有權勢,甚至都快沒有家人的家庭,要忽然養一隻不合時宜的大麥町,然後又巨大悽慘地死去?當時只是在唸小學四年級的我,沒辦法問出這樣的問題,我只問了朋友說:「狗半夜沒有叫嗎? 」
「我只有聽到嗚嗚的聲音而已。」他說。過了幾個月,唸小學六年級的朋友一家便搬離公寓,不知去向。當然那時候還沒有專門當作住家的電梯大樓,我心中也沒有那樣的觀念存在,後來我們家搬到一棟電梯大樓,但我已來台北求學工作,而在這二十幾年間,只有最近四年是住在大樓,逐漸明白類似大樓的空間設計、動線規劃與運作模式,如何將人們切隔成一戶一戶獨立如太空艙般的生活,例如僅僅樓上樓下的距離,卻彼此不願意登門拜訪,而盡可能透過管理委員會、警衛、總幹事和對講機來溝通,就像太空艙得依賴NASA 控制中心才能與地球連絡一樣。
很奇妙的,我讀陳雪的《摩天大樓》時一直想起《星際效應》這部電影,那些操作太空艙在廣漠
宇宙裡四散發射、漂浮、降落、搜尋美好未來的宇航員,彷彿是勇於孤獨前進的新人類,但最終仍得回到一種舊式的情懷:「想要與你相遇相知」,即便要花掉幾十年時間等待只得到一場短短會面,即便對方是活在五次元空間的人類,即便要讓自己陷入傳統人情世故,千瘡百孔,無法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