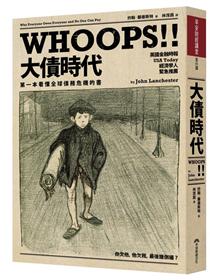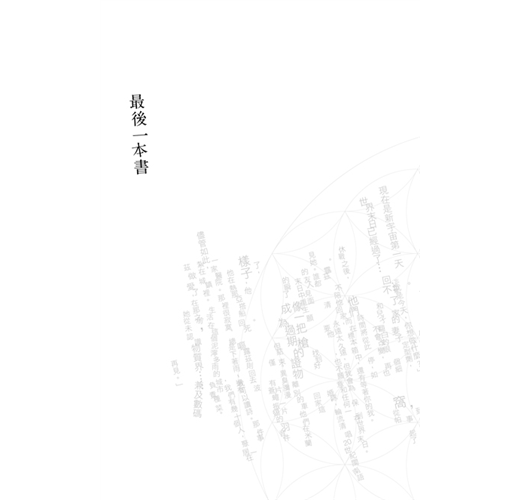八月六日/峠三吉(1917-1953) 翻譯:汀汀忘掉那道閃光吧
三萬人從街道上瞬間消失了
而被壓潰的黑暗深處
還有五萬人的悲鳴
黃色煙霧如同漩渦
大樓龜裂
橋樑毀壞
燒焦的電車始終客滿
無窮無盡的瓦礫與火
堆砌成廣島
體無完膚的人們
兩手抱胸 踏過腦漿
燒焦的布 纏繞腰間
裸體的人群
邊哭邊走
練兵場上的死屍猶如
崩散的石製地藏
自河岸堆疊 成群淹向岸邊的竹筏
所有烈日照射到的地方
均逐漸被屍體取代
壓在建築物底
卻仍活著的母親和弟弟
居住的城鎮則被吞噬夕陽的火感染
在兵工廠 散滿糞尿的地板上
躺滿未逃走的女學生
鼓脹的肚腹、一隻壓爛的眼球、剝落的半身、削去的頭髮
就算晨光再度灑落
也不會再動了
已經無法分出誰是誰
異臭瀰漫 鐵臉盆裡
僅有蒼蠅振翅的羽音
三十萬人的都市
消失了
在寂靜之中
忘掉寂靜吧
回不了家的妻子
和兒子翻白的眼窩
我們的靈魂已經被切斷
忘掉許過的
心願吧 它們已經
無法實現
底本:《原爆詩集》,青木書店
一九五二(昭和二十七)年六月初版發行
潤稿:鄭哲涵
=============================================================================
世界末日/陳頭頭
=============================================================================
保存期限/沙特自從你離開之後,
我就一直等著,一直等著,一直等著
一直等著,一直等著。
一切都會保持原狀,
房間的裝飾、家具的位置,
書桌上攤開的書、曬衣架上曬著的衣服,
窗戶打開的角度、牆上的霉斑,
冰箱中的包著保鮮膜還未吃完的剩菜,
馬克杯中的水漬,盤子上的裂痕,
慵懶的躺在陽光下的我們的小狗,
還有我,
我保證,一切都不會變,
不管幾十年,幾百年,幾千年,
只要你回來你就一定會看到。
把一切噴上定型劑,
讓防腐劑滲透每個細胞,
再也不會改變,再也不會腐敗,
時間將從此暫停,如同冰封的標本,
而在標本箱中,還有等著你的我。
永遠太久遠,但我會為你保存到世界末日。
=============================================================================
在河這邊/張維尼(「拍謝少年」樂團吉他手)其實啊是國中同學阿誠帶我聽陳昇,第一張我買《鴉片玫瑰》吧,存夠了錢他騎車幫我去唱片行買。午休偷聽<流星小夜曲>,脫了鞋在溫暖的晚風裡奔跑—聽到入迷,上課開始用隨堂測驗紙寫歌詞。也買了《Summer》的卡帶,裡面一張前中年的陳昇黑白照小卡,把它夾進塑膠墊板裡頭沒事盯著,心悄悄晃動。
多想抵達陌生的街道,走在斜度溫度都不同的馬路上。
年底,《魔鬼的情詩二》出版,狠心買了木盒精裝版;內容物豐富,也順便宣傳了跨年演唱會。明年你還愛我嗎?千禧年前夕,我也能感覺空氣漸漸濃烈起來,世紀之交的狂歡又帶著宗教末日性的神經質。那時世界尚未在我眼前完全開展,遠方傳來喧鬧歡笑聲,距離讓我感到危險也覺得失落。
阿誠跟我絕配,是成長過程中常出現的大小漢組合。他粗壯大漢好像特力屋的起重機,每天艱難地塞進尺寸不合的國中桌椅;我靈精小漢活在自己世界,跟不太上同學著迷的事物。阿誠騎腳踏車上下學,有時也載我去補習,模型型錄會多幫我拿一本。我像個外星落難大使一樣對於地球的重力與摩擦力過敏,還好他是我的翻譯與保鑣。
其實啊國中環境是好的,學校在河邊,想坐渡輪也一下就到,班級不多規模小,圍牆低,翻出去買冬瓜茶方便沒罪惡感;只是啊想做的事很多,世界資訊在蠢蠢欲動的爆發邊緣,我好想要知道,只是啊伸出手腳連自己的輪廓都看不清楚。
有次整天大雨,還沒整治好的愛河下得一陣滾濁,中午不到就漫了出來。臨時放半天假,我坐著午餐籃在洩洪般的樓梯滑了幾遍,玩夠了打電話叫爺爺來載。等好久,自己先走,過橋的時候對面馬路爺爺一身灰雨衣,騎著也是鐵灰的偉士牌從橋上經過,喊他沒聽見,才想到他耳朵不好,才想到我可能從來都不了解他。
以雨為背景走到奶奶家,奶奶催我上二樓吹頭,一會爺爺回來,奶奶喚我吃飯。這是我們三人倒數幾次的安靜相聚,這已經是上個世紀的事情。
=============================================================================
樹倒/吳明益收到同事傳來宿舍門口積水的照片,不習慣麻煩學生處理自己的私務,只好當天處理好一些事後,立即回花蓮。就像預期的一樣,坐在車上經過黑暗的台九線,樹倒的台九線。台九線上的樹有不少是種植大約七、八年的樟樹,我心中暗記了一下,倒了三成左右。
回到宿舍先從除積水開始,隨即整理前後陽台。由於落葉甚多,水易淤積,看來是該換一個有點高度的排水口才是,這樣一旦落葉堵塞,也不會很快積水。
盆植多半沒有死去,只是傾倒或土壤流失,倒是一株手植已高二公尺的樟樹倒了。我一個人挖坑、扶正、踏實土壤,在雨中全身濕透。陽台植株則重新用園藝用軟鐵絲再次固定於欄竿上,已近中秋卻尚未有涼意,說不定還有秋颱會來。
清晨搭六點十五的火車離開,幾乎一夜未眠,四點多開始在昏暗的校園走看。我記下傾倒的樹種,成樹以刺桐最為嚴重,其次是樟樹。倒樹又分兩種,一種是連根拔起,一種是幹身斷折。連根拔起的還再分主根斷裂的,或主根仍在的,主根仍在雖有希望重生,但三五年內無法紮深根,颱風一來若無支撐,必將再倒。我宿舍前兩株光臘樹,一株楓香,俱是龍王颱風時的倒樹,此次再倒。至於幹身斷折的樹,雖然魂魄尚在,頂端生長點一失,很難長成完整樹形了。
看著這些倒樹我心情低落,它們是我這八年來的朋友,我未必記得每一株樹,但嘗試記得每一株。任何一位東華的訪客或學生告訴我哪一條路,我的腦中的影像會先長出樹,然後才長出天空、長出建築。它們給我更多不恨這世界的理由,因為陰影、每年新生的樹葉、蟲癭、鳥巢……,也許也因為樹會成蔭,樹會傾倒。
可惜今天下午在台北有約,明天和學生在淡水有約,我只好搭早班車離開。苦等天光,只得十分鐘,匆匆地拍了幾張照片。心底更急切的,是希望學校能派人用最短的時間統計倒樹,並研究原因。哪種樹倒的比例最高?是樹折還是根拔?推測是因為受風面太大(日後應在颱風來前修剪),還是植株附近太過空曠?是因為樹本身根淺,還是種植的地方土層太薄?(宿舍旁邊的土根本只有兩、三鏟深!)是樹種選擇的問題(水黃皮顯然不愧九重吹之名),還是平日維護的問題?像東華這樣總是「面向颱風」第一線的學校,校樹竟很少有大木樁支撐,一時看來是省預算,長久下來就變花大錢。每株五到十公尺高的成樹,若單以市價來論,少說數萬,多則十餘萬,理應被視為重要資產珍視,一般樹種約五年伸根初步完成,這之前更應用四腳樁固定。更何況每株樹都承載了不同學生的記憶,其珍重難以計量。
樹生有年,樹倒有時,但就像每種生物都想辦法適應環境,遷就環境,人工校園理應順應地理,逐步修正。
當研究生載我通過木瓜溪橋時,曙光在東方,木瓜溪水急而不泛漫,彷彿暴雨未曾來過。我匆匆下車,匆匆站上橋護欄拍照,正當此時,據說溪那頭的銅門傳出山崩。
樹生有年,樹倒有時,我們脆弱地活在一個脆弱的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