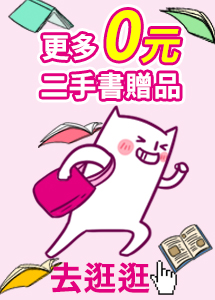龍應台
一年半以來,收到太多的讀者來信,來自不同年紀閱歷的世代,來自全世界各個不同的地方。《大江大海》像黑色深海中鯨魚以震動微波發出的密碼--有些失散半世紀的親人,找到了;有些完全淹沒的歷史,浮出了;有些該算沒算的賬、該謝沒謝的恩,找到了遺失多年的投遞地址;有些背了一輩子的重擔,放下了。
這不是走到民國百年了嗎?開啟一封一封來信,每一封信都帶著熱流,像大河穿過大地,像血液流過血管。民國百年的土壤,一定是鹹的,有多少人的眼淚和汗。
書出當時只有“跋”,沒有“序”,在書出版一年半以後,離散的「民國三十八年」更為人知了,而書中很多涉大江大海的人,也走完了人生的旅程,回到他曾經用眼淚和汗澆過的大地。 捧著這把我無以回報的信,就以一篇短序,來跟讀者做個很難及格的「進度報告」吧。
1
二零零九年秋天,《大江大海》出版,好像有一道上了鎖,生了鐵锈的厚重水門,突然之間打開了,門後沉沉鬱鬱六十年的記憶止水,「嘩」一下奔騰沖洩而出,竟然全是活水。
老人家在電話上的聲音非常激動,大江南北各地的鄉音都有,他們的聲音很大,可能自己已經重聽;他們的敘述混亂而迫切,因為他們著急:一通電話怎麼講清一輩子?
一位八十八歲的長者說,他無論如何要親自把手寫的自傳送過來,現在就送過來,因為,他說,「他們馬上要送我進老人院了,一進老人院,大概就沒人找得到我了…」
「他們」是誰?我不知道,也不忍問,只是想到,人生的不由自主,除了十八歲時可能被送上一條船而就此一生飄零之外,竟然還包括在八十八歲時被送進一輛不知所終的車。
無數的自傳到了我的手裡,很多是手寫的,有的童拙,每個字都大手大腳跨出方格,雜以錯白字,憨厚可愛;有的,卻是一筆有力的小楷書法,含蓄雅致。字體大小錯落,墨跡深淺斑駁,可以想見都是花了很長時間,晨昏相顧,一再琢磨的掏心之作。我將大大小小的自傳手稿在地板上攤開,夕陽的懶光照進來,光束裡,千百萬粉細的塵粒翻滾,一部民國百年史,是否也包含這些沒人看見的自傳呢?
更多的信件,來自和我同代的中年兒女們。
…我在父親的遺物中看見一個臂章,寫著某某 「聯中」的字樣,從來不知道那是什麼,其實也沒在乎過,懶得問。讀了你的書,才知道自己的父親竟然是那八千個孩子中的一個,他竟然是這麼走過來的。想起從前每次他想跟我談過去時,我就厭煩地走開…
開放之後,他一路顛簸回到老家,只能拜倒在墳前哭得死去活來,太遲了,太遲了…
讀你的書,我也才認識了父親,可是也太遲了…
在戰後和平歲月出生的這一代,也都六十歲了,已經懂得蒼茫,凝視前一代人逐漸消瘦,逐漸模糊的背影,心中有感恩,更有難以言說的疼。火車錯過,也許有下一班,時光錯過,卻如一枚親密的戒指沉入大海,再多的牽掛惆悵也找不回來。
年輕的一代,很多人真的拿著錄音機磨蹭到祖父母身邊,請他們「說故事」。香港珠海學院的學生為長輩拍紀錄片,小學生回家問外公外婆 「當年怎麼來香港的」,問出連自己父母都嚇一跳的身世。羅東高中的學生遍訪鎮上的眷村長輩,一個一個做口述歷史。但是被封藏的記憶並不僅止於流離的難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記憶也有「流亡」的可能:
外公很恨外省人,媽媽嫁給外省人他一直都不高興。我和媽媽去他家,他拿出他做日本兵的照片給我看,很得意說,你看,日本兵制服多神氣,哪像中國兵那麼爛。我對他反感得要命,但是,現在我有點明白了:他在南洋打仗,很多年輕時的好朋友都死在南洋,他喝醉唱歌,其實是在想念過去,就像爺爺一天到晚說他的老家山東如何如何…
2
《大江大海》至今在大陸未能出版,但是在一個防堵思想的社會裡,「未能出版」等於得了文學獎,人們於是花更大的工夫翻牆尋找。對於內戰的「勝利者」而言,六十年來「失敗者」被罩在一個定型的簡單的「敵我意識」硬殼裡頭,攤開《大江大海》,猶如撬開那個硬殼,看見的卻是渾身傷痕一個又一個的普通人─原來所謂敵人也不過就是當年鄰村的少年。讀他人史,澆自己愁,「勝利者」自己心中多年深埋的傷,也開始隱隱作痛。
您的書我讀得很慢,讀時淚流滿面,無法繼續,只能掩卷使自己平靜下來才能再讀下去。有時,需平靜數日才能續讀。
抗日戰爭勝利的1945年,我已經是讀小學四年級的少年了。今年,我是一個行將就木的老人了,我的家鄉是在東北吉林省的一個小山城…
隱忍不言的,是一個深不見底的傷口。北京作家盧躍剛給我一封長信,說的是「勝利者」的傷,其實比「失敗者」還痛:
失敗者”轉進”到了台灣,臥薪嘗膽,蝸居療傷。勝利者的行徑卻著實怪誕。他們不是像歷史上所有改朝換代的勝利者那樣,輕徭薄賦,獎勵耕織,休養生息,而是按照革命的血統論,把中國人嚴格地階級成份等級化...先是向農民翻臉...把幫助自己打下江山的自耕農變成了農奴;次之向知識分子翻臉,向民主黨派、工商界人士翻臉,把過去的同盟者打成自己的敵人...
國共內戰,死個幾百萬人暫且不算,戰爭本來就是血腥的。我們要問,中共建政後,和平時期冤死了多少人?
在「失敗者」飄搖度日,倉皇求存的時候,「勝利者」卻開始進入「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時代。學者最新的研究成果把大躍進時期的饑荒死亡人數定在四千五百萬人,其中絕大多數是底層農民。
(局部,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