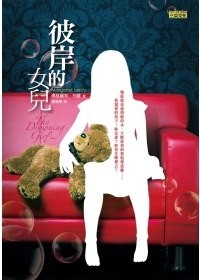我是如此愛妳,卻對妳一無所知……
「為什麼那張照片這麼特別,甜心?」
「那是我的海邊哪,葛蕾絲。」她說:「我曾經住過那兒。」
她說話的語氣,彷彿有個陌生人正在透過我的孩子發聲──
彷彿她已經遺忘了我,而那遙遠的彼方才是她的歸屬。
我的心撞擊著胸口,戰慄竄過全身; 儘管發生了這麼多事,都比不上眼前這一幕能讓我如此恐懼。
~*~
四歲大的希薇究竟怎麼了?
年輕的單親媽媽葛蕾絲憑著微薄的薪水,獨力撫養她唯一的小女兒。
然而,希薇從小就跟一般同齡的孩子有著明顯不同:
她不僅沉默寡言,從來不肯叫葛蕾絲「媽媽」,
對水還有一種莫名強大的恐懼。
不久,當希薇開始反覆畫起一棟她從未造訪過的水畔小屋,
夜復一夜在「無法呼吸」的噩夢中哭叫驚醒,
心急如焚的葛蕾絲不得不向兒童心理學家亞當‧威特斯博士求救,
卻發現,一切線索似乎都將三人引向愛爾蘭遠方狂風吹拂的海岸,
而來自過去的幽暗祕密,
也正朝著這對絕境中相依為命的母女步步進逼……
作者簡介:
瑪格麗特‧列羅Margaret Leroy
英國暢銷女性小說家。生於英格蘭,在牛津大學音樂系畢業後,曾經擔任音樂治療師、特教老師、心理輔導師與兒童保護社會工作者。成為全職作家後,至今已出版四本小說《信任》(Trust)、《艾莉森的鞋》(Alysson’s Shoes)、《來自柏林的明信片》(Postcards from Berlin)、《河畔之屋》(The River House),皆廣受好評,以其書中堅強、獨立的女性角色著稱,其中《來自柏林的明信片》一書更獲選為2003年《紐約時報》的「年度焦點新書」。
關於她的新作《彼岸的女兒》,列羅在《歐普拉雜誌》的專訪中提到:英國第五頻道一部相關主題的紀錄片《這個男孩從前活過》(The Boy Who Lived Before)、人們對愛爾蘭西海岸的浪漫想像,甚至連《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這部經典鉅作,都是催生這部小說的幕後功臣
譯者簡介:
羅曉華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畢業,現為文字工作者。平日喜愛閱讀小說,尤以成長療癒小說為最。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國內強力推薦】
作家、精神科醫師 王浩威
【國際佳評如潮】
「瑪格麗特‧列羅的這本小說是少數會讓人一坐下開始讀,就非得讀到全身骨頭都在發痛了還不能停止的作品!……《彼岸的女兒》就如童年本身一樣危險,也一樣令人心醉神迷。」
──歐普拉‧溫芙瑞(Oprah Winfrey)著魔推薦!
「《彼岸的女兒》結合了未解的謎團、超自然事件及一位母親所面臨的艱難處境等元素,使得故事讀來格外引人入勝……這本小說會讓你想要熬夜讀完,或希望自己通勤時搭的不是一輛特快車,而是每站都停的火車,好讓你一路看到最後!」
──莎拉.明斯(Sarah Minns),《好讀》雜誌(Good Reading)
「《彼岸的女兒》這部讀後讓人久久難以忘懷的小說,稱之為現代版的《蝴蝶夢》,的確當之無愧!」
──黛安.史特雷辛(Diane Stresing)
「打從一翻開書,我就無法自拔──書裡的諸多轉折起伏讓人大呼過癮。我的英國讀者將能體會我為何說這本小說非常適合拍成ITV的迷你影集!」
──克萊兒.史威朵赫斯特(Clare Swindlehurst)
「一個關於母愛令人心驚、著迷並予人啟發的故事……此為哥德式懸疑小說的上乘之作。」
──凱薩琳.貝利(Katherine Bailey)
「對於照顧一個你深愛卻無法真正理解的孩子時會是什麼模樣,我鮮少看到有作者能夠對其做這樣精確而感人的處理──但瑪格麗特.列羅做到了!」
──安德利.季拉斯(Adele Geras)
「這真是本非常特別的小說……作者深入刻劃出書中小女主角希薇的脆弱,讓人不禁想進到故事裡,親自保護宛如真實血肉之軀的她。」
──露易絲.肯利許(Louise Candlish)
媒體推薦:
「如果真有令人無法釋手的小說,《彼岸的女兒》無疑就是這樣的作品。儘管讀來令人毛骨悚然卻魅力十足,從故事開始到完結都讓人目不轉睛……如果一本完美夏日讀物的定義是從頭到尾都讓人無法分神,並能帶領讀者進入未曾造訪之地的話,本書就是最佳選擇。瑪格麗特.列羅成功地塑造出能讓人深感認同的角色,以及令人膽顫心驚的情節。」
──愛爾蘭《克萊爾人報》(The Clare People)
「在《彼岸的女兒》裡,列羅女士深入描繪出了書中女主角做為母親的恐懼:她不計一切想幫助自己的孩子,卻發現自己正在接近她所無法理解的事物。」
──《華盛頓時報》(The Washington Times)
「列羅以氛圍、豐富細膩的文字,誘引讀者一步步踏入一樁令人不安的疑雲。書中人物就如同她所描繪的英國及愛爾蘭場景一般栩栩如生、引人入勝。」
──《出版人週刊》(The Publishers’ Weekly)
「讀來引人入勝、讓人戰慄,但仍是非常愉快的閱讀經驗……是喜歡《蝴蝶夢》的文學讀者絕佳的選擇。」
──《克里夫蘭據實報》(Cleveland Plain Dealer)
「不安的孩子。離奇的謎團。絕佳的閱讀經驗。」
──「推特讀書會」
名人推薦:【國內強力推薦】
作家、精神科醫師 王浩威
【國際佳評如潮】
「瑪格麗特‧列羅的這本小說是少數會讓人一坐下開始讀,就非得讀到全身骨頭都在發痛了還不能停止的作品!……《彼岸的女兒》就如童年本身一樣危險,也一樣令人心醉神迷。」
──歐普拉‧溫芙瑞(Oprah Winfrey)著魔推薦!
「《彼岸的女兒》結合了未解的謎團、超自然事件及一位母親所面臨的艱難處境等元素,使得故事讀來格外引人入勝……這本小說會讓你想要熬夜讀完,或希望自己通勤時搭的不是一輛特快車,而是每站都停的火車,好讓你一路看到最後!」
──莎拉.明...
章節試閱
一則廣告吸引了我的注意。裡頭有個站在寬闊岩岸邊的男子,厚實魁梧的身材像極了多明尼克,身上那件隨著他的腳步翻飛的綠色長風衣,正是多明尼克常穿的那種外套。我總是會反射性地注意到跟多明尼克相關的東西:他的圖章戒指、社團領帶、他抽的香菸的氣味。有時在街上,我會突然回過頭、心神恍惚,只因為突然到行經的路人身上帶著多明尼克的香水味。現在,看著那張照片,我彷彿能嗅到他身上的氣息,感受到他的撫觸。那則廣告是在幫一家專門販售戶外運動衣物的公司促銷產品。畫面的背景是空曠的海景:白色的沙灘、黑色的礁岩、明亮的天空。
希爾薇注意到我出神地盯著照片。她坐在我對面,所以得歪著頭才能看清楚照片。她看看照片又看看我之後,視線又回到照片上,這時她睜大了眼睛,眼裡散發出光采,最後,她突然猛地投入我懷中。她給了我一個短暫熱情的擁抱,臉跟身體一側被爐火烘得暖暖的。我能感覺到她的心跳。
「你找到它了,葛蕾絲!」她臉上綻出笑容,宛如一盞燈倏地捻亮。
我不明白自己做了什麼。我一度瘋狂地以為,她是否暗中探得她父親的一些事,並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找到了他?又或者她知道照片上的男子長得像她父親?
然而,她很快就伸長了手,極其輕柔地用指腹撫觸著頁面。
「就是那兒,」她說:「那就是我的海邊,對吧,葛蕾絲?」
「當然,」我說:「你可以把它放到你的拼貼畫裡。」
「那兒真美,對吧?」
她臉上掛著燦爛自信的笑容,彷彿她正期待的事情發生了。她的舉動讓我一陣戰慄。她是如此地篤定,如此地認真。
我更仔細地看了看照片。它的構圖相當出色,水面上的光線明晰,卻感覺稍縱即逝。你能感受到畫面中氣候的轉變,從海面上逐漸逼近。白色的沙灘在忽明忽暗的陽光下閃爍不定;方才為潮汐撫平的沙子,如絲綢般鋪展開來;黑色礁岩上披覆著一片白堊般的藤壺。潮水捲向岸邊的速度肯定相當快,烏雲所投下的暗影在水面上挪移,天色亦逐漸加深為最深邃的藍。在照片的一側,有座停靠著漁船的海港。
「是啊,真美,」我說。
我開始把頁面撕下來。
她伸出手捉住了我的手臂。
「小心點,葛蕾絲,」她突然嚴厲地說,用力地掐住我的手腕。「別撕壞了。」
「好,我用剪的,」我說。
我拿起剪刀開始小心剪下。她在一旁熱切地注視著,屏著呼吸。
「你要非常非常小心喔,」她說。
剪下後,我將照片遞給她。
「來吧,你現在可以把照片貼上去了。」
她搖搖頭。
「我想把它貼在床旁邊。葛蕾絲,我們可以把它貼在我的床旁邊嗎?」
「當然,如果你想的話,」我答道,大感訝異。
我找來紙黏土,跟希爾薇把照片貼在她衣櫥的那一側,這樣她躺在床上時就能看到它。
那幅拼貼畫已不再能引起她的興趣。她跪坐在床上,凝視著照片,緋紅的小臉上滿是激動的神情。她在床上坐了許久,整個晚上都顯得極為開心。
§
當天晚上,將她裹進棉被裡後,我在她床邊又逗留了一會兒。房裡只有床頭燈亮著,讓她的房間顯得更為寬敞、空曠,房內的角落以及她掛在門後掛勾上的衣服,則顯得更加黑暗。靜坐在房裡時,我開始逐漸能辨認出在這片無法穿透、層層疊疊的暗影裡的東西--蜘蛛的形狀,或是扭曲的臉孔。我真希望自己有能力負擔更多的家具,像是替希爾薇買張書桌,或是有幾層抽屜的衣櫃。我們現在看起來就像是非法闖進了空屋,彷彿我們從未真的搬進這個家一樣。如果房裡的家具能豐富些,住在這裡或許就不會讓人感到如此寂寥了。
希爾薇幾乎就要睡著了,正不停地貶著眼睛。她打了個呵欠,轉過身背對我。我的心跳加快,但我試著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很冷靜。
「希爾薇,告訴我你對那張照片的感覺。為什麼它這麼特別,甜心?」
一時之間我以為自己錯過了時機,以為她早已經睡著了。
就在這時候,她又轉過來面向我。
「那是我的海邊哪,葛蕾絲。」她用極為就事論事的口吻說道,彷彿這事實應當再明顯不過。
「那地方很美,」我又說了一次。
「是啊,」她說:「我以前住過那兒,葛蕾絲。」
我僵坐了一會兒,那一刻感覺如此漫長、緩慢。戰慄竄過全身。
「我不知道這件事,」我說。
「你不知道嗎,葛蕾絲?」她似乎很驚訝。
「不知道,我從沒去過那兒。所以你得告訴我,你能告訴我任何細節嗎?你能告訴我關於那地方的事嗎?」
「那是我的海邊,」她又強調了一次:「我住過那兒。」
「告訴我你住過哪兒,」我說。
「我住在一間很小的房子裡,」她說:「一棟白色的小房子。」她再次翻過身去,打了個大大的呵欠。「我住過那兒,而且我還有一個洞跟一隻龍。」
我先是感到失望,接著又放下心來。那肯定是因為她在托兒所裡看了一本故事書,或是她在想像的世界裡,憑空捏造出來的幻想。
「哇,給龍住的洞啊ˋ?」我試著用平常平靜的口吻說道:「有條龍很炫呢。」
這時她張開了眼睛,眉間擠出一道小皺紋。我說話的口氣肯定令她有些不悅。
「葛蕾絲,我不是在說傻話。」她對著我皺眉。對於我沒有嚴肅地對待她,她似乎感到有些惱火。「真的,我真的有過一條龍。」
「那地方肯定很美,」我又說了一次。
「是啊,葛蕾絲,」她說:「我就住在那裡。我曾經住過那裡。」
§
校園裡到處都找不到停車位。
我穿過草坪,經過開著白色花絮的櫻桃樹,走進側門。告示寫著所有訪客一律都必須到櫃檯報到。我不予理會,直接進入門廳,循著心理系的指標,走下回音繚繞的長廊,長廊裡飄散著濃烈嗆人的浴皂味。一路上有不少貼滿告示的布告欄,上頭隨風飄動的紙張像是在招手般,吸引妳的目光。學生三三兩兩經過:男孩身穿皮夾克,滿臉倦容的女孩則穿著牛仔褲,不停把頭髮往後撥。根本沒人注意到我。我透過一道玻璃門,看到裡頭的班級正在上課,裡頭的擺設就像一般的教室,有成排的桌椅跟一個白板,差別只在於所有學生都很專心在聽講,而女教師穿著鼻環。
走廊底端通往左右兩個方向,但沒有任何標示。我往左轉直走,知道自己迷路了。我肯定錯過了某個指標,放眼望去不見任何指向心理系的標示。我覺得自己正非法闖入禁地,在迷宮般的走廊上搜尋著目標。一名女子朝我走了過來。她看起來年紀稍長,不像是學生,或許是講師吧。她身穿緊身牛仔褲,頂著隨性凌亂的暗金色鬈髮。她狐疑地看了我一眼,我不禁擔心她會問我在這兒做什麼。我避開她的目光,繼續往前走。
就在我打算放棄的時候,我來到了玻璃旋轉門前,看見門上標示著「心理系」,於是我穿過旋轉門。
櫃檯前有個接待員。她看起來像是來自地中海一帶,眼周畫著濃濃的煙燻妝,正興高采烈地講著電話。她身旁有一整排靠牆而立的座椅、幾個檔案櫃、一個洗手台,洗手台旁還嵌著紙巾箱。
我左右張望,不知接下來該往哪走。接著,我看右側的一扇門上,正好寫著「亞當.威特斯」的名字。我不假思索,便直接走到門前敲了敲。無人回應。
「抱歉?」接待員尖聲說道:「需要我幫忙嗎?」
我轉向她。
「我想見亞當.威特斯先生。」
因為麻藥未退,我嘴邊的肌肉仍然很僵硬,所以得用力擠出話來。
「好的。」她翻翻桌上的文件。「您預約的時間是?」
「我沒預約。我是臨時來訪的。」我一邊說,一邊用手摀住臉頰。我知道自己看起來肯定很可疑。
「如果您沒有預約的話,恐怕沒辦法見威特斯博士。」
「呃,或許他見到我的時候,會願意撥點時間給我。」
「不,那樣行不通的。」
空間感覺有點傾斜。我擔心自己會暈倒,趕緊坐到椅子上。
她有著水潤的大眼,讓她看起來好像一個不安、嚴肅的孩子。
「我得見他,」我又說:「我想向他請教關於我女兒的事。我是指,我得先跟他談過,才能確定是不是需要再跟他約時間。」
她噘著嘴。「我得檢查妳的通行證。」
「很抱歉,我沒有通行證。櫃檯的人沒給我。」
「那麼妳真的不該待在這裡。這裡嚴格規定訪客都得配戴通行證。恐怕我得請妳離開這兒了。」
「別擔心,我可以坐在這兒等就好。我保證不會給妳添麻煩的。」
但她卻別開頭,拿起了話筒。
兩名保全人員幾乎就在同一時間穿過了旋轉門。他們身穿灰色制服,面色凝重,身材壯碩。他們分站在我身旁,其中一人甚至使勁捉住我的臂膀。
「女士,我們得請妳跟我們來,」他說。
我已無能為力,只好站起身來。
走廊一頭傳來兩名男子熱烈交談的聲音。我猜他們應該是意見不合,但聽不清談話內容。接著一名男子背著身子用肩膀頂開迴轉門,進到了門廳,雙手各拿著一杯裝著咖啡的保溫杯。任誰都看得出來他這麼做太勉強了。他突然停下腳步,看著我和保全,接著門片彈回,打到了他的手腕。咖啡灑得他滿手臂跟袖子都是。
「幹!」
看到他動怒的感覺有些奇怪。他比照片上看起來更邋遢:他捲起袖子,襯衫下襬沒塞進褲頭,下巴的鬍碴也沒刮。他把兩杯咖啡放在一個檔案櫃上,從紙巾箱裡抽出幾張紙巾。另一名男子往後勾住一扇門片。他穿著剪裁俐落的運動上衣,厭惡地看著眼前混亂的場面。
我面向第一名男子。
「威特斯博士?」我問道。
他望向我,快速朝我看了一眼,視線再轉向兩名保全人員,再落回我身上。他張大了眼睛。
「我想跟你談談我女兒的事,」我說。
他機械性地用紙巾擦著手腕,始終注視著我。灑在地上的咖啡散發著濃郁的香氣。
「妳想見我?」他問。
「是的。」
「老天。」他露出困惑的表情。
穿著運動衣的男子稍稍揚起一側眉毛。「有些人還真是走運啊。或許我該改變研究領域才對……」他說完便走進其中一間辦公室。
亞當.威特斯接著對兩名保全人員說:「不礙事的,她現在跟我在一起。」
但兩名保全人員依舊佇立在原地。
「你們走吧。真的。相信我,沒事的。」
兩名保全人員只好心不甘情不願地離開,離開時還回頭張望,彷彿我是隻脫韁的野馬。
他茫然地把紙巾拋向垃圾桶,接著把其中一杯咖啡放在接待員桌上。
「卡拉,請慢用。我要在辦公室裡跟……」
他面向我,揚起一側眉毛,顯然在等我報上名來。
「雷諾茲。葛蕾絲.雷諾茲。」
「我要跟雷諾茲小姐談談。如果我按下緊急按鈕,就直接衝進我辦公室吧。」
她皺起眉頭。「你辦公室裡並沒有緊急按鈕。」
「沒錯。」他突然露出帶著邪氣的笑容。「嗯,那麼只好請妳雙手合十為我祈禱了。」
他對著我輕輕點頭,示意我跟他進辦公室。
我可以瞭解《垂根漢郵報》的記者為何會說他的辦公室乏味至極。裡頭凌亂不堪,四處散落著文件,檔案盒背脊的標籤上寫著無法判讀的文字。他為我清空疊在一張椅子上的書籍。我坐了下來,隨即用手摀住一側臉頰。
「妳看起來糟透了。去看了牙醫是嗎?」他問。
我點點頭。
「純粹是直覺。妳的表情很痛苦,臉也腫了一大塊。真是的,牙醫究竟對妳做了什麼?」
「我剛拔完牙。」
「真可憐。」
他站在桌子後頭啜著咖啡,從未別開目光。我注意到他拿著杯子的手指又細又長。
「妳得喝點東西,但我想該是不熱的東西吧,」他說。
他打開桌子抽屜,取出一瓶可樂。從他的動作跟突如其來的笨拙舉動看來,他似乎有些焦躁不安。我納悶他是否有跑步的習慣,是不是那種得隨時走動才能驅走心魔的類型。窗檯上放著幾只馬克杯。他選了其中一個,皺著眉頭懷疑地往杯裡瞧了瞧,接著把可樂倒進去。
「謝謝你,威特斯博士,」我說。
「叫我亞當就好,」他說。
我感激地喝著。甜膩的飲料發揮了功效,我覺得自在多了。
我環視辦公室,裡頭的私人物品非常少:沒有盆栽也沒有海報,唯一的圖像就只有桌上的一張照片。看起來像他,但年輕多了,裡頭的男孩穿著骯髒的工作褲,正在修理車子。望向窗外可見草坪跟櫻桃樹。
他看著我,用手耙過棕色的亂髮。他方才的舉動讓頭髮豎了起來,讓他看來一臉驚恐。
「妳為什麼想見我?」他問道。
「我有個女兒,她叫希薇。她不太好相處,有時還會說些奇怪的話……我在報紙上讀到關於你的報導。」
他點點頭,不發一語,等著我再說下去。
「我女兒的情況很類似報導裡的小男孩。所以我想,她會不會是記得前世的事?我是指,你覺得那有可能嗎?我之前從沒聽過那種事,所以我想問你……」
他推開桌子後頭的椅子坐了下來。他張開雙手,像是願意接受我或鼓勵我繼續說下去。因為他捲起了袖子,所以我看得見他手臂上細密的黑色毛髮。
「好,妳說吧。」
我把所有情況一一告訴他,像是希薇夜裡做惡夢的情形,她對水的恐懼,還有她老是畫同一幅畫,說蓮妮「不是真的蓮妮」,還有那個她似乎認得的小漁村。我把發生的一切都對他說了。我肯定連來這裡的路上都反覆排演著,不斷在心裡與他對談,儘管我們還沒碰到面。
他只打斷我一次。
「妳知道照片中的地方是哪裡嗎?」
「知道。我查到了。它就在愛爾蘭,就叫冷灣。」
他點點頭,看起來很興奮。他的眼睛突然瞪大了。
「幹得好。這很有幫助,」他說。
我很滿意自己查出了地點。
我稍作喘息,喝著杯中的可樂。麻藥就要完全消退,我感覺到嘴邊隱隱作痛。
「葛蕾絲,妳是個單親媽媽嗎?我沒聽到妳提起另一半,」他接著問道。
「是的,我是單親媽媽。」
「妳肯定很難受吧,得一個人處理所有問題……」
我順勢提起佩斯巴登女士要我們離開幼稚園的事,以及我對未來的恐慌。我事先並未排練過這段話;我原本並不打算提起這些事的。他把手肘靠在膝蓋上,傾身靠向我。他神情急切,在我說話的同時,一口咖啡都沒喝。
我敘述完時,他只坐在原位上看著我,用手耙著頭髮。
「所以你覺得呢?你能幫我們嗎?」我問道。
他這時才啜了一口咖啡,又細又長的手指環繞著杯緣,弄得保溫杯吱嘎作響。
「我們這裡專門調查一些無法解釋的事情。就是用科學的方式去驗證超自然現象。」
「但你們會怎麼做?你們要如何檢驗希薇說的話?」
「妳得把整個故事調查清楚。妳得非常客觀。妳得找出是否有左右當事人說法的證據。像是她是否有可能從任何其他來源取得故事的內容?或是有沒有可能是她從書上看來,或是從電視上看到的?」
「都不是。」
「她從沒看過任何相關的訊息嗎?」
「不可能。她從沒去過那個地方。再說,她從沒離開過我身邊,我也從來沒去過愛爾蘭。」
「那麼,有沒有可能是從書上讀到的?」
「我覺得不太可能。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家沒有那類書籍,幼稚園裡也只有童書。電視的話我就不是那麼確定了。老實說,我不會去檢查她看的每一個節目。如果我有很多事得做的話,就會讓她坐到電視機前。」
「好,所以電視是可能的管道,但看起來可能性不大。」
「那麼,如果影響當事人的資訊並不存在的話,你會怎麼做?」
他沉默了一會兒。
我滿懷希望,因為他能提供某種解決之道,幫助希薇放下所有奇怪的執念。或許他懂得報導提到的催眠療法。我納悶自己會如何看待那樣的做法,就是決定我同意嘗試,也同意他做任何能讓希薇變成快樂孩子的嘗試。
他放下手中的咖啡,往前靠近我一些。
「妳或許可以考慮把孩子帶到現場,如果妳覺得我這麼說有說服力的話。」
我瞪大了眼睛。我感到地轉天旋,全身戰慄。
「你是指,真的把孩子帶回他們似乎記得的地方?」
我不敢致信。我感到震驚,甚至憤怒。
「是的。」
我想著希薇看著照片時的模樣,那張臉寫滿了渴望,有時她甚至會把照片放在枕頭下才能安心睡去。
「但那麼做不會只讓情況變得更糟嗎?」
「我可以理解表面上看起來可能是如此。但這麼做通常對那些孩子有幫助。就好像他們回到那些地方之後,才能開始放下跟遺忘那段記憶。這大概跟我們所期望的不謀而合,就是幫他們去遺忘……」
「我實在聽不出這種做法有何邏輯可言,」我聽得出自己的語氣滿是抗議。「若你真想幫他們放下那段記憶,讓情境在他們眼前真實上演怎可能會有幫助?」
「證據顯示那麼做很有用。文件記載那麼做確實對那些孩子有幫助。」
我發現自己正搖著頭。
我想,我沒辦法這麼做。這麼做對希薇一點好處也沒有。如果連幼稚園的玩水遊戲她都無法處理了,又如何能承受這種做法?我感覺自己退縮了。他不懂。他不懂這麼做會有多糟。他怎麼能這麼做?我不知道自己來這兒是為了什麼。我不屬於這裡,不該跟這個聰穎卻過於熱切的男子在一起,更何況他還滿腦子駭人的理論。我這麼做真是太奇怪了。
「我實在不覺得那種方法適合希薇。我不敢想像那樣的情景。」
「不,我倒是可以想像。」
他眉間出現幾道銳利的線條,我感覺得出來自己讓他失望了。或許我的語氣太堅決了。我們之間流動著一股微妙的氛圍,就好似有什麼碎裂了一般。
「那麼,好吧。」我扣上外套。
他望向我,微微蹙眉,接著用手搓揉臉頰。
「等等,我能提供她一些諮詢。如果妳覺得那麼做有幫助的話。」
若是他早些提出這項建議,我立刻就會答應他,但現在我不是那麼肯定了。
「如果我們來的話,你會怎麼做?」
「首先我想檢查她基本的認知能力。」
「你是指,看她是否正常?」
他露出笑容。「是的。多少能這麼說。接著我會跟她談談她記得的事,就是她跟妳提過的那些事。這些孩子通常記得的記憶都很片斷。他們或許會提到某些地方,或某些人。如果妳走運,他們可能會記得一些名字,但大部分的孩子都不記得。所以我想搞清楚她說的事,或許也會要她畫張圖給我看……」
「我不知道。」
「妳可以先來接受幾次諮詢後,再做決定也不遲。」
我保持沉默。
「還有,妳當然無需付費。我們從來不向求助的人索取費用。」
他試著保持輕鬆的口吻,但我聽得出來他聲音中的急切。我看得出他有多想研究這個案例。
「她可能會很安靜。她可能一句話也不說。」
「沒關係,真的。」
他靠向我,凝視著我。他熾烈的目光讓我心意動搖,就快被說服。
我坐在椅子上一會兒,不知該怎麼辦。我想起在蓮妮的生日派對時,一個人站在窗邊望著漆黑的夜色。我想起凱倫說過的話,還有跟其他母親有多疏遠,以及之前熟悉的生活就要從指縫中溜走。
「我想,我們可以來參加幾次諮詢,」我緩緩說道。
「太棒了。」
他請我留下連絡方式。我給了他手機跟花店的電話。
「約拿與巨鯨?」他複誦道,彷彿這名字饒富興味似的。
「只是個花店的名字,」我說。
他注視我的時間總是久了些。
「妳在花店工作,我滿喜歡那種感覺的。」
我感覺自己臉紅了,試著想分辨這句話究竟是不是讚美。
對話結束,我拿起包包。但我還有件事想問他。
我猶豫遲疑地問道:「亞當,你覺得呢?你覺得那會是真的嗎?她真的有可能記得上輩子的事嗎?」
他放下手中的筆,表情深不可測。
「我曾經讀過古希臘的懷疑論者,他們認為世上充滿各種可能,所以堅持拒絕做出任何結論。我很認同這樣的觀點。所以,就說我也是個懷疑論者吧……」
聽起來像千篇一律的回答。這問題人們已經問過他無數次。
「但你心裡肯定有想法吧。」
「我可以告訴妳我對特定案例的想法,也就是證據指向何處。但即使妳著手調查的每一個案例看起來都像一場騙局,妳也不能就此論定未來的案例都無法說服妳……」
「那麼……如果連你都不肯定自己是不是相信這些事,為什麼還要從事現在的研究?」
他又露出帶著邪氣的笑容,稍做了思考。他很愛笑,但我感覺他的笑裡似乎隱藏著悲傷,彷彿他很容易就會受傷似的。
「好問題。理由可能很多。我跟蘇格蘭的一個大學女生有聯絡。她在吃下魔菇後曾有過所謂的『靈魂離體』經驗。她想瞭解……」
我們彼此都清楚他在逃避我的問題。我好奇是為什麼,但並不想逼問他。
他快速翻閱手中的文件。「那麼妳何時能來?」
「除了星期六以外,我每天都得工作。」
「那麼,我們就約星期六。」
「真的,這樣沒問題嗎?」
「我女朋友應該早習慣了。」
我知道他這麼回答是有原因的,是想事先把話說清楚。說來愚蠢,我卻感到有些失望。
「她也在這兒工作嗎?」
他點點頭。「她是生物物理學家。」
我想像著她的模樣:緊身牛仔褲跟蓬亂有型的頭髮,就像我在走廊上看到的那個接待員。她聰明、幸運,做的是精密而有價值的工作。我回顧自己的人生,跟我少數幾件擅長的事物:不過是把半邊蓮種到花盆裡,或者用碎絲布拼湊成小天使罷了。
他在收件匣裡翻找著東西。
「怎麼會這樣呢?我有辦法拿了一堆學位,卻老是搞丟日誌……」
但他還是找到了,下下星期六他有空。他在卡片上寫下日期跟他的手機號碼。
我拿起包包,打算離開。
他仍凝視著我,因為想到什麼而面露憂心。
「一定很辛苦吧,葛蕾絲?」他問。
他的聲音是如此溫暖,我發現自己竟哭了出來。
他似乎並不覺得尷尬。他找來幾張面紙,坐著等我整理好情緒。
我擦著淚水。面紙沾上脫落的睫毛膏跟嘴角的血絲。我沒法想像自己的模樣;我的臉肯定看起來又髒又怪吧。
「真抱歉,」我說。
他又像方才那樣,急切地靠向我。
「葛蕾絲,妳為什麼哭呢?」
「我覺得,她好像要從我身邊溜走了。」我不知該如何表達,掙扎著想說出對的形容。「有時她望著我的眼神,就好似她沒看到我,認不出我。她總是一臉拒人於千里之外的表情……她是我的女兒……我是指,老天,生下她的人是我……但怪的是,有時我覺得她並不真的是我的孩子。」我擤了擤鼻涕。「該死,我很抱歉。」
「所以妳感到徬惶無主。」
「嗯。」
「葛蕾絲,我不能向妳保證一定能解決問題……呃,對我自己也是一樣。事實上,我沒辦法給妳任何保證。我希望可以,但我真的做不到。」
「當然。我瞭解。」
我站起身,突然為自己剛才的失態感到尷尬。
「我送妳。」
經過卡拉桌前時,他咧嘴笑了。
「我還好好的,」他對她說。
他站在迴轉門前道別,把手輕輕放在我袖子上一、兩秒的時間。
我循著迷宮般的走廊走出大樓,想著亞當.威特斯的種種。這個態度熱切、外貌邋遢、神情緊張的男子,還有他對特殊主題的關注,以及他笑容裡隱藏的悲傷。老天,我究竟做了什麼?
一則廣告吸引了我的注意。裡頭有個站在寬闊岩岸邊的男子,厚實魁梧的身材像極了多明尼克,身上那件隨著他的腳步翻飛的綠色長風衣,正是多明尼克常穿的那種外套。我總是會反射性地注意到跟多明尼克相關的東西:他的圖章戒指、社團領帶、他抽的香菸的氣味。有時在街上,我會突然回過頭、心神恍惚,只因為突然到行經的路人身上帶著多明尼克的香水味。現在,看著那張照片,我彷彿能嗅到他身上的氣息,感受到他的撫觸。那則廣告是在幫一家專門販售戶外運動衣物的公司促銷產品。畫面的背景是空曠的海景:白色的沙灘、黑色的礁岩、明亮的天空。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