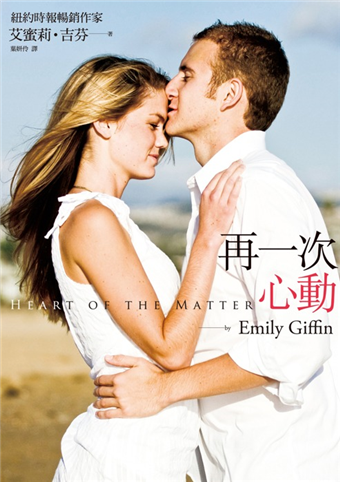◎《紐約時報》暢銷作家艾蜜莉‧吉芬的全新力作,在美國精裝版首印量高達 1,300,000 冊。
◎處女作《結婚友沒友》、《幸福來不來》已改編為電影,台灣6月上映。
當妳愛的人,已經有一個牽絆的時候,
妳該説服自己離開,還是奮不顧身地深陷?
泰莎與小兒科醫師丈夫結婚七年,依舊深深相愛,還共同養育了兩個孩子。儘管她媽媽再三告誡,她還是辭了工作專心持家。外人看來,她過著人人稱羨的完美生活。
薇樂莉是律師也是單親媽媽。她的兒子查理今年六歲,至今都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誰。薇樂莉經歷過太多失落,已經對愛情不報任何希望,甚至連友情也不敢奢望,將心思都寄託在兒子查理身上。但是在那通告知她查理發生意外的電話響起之後,她的世界完全被顛覆了。
查理參加同學家中舉辦的派對,結果意外灼傷,幾乎危及生命。薇樂莉在替兒子治療的醫生尼克身上看到夢想、找到希望;尼克對工作的熱忱也漸漸拌入他對薇樂莉的迷戀,但是,尼克卻是泰莎的丈夫。
這兩個原本互不相識的女人,生活因此有了意想不到的交集。她們被迫去質疑原來所摯愛的一切,面對自己未曾想像過的未來……
作者簡介:
艾蜜莉‧吉芬 Emily Giffin
畢業於北卡羅來那州的北威大學,之後在維吉尼亞州立大學進修取得法律碩士學位,曾在紐約擔任律師多年,後來搬到倫敦全心投入小說創作。
艾蜜莉的作品兼具精彩、悲傷及詼諧的特質,撫慰許多渴愛卻為愛所傷的心靈。處女作《結婚友沒友》(Something Borrowed)及其姊妹作《幸福來不來》(Something Blue),娓娓道來介於好友與男友之間糾結的愛情習題,男女主角的三角關係不僅不落入俗套,更令人動容。此二書已被改編為電影,女主角由凱特.哈德森飾演。
《再一次心動》中,艾蜜莉.吉芬依舊挑戰糾結難解的愛情習題,創造出一個情感揪人的三角故事,講述關於愛情、婚姻以及原諒。她呈現了兩個真實的女人,成功地捕捉了主角們複雜的情緒,讓我們在愛情的世界裡,最終發現究竟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譯者簡介:
葉妍伶
英國愛丁堡大學翻譯研究所、國立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口譯組。譯作有《消失的艾思蜜》、《愛情失憶症》、《愛情的抉擇》等書。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再一次心動》是艾蜜莉.吉芬目前最棒的作品。這本小說特別之處在於吉芬將讀者帶到情感深處……」
──《達拉斯晨報》
「這本小說從一開場就扣人心弦到最後驚訝的結局,而扉頁中沒有簡單的答案。」
──《西雅圖時報》
「艾蜜莉.吉芬的特色在於她總是有辦法深究感情。但在她的最新力作中,這位暢銷作家鑽研得更深入了……聰穎、幽默、鞭辟入裡,吉芬讓我們看到在愛情的世界裡,我們的所作所為可能很正確卻又錯得離譜。」
──《Family Circle》
「艾蜜莉.吉芬的最新創作深入探究複雜難纏的心的真相……生動的文字會讓你覺得好像在偷窺摯友的祕密。」
──《紅皮書》
名人推薦:「《再一次心動》是艾蜜莉.吉芬目前最棒的作品。這本小說特別之處在於吉芬將讀者帶到情感深處……」
──《達拉斯晨報》
「這本小說從一開場就扣人心弦到最後驚訝的結局,而扉頁中沒有簡單的答案。」
──《西雅圖時報》
「艾蜜莉.吉芬的特色在於她總是有辦法深究感情。但在她的最新力作中,這位暢銷作家鑽研得更深入了……聰穎、幽默、鞭辟入裡,吉芬讓我們看到在愛情的世界裡,我們的所作所為可能很正確卻又錯得離譜。」
──《Family Circle》
「艾蜜莉.吉芬的最新創作深入探究複雜難纏的心的真相……生動的文字會讓...
章節試閱
1.泰莎
每次當我聽到別人生命中的悲劇,我不會太專注在那場意外或病情上,也不會耽溺於震驚或悽愴的情緒中,我總會在腦海中回想發生悲劇之前,平淡正常的時刻。這些時刻交織成我們的生活。我們習以為常、認為理所當然的恬淡時刻,通常在悲劇發生之後便被人拋諸腦後。若將生命分割成悲劇前、悲劇後,那就是悲劇前的快照。
我可以清楚地想像三十四歲的女人在星期六傍晚走進浴室裡,伸手拿了她最喜愛的蜜桃香氛沐浴乳,正想著晚上去參加宴會時該穿哪一件衣裳,正盼望在咖啡店遇到的帥哥也會出席,她卻突然發現了左乳房裡的腫瘤。
或是那個愛家的年輕爸爸,準備開車載上小學的女兒去買花俏精緻的文具用品,隨著廣播裡的〈太陽出來了〉一起哼,不斷地對她說披頭四「絕對是史上最偉大的樂團」,而徹夜暢飲、滿眼血絲的青少年這時在他面前闖了紅燈。
或者是血氣方剛的高中足球小將,前途光明、趾高氣昂的他在大賽的前一天到燠熱的練習場上,他的女友和平常一樣在鐵欄外觀看。他對她眨眨眼,轉身一躍,接住那別人都接不到的高球,突然身體一扭,頭部朝下以最危險的角度著地。
我想生命總有一條脆弱的細線,分隔著平安與不幸的生活。我覺得在感恩的量尺上,我用小小的許願硬幣將那條線往後推,希望能保佑我,保佑我們,保佑露比、法蘭克、尼克和我。我們一家四口--是喜樂與擔慮的核心。
因此,當我丈夫的呼叫器在我們共進晚餐時大響,我不允許自己有一丁點怨懟或失望。我會對自己說,這只是一頓飯,只是一個晚上,儘管這是我們結婚紀念日,儘管尼克和我已經一個月沒好好相處了,嗯……可能已經兩個月了。和別人此刻所承受的苦痛相比,我根本沒什麼好難過的。我以後不需靠回憶才能體驗這一刻,我還是很幸運。
「該死,小莎,對不起。」尼克用拇指將呼叫器轉為靜音,然後撥撥他深色的頭髮。「我馬上就回來。」
我體諒地點點頭,看著老公以性感自信的步伐走到餐廳門口去回那通緊急的電話。他靈活輕快地穿梭在餐桌之間,我從他直挺的背脊和寬闊的雙肩就能看得出來他會聽到壞消息,接下來他就得去治療疾病,去拯救生命。他在那個崗位上最得心應手,這就是我為什麼會愛上他,結縭七年,生了兩個孩子。
尼克消失在眼角時,我深深呼吸、環顧四周,這時才注意到餐廳的細節:壁爐上灰綠色的抽象畫、燭光的柔和微光、隔壁桌傳來爽朗的笑聲,銀髮老翁和四個已成年的子女聚餐,另一位女士應該是他的妻子。我獨飲著卡本內香醇葡萄酒。
過了幾分鐘後,尼克回來了,他扮個苦臉,再度道歉,但這絕對不是最後一次道歉。
「沒關係。」我轉頭尋找服務生。
「我已經交代好了。」尼克說。「他會幫我們打包晚餐。」
我的手滑過餐桌,牽起他的手輕輕一捏。他也捏捏我的手,然後我們一起等著保麗龍餐盒裝的牛排。雖然我每次都很猶豫,該不該問他怎麼了,但我只在心中為那素不相識的病患默禱,也為孩子祈求,平安入眠。我想像著露比縮在被子下,發出輕柔的鼾聲,她就算在睡夢中也很調皮。露比是我們家早熟、無畏的老大,四歲的她表現得好像十四歲。她的笑靨迷人,深色的捲髮在自畫像裡捲度更立體,水藍色的眼眸是基因的奇蹟,因為我們夫妻倆的眼睛都是棕栗色。她年紀還太小,不知道女孩兒可以想要一些她得不到的東西。她打從出生的那天起就主宰了我們的家、駕馭了我們的心,讓我精疲力盡卻又滿心歡喜。她就和她爸爸一模一樣,固執、熱情、俊美得懾人心魂。標準的掌上明珠。
還有法蘭克,我們的小男孩,他的稚氣和甜美就連嬰兒海報也無法相比,就連超市裡的陌生人也忍不住停下腳步誇他幾句。他快兩歲了,但還是喜歡被擁抱,喜歡把滑嫩圓潤的臉頰往我頸子貼,全心全意地愛著媽媽。我才不偏心,我曾經私下對尼克保證,當時他揚著嘴角說我是壞媽媽。我真的沒偏心,除非說我最愛的是尼克,當然那是不一樣的愛。對孩子的愛沒有條件、沒有終點,如果發生急難,我一定會先救小孩,假設他們在露營時被響尾蛇咬了,而我背包裡又只有兩份血清的話。不過,世界上我最想說話、靠近、凝望的還是我老公,我在初次相遇時才首次體會這種感覺。
過了一陣子,我們的晚餐和帳單都送來了。我和尼克站起身,離開餐廳,走進星光閃閃的暗紫夜裡。十月初的秋季感覺像隆冬,波士頓也不會這麼冷。我穿著喀什米爾長大衣仍不斷哆嗦,尼克將停車卡拿給泊車人員,然後我們進了車裡,離開市區,聽著尼克收藏的爵士音樂,靜靜地往威勒斯里駛去。
三十分鐘後,我們停在鬱鬱青青的車道上。「你覺得今天會忙到多晚?」
「很難說。」尼克把車停好,側過身來吻我的臉頰,我把臉偏過去,四脣輕觸。
「結婚紀念日快樂!」他低語。
「結婚紀念日快樂!」我說。
他身體往後退,我們四目相對,他說,「晚點再繼續?」
「等你。」我試著勾起嘴角,輕步走下車。
我還沒關上門,尼克將音量調高,戲劇性地為今晚畫下逗點,準備工作。我進屋時,爵士樂手文斯‧葛拉迪的〈落葉搖籃曲〉迴盪在我腦中,我付錢給保姆、去看看小孩、換下裸背黑洋裝、靠著廚房流理臺吃掉冷牛排後,樂音仍繼續悠揚。
過了一陣子,我拍拍雙人床上尼克那一側,蜷縮在自己的這一側,孤身在黑暗中,回想起餐廳裡的那通電話。我閉上眼睛,不確定厄運是否總是攻其不備。或者,我們在同情、擔心的情緒下,其實已經隱隱察覺到生命的低潮即將來臨?
我沉沉睡去,沒有答案。全然不知過了這晚,我竟跨越了那條細線。
2. 薇樂莉
薇樂莉知道她應該拒絕──或更精確地來說,她應該堅持拒絕,查理之前求她求了十幾次,希望能去參加派對,她都不答應。他用過各種策略,包括「我沒有爸爸、我沒有小狗」這種訴諸她愧疚感的做法,當這些手段都失效時,他轉而向傑森舅舅求救,只有他才能說得動薇樂莉了。
「噢,小薇。」他說。「就讓小朋友去玩玩嘛。」
薇樂莉對她的雙胞胎哥哥噓了一下,朝起居室指一指,查理正在那裡用樂高積木打造精巧的地牢。傑森又逐字不漏地重複剛剛說過的話,這次很刻意地壓低音量用氣音說話,薇樂莉搖搖頭,說六歲小孩還不到可以去朋友家過夜的年紀,尤其是在戶外的帳篷裡。這種對話很頻繁,傑森總是嫌他妹妹對獨生子保護過度,又要求太嚴格。
「沒錯。」傑森嬉皮笑臉地說。「我聽說波士頓市區裡野熊攻擊人類的頻率愈來愈高了。」
「不好笑。」薇樂莉說完便解釋她對那一戶人家的瞭解不夠深入,就她從旁觀察的結果,她不太喜歡那一家人。
「我來猜猜──他們很有錢嗎?」傑森採激將法,他的體型很纖瘦,牛仔褲一直往下滑,露出內褲的褲頭。他拉拉牛仔褲,繼續問,「妳不希望查理和那種人混在一起?」
薇樂莉聳聳肩,微笑是她宣布投降的方式,真不曉得他怎麼會猜中。是她太好猜了嗎?她心中有個謎團,儘管她自問了一百萬遍也沒有答案: 兩人明明在麻州南橋區同一片褐瓦下長大,她和她的雙胞胎哥哥怎麼會差那麼多?他們小時候的鄰居都是篤信天主教的愛爾蘭移民,兄妹兩人是彼此最要好的朋友,一直到十二歲才擁有自己獨立的寢室,傑森搬進通風良好而冷颼颼的閣樓,讓妹妹有更多空間。他們倆是典型的愛爾蘭移民第二代──深色的頭髮、湛藍的雙眼、細緻的肌膚──連外表都很像。不過,他們的媽媽說傑森帶著微笑爬出子宮,而薇樂莉卻愁眉苦臉,這現象一直持續到他們的童年時光都沒變。薇樂莉害羞地獨來獨往,而早她四分鐘出生的哥哥大方又健談,頂著人氣王的光環。
而現在,三十年後,傑森和以前一樣逍遙快樂,隨和樂觀,不斷嘗試不同的興趣和工作,對自己的外表充滿自信。他們高三那年父親過世後,他就出櫃了,從此更添一份自得。他是很典型的那種潛力無限但表現平凡的人,他目前在燈塔山的咖啡廳裡工作,和進門的每一個客人打成一片,走到哪裡都能交朋友,一如從前。
而薇樂莉大部分的時候防備心都很重,總是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儘管她成就非凡。她很努力要離開南橋區,高三時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就讀安姆赫斯特大學,獲得全額獎學金。念完大學後,她一邊準備法學學校入學考試,一邊在波士頓的律師事務所擔任法務助理,存下法學院的學費。她不斷地對自己說,其實她和其他人一樣好,又比大部分的人聰明,可是她離開家鄉後就一直沒真正體會過歸屬感。而且,她的成就愈高,她就愈明確感受到自己和老朋友的距離,尤其是她的姊妹淘蘿瑞,她以前的家離小薇和傑森家只有三戶。那種疏離感,剛開始很細微、很難察覺,但某年夏天在蘿瑞家烤肉時,那種感覺累積到高點,她們大吵一架。
酒過三巡,薇樂莉不經意說出在南橋區的生活令人窒息,蘿瑞的未婚夫更讓人無法靠近。她這麼說只是好意,企圖暗示蘿瑞搬到她劍橋區的小公寓來一起住。不過她的話一出口就後悔了,接下來那幾天她努力收回她所說的話,並不斷地道歉。可是蘿瑞本來就脾氣火爆又固執拗強,她因此和薇樂莉絕交,並且在以前的朋友圈裡散播流言說薇樂莉是個勢利鬼。她們以前的朋友就像蘿瑞一樣,在同一個社區長大,幾乎都嫁給高中時期的男友,週末總是去那幾間酒吧小敘,平常則朝九晚五地做著和他們爸媽相同的工作。薇樂莉盡力反駁各項指控,設法維持表面和諧,但始終沒搬回去南橋區居住,所以她也難力挽狂瀾。
就是在這種孤單寂寞的時刻,薇樂莉會做出一些她無法解釋的舉動,做出她發誓自己絕對不會做的事──也就是愛上錯的人,在他提分手前把肚子搞大,害她無法按照自己的規劃上法學院就讀。多年之後,她經常懷疑自己是否潛意識中破壞了逃離南橋的計畫,而為自己開創另一種人生──或許她只是覺得哈佛法學院的錄取通知函不配和超音波胎兒照一起貼在冰箱上。
不管怎樣,她無法勉強自尊向蘿瑞和其他兒時玩伴低頭,大著肚子的她又羞於面對大學同學,也不敢在哈佛結交新朋友,所以她比過去更孤單,一個人勉力一邊照顧新生兒,一邊唸完法學院。傑森知道她剛當媽媽的那幾個月、那幾年有多麼辛苦。他可以看出她在工作、壓力、疲倦下硬撐,看著他妹妹含辛茹苦地為生活打拼,他敬佩得五體投地。但他不明白為什麼她要隔絕自我,犧牲各種社交生活,只有一些平淡如水的朋友。她總是推托說沒時間,再加上她所有心思都在查理身上,不過傑森不相信這些理由,三不五時就打電話約她出去,總是說她拿查理當擋箭牌,不願意面對風險,只怕被人拒絕。
她這時想起她哥哥的論調,轉身面對火爐,煎出完美對稱的圓形鬆餅。她不是大廚,不過因為打過工,所以很擅長做各種早餐料理。當時她在餐廳當服務生,迷戀著餐廳裡的一個快餐廚師。那件事已經過了很久,不過對傑森來說,她還是比較像當年那個為客人續咖啡的小女孩,而不是身兼母職的優秀律師。
「妳這叫做反向勢利。」傑森繼續說。他抽出三張紙巾當做餐巾,然後幫忙擺餐具。
「我才不是。」薇樂莉反駁。她覺得蘿瑞的指控很諷刺,覺得自己被困在兩個世界中:她在南橋很勢利,在威勒斯里則反向勢利。她仔細思索「反向勢利」這個新詞,在腦中反覆地辯證,怯怯地承認自己開車經過峭壁路上氣派的宅邸時,總先入為主地假設住在那裡的人最好也不過是膚淺,最差的可能都是詐騙之徒。彷彿她在潛意識中將財富與卑劣人格畫上等號,除非那些陌生人能夠舉證說明他們沒那麼惡劣。她知道這樣並不公平,不過她生命中有太多不公平。
反正,丹尼爾‧克羅福特與柔蜜‧克羅福特上星期在學校開放家長參觀時,並沒有證明她的看法錯誤。他們就像朗米爾私立小學的家長一樣,聰明風趣、談笑風生。可是當他們掃視她的名牌,和她閒話家常時,薇樂莉隱隱感覺到他們的眼神不在她身上,他們的視線落在後方,他們在教室裡搜尋其他人──更好的人。
就連柔蜜提到查理的時候,她的口氣裡有種虛偽做作、高人一等的調調。「我們家的葛瑞森最喜歡查理了。」她刻意將一縷淡金色的髮絲塞到耳後,然後停格,纖手留在空中,似乎要展示無名指上碩大的鑽石。薇樂莉來自礦產豐富的小鎮,不過她也從沒看過那麼耀眼的寶石。
「查理真的也很喜歡葛瑞森。」薇樂莉雙臂交叉在胸前,她穿著桃粉紅色的襯衫,很後悔自己沒穿上碳灰色的套裝。不管她多麼努力,不管她花了多少錢治裝,她好像總是穿錯衣服。
這時,兩個小男孩牽著手跑步穿越教室,查理帶頭往倉鼠的小窩跑去。對任何一個旁觀者來說,他們看起來就像是一對好朋友,毫不羞赧地喜歡著對方,那麼為什麼薇樂莉會覺得柔蜜不誠懇呢?為什麼薇樂莉不能給自己和兒子多一點肯定?她正暗自尋思,這時 丹尼爾‧克羅福特拿著裝綜合果汁的塑膠杯走過來加入她們的談話,手輕輕搭上妻子的背。她經常觀察已婚夫婦,所以很清楚這個細微的小動作代表著什麼意思,同時讓她又嫉又悔。
「親愛的,這就是薇樂莉‧安德森……查理的媽媽。」柔蜜立刻介紹她,讓薇樂莉覺得他們可能前一晚就討論過她──還有為什麼家長名冊上沒有登記查理的爸爸。
「噢,當然了,對。」查理點點頭,帶著董事長的氣魄和她握手,並以短暫、冷漠的眼神看了她一下。「妳好。」
薇樂莉也打個招呼,然後空洞地閒聊幾句,接著柔蜜便拍拍手說,「對了,薇樂莉,妳有沒有收到邀請函?葛瑞森要辦個派對,我幾個禮拜前就寄出去了。」
薇樂莉覺得自己回答時臉色發燙。「有,有啊,真謝謝妳。」她真氣自己沒回覆,好想揍自己一拳,她敢說沒即時回覆邀請函一定惹惱了柔蜜,就算那是小孩子的派對。
「那麼?」柔蜜追著問。「查理能來嗎?」
薇樂莉好猶豫,他覺得自己在這個妝扮無瑕、自信過人的女性面前屈居下風,好像回到了高中歲月,小米送她一根菸,還要用櫻桃紅的重機車載她一程的感覺。
「我不確定,我得回去查查行事曆……下個禮拜六,對吧?」她支支吾吾地,好像她真的有上百個行程要安排。
「沒關係。」柔蜜笑顏如花地和另一對夫婦打招呼,他們剛帶著女兒走進教室。「親愛的,你看,艾波和羅勃來了。」她輕聲地對丈夫說,然後碰碰薇樂莉的手臂,草率地對她露出最後一抹微笑說,「真的很高興認識妳,我們都很期待查理下星期六能來。」
兩天後,她手中拿著帳篷形狀的邀請卡,按下克羅福特家的電話。她無法解釋自己為何在等電話接通時如此緊張──她的醫師說這是社交焦慮障礙──當她聽到自動答錄機要她留言時又感到很安心。雖然她之前一直反對,不過她以高八度的聲音說,「查理很期待能參加葛瑞森的派對。」
她帶著查理,提著他的恐龍睡袋和太空船睡衣到克羅福特家。兩個小時後,天色還沒暗,她接到了電話,接下來她滿腦子都不斷重播「很期待」、「很期待」,而不是柔蜜‧克羅福特說的「意外」、「燙傷」、「救護車」、「急診室」。那些單字模糊地傳進她耳中,她無法思考,急忙套上外衣、抓起錢包、飛車衝進波士頓市區。她在車上打電話給她哥哥的時候也無法大聲重述這些字句,無理由地擔心著一說出口,這一切就會成真。
她只能簡短地說,「過來,快點。」
「去哪?」傑森問。他背後的聲音很吵雜。
她沒回答,所以他關掉音樂,用更急促的聲音問,「薇樂莉?去哪裡?」
「麻州綜合醫院……查理出事了。」她回答地很忙亂,一心只想著用力踩下油門,現在已經比速限更超出三十英里。
她指節發白、手心冒汗地抓著方向盤,剛闖了紅燈,又闖了下一個,不過內心卻異常地冷靜。這感覺好像她看著自己,或像是看著別人。原來這就是大家會做的事:他們會打給親愛的家人、會一路狂飆到醫院、會連續闖紅燈。
查理很期待,她又聽到自己的聲音。她走進醫院,順著指標來到急診室,不知道自己怎麼那麼粗心,穿著居家服,捧著微波爆米花,看著丹佐華盛頓的動作片。她怎麼會不知道利維摩爾的豪宅區會發生什麼事?她為什麼沒依循自己的直覺?她大聲咒罵,又粗啞又洩氣的「他媽的」,她滿心愧疚,後悔地抬頭望著這棟磚紅色的建築物如幻影般矗立在面前。
接下來那一夜的經歷都很匆促朦朧──由不連貫的跳躍時刻拼湊起來,一點也不平順。她記得自己把車停在路邊,儘管旁邊的告示寫著「禁止停車」,然後她在雙層玻璃門後面找到了臉色蒼白的傑森。她記得醫院裡幫病患分科的護士很冷靜、很有效率地在電腦上打出查理的名字,再讓另一位護士帶他們走下漫長的走廊到兒童加護病房燒燙傷專科,一路上都能聞到消毒水的味道。她記得在路上碰見了丹尼爾‧克羅福特,停下腳步讓傑森問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她記得他內疚的、模糊的回答──他們在生營火。我沒注意到──她腦海中浮現出他忙著用黑莓機或只顧著欣賞庭院造景,而背對著營火和她的獨子。
她記得看到查理那靜止的、小小的身體時恐怖的第一眼,他已經插管,並施打鎮定劑了。她記得他藍色的嘴脣、被剪開的睡衣、右手與左臉上白色的繃帶。她記得機器的嗶嗶聲、呼吸器的嗡嗡聲、還有忙碌而冷淡的護士。她記得自己握著兒子完好的那隻手,向她早已遺忘的上帝祈求,然後聽到醫護人員說查理不會死。
但最最重要的是,她記得那個走進來替查理檢查的男人,當時似乎是半夜,她的驚恐已漸漸消退。她記得他溫柔地掀開查理臉上的紗布、露出繃帶下灼傷的皮膚。她記得他領著她走到長廊盡頭,轉過身面對她,輕啟雙脣,開口說話。
「我是尼克拉斯‧盧梭醫師。」他的聲音低沉而緩慢,「我是全世界最頂尖的小兒整形外科醫師之一。」
她望向他深邃的眼眸,輕輕一嘆,心神一舒。她告訴自己:如果她兒子仍命在旦夕的話,醫院才不會派整形外科醫師過來。
他沒事。他不會死。她看著醫生的雙眼就知道。這時候,她才想起來他的生命從此丕變了,這一夜會在他的身上留下永恆的傷痕。她感覺到一股堅強的毅力,她要保護查理,不管要付出多少代價,因此她聽到自己問他是否能修復查理的手和臉,是否能讓她的兒子恢復光彩。
「我一定會為您的小孩付出全力。」他說,「但我希望您記得一件事。妳願意為我牢牢記住嗎?」
她點頭,以為他要她別期待奇蹟。她其實根本不敢奢求奇蹟,這一輩子都不曾奢望過。
但盧梭醫生凝望著她的眼眸,說出她此生絕對不會忘的一句話。
「妳的兒子很俊帥。」他對她說。「他現在就已經很帥了。」
她再點點頭,相信他,信任他。
就在那時,撐了很久很久以後,她的眼淚才首度滑下來。
1.泰莎
每次當我聽到別人生命中的悲劇,我不會太專注在那場意外或病情上,也不會耽溺於震驚或悽愴的情緒中,我總會在腦海中回想發生悲劇之前,平淡正常的時刻。這些時刻交織成我們的生活。我們習以為常、認為理所當然的恬淡時刻,通常在悲劇發生之後便被人拋諸腦後。若將生命分割成悲劇前、悲劇後,那就是悲劇前的快照。
我可以清楚地想像三十四歲的女人在星期六傍晚走進浴室裡,伸手拿了她最喜愛的蜜桃香氛沐浴乳,正想著晚上去參加宴會時該穿哪一件衣裳,正盼望在咖啡店遇到的帥哥也會出席,她卻突然發現了左乳房裡的腫瘤。
或是那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