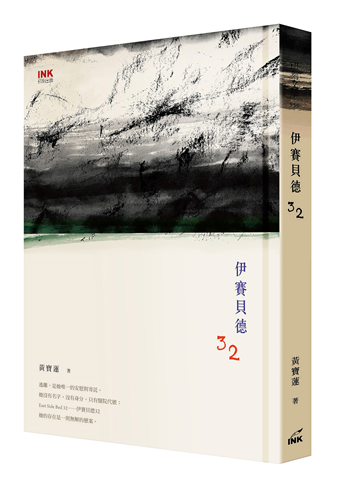黑貓過街
所有的人都用一種溫柔但又迫切的聲音呼喚CHANTELLE,彷彿CHANTELLE是個寵物、天使或什麼易受驚嚇的小東西。CHAN—TEL—LE,CHAN—TEL—LE……。
夜裡近十二點,街上還有些動靜,一種屬於夏天的活力,什麼都難以安適的躁動。漸漸的,那個溫柔迫切的呼喚變成焦慮絕望,一聲聲穿過夜空,穿透人們的睡夢,在街頭巷尾回響著。
CHAN—TEL—LE,那麼清晰的音節,拖著長長的尾音,延蕩到虛無廣渺的夜幕裡。
CHANTELLE,一個被人呼喚、想念、渴求的美麗名字!此時在哪裡?讓呼喊她的人如此焦慮不安?誰是那個懷春的少男?如此魂不守舍?誰又是那個情竇初開的少女?兩顆躁動的心彼此渴求,有如春臨大地的一場求歡盛典,彼此熱切的尋找著相互的秘密訊息。
夜更深了!街道盡頭閃進來兩道刺眼的光,一輛白色汽車停在路邊,有節奏富韻律的按了三下喇叭,彷如暗語呼喚CHAN—TEL—LE。
一個纖瘦高 的黑美人出現在巷口,貓似的妖嬈身影,身上的薄紗還帶著夜夢的纏綿,一閃身就進了車裡,一眨眼,汽車揚長而去。
這條街叫瓦特斯維爾街,幽深靜秘,有個T字型的路口,教堂在路的盡頭,伊賽貝德的窗口面對教堂的鐘塔,塔頂經常聚集著鴿子,終日聒噪不休不時泄下粉白糞便,有的飛到療養院前的水池邊,洗澡、戲水,有一對恩愛的鴿子夫妻,總是形影不離,讓人相信:動物的世界也有忠誠和愛戀。
沿著瓦特斯維爾街兩旁是巨大的馬栗樹,下午三點的放學時分,樹下定時來了賣冰淇淋的小販以及爭先恐後搶著買冰淇淋的孩子們;包著頭巾的穆斯林女子和她坐在輪椅上的白髮丈夫;一個手抱泰迪熊的女孩,粉紅色的髮結,緊蹙的眉頭,謹慎靜默的眼睛,守著難以參透的秘密。
伊賽貝德總是擔心女孩會遇見壞人,遭人在幽暗的花叢裡、廢棄的空屋內或什麼陰暗的角落強暴姦污,或者意外發生車禍,從此半身不遂或昏迷不醒,所有年輕漂亮的女子都讓她心驚,好似紅顏是命定的罪愆。
西北半球短暫的夏日一閃即過,秋風帶來早到的寒意。轉眼,葉落霜降,馬栗樹上的松鼠忙上忙下,撿拾熟落的栗子。那深夜裡呼喚CHAN—TEL—LE的聲響依舊持續,而且益發迫切,加倍深遠。
整個季節,伊賽貝德是這樣莫名憂心著Chantelle,不時探頭往窗外察看。除了一隻經常暗夜出沒的黑貓,空氣中偶有浪蕩的耳語從漆黑的角落傳來,秘密幽會的歡愉神色!
伊賽貝德無法安適,Chantelle必定是個浪蕩妖嬈的女子,夜裡那一聲聲神秘的叫喚,同時喚醒她內心莫名的慌亂和恐懼,彷彿在她靈魂深處意識無法觸及之處,存在著另一個時空,她在那裡曾有過另一種人生?
她摸黑下床來到窗前,掀開窗簾又看見那隻黑貓匆匆橫過馬路。夜裡下過一場雨,地上的水痕映著街燈,一個濕濕的貓影子,提著腳尖,芭蕾舞孃似的輕盈漫步,有如夜訪秘密戀人,抑制著興奮與急躁,準備去偷情。
黑貓過街,這件事必然具有某種寓意,黑色的迷信或是死亡的暗示?必然有件她所不知道的事在秘密中發生……進行!
露西亞:
我又做噩夢了!幾乎又瀕臨窒息,這一次差一點就要被水淹死。夢裡,我要去花東,山路上到處發大水,濁浪翻滾,橫木竄流,人畜都在倉皇中死命逃生……。
露西亞,妳一點都不相信這些夢境。妳那麼篤定,那麼堅信科學與客觀的真理,不肯正視靈魂深處可能的晦暗幽深曲折神秘狂野浪蕩或邪惡。妳看到的生命只是從生到死一條直線,陰陽正負因果善惡得失用邏輯就可以推演盤算。
妳說我這個夢遊者,用一種不肯苟同的輕蔑。
露西亞,我渴望人生是一場電影,這樣,我可以根據想像描繪自己的身世,編撰自己的愛情,讓生活的空虛與生命的殘缺一一都獲得補償!
時間的魔法
一日,一日,又一日。
報紙和牛奶按時送抵大門,郵差總是大聲說日安!光影落在桌燈前的燈罩上,就快是下午茶時刻;那是秋冬日光短照的時節;一到夏天,長長的日影在書桌前久久的駐留,時間變得緩慢而悠長,日子變得孤單而寡味。
伊賽貝德倚著窗聆聽走廊盡頭由遠而近的腳步聲,露西亞的內八字,腳板著地略帶遲疑,側肩的背包讓她的身體在走路時微微前傾,步伐因此有了輕重節奏,老遠就能辨識她的到臨,甚至能從步伐的快慢聽出她的心情;快樂的時候,她的腳尖提起腳步跳躍,疲累的時候腳跟沉湎湎在地面拖磨。
伊賽貝德每天總是皺著眉頭醒過來,天還黑著呢!隔鄰老先生清晨按馬桶嘩啦啦的沖水聲,固定是她一天開始的序曲。
初冬的天色亮不起來又暗不下去,曖昧難分,晨昏莫辨。她習慣在房間裡收拾衣物,穿好鞋襪,隨時準備著要出發,彷如遠方海岸港口有渡輪即將啟航,她站在窗前眺望、癡想,用一種深邃悠遠又期待的神色。
書桌前有本黑皮記事簿,腦子裡有念頭冒出來的時候,她就在上面塗塗寫寫,都是些瘦長歪斜,集體左傾的怪異字體,不是象形甲骨也非拉丁外文,最可能是腦海裡閃現的浮光掠影,她所極力要緝捕歸案的潛逃的意識片斷。
大部分時候,她坐在窗前喝茶看窗外的天色,生活就是不斷醒來再過同樣的一天,她已經無法分辨昨天、今天;重複而單調的作息,使時間失去日月星期,只剩下季節與冷熱,時間以如此鬼祟的步伐侵蝕著她的內裡器官,頑固而執著的伴隨著她每天的二十四小時……。
一定是時間施了魔法,以及鏡子的奸險和惡意,原本纖細窈窕的青春女子,不知不覺就成了慵懶嗜睡的婦人;伊賽貝德不喜歡鏡子,總是迴避和鏡子打照面,那是她逃避一切不想面對事情的方法。
露西亞:
時間都去了哪裡?我睡這麼多,那睡夢便成了我的生活。夢比醒更真實。
夢裡,有一條河流,河面上粼粼波動的水光是晃蕩流動的書法,河底是閃爍的金沙,四周黑黝黝,只在遠處泛著幽藍晦澀的光影,夢裡不用眼睛,夢是黑白的;但是,醒來我就看見蝴蝶黃色的翅膀,停在灰藍的背景裡……
我為什麼在這裡?而不是在那裡?
無名女子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凌晨三時許,倫敦近郊的史坦斯特(Stansted)機場主航站入境處的女廁所裡,被人發現一個昏迷倒地的年輕女子,身穿芥末色呢外套、牛仔褲、運動鞋,身上沒有明顯傷痕或遭受暴力襲擊的跡象,現場也沒有打鬥、掙扎的混亂情形,身上沒有任何證件。
女子被救護車送往機場附近的霍爾斯特德醫院(Halstead Hospital)。急診室裡,女子臉色蒼白、脈搏快而微弱,四肢冷涼;醫護人員初步判斷是:血糖過低造成的昏迷或嚴重脫水造成低血容量休克。
經過靜脈注射葡萄糖溶液後,女子脈搏逐漸恢復正常,四肢回暖,意識略微清醒;醫護人員問女子姓名年紀,女子表情困惑遲鈍,眼神空洞迷茫,彷彿剛從另一個時空異境降臨,對周遭一切全然陌生,對醫護人員的提問一無反應。
女子身上沒有任何證件、行李、現金,無法確知是昏迷後失去隨身物品?還是遭打劫失去所有?身上的衣著、牛仔褲、鞋子,都是世界通行的無國界品牌,沒有任何地域特徵,即使衣服上標示著Made in China,也無法說明她來自中國,中國產品已經遍布世界市場,警方無法根據她身上衣物查詢與她身分來處相關的線索。
血液檢驗結果除了低血糖之外,還顯示藥物過量,舞會轟趴裡常見的一種讓人暫時失憶的迷魂藥(Rohypnol),過量使用可能引起腦部缺氧造成永久性的傷害。
是日晚,女子並未從醫生所推測的藥物過量裡醒轉過來,顯然還有某種精神或腦神經方面的問題,需要更進一步的診斷,有可能是一種病源未確定的腦炎,一種罕見的自體免疫異常疾病,病人會有發燒、頭痛、神智不清、幻覺、癲癇以及認知缺損,需要觀察臨床表現、實驗數據、加上腦波磁振造影來補助判斷;如果腦部磁振造影顯示異常,就需進一步做腦脊髓檢查;所有這些情況都需時間,不是幾日內可以查驗清楚。
關鍵是:病人真實身分無法確知,沒有姓名國籍出生年月,醫院不能提供更進一步的診斷治療。醫護人員推測:女子也許有語言障礙,無法表達自己,特地從新移民較多的婦產科請來雙語社工露西亞嘗試和病人溝通;露西亞來自中國哈爾濱,母語之外能說英語和簡單的韓語、日語,在醫院裡專門協助需要語譯的新移民婦女,特別是產科的孕婦和新手母親。
露西亞有一張紅潤又喜感的臉,聲音軟軟的像大提琴悠緩的傾訴,聽了就叫人安心。
「我叫露西亞,是這裡的社工,妳好嗎?」露西亞關切的伸出手握住女子的手。
女子警戒的將被握住的手縮回,眼神淡然,完全沒有與人交流的意願。
「別擔心!一切都會沒事的,我是來幫助妳的,能不能告訴我,妳叫什麼名字?」露西亞輕聲細語,生怕驚嚇了她。女子無動於衷的沉默頑固堅決,沒有一絲通融的縫隙。
「妳能說漢語嗎?明白我的話嗎?」露西亞嘗試說中文。女子眉角輕蹙,好像不同意不情願不理解不高興也不回應。
「o gen ki de su ka!」露西亞於是改用日語問好。
女子面無表情。露西亞繼續又問了她姓名、國籍,女子依舊封鎖在自己的世界裡,不與露西亞做眼神接觸,拒絕和眼前的世界發生關聯,孤零零躺在病床上,像個被遺棄人間的域外人。
露西亞繼續又試了韓語,女子斗大的眼神空茫茫望向窗口,彷彿在祈求上天的憐憫和指示。
露西亞一點也不氣餒,女子年紀看起來和她不相上下,讓她很自然多一份親切和關懷,私下裡也好奇她的身世和際遇;在露西亞的想像裡:這麼年輕不外就是桀驁不馴的青春叛逆或情傷心碎暴走天涯的浪女,緣於任性或者過度的天真以致遭逢原本不該發生的不幸,偏離了人生正途社會常軌;女子姣好的面容遍布滄桑的印記:嘴唇乾裂,嘴角潰爛,粗糙的皮膚消瘦的身形在在顯示著飲食的失常、生活的失序。
露西亞一心想讓她開口說話,偶爾,女子現出陶然迷醉的神遊狀,有如夢境中盡是美酒佳餚,天使正在為她跳舞歡唱,讓露西亞心裡生出一線希望,以為她會忽然開口說出什麼話來。
然而,幾次嘗試皆無所獲,女子似乎閉鎖在自我的世界裡做神秘的遨遊;為了讓她開口說話,露西亞特地帶了份中文報紙,一字一句念給女子聽:「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社會主義陣營崩潰,冷戰時代正式結束。美國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認為共產政權必定滅亡……。」
女子依舊無動於衷,不知是聾?是啞?是語言障礙?或是遭受巨大變故,情緒受刺激,致使本能的防衛系統驟然關閉?
露西亞在紙上寫下自己的名字,然後把紙和筆放在她手上,讓她寫下自己的姓名,女子空茫的眼神落在筆記本上又漫無目的的飄離。
那一點點投落紙筆的視線,給了露西亞極大的希望,代表著她仍能感知外界的事物,只是無法開啟心扉和外面溝通。露西亞一點也不放棄即使只有一點點的希望,她迫切的想知道女子的身分,從何處來?要往何處去?路上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一個人夜裡昏倒在史坦斯特機場?
兩星期以來,露西亞每天下了課、輪完班就匆匆趕到療養院探望女子,嘗試各種方法和女子溝通,給她聽羅大佑、崔健、蔡琴一直聽到蕭邦、舒伯特甚至巴布‧狄倫、披頭四。可
惜種種努力都徒勞無功,女子的狀況毫無進展也無變化,除了眼神偶爾投向窗外或門口來去的人,她的沉默比鐵堅固,比石頭頑強,幾乎無法攻破那道防衛性的銅牆鐵壁。
兩個星期裡,女子像白日夢遊者一般,躺在急診室東邊走廊的床位,那裡沒日沒夜亮著慘淡的日光燈;除了吃飯、睡覺、上廁所,女子幾乎完全活在自我內化的封閉世界裡,除了偶爾望向窗外綠色的田野和遼闊的天空。唯一發出聲響的時刻就是夜裡噩夢,不時會聽見她驚惶的叫喊和急迫的呼吸。
露西亞不忍心看著那麼年輕的生命遭逢如此變故,她費盡心思想讓女子開口說話,渴望了解她的遭遇,分擔她的心事;也許因為年紀相仿,露西亞對女子有份特殊的親近感,甚至以為女子會是她的族類;但女子帶琥珀光澤的眼眸、凹深的眼窩又非典型的亞洲品種,看來看去居然有點像台灣的原住民;露西亞在醫院的同事有個來自花蓮的阿美族,眼窩也是深深的,眼睛大大的,說話帶著旖旎的柔美聲調,唱歌特別好聽。
露西亞對女子不時出現的夢囈突發奇想,靈機一動帶了袖珍錄音機,連續幾夜守在女子床邊,斷續錄下支離破碎的夢中囈語,興致勃勃送到大學語言研究中心,讓語言教授從口音和環境地域尋找蛛絲馬跡,夢中譫語當然未必有根據也不一定能採信,然而作為參考資料肯定有所助益。
語言研究中心的史密斯教授在做過分析之後判斷,女子的囈語略帶中國南方口音,有點接近福建山區一帶臨近客家語系的腔調,史密斯教授推測:有小小的可能是台灣島上的原住民。為此,露西亞興奮的找來阿美族同事利瑪一起去醫院。
利瑪一見女子就跟她說:「Kapah kisu haw? Maolahay kako tisowanan!」妳好嗎?我愛妳!利瑪說話像唱歌,天生還有一副好嗓子。
女子瞠著眼眸望著利瑪,沒有歡喜亦無退避,利瑪溫柔的握住女子的手,專注又深情的為她唱了一首〈娜奴娃情歌〉。
女子目不轉睛的看著利瑪;受了鼓舞的利瑪接著高歌一首貝多芬的〈歡樂頌〉,女子的眉毛隨著高亢的音符揚起又落下,臉上浮現一絲難得的短暫的笑意,彷彿終於回到人間;可惜,僅止剎那的靈光一現,聽完又恢復無知無感的漠然狀態,和眼前的世界無所關聯。
一晃兩個月,露西亞期待的事情沒有發生,沒有任何人前來指認或探問女子的下落;在這個地球上似乎沒有人在意一個消失在旅途中的年輕女子,在那個手機還未普及,網路還未鋪天蓋地的相對單純年代,一個人的消失可以是徹底的斷線失聯,沒有衛星定位也沒有網路肉搜;警方一籌莫展,只能將她列入失蹤人口處理,記下她的外貌特徵、概約年齡、膚色、髮型、穿著等基本資料以及錄製了指紋,送到各國領事館、紅十字會等相關機構,試著尋找與女子有關的資訊和線索。
在她開口說話之前,沒人知道真正發生在她身上的事,她的存在成為一個無解的檔案。
由於沒有任何關係人,女子成為醫院長期的負擔。警方最後將案子送到法院;法官無法裁決,因為無法處置一個沒有身分的人,醫院束手無策;紅十字會和大使館曾透過電視報紙尋找她的家人,也是一無所獲。最終,在警察局的記錄裡成了無人問津的過期檔案,一個無法定案的懸疑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