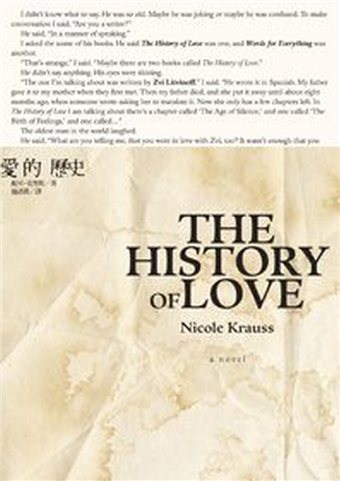李奧是位獨居在紐約的退休鎖匠,寂寞終日,生怕孤單死去無人知曉。他的祕密是:六十年前在祖國波蘭,他有一位非卿莫娶的青梅竹馬;後來,他有了一個永遠不能相認的兒子;還有,他寫了一本書《愛的歷史》,書中的女主角,就是他的摯愛艾瑪……
戰亂拆散了李奧與艾瑪,也迫使他逃離波蘭,無法把《愛的歷史》手稿帶在身邊,只得託付給好友茲維保管。李奧萬萬沒有料到,這本手稿幾經磨難,最後竟在南美洲問世,但書的作者不是他,他也完全不知道它的出版……
同樣在紐約,有位同樣叫做艾瑪的十四歲少女,是個單親家庭的長女。艾瑪的母親始終無法忘懷亡夫,努力寄情於翻譯工作。艾瑪見母親因寂寞日益憔悴,千方百計想為母親尋得第二春。此時,有人願出重金委託艾瑪的母親翻譯一本書,正是那本《愛的歷史》!原本只想代母尋友的艾瑪,在看了母親的譯稿後,不由自主,開始尋找書中那位與她同名的艾瑪……
一個名字、一本書,在命運的棋盤上,竟串聯著三個乍看之下毫不相干的家庭,牽動三代之間的愛恨。這些在浮世間漂流的小人物,在各自的世界裡飽嚐孤寂、歷經死別,卻沒想到,因為對愛的追尋,他們的人生之路,逐漸交錯……
作者簡介:
妮可‧克勞斯 著
1974年生於紐約,長於長島。史丹福大學、牛津大學畢業,主修文學及藝術史。自小博覽群書,文采洋溢。未上中學前,即已涉獵亨利‧米勒、菲利普‧羅斯等人作品。十九歲開始寫詩,詩作曾發表於Paris Review、Ploughshares等刊物;小說作品散見New Yorker、Esquire等雜誌。 2002年出版第一本長篇小說 Man Walks Into a Room,同年即獲選《洛杉磯時報》年度最佳好書,Esquire雜誌並稱讚她為「全美最佳新秀作家」。 亦自2002年起,開始發展《愛的歷史》故事雛形,2004年以短篇小說形式發表於《紐約客》雜誌(New Yorker),大獲好評,迴響熱烈,決心擴寫為長篇小說。《愛的歷史》在2005年問世後,立刻登上英美重要暢銷排行榜,更迅速售出全球多種語文版權,可謂奠定國際文壇地位之作。 與小說家 Jonathan Safran Foer為美國文壇知名夫妻檔,兩人育有一子,現居紐約的布魯克林。
章節試閱
【以下摘錄自本書章節〈在世的最後一番話〉】
明天或後天,當他們撰寫我的訃聞時,訃聞上將寫道:李奧‧葛斯基身後留下一屋子廢物。我很驚訝自己沒被活埋。這個地方不大,但我得費勁在床鋪和馬桶、馬桶和餐桌、餐桌和前門之間,清出一條通道。我若想從馬桶走到前門,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我必須繞過餐桌才到得了。我喜歡把床鋪想像為本壘,馬桶為一壘,餐桌為二壘,前門為三壘。如果躺在床上的時候門鈴響了,我得繞過馬桶和餐桌才走得到門口。如果來人碰巧是布魯諾,我就一語不發讓他進來,然後蹣跚走回床邊。那群隱形觀眾的吼叫聲,在我耳邊隆隆作響。
我時常猜想誰會是最後一個看見我活著的人。如果我得打賭,我敢說一定是中國餐館送外賣的小弟。我一星期有四天叫外賣,每次他上門時,我總是為了找錢包大肆翻箱倒櫃。他捧著油膩的紙袋站在門口,在此同時,我則猜想今晚會不會是我吃了春捲、爬上床,然後在睡夢中心臟病發的一夜。
我設法盡量讓人看見。出門在外時,有時雖然口不渴,但我還是買瓶果汁。如果店裡很擠,我甚至誇張到故意把零錢灑了一地,五分和十分錢銅板朝四方滾去,我則雙膝跪地。我跪下來得花好大功夫,站起來更是費力,不過嘛,或許我看來像個傻瓜。有時我走進體育用品店,問,你們有什麼樣的球鞋?店員上下打量我這個可憐的笨蛋,帶我看店裡一雙白得發亮的 Rockport球鞋。不,我說,我已經有這款了,然後我奮力走到Reebok那一區,拿起一雙根本不像球鞋的鞋子,說不定是雙防水靴。我跟店員說我穿九號,那個年輕小夥子神情更加謹慎地再瞅了我一眼,冷冷瞪了我好一會兒。九號,我緊抓著那雙有網邊的鞋子又說一次。他搖搖頭到店裡後面拿靴子,等到他回來時,我正脫下襪子,還捲起褲管,低頭看著自己老朽的雙腳。過了尷尬的一分鐘,店員才曉得我等他幫我套上靴子。我從來沒打算買鞋,我只是不想在我死去的那天,沒有半個人注意到我。
幾個月前我在報上看到一則廣告,說:繪畫班誠徵裸體模特兒,每小時十五美金。這麼多部位讓人觀賞,而且有這麼多人看,似乎理想得令人難以置信。我撥了電話,一個女人叫我下星期二過去,我試著描述我的長相,但她不感興趣,什麼樣子都可以,她說。
日子過得好慢,我跟布魯諾提起這事,但他聽錯了,以為我為了看裸女,才報名參加繪畫班,他也不想聽我解釋,她們會秀兩點嗎?他問,我聳聳肩。還會秀下面那裡嗎?
四樓的弗萊德太太死了三天,才有人發現她的屍體。我和布魯諾從此養成查看彼此的習慣。我們不時找些小藉口,比方說,布魯諾開門時,我跟他說,我的衛生紙用完了。一天後,有人敲敲我的門,我的《電視節目指南》不見了,他說。雖然我曉得他的《電視節目指南》跟往常一樣擺在沙發上,但我依然找出我那一份給他。有次他星期天下午過來,說,我需要一杯麵粉。這招可就不太高明,我忍不住點醒他:你又不會燒菜。接下來一片沉默,布魯諾瞪著我的雙眼,你懂什麼,他說,我在烤蛋糕。
初抵美國之時,除了一個遠房表哥之外,我誰也不認識,所以我幫他做事。我表哥是個鎖匠。他若是個修鞋師傅,我也會變成修鞋師傅;他若掏糞,我也會跟著掏糞。但是嘛,他是個鎖匠,他教我這一行,所以我成了鎖匠。我們合夥開了一家小店,後來他感染了肝結核,他們不得不切除他的肝。他發燒到攝氏四十一度,不治身亡,所以我接管了生意。他的遺孀後來嫁給一位醫生,搬到紐約海灣區,但我還是把店裡一半的利潤寄給她。我就這樣當了五十幾年鎖匠,但之前可從沒想到會過這種日子,不過嘛,其實我慢慢喜歡上這一行。我幫助那些被鎖在門外的人,也將某些不該進門的人屏除在外,讓大家高枕無憂、免做惡夢。
後來有一天,我凝視窗外,或許是望著天空沉思吧。即使把一個笨蛋擺在窗前,他也會變成大哲學家。午後時光漸逝,夜幕漸垂,我伸手去拉燈泡開關,忽然間,彷彿有頭大象一腳踩上我的心臟,我雙膝跪倒在地,心想我不可能永遠不死。過了一分鐘,再過一分鐘,然後又一分鐘,我在地上爬行,拖著身子爬向電話。
我心臟百分之二十五的肌肉已經壞死。我花了一段時間才復元,自此再也沒有回去工作。一年過去了,時光冉逝,對我而言也僅只如此。我凝視窗外,看著秋天變成冬天,冬天變成春天,有時布魯諾下樓陪我坐坐。我跟他從小就認識,一塊兒上學,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他戴著厚厚的眼鏡,有著一頭他討厭的紅髮、一激動起來就會啞掉的嗓子。我本來不曉得他還活著,有天走在東百老匯街上,我忽然聽到他的聲音,轉身一看,他背對著我,站在雜貨店門口,詢問某種水果的價錢,我心想:你又產生幻覺了,你老做白日夢,你怎麼可能碰到小時候的朋友?我呆站在人行道上,告訴自己他已入土為安:你人在美國,眼前有家麥當勞,控制一下自己吧。我等了等,只想確定一下。我不可能認得出他,但是嘛,他走路的模樣絕對錯不了。他快要走過我身旁了,我伸出手臂。我不曉得自己在做什麼,說不定真的是我的幻覺。我捉住他的袖子,布魯諾,我說。他停下來轉身,剛開始似乎嚇了一跳,然後一臉困惑。布魯諾。他看著我,眼中逐漸充滿淚水,我捉住他的另一隻手,這下我捉住了一隻衣袖和一隻手。布魯諾。他開始顫抖,伸手摸摸我的臉頰。我們站在人行道中央,行人匆匆而過,那是一個溫暖的六月天。他的頭髮稀疏灰白,手中的水果掉落在地。布魯諾。
兩年之後,他太太過世了。他們公寓裡的每樣東西都讓他想起她,少了她,他沒辦法再住下去,所以當我樓上有間公寓空出來,他搬了進來。我們時常坐在我餐桌旁,整個下午說不定沒講半句話。就算真的聊起來,我們也從來不說意第緒語。我們小時候用的語言已變得陌生,我們沒辦法像以前一樣使用它,所以決定乾脆不用。生命勒令我們使用新的語言。
很久以前,有次我發現布魯諾躺在客廳中央,身旁有個空藥瓶,他受夠了,只想永遠沉睡。他胸口貼了一張紙條,紙條上寫了幾個字:再見,我心愛的大家。我大喊,不、布魯諾、不、不、不、不、不、不、不!我猛拍他的臉,最後他終於顫動地張開雙眼,眼神空洞而呆滯。醒過來,你這個大笨蛋!我大喊:聽我說,你一定得醒過來!他又慢慢閉上眼睛。我打電話叫救護車,然後盛了一盆冷水,往他身上潑,把耳朵貼在他胸口。遠處依稀一陣騷動,救護車來了。醫院裡的人幫他洗胃,你為什麼吞了那堆藥丸?醫生問道。病懨懨、精疲力竭的布魯諾冷冷抬眼:你想我為什麼吞了那堆藥丸?他尖聲說。康復室變得寂靜無聲,每個人都瞪著他。布魯諾呻吟了一聲,朝著牆壁轉身。那天晚上,我扶他上床,喚他:布魯諾。真對不起,他說,我真自私。我嘆了口氣,轉身離去。留下來陪我!他哭喊。
在那之後,我們從未提起此事,正如我們從來不談童年、曾經共享卻失落的夢想,和所有曾經發生和沒有發生的事。有次我們默默坐著,忽然之間,我們其中一人開始大笑,另一個人也跟著笑,我們笑得毫無理由,但我們吃吃笑,笑得在椅子上猛力搖晃、放聲狂笑,笑得發出嚎叫、淚水流下臉頰。我胯下潮濕之處逐漸擴散,這讓我們笑得更厲害。我猛拍桌子,掙扎著呼吸,心想:說不定我就這麼走了,在狂笑中過世,還有什麼比這樣更好?──又笑又哭,又笑又唱,笑得讓我忘記自己孤苦伶仃、生命已到盡頭、死神正在門外等著我。
我小時候喜歡寫東西,這輩子只想當個作家。我塑造了假想人物,筆記本裡寫滿了他們的故事。我寫說有個男孩長大之後全身毛茸茸,毛髮多到人們為了他的皮毛而追捕他,他不得不躲到樹上,而且愛上一隻自以為是三百磅大猩猩的小鳥。年紀稍長之後,我決定成為一個真正的作家,我試著寫些真實的事情,我要描述世界,因為活在一個未被描述的世界太孤寂了。不過嘛,當我把書拿給全鎮我唯一在乎怎麼想的那人看時,她只是聳聳肩,說她比較喜歡我編故事。於是我寫了第二本書,全書純屬虛構,書中盡是長了翅膀的男子、樹根朝天空生長的大樹、忘了自己姓名的人,以及什麼都忘不了的人,我甚至自己造字。寫完之後,我一路跑到她家,衝過大門,奔上樓梯,把書交給全鎮我唯一在乎怎麼想的那人。她閱讀之時,我靠著牆,看著她的臉龐。外面愈來愈暗,但她繼續閱讀;好幾小時之後,我滑坐到地上,她依然讀了又讀。讀完之後,她抬起頭來,久久不置一詞,然後她說或許我不該編造每一件事,因為這樣讓人很難相信任何事情。
換作另一個人可能放棄,但我重新開始,這次我不寫真實事件,也不寫杜撰故事,我寫我唯一曉得的事情。紙張愈疊愈高,即使我唯一在乎怎麼想的那人搭船前往美國,我依然繼續在紙上寫滿她的名字。
她離開之後,一切分崩離析,所有猶太人都面臨險境,大家謠傳種種令人想不透的事,因為想不透,所以我們也不相信事情真的會發生,直到我們走投無路,一切卻已太遲。那時我在明斯克工作,但我丟了差事,返回斯洛尼姆的家中。德軍東進,愈逼愈近。大夥聽到坦克車逼近的那一天,我母親叫我躲到樹林裡,我想帶著年僅十三歲的小弟一起走,但她說她會自己帶他去。我為什麼聽信她的話呢?因為這樣比較容易嗎?我跑到樹林裡,直挺挺躺在地上。狗群在遠處猛吠,好久之後,遠處傳來槍聲,好多、好多起槍響,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傳來人的驚喊,說不定是我聽不見他們的尖叫。後來,只剩下一片沉寂。我全身發麻,還記得嘗到嘴裡的血。不知道過了多久,或許時隔多日,但我從未回頭。再度起身時,我已經捨棄心中唯一的文學因子,我再也找不出語彙,即使是生命最單純的事件,我也無語以對。
【以下摘錄自〈我媽的憂傷〉】
1. 我的名字是艾瑪‧辛格
我出生的時候,我媽用一本書裡每個女孩的名字幫我取名。這書是我爸送她的,書名叫做《愛的歷史》。她用猶太歷史學家艾曼紐‧林格布姆(Emanuel Ringelblum)、猶太大提琴家艾曼紐‧費爾曼(Emanuel Feuermann)、猶太作家伊薩克‧艾曼紐拉維奇‧巴別爾(Isaac Emmanuilovich Babel),和她的叔叔哈伊姆(Chaim)之名,把我弟命名為艾曼紐‧哈伊姆。但我弟拒用「艾曼紐」這個名字,當大家問他叫什麼,他就隨便編一個,總共大概用過十五或二十個名字。有一個月,他還用第三人稱「水果先生」稱呼自己。六歲生日時,他從二樓的窗戶猛然一跳,試著飛起來,結果摔斷了一隻手臂,額頭上留下一道永遠的傷疤,但從那之後,大家不叫他別的,只叫他「鳥弟」。
2. 我弟信奉上帝
鳥弟九歲半時,找到一本叫做《猶太人思想》的紅色小書。這書是我爸大衛‧辛格成年禮的禮物。鳥弟找到這本書不久之後,就戴上黑色絨布的小圓帽,而且到哪裡都戴著,即使帽子太大、後面突起一大塊、讓他看起來像個呆瓜,他也不在乎。說不定因為如此;說不定因為他習慣用手臂遮住臉,還挖鼻孔,以為大家看不出他在做什麼;說不定因為他有時發出像電動玩具一樣奇怪的噪音。反正不管是什麼原因,他本來有兩個朋友,那一年他們卻都不來找他玩。
每天早晨,他早早起床,走到屋外面對著耶路撒冷的方向禱告,我從窗戶看著他,心裡真後悔在他才五歲的時候,就教他唸希伯來字母。我想了就難過,也很清楚這種情況不能持續下去。
3. 我爸在我七歲的時候過世
我所記得的都是片段。他的雙耳、他手肘上起皺的皮膚、他跟我說過的,在以色列的童年往事。他坐在他最喜歡的椅子上聽音樂的模樣、他多麼喜歡唱歌。他跟我說希伯來語,我叫他阿爸。
我媽是英國人,她在亞實達港附近的一處集體農場工作時,認識了我爸。那年夏天過後,她就要到牛津大學唸書。他比她大十歲,曾經擔任軍職,離開軍隊之後遊遍南美洲,然後回學校唸書,成為工程師。他喜歡到戶外露營,卡車裡始終擺著一個睡袋和兩加侖的水,如果有必要的話,他還可以用一塊打火石生火。星期五晚上,其他在農場工作的人躺在草地上、縮在毛毯下,在巨大的電影銀幕下拍著小狗或是吸大麻,我爸則過來接我媽,開車載她到死海,兩人在海中姿態怪異地沉浮。
4. 我媽是我認識的人之中,最頑固的一個
五分鐘之後,她就決定她討厭牛津。她幾乎每天都用昂貴的法國信紙,寫信給在以色列的我爸。昂貴的信紙用完之後,她撕下筆記本的方格紙,繼續寫信給他。在其中一封信中(我在她書房沙發下面的一個舊巧克力罐裡,找到這封藏在罐子裡的信),她寫道:你給我的那本書擺在我書桌上,我每天都學著多讀一點。這本書是用西班牙文寫的,所以她必須學著讀。我媽還買了本《教你學會西班牙文》的書,自修西班牙文。她花很多時間在牛津的巴德里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讀了幾百本書,而沒有交到任何朋友。她借了好多書,借書的次數多到每次值班的圖書館員從座位上看到她走過來,馬上就想辦法躲起來。那年年底,她考試成績都名列前茅,但儘管她父母反對,她還是輟學,搬到特拉維夫跟我爸住在一起。
5. 接下來是他們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
他們住在拉馬特甘的一棟房子裡,屋內採光極佳,屋頂覆滿了九重葛。晚上,他們收聽他短波收音機中播放的美國音樂。窗戶大開、風向正確的時候,他們可以聞到大海的氣息。後來他們終於在特拉維夫的海灘上結婚,婚後到南美洲度蜜月,旅行了兩個月。回到特拉維夫之後,我媽開始譯書,剛開始是把西班牙文譯成英文,後來也做希伯來文的英譯。他們這樣過了五年,然後我爸拿到一份好得讓他無法拒絕的工作,受聘幫一家美國航太公司做事。
6. 他們搬到紐約,生下了我
我媽懷我的時候,讀了三千兆本各種主題的書籍。她不喜歡美國,但也不至於討厭。兩年半、八千兆本書之後,她生下了鳥弟。然後我們搬到了布魯克林。
7. 我爸在我六歲的時候,發現罹患胰臟癌
那一年,我媽和我一起開著車,她叫我把她的袋子遞給她。「我沒看到袋子。」我說。「說不定在後座。」她說。但袋子不在後座。她把車停在路旁,在車裡找了半天,卻依然找不到。她把頭埋在雙手裡,努力回想先前把袋子留在哪裡,她老是丟東西。「總有一天啊,」她說:「我會把自己的頭給丟了。」我試圖想像她若遺失了頭將會如何,但最終失去一切的是我爸,他失去了體重、頭髮,和體內各種器官。
8. 他喜歡燒菜、大笑、唱歌。他可以徒手生火、修理壞掉的東西、解釋怎樣把東西投射到太空中,但他九個月之內就過世了
9. 我媽從來沒有忘卻對我爸的愛
她一直守著對他的愛,也守著他們初識的那個夏天。為了這麼做,她排拒了生命。有時連著好多天,她只靠開水和空氣過活,她是唯一做得到這一點的高等生物,他們實在應該把某一物種取作她的名字。朱利安舅舅曾告訴我,雕塑家暨畫家賈克梅第(Alberto Giacometti)說,有時為了描繪一顆頭顱,你必須放棄整個軀體;為了一片樹葉,你必須枉顧整個風景。剛開始看來似乎自我設限,但過了一會之後,你會明瞭好好畫出某個景物的四分之一吋,比你假裝描繪整片天空,更能掌握住宇宙間的某種感情。
我媽沒有選擇一片樹葉,或是一顆頭顱,而選了我爸;為了留住某種感情,她犧牲了整個世界。
【以下摘錄自本書章節〈在世的最後一番話〉】
明天或後天,當他們撰寫我的訃聞時,訃聞上將寫道:李奧‧葛斯基身後留下一屋子廢物。我很驚訝自己沒被活埋。這個地方不大,但我得費勁在床鋪和馬桶、馬桶和餐桌、餐桌和前門之間,清出一條通道。我若想從馬桶走到前門,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我必須繞過餐桌才到得了。我喜歡把床鋪想像為本壘,馬桶為一壘,餐桌為二壘,前門為三壘。如果躺在床上的時候門鈴響了,我得繞過馬桶和餐桌才走得到門口。如果來人碰巧是布魯諾,我就一語不發讓他進來,然後蹣跚走回床邊。那群隱形觀眾的吼叫聲,在我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