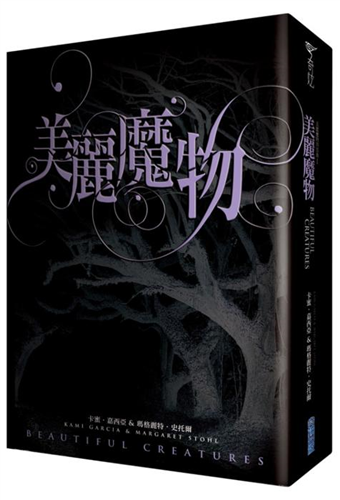九月二日
夢境
墜落。
我以自由落體的速度向下直墜,在空中瑟瑟發抖。
「伊森!」
她在叫我,光是她的聲音就讓我心跳加速。
「救我!」
她也在墜落,我伸長手想抓住她,卻只抓到空氣,我的雙腳踩空,兩手在泥濘中亂抓,我們的指尖短暫接觸了一下,接著就看到綠光消失在黑暗中。
她從我的指尖滑掉了,我感到失落無比。
但我還能聞到她身上的味道,那是檸檬和迷迭香。
可是我抓不住她。
感覺沒有她,我就活不下去了。
※※※
我猛然坐起來,有些喘不過氣。
「伊森魏特!快點起床!你不要上學第一天就給我遲到。」艾瑪在樓下扯開嗓門吼我。
我在黑暗中瞥見一抹微弱的光線,也聽到雨點打在農莊的百葉窗上。今天八成是下雨天,現在應該天亮了,而我應該在自己的房間沒錯。
因為下雨的關係,我的房間又冷又濕,為什麼我房間的窗戶沒關?
我頭疼不已,旋即又倒回床上,夢境來得快去得也快,我依舊在家中這棟古老大屋,依舊安然躺在我的房間裡,我的紅木老爺床依舊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音。在我之前恐怕有六代的魏特家族睡過這張床,但是沒有人掉到泥濘的黑洞,這一切都不是真的。
我瞪著刻意漆成藍色,防止花蜂前來築巢的天花板,想不通自己怎麼了?
幾個月以來我不斷地作著這個夢。雖然內容我幾乎全忘了,但我記得的部分都一樣,有個女孩在往下墜,我也是,我必須緊緊抓住她,但是我做不到。如果我鬆開手,她會發生相當可怕的事,所以我不能放手。我不能失去她。就好像她是我深愛的女孩,可是我根本就不認識她,這有點像一見鍾情,只是我還沒見過她就已經愛上她了。
這麼說似乎很瘋狂,畢竟她只是我夢到的女孩,我甚至不知道她的長相,雖然幾個月來都作著相同的夢,但我不曾看過她的臉,或者我不記得了,我只知道每次在夢中失去她,我就難過得快死掉了。當她滑出我的指尖,我總覺得胃部一陣翻騰,簡直快跳出口中,感覺很像坐雲霄飛車突然俯衝的那一刻。
人們常形容忐忑不安是「胃裡有蝴蝶在飛」,這種比喻還真爛,那種感覺才不像蝴蝶在飛,說是殺人蜂還比較貼切。
也許我迷糊了,也許我只是需要沖個澡,我的耳機還掛在脖子上,iPod就掉在旁邊,上面出現一首我不認識的歌。
《十六個月亮》。
那是什麼?我按下鍵播放,歌曲聽起來很耳熟,我說不出是誰唱的,但感覺以前聽過這首歌。
十六個月亮,十六年歲月。
十六年最深刻的恐懼。
十六次你夢見我的淚水。
墜落,墜落這些年的穿越——
歌曲有些憂鬱、毛骨悚然,甚至有點催眠的味道。
「伊森勞森.魏特!」艾瑪的嗓門蓋過了音樂。
我關掉音樂從床上坐起來,同時把被子拉開。感覺底下的床單都是沙子,但我知道那是什麼。
那是泥土,我的指甲縫也塞滿汙泥,上次作夢也是這樣。
我扯下床單丟進洗衣籃,將它塞到昨晚換下的臭運動服底下,然後就去沖澡,試著忘掉整件事,我拼命刷洗手指,讓指甲縫隙的髒汙逐漸流進排水孔,我不去想它,假裝這一切不曾發生,過去這幾個月以來我都是這麼做的。
但是我忘不了她,怎麼就是忘不了。我不斷地想到她,不斷地回到相同的夢境,連我自己也無法解釋。這就是我的秘密。我今年十六歲,愛上一個不存在的女孩,感覺自己慢慢步入瘋狂之中。
然而不管我怎麼用力刷洗,我的心依舊怦怦狂跳,雖然滿身是象牙肥皂和洗髮精的味道,但我依稀聞到另一股香味,味道雖然很淡,不過我知道那股香味依然存在。
那是檸檬和迷迭香的味道。
我走到樓下,只想確認一切如常。艾瑪照例在餐桌擺上藍白花紋的古老瓷盤,我媽以前都說這叫「龍紋餐具」,此刻餐盤上放著炒蛋、培根、奶油吐司和玉米粉。艾瑪是我們的管家,不過她更像我的奶奶。只是她比我真正的奶奶更聰明,也更頑固。我算是艾瑪一手撫養長大的。儘管我的身高將近一百八十八公分,但是她認為她的職責就是讓我再長高一點。不過今天早上我覺得特別餓,就好像一個星期沒吃東西似的。我快速吞下炒蛋和兩片培根,這才覺得好了些。我塞了滿嘴食物,對著艾瑪滿足地微笑。
「別再拼命餵我了,艾瑪,今天是我開學第一天呢!」艾瑪又把一大杯柳橙汁和一杯更大杯的全脂牛奶推到我面前。我們全家都喝這種牛奶。
「沒有巧克力牛奶了?」我喝巧克力牛奶的方式,大概就像某些人狂灌可樂或咖啡一樣。即使在一大早,我總是等不及補充糖分。
「適,應,力。」艾瑪最愛玩填字遊戲,越困難的越好,而且她超愛運用這些字彙。她總是一個字、一個字大聲唸,感覺好像在拍打你的頭似的。「就是這樣,習慣吧!而且我剛給你的牛奶如果沒有喝完,你休想踏出大門一步。」
「遵命,女士。」
「看來你已經打扮好啦!」其實沒有,我就是平常的穿著,牛仔褲配上褪色的T恤。我有各式各樣的T恤,今天這件印的是哈雷機車,而腳上那雙黑色球鞋我已經穿三年了。
「你不是說會去理頭髮?」艾瑪的大嗓門真像在罵人,但我知道這只是她表達深情的方式。
「我何時這樣說了?」
「你不知道眼睛是靈魂之窗嗎?」
「也許我不想讓人看透我的靈魂啊!」
艾瑪罰我再吃掉一盤培根。她身高大概一百五十公分,雖然她每年過生日都說自己剛過五十三,但她的年紀說不定比那套龍紋餐具更老。反正艾瑪就是一個溫和善良的老太太,不過她在我們家可是有十足的權威性。
「嗯,反正這種天氣,你不准頂著濕頭髮出門。我不喜歡這場暴風雨,感覺風中有什麼壞東西,而且一整天颳個不停,好像它有自己的意志似的。」
我忍不住翻白眼,艾瑪凡事都有一套看法。當她情緒一來的時候,我媽總說她又要開始怪力亂神了。這是南方才有的宗教和迷信,反正只要艾瑪一搞起這套,最好就是離她遠一點。千萬別去動她貼在窗檯的符咒,以及她親手縫製,放在抽屜的布娃娃。
我叉起滿滿一匙炒蛋,吃掉一份重量級的早餐:一個夾滿雞蛋、果醬、培根的吐司三明治。我一邊吃,一邊習慣性望向走廊那頭,書房的門關上了。老爸習慣在晚上寫稿,白天就在書房的舊沙發睡一整天。自從去年四月我媽過世之後,老爸的作息一直是這樣,真像吸血鬼,去年春天卡洛琳阿姨來陪我們住了一陣,忍不住就這樣形容老爸。看來我今天已經錯過和他碰面的機會,只好等明天了。書房的門一旦鎖上,就不會再打開了。
街上有人按喇叭,那是林克。我抓起破爛的黑色背包,打開門衝進雨中,早上七點的天色居然和晚上七點一樣黑,這麼奇怪的天氣已經持續好幾天了。
林克的破車停在街上,引擎發出低沉的吼聲,車上的音樂更是震天響,我從幼稚園開始就和林克一起搭車上學。那時他分了半條海綿夾心蛋糕給我,從此我們成了最麻吉的朋友。後來我才發現那半截蛋糕是掉到地上,他才撿起來送我的。我們今年夏天一起考到駕照,林克馬上去弄了輛汽車,只是那樣的破車實在很難說是「汽車」。
至少這輛破車的引擎聲可以壓過外頭的暴風雨。
艾瑪站在門廊兩手抱胸,一副不以為然的樣子。「在這裡不准把音樂開那麼大聲。衛斯理傑佛瑞.林肯,否則我就打電話給你媽,告訴她你九歲那年整個夏天躲在地下室都在幹些什麼。」
林克眨眨眼,很少有人這麼連名帶姓地喊他。大概只有他媽和艾瑪例外。「是的,夫人。」艾瑪隨即進屋,紗門砰地一聲又關上了。林克咧嘴而笑,隨即加足馬力揚長而去,好像我們在逃命似的。他開車一直都是這副德性。只是我們從來不曾逃去哪裡。
「你九歲的時候到底在我家地下室做了什麼?」
「九歲的時候,我在你家地下室什麼事沒做過?」林克將音樂轉小聲一點。這樣好多了,不然實在很恐怖,音樂難聽,偏偏他又要問我喜不喜歡,這幾乎天天都要上演一遍。他組的樂團「誰殺了林肯」也是一樣慘。每個團員根本就不是玩樂器或唱歌的料。但林克老是嚷嚷畢業後要搬到紐約去打鼓。幻想唱片公司會找上門。我覺得這個機率就好像瞇著眼睛喝到半醉,還妄想從體育館的停車場投進三分球一樣。
林克不打算念大學。但他有一點勝過我,就是他很清楚自己要什麼,儘管機會渺茫也一樣。我有的只是滿滿一鞋盒的大學簡章,我不能拿給我爸看,也不在乎這些大學在哪裡,只要離蓋林鎮至少一千五百公里遠就行。
我不想落得和我爸一樣的下場。我不想住在相同的祖宅,住在從小生長的小鎮,每天面對一群不曾夢想離開此地的人。
※※※
街道兩旁都是維多利亞式的舊房子,這些房子從一百年前蓋好後幾乎不曾改變。我住的街道叫做棉田街,因為這些舊房子的後方曾是綿延不絕的棉花田。不過現在這些棉花田都變成九號公路了。這大概是此地唯一的改變。
我從車內盒子拿出一個不太新鮮的甜甜圈。「昨晚你是不是下載一首怪歌,放到我的iPod裡面?」
「哪首歌?你覺得這首怎麼樣?」林克播放他新錄的試唱帶。
「我認為還需要修一下,就像你做的其他歌曲一樣。」我每天都這麼告訴他。
「是啊,等我揍你一頓之後,你的臉也需要好好修一下。」他每天都是這樣回答我。
我瀏覽播放清單。「那首歌好像叫《十六個月亮》。」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歌不見了,iPod裡面找不到那首歌,但我今天早上才聽過的,我知道這不是我的想像,因為那首歌還在我腦海縈繞不已。
「如果你想聽歌,我放首新歌給你聽。」林克低頭去挑選歌曲。
「嘿,老兄,眼睛看路啦!」
但是他沒有抬頭。我從眼角看到一輛奇怪的車子超到我們前面——
有那麼一瞬間,路上的聲音、暴風雨和林克完全靜下來,好像慢動作的畫面。我的視線無法離開那輛車子。那種感覺我無法形容,其實那輛車只是超車經過我們,然後就轉彎走另一條路。
我不認得那輛車,以前從沒見過。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因為鎮上每一輛車我都認得,這個季節也沒有遊客,誰會冒險在颶風季節來啊!
那是一輛黑色的長型轎車,很像靈車那種,事實上我確信那就是一輛靈車。
也許這是一個徵兆,也許今年比我想像中更糟。
「這裡,這首《黑色頭巾》將會讓我聲名大噪。」
等林克抬起頭來,那輛車子已經不見了。
九月二日
新來的女孩
從棉田街到石牆中學只要過八條街。我的人生就在這八條街來來回回,當我們穿過這八條街,也足以讓我把那輛奇怪的黑色靈車拋諸腦後。或許就是因為這樣,我並沒有向林克提起這件事。
車子行經「得速購」,我們稱之為「得速偷」,這是鎮上最接近7-11的商店,所以每次和朋友在店門口閒晃,都要祈禱不要碰見某人的老媽出來採買晚餐,最重要的是別遇到艾瑪。
一輛熟悉的跑車停在店門口。「糟糕,費提已經出來駐守了。」他坐在駕駛座看《星條旗日報》。
「也許他沒看到我們。」林克從後照鏡緊張地觀察。
「也許我們完蛋了。」
費提是石牆中學專抓逃學的督察,也是蓋林鎮警局最得力的一員,他的女朋友亞曼達在「得速購」當店員,費提幾乎每天早上都守在門口,等著現烤的食品送來。對於像林克和我這種經常遲到的學生來說,這實在很不方便。
要到石牆中學上課,就不能不知道費提的習慣,必須像課表記得清清楚楚才行。今天費提心情不錯,他忙著看體育版的新聞,揮揮手要我們過去,連頭也不抬一下。
「他的心思都在運動版和小圓麵包上,你懂吧!」
「我們還有五分鐘。」
※※※
我們把車子停在學校停車場,希望偷偷溜進去不要被教官發現。但外頭還是傾盆大雨,等我們跑到教室大樓時,全身早就濕透了。球鞋也因為浸水發出啾啾聲。聲音之大,讓我們很想停在原地不要跑了。
「伊森魏特!衛斯理林肯!」
我們濕答答地在辦公室罰站,準備接受處罰。
「上學第一天就遲到,你媽肯定會罵你一頓,林肯同學。你也別得意,魏特同學,艾瑪絕對會好好修理你的。」
海絲特小姐說得不錯。艾瑪要是知道我上學遲到五分鐘,肯定會扁我一頓。事實上她應該已經知道了。我媽曾說郵差卡爾頓會偷看寄來的信件,管它內容是不是有趣他都照看,甚至懶得再把信封黏回去。這個小鎮沒有新鮮事,每戶人家都有秘密,但街上每個人都知道你的秘密。就連這點也早就不是秘密。
「海絲特小姐,我只是因為雨下得太大,所以刻意開慢點。」林克試圖辯解,海絲特小姐把眼鏡拉低一點,掛眼鏡的頸鍊來回晃動起來,她回頭看著林克,完全不為所動。
「我沒時間聽你們鬼扯。我正忙著填寫處罰單,你們今天下午就留下來勞動服務吧!」她說完就把藍色的留校單遞給我們。
沒錯,她可忙了,我們走到轉角的時候,還能聞到指甲油的味道呢!唉!又開始學校生活了。
※※※
蓋林鎮的開學第一天總是老樣子。打從小時候上教堂,那些老師就認識我們了。在我們上幼稚園的年紀,他們已經認定哪個小孩聰明,哪個小孩愚笨。我是聰明小孩,因為我的爸媽都是教授,林克被歸類為笨小孩,因為他小時候把聖經讀本撕得稀爛,有一次還拿聖經丟向聖誕劇的演出人員。由於我被歸類為聰明學生,我的作業總是拿高分;林克因為是笨學生,他的成績就很爛。我猜根本沒有人會認真看我們的作業,有時我在作業中段亂寫一通,就是為了測試老師會不會說什麼,結果老師果然什麼都沒有發現。
可惜考複選題不能用這種方式。第一堂英文課我才發現老師──她剛好也姓「英」,而且老得就像幾百歲的人瑞,要我們在暑假讀《梅岡城故事》 。因為沒念書,我第一堂課的考試就不及格了。這下可好!其實我在兩年前就看過這本書,那是我媽最喜歡的小說之一,只是時間一久,很多細節都忘光了。
介紹一下我自己好了:我無時不刻都在看書。書本是唯一讓我逃離蓋林鎮的法寶,哪怕只是短暫片刻都好。我的牆上貼了一張大地圖,每次在書中讀到令我嚮往的地方,我就在地圖上標示出來。《麥田捕手》讓我想去紐約,之後是《阿拉斯加之死》的阿拉斯加,看過《旅途上》之後,我又在地圖上標出芝加哥、丹佛、洛杉磯及墨西哥市。凱魯亞克 的作品總能讓人神遊各地,每隔幾個月我就會把地圖上標示的地點連成一條線,想像我要趁上大學之前的暑假離開這個小鎮,沿著地圖上的綠線來趟公路旅行,地圖和閱讀算是我私底下的興趣,在這個小鎮,書本和籃球是格格不入的。
化學課也沒有好到哪裡去,霍老師讓超痛恨我的愛蜜莉艾雪和我同組做實驗。自從去年舞會的事件,她就再也不理我了。我只不過誤穿了球鞋配燕尾服,又讓我爸開著那輛生鏽的富豪汽車送我們到學校體育館罷了。那輛車有扇車窗故障關不起來。愛蜜莉特地吹整了一頭完美捲翹的金髮,沿路被風一吹自然全毀了。等我們抵達體育館,她看起來就像法國皇后瑪麗安東尼,頭髮有如豎立的屏風那麼誇張。那一整晚愛蜜莉完全不和我說話,只派了莎凡娜史諾出面,把我從三級階梯高的雞尾酒平台推下去,從此我們兩個就算吹了。
這件事成了同學之間的笑談,大家都在猜測我們何時會和好,不過他們並不知道愛蜜莉不是我喜歡的類型,她是很漂亮,但就只是這樣而已。光是欣賞她漂亮的臉蛋,並不足以彌補她的言語乏味。我要的是另一種女孩,一個不是滿口派對,只關心如何在冬季舞會贏得后冠的花瓶,而是可以天南地北無所不聊的女孩。我要的女孩必須風趣、聰明,至少在實驗室必須是容易相處的夥伴。
或許這種女孩只有夢中才有。但美夢總好過噩夢,愛蜜莉就算穿上可愛的啦啦隊短裙,還是可怕的噩夢。
我還是熬過開學第一天的化學課了。但接下來更糟,顯然今年又要念美國史,石牆中學的歷史課只教美國史,所以這個名稱實在多餘。我必須繼續上李老師的「北方侵略戰爭」,李老師和南北戰爭著名的李將軍並沒有關係。但是大家都知道,他的個性和李將軍還真是一模一樣,李老師是少數幾個真正痛恨我的老師之一。去年我和林克打賭,大膽交了一篇「南方侵略戰爭」的作業,李老師只給我六十分,看來有些老師確實會看我們寫的內容。
我在教室後面找到一個空位,剛好就在林克旁邊,林克上一堂課八成都在睡覺,現在忙著向同學借筆記來抄。但是我一坐下來他就停止抄寫了。
「聽說了嗎?」
「聽說什麼?」
「學校來了新女孩。」
「剛開學,學校當然有一籮筐新生啊!笨蛋!」
「我不是在講新生,是我們班來了一個新女孩。」對其他中學來說,高二轉來一個新同學也沒什麼,但這裡是石牆中學,上一次有轉學生是國小三年級的事了。當時是凱莉威克斯的老爸在鹽湖市的自家地下室經營非法賭場,在她爸被補入獄後,凱莉只好搬來這裡和爺爺奶奶住。
「她是誰啊?」
「不知道,第二節公民課我和樂團成員一起上,他們知道的也不多,只聽說她拉小提琴之類的,不知道她辣不辣?」林克馬上就想到這個,其實多數男孩也一樣,只不過林克很直,心裡想什麼就馬上說出來。
「所以她也是玩樂團的?」
「不是,她是音樂家,也許我們能一起欣賞我喜愛的古典音樂。」
「古典音樂?」林克唯一聽過的古典音樂大概是牙醫診所放的。
「你知道的啊,就是那些經典嘛!平克佛洛伊德、黑色安息日、滾石合唱團之類的。」我開始大笑。
「林肯同學、魏特同學,抱歉打擾你們聊天。但如果你們同意的話,我要開始上課了。」李老師講話和去年一樣尖酸諷刺。那一頭抹油梳成條碼狀的頭髮、身上的汗漬也和去年一樣糟。李老師發下一模一樣的講義影本,這套教材他可能已經用上十年了。想也知道,老師還要求我們必須參加一次美國內戰的重演活動,不過我可以輕易向親戚借到軍服,他們也會為了好玩,利用週末去參加戰役重演活動,這點我還算是幸運的。
下課鐘響之後,我和林克留在走廊的寄物櫃旁邊閒聊,希望有機會瞄到新同學,照林克的說法,這個女孩已經是他將來的心靈夥伴、樂團夥伴和其他琳瑯滿目的活動夥伴,我連聽都懶得聽了。但是等了半天,我們只看到夏洛蒂崔斯穿著小了兩號的牛仔裙經過。這表示我們要等到午餐時間才能繼續打聽新同學了。因為下一節是手語課,上課期間是嚴禁說話的,沒有人的手語好到可以比出「新女孩」來,尤其上這堂手語課的人多半是石牆中學的籃球隊員。
我從八年級就加入籃球隊,那一年暑假我突然長高十五公分,至少比班上其他同學高出一個頭,況且當你的父母都是教授,你就必須參加一些正常活動才不會被當成怪胎,結果我成了籃球高手。我就是知道對方球員會往哪裡傳球。會打籃球的人在石牆中學頗吃得開,每次到學校餐廳吃飯,總會有人幫我留好位子。
今天的餐廳座位更是超值,因為大家都圍著我們的控球後衛蕭恩畢雪,他是親眼看過新女孩的人。林克問了大家最關心的問題。
「她辣嗎?」
「相當辣。」
「有莎凡娜史諾那麼辣?」
莎凡娜是我們用來衡量學校女生的標準。此時她剛好和愛蜜莉手牽手走進來,大家全盯著她看,莎凡娜身高一七三,有一雙修長的美腿,愛蜜莉和莎凡娜簡直就像一對姊妹花,即使不穿啦啦隊制服,兩人的相似度還是很高,她們都是金髮、仿曬的麥色肌膚、穿夾腳涼鞋,牛仔裙短得幾乎像腰帶。莎凡娜是美腿傲人,愛蜜莉則是胸前偉大,夏天去湖裡游泳時,每個男孩都在瞄她的比基尼上圍。她們上學似乎不帶書的,手上那只小小的亮面皮包大概只放得下一支手機,不過她們很少把手機放裡面,總是不時拿在手上發簡訊。
但她們在啦啦隊的位置就完全不一樣了。莎凡娜是隊長,位置在底部,負責支撐上面兩排的隊員,她們最有名的隊形就是野貓金字塔,愛蜜莉是飛躍者,也就是站在金字塔頂端的隊員,她會被拋高一、二百公分,來個空翻或其他瘋狂的啦啦隊特技再落地,愛蜜莉不怕摔斷脖子,她願意付出一切代價保持金字塔頂端的位置。當愛蜜莉被拋到空中,整個金字塔隊形少了她也依舊挺立,但如果莎凡娜動了一下,整個金字塔就會搖晃倒下了。
愛蜜莉發現我們都在瞄她們,就狠狠瞪我一眼,大夥兒都笑了。艾默里瓦金斯拍拍我的肩。「想開點,魏特,你知道愛蜜莉的,她瞪得越凶,表示她越在乎你。」
我今天根本不願想起愛蜜莉,只對和愛蜜莉相反的人有興趣,自從林克在歷史課提起,我就一直想像這位新來的女孩。她可能非常獨特,可能來自其他地方,她的生活經歷可能比我們都豐富,我猜至少比我豐富。
也許她就是我夢寐以求的女孩,我知道我想太多了,但我願意這樣相信。
「你們都聽說新女孩的事了吧?」莎凡娜坐上厄爾派提的大腿,厄爾是我們的籃球隊隊長,也是莎凡娜分分合合的男朋友。現在是他們和好的時期,他撫著女友麥芽色的大腿,兩人親熱得要命,讓人不知眼睛該往哪裡看。
「蕭恩正在告訴我們。聽說她很辣,妳們要讓她參加啦啦隊嗎?」林克從我的餐盤抓了幾個薯球吃。
「應該不會,你們應該看看她的穿著打扮。」一好球。
「而且她太蒼白了。」兩好球。女孩絕對不能太胖或太白,這是莎凡娜最在意的。
愛蜜莉在艾默里身邊坐了下來,身體還刻意往前傾。「你們知道她是誰嗎?」
「什麼意思?」
愛蜜莉停頓了一下,製造懸疑效果。
「她是雷老頭的外甥女。」
她根本不需製造效果,光是這句話就夠戲劇性了。四周空氣突然為之凍結,有幾個男孩開始大笑,以為她在開玩笑。但我看得出來她沒有。
三好球,她被三振了。事到如今,我無法再想像她的樣子,她是我夢中女孩的可能性已經微乎其微,我甚至還沒開始想像我們的第一次約會呢!未來三年我註定只能和愛蜜莉牽扯不清了。
這麼說好了,麥坎雷是鎮上最孤僻的怪老頭。
如果以我看過的《梅岡城故事》來說,書中搞孤僻的布芮德和雷老頭一比,簡直就成了社交蝴蝶。雷老頭住在一間殘破不堪的老房子,那是蓋林鎮最古老、最惡名昭彰的農莊。從我出生以來鎮上就沒人看過他,說不定他離群索居的時間還更早。
「妳說的是真的?」林克問。
「當然,卡爾頓昨天送信到我家時,親口告訴我媽的。」
莎凡娜點點頭。「我媽也是這樣聽說的。她幾天前搬來和雷老頭住,之前不知是住在維吉尼亞州還是馬里蘭州,我不記得了。」
他們繼續談論這個新女孩,關於她的穿著、頭髮,還有她舅舅,談論她可能也是怪胎一個。這也是蓋林鎮最讓我痛恨的一點。不管你說了什麼、做了什麼,鎮上的人總有話說,像這個新女孩連穿衣服都要被批評。我只好盯著眼前那盤浸在橘色醬汁中的麵條,而那種稀稀的醬汁一點也不像起司醬。
還有兩年八個月,我心中暗自盤算,之後我一定要離開這個鎮。
※※※
放學後啦啦隊在體育館進行排練,雨總算停了,所以籃球隊可以到戶外場地練球。只不過龜裂的水泥地積了不少水,必須小心避開裂縫,免得像大砲發射一樣被汙水濺了一身。從戶外操場可以看到學校停車場,我們在做熱身運動的同時,幾乎就看遍石牆中學的社交活動。
今天我的手感很好,站在三分線投七球進七球,但厄爾也一樣,兩人成績不相上下。
咻!投進第八球!好像我只要盯住籃框,球就會自動導航進去一樣,有時投籃就是這麼順手。
咻!第九球,厄爾有點氣惱,看得出來他不太爽,因為每次我投進一球,他運球就特別用力。他是隊上的焦點人物,事實上我們有個不成文的默契:我讓他在球隊當老大,他則放我一馬,如果放學練完球,我不想和隊員去「得速偷」殺時間,他就不來囉嗦我。他們再怎麼聊就是那幾個女孩子,再怎麼吃也是那幾樣零食,我實在興趣不大。
咻!第十球。今天我百發百中。也許我是天生好手,也許有別的原因,我也想不透,但自從我媽去世,我也沒心思去想這些,反正這就是我創下的投籃奇蹟。
咻,第十一球,厄爾在我身後低聲咒罵,球拍得更用力了,我轉身又投出一球,轉頭望向停車場,試著不笑出來,結果我看到一頭鬈曲的黑色長髮,有個女孩開著一輛加長型的黑色禮車。
是那輛靈車,我愣住了。
接著她轉頭了,透過打開的車窗,我可以看到那個女孩朝我這邊看過來。至少我以為是這樣。我聽到籃球碰到籃框的聲音,然後彈跳到球場上。
咻,第十二球沒進。厄爾可以放心了。
等那輛車開走,我轉身回到球場,發現大夥都站在那邊像見鬼了一樣。
「那是——」
比利瓦茲點點頭,他是我們的前鋒。「雷老頭的外甥女。」
蕭恩把球丟給他。「對,就像他們說的,開他的靈車來學校。」
艾默里搖搖頭。「她是很辣沒錯,真是可惜啊!」
大夥又回去練球,可是輪到厄爾投球的時候又開始下雨了,三十秒之後我們全淋成落湯雞,這是今天以來雨下得最大的時候,雨水劈哩啪啦打在我身上,濕髮貼住眼睛,阻擋了我的視線,我看不到學校,也看不到場上的隊員。
壞徵兆並不是那輛靈車,而是那個女孩。
幾分鐘之後,我要自己保持希望,這表示今年會有些不同,不再像往年總是一成不變。我會有個說話對象,有個真正瞭解我的人。
目前我只是在球場上有不錯的表現,這對我來說實在不夠。
九月二日
天空的破洞
炸雞、馬鈴薯泥、肉汁、四季豆、麵包。從煮好就一直擱在爐子上,此刻已經冷冰冰地凍成一團。通常艾瑪會幫我保溫晚餐,等我練完球回家就可以吃。但今天居然沒有,看來我麻煩大了。艾瑪正在氣頭上,她一邊吃紅色的肉桂糖,一邊填寫《紐約時報》的填字遊戲。我爸偷偷幫她訂了週日版,因為《星條旗日報》的填字遊戲拼錯太多字,而《讀者文摘》的填字遊戲又太短,我不知道他是怎麼瞞過郵差卡爾頓的。否則他早就告訴全鎮的人,說我們家有多麼「高人一等」,居然不屑看《星條旗日報》。不過為了艾瑪,我爸願意做任何事來討她歡心。
她把餐盤從我的方向推過來,面無表情地看我一眼。我知道艾瑪不喜歡食物剩下來,只好把冷掉的馬鈴薯泥和雞肉往嘴裡塞。試著不去看她手中的二號鉛筆,那是她專門用來玩填字遊戲的。她把鉛筆削得很尖,尖到可能真的劃破皮膚,我看今晚很可能會發生這樣的流血事件。
雨滴持續拍打屋頂,屋裡靜悄悄的,只有艾瑪拿鉛筆輕敲桌面的聲音。
「五個字,一弄錯就走進死胡同,真是痛苦。」她看了我一眼,我把一匙馬鈴薯泥再送進嘴裡。我知道接下來是什麼,五個橫向字彙。
「恨,鐵,不,成,鋼,五個字。是啊,該罰你的,如果你不能準時到校,就不必離開這間屋子了。」
真不知是誰告訴艾瑪我遲到的事?我猜鎮上每個人都打過電話。艾瑪又開始削鉛筆,其實鉛筆已經很尖了,但她還是把筆放入老舊的手搖式削鉛筆機,看也不看我一眼就繼續削了起來。
我走到她身邊緊緊抱了她一下。「拜託,艾瑪,別生氣嘛!今天早上雨下得好大,妳不喜歡我們在雨天開車太快的,對不對?」
艾瑪瞪我一眼,但表情柔和多了。「看來你一天不去剪頭髮,就一天不會放晴,所以你最好想辦法給我準時到校。」
「是的,遵命。」我再給她一次擁抱,然後走回去吃那盤冷掉的馬鈴薯。「妳一定不相信今天發生什麼事,我們班上有個新來的女同學。」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講這個,大概是心裡還一直記得這件事吧!
「你以為我不知道蕾娜杜凱的事?」我差點被麵包噎住,以南方口音唸,這名字還頗合雨聲的節奏,艾瑪的捲舌音總會多唸一個音節,所以就變成「杜凱亞」。
「她叫蕾娜?」
艾瑪推過來一杯巧克力牛奶。「不管是不是都不關你的事。你不該攪和你不知道的事,伊森魏特。」
艾瑪講話總是像謎語一樣。她一向不多作解釋。她家在瓦溪村那邊,我只在小時候去過,但我知道鎮上的人常去拜訪她。艾瑪是蓋林鎮方圓百里內最受敬重的塔羅牌專家。就像之前她的母親和外婆一樣,她們是相傳六代的塔羅牌算命師,蓋林鎮住的都是敬神的浸信會、衛理會和五旬節教派的基督徒。但他們都無法抗拒塔羅牌的魅力,都想改變自己的命運。他們相信厲害的塔羅牌專家可以做到這點,而艾瑪就有這樣的靈力。
有時我會在放襪子的抽屜找到她自製的符咒,有時則是掛在我爸書房的門上。我只問過一次那是什麼東西,我爸每次找到一個就要取笑艾瑪,但是他並沒有把符咒拿下來。「寧可安全,也不要有遺憾。」我想他的意思是這樣才不會惹到艾瑪,否則鐵定安全堪慮,她絕對會讓你抱憾不已。
「妳還聽到哪些關於她的事?」
「你管好你自己,總有一天你會把天空捅出一個大洞,讓宇宙萬物墜落無底深淵。到時候我們麻煩就大了。」
老爸穿著睡衣走進廚房,我看到他還塞著黃蠟耳塞。他替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從廚櫃拿出一盒麥片,這表示他的一天才正要展開。
我靠到艾瑪身邊耳語:「妳到底聽到什麼?」
艾瑪抽走我的餐盤拿到水槽那邊,她沖洗了一些骨頭,看起來很像豬的肩胛骨,這就怪了,今晚吃的明明是雞肉。接著她把骨頭放在一只盤子上。「那不關你的事,我倒想知道你為何這麼感興趣?」
我聳聳肩。「沒什麼,只是好奇嘛。」
「你知道太好奇會怎麼樣吧!」
她把叉子叉在我的白脫奶油派上,意味深長地瞪我一眼就走開了。
就連老爸都注意到廚房門被她甩上的震動。他拿下一邊耳塞。「學校還好吧?」
「還好。」
「你怎麼惹艾瑪生氣了?」
「我今天上學遲到。」
老爸打量我,我也看著他。
「二號鉛筆?」
我點頭。
「削得很尖?」
「一開始就很尖,但是她又繼續削得更尖。」我嘆了一口氣。
老爸幾乎要笑出來,那真是罕見,這讓我覺得比較放心,甚至有些成就感。
「你知道我小時候有多少次坐在這張老餐桌前面,被她拿鉛筆戳嗎?」老爸雖然這樣問,但並不是真的在問我。這張餐桌老舊斑駁,上面又是漆又是黏膠,是整個屋子最古老的傢俱,也是當年最早一代的魏特祖先做的。
我露出微笑。老爸端起麥片碗,對著我揮揮湯匙。我爸也是艾瑪撫養長大的。小時候如果我想對艾瑪不禮貌,她就會拿這個事實來提醒我。
「蓬,勃,大,量。」老爸把吃完的空碗拿去水槽,同時唸出填字遊戲的字彙。
「過,剩。」這個字簡直就是在形容我了,伊森魏特。
等老爸再次走到廚房的燈光下,他臉上的笑意已經消失了。他看起來甚至比平常更糟。他比以前更瘦削,幾乎像是皮包骨了。老爸很久沒離開這間屋子,膚色顯得蒼白許多,幾個月過去了,現在的他看起來就像活殭屍。很難想像這和當初帶我去湖邊釣魚,坐下來一聊數小時的老爸是同一個人。以前我們總是坐在湖邊吃雞肉沙拉三明治,老爸會教我怎麼拋釣竿。「前後甩,就像指針的十點鐘和兩點鐘方向。」過去這五個月他很難熬,因為他真的很愛老媽。但我也一樣。
老爸端起咖啡準備走回書房。該面對現實了,我以為這個小鎮容不下兩個離群索居的布芮德,但麥坎雷或許不是鎮上唯一搞孤僻的怪人,這是我和老爸幾個月來最接近談話的一次,我不想讓他離開。
「新書寫得怎麼樣?」我脫口而出,其實我心裡想說的是:留下來陪我說話。
老爸似乎很驚訝。他聳聳肩。「還在寫,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他其實想說的是:他寫不出來。
「麥坎雷的外甥女剛搬到鎮上來。」我話才出口,老爸正好把耳塞戴回去,感覺真沒默契,我們的時機總是抓不準。想到這裡,最近我和其他人也常有抓不準時機的問題。
老爸嘆了一口氣,再度把耳塞拉下來。「你說什麼?」他已經往書房的方向走過去,這表示我們的談話時間所剩無幾。
「麥坎雷,你知道他是誰吧?」
「就是大家知道的那樣,他是一個隱居者。好幾年沒離開家了,我只知道這樣。」他推開書房的門,跨過門檻,但我沒有跟上去,只是站在走廊上。
我不進去老爸書房的。從小到大我只進去過一次,那時我才七歲,老爸發現我在讀他還沒有修改好的小說。他的書房暗暗的很嚇人。牆邊有張破破爛爛的維多利亞式沙發,上方的牆面有一幅畫,但老爸總是用床單遮蓋起來。我知道絕對不能去問老爸床單底下是什麼。沙發再過去的窗邊擺著老爸的紅木書桌,那是屋裡另一件傳承好幾代的老傢俱。還有一堆皮面裝訂的古老書籍,這些書又厚又重,所以有專門放置的大型木架,以便支撐書本翻開時的重量。這些書籍記載了我們家和蓋林鎮密不可分的關係,以及我們和一百多年來的祖先一樣,離不開這間魏特古宅的複雜歷史。
桌上放著老爸的手稿,他一向把手稿放在桌上打開的紙盒,我就是必須知道裡面到底寫了什麼。我爸寫的是哥德式的恐怖小說,其實並不適合七歲男童閱讀,但蓋林鎮的每棟古宅都是充滿秘密的,美國南方一向如此,我們家自然也不例外,即使在我七歲時也是一樣。
老爸發現我蜷縮在書房的沙發,四周盡是散落一地的書稿,好像放書稿的紙盒發生過爆炸似的。我顯然還不懂要掩飾偷看的行為,那次之後我很快就學會這一點。我記得老爸當時對著我大吼,後來老媽在後院找到我,我躲在老樹下哭得很傷心。「有些東西是很私人的,伊森,就連大人也是這樣。」
我只是一定要知道故事寫了什麼。這一直是我的毛病,就算到現在也一樣。我想知道老爸為何不肯離開書房,我想知道為何我們不能離開這間一文不值的老屋,就算有多少代魏特家的人住過又怎樣?特別是老媽已經去世了,為什麼我們就不能離開?
但今晚我沒有追根究底的心情,今晚我只想記住雞肉三明治,記住兩點鐘和十點鐘方向的甩竿動作,只想記住老爸一邊喝早餐麥片,一邊和我在廚房說笑的情景。晚上睡覺之前,我滿腦子想的都是這些。
※※※
隔天上課鐘響之前,石牆中學的每個人都在討論蕾娜杜凱,雖然昨天鎮上又是暴風雨,又是不時停電,但顯然莎凡娜的母親蘿瑞塔及愛蜜莉的母親尤金妮還是有辦法準時端出晚餐,同時打電話給鎮上那些三姑六婆,確保她們都知道雷老頭的「親戚」正開著那輛靈車在蓋林鎮橫衝直撞。她們都相信瘋狂的雷老頭曾利用那輛車載運屍體,只是沒有人親眼看過,但謠言卻越傳越誇張。
蓋林鎮有兩件事是不會改變的。第一,你可以與眾不同,甚至瘋顛反常,只要你 深居簡出,大家就不會認為你是手持斧頭的殺人狂。第二,如果鎮上有什麼精彩故事,一定有人會到處去講。鎮上來了一個新女孩,還住進陰森古宅,這可能是自從我媽意外身亡之後,蓋林鎮最驚人的故事了。所以我不知道為何會感到訝異,大家都在談論她是很正常的。不過我們幾個男孩例外,我們有更重要的事要談。
「結果怎麼樣?艾默里。」林克關上置物櫃的門。
「數過啦啦隊甄選了,大概有四個八分、三個七分,剩下一堆都是四分的水準。」低於四分以下的新生女孩,艾默里是懶得去算的。
我關上置物櫃。「這算什麼新聞嗎?這些女孩不就是我們每個周末在乍奚王看到的同一批嗎?」
艾默里笑著拍拍我的肩膀。「但現在她們是球賽啦啦隊了,伊森。」他看著走廊上的女孩。「我準備大展身手了。」艾默里就只會說大話。去年我們還是高一新生,就聽他一直說哪幾個學姐特別正,等他加入球隊就要追到她們,結果一年過去了也沒看到他行動。他就像林克一樣充滿幻想,只不過他沒有林克的好脾氣,瓦金斯一家向來惹不得。
蕭恩搖搖頭。「簡直就像從藤蔓上摘桃子,唾手可得啊!」
「桃子是長在樹上的。」我已經有些不耐煩。這些傢伙上學途中已經先在「得速偷」的雜誌區討論過同樣話題,厄爾在翻閱雜誌的比基尼女郎時,我們就有過幾乎相同的對話。
蕭恩一臉困惑地看著我。「你在說什麼?」
我不知道自己幹嘛不耐煩,這些對話一向很蠢。每個星期三早上我們上學前會先碰頭,這就像籃球隊的點名一樣。身為籃球隊的一員不能缺席。這是不成文的規定之一,其他例如吃午餐時要坐在一起,莎凡娜的派對務必參加,冬季舞會要邀請一位啦啦隊員作舞伴。還有就是學期末最後一天上課,大夥要到墨翠湖玩水。只要這些「點名時間」出席了,其他活動你要怎樣蹺頭都沒關係。只不過我越來越不想參加這些球隊聚會,我也說不上為什麼。
直到她在走廊出現時,我都還沒想通自己為何會變這樣。
即使我還沒看到她本人,也知道她人已經來到學校走廊。平常這裡總是擠滿學生,大家匆匆忙忙開取置物櫃,趕在第二次鐘響前衝到教室,幾秒鐘後走廊就空無一人。可是現在走廊上的學生突然自動分站兩旁,整個走廊幾乎讓給她一個人經過,彷彿她是什麼搖滾明星一樣。
或者當她是痲瘋病人。
我看到一個穿灰色長洋裝的漂亮女孩。她上半身套了一件繡著「慕尼黑」的白色運動外套。腳上是一雙破爛的黑色球鞋。胸前有一條銀色長項鍊,上面掛滿叮叮噹噹的小配飾,像是泡泡糖販賣機的塑膠套環、安全別針,還有一堆有的沒的,我站得太遠看不出是什麼東西。她看起來和蓋林鎮格格不入,我就是沒有辦法將目光從她身上移開。
她是雷老頭的外甥女耶!我到底哪根筋不對了?
她的黑色鬈髮塞在耳後,手上的黑色指甲油閃閃發亮,而且手背有黑黑的墨印,好像寫了什麼,她走過長廊,把旁人全當作空氣。我從沒看過那麼綠的眼珠,綠到你會覺得這是某種新的顏色。
「對,她是很辣。」比利說。
我知道他們在想什麼。有那麼一刻他們全想甩掉現在的女朋友,希望有機會把到她。有那麼一刻她會是你想交往的對象。
厄爾打量她一番,然後用力關上置物櫃。「如果不在意她是個怪胎,她是很辣沒錯。」
他的語氣怪怪的,這不難理解。因為她不是蓋林鎮的人,她沒有報名啦啦隊甄選,因為她連看都不看厄爾一眼。所以她成了怪胎。平常我才不在意厄爾說什麼,但今天我忍不住要回嘴。
「她馬上變怪胎了?為什麼?就因為她沒有金髮,沒穿啦啦隊制服和短裙?」
厄爾的臉上藏不住情緒,這種情況我應該附和隊長的看法才對,但今天我沒有遵守這項不成文規定。「因為她是雷老頭的外甥女。」
答案很清楚了,她是很辣,但想都不用想,她已經出局了。不過這不妨礙大家繼續偷看她,事實上走廊全部的人都在看她,每個人都是屏氣凝神、目不轉睛地看著,好像她是被槍口瞄準的一隻鹿。
但她不以為意,任由長鍊的墜飾繼續叮叮噹噹,旁若無人地走過長廊。
※※※
幾分鐘後我站在英文課的教室門口,蕾娜杜凱就在那裡,那個新來的女孩。也許往後五十年大家還是會叫她「新來的女孩」,要不然就是「雷老頭的外甥女」。她把粉紅色的轉學單拿給英老師,老師瞇起眼睛正在研究。
「他們弄錯我的課表,我沒有英文課,」新來的女孩解釋,「卻有兩堂美國史,我在以前的學校修過美國史了。」她聽起來有點洩氣,我忍著不要笑出來。她一定沒上過這樣的美國史,至少不是李老師教的方式。
「沒問題,自己找空位坐下。」英老師遞給她一本《梅岡城故事》,感覺那本書根本沒人翻過,或許小說拍成電影之後就沒人去翻閱了。
新來的女孩一抬頭,就發現我在看她,我連忙轉開目光,但已經太遲了。我試著不要笑出來,但因為很尷尬,更讓我傻笑起來,幸好她似乎沒注意到我的窘態。
「沒關係,我自己有。」她抽出一本精裝本,封面是大樹形狀的蝕刻紋,看起來古老破舊,好像她不止翻閱過一次。「這是我最喜歡的小說之一。」她就是這樣脫口而出,好像愛看書一點也不古怪,現在我真是目瞪口呆了。
我感覺背後有股排山倒海的壓力,接著愛蜜莉擠開我進入教室,無視我站在門口,這是她打招呼的方式,意思是希望我跟隨她到教室後排的座位,我們的朋友都坐在那一區。
新來的女孩在第一排找了空位坐下,剛好正對著英老師的講桌,這裡一向是無人區域,她真是選錯位子了。大家都知道絕對不要坐在那裡,英老師有一邊的眼睛是義眼,而且她的聽力很差,彷彿她家是全美唯一的槍擊練習場,才造成那樣的重聽程度。總之只要不坐在講桌正前方,英老師就不會看到你,自然也不會叫你起來回答問題,看來這堂課要由蕾娜包辦老師的發問了。
愛蜜莉經過她身邊似乎覺得很有趣,她故意踢掉蕾娜的書包,裡面的書全掉在座位間的走道。
「哎呀!」愛蜜莉彎身撿起一本破破爛爛的筆記本,感覺只要稍微扯一下就會散開。愛蜜莉拿在手中,好像那是一隻死老鼠。「蕾娜杜凱,那是妳的名字?我以為妳姓雷。」
蕾娜抬頭,慢慢地說:「把書還我好嗎?」
愛蜜莉開始翻閱,假裝沒聽見她的話。「這是妳的日記嗎?妳是作家?真酷!」
蕾娜把手伸出來。「請還我。」
愛蜜莉把筆記本闔起來,藏在身後不給她。「可以借我一下嗎?我想拜讀妳寫的大作呢!」
「我要妳立刻還我。」蕾娜站起來,情況似乎越來越有趣了。雷老頭的外甥女即將掉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愛蜜莉的記性無人能及。
「那也要妳讀得懂才行。」我從愛蜜莉手中抽走筆記本,把它還給蕾娜。
然後我在蕾娜旁邊的空位坐下。沒錯,就是無人區域的空位,是英老師看得見的那一區,愛蜜莉不敢置信地看著我,我不知道為何這樣做,我自己也和愛蜜莉一樣震驚。我這輩子從來不曾坐在教室第一排呢!愛蜜莉還來不及說什麼,上課鐘聲就響了,不過這不重要,我知道我遲早要為此付出代價,蕾娜打開她的筆記本,壓根不理會我們兩個。
「可以開始上課了吧?各位。」英老師從講桌前抬起頭來。
愛蜜莉溜到後面最遙遠的座位區,坐在那裡整年都不會被老師問到問題,同時也遠離雷老頭的外甥女、遠離我。這讓我稍微鬆了口氣,只是接下來五十分鐘上課時間,我必須在沒有預習的情況下分析杰姆和思葛的關係。
下課鐘響後我轉頭看著蕾娜,不知道自己要說什麼,也許只是期待她會開口謝謝我,但是她什麼都沒有說,只是把書本再放回書包。
156,她寫在手背的並不是文字。
那是一個數字。
※※※
蕾娜那天並沒有和我說話,事實上之後整個星期都沒有。但我還是一直想到她,甚至到哪裡都看到她,好像避都避不掉似的。其實讓我困擾的並不是她這個人,不是她的樣子。她確實很不會配衣服,球鞋也總是破破爛爛的,但她真的很漂亮。困擾我的也不是她在上課時所講的話。她說的話往往都是我們意想不到的,要不然就是我們雖然知道,卻沒有膽子說出口。她和石牆中學的女孩完全不一樣。不過這也不是困擾我的地方。
主要是她讓我瞭解到:儘管我總是假裝自己與眾不同,但其實我和石牆中學的其他人並沒有什麼兩樣。
外頭一整天都在下雨,我坐在陶藝課教室,這堂課又叫營養課,因為保證每個人都能拿到高分。這也是我在去年春天選陶藝的原因,一來我需要修滿藝術學分,二來我只想遠離樓下的樂團練習,負責指導樂團的史派德老師身材瘦小,但熱情過度,每次樂團練習真是吵死人了。我是陶藝課唯一的男生,莎凡娜就坐在我旁邊,我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
「今天讓你們自行體驗,老師不會打分數,只是要你們去感受陶土,自由拓展你的想法,同時別去在意樓下的音樂。」艾老師聽到樓下荒腔走板的音樂,眨眨眼又加了最後一句。
「挖深一點,探索你的靈魂深處。」
我啟動拉胚機,看著陶土開始旋轉,忍不住嘆了一口氣,這也沒比樂團好到哪裡去。然而等教室靜下來,只剩拉胚機嗡嗡旋轉的時候,我卻聽到樓下樂團的音樂為之一變。那個聲音好像來自小提琴,或者是再大一號的中提琴。那段旋律好優美,同時又好哀傷,讓人感到激動不安,這比史派德老師以往指導的音樂好太多了。我環顧四周,四周沒有人注意到音樂,但這段音樂卻讓我渾身起雞皮疙瘩。
我記得這個旋律,心裡隨即浮現了歌詞,字字句句就像之前聽iPod那樣清晰。只不過這次歌詞改變了。
十六個月亮,十六年時光。
耳中傳來轟雷巨響。
十六哩,她的芳蹤將至。
十六年的探尋,十六年的恐懼——
我凝視眼前旋轉的陶土,那團陶土開始模糊起來,我越是專注凝視,陶土中央的空洞就越大,到最後好像陶土圍著整個教室在旋轉,我的桌椅全被包圍在中間了,我們彷彿陷入一團持續旋轉的風暴,教室漸漸消失了,我緩慢伸出手,將指尖伸入陶土中。
我眼前一花,旋轉的教室溶入另一個畫面——
我在墜落。
我們在墜落。
我又回到那個夢境,看到她的手,看到我緊緊抓住她的手,手指深深掐進她的皮膚、她的手腕,好像拼命要抓牢她。但是她又快滑掉了,我可以感覺她的指間滑過我的手掌。
「別放手!」
我想幫助她,想抓牢她,這種渴望勝過一切。然而她還是溜出我的指尖——
「伊森,你在做什麼?」艾老師的聲音充滿關切。
我張開眼睛,努力讓自己回到現實,自從老媽死後我就不斷地作這個夢,不過這還是頭一次我在白天就墜入夢境。我瞪著沾滿半乾泥土的雙手,只見拉胚機上的陶土清楚印出一個掌形,彷彿我剛才把手掌壓印在上面。但是我湊近一看,那個掌印不是我的,它太小了,應該是女孩子的手。
那是她的掌印。
我的指甲縫隙都是陶土,那是我為了抓緊她的手腕,拼命在泥中亂抓才留下的。
「伊森,你至少可以試著創作一些東西吧!」艾老師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嚇得跳了起來。外頭雷聲大作,從教室窗戶可以看到閃電交加。
「艾老師,我想伊森忙著探索他的靈魂呢!」莎凡娜咯咯笑著,靠過來仔細看了一下。「同時也需要剪指甲了,伊森。」
四周的女同學都笑了。我一拳毀掉陶土上的掌印,拉胚機上又是一團什麼也不是的陶土。下課鐘響了,我站起來以牛仔褲揩淨雙手,隨即拿起書包衝出教室,完全沒注意球鞋的鞋帶鬆了,害我轉彎時差點絆倒。我只是急著衝到樓下的音樂教室,因為我必須知道這一切是否出自我的想像。
我推開音樂教室的厚重大門,舞台已經空無一人,成群的學生從我身旁經過,我的方向剛好和大家相反,每個人都準備離開教室,只有我往裡面衝,我做了一次深呼吸,知道自己會聞到熟悉的香味。
檸檬和迷迭香。
史老師在舞台下方收拾散落在椅子上的樂譜。她就是用這些樂譜來指導石牆中學這個慘兮兮的樂團。我走到她身邊。「對不起,老師,剛剛是誰在演奏——那首歌?」
她對我微笑。「我們的弦樂部有了新成員,是一名中提琴手,她剛剛搬到鎮上——」
不,不會吧!不會是她。
還沒等到老師說出她的名字,我轉身就跑。
※※※
第八節下課鐘響,林克在置物櫃旁邊等我,同時忙著以手指梳理那顆刺蝟頭,拉直身上那件「黑色安息日」的褪色T恤。
「林克,我需要你的車鑰匙。」
「那練習怎麼辦?」
「我不行,因為我有事要處理。」
「喂,你到底在說什麼?」
「車鑰匙給我就對了。」我必須離開這裡。這些日子以來我不斷作夢、不斷聽到怪歌,如今大白天上課還「失去意識」。我甚至不知道這種說法對不對,我不知道自己怎麼了,但我知道這絕對不是什麼好事。
如果老媽還活著,我可能會把這些事都告訴她。她是可以無話不談的對象。但是她死了,老爸又成天把自己關在書房。如果告訴艾瑪,她準會拿鹽巴灑滿我的房間,而且整整灑上一個月。
如今我只能靠自己。
林克拿出鑰匙。「教練會殺了你的。」
「我知道。」
「艾瑪會發現的。」
「我知道。」
他揚手丟出鑰匙,我一把抓住。「艾瑪準會把你踢到九霄雲外,你別傻了。」
我轉身往外就跑。太遲了。
更多精采內容請見《美麗魔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