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埠頭奇客顯身手 艙內名士弄玄虛
「起錨了!」泉州府港埠邊一艘待行大船,艙內傳出雷鳴般的大喊。
五名光著膀子的水手本來蹲在甲板邊納涼,聽聞艙內吩咐,忙吆喝著齊向船尾奔了去。五名水手均十分黝黑精瘦,領頭那人約莫三十歲年紀,生得一對刀眉三白眼,粗紅傷疤橫跨臉頰鼻樑,身上刺有單色下山虎,看來頗為狠惡;其餘四人則較為年輕,亦是長得桀驁不馴。甲板上原多商旅及扛貨工,見這五名水手直衝過來,忙不迭讓開條通道給過。
五人至船尾放錨所在,那名刀疤水手命兩人扶著絞盤,一人抓緊連接錨身的粗大鐵鍊,自己則與最末那人一前一後捉住絞盤把手。
刀疤水手將頭一甩,腦後長辮呼呼一聲在他頸子繞了幾圈,說道:「我一喊『起』,咱們就一道出力;來,『起』!」刀疤水手「起」字一出,五人一道使勁,捉著鐵鍊及絞盤的兩人尤其卯足了氣力,肩臂肌肉墳起,青筋直冒。
鏘啷、鏘啷一陣刺耳的鐵鍊捲絞聲響處,絞盤捲動,大船隨之輕輕晃了幾下。
那刀疤水手粗聲氣喝道:「幹!沒吃飽飯喔?加緊出力哦!……嘿咻!」
其餘四人一起應聲,大喝著:「嘿──咻──」
猛地裡噹一大響,鐵鍊突然間繃得死緊,拉鐵鍊那人雙掌給大力震彈開來,垂眼望去,卻見雙掌虎口爆裂開來,滿是鮮血。
船艙內那人復又喊道:「是又怎樣了?阿義快一點!咱們該起帆啦!」
刀疤水手大聲應道:「老大,阿狗的手心破了!咱們的錨一定是卡死在石頭縫裡了!」
船艙應聲走出兩人。當先一人步履甚快,直望絞盤處走去;只見這人約莫五十歲年紀,獅鼻大口、一雙黑豆小眼上安著兩條羅漢眉,光著的上身臂膀遍是肌肉,形貌十分粗獷;儘雖不滿五尺高,卻猶如鐵塔般令人生畏。
壯漢身後是名二十五歲左右的青年書生。那書生容貌十分俊秀,一張白皙無垢的臉上是劍眉鳳眼、長準薄唇,頭頂著淄色瓜皮帽,身襲一件青綿袍,手中兀自捉著書本,肩背一只四尺長包裹。有道是「腹有詩書氣自華」,這青年雖非穿著綾羅綢緞好衣衫,卻隱約透著貴氣。
「你老母咧!」那壯漢面色不善、瞪眼罵道:「跟老子這樣久了不會做事?這樣簡單的事你們不會處理?」壯漢話聲響若雷鳴,原來便是之前在艙內發號司令的船老大。
那書生對船老大低聲道:「林二叔,不過就是錨頭卡在礁岩上,待會我下水去把錨取了出來便是,又何必動怒?」
那船老大忙搖手低聲道:「不行!不行!三公子身分尊貴,這些粗活,讓弟兄們幹去。」船老大面對水手說得一口泉州腔閩南話,對書生言語卻換了口北京官腔,語言轉換得十分精巧。
書生微微一笑,對船老大的說話不置可否。
船老大說著,叫那名叫阿狗的負傷水手進艙擦藥。他是天生的大嗓門,同書生的對話一字不漏傳進眾水手耳中,只見刀疤水手等五人臉上均透出忿忿然的表情。
這書生倒是個知趣之人,明白船老大的話已讓水手心生不滿,微笑道:「母地父天,我們都是義結金蘭的好兄弟,如何有尊卑之別?」
船老大恭敬回道:「是……」看向刀疤水手,道:「阿義,咱們泉州的弟兄,總不能在總舵的兄弟面頭前漏氣!」
刀疤水手雖心有不滿,卻未敢造次,將辮子紮緊,走到船舷邊看了看,活絡一下筋骨,縱身入海。約二十來息後,探頭出水,叫道:「老大!礁石把咱們的錨卡得緊緊緊,拉不起來。」
船老大皺眉道:「鬼扯,老子來瞧瞧。」說著脫鞋勒緊褲腰,亦要下水。
刀疤水手叫道:「老大,你別下來……」說著瞪視書生道:「叫那小白臉下來!他要是無膽下水,我看不起他!」舉臂朝書生用力揮幾下,示意對方下水。
船老大怒意上來,罵了聲「幹」,正欲再罵,書生扳住船老大肩頭道:「林二叔,張有義說得不錯,我若不下去幫忙,不但有虧義氣,實也不能令泉州的兄弟們心服。」
船老大忙道:「三公子,你別聽阿義胡說,海潮還涼著呢!你如下水著涼,我林二官怎麼向總舵主交代?」
書生哈哈一笑,快手快腳除下帽袍鞋襪,連同手上之書、肩負包袱一股腦地塞在船老大林二官手上,橫咬髮辮,向海中跳落。
林二官見這書生入水姿態俐落,心中寬慰:「三公子好歹是總舵主的弟子,總舵主的武功、膽氣,少說得繼承個三成……日後要領帥天地會的人,總不成是個肩不能擔、手不能提的紈褲子弟。」待見得張有義露出得意表情,心中更驚:「阿義這小子定是想在水裡搞鬼──想,三公子也不必出啥意外,只要出醜丟臉,老子定吃不完兜著走!」
書生向張有義拱手道:「請張兄帶路。」張有義冷笑道:「隨我來……」深吸口氣,鑽入水中。書生效張的姿勢,跟著潛入。
張有義久為水手,游泳潛水猶如吃飯拉屎般再熟不過,只見他身軀柔似游魚,不過一曲一扭,身子便潛進丈許。書生見張的潛水姿態好看,有心仿效,然而面前海水好像藏了一道透明牆,明明使足吃奶力氣,卻遠為落後,不覺暗暗佩服。
張有義不一會兒便到落錨處,選塊礁石穩穩站定,回見書生緩緩潛來,暗自冷笑:「哼哼,總舵的人向來自大慣了,三公子又如何?未必有甚麼真本領……看老子怎麼修理你!」揮手招呼書生過來,指了指鐵鍊鐵錨。
書生游了過去,隨手扯動鐵錨鐵鍊,鐵錨緊緊鉤住岩縫,未有動靜。書生蹲下細觀礁岩,心道:「鐵錨當真卡死了,要拉出實非易事……」正思索間,張有義突然欺近,伸腳踏住書生雙足,右手逕往書生咽喉掐去。
書生猛吃一驚,忍不住吞了口海水,抬肘架開攻招,心道:「果然張有義存心搞鬼來著!」他不願出手傷人,左掌望張有義胸口平推,綿勁一發,將張有義送出兩尺。
張有義得意地盤算著:「小白臉喝了海水,撐不得多久就會上去換氣──老子偏不給你換氣!」腰際一縮一彈,肩頭直衝書生胸膛。
書生側身避過,曲膝發勁,欲衝出海面換氣。人在中途,被張有義出手捉住髮辮,用力下扯,瞧準書生頭顱向後仰的當兒,手刀朝喉頭劈落。
任書生修養再好、脾氣再佳,這時也不禁恚怒:「這廝惡作劇也忒火了,根本是想取我性命!我若非習過武藝,豈不便死在他的手裡?」順著張有義扯辮力道,收腰出腿,抵住張的手刀。
張有義一連三擊未中,心裡不禁緊張起來:「小白臉拳腳功夫當真厲害,他若是全力殺來,結果反而是老子被他殺了!」這麼一想,忍不住便想逃將上去。然而他心急之下忘了放開書生髮辮,手這麼使力揮舞,直拉得書生頭疼腦暈。
書生頗為著惱,見得張有義心慌貌,突起頑皮念頭:「眼下卻該換我整治他了!」體內真氣數轉,不再氣悶,驀地扭身力旋,身軀急轉十來圈,扯得張有義一齊翻滾。張有義驚駭過度喝了好幾口海水,不由得暈死過去。
書生暗自好笑,急使個千斤墜,穩站礁石,見鐵錨邊鉤給咬在岩縫內,倘使盲目拉扯鐵鍊,只有卡得更緊,只有將錨往原方向推開一途;遂將雙掌貼緊錨頭,先輕施沾黏勁,接著勁力急吐,只見得岩床上泥沙漂起,鐵錨反向退開數寸;書生心中甚喜,把鐵錨推離岩縫。心想張有義昏迷,再不上水恐怕誤了他一條人命,忙肩著他游出水面。
林二官見二人入海後遲遲不出水換氣,心裡大為擔心。他這艘寶陞號貨船共二十四名水手,每一個放回陸上都是青面獠牙的兇神惡煞,當中便屬張有義最為兇狠,身上兀自積累兩條人命官司,走投無路下才被自己收羅進寶陞號。去年一回同海盜械鬥中,張有義救了蓮花堂香主陳玄龍性命,這才由陳香主開香堂起重誓薦入了天地會。然而張有義天生反骨,入天地會後仗著功勞大又惹了不少事端,若非近幾年來天地會凋零,否則依舊時幫規,老早便開革出會。
此番張有義再度對總舵使者不敬,雖說這位駱三公子溫文有禮、脾氣甚佳,難免不是個心胸狹隘之人,張有義便算不被開除會籍,挨受個三刀六眼之刑或是鞭撘個十來下想必少不了。
「三公子若有甚麼閃失就糟了!阿義這賊胚死三遍都不夠賠命!」想到這裡,林二官更加憂心,轉對身旁幾名水手道:「暖暖筋骨,咱們準備下水救人!」眾水手本來還幸災樂禍的,聽老大說得嚴重亦不免緊張起來:「阿義會殺三公子?」「不會啦!老大,我保證阿義不會亂來!」「咱們快去將他們分開!」眾人你一句我一句猶如熱鍋上的螞蟻,卻遲遲未見水手們褪衣準備下水。就在亂成一團的當兒,海面上「噗噗噗」雞卵大的氣泡連冒,接著嘩啦啦破水聲起,那書生冒出頭來大口換氣。
「他上來囉!」一名水手驚呼道:「老大,那駱三公子出水囉!」林二官忙將腦袋探出船舷,衝書生叫道:「三公子!阿義沒對你做甚麼吧?」他鬆口氣,心頭之欣喜不亞於添房媳婦、多個孫子。船上眾水手齊集過來,大聲歡呼。
「咦!」一名水手問道:「阿義咧?」才說著,那書生舉臂一提,將昏迷中的張有義拉出海面。書生道:「林二叔,阿義噎了幾口海水,我們先救他!……人來啦!你們可得接好了!」書生將張有義身軀高舉過肩擺個「霸王舉鼎」式,起勁力擲。張給高高拋出,越過船舷,眾水手只瞧得目瞪口呆,簡直不敢相信天下有這般奇事。林二官罵道:「蠢材!還不快將阿義接住!」眾人這才回過神接抱張有義。
林二官回身取條繩索欲拋予書生,可那書生已逕自游到了船邊,雙掌貼著船壁,「呵哈」幾響吐氣聲起,拔水而出,半空中扭身借力,輕飄飄地沿船壁攀游而上。林二官大聲讚道:「三公子好個『壁虎游牆功』!」船上一眾貨工、商人老早便站在甲板上瞧熱鬧,見識了書生功夫,忙不迭用力鼓掌叫好。采聲雷動中,書生翩然踏上甲板,打個四方揖道:「雕蟲小技不足掛懷。」眾水手見他身子雖白,肌肉卻有如鐵鑄般稜角分明,不由得對他刮目相看。
林二官忙將頸上一條污穢的拭汗巾遞與書生,道:「您先擦乾身體。阿義他……」低頭看著張有義。張有義被眾水手施救後,大吐幾口海水,甦醒過來,睜眼便見到書生,忍不住懼意大起,長呼道:「我的媽啊,見鬼了!」眾人聞言莞爾。
那書生著整衣衫,神態輕鬆地回到船艙。這艘寶陞號原本是貨船設置,在林二官手裡改了裝潢,加設座位;以是故,艙內除堆放貨品也有許多旅客。五十人容量的船艙內眼下塞了將近七十人,略顯擁擠。有些坐不到位置的旅客,便只好坐在艙板上。
眾旅客中不少人才目睹了書生手擲張有義一幕,既敬且畏的眼光紛紛投了過來。書生微笑拱手、輕輕說了幾聲「勞駕」、「借光」、「大家好」的話,從艙口擠向艙尾。
艙尾設了幾間包廂,是給大戶富商專用。書生走到一間包廂前,輕拍門板低聲道:「藍兄,小弟駱奇峰回來了。」
擦地聲,廂門開啟,門邊一名妙齡女子盈盈行個萬福,低聲回道:「駱公子,我家公子正打著盹呢!他剛剛睡下。」少女作丫鬟打扮,衣飾雖簡單,卻是上佳絲質衣料。少女有著柳眉大眼巧鼻小口,雖非甚美,卻是八分伶俐機巧外加兩分靈秀之氣;眼睛眨呀眨地直盯著駱奇峰看。
駱奇峰給少女瞧得有些羞赧,移開目光道:「那駱某就不便打擾了……」話未說完,廂內傳出清亮話聲:「是駱兄麼?駱兄快來,我們還沒聊夠呢!……蕾兒……蕾兒!」
少女蕾兒笑應句「就來啦」,回對駱奇峰道:「我家公子倒醒來了。駱公子請先入來。」然後向廂房內裡臥舖上的錦袍男子行去。
錦袍男子吩咐道:「駱兄的茶冷了,給重新沏上一碗。另外這一碗不要碧螺春,換個武夷山烏龍茶。」待蕾兒收去茶碗,錦袍男子手招駱奇峰,大聲道:「駱兄,剛才之事,我可都見著啦!所謂『劍客奇材』,正是像駱兄這等人物!」翹起大拇指比畫一下。這錦袍男子年約三十歲,長眉俊目隆鼻薄唇,唇上蓄有短鬚,目光澄澈柔和。
駱奇峰笑道:「兄弟一身尋常把式,沒甚麼瞧的。藍兄當年福州府應舉時,難道沒趁閒暇上市集瞧瞧師傅們玩胸口碎石、喉頂槍尖的玩意?兄弟這點東西,還不及走江湖的師傅呢!」說著在錦袍男子畔坐下。
蕾兒沏好茶擱在駱奇峰身旁几上,自尋張小椅坐下,縫製衣衫。
錦袍男子微笑道:「當年應舉時哪有這份閒情逸致上街兒逛?」啜口茶,續道:「再說我家風極嚴。就在制科前,家嚴捎了封信予我堂兄藍廷珍,叫廷珍看我嚴些,倘若我私入青樓尋樂子甚麼的,便先打斷我左腳;待我回到家,他老人家再打斷我的右腳!」
駱奇峰知曉藍廷珍眼下新任南澳鎮總兵,隸屬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驃,會心一笑,說道:「結果呢?想來尊大人還是捨不得的了。」錦袍男子做個狡獪表情道:「這信若是捎給其他房的叔伯兄弟手上,說不定我就劫數難逃──可偏生是捎給了藍廷珍,廷珍是軍人出身哪!」
駱奇峰笑道:「怎說?」舉碗喝茶時,見蕾兒正好轉頭過來好奇地看著自己,不禁一愣。
錦袍男子眼透笑意,卻嚴肅地道:「想軍人日常多鍛鍊身體,氣血旺盛,女人是缺不得的。廷珍那時讀完信便說:『鼎元,阿伯說你如果考試不認真,跑去逛窯子,他要打斷你雙腳……還叫我當他老人家的內應呢!』可是他當晚便領我上福州府最為精采的妓院抱姐兒玩個通宵!」藍駱二人同時大笑。
在一旁的蕾兒臉紅過耳,啐了一口,忙低下頭去作著女紅。駱奇峰見蕾兒羞澀神情,心中一動。
藍鼎元斂笑收聲,注視駱奇峰。駱但覺藍眼光有異,問道:「怎麼啦?」藍鼎元問道:「駱兄目下有意中人沒有?」駱奇峰愣呼半晌,回道:「沒有……小弟事功未成,未敢有家室之念。」
藍鼎元笑道:「何謂事功?難道非得名登國子監榜頭、乾清門前掄狀元才叫事功?」駱奇峰乾笑幾聲不接話。藍鼎元續道:「蕾兒這丫頭跟我有段時日,儘管稱不上秀外慧中,倒也算得知書達禮,不遜於一般人家的閨女。她是清白好人家的出身,最要緊地是……」靠近駱奇峰附耳道:「還是處子之身。」駱奇峰吃了一驚,隱約猜到藍接下來要說甚麼,冒了陣手汗。
「我做主將蕾兒許了給你,若何?」藍鼎元神情悠閒地端起碗啜茶,緩緩說道。
駱奇峰心中微動,嘴頭卻道:「不可不可!小弟焉可奪人所好?」
藍鼎元大笑道:「駱兄莫推辭。你難道覺得蕾兒不好?」駱奇峰忙道:「蕾兒姑娘人極好的,我哪裡不喜歡?只是……」
藍鼎元道:「你喜歡便好。我同蕾兒名曰主僕,其實情同兄妹,望你好好待她……」轉對蕾兒道:「蕾兒,從今兒起,你便是駱家的人啦,好生服侍駱兄。駱兄前程大好,妳沒幾年說不定就成了官誥夫人!」蕾兒一旁聽著兩男人說話,未想沒兩句便談到了自己,嬌羞無限,恨不得尋個洞穴鑽將進去。
藍鼎元下床站起,踱向廂房窗邊,開窗透氣。回首道:「蕾兒,去一旁駱兄的房間。我有事單獨同駱兄談談。」蕾兒紅著臉應聲出房,帶緊房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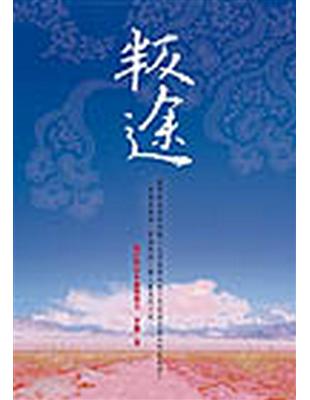

 收藏
收藏

 二手徵求有驚喜
二手徵求有驚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