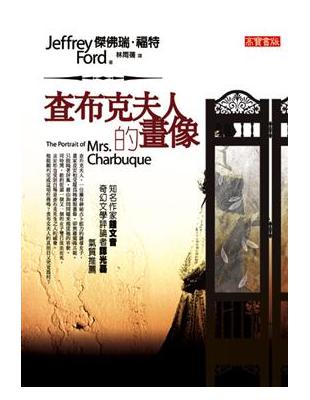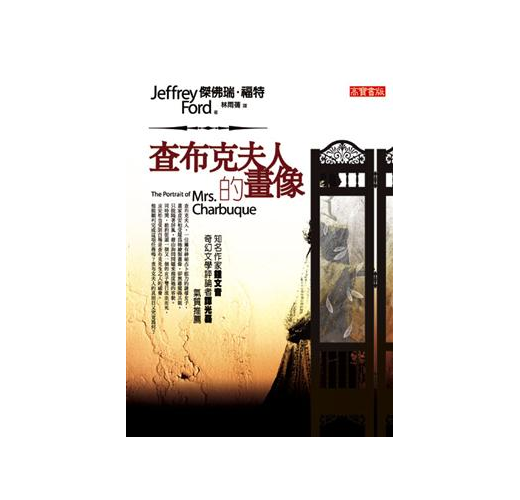世界奇幻獎單年入圍最多項目記錄保持人──美國幻想文學作家傑佛瑞‧福特!
集藝術史、超自然血案、希區考克式懸疑、奇幻謎題和舊時代紐約風華的跨界大作!
鍾文音(知名作家)、譚光磊(奇幻文學評論家)氣質推薦!查布克夫人,一位擁有神祕占卜能力的謎樣女子1893年紐約畫家皮安柏接受了一樁怪異的委託,委託人查布克夫人以驚人的超高報酬,請他繪製自己的畫像,條件是皮安柏必須隔著一道屏風為她做畫,他可以問任何問題,但不可涉及她的外表。一個又一個的奇遇故事,讓畫家陷入想像與現實的謎團隨著皮安柏提出的問題,查布克夫人一一揭露她的過去。她的父親是個雪花占卜師,受雇為富豪占卜未來。一日,她和父親發現了兩片一模一樣的雪花,而這兩片雪花似乎賦與了她預知未來的能力。在父親死後,她周遊列國,以占卜賺取大量財富,如今深居豪宅之內,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隨著查布克夫人愈來愈多的自白,皮安柏發現自己愈來愈陷入她所編織的謎團中……。雙目流血的連續死亡事件,是他殺還是傳染病?同時間,紐約街頭一個又一個的女子雙目流血而死,而皮安柏也受到自稱是查布克先生之人的威脅。他皮安柏能順利完成這項任務嗎?查布克夫人的真面目又究竟為何?
作者簡介:
傑佛瑞‧福特( Jeffrey Ford)1997年以《千面之城》一舉成名,名列紐約時報年度矚目選書,更榮獲1998世界奇幻獎殊榮。隨後又創作《記憶之島》、《彼方之旅》,共稱為《面相師三部曲》。
2003年,傑佛瑞‧福特一舉以四部作品入圍長篇、短篇、小說集等三項世界奇幻獎,締造單年最多入圍數的輝煌記錄。最後他以《奇幻作家的助手》榮獲年度最佳小說集,〈造物〉獲選年度最佳短篇。
《查布克夫人的畫像》雖沒有得獎,但這部集藝術史、超自然血案、希區考克式懸疑、奇幻謎題和舊時代紐約風華的跨界大作早已獲得各界最高評價。
本書已售出法國、塞爾維亞、義大利、日本等國版權。福特現居美國紐澤西州,十六年來在社區大學教授研究寫作、作文和早期美國文學。福特的最新作品是短篇集《冰淇淋帝國》( Empireof Ice Cream)和長篇小說《玻璃中的女孩》( The Girlinthe Glass),前者獲美國科幻學會頒發的星雲獎,後者以1932年經濟大恐慌時期的加州靈媒詐騙集團為題材,獲推理界最高榮譽愛倫坡獎。
Jeffrey Ford得獎記錄:l1997《千面之城》獲紐約時報年度選書l1998《千面之城》獲世界奇幻獎,年度最佳長篇l1999《記憶之島》獲紐約時報年度選書l2000〈奇幻作家的助手〉入圍星雲獎,年度最佳短篇l2002〈蜂蜜結〉入圍世界奇幻獎,年度最佳短篇l2003《查布克夫人的畫像》入圍軌跡獎、世界奇幻獎,年度最佳長篇l2003〈造物〉獲世界奇幻獎,年度最佳短篇。l2003〈造物〉入圍星雲獎、雨果獎、軌跡獎,年度最佳短篇。l2003〈文字的重量〉入圍世界奇幻獎,年度最佳短篇。l2003《奇幻作家的助手》獲世界奇幻獎,年度最佳小說集。l2003《奇幻作家的助手》入圍軌跡獎,年度最佳小說集。l2004〈冰淇淋帝國〉獲星雲獎,年度最佳中篇。l2004〈冰淇淋帝國〉入圍雨果獎、軌跡獎、世界奇幻獎,年度最佳中篇l2006《玻璃中的女孩》獲愛倫坡獎l2006日本講談社推出《查布克夫人的畫像》單行本,入選2006年海外作品最佳科幻/奇幻小說第20名
譯者簡介:
林雨蒨
曾任路透新聞編譯與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海外公關,現為專職譯者,譯有:《蘇格拉底的咖啡館—哲學新口味》(麥田出版)、《療傷的對話》(商周出版)、《我閉上眼睛》(商周出版)、《紫色童話》(商周出版)、《與女人交心》(商周出版)、《女人就是要有野心》(商周出版)、《我44歲,兒子53歲》(商周出版)、《創業致勝的第一本書》(麥格羅希爾出版)、《劣勢者的優勢》(麥格羅希爾出版)等書
各界推薦
媒體推薦:
內容設計精妙、風趣、怪誕且魅力十足,並充滿了不可思議的維多利亞時代文物,是一本充滿閱讀趣味的詭詐驚悚小說。──《蒙特婁公報》( Montreal Gazette)
福特以一派輕鬆自如的筆調,書寫出充滿神秘氣息的文藝作品,從一開始即建立起懸疑感……隨著主人翁皮安柏越來越深陷屏風之後的神秘,小說的高潮一個接一個,很有技巧地一點一點增加張力,因此越逼近尾聲時,讀者就像為了聽故事而活的皮安柏,不惜一切代價只想多知道一些查布克夫人的事情。──《書頁》( Book Page)
在故事中添入說著絕妙華麗詞藻的危險不穩定角色,出人意料的恐怖幽默和暴力,加上與性別有關的次要情節微妙地累積張力,如此你就有了一本傑出的驚悚文學作品。──《出版人週刊》( Publishers Weekly)推薦書評
媒體推薦:內容設計精妙、風趣、怪誕且魅力十足,並充滿了不可思議的維多利亞時代文物,是一本充滿閱讀趣味的詭詐驚悚小說。──《蒙特婁公報》( Montreal Gazette)
福特以一派輕鬆自如的筆調,書寫出充滿神秘氣息的文藝作品,從一開始即建立起懸疑感……隨著主人翁皮安柏越來越深陷屏風之後的神秘,小說的高潮一個接一個,很有技巧地一點一點增加張力,因此越逼近尾聲時,讀者就像為了聽故事而活的皮安柏,不惜一切代價只想多知道一些查布克夫人的事情。──《書頁》( Book Page)
在故事中添入說著絕妙華麗詞藻的危險不穩定角色,出人...
章節試閱
一幅美好的小品讓我頗不自在的是,里德夫人整晚若不是站在她的新畫像之下,就是站在緊鄰的兩側。為了這個場合,她穿戴了替我擺姿勢時我所要求的黑色禮服和鑽石項鍊。在這種情況下,上帝的創作和我作品之間的比較是不可避免的。我料想,在面對我的油畫版本時,全能之神的原作看得出來多少是不夠完美的。祂以無可質疑的智慧決定讓她的鼻子生得很誇張,並認為在門牙之間留下一個顯著的縫隙是適宜的,但我卻讓它們密合,並讓那些使她所以為她的面相特徵,輕描淡寫為一般的美貌。運用淡淡的玫瑰色並省略明暗對照,我在色調上添加了青春的光澤,並在她的肌膚上增加彈性,把時間拉回至這些改變恰好不致顯得可笑的那一點上。里德夫人或許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些差異吧,或者,儘管意識到了,卻相信藉由盡可能地靠近那個較美的自己,她可以讓朋友和家人心中所見的畫像和現實永遠混淆。或許她希望的是肉體和畫像之間能有某種超自然的轉換,一如王爾德最近的小說《格雷的畫像》( The Portraitof Dorian Gray)裡的情節。無論如何,她顯然一臉喜色。至於我們這些其餘的出席者,全都是不自在地忽略真相的計謀共犯。還好她先生為了畫像的揭幕花了不少錢買了上好的香檳,並鼓勵大家隨意飲用。五十多位的賓客中有許多人覺得,無論如何都有必要前來讚譽我的作品,而如果不是有酒精的話,我的表情可能會抽搐個不停吧。
「皮安柏,里德夫人旁邊的桌上,那個碗裡頭的金魚畫得真是驚人啊。我從這裡就可以數算那些鱗片。」
「她後面那只中國花瓶裡貧乏枯萎的水田芥真是栩栩如生。」
「沒有人像你那麼會畫禮服的皺摺,而且天呀,那些鑽石多閃亮啊!」我禮貌地謝謝大家,心裡明白接下來的一年,我會替他們之中某些人做我替里德夫人所做完全一樣的事情。當我以為自己終於可以一個人的時候,我在畫像藝術界的同僚錫尼斯側著身子走到我身邊。這位玩弄著自己修得很緊密、尖尖山羊鬍的矮個子男人,以信奉前拉斐爾信條,和替范德堡親族中不那麼閃亮的人物畫畫像而出名。他用一根大雪茄隱藏他惡作劇般的露齒微笑,眼神越過寬敞的客廳凝望畫像。
「一幅美好的小品,皮安柏。」他說,然後微微轉過頭來,盯著我看。
「再多喝點香檳。」我對他輕聲說道,他也低聲笑了。
「是我就會說有益健康,」他說,「沒錯,相當有益健康。」
「我在做紀錄,」我告訴他,「看看大家是比較欣賞金魚還是水田芥。」
「把我算在喜歡鼻子的人裡,」他說,「真是巧妙的繪畫配置。」
「我想那也是里德最喜歡的。他為了這個鼻子付我特別高的費用。」
「應該的,」錫尼斯說,「我認為你的神奇已經蠱惑了他的夫人,完全忘了他與梅西百貨那位售貨小姐的言行不檢。他的現貨鞋廠最近賺的大筆財富不管用,只有你的才能可以挽救他的婚姻和面子。」
「上帝知道這事兒不只是畫畫這麼簡單。」我說,「誰是你的下一個受害者?」
「我今晚才剛接到一件委託,要化海德史戴爾斯的肥胖子嗣為不朽。那是兩個過度餵食的小怪獸,我打算給他們吃鴉片酊,好讓他們可以在我面前坐著不動。」他走開之前舉起他的香檳酒杯敬酒。
「敬藝術。」水晶玻璃杯的邊緣相碰時他說。錫尼斯走開後,我在一盆蕨類植物旁邊坐下,點燃自己的雪茄,呼出讓我可以隱身在後的一陣煙霧。這時候我已經喝了太多杯香檳,頭都暈了。室內中央垂掛的裝飾水晶燈反射出的光線,加上那些讓紐約社會有錢暴發戶的夫人們更添花容月貌的珠寶閃光,幾乎讓我目盲。偶爾,片段的對話會從聚集賓客如海洋般低沉的嘈雜聲中跳出,於是在短短幾分鐘內,我已聽到各式各樣討論的隻字片語,從芝加哥哥倫布博覽會的開幕,到《世界報》的新漫畫中那個住在「下豪根後巷」、穿著男用睡衣小孩的滑稽行為等。在恍惚之中我突然想到,不只所有人都要找我,他們還需要我。我發現自己最近在吊有水晶燈的客廳內喝酒喝到快不省人事的時間,比我坐在畫架前還長。此時,社交聚會常客所形成的海洋轉了個方向,我的眼睛也在此時聚焦了,我瞥見里德夫人獨自一人站著,凝望自己的畫像。從我這裡只看得到她的背影,但我看到她慢慢抬起一隻手臂,從她的手摸到她的臉,然後迅速轉身離開。下一瞬間,我的視野再度被一位穿著綠色絲質禮服的女人所遮蔽,那個顏色讓我想起自己現在正感受到的那股想要嘔吐的痛苦。我在蕨類植物的花盆裡熄滅雪茄,然後蹣跚地起身。幸運的是,不用在密集的歡鬧中走太遠,我就找到女傭,要求她將我的外套和帽子遞給我。我的計畫是趁別人不注意的時候盡快離開,但在朝著通往樓下大門的樓梯走去時,卻被里德擋住。
「皮安柏,」他叫道,「你還不能走。」我轉過身,看到他站在那裡,身子微微搖晃著,眼皮半掩。他露出里德專屬的緊閉雙唇式微笑,這對所有人,除了那些善於分析肢體效果的肖像畫家之外,都是一個善意的微笑。這個男人的俊帥很有現代感,蓄著鬢角和八字鬍,還有宛如由聖高頓之手雕刻出來的輪廓。他也非常走運,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我告訴你,當我研究他的時候,我看到的是一個機械化的偽善工廠。
「你可是貴客。」他說,走向我,把一隻手放在我肩上。
「原諒我,」我輕聲說,「但我有罪,居然想自己一個人喝掉那些美好的香檳。我的頭在暈了,所以我需要一些空氣。」他大笑出聲,而他的喧鬧聲引得附近的賓客都轉頭來看。我尷尬地注視這群人一會兒,而在所有這些搞不清楚里德何以發笑、卻跟著他一起笑我的面孔中,我看到錫尼斯搖著頭望向天花板,對我發出祕密的訊號,是的,里德真是個蠻橫的白痴。
「在你走之前,讓我把我夫人找來。我肯定她想向你道謝和道別。」
「好的。」我說。里德走開不見人影,我則站著,往下凝視通往逃難出口的那一段漫長階梯。過了一會兒,他拉著他太太回來了。
「皮安柏在城的另一頭還有急事,親愛的,」他告訴她,「他不得不離開了。我想你會想要感謝他畫的畫像。」里德夫人面露微笑,我則注視著她牙齒間的縫隙。在我和她相處的那些日子裡,她看起來幾乎沒有自己的人格。她一直是個順從的模特兒,不會不愉快,但我從未嘗試捕捉她真正的本質,因為她先生雖然沒怎麼明說,卻讓我知道這幅畫像的內在精神並不是重點。她往前跨出一步,看起來似乎要親吻我的臉頰。在那一瞬間,就在她靠向我的時候,我瞥見了一種一閃而逝,比我所習以為常的呆滯更點什麼的東西。然後,她的雙唇掠過我的臉龐,而在她抽身之前,我聽到她的細語,聲音不比濕水彩筆滑過畫布那樣更大聲:「我希望你死。」當她的臉再整地出現在我面前時,我看到她微微笑著。
「謝謝你,皮安柏。」現在她說。里德以手臂環抱著她,兩個人站在一起的樣子,宛如在替一幅描繪婚姻至福的作品擺姿勢。本來我這麼多年已訓練出好眼力,可以看到坐在我面前的人的靈魂的技能,為了交換錫尼斯所謂的有益健康,這能力最近都被我擱置一旁,現在卻突然作用起來,而我看到的是一位被吸血鬼抓住的蒼白且疲倦已極的婦女。我轉過身快步離開,在樓梯上走得有點踉蹌,閃避那種把小孩拋棄在冰冷河中時可能會有的感覺。
2?帶信人我經過里德請來送賓客回家的有蓋雙座小馬車,朝自己的左邊轉過去,沿著第五大道往南走。我的頭依舊因為酒精和里德夫人輕聲說出的話語而暈眩著。我豎起外套的衣領,壓低帽緣,因為在宴會進行的過程中,夏天似乎靜悄悄地消逝了。一陣狂風沿著大道吹向我的背,一張變黃的報紙飛搞過我的左肩,並在瓦斯燈下拍動飛舞著,有如這個溫暖季節中奔逃的鬼魂。時間很晚了,我還要走過很多個十字路口才能回到位於格拉莫西公園的家,但我現下最需要的就是空氣、移動和夜晚,作為擁擠客廳裡的污濁,和那該死的水晶燈虛假散裂光線的解毒劑。城市街道在這個陰暗的時間是很不安全的,但不論我會遭遇到多麼惡意的攻擊者,肯定不會像里德那樣傷人於無形。想到他可憐的妻子可能忍受了些什麼,以及我自己儘管不太明智卻自願參與了對她的虐待,我搖了搖頭。現在對我來說很清楚的是,她一直都知道我們在玩些什麼。最有可能她是顧及小孩,同時也是為了自己的生存,因此假裝很喜愛里德的誇耀。如果這是第一次,我懷疑這不會是最後一次,但是,未來她的尊嚴每受一次攻擊,我畫中那迷人而永恆的美將永遠是她醜陋婚姻和人生的見證。那個幾乎和她一模一樣卻又不盡相同的面容,無疑是她先生想要的女人。事實上,真正的里德夫人更像是受困於那只碗裡的金魚,以及華美的中國花瓶裡剪下並枯萎的花朵。我選擇這些道具時,並沒有意識到它們無意間透露出我自己的感受。
「皮安柏,你變成了什麼啊?」我對自己說,並發現我是真的大聲說出口。我左顧右盼有沒有哪個路過的人聽到我說的話。不過,沒有,其他幾個少數在這麼晚的時間裡上街走動的人只是繼續走著,包覆於他們自己的渴望和告誡中。白天時,這座城市像是對他人有巨大影響且不顧一切的百萬富翁,以狂亂的能量追求未來,並終有一日戰勝它的目標;但在夜晚,當城市在做夢的時候,街頭卻像是一個深海王國裡被魑魅魍魎纏繞的大道。連有軌電車都以較為倦怠的步調移動著,像是在黑暗中遊走的一條大蛇,那黑暗因為白日所不容的懊悔而更添濃郁。我在三十三街的角落駐足,在月光下窺視大道對面那曾經是約翰.雅各.阿斯特1的豪宅遺跡,好讓自己不去回答前面提出的問題。我在報紙上看到,他的兒子不顧母親的惱怒,要把這座老建築夷為平地,並豎立起一間精緻的飯店。它就在那裡,已經被拆了一半,像是維德2畫筆下某隻沖刷上岸的腐爛巨獸屍體。這是對這座城市新財富的腐蝕力量提出證詞。即使是老舊的神像和它們留給後人的東西,都無法在這樣的猛烈攻勢下倖免於難。財富是新的神祇,而且有一大票里德之屬,願意修正自己的道德標準以加入祭司的行列。它的教義問答從曼哈頓島的上方一路往下涓流至下東城,那裡的移民家庭追逐著這個他們尚未能輕易掌握的不實在精神。在面對如此滲透的社會狂熱,我一介小小的畫家如何能不為它所改變?當攝影在不算太久之前也成為一門藝術的時候,和我同樣專業的人倒抽一口氣,驚慌地摒住呼吸,以為自己將窮途末路。但當那些富有的人發現,即使是一個散工現在也可以廉價地擁有一幅自己的肖像時,支付畫像潤筆費給有名畫家的做法,在貴族階級和白手起家的菁英之間突然大行其道。畢竟,照片在一或兩個世代內就會變黃碎裂,但油畫卻能長久封存它所頌揚的主題。於是,鈔票的暴風雪開始降下,朦朧了我起初意圖以我的才能所追逐的遠景。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開始受到人像藝術這一方面的鞭苔,約翰.薩金特3稱之為「虛榮的專橫」──由委託人一手策劃和建立之錯綜複雜的陰謀網絡。由於薩金特是肖像畫之王,我的風格不由得逐漸變化成他那運筆自如的現實主義但彈性略有不及的版本。我應該說,我比大多數也從善如流的同僚更精於此,但薩金特只有一位,而我並不是他。不過,錢財與特定的名聲還是來到我身上,我在幾乎不知不覺的情況下,對自己做了我對里德夫人所做的事情。我能失去的比她少很多,但我也選擇了金魚缸那確切卻看不見的框限,因此我的生命也一如安置在華美花瓶中被剪下來的花朵一樣由內凋萎。走著走著,新鮮的空氣發揮了它的效果,我清楚地發現重要的問題不是:「我變成了什麼?」而是:「我現在要做什麼?」我要如何回到舊有的自己,並在我老到已經不在乎且虛弱到無法嘗試之前,畫出有價值的作品呢?我轉過頭看自己的影子經過一間商店的玻璃櫥窗,就在此時我想起自己約於一年前在美國設計學院看到的一幅畫。我忘了那幅畫名叫「賽馬場」還是「挫敗」,是由生於新貝福德、畫風如謎的亞伯特.平可漢.萊特1所畫。他現居於東十一街上某個地址,但在十五街上一間狹隘、破敗的閣樓裡作畫。我透過我在格拉莫西的鄰居,也就是《世紀雜誌》的編輯理查.吉爾德,曾與他有過短暫會晤。那幅畫給人的感覺很痛苦,因為它描繪的是一個骷髏般的死神,騎在一匹獨自在賽馬場上順時鐘奔跑的馬上,揮舞著鐮刀。前景有一條蜿蜒前進的蛇,背景則是低垂的赭色、火燒似的黃褐色,和一點難以區分但潛伏的緋紅色天空,完美地捕捉到暴風雨前夕的昏暗死寂。這幅作品描繪的是陰冷的恐怖情緒,而任何膽敢買下它並掛在客廳的人根本是在邀請惡夢入內。那幅景象訴說的是真實,這和廣受有錢階級歡迎、技巧完美且風格安全的薩金特作品正好相反。吉爾德曾告訴我,萊特是在聽到一位服務生的故事後畫下這幅畫的,那位服務生在他兄弟的飯店裡工作。這個可憐人克勤克儉地省下五千美元,卻在漢諾威一次賭馬的失敗中全盤皆輸。輸光一切後,他自殺了。這幅畫是萊特對他的悼辭。有買主的時候萊特會出售作品,但他作畫時並沒有把錢考慮在內,只是盡心盡力地用畫來捕捉那些不能言喻之事。不論怎麼說,他都是一個怪人,有點羞赧,離群索居,作畫時則會利用手邊任何東西──酒精、蠟燭的蠟、亮光漆、汽油等。當筆刷表達不出他要的效果時,據說他用調色刀來擴散濃稠的大塊塗料。當調色刀也不管用時,他用自己的手,而當亮光漆塗抹不出他要的質地時,據說他還用了自己的唾液。他會先畫一幅畫,然後在顏料乾掉以前,又在上面另畫一幅。我不會說他很天真,但當我遇到他時,我察覺到他身上一望即知的純真。他平靜的舉止,碩大的體格和滿臉的鬍子,給我的印象猶如聖經中的先知。我記得自己在還是 M.沙布特的年輕門生時,曾看過萊特的一幅海景畫。那是一艘在波濤洶湧海上的小船,散發出大自然勢不可擋的力量,以及船首渺小水手的過人勇氣。沙布特站在我旁邊,稱這幅畫為「一團混亂」。
「這個人像是拿自己的糞便塗抹在育嬰室牆上的寶寶。沒什麼成為大師的可能。」他說。有好一陣子,在我碰巧到萊特的畫廊高提爾公司,或是在入選展上看到他的油畫時都會想起這個評語。沙布特或許言之有物,但是,喔,回歸嬰兒時代,陶醉在那樣奇異的視野中,甚至忽略這個世界的里德以及他們的財富!萊特的一位熟人曾經對我引述萊特寫給他的信。
他在信上寫道:「你曾經看過尺蠖爬上一片葉子或是小樹枝,然後抓著那個尖端,在空中旋轉一下,想要去感覺什麼,想要去碰觸什麼嗎?那就像是我這個人。我試著在超越自己的立足處找到什麼。」我在二十一街左轉,走向我的住處,並明白這正是我所需要的。祕訣就是超越我自己目前存在的安全範圍,並重新發現身為藝術家的自己。我唯一的恐懼是,在往外伸展時,我可能什麼也抓不到。我的年紀已經過了巔峰期,開始朝終點邁進。或者容我們這麼說吧,我可以感受到我越來越稀薄的頭髮上方呼嘯而過。萬一我失敗了,又失去紐約最受歡迎肖像畫家之一的地位怎麼辦?我又想起萊特所畫馬背上的死神,然後是那個存了錢又一次揮霍掉所有的傻子。我在認真沉思過後,變得更迷惑了。對於財富和安全的追求,以及對一種道德真實的追求,我可說是聰明地在中途換了馬。我想成為不是自己的另一個人,這渴望浮現檯面,充滿了好的意圖,卻如香檳上的泡沫一樣幻滅。我搖搖頭,對自己的兩難笑出聲來,同時感覺到左邊的皮膚微微碰觸到了什麼。我抬起頭看到有個男人倚牆而立,讓我吃了一驚。
我雖然打起精神說:「很抱歉,先生。」語氣中卻有股惱怒。他抽回他碰觸到我的黑色拐杖,走上前來。他體型碩大但年邁,蓄著短短的白鬍子,光禿禿的頭皮周遭也有一圈的白髮。他的三件式西裝是淡紫羅蘭色的,在人行道邊欄附近的街燈照射下,映出一抹有趣的淺綠。這不尋常的光影吸引了我片刻的注意,直到我看向他的臉並因此嚇了一跳,因為我發現他的眼睛沒有清楚的瞳孔和虹膜,兩隻眼睛都被一片白色所覆蓋。
「我相信你就是署名為皮安柏的那位畫家。」他說。任何和眼睛有關的壞事都會讓我很難受,我好一會兒才從他的視線中回神。
「我是。」我說。
「我的名字是瓦金。」他說。
「有什麼事嗎?」我問,以為他接下來會想碰我,跟我要點零錢。
「我的雇主想請你幫她畫一幅畫像並支付你潤筆金。」他的聲音柔和,但在精準的話語中卻隱含著一股威脅。
「恐怕我接下來幾個月都已經有約了。」我說,準備離開。
「要畫就是現在。」他說,「她除了你以外不作他想。」
「我讚嘆這位好女性的品味,但我恐怕已經對其他的安排做出承諾。」
「這是一件非比尋常的工作。」他說,「你可以提出你的價格。把其他你已經承諾的潤筆金加進來,算出你可以收到的總數,她會給你這個總數的三倍。」
「你的雇主是誰?」我問。他把手伸進他的外套口袋,拿出一只玫瑰色的信封。他拿給我的樣子,與其說是給我,還不如說是遞給全宇宙,讓我更加確認他是位盲人。我遲疑著,感覺自己並不想和這位瓦金先生有什麼牽連,但他說「這是一件非比尋常的工作」的那種方式,卻讓我伸手接下信封。
「我會考慮的。」我說。
「這樣就好,這樣就好。」他微笑著說。
「你怎麼知道要到這裡找我?」我問。
「直覺。」他說,同時把拐杖往前伸,掉頭面西,與我擦身而過。他一邊走,一邊以拐杖的尖端間歇地輕敲著建築物的外牆。
「你怎麼知道是我?」我在他身後大聲問道。在他的身影消失於夜色之前,我聽到他說:「自滿的味道;瀰漫著一股肉荳蔻和發霉的氣息。」
一幅美好的小品讓我頗不自在的是,里德夫人整晚若不是站在她的新畫像之下,就是站在緊鄰的兩側。為了這個場合,她穿戴了替我擺姿勢時我所要求的黑色禮服和鑽石項鍊。在這種情況下,上帝的創作和我作品之間的比較是不可避免的。我料想,在面對我的油畫版本時,全能之神的原作看得出來多少是不夠完美的。祂以無可質疑的智慧決定讓她的鼻子生得很誇張,並認為在門牙之間留下一個顯著的縫隙是適宜的,但我卻讓它們密合,並讓那些使她所以為她的面相特徵,輕描淡寫為一般的美貌。運用淡淡的玫瑰色並省略明暗對照,我在色調上添加了青春的光澤,...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