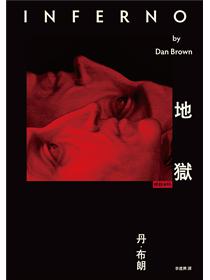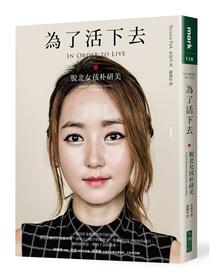「看了小說後,對這部電影有了新的感動。」
「原著小說是理解這部電影不可或缺的關鍵。」
「看過電影後,讀小說仍讓我感動到流淚。」★創下台灣影史新紀錄,日片票房No.1,千萬人次淚眼推薦──新海誠最新力作《你的名字。》,原作小說終於登台!
★附《你的名字。》製作人、《如果這世界貓消失了》作者──川村元氣解說,暴露《你的名字。》創作源起。
★《你的名字。》原著小說在日銷售突破1,000,000冊,日本Amazon網友五星好評:
「看了小說後,對這部電影有了新的感動。」
「原著小說是理解這部電影不可或缺的關鍵。」
「看過電影後,讀小說仍讓我感動到流淚。」未曾相識的兩人,
不可解的相遇,
讓命運的齒輪開始轉動──
家住深山的女高中生三葉,每天過著鬱鬱寡歡的生活。
身為鎮長的父親參與的選舉、家中神社的古老習俗、狹小的村莊──在莫名在意四周眼光的年紀,她對都會生活懷抱強烈憧憬。
「下輩子,請讓我生為東京的帥哥!」
某日,三葉夢見自己變成男高中生。
不曾看過的房間、不認識的朋友、繁華的街道與時髦的咖啡廳──三葉在夢裡盡情享受了渴望的都市生活。
住在東京的男高中生──瀧,也做了奇怪的夢。在夢裡,他是家住深山的女高中生。
偶有遺落的記憶與時間,不可思議卻不斷持續的夢境……三葉和瀧終於察覺:
「我和他(她)互換靈魂了嗎?」
作者簡介:
新海誠
Makoto Shinkai
日本動畫導演,一九七三年出生於長野縣。二○○二年,以幾乎是個人獨立製作完成的《星之聲》獲得注目,之後陸續發表了《雲之彼方•約定的地方》、《秒速五公分》、《追逐繁星的孩子》、《言葉之庭》等廣獲國內外好評的動畫作品。除了動畫之外,親自執筆的《秒速五公分》、《言葉之庭》原作小說也獲得極高評價。
譯者簡介:
黃涓芳
畢業於台灣大學外文系及語言所,曾任創意編輯、英語研究員等職。目前為英、日文自由譯者。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夢
懷念的聲音與氣味,依戀的光線與溫度。
我和心愛的某個人緊密地貼合,彼此難分難捨地連結在一起。就像夾在乳房間的嬰兒時期,沒有絲毫不安與寂寞。我尚未失去任何東西,幸福甜美的情感擴散至整個身體。
眼睛突然張開。
天花板。
房間。早晨。
一個人。
東京。
──原來如此。
剛剛在做夢。
我從床上起身。
僅僅在這大約兩秒的時間裡,先前包覆著我的溫暖歸屬感已消失殆盡,不留痕跡,也沒有餘韻。由於太過突然,我還來不及思考就掉下眼淚。
早上醒來時,我有時會不知為何在流淚。
我總是想不起前晚的夢境。
早上醒來時,我盯著右手,食指上沾著小小的水滴。前一刻的夢以及短暫沾濕眼角的淚水,都在不知不覺中乾涸了。
曾經,有過很重要的東西。
在這隻手上。
──搞不懂。
我放棄思考,下了床,走出房間前往洗手間。我邊洗臉邊覺得,自己之前好像也曾為了自來水的溫熱和味道感到驚訝。
我凝視鏡子,帶著些許不滿的臉從鏡子裡回瞪著我。
我看著鏡子綁起頭髮,穿上春天的套裝。
我繫上總算習慣打法的領帶,穿上西裝。
我打開公寓的門。
我關上大廈的門。在我眼前──
總算開始熟悉的東京風景出現在眼前。就如過去自然而然記住各座山峰的名字,現在我也能說出幾棟高樓大廈的名稱。
我穿過擁擠的車站驗票口,下了電扶梯,
我搭上通勤電車,靠在車門望著流動的風景。不論是大樓窗戶、車輛、天橋,街上到處都有許多人。
春季的陰天,天空白茫茫的。一百人搭乘的車廂,載送一千人的列車,一千班像這樣的列車行駛的城市。
不知不覺中,我像平常一樣,一邊望著街道──
一邊尋找唯一的某一個人。
一邊尋找唯一的某一個人。
第二章
開端
沒聽過這種鈴聲。
我在朦朧意識中這麼想。
是鬧鐘嗎?可是我還想睡。昨晚我全神貫注地畫畫,直到天快亮才上床。
「……瀧。」
接著聽到有人呼喚我的名字。是女人的聲音……女人?
「瀧、瀧。」
聲音彷彿快要哭出來般急切,宛若遠處閃爍的星星般寂寞而顫抖。
「你不記得了嗎?」
聲音不安地問我,可是我不認識妳。
電車突然停止,車門打開。對了,我正在搭電車。當我意識到的瞬間,發現自己站在擁擠的車廂中,眼前有一雙張大的眼睛。直視著我的少女穿著制服的身影,被下車的乘客推擠,自我身邊遠離。
少女喊:「我的名字是三葉!」
她解開綁頭髮的髮繩遞給我,我不加思索地伸出手。鮮橘色的髮繩彷彿射入昏暗電車中的一道細細夕陽光線。我將身體鑽入人群,用力抓住那道色彩。
這時我醒了過來。
少女聲音的殘響仍舊隱約留在我的耳膜。
……名字是三葉?
我沒聽過這個名字,也不認識那個少女。她的態度非常急切,我想起她那雙快湧出淚水的眼睛、陌生的制服、宛若關係到宇宙命運般嚴肅而凝重的表情。
不過,反正只是個夢,沒有任何意義。此刻我已經想不起那張臉,耳膜的殘響也已經消失。
即使如此……
即使如此,我的心跳仍舊異常劇烈,胸口感覺格外沉重,全身大汗淋漓。我姑且深深吸了一口氣。
吸~
「……嗯?」
是感冒了嗎?鼻子和喉嚨有些怪怪的,空氣流經的通道比平常更窄。胸口異常沉重,說得更明白一點,是物理性質的沉重。我低頭看自己的身體,看到乳溝。
──看到乳溝。
「……嗯?」
豐滿的胸部反射朝陽,白皙的肌膚柔滑光亮。雙峰間沉澱著湖水般青色深邃的影子。
先揉揉看再說。
這是我腦中第一個念頭。這個念頭就如蘋果掉落到地面般,幾乎依循普遍而自動的法則出現。
………………
…………
……嗯?
!
太感動了。哦哦哦!這是什麼?我很認真地繼續揉。該怎麼說……女人的身體真是神奇……
「……姊姊,妳在幹嘛?」
我聽到聲音轉頭,看到一個小女孩打開拉門站在那兒。我邊揉胸邊說出老實的感想:
「沒什麼,只是覺得好有真實感……咦?」
我重新審視眼前的女孩,她大概十歲左右,綁了兩條馬尾,眼尾有些上揚,一副囂張小鬼的樣子。
我指著自己問:「……姊姊?」
這麼說,這傢伙是我妹妹?
女孩露出傻眼的表情對我說:
「妳在說什麼夢話?吃、飯、了!快點來吃!」
她重重關上拉門,發出「啪」的聲音。這女孩真是凶暴。我從被窩起身,感覺到肚子也餓了,這時注意到視野角落的梳妝台。我在榻榻米上走了幾步,來到鏡子前方,把鬆垮的睡衣從肩膀拉下來,睡衣便滑落到地板上,露出赤裸的身體。
我仔細檢視映照在鏡子裡的全身。
黑色流水般的長髮,有幾處因為睡覺時壓到而翹起來。小小的圓臉、彷彿會說話的大眼睛、像是在笑的唇型、細細的脖子和深凹的鎖骨、彷彿在主張「承蒙關照,發育得很健康!」的胸部隆起,然後是隱約浮現的肋骨陰影,以及肋骨下方柔和的腰部曲線。
我雖然沒有親眼看過,但這無疑是女人的身體。
……女人?
我是女人?
先前還籠罩在身上的睡意消失了,我的腦袋頓時清醒,並頓時陷入混亂。
然後,我忍不住大聲尖叫。
* * *
「姊姊,妳~好~慢~!」
我打開拉門進入起居室,四葉就用攻擊性的聲音指責我。
「明天我來做飯。」
我用這句話代替道歉。這孩子雖然是個乳牙都還沒全部換齊的小鬼,卻似乎自認比姊姊更可靠。我絕對不能道歉,免得被她抓到把柄。我邊這麼想邊打開電子鍋,把晶瑩剔透的白飯盛入自己碗裡。嗯?會不會太多?算了,沒關係。
「開動~」
我在滑嫩的荷包蛋上淋了滿滿醬汁,和白飯一起放入口中。啊啊啊,好好吃,真幸福……嗯?我的太陽穴一帶似乎感覺到視線。
「……今天很正常。」
「嗯?」
我發現外婆正盯著咀嚼米飯的我。
「昨天真的很誇張!」
四葉也笑嘻嘻地看著我。
「還莫名其妙地發出尖叫。」
尖叫?外婆的視線好像在檢查可疑物品,四葉的笑容則(一定是)把我當成傻瓜。
「什、什麼?怎麼回事?」
搞什麼?這兩人好像聯合起來,感覺真討厭。
『嗶波啪波~』
位在拉門上端橫木的喇叭,突然發出暴力般的音量。
『各位鄉親,大家早。』
這聲音是好友早耶的姊姊(任職於鎮公所的地區生活資訊課)。這座糸守鎮是人口只有一千五百人的窮酸小鎮,因此大多數人都彼此認識,或者是認識對方認識的人。
『現在開始播報糸守鎮的晨間通知。』
從喇叭傳來的聲音在每個詞之間都會停頓,非常緩慢地念出「現在、開始、播報、糸守鎮的、晨間、通知」。全鎮的戶外也設有喇叭,所以廣播會在群山之間迴盪,重疊出輪唱般的回音。
這是每天毫無間斷、早晚兩次對全鎮播放的防災廣播。鎮內家家戶戶都有接收器,每天規律地播報各種鎮上活動,譬如運動會日程、聯絡掃雪值班、昨天誰家生了小孩、今天是某某人的喪禮等等。
『針對下個月二十日舉辦的糸守鎮長選舉,鎮上選舉管理委員會──』
噗吱。
橫木上的喇叭沉默了。喇叭設在伸手無法搆到的地方,因此外婆直接拔掉插頭。年過八十、總是穿著傳統和服的外婆,以行動表達無言的憤怒,真酷。我邊想邊拿起遙控器,合作無間地打開電視。早耶姊姊的聲音消失後, NHK的大姊姊笑容可掬地播報起新聞。
『一千兩百年一度的彗星終於要在一個月之後來臨。屆時連續好幾天,都可以用肉眼觀測到彗星。為了迎接難得一見的天文奇景,JAXA等全球研究機構都準備進行觀測。』
畫面上出現「一個月後肉眼即可觀測到提阿瑪特彗星」的文字,以及模糊的彗星影像。起居室的對話中斷,在NHK的播報聲中,只有我們三個女人用餐的聲音,彷彿上課中的悄悄話,發出窸窸窣窣、喀喳喀喳,感覺有些內疚的聲音。
「……差不多該和好了吧?」
四葉突然不識相地發言。
「這是大人的問題!」
我斬釘截鐵地說。沒錯,這是大人的問題。什麼鎮長選舉嘛!不知從何處傳來老鷹「嗶~咻嚕嚕~」的叫聲,聽起來有點愚蠢。
「我們去上學了!」
我和四葉齊聲向外婆道別後走出家門。
夏天山上的鳥叫聲量相當驚人。
我們沿著斜坡走下狹窄的柏油路,爬下幾階石牆階梯便走出山的陰影,迎向直射的陽光。底下是圓形的糸守湖,平靜的湖面映照著朝陽,毫不客氣地反射刺眼的強光。深綠色的山巒、蔚藍的天空、白色的雲,身旁還有一個背著紅書包的雙馬尾小女孩莫名其妙地蹦蹦跳跳,而我則是穿著短裙、裸露著雙腿的女高中生。我試著想像宏壯的弦樂合奏背景音樂。喔,感覺好像日本電影的開幕場景。換句話說,我們所住的地方就是日本昭和時代風格的鄉村。
「三~葉~!」
我在小學門口送走四葉後,有人從背後呼喚我。我回頭看到板著臉踩著腳踏車的勅使,還有坐在後座笑咪咪的早耶。勅使喃喃抱怨:「快點下車!」「有什麼關係,小氣鬼!」「很重耶!」「真沒禮貌!」兩人從早上就像在上演夫婦相聲般打情罵俏。
「你們感情真好。」
「一點都不好!」
兩人異口同聲說道。他們一本正經地否定的態度實在太好笑,我不禁呵呵笑出來,腦中的背景音樂切換成輕快的吉他獨奏。我們三人是十幾年的老朋友。早耶的個子嬌小,留著齊眉瀏海,綁著兩條辮子;勅使瘦瘦高高的,平頭的髮型有些土氣。兩人雖然好像總是在吵架,可是對話節奏搭配得完美無缺,因此我暗自覺得他們其實是天生一對。
「三葉,妳今天頭髮很正常。」
早耶下了腳踏車,摸著我的髮繩附近嘻嘻笑。我總是梳同樣的髮型:把左右兩邊的辮子繞到腦後,用髮繩綁起來。這是很久以前媽媽教我的綁法。
「頭髮?什麼意思?」
我又想起早餐時曖昧不明的對話。「今天很正常」的意思,是指昨天不正常嗎?我正努力回想昨天的情況,勅使便擔心地湊過來問:
「對了,妳有沒有請外婆幫妳驅邪?」
「驅邪?」
「一定是被狐狸附身了!」
「啥?」唐突的言論讓我皺起眉頭。早耶似乎也對他的說法不以為然,替我代言:
「你為什麼一定要扯到靈異事件?三葉一定是累積太多壓力了。對不對?」
壓力?
「呃……等、等一下,你們在說什麼?」
為什麼大家都在替我擔心?我昨天……雖然一時想不起來做了什麼,不過應該是很平常的一天才對。
──咦?
真的是這樣嗎?昨天我……
『更重要的是──』
透過擴音器的粗嗓子打消我的疑惑。
道路對面林立著塑膠布溫室,另外還有一座過於寬敞的鎮營停車場。停車場內聚集了十幾個人,站在中央手拿麥克風、個子特別高而威風凜凜的人物就是我爸。掛在西裝上半身的布條自豪地寫著「現任.宮水俊樹」。他正在進行鎮長選舉的演說。
『更重要的是持續進行聚落再生計畫。為此必須讓鎮上財政健全化!滿足這些條件,才能打造安全、安心的城鎮。身為現任鎮長,我希望能繼續完成目前的造鎮計畫,並且更加精進!我會以全新的熱情引導這座小鎮,使其成為男女老幼都能安心居住,並且充滿活力的地方社會!我將以嶄新的決心,把這項任務當成自己的使命……』
純熟到專橫地步的演說,簡直就像電視上的政治人物,和這座農田環繞的停車場完全不搭調,讓我覺得很尷尬。聽眾當中有人交頭接耳地說「反正這次一定也是宮水先生當選」、「聽說他撒了很多錢」,使我的心情更加灰暗。
「嗨,宮水。」
「……早安。」
慘了,和我打招呼的是我在班上最不擅長應付的三人組。他們在高中屬於時髦華麗階級,對我們這些樸素類型的同學總是語中帶刺。
「鎮長和搞建築業的。」其中一人刻意看著演說中的鎮長說道。我看到勅使的爸爸滿面笑容地站在父親身旁,穿著自家建設公司的外套,手臂上戴著「宮水俊樹加油團」的臂章。那個同學看看我又看看勅使,繼續說:
「連他們的孩子都勾結在一起。你們是因為家裡吩咐,所以才湊在一塊嗎?」
真蠢。我沒有回答,加快腳步想要離開這些人。勅使也面無表情,只有早耶顯得不知所措而坐立不安。
「三葉!」
突然有人大喊,我差點停止呼吸。真不敢相信!演說中的父親沒有透過麥克風,而是以大嗓門朝我大喊,聽眾也同時轉向我。
「三葉,走路要抬頭挺胸!」
我滿面通紅。太過不近情理的對待差點讓我掉下眼淚。我忍住想要奔跑的衝動,大步離開現場。聽眾當中有人悄悄說:「他對家人也這麼嚴厲。」「不愧是鎮長。」我也聽到班上同學嘲諷地說:「哇,好凶!」「好可憐喔!」
太慘了。
腦中先前的背景音樂不知何時已經消失。我想起這座小鎮如果沒有搭上背景音樂,就只是一個令人窒息的場所。
喀、喀、喀,粉筆在黑板上寫出類似短歌的文字。
莫問彼何人菊月寒霜露濕身吾依然待君
「『彼何人(tasokare)』,這是日文裡『黃昏(tasogare)時分』的語源。你們聽過『黃昏時分』吧?」
小雪老師用清脆的聲音說完,在黑板上寫了大大的「彼何人」三字。
「傍晚,既非白天也非夜晚的時間。人的輪廓會變得模糊,無法辨識對方是誰。在這段時間,有可能遇到非人的鬼怪。因為會遇到妖魔或死者,因此也有『逢魔時刻』的說法。不過更古老的用語還有『彼者為何(karetaso)』或『彼為誰人(kahatare)』。」
小雪老師又寫下「彼者為何」與「彼為誰人」。這是什麼?雙關語嗎?
「老師,我有問題。不是應該稱作『分身(kataware)之時』嗎?」
有人如此發問,我也贊同他的說法。我當然聽過「黃昏時分」,不過提到傍晚,從小最常聽到的還是「分身之時」。小雪老師聽到發問便露出柔和的笑容。說個題外話,這位古典文學老師是一位和這所鄉下高中極不相稱的大美女。
「『分身之時』或許是這一帶的方言吧?我聽說糸守鎮的老人家還保留了古老的萬葉語言(註1)。」
「因為這裡是偏鄉啊!」有男同學這麼說,引來大家的笑聲。的確,外婆有時候也會使用令人懷疑是哪國語言的用語,而且第一人稱還是「儂(washi)」。我邊想邊翻開筆記本,看到原本應該是空白的紙上寫了大大的字。
妳是誰?
……咦?
這是什麼?周圍的聲音好像被這個陌生的字跡吸收,突然變得很遙遠。這不是我的字,我應該也沒有借別人筆記本才對。「你是誰」……是什麼意思?
「……同學。接下來請宮水同學!」
「啊,是!」
我連忙站起來。小雪老師說「請妳從九十八頁開始念」,然後看看我的臉又忍俊不禁地加了一句:
「宮水同學,妳今天記得自己的名字呢。」
全班哄堂大笑。咦?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妳不記得?」
「……嗯。」
「真的?」
「我都說『嗯』了!」
我回答後猛吸一口香蕉果汁。咕嚕,好好喝。
早耶看我的眼神,彷彿看到很奇怪的東西。
「……妳昨天連自己的位子和置物櫃都不記得。頭髮像剛睡醒一樣亂七八糟,也沒有綁制服緞帶,而且不知道為什麼,心情一直很差的樣子。」
我試著想像那樣的姿態……咦?
「咦~~~~妳說什麼?真的假的?」
「三葉,妳昨天好像喪失記憶一樣。」
我連忙試著回想……果然有點奇怪,我想不起昨天的事。不,我記得一些片段的情景。
那是……某個陌生的城市?
鏡子中的是……男生?
我努力喚起記憶。老鷹發出「嗶~咻嚕嚕~」的叫聲,好像把我當傻瓜。現在是午休時間,我們在校園角落喝著紙盒裝的果汁閒聊。
「嗯~我好像一直在做很奇怪的夢……感覺像是在過別人的生活……的夢?唔,我不太記得……」
「……我知道了!」
勅使突然大喊,讓我嚇一跳。他把讀到一半的神祕學雜誌《MU》舉到我面前,口沫橫飛地說:
「那一定是前世的記憶!妳們或許會認為這種說法沒有科學根據,那麼就換個說法:以艾弗雷特的多世界詮釋為基礎的多元宇宙連結到妳的潛意識……」
「你閉嘴!」早耶毫不容情地斥責,我則大喊:「啊!該不會是你在我的筆記本上亂塗鴉的吧?」
「什麼?塗鴉?」
啊,好像猜錯了。勅使不是會做這種無聊惡作劇的人,而且他也沒有犯罪動機。
「呃,沒事,沒什麼。」我取消前言。
「妳說的塗鴉是怎麼回事?妳在懷疑我?」
「我都說沒事了!」
「哇!三葉,妳好過分!早耶,妳聽到了嗎?她竟然冤枉我!去找檢察官!還是應該找律師?喂,這種時候要找哪一種?」
「可是三葉,妳昨天真的很奇怪。」早耶華麗地漠視勅使的控訴。「妳是不是身體不舒服?」
「嗯~真奇怪……難道真的是壓力嗎……」
我重新思考先前得到的各種證詞。勅使又埋頭繼續讀那本神祕學雜誌,彷彿什麼都沒發生過。這種不記恨的態度是他的優點。
「沒錯,一定是壓力!三葉,妳最近應該面臨很多問題吧?」
沒錯。鎮長選舉當然不用提,還有今晚終於要舉行的那個儀式!在這麼小的鎮上,為什麼偏偏我父親是鎮長,外婆則是神社的神主呢?我把臉埋在雙膝之間,深深嘆息。
「唉,我真想早點畢業去東京。這座鎮實在太小、人際關係太緊密了!」
早耶也點頭說:
「我懂,非常明白。我們家母女、姊妹連續三人都負責鎮內廣播,所以我從小就一直被鄰居阿姨稱為『廣播小姐』!可是,我竟然還加入廣播社!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想什麼!」
「早耶,等我們畢業之後一起去東京吧!待在這種小鎮,即使長大之後也會原封不動維持學校的階級關係!我們得從這種舊框架解脫才行!勅使,你也會跟我們一起走吧?」
「嗯?」
正在讀神祕學雜誌的勅使懵懵懂懂地抬起頭。
「……你有在聽我們說話嗎?」
「嗯~還好……我應該會繼續待在這座小鎮,過普通的生活吧?」
「唉~~」我和早耶香深深嘆息。這傢伙就是因為這樣,才沒有女人緣。雖然說我也沒交過男朋友……
一陣微風吹來。我望向風吹來的方向,看到下方的糸守湖一副漠不關心的樣子,水面安詳平靜。
這座小鎮既沒有書店也沒有牙醫,電車兩小時才一班,公車一天只有兩班,天氣預報不報導,Google Map的衛星照片直到現在還是馬賽克,便利商店九點就關門,可是店裡卻有賣蔬菜種子和高級農具。
放學途中,我和早耶對糸守鎮的牢騷仍舊沒有結束。
沒有麥當勞也沒有摩斯漢堡,卻有兩間小酒吧;沒有就職機會,也沒有女人要嫁過來,日照時間又短……平常雖然覺得鎮上這種人口過稀的狀況,反而令人覺得清爽也頗值得自豪,但今天我們卻非常認真地感到絕望。
勅使原本默默推著腳踏車跟著我們走,忽然按捺不住地開口:
「妳們啊!」
「怎樣?」我們很不高興地問。勅使泛起詭異的笑容說:
「先別討論這個,要不要去咖啡廳?」
「咦……」
「什……」
「什麼!」
「咖啡廳?」
我們異口同聲地大喊。
喀鏘!金屬碰撞聲消失在暮蟬的叫聲中。勅使從販賣機取出罐裝果汁遞給我們。種田回來的老爺爺騎著電動機車,發出「嗡~」的聲音經過我們面前。路過的野狗好像在說「我來陪陪你們吧」,坐下來打了呵欠。
這個咖啡廳不是一般想像的咖啡廳。它不是星巴克或Tully’s,或是據說存在於世界上某個角落,提供鬆餅、貝果、義式冰淇淋的夢幻空間。這裡只是鄰近的公車站,設有長椅和自動販賣機,長椅上還貼著三十年前左右的冰淇淋看板。我們三人並肩坐在長椅上,那隻野狗坐在我們腳邊。我們慢慢地喝著罐裝果汁。與其說感覺被勅使騙了,不如說早該預料到會是這樣。
我們聊著無關緊要的話題,譬如:「今天的氣溫比昨天低一度。」「不,我覺得高一度。」之類的。喝完一罐果汁後,我對兩人說:
「那我先回去了。」
「今晚要加油喔!」早耶說。
「我會去看妳的。」勅使說。
「不用來了!不,應該說絕對不要來!」我嘴上警告他們,內心卻在替兩人祈禱:「加油~要成為戀人喔~」我爬了一段石階後回頭,看著兩人以暮色湖面為背景坐在長椅上,偷偷為他們配上抒情的鋼琴曲。嗯,他們果然是天生一對。雖然我接下來必須執行不幸的夜間勤務,不過還是要祝福你們享受青春年華。
「啊~我也比較想做那個。」
四葉發出不平之聲。
「那對妳來說還太早了。」外婆說。
八個榻榻米大的工作室內,毫無間斷地發出線軸碰撞在一起的聲音。
「聽聽線的聲音。」外婆沒有停下手邊的工作,繼續說:「像這樣一直纏著線,慢慢地人和線之間就會有感情流動。」
「啊?線又不會講話。」
外婆無視四葉的反駁,繼續說:「我們的組紐編織──」
我們三人都穿著和服,正在製作今晚儀式中要使用的繩子。自古流傳的傳統工藝「組紐編織」,是把細線編在一起成為一條繩子。完成的組紐編織呈現各種色彩繽紛的圖案,非常可愛。由於這項工作需要一定的嫻熟度,所以四葉的部分由外婆製作,四葉則擔任助手,不斷把線捲到線軸上。
「我們的組紐編織刻印著糸守千年的歷史。妳們學校也應該先教小孩鄉鎮歷史才對。聽好了,距今兩百年前……」
又開始了。我偷偷苦笑。我從小就在這間工作室裡,聽外婆一再提起這段話。
「草鞋店的山崎繭五郎家浴室失火,將這一帶都燒光了。神社和古代文書也全被燒掉,這就是俗稱的──」
外婆瞥了我一眼。
「『繭五郎的大火』。」
我流利地回答,外婆滿意地點點頭。四葉顯得很驚訝:「什麼?火災還有取名字?」她還喃喃說:「繭五郎先生因為這種事留下名字,真是可憐。」
「也因此,我們這些組紐編織的圖案意義,或是舞蹈的意義都沒有流傳下來,剩下的只有形式。不過即使意義消失,形式也絕對不能消失。刻印在形式中的意義,總有一天會復甦。」
外婆的話帶有歌謠般的獨特拍子。我邊製作組紐編織,邊小聲背誦同樣的語句。刻印在形式中的意義,總有一天會復甦。這就是我們宮水神社的──
「這就是我們宮水神社的重要職責。可是……」
說到這裡,外婆柔和的眼中顯露悲傷的神情。
「可是那個笨女婿……不只拋棄神職離家出走,還去搞政治,真是無可救藥……」
在外婆的嘆息聲中,我也偷偷地小聲嘆氣。我其實也不太確定自己是喜歡或討厭這座小鎮,是想要逃到遠方或是一直和家人朋友在一起。我把色彩繽紛的組紐編織從圓台上拿下來時,發出「喀噠」的寂寥聲音。
夜晚的神社傳來的大和笛樂音,或許會讓都會居民聯想到恐怖電影吧?例如某某村殺人事件、某某家一族之類凶殺事件發生的舞台。我也懷著「不管是佐清或傑森(註2)都可以,乾脆把我殺掉,讓我解脫吧~」的陰沉心情,從剛剛就在跳巫女舞。
每年這個時期舉行的宮水神社豐穰祭的主角,很不幸的是我們兩姊妹。這天我穿著筆挺的巫女服、塗著鮮紅色的口紅、戴上垂掛金屬墜子的頭飾,在神樂殿出現在站立的觀眾前,跳外婆教我的舞蹈。先前提到因為火災而失去意義的舞蹈,就是這套雙人對舞。兩人各自拿著繫有繽紛組紐編織的鈴鐺,鏘鏘作響,並且一再繞圈,讓輕飄飄的繩子隨之旋轉。剛剛繞圈的時候,我看到勅使和早耶的身影,明明一再叮嚀,他們竟然還來,讓我的心情沮喪到谷底。我一定要用巫女的力量詛咒他們,並用LINE狂送詛咒貼圖給他們。話說回來,最討厭的還不是這個舞蹈。雖然跳舞也有點丟臉,不過因為從小就在跳,已經習慣了。然而,豐穰祭裡還有另一項年紀越長越覺得丟臉的儀式。在這之後必須進行的那項儀式,怎麼想都是在羞辱女孩子。
唉~真是的。
好~討~厭!
我邊想邊跳舞,舞蹈很快就結束了。啊啊,「那個」終於要開始。
嚼嚼嚼。
嚼。
嚼嚼嚼嚼。
我不斷嚼米。盡可能什麼都不想,不去感受味道、聲音和色彩,只是閉上眼睛不斷咀嚼。一旁的四葉也和我一樣。我們並肩正坐,各自前方都擺著小小的木頭酒盅。面前當然還有觀賞我們的男女老幼觀眾。
嚼嚼嚼。
嚼嚼。
唉,真是的。
嚼嚼嚼。
差不多該吐出來了。
嚼嚼。
唉。
嚼。
我終於放棄抵抗,拿起眼前的木頭酒盅舉到嘴前,盡可能用巫女服的袖子遮住嘴巴。
然後,唉……
我噘起嘴,把剛剛嚼過的米吐在木頭酒盅裡。吐出來的東西混著唾液,形成黏稠狀的白色液體從口中流出來。好像聽到觀眾在交頭接耳,嗚嗚嗚嗚,我在心中哭泣。拜託,大家不要再看了!
這就是口嚼酒。
嚼過的米混合唾液放置一陣子,會發酵而產生酒精,是日本最古老的製酒方式。這是要供奉給神明的,從前似乎很多地方都有在製作,不過到了二十一世紀,不知道還有哪間神社會繼續做這種事?話說穿著巫女服做這種事,未免太瘋狂了吧?到底有誰會高興?我腦中想著這些問題,但還是很認命地又抓了一把米放入嘴裡,然後繼續咀嚼。四葉也若無其事地做同樣的事。在這小小的木頭酒盅裝滿之前,我們得一再反覆這個動作。我再次吐出黏答答的唾液和米,心中再度啜泣。
這時,突然聽到熟悉的聲音。心中湧起漣漪般的不祥預感,我稍稍抬起視線。
──唉。
我忍不住想要炸毀整座神社。時髦華麗階級的三個同班同學果然在那裡。他們露出不懷好意的笑容盯著我,開心地不知道在說什麼。雖然就距離來說不可能聽到他們的談話內容,但我甚至覺得好像聽到:「哇!那種事人家絕對不敢做。」或是「好淫穢喔!」或是「竟然在人前做這種事,一定嫁不出去。」之類的。
畢業之後,我一定要離開小鎮,去到很遠的地方。
我在心中非常強烈地發誓。
「姊姊,振作點啦!有什麼關係?只是被學校同學看到而已。我真搞不懂妳為什麼受到那麼大的打擊。」
「真羨慕青春期前的小孩子,講得這麼輕鬆!」
我怒瞪四葉。我們這時已經換上T恤,走出神社社務所的玄關。
豐穰祭之後,姊妹倆今晚最後的工作,是要參加宴請協助祭典工作的附近老先生老太太的宴會。宴會女主人是外婆,我和四葉則負責倒酒和陪客人聊天。
「三葉,妳今年幾歲啦?什麼?十七歲?有這麼年輕可愛的女孩子替我倒酒,爺爺感覺都要變年輕了。」
「請盡量返老還童吧!來,繼續喝繼續喝!」
我用近乎自暴自棄的態度招待客人,感覺筋疲力盡,後來終於有人說「小孩子該回去了」,我們才得以解放。外婆和其他大人仍繼續留在社務所飲酒談笑。
「四葉,妳知道剛剛社務所裡的平均年齡嗎?」
神社參道旁的燈光已完全熄滅,周圍處處傳來給人涼爽印象的蟲鳴聲。
「不知道。六十歲嗎?」
「我在廚房算過,是七十八歲!七十八歲耶!」
「喔。」
「我們離開之後,現在那個空間的平均年齡是九十一歲!簡直就是人瑞、人生最終階段,陰間使者都可以來接收整間社務所了!」
「嗯……」
因此,我必須早日逃離這座小鎮。這就是我想說的,可是四葉對於姊姊迫切的訴求卻沒有太大反應,似乎在想別的事。看來小孩子是無法理解她姊姊的苦惱。我放棄解釋,抬頭仰望天空。滿天燦爛的星星似乎對地面上的人們毫不關心,超然地閃爍著。
「……對了!」
我們並肩走下神社漫長的石階時,四葉突然大喊。她的表情好似找到藏起來的蛋糕。她對我說:
「姊姊,妳乾脆做很多口嚼酒來賣,當作去東京的資金!」
我一時無法接話。
「……妳竟然想得出這種怪點子。」
「還可以附上照片和製作過程的影片,取名『巫女口嚼酒』之類的!一定會大賣!」
我有些擔心,九歲就抱持這種世界觀,沒問題嗎?不過想到四葉也是在用她自己的方式替我擔心,就覺得她還是滿可愛的。好,要不要認真考慮口嚼酒販賣事業呢……咦,酒可以隨便販賣嗎?
「姊姊,妳說我這個點子好不好?」
「嗯……」
嗯~
「還是不行!違反酒稅法!」
咦,是這種問題嗎?我自己說完都覺得奇怪,不知不覺就開始往前衝。心中混雜著各種事件、感情、展望、疑問與絕望,感覺胸口要爆炸了。我一步跳過兩階跑下石梯,在樓梯平台的鳥居下方緊急煞車,從喉嚨吸入滿滿的夜晚冷空氣,然後,把心中亂七八糟的雜念連同空氣使勁吐出來:
「我討厭這座小鎮~!我討厭這種人生~!下輩子請讓我成為東京的帥哥~!」
哥~哥~哥~哥……
我的願望迴盪在夜晚的山巒間,彷彿被吸入底下的糸守湖般消失了。脫口而出的話語實在太蠢,讓我的腦袋連同汗水迅速冷卻。
唉,即使如此。
如果神明真的存在。
請祢──
如果神明真的存在,連我自己都不知道該許下什麼願望。
第一章
夢
懷念的聲音與氣味,依戀的光線與溫度。
我和心愛的某個人緊密地貼合,彼此難分難捨地連結在一起。就像夾在乳房間的嬰兒時期,沒有絲毫不安與寂寞。我尚未失去任何東西,幸福甜美的情感擴散至整個身體。
眼睛突然張開。
天花板。
房間。早晨。
一個人。
東京。
──原來如此。
剛剛在做夢。
我從床上起身。
僅僅在這大約兩秒的時間裡,先前包覆著我的溫暖歸屬感已消失殆盡,不留痕跡,也沒有餘韻。由於太過突然,我還來不及思考就掉下眼淚。
早上醒來時,我有時會不知為何在流淚。
我總是想不起前晚的夢境...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15收藏
115收藏

 81二手徵求有驚喜
81二手徵求有驚喜




 115收藏
115收藏

 81二手徵求有驚喜
81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