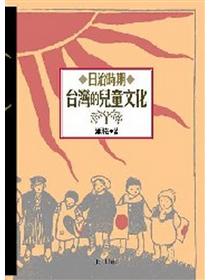本書以台灣與西方比較視點為開端,探討戰後台灣「少年小說」的論述、界域及其流變,其後聚焦於小說文本中的兒少主體形構,以及性別、家國、鄉土、童年純真論述與童年文化等現當代文學及文化研究所關注的課題,藉由理論的導引,探索、開拓並深化台灣少年小說的多元視角與文本內涵。
作者簡介:
吳玫瑛(Andrea Mei-Ying Wu)
現職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副教授
台灣兒童文學研究學會(TCLRA)理事
經歷
國際兒童文學研究學會(IRSCL)理事
傅爾布萊特資深學者研究獎助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課程與教學系訪問教授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專長
兒童、青少年文學
性別與童話
台灣少年文學
章節試閱
一、前言
台灣文學及文化場域自二十世紀八、九○年代以降,內因政治社會環境丕變,外受西方學說思潮影響,「後現代」、「後殖民」、「去中心」、「多元化」等各式論述蔚為風潮,女性、原住民、少數族裔等邊緣個體紛紛浮出檯面,各自發聲或集體交響,在性別、階級、身分認同、身體政治等議題上提出異議或新詮,試圖建構或重構主體,在各自開展或相互交織的言說實踐中,意圖凸顯或伸張文化的多元性(multiculturality)與異質性(heterogeneity),以多聲複調(polyphony)對抗或破除傳統單一、線性的史觀論述。例如,邱貴芬的〈台灣(女性)小說史學方法初探〉及〈從戰後初期女作家的創作談台灣文學史的敘述〉兩篇即嘗試以多元觀點,重新審視(戰後初期)女性作家的文學書寫與創作地位,以此檢視、擴充或另構台灣文學的整體面貌。兒童文學在當今文學及文化研究場域得以(被)識見,並(重新)投以關注,此「異軍」突起現象,部分原由或可歸結於後現代/後殖民文化脈絡中的多元實踐與開放想像。
兒童文學向來予人甜美、溫馨的印象, 是專為兒少讀者而設的文學類項,因內容輕淺,經常被視為是簡單、純淨(transparent)、無害(innocent)的教化工具,或是無足輕重的文化製品。美國兒童文學及文化研究學者比佛利‧克拉克(Beverly Lyon Clark)便曾以 “kiddie lit” 此兼具戲謔與嘲諷雙關意涵的標語為題,於 2003 年發表《弁髦文學:美國兒童文學的文化建構》(Kiddie Lit: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America)。她以美國文學為觀察場域,直言不諱兒童文學在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美國文學全集為例,說明其內容編選可謂鉅細靡遺,應有盡有,舉凡種族、階級、性別、少數族裔等各式新興文化議題皆已涵納其中,唯獨不見「年齡」的考量(Clark 3)。然而,更弔詭的是,知名作家《小婦人》(Little Women)的作者艾考特(Louisa May Alcott)雖名列其中,但收入的篇章並非這部名聞遐邇的經典作品的節錄,而是她所寫的一篇不甚了了的成人短篇故事。或者,更精確地說,即使文集中提到某些作家曾發表兒童文學作品,但也僅僅點到為止。克拉克因此認為這是普存於文學界掌門人(elite literary gatekeepers)的保守認知,一味將兒童文學作品視為僅是「童言童語」的表徵,難以同登或列入「嚴肅」文學的大雅之堂。而諸如此類將兒童文學視為或斥為「幼稚化」或「弱智化」的言說(the discourse of infantilization)不經意造成了對「年齡」的歧視(Clark 5),連帶的也影響並且侷限了社會大眾看待、理解、論述、書寫兒童文學及童年的方式。一般文學場域經常遭逢漠視,並舉頗具權威且流通甚廣的
西方兒童文學研究先驅彼得‧杭特(Peter Hunt)自二十世紀八○年代中葉起便接連撰文,主張將「兒童文學」納入文學研究的範疇,並以「女性主義」(feminism)等說詞作為參照, 提出「兒童主義批評理論」(childist criticism),欲以此凸顯兒童文學作為專門學科研究的嚴肅性及其基進(radical)意涵。杭特的「兒童主義批評理論」一方面企圖翻轉並改造兒童文學研究長久以來偏重教育與閱讀教學等應用層面的現象,另一方面也不無企圖藉此與「成人文學」研究的傳統與霸權相抗衡, 強調以「兒童」作為本位思考,以此開闢兒童文學研究的新路徑。然而,瑪莉亞‧尼可拉耶娃(Maria Nikolajeva)在《兒童文學轉大人》(Children’s Literature Comes of Age)中,對杭特企圖解決兒童文學研究的尷尬處境所提出的獨特見解,並不以為然,她認為這樣的「轉變」,只會將兒童文學的研究更加邊緣化,徒使兒童文學自外(或隔絕)於一般的文學批評理論(10)。尼可拉耶娃雖不認為兒童文學可獨立於一般文學理論與批評探究之外,但她也強調,兒童文學比起成人文學,其複雜度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兒童文學雖是以「兒童」為主要對象,然而,「兒童」身旁或身後的「成人」,經常也是兒童文學的訴求對象。尼氏因此以「雙重符號系統」(two systems of codes)勾勒並強調兒童文學「既為兒童,也屬成人」的雙重特性 (57)。在此之前,以色列兒童文學專家及符號學學者柔哈‧莎薇特(Zohar Shavit)在《兒童文學詩學》(Poetic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中,便曾以「曖昧的文本」(ambivalent texts)指稱兒童文學所具有的多重面貌與複雜意涵。
二、「少年小說」論述:台灣與西方比較視點
觀諸台灣兒童文學論述,戰後以來,注重兒童文學的美學意義與形式者雖不乏其人,然而,關於兒童文學的評述,大抵是以 兒童文學的功用論或價值性為尚,或標舉兒童文學為「真」、「善」、「美」的讀物,是實現「兒童教育理想的工具」(李畊 13, 19),或是以其為兒童成長過程中「知識灌輸」與「精神養護」的重要來源(林守為 23),或者著重兒童文學與品格教育的相關(黃堅厚 115-18)。台灣兒童文學資深作家林良曾指出,兒童文童文學範疇的「少年小說」則可說是「一種非常年輕的新小說類型」,其與成人小說之間的差別就在於「讀者對象的不同」(〈論少年小說作者的心態〉6)。誠然,兒童文學長久以來因特定(或特殊?)讀者群的設定而首重其教化之功,然而,林良也強調, 少年小說為使讀者有益,除了具「嚴肅性」的價值,也不應排除其「娛樂性」的功能(〈談少年小說〉69-70)。因此他在〈論少年小說的勵志傳統〉中曾提及少年小說作家經常呈現兩種不同的寫作態度:「勵志的」和「趣味的」(73)。兒童文學兼具「教誨」(instruction)和「樂趣」(delight)雙重意涵,在西方早已成為金科玉律,且有不少學者提出具體研究。學較之於一般文學來說「是較晚出現的新文學類型」,而屬於兒反觀台灣,兒童文學─尤其是少年小說,在二十世紀六、七○年代仍屬新興文化產物,論者所重仍大多環繞於兒童文學的「教育」意義與功能,林良以兒少為關注對象,對於兒童文學及少年小說的創作提出雙向見解,別具啟示作用。
然而,值得注意的,以林良和馬景賢等資深兒童文學作家為代表的傳統論述對於兒童文學乃至少年小說的界分,仍大致將其視為自外或有別於成人世界的特殊產物。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於1986年出版《認識少年小說》,是台灣戰後首部以「少年小說」為探討主題的文集,當中收錄林良〈論少年小說作者的心態〉一文。他採擷人文主義的關懷視角,主張
對於少年小說,我的一個文學信念是:
用人生的光明面來滋潤少年的心靈。有了為愛所滋潤的孩子,人類就會有光明的未來。
把人生的黑暗面交給大人去承擔。只要大人有面對事實的勇氣,又能發揚理性和良知,人類必定能消滅黑暗和野蠻。(8)
上述說法以「光明」和「黑暗」二元對立概念劃分兒童和成人世界,除具幾分浪漫主義理想色彩,更清楚表明「兒童文學」, 以及在其範疇內的「少年小說」是植基於成人/兒童截然二分的立論觀點上;亦即,兒童與成人分屬兩個不同的世界, 「兒童文學」是獨立於成人文學之外的特殊文類。彼得‧杭特(Peter Hunt)在《批評、理論與兒童文學》(Criticism, Theory, & Children’s Literature, 1991)中曾以「隔離」(segregation)此略具負面意涵的說法,指出「成人─兒童」的區隔(adult-child segregation)這個觀點也普存於英國社會,其所強調的是「兒童自成一類;他們受成人既定觀念保護,而生活運行於他處(work in different places)」(59)。
在西方,將兒童浪漫化(Romanticize the child)由來已久,尤其,自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洛克(John Locke)以降, 乃至英國浪漫主義文學大家如布列克(William Blake)和華爾華茲(William Wordsworth)等皆將兒童視為未受世俗汙染的純淨個體,是理想的化身,也是改造社會與人類救贖希望之所繫。林良上述說法所呈顯的,實為古典人文主義脈絡下強調兒童文學具有普世性(universal)、去歷史(ahistorical)和去政治(apolitical) 的價值意涵。這點與前述美國學者克拉克對兒童文學的關注,以「兒童」(一如女性、種族、階級、少數族裔等)作為文化形構與權力衝突場域的看法,容或有別。在二元分立的概念下,林良將「為少年的幸福與權益而吶喊」的小說視為「少年問題小說」,並將之歸類為成人文學的範圍(〈論少年小說作者的心態〉7)。殊不知,這類「問題小說」在美國二十世紀六○年代已紛紛冒現,至七○年代已成為(青)少年閱讀市場主流出版品,如今已是形塑(青)少年文學的重要指標。
泰瑞茲(Roberta Seelinger Trites)在《撼動宇宙:青少年文學的權力與壓抑》(Disturbing the Universe: Power and Repression in Adolescent Literature)這部探討青少年文學的重要論著中即指出, 青少年文學在美國成為獨特文類(a distinct literary genre)約莫出現於二十世紀六○年代末期(9)。雪拉‧伊果夫(Sheila Egoff) 〈訓誡、歡愉和預兆:兒童文學的典範流變〉(“Precepts, Pleasures, and Portents: Changing Emphase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一文也清楚說明:「在北美,〔二十世紀〕六○年代和七○年代主要是問 題小說的年代」(428)。例如,《邊緣小子》(The Outsiders) 於 1967 年問世(中文版於2004年由小魯文化出版),作者辛頓 (S. E. Hinton)寫作該書時年僅十六歲,故事內容對於青少年幫派文化、階級與暴力衝突等多所著墨,可視為美國「問題小說」的經典之作。其後崛起於七○年代的羅伯特‧寇米耶(Robert Cormier),於 1974 年出版《巧克力戰爭》(The Chocolate War;中文版於 2008 年由遠流出版),咸以為是美國「問題小說」的代表之作,內容直探美國校園文化中的階級暴力與邪惡勢力,赤裸裸描繪個體與威權體制抗爭的悲劇性下場,以及少年於單親家庭成長的邊緣處境。
在英國,彼得‧哈林戴爾(Peter Hollindale)亦發表〈青少年思想小說〉(“Adolescent Novel of Ideas”)一文,爬梳青少年小說等(the category variously known as teenage, adolescent, or young adult fiction),小說內容主要是以「打破禁忌」(taboo-breaking) 的寫實主義作為標誌(315)。此類「問題小說」在台灣二十世紀六○年代似已浮現,例如白先勇與王文興等人便曾勾畫另類或邊緣少年的生命故事,前者寫成〈寂寞的十七歲〉(1961),後者則發表〈命運的迹線〉(1963)等多篇短篇小說。只是彼時台灣文學板塊正在/待增成,兩人的作品大多被標舉為現代主義文學的代表,與西方「問題小說」的關涉自是較少引起注意。
林良意圖將「少年小說」圈立於成人文學之外,實別具用心,檢視其稍早的論述,例如 1976 年發表〈少年小說的任務〉一文,即明白指出「少年小說」的創作主要在為年輕讀者「造橋」。他舉中國古典文學中的《紅樓夢》為例,認為這部作品雖然是小說中的經典,但並非少年讀者適讀,因為
《紅樓夢》跟「童話」的中間缺少一道「橋」。他們很可能一下子沉醉在那奇異的、陌生的、很有說服力的,足以使他們引起「今是而昨非」的幻覺的敘述中,以書中的哀愁灌溉自己心中的田野……完全接受了曹雪芹的「空空思想」。……這不是《紅樓夢》帶壞了他。這是沒有「少年小說」,沒有「橋」,使他掉進了那個叫做「距離」的深溝。我們不該為了怕少年掉進那個溝,而焚燒一部傑出的中國小說。我們應該以「少年小說」來造橋,讓少年讀者順利走過那道溝;甚至以「少年小說」做土壤,填平那道溝!(241-42)
林良這段話說來語氣鏗鏘,別具洞見,他斷非認為《紅樓夢》「有害」或有礙年輕讀者,而是強調因著少年讀者的特殊性及特定成長階段的需求,而須有不同的創作取材與考量,以協助他們渡過成長的摸索期,並為邁向複雜的成人世界預作準備,少年小說所扮演的即此樞紐角色。
巧妙的是,林良此語似乎呼應了美國兒童批判教育及馬克思主義學者赫伯特‧寇爾(Herbert R. Kohl)的主張,他在《我們是否該燒了巴巴?》(Should We Burn Babar? Essays o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the Power of Stories, 1995)中揭示,諸如《大象巴巴》(Story of Babar, 1931)這類經典兒童文學作品中經常包藏濃厚的殖民主義色彩,以及階級和種族不平等意識,然而解決此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是否該將這類書籍列為禁書,以免兒童受其不良影響,而是「正視」這些問題的存在,並且一一加以檢視;與其採取迴避的方式,不如積極引導兒童建立正確觀念並培養其批判意識。林良所重顯然與寇爾不同,前者意在另闢蹊徑,為少兒另行拓植閱讀內容,為其提供適讀的文學作品,而後者則側重直接探觸童書出版品的問題核心,揭露童書中潛藏的意識形態,期使作為閱讀者的兒童能經由導引,思考並了解書中或隱或顯的社會問題或偏見。兩者看似論調相近,取徑實則大異其趣。
一、前言
台灣文學及文化場域自二十世紀八、九○年代以降,內因政治社會環境丕變,外受西方學說思潮影響,「後現代」、「後殖民」、「去中心」、「多元化」等各式論述蔚為風潮,女性、原住民、少數族裔等邊緣個體紛紛浮出檯面,各自發聲或集體交響,在性別、階級、身分認同、身體政治等議題上提出異議或新詮,試圖建構或重構主體,在各自開展或相互交織的言說實踐中,意圖凸顯或伸張文化的多元性(multiculturality)與異質性(heterogeneity),以多聲複調(polyphony)對抗或破除傳統單一、線性的史觀論述。例如,邱貴芬的〈台灣(女性...
推薦序
推薦序
如何閱讀,怎樣剖析
張子樟(青少年文學閱讀推廣人)
一
台灣兒童文學的推廣工作早已超過半世紀,但多年來政府機構(如教育部或臺灣省教育廳)均以鼓勵創作為主,關於理論或作品研究的倡導一向少之又少,即使是教科書型的所謂「兒童文學研究」,能夠深入討論各種文類的變遷、創作原則、讀者反應、作品研究及科際整合研究等等,幾乎找不到理想的。每本專書在介紹少年小說時,也是聊備一格,點到為止。但兒童文學理論專書或作品研究的不足並不影響作品的出版,尤其外國少年小說及繪本的譯本幾乎佔了當前兒童文學出版品的七八成。
國內獨一無二的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班創立於 1996年,至今已二十年;2004 年又設博士班。研究所應以研究為主,研究生必須撰寫論文才能獲得學位。隨著兒童文學研究所的成立,其他院校的文史哲研究所似乎突然間找到另一塊研究空間,於是研究兒童文學作品形成一股風潮,並且延伸到其他相關系所,如美術所、中文所、教育所、教育心理所、比較文學所、語創所、台文所等,從不同的文學或文化角度切入,都可以找到可以研究的方向,一時頗有顯學的味道,尤其在少年小說方面的論文特別多。但研究成果一直參差不齊,主要是由於研究者涉獵文學理論書不多,對於作品的閱讀與詮釋的量與質也不盡理想。把碩士階段說是初學階段,論文只是初入文學殿堂的敲門磚,無法寫得盡善盡美,一般人還可以容忍接受。如果到了博士階段,研究功力仍然只有碩士程度,那就不值得原諒了。
這些年來,一些具備社會責任理念的出版社不怕虧損,先後翻譯了好幾本重量級的兒童文學理論書,頗具影響力。本地相關科系的學者也努力書寫論文、參加研討會,或把多篇論文結集出版。但嚴格來說,近幾年由於繪本掛帥,學生追隨流行,偏愛書寫討論繪本的論文,文字書(包括童話、少年小說、文學史、兒童散文、兒童戲劇等)的研究反而被擺在一邊了。這種趨勢令人擔心。擔任指導教授的人似乎不應逃避自我反思,學生趨易避難是否與自己的教學方向、研究態度和研究成果有關。
二
吳教授的這本新書雖是論文集,但每篇論文都未偏離台灣戰後的少年小說,深具「史」的滋味。她回溯早期的篳路藍縷階段,慧眼獨具,並沒有忽略一些老作家的作品,嘗試老少並列, 新舊熔於一爐。論文重心在於探討戰後台灣少年小說中的主體、性別、地方論述與(後)現代童年想像,但並不侷限於以書寫少年小說的作家的作品,成人作家作品中的青少年內外描繪一併論述。全書只有五章,但其引用的作品及理論之多遠遠超過現有的相關著作。全書必須細讀,才能品嚐其隱含的精髓。
如何引用現有的新舊理論來詮釋或剖析已設定的文本,端視作者的能耐。吳老師中英文俱佳,從其用字遣詞便可看出其功力,尤其是理論專門名詞的翻譯更是不易。全書行文流暢,說理清楚,毫無乾澀之感。她不僅提供了許多可以應用在這特殊領域的研究專書,而且在註釋方面更不嫌麻煩,盡量詳細。這方面是其他論文書寫少見的,值得有心撰寫論文的人仿效。
雖然吳老師把研究時空限定為「戰後」,但實際上只論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台灣少年小說第一天王」李潼的《少年噶瑪蘭》、《望天丘》、《魚藤號列車長》和十六本《台灣的兒女》沒有列入,更不用提「九歌兒少文學獎」將近 200 多冊的得獎作品了。其實這些作品同樣提供了不少文學和文化層面的研究空間,可以放手一試再試,或許吳老師已經將這些新近作品列為第二階段的研究對象。
「十年磨一劍」不是易事,但吳老師的這本專著並無「霜刃未曾試」之憾。我們期待吳老師不久將展示另一把削金斷玉的利刃。
推薦序
如何閱讀,怎樣剖析
張子樟(青少年文學閱讀推廣人)
一
台灣兒童文學的推廣工作早已超過半世紀,但多年來政府機構(如教育部或臺灣省教育廳)均以鼓勵創作為主,關於理論或作品研究的倡導一向少之又少,即使是教科書型的所謂「兒童文學研究」,能夠深入討論各種文類的變遷、創作原則、讀者反應、作品研究及科際整合研究等等,幾乎找不到理想的。每本專書在介紹少年小說時,也是聊備一格,點到為止。但兒童文學理論專書或作品研究的不足並不影響作品的出版,尤其外國少年小說及繪本的譯本幾乎佔了當前兒童文學出版品的七八成。...
作者序
序
兒童文學的批判意識
本書的構成始於 101 年度國科會(現為科技部)專書寫作計畫,從近年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的成果出發。民國96年度開始執行國科會計畫,是以台灣二十世紀六○年代少年小說為研究場域,聚焦探討文本所形構的男童文化(boyhood)與性別建構的指涉關係,研究發現「好孩子」,或謂「模範兒童」的(陽剛) 主體形構與身分認同乃是六○年代少年小說(男童)敘事的核心。此敘事模式所呈顯的除了關乎男童的性別身分建構,也隱指國家認同的政治意識與兒童(國民)教養的相關。接續的計畫雖仍以六○年代少年小說為範域,但研究焦點已轉向童書創作所涉及的(成人)欲望書寫,其中,對於兒童(期)性慾的壓抑與回返,反映在童書作品的生成與創作,最顯明的印記,也是最為弔詭的面向,莫過於童書中一再申明及強化的「童年純真」論述。「童年」(childhood)與「純真」(innocence)每每在童書作品中化為一體,彼此交相疊映,緊密相依,難分難離,「童年純真」(childhood innocence)儼然成為書寫、再現、言說「兒童」難以撼動的文化信念與準則。
其後,文本的爬梳進入二十世紀七○及八○年代出版的少年小說,主要以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少年小說得獎作品為研析對象,研究發現鄉土書寫是這時期少年小說創作的主軸,兒童主角頻頻游移於「城」與「鄉」的拉扯與協商之中,形成不同或多重的身分想像,種種涉及「地方」與「空間」的論述,以及兒少主體在其中的顯影與變貌,成為探索重心。100 年度執行的專題計畫則是以跨國、跨文化的比較視野,探究「野孩子」此一特殊文化符碼(cultural code),在台灣社會解嚴解禁之後所出版的少年小說文本,尤其在成人文壇健將(如張大春和袁哲生)相繼「跨界」書寫下,如何開展「邊域」少年的主體空間與想像,以呈顯並折射出台灣社會、文化、政治諸多異相及其繁複紛雜的面貌。
本書的撰寫大抵依循上述研究路徑,然而,以嚴謹論文為標竿的專書寫作,亦如小說創作,在閱讀、書寫與思考的反覆、交叉進行過程中,每有「靈光閃現」或「突發奇想」,或者難得的「重大發現」,於是,原本預設的章節架構與擬定題目,只得一再微調、修整或重新校準,這樣來回往復的過程,竟使得本書每章內容與篇幅不斷擴增,遠遠超過原先以為的成果彙整;再加上部分篇章原是以英文寫成,如今進行語言轉換,與其說是修訂或改寫,毋寧篇篇皆是新撰了。這一路的撰寫與鑽研,雖仍不脫以台灣「少年小說」為研究焦點,但與過往所行之路徑相較,「視野」已然加深、加廣,對於戰後台灣「少年小說」的生成演化及其文化意涵也有了更深刻的思考與反饋。
這本專書的研究範疇涵蓋台灣戰後以來出版的少年小說, 文本的爬梳始自二十世紀六○年代以至二十一世紀初,時間約莫橫跨半世紀,可略窺台灣戰後少年小說的出版樣貌及其衍成。雖然如此,這本專書的寫作目的並不在於建構一個統整的史觀,或是提交一份系統化或全盤概括的台灣少年小說史論,而是試圖藉由理論的導引與議題的深化,探索並開展(閱讀)台灣少年小說的多元視角與文本內涵。依此,本書共分五章,首章為導論,以台灣與西方比較視點,探討戰後台灣「少年小說」的相關論述, 東西方(學界)對「少年小說」的界域想像,以及「少年小說」在世紀跨越轉折中所呈現的「流變」現象。其後各章分別聚焦於少年小說文本中的兒少主體形構,以及其所關涉的性別、童年純真、地方認同與(後)現代童年論述等現當代文學及文化研究所關注的課題。這些研究議題也是目前台灣兒童文學研究領域尚待開拓,或仍未深耕的面向。
本書以「少年小說」為關注焦點,如前所述,並非企圖對戰後以來在台灣出版的少年小說進行全盤檢視,而是以「焦點文本」(focal texts)作為探研對象。實際而言,本書是以研究「議題」為導向下,逐次開展文本的探索─六○年代台灣少年小說文本中明顯可見(或不容置疑的)「好孩子」與「純真兒童」及其(中)潛藏的(兒少)主體建構與文化政治的曖昧相關,七○年代逐漸興起及此中所揭示的「鄉土兒童」的主流(游移)想像與轉向,乃至九○年代及跨世紀之交翻上檯面的「野孩子」與「酷異兒童」的新興/另類「兒童典型」(alternative child images),種種小說文本敘事空間所「擬造」(invent)、「再現」(represent)、「交涉」(negotiate)的兒童構像、論辯與折變,毋寧是這部專書主要的關注焦點,並試圖以此為脈絡,細緻化小說文本的分析與探研。也因此,本書在「議題」的開導下,對於小說文本的擇取便不偏重於「名家」(包含名家所論)或「為數可觀」(如特定文學獎支撐下持續產製)的少年小說作品,而是著重於挖掘戰後以來若干值得關注,但已遭遺忘或淡忘,或尚未深入檢視,但十分值得探究的少年小說文本。
這般文本「採樣」的動機與原則,部分實受英國學者丹尼斯‧巴特(Dennis Butts)的啟迪影響。在《兒童文學與社會變遷:從芭芭拉‧郝芙蘭到菲力普‧普曼》(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Social Change: Some Case Studies from Barbara Hofland to Philip Pullman)這部專著中,巴特這名開創英國兒童文學與文化研究的先驅學者,以當代論題、文類推移、世代變遷的觀察視角, 探研英國自十九世紀中期以來至二十世紀末的兒童文學作品與英國社會變遷的脈動關係,其文本選樣即兼採較不起眼的作家的童書作品─如與珍‧奧斯汀(Jane Austin)同輩,同樣書寫「居家生活」(domestic life)故事的女作家芭芭拉‧郝芙蘭(Barbara Hofland),以及雖為名家之作,但較少受到關注的作品,例如以《黑暗三部曲》(His Dark Materials)著稱,並以其中《琥珀望遠鏡》(The Amber Spyglass)奪下成人文壇「惠特比文學獎」(Whitbread Book Award),以此成功打破「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藩籬的成名作家菲力普‧普曼(Philip Pullman) 早期發表的幾部較鮮為人知的歷史小說。誠如大衛‧洛德(David Rudd)的觀察分析,巴特以童書作品為研究對象,其所重並非在於理解這些童書作品的單獨意義與價值,而是「揭示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的密切相關」,以及更廣泛而言,童書作品「與其文化脈絡和所處時代的脈動牽連」,甚或超乎其上,「顯示了對於整體(通常是國際性而非僅屬國內的)社會、政治、歷史關 連影響下的文化生產」的洞悉(“Review” 485)。換句話說,巴特 研究文本的「採樣」,並不局限於「主流」或「重要」作家作品, 而是尋找具時代意義,但尚未或仍待發掘的文本,以其作為文化探究的重要啟示。
循此研究思路,本書少年小說「焦點文本」的擇取主要有:林鍾隆《阿輝的心》(1965)與謝冰瑩《小冬流浪記》(1966) 兩部台灣戰後少年小說的濫觴之作,以寫實手法呈現或「再現」台灣(戰後)早期的兒童主體樣貌與童年記憶;以及,張大春《少年大頭春的生活週記》(1992)與袁哲生《倪亞達》系列小說(2001-3),兩者於解嚴解禁後相繼問世,以「日記體」開創、營造少年小說文體與童年觀的世紀變革,凸顯少年小說文類的「另類」想像。戰後遷台作家(謝冰瑩、琦君、畢璞)的少年小說作品,以及由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所培植的「戰後世代」作家(林立、曾妙容、陳玉珠)的少年小說得獎作品,則可說是較少受到(研究者或讀者)關注,但別具歷史指標或文化象徵意涵。除可藉此微觀並細探(女)作家作品中對於「兒童」與「童年」主題意識所開展的多元論述與思考,從中亦可窺看不同世代(女)作家群以「少年小說」作為創作領地所開顯的(兒童)主體身分的殊異想像。
基於此,本書第壹章〈論述、界域與流變:台灣「少年小說」導論〉探討戰後台灣少年小說之生成與演化,內容含括少年小說概論及界義問題,除了綜述台灣兒童文學學界各家說法,包括林良、馬景賢、洪文瓊、洪文珍、楊思諶、張清榮、張子樟、李潼、傅林統、邱子寧等人之論說,也延伸「少年」一詞在中文及歐美文學及文化上的援用與想像。另外,探討「少年小說」, 乃至「青少年小說」文類的生成與發展,實無法排除歐美專家學者之見,尤其以蘿貝塔‧泰瑞茲(Roberta Seelinger Trites)、蘿蘋‧ 麥卡蘭(Robyn McCallum)及瑞秋‧費康納(Rachel Falconer)等人的論著最具啟發意義。不論就「少年小說」或「青少年小說」作為一文類的歷史沿革與變貌及其所彰顯或隱含的政治、社會、文化意涵,或是「(青)少年小說」所呈顯的權力與壓制等個人與(家庭、學校、社會、乃至國家等)體制的對抗與協商,還是「(青)少年小說」對「主體性」(subjectivity)議題的開顯與側重,種種論述皆足以援引為探討台灣「少年小說」文類的開展及其流變的重要參照。
第貳章〈再探「好孩子」:《阿輝的心》與《小冬流浪記》中的性別/家國論述與兒少主體形構〉採擷精神分析及主體建構論為研究視角,回訪林鍾隆《阿輝的心》(1965)及謝冰瑩《小冬流浪記》(1966)兩部戰後台灣少年小說的濫觴之作。本章著重探研小說文本中的「好孩子」主體形構與性別及家/國論述的相關,主要參酌茱莉‧克里斯蒂娃(Julie Kristeva)、朱蒂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保羅‧史密斯(Paul Smith),以及史都華‧霍爾(Stuart Hall)的理論學說,援以探討「主體性」(subjectivity)、「主體位置」(subject position),以及「主體能動」(subject agency)等後結構主義思維下對「主體」概念的思辨。本章試圖指出「好孩子」的主體形構,在台灣戰後早期童書作品中看似理所當然或不言可喻,卻每每在其「簡單」的敘事表象下,呈顯(或揭露?)此主體位置的複雜多變與弔詭曖昧。「好孩子」的主體身分與其說有何單純、一致的面貌,毋寧是複合、交混的「縫合」圖像,且一再透顯「折變」的可能。
第參章〈「可愛的兒童像」?戰後遷台女作家少年小說中的童年純真論述〉以遷台女作家謝冰瑩、琦君、畢璞產製於二十世紀六○年代的少年小說作品為關注焦點,探討其中所隱含或具現的「童年純真」論述。謝冰瑩的《林琳》(1966)側寫早期都會生活下貧苦少女的奮鬥故事,兒童的「純真」構像並非自外於成人世界呈顯一派無憂無慮,而是飽經風霜。女童主角在故事中幾度浮凸、強化的「模範兒童」造像,可謂「兒童純真」的昇華表現, 也是(成人)模塑「可愛」兒童像的極致樣板。琦君的《賣牛記》(1966)則是將兒童的純真與良善存記於懷鄉抒情之作,以之對比於成人世界的虛矯疏離或曲折難辨。故事中一段男童主角的離家尋牛,或許是琦君溫情主義的另類投影,其所彰顯的並非兒童對成人世界的「逆反」或「控訴」,而是直指「(兒童)純真」作為(成人)逃逸路線的可能,藉以尋覓或重溫失落已久的家庭溫暖。畢璞的《難忘的假期》(1967),簡言之,是以兒童的「純真」作為成人幽閉世界與禁錮心靈的救贖力量。這幾部少年小說文本所呈顯的「童年純真」觀,雖可見「可愛的」兒童構像,但小說文本所構築的兒童「純真」面貌,也依違在各式的文化建構與想像中,或作為療癒歷史傷口的解藥,或是以其作為重返想像家園的心靈秘境,或是,保守而言,作為因應政治變局下重建「進步社會」的理想寄託。
第肆章〈想像「鄉/土」: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少年小說得獎作品中的地方與認同論述〉聚焦於台灣七○年代少年小說作品,主要以林立(林玉敏)的《山裏的日子》(1975)、曾妙容的《飛向藍天》(1977)、《春天來到嘉和鎮》(1979),以及陳玉珠的《玻璃鳥》(1978)四部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少年小說首獎作品為探研對象。這些少年小說文本不約而同以「鄉/土」(home/ land)作為言說場域,或存記鄉野童年的美好想像,或側記台灣自然災害與人文地理環境的變遷,或再現台灣二十世紀七○年代工業化與都市化下兒童生活樣貌。兒童(主角)在這些小說文本中,經常折衝於懷舊與現實交錯的時空而成為流動主體,既跨越傳統農村的範限,周旋、擺盪於「城」與「鄉」交錯的時空中, 試圖建構自我主體,或探尋(新)身分認同;或是在城鄉差距的衝突與拉扯中,扮演雙重身分,既為傳統(鄉土)文化得以綿延與承繼的關鍵角色,也是新興社會步入現代化亟欲吸納的改革力量。與鄉土意識相關的童年書寫,在這些文本的演繹之下,遂成為多重(新舊)文化勢力相互角力、競逐、協商,以及再現的重要場域。
第伍章〈日記體少年小說、文化流動與(後)現代童年想像─以《少年大頭春的生活週記》與《倪亞達》系列小說為例〉探看少年小說另一書寫形式,舉出台灣九○年代及其後的少年小說創作,以張大春和袁哲生的「日記體少年小說」尤為令人矚目。小說文本所再現的童年生活圖景,在看似平淡無奇的「日常」敘事中往往可見兒童主體的「酷異化」。無論是「天真」與「酷異」的相關相涉,抑或「兒童成人化」與「成人兒童化」的難分難解,皆指向兒童/成人主體「易位」與「移位」的弔詭現象。張大春以「大頭春」此「非經典」(non-normative)兒童角色,巧妙開啟全球化/後現代視景下光怪陸離的都會童年想像; 袁哲生繼之而起,以「倪亞達」此平凡而幾近愚拙的兒童角色, 側錄新世紀都會兒童的另類成長面貌。兩者,無論就少年小說由傳統寫實跳躍至後現代日記體實驗性作品的文體變革,或是「兒童」觀點的突破,例如指出「童真」與「酷異」的曖昧難辨,皆為戰後台灣少年小說於世紀交替之際,開啟新頁並揭示新意。
身為兒童文學研究學者,多年以來,我一直思考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如何教我分析及閱讀兒童文學文本,而兒童文學文本又如何呈顯、拉伸、質詰或顛解(甚至拆解)理論的種種內涵和框架。在與「理論」及「兒童文學」兩者交涉的過程中,或試圖將兩者拉攏並置,以一窺究竟,最常遇到的問題,或經常得面對的質疑(不論這疑問是來自學院內或局外人):「理論」與「兒童文學」怎能搞在一起?有學界的聲音高喊,拿「理論」研究「兒童文學」太硬了吧?殺雞焉用牛刀?想想兒童文學那溫馨、可愛又美好的模樣,哪能禁得起理論的殘殺?(言下之意,這太不像話吧?!)另一方面,面對「淺薄」(字少、圖多)的兒童文學, 「深厚」的理論往往看似派不上用場,不免時而陷入窘境或不知如何是好。於是,這條研究之路,一路走來,總覺磕磕絆絆,時而窒礙難行,有時也因瞻前顧後而停筆許久。然而,理論和兒童文學真的那麼風馬牛不相及嗎?
就在這本書日漸成形時,英國兒童文學及文化研究學者大衛‧洛德(David Rudd)出版了近作《閱讀兒童文學中的兒童: 異端之見》(Reading the Child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 Heretical Approach),該書以精神分析作為理論基礎,試圖將令人望之生畏的「理論」(無論指涉其深奧義理或機械式操作)轉/化為探討兒童文學諸般樂趣與深意的「動力」(energetics)。洛德以「異端」自解自嘲,部分原由或是深知以「精要」的理論,琢磨「輕淺」的兒童文學,對兩者而言,恐怕都屬「大逆不道」。學養俱佳的洛德,在兒童文學研究領域,尤其「批判理論」的開拓,可謂執牛耳者,仍須如此「戒慎恐懼」,以理論閱讀/悅讀兒童文學之大不易,可見一斑。此外,洛德在該書引言中,以英國文學及文化研究的現況為例,幽幽指出過往居各類知識探究核心的「哲學」已趨式微,在各式標準化並講求「績效」的現當代研究生態中,(強調哲學思辨的)「理論」之無用(難以凸顯「亮點」),自不待言。
然而,洛德也借用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瓜達里(Félix Guattari)的論說闡釋理論閱讀與思辨的重要:「理論思想並非自外於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愈是「沉浸其中」愈能發現新意,以「探索新的『逃逸路線』」,並「釋放種種新式體驗文本的可能」(Reading 3)。這樣的研究路徑較似「球根」思考方式,呈現開放式的對話關係,而非直指書寫的完整或閱讀的完結。這本專書寫作,雖告一段落,但與其說已然走入終點,毋寧剛開啟一個新起點。這樣的書寫與思辨,使得「閱讀」兒童文學不再只是「貼近兒童」或為「教化兒童」等本質論或功用論的自然想像或「理所當然」,而是指向文學與文化層面的「思想」與「對話」,以及相關議題的開拓與挑戰─不僅探討「兒童」在小說文本中的形構與再現,更著眼於反思以「兒童」為主題/主體的文學作品或文化製品,在成人主導的(市場化、商品化、教育性)生產過程中無可避免的「客體化」問題。本書的寫作,試圖將主體、性別、地方論述、身分認同、鄉土意識,以及(後)現代童年想像等現當代文學及文化研究所關切的議題,納入兒童文學的研究範疇與視域,希冀如此的嘗試得以在台灣文學及兒童文學研究場域激盪出(更)多元而異彩紛呈的交流、對話與批判思維。
序
兒童文學的批判意識
本書的構成始於 101 年度國科會(現為科技部)專書寫作計畫,從近年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的成果出發。民國96年度開始執行國科會計畫,是以台灣二十世紀六○年代少年小說為研究場域,聚焦探討文本所形構的男童文化(boyhood)與性別建構的指涉關係,研究發現「好孩子」,或謂「模範兒童」的(陽剛) 主體形構與身分認同乃是六○年代少年小說(男童)敘事的核心。此敘事模式所呈顯的除了關乎男童的性別身分建構,也隱指國家認同的政治意識與兒童(國民)教養的相關。接續的計畫雖仍以六○年代少年小說為範域,但研...
目錄
序 兒童文學的批判意識
第壹章 論述、界域與流變:台灣「少年小說」導論
前言
「少年小說」論述:台灣與西方比較視點
「少年小說」界域問題
(青)少年小說 vs 小說中的(青)少年
(青)少年小說 vs 成長小說:關於少年「主體」的思考
「少年小說」的後現代轉向
第貳章 再探「好孩子」:《阿輝的心》與《小冬流浪記》中的性別/家國論述與兒少主體形構
前言
兩則引文與「主體」演繹
《阿輝的心》中的女性/他者與(陽剛)主體形構
《小冬流浪記》中的「家/國」論述與兒少主體形構
結語
第參章 「可愛的兒童像」?戰後遷台女作家少年小說作品中的童年純真論述
前言
賈桂琳 • 羅絲與《彼得潘個案》
《彼得潘個案》:「童年純真」論述及相關評述
戰後遷台女作家少年小說中的「童年純真」論述
《林琳》:童年純真與「悲苦」少女
《賣牛記》:童年純真與「叛逆」兒童
《難忘的假期》:童年純真與「野」孩子
結語
第肆章 想像「鄉/土」: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少年小說得獎作品中的地方與認同論述
前言
歷史語境、文學生產與台灣「鄉土少年小說」
鄉土少年小說中的「地方」與「認同」論述
《山裏的日子》:童年記述與「地方感」多重演繹
《飛向藍天》:「城/鄉」論述與「雙重」身分建構
《玻璃鳥》:「尋根」與「地方」認同
《春天來到嘉和鎮》:「地方」與「他者」想像
結語
第伍章 日記體少年小說、文化流動與(後)現代童年想像——以《少年大頭春的生活週記》與《倪亞達》系列小說為例
前言
日記體小說:文類發源與文體特徵
日記體少年小說:全球化文化流動與文學生產
日記體少年小說中的(後)現代童年想像
《少年大頭春的生活週記》中的「酷小子」
《倪亞達》中的「笨小孩」
結語
引用書目
論文出處
後記
序 兒童文學的批判意識
第壹章 論述、界域與流變:台灣「少年小說」導論
前言
「少年小說」論述:台灣與西方比較視點
「少年小說」界域問題
(青)少年小說 vs 小說中的(青)少年
(青)少年小說 vs 成長小說:關於少年「主體」的思考
「少年小說」的後現代轉向
第貳章 再探「好孩子」:《阿輝的心》與《小冬流浪記》中的性別/家國論述與兒少主體形構
前言
兩則引文與「主體」演繹
《阿輝的心》中的女性/他者與(陽剛)主體形構
《小冬流浪記》中的「家/國」論述與兒少主體形構
結語
第參章 「可愛的兒童...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收藏
收藏

 6二手徵求有驚喜
6二手徵求有驚喜





 收藏
收藏

 6二手徵求有驚喜
6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