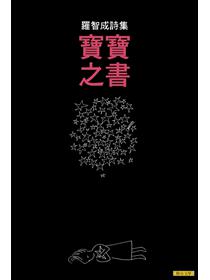第一章 詩的基本式
詩與非詩
經過後現代超前衛觀念洗禮的人,習慣把「去中心」、「泯除界域」和「消解大敘述」等口號掛在嘴邊,動輒顯現一副新虛無主義的樣子。這樣牽連過來所有學科/文類的劃分區別,也就成了徒然、甚或是一項不識趣的舉動!而原來極為可貴的「一種特殊的審美對象」的詩(周慶華,2008a:146~148),遇到這種解構威脅,想要標榜它來跟非詩對列,恐怕也處境顛危而要惶惑瘖啞以對了。
但情況又不能這般「任其發展」!因為凡是要解構別人的言論都得先保障自己不被解構的權利,以至「去中心」、「泯除界域」和「消解大敘述」等喧嚷也就形同假相;權力意志的介入和約定俗成的律則等總會在當中確保話語的存在(周慶華,2009a:36~42),而使得任何一種反抗論述的穿透動能失去效力。
所謂「詩」和「非詩」對列的邊界尋跡,自然就通過上述的「險巇」考驗而可能了。因此,有人要再盡情的說「詩是在理性之前所作的夢」(Diane Ackerman, 2004:287引)或「詩就是一個靈魂為一種形式舉行的落成禮」(Gaston Bachelard, 2003:41引)或「詩就像是一座愛的發電廠」(Mary Pipher, 2008:246引),就全憑自由而可以轉由我們予以附和或試為證成。而從現有的經驗來看,詩的「習造」獨特性已經有人在掀揭規模了:
跟《愛麗絲夢遊奇境記》中的白皇后一樣,詩人在早餐之前可以相信六件不可能的事為可能的。下面是我所開列的詩使其成為可能的各種學理上的不可能:(一)字面不可能;(二)非我存在的不可能;(三)做前所未有事的不可能;(四)改變不可改變事物的不可能;(五)等同對立雙方的不可能;(六)完全翻譯的不可能。詩運用包括譬喻和想像的聯想跳躍在內的許多手段,使這些不可能成為可能。(Philip J. Davis等編,1992:284)
具體的例證,分別如「歐文動人的一戰時的詩歌〈奇異的會見〉為字面不可能提供了一個具體例子。詩人在『深而昏暗的地道下』見到了他所殺死的敵人並相互交談。從字面上來看這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在夢境或幻覺中卻會成為千真萬確的事」、「人們在詩以及其他文學創作形式中常把自我同化於某些非我(如狄金蓀常用某位死者的聲音講話:『我死了,一隻蒼蠅嗡嗡叫』)」、「夢想、幻覺和想像乃是詩人創作的一些最有力的動機。詩人常常不加思索地把習以為常和熟諳的世界拋在一邊。丁尼生勛爵1842年的青年之作〈羅克司烈大廳〉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如果你覺得自己身處絕境,那麼努力想像會使你絕處逢生。在歐威爾的小說《1984》中,犯人被關在可怕的『101號房』,禁受各種各樣的恐怖和威脅,試圖給他們洗腦,使他們熱愛『老大哥』。在我的詩〈不!老大哥1984:練習〉中,對於蟲子的一種瘋狂恐懼被克服了,『老大哥』實施控制的環境失去了效用」、「對於詩人們來說,悖論和自相矛盾乃是生命的正當情形。在羅特克的歌謠〈清醒〉中,詩人把一系列看起來對立的東西等同起來了:醒和睡、思想和感覺、消失和持久、動搖和穩定」、「在上述諸種學理上的不可能和詩歌中存在的少數幾個真正的不可能之間,完全翻譯的問題可以成為一座過渡的橋樑(也就是由『再創作』來克服完全翻譯的不可能難題)」(Philip J. Davis等編,1992:284、286、288、289、290)。詩這種可以使不可能的事物成為可能的殊異色彩,就跟「無法如此」的非詩截然的區分開來。
其實,詩所要區別的還不止泛泛的「非詩」,它更要區別在非詩裏頭可能「近於詩」的作品。近於詩的作品,可以有非詩的成分,也可以有詩的成分,但終究因為它的「居間」性而不便讓它混淆於詩。這以光譜儀來表示,一端明顯是詩而另一端明顯是非詩,中間模糊地帶就是該一可以「相近於兩端而終不似」的作品:

同樣關係一個「精神勝利法」的課題,左邊項為直說,右邊項以意象比喻和象徵,而中間項則以事件象徵,彼此「各稱其職」而互不相侔。只是中間項可以彈性容受,或跨向詩,或跨向非詩,而以「近於」的特徵在兩端之間游移。如:
李龍第重回到傾瀉著豪雨的街道來,天空彷彿決裂的堤奔騰出萬鈞的水量落在這個城市……李龍第看見此時的人們爭先恐後地攀上架設的梯子爬到屋頂上,以無比自私和粗野的動作排擠和踐踏著別人……他暗自感傷著:在這個自然界,死亡一事是最不足道的……人的存在便是在現在中自己與環境的關係。(七等生,2003:176~178)
女孩咬著枕頭,彷彿要證明,她能扯碎纖維或肉類的嘴,一樣能撕裂誘惑,然後她憤然大吼……她母親爆炸了,「現在你的微笑像蝴蝶,可是到了明天,你的乳房就會像兩隻唧唧咕咕的鴿子,乳頭是兩顆鮮嫩多汁的野莓,舌頭是眾神溫暖的地毯,臀部是迎風的船帆,而燃燒在你兩腿之間的,是烈焰炙熱的熔爐,倨傲勃起的傳種金屬,在其中得以鍛鑄焠鍊。現在,晚安!」(Antonio Skármeta, 2001:77)
前則在敘事中所嵌進的「在這個自然界,死亡一事是最不足道的」、「人的存在便是在現在中自己與環境的關係」等存在主義式的議論,就有要向非詩端靠近的傾向;而後則在敘事中所取譬的「蝴蝶」、「鴿子」、「野莓」、「地毯」、「船帆」、「熔爐」、「傳種金屬」等意象,則又緊相對詩端招手,使得一個「模糊地帶」真的就這樣不定性的模糊起來(如果詩和非詩中也摻雜對方的成分或模擬中間項的情況,那麼它們就會逸離自己的位置而向此一模糊地帶靠攏)。
我們通常所認可的詩,就得像這樣排除敘事、說理等成分而僅以意象來比喻或象徵,將所要表達的情意高度的凝鍊濃縮。這樣敘事性作品裏縱使也會有意象,但它所重在事件的安排鋪陳,意象只是旁襯而不如在詩中為主調;至於說理性作品既以說理行文,偶爾可能藉點意象但也同樣無緣晉身為詩(更何況它根本不藉意象時,連「嘗試過渡」的影子都沒有)。這是緣所有文類/學科必要分類以為認知的前提而來的設定,權力意志(可以兼及文化理想)為它終極的制約力;此外,就無從再卯上所謂的客觀性或絕對性一類的形上意涵(周慶華,2004a;2006;2009a)。
雖然如此,以意象間接表達情意而撐起詩的「一片天」本身,還是有心理審美和生命解脫等特殊考慮,而使得有關詩質的設定不同於「泛泛之流」。這是文人殫精竭思所摶成的,它最基本的形式是以「外在之象(事物)」來表達「內在之意(情意)」;而為了整體的審美效果,文人還會將它作一有效的組織而使它同時具備音樂性;倘若還有需求(如為著繪畫效果或基進創新),那麼就會再額外附加或變形伸展詞語和組構的新表方式,以至一個專屬於詩的思維模式就這樣「排它自得」了:

這全為心理審美而設(供人玩味而從中獲得樂趣),也是詩作為一種文類(或領銜代表「文學」這個學科)所能區別於其他文類的特徵所在。但再深一層來看,詩的意象化特性卻不止為產生心理審美一項功能而已;它的藉以克服「言不盡意」的困擾和可逃離惱人問題的糾纏等生命解脫的效應,則又看似隱藏而實則隨時都會浮現出來。
所謂藉以克服「言不盡意」的困擾,這是起於語言多有「不盡達意」而又必須表出時的一種策略運作:
語言屬於抽象的符號,難以表達具體的情意,這就是它的侷限所在……面對這種困境,作者不是像劉勰《文心雕龍.神思》所說「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那樣自動擱筆,就是像《易繫辭傳》所說「聖人立象以盡(概略的意思)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那樣勉為設言。而比興的運用(比是比喻,興是象徵,二者為意象的主要呈現方式),就是基於後者而藉以「解決」言不盡意的難題。因此,當直敘繁說仍不能盡意時,使用比興就能「掩飾」困窘,並且可以繼續保有想要盡意的「企圖」。(周慶華,2000a:174)
這在詩中因為全部意象化而更容易「混合」或「強為寄存」。而所謂可逃離惱人問題的糾纏,則是另有不逮或有所規避時,藉助意象來「應付了事」以為脫困而著成典範的。好比宗教中人也偶爾要藉意象來「自我逃避」一樣:「宗教人採用意象,因為無法『直接』說出他想要說的,而意象容許他逃避『既成的』實在界。但他討厭把某種明確的實在界劃歸意象本身。事實上,宗教心靈創造了意象,同時又對這些意象保持一種『打破偶像的』態度。它今日斥為偶像者,正是它昨日奉為聖像者。黑格爾雖然把一切宗教符號貶抑到表象的層次,但卻清楚覺察當中有一種否定的驅力,使宗教反對它自己的意象」(Louis Dupré, 1996:160)。宗教的意象性語言弔詭的自我「宣示」所謂實在界或終極真理的不在場;同樣的,詩的意象性語言也等於不敢保證相關旨意的表達可以成功。因此,「自我逃避」也就成了一種戲玩意象的修飾詞,它終究要跟生命解脫的課題連結在一起(周慶華,2007a:125)。此外,明知可以達意卻刻意避開(丟下意象走人)以為逃脫他人的追問或逼仄,這就更深戲玩意象而可以併陳為生命解脫的形式。
顯然詩的意象化在審美經驗中必要獨標一類,這背後是有「辛苦經營」過程的。換句話說,即使詩的存在也跟其他文類/學科的存在一樣沒有什麼先驗性(儘由權力意志所終極促動左右),但它的「位階」明顯已經授權文人階層所賦予而進駐文化的精緻面領域;而這跟泛泛的語言成品或其他非詩的作品自然就要在有無「刻意摶造」或「別為鍾情」上拉開距離。
從抒情到創新世界
詩的這種獨樹一幟的心理審美和生命解脫風格,在「跨域升沈」中還會有一些系統內的變數。也就是說,同樣是詩,表現看似沒有什麼不同了,其實它們仍會緣於文化背景的差異而各有偏向;而這一偏向所徵候的是相異文化背景中人的心理審美和生命解脫不能不有內在的質差,以至總詩觀為一而內質取向則有偏強/偏弱或偏外/偏內的分別。試看下列兩首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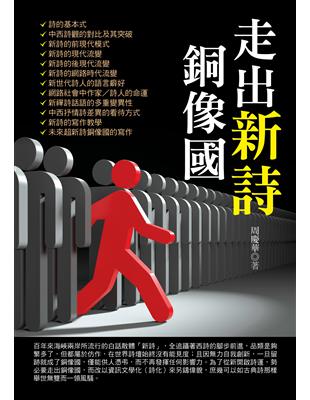


 收藏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