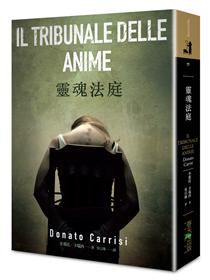在生命最低迴的角落,綻放人性與藝術的光芒!
《金翅雀》同名電影改編原著得獎小說
強勢橫掃歐美文學榜單NO.1當代不凡鉅作
博客來、誠品暢銷榜書
史蒂芬金說:十年難得一見的精采故事!
譽為21世紀版《孤雛淚》「當我們自根本升起,又屈辱地沉沒回根本中時,
那些死亡無法觸碰的,就是愛的光輝與榮耀。」
博物館出現的紅髮女孩,攫住我的目光。
當時,母親正細訴她最愛的畫作:「金翅雀」,
一隻黃色的小雀鳥,身後襯著一片蒼白背景,鐵鍊鎖著纖細腳踝──正如母親的面容,
瞬間,博物館發生大爆炸。救我一命的,是那個紅髮女孩。
母親的死訊,硬生生斬裂過去與未來。
十三歲的我奇蹟倖存,住進紐約公園大道空洞冷清的豪宅。
然而,我是如此悲傷、如此空茫,很難回憶這個世界除了死亡之外,還有其他模樣。
沒有人知道的是:
在爆炸的漫天煙塵與神智不清下,我悄悄拾走那幅名為「金翅雀」的畫作。
成年之後,穿梭在上流畫室與遍布灰塵的古董店間,遊走於墮落之城的迷失與混亂之際,
──我始終將那幅畫帶在身邊。
這幅不該屬於我的畫作,與我的命運愈來愈密不可分,引發連串波瀾不斷的驚險事件,
就像兩股洶湧交纏的暗流,將彼此捲入深不見底的黑暗之中……
【本書特色】• 唐娜.塔特以大師級的寫作功力帶來這部讓人繃緊神經的偉大作品。
• 書中角色鮮明深刻,對白暗藏機鋒,充滿精雕細琢的文學韻味。
• 彷彿哲學家冷靜清晰地將這段關於美好幻滅、迷失墮落,救贖追尋的懸疑故事娓娓道來,在生命最低迴的角落綻放人性與藝術的光芒。
【名家媒體讚譽】《金翅雀》是一本稀世之作,是一個偉大的成就。唐娜.塔特寫出了一本傑出的小說。
──史蒂芬金
這是一本燦爛輝煌的小說,收集了所有她說故事的傑出天分,成就了一個讓人痴迷又低迴不已的整體,喚醒讀者一種身歷其境、徹夜不眠的閱讀樂趣。
──紐約時報
這是一個驚人的成就。如果有哪個人失落了對說故事的愛,《金翅雀》一定會讓他找回來。小說的最後幾頁,將表象之下所有嚴肅、偉大、複雜的意念捧向光明的那一面。
──衛報
這是一則現代的史詩,老式的朝聖:想像狄更生的作品裡出現槍、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書裡出現毒品,托爾斯泰的書裡出現古董。如果這本書沒讓唐娜.塔特儕身多為男性成員組成的「美國偉大小說俱樂部」,讓她跟史坦貝克、哈波.李、索爾.貝洛、菲利普.羅斯……等人喝一杯的話,那麼我們應該讓那家俱樂部關門大吉,然後再開另一家「全球偉大小說俱樂部」──因為就該如此。
──泰晤士報
【獲獎紀錄】★ 榮獲2014年美國普立茲小說獎!
★ 紐約時報年度十大好書、暢銷榜No.1
★ 亞馬遜年度編輯嚴選好書No.1
★ 亞馬遜年度好書No.1
★ BookPage年度好書No.1
★ 科克斯書評年度好書
★ 衛報年度十大小說
★ 邦諾書店年度小說
作者簡介:
唐娜.塔特Donna Tartt
美國當代著名女作家,1963年出生於密西西比州的格林伍德,五歲時,寫了第一首詩,十三歲時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份文學評論雜誌上發表了第一首十四行詩。至今除了一些散見於報章雜誌的詩與短文,只有三本長篇小說問世,而這三本小說各自花了十年的時間寫作。她認為寫作最深層次的滿足來自雕琢句子──正確的詞,適當的比喻。彷彿一個微型畫畫家,用一支眼睫毛大小的畫筆,創作一幅大型壁畫。她的寫作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沉浸式體驗」──寫一本可以讓自己沉迷其中的書;進入一個迥異的世界。
處女作《祕史》(The Secret History),出版後震驚文壇,評論家認為《祕史》充滿懸疑,探尋人類罪惡的本性,並對古典與當代的價值和哲學作了比較,是一位天才作者的閃亮登場。她的文字似乎有一種魔力,而每一頁密密麻麻的《祕史》,閱畢之後久久無法跳離書中的冷冽氣氛,是一本歷久彌新的當代文學經典。
2002年,隨著《小友》(The Little Friend)的出版,唐娜.塔特證明自己並不是曇花一現的作家。評論家高度讚揚了這本小說,認為它具有散文的文風,人物性格鮮明,敘述緊湊而綿密。2004年,她成為英國坎農格特出版社發起的「重述神話」寫作專案的首批入選作家。
睽違十二年,唐娜.塔特耗費十年時間寫作《金翅雀》,是她三部作品中篇幅最長的。一推出便掀起英美文壇巨浪,橫掃各大年度暢銷榜單,並榮獲2014年普立茲文學獎。
相關著作:《金翅雀(同名電影改編原著普立茲獎小說,上冊)》《金翅雀(同名電影改編原著普立茲獎小說,下冊)》《金翅雀》《金翅雀(燙金木紋藏書箱獨家限量典藏版)》
譯者簡介:
劉曉樺
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學士,美國加州聖地牙哥州立大學會計所碩士。現為專職譯者。譯作有《最仁慈的愛》、《聖骨之匣》、《教育大未來──我們需要的關鍵能力》、《帕迪多街車站》、《寫作的祕密》等書。
個人部落格:kayhua725.blogspot.com
各界推薦
得獎紀錄:
★ 榮獲2014年美國普立茲小說獎!
★ 紐約時報年度十大好書、暢銷榜No.1
★ 亞馬遜年度編輯嚴選好書No.1
★ 亞馬遜年度好書No.1
★ BookPage年度好書No.1
★ 科克斯書評年度好書
★ 衛報年度十大小說
★ 邦諾書店年度小說
得獎紀錄:★ 榮獲2014年美國普立茲小說獎!
★ 紐約時報年度十大好書、暢銷榜No.1
★ 亞馬遜年度編輯嚴選好書No.1
★ 亞馬遜年度好書No.1
★ BookPage年度好書No.1
★ 科克斯書評年度好書
★ 衛報年度十大小說
★ 邦諾書店年度小說
章節試閱
第一部
荒謬並不帶來自由,而是束縛。
──卡繆
第一章 捧著骷髏的男孩
1.
仍在阿姆斯特丹時,我夢見了母親,那是許多年來的第一次。當時我已在旅館裡躲了超過一週,不敢打給任何人,也不敢出門。即便是最細瑣尋常的聲音都令我心驚膽戰,惶惶不安:電梯的叮鈴聲、哐啷作響的飲料推車,甚至是教堂大鐘的報時。在那宏亮的鐘鳴聲中,德維斯特圖倫飯店與聖方濟各沙勿略堂猶若一抹幽影,一幅末日童話的織錦繡帷。白天時,我坐在床尾,絞盡腦汁想要解讀電視上的荷蘭新聞(但完全是白費力氣,因為我一句荷蘭文也不懂)。放棄後,便裹著駝毛大衣,坐到窗邊,遠眺運河──我離開紐約時太過倉促,帶的衣服不夠保暖,即便在室內也不足以禦寒。
屋外熱鬧非凡,生氣蓬勃。時值聖誕,夜裡,運河橋上的燈火輝煌璀璨,路上男女面頰通紅,圍巾在刺骨寒風中翻騰飛舞,載著耶誕樹的腳踏車唰然駛過石板路。午後,一支業餘樂團演奏聖誕頌歌,微弱的旋律顫巍巍地飄盪於冬日之中。
房內,客房服務的餐盤狼籍一地,到處都是菸蒂,從免稅商店買來的伏特加早已變得溫熱。在那些坐立難安的幽禁時光中,我就像囚徒熟悉牢籠般,把房裡每一個角落摸得清清楚楚。這是我首次造訪阿姆斯特丹,雖然一眼也不及好好欣賞這城市,但這間客房,在它那荒涼蕭索、寒風穿隙、陽光濯滌的美麗中,彷彿散發著一種明銳的北歐感,有如一具迷你小巧的荷蘭模型,在淨白如清教徒式的儉樸中又點綴有東方商船運來的奢華飾品。寫字桌上掛著兩幅小小的金框油畫,我花了異常久的時間凝視端詳。其中一幅畫的是一名農民在教堂旁的結凍池塘上溜冰,另一幅是一艘小船在波濤洶湧的冬海上顛簸掙扎。它們只是裝飾用的複製品,沒有任何特別之處,但我仍細細打量,彷彿畫中藏有什麼能破解古法蘭德斯大師內心祕密的關鍵線索。飯店外,凍雨敲打窗戶,運河上煙雨朦朧。儘管房內的錦鍛鮮明濃豔,地毯柔軟舒適,但冬日的燈火仍散發一種一九四三年的冰冷色調,令人不由想起貧困的生活、無糖可加的稀薄淡茶、饑腸轆轆進入夢鄉。
每日清晨,我會趁天光依舊黯淡,早班的服務人員仍未上班,大廳依舊冷清前下樓取報。飯店裡的員工壓低音量,輕聲交談,腳步靜悄無聲,淡漠的目光在我身上一掃而過,彷彿我並不存在:那個住在二十七號房、白天裡從不下樓的美國人。我也努力安慰自己,那名夜班經理(深色西裝、平頭、玳瑁眼鏡)大概也費心做了些安排,以免飯店引來什麼騷動或麻煩。
儘管先驅論壇報對我隻字未提,但消息已在荷蘭的各報章媒體傳了開來。密密麻麻的外國文字如吊人胃口般擺盪於我理解範圍之外。Onopgeloste moord 。Onbekende 。我上樓,回到床上(身上依舊緊裹大衣,因為房裡實在太冷了),將報紙鋪滿被單。照片裡有警車、有犯罪現場的封鎖膠條,但就連標題都如天書一般。雖然媒體似乎仍未掌握我姓名,但我看不出文章裡有沒有任何關於我的描述,或是否仍有線索尚未公開。
客房。暖氣。Een Amerikaan met een strafblad 。運河裡橄欖色般的綠波。
因為我又冷又病,加之多數時候根本不知該做些什麼才好(除了保暖的衣物外,我也忘了帶書),所以白天裡幾乎都窩在床上。夜暮似乎在午後三、四點便拉下。滿床的報紙窸窣作響,我不停在夢境中穿進穿出,而且幾乎所有夢境都瀰漫著同一股朦朧焦慮,無聲無息地滲透至清醒時刻:法院開庭審理;行李在停機坪上爆開,衣物散落滿地;我在機場裡看不見盡頭的走廊上拔足狂奔,努力想趕上飛機,卻知道自己永遠趕不上。
多虧這場高燒,我做了許多詭異矜奇又栩栩如生的怪夢,在床上大汗淋漓,抽搐掙扎,分不清外頭是日是夜。但就在最後也最糟糕的幾個夜裡,我終於夢見了母親。那夢境神祕倏忽,感覺不像夢,反而更像一次探訪。我夢見自己在霍比的店裡──或者說得準確些,在某個陰森昏暗的異夢空間裡,四周約略布置成店裡的模樣──而母親驀然出現身後,我在鏡中看見她的倒影。一見到她,我便欣喜欲狂,傻楞原地,動彈不得。是她,從頭到腳、寸寸分分都是如假包換的她。她身上的雀斑、凝視我的笑容,都比往昔更加美麗,卻不見絲毫年耄,烏黑的秀髮與俏皮上揚的嘴角也一如過往。那不是夢,而是一種充盈房內的存在;一種力量,一個真真切切的化外之物。儘管我極度渴望,卻曉得自己不能轉身。與她正眼相望是不為我和她世界所允許的,這是她唯一能夠探視我的方式。我們的目光在鏡中默然交會良久,就在她彷彿要開口時──愉悅、憐愛與著惱的神情在臉上摻雜交錯──一團白煙在我們之間裊裊升起,而我,就這麼醒來了。
2.
假若她仍在世,事情就不至演變於此。但不幸地,她在我幼時便意外亡故。儘管在那之後,我所經歷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但失去她時,我仍像失去所有標的,再也無可前往幸福的國度,擁有其他更熱鬧或更和諧的生活。
她的死猶如分野,劃分了過去與未來。儘管悲傷,我卻不得不承認,在這麼多年過去之後,我仍未遇到一個像她一樣,能讓我覺得自己備受寵愛的人。只要有她在身邊,世界就彷彿活了起來。她就像一盞迷人的舞台燈,將四周照得明亮閃耀,透過她雙眼所見的一切都比平常更鮮明、更繽紛──我還記得在她過世的前幾週,我們在東村一家義大利餐廳共進遲來的晚餐。她陡然抓住我衣袖,只見一個插滿蠟燭、可愛至極的生日蛋糕從廚房裡端了出來,微弱的燭光映照在漆黑的天花板上,昏黃搖曳。侍者將蛋糕放到桌上,火光在家人間跳耀,照亮老婦人幸福洋溢的面孔,滿室盡是溫馨的笑容。侍者雙手背在身後,往後退開──其實就是一場你可以在下城任何一家平價餐廳看見的普通生日晚餐。我敢保證,若非母親之後沒多久就意外身亡,我連記都不會記得。但她死後,那畫面一遍一遍浮現腦海,此生或許再難忘懷。那圈暈黃的燭火,那在我失去她時,也同時失去的日常幸福。
而且母親非常美麗。雖然這並非重點,但她確實是個美人。剛從堪薩斯來到紐約時,她曾當過一陣子的兼職模特兒,但面對鏡頭時總是過於緊張,因此無法成為一流的模特兒。無論她擁有什麼樣的美麗,都無法轉譯至底片之中。
但她就是她,一件舉世罕見的珍寶。我不記得看過任何真正與她相像的人。她有一頭烏黑的秀髮,在夏天裡會冒出雀斑的嫩白肌膚,明亮的瓷藍色眼瞳。那對斜斜的顴骨散發著一種混合部落與如凱爾特曙光般陰鬱夢幻的奇異氣質。別人有時會猜她是冰島人,但實際上她來自奧克拉荷馬邊境附近的一座堪薩斯小鎮,擁有一半一半的愛爾蘭與卻洛奇血統。她就像賽馬般亮麗動人、大膽沉著、光鮮優雅,卻總喜歡自稱是土包子,逗我發笑。不幸的是,她這份異國風情在照片中卻顯得有點過於嚴厲與冷酷──化妝品遮去了她的雀斑,黑髮在頸後束成馬尾,看上去就像《源氏物語》中的貴族──卻絲毫不曾捕捉到她的溫暖、活潑,以及我最愛她的飄忽性情。你可以從照片散發的僵硬感中明顯看出她有多不信任鏡頭。那是一種如老虎般的警戒神態,彷彿準備好隨時迎接攻擊。但平時的她完全不是那樣。她的腳步迅捷雀躍,動作倏忽輕盈,總是坐在椅子邊緣,彷彿一隻優雅纖長的水鳥,隨時可能振翅驚飛。我好愛她身上的檀香香水,那味道是如此濃烈、如此猝不及防。也好愛她彎腰親吻我額頭時,漿挺的裙子總會發出細微的窸窣聲。聽見她笑,你就會想放下手邊的一切,隨她而去。無論她去哪兒,男人總會用眼角餘光偷偷打量她,他們的眼神有時甚至會讓我有些著惱。
她的死是我的錯。其他人總是有點太急著想要安慰我。他只是個孩子;誰想得到呢;太可怕了;運氣真糟;這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沒錯,這些話句句不假,只是我一個字也不相信。
事情發生在紐約,十四年前的四月十日(光是寫到這日期,我的手也忍不住停滯。我必須強迫自己寫下去,強迫自己繼續動筆。那原本是再平凡不過的一天,如今卻彷彿一根插在月曆上的生鏽鐵釘)。
倘若那天一如預期地度過,那麼它將平平淡淡消融於夜空,與我其他所有八年級的日子一同無聲無息地淹沒於時光洪流之中。我現在會記得什麼呢?或許零星的斷簡殘篇,或許什麼也不記得。但想當然爾,那天早晨的紋理已深深烙印於腦海,甚至比此時此刻還要清晰,即便是空氣中的浸濡濕意也依舊飽滿鮮明。前一夜下了雨,猛烈的暴風雨,不僅店鋪淹水,就連幾個地鐵站都關閉了。我和母親站在公寓外那塊吸飽雨水、踩上去就啪滋作響的門毯上;她最喜歡,同時也對她極為仰慕的門房阿金高舉手臂,倒退走在五十七街上,大聲吹口哨,替我們招攬計程車。車輛呼嘯而過,濺起波波骯髒水花。雨水盈潤的烏雲在摩天大樓上的高空翻騰變幻,遮蔽清澈的藍天。廢氣瀰漫街道上,寒風濕濡輕柔,宛若春日。
「唉呀,那輛車有人了。」阿金在街頭的嘈雜聲中高喊,往後退開,看著計程車揚起水花,轉過街角,空車提示燈啪地熄滅。在所有門房之中,就屬他身材最為矮小:一名蒼白削瘦、活潑開朗的小個子,來自波多黎各,膚色淺淡,過去曾是羽量級的拳擊手。儘管因為嗜酒的關係,面孔略顯浮腫(有時值夜班時可以聞到他身上有J&B的啤酒味),但身材依舊結實,動作也依舊敏捷──滿口玩笑,老愛躲在街角抽菸,天冷時就原地踱步,朝戴著白手套的雙手呵氣,用西班牙文的笑話逗得其他門房哈哈大笑。
「趕時間嗎?」他問母親。他的名牌上寫著波特.D,但大家都叫他阿金,因為他嘴裡鑲了顆金牙,也因為他的姓「de Oro」在西班牙文中即「黃金」之意。
「不,我們不趕時間,別擔心。」但她一臉疲憊,用顫抖的雙手將頸間鬆脫翻飛的圍巾重新繫好。
阿金一定是發現了,因為他瞥了我一眼(我逃避似地靠在公寓門口的水泥花架上,視線四處飄移,就是不敢看向她),臉上隱隱流露不以為然的神色。
「今天不搭地鐵嗎?」他問我。
「嗯,我們有些事要辦。」見我一時語塞,母親便代為回答,但聽起來不是太有說服力。我通常不會注意她穿了什麼,但她那天早上的裝扮(白色風衣、粉紅色薄圍巾、黑白雙色的樂福鞋)卻深深烙印在我腦海,讓我再難回想她其他模樣。
那時我十三歲。我非常不願回想我們共度的最後一個早晨是多麼彆扭,就連門房都察覺到我們之間的尷尬。其他時候我們總是有說有笑,但那天早晨卻幾乎無話可說,因為我剛被學校勒令休學。前一天,校方打去她的辦公室,回家後,她一語不發,怒不可遏。最糟的是我根本不曉得自己為什麼會被休學,但有七成五的把握,應該是畢曼先生(在從他辦公室走去教師休息室的路上)向二樓樓梯間窗戶瞄了一眼,卻好死不死撞見我在校內抽菸(或該說看見我站在吞雲吐霧的湯姆.蓋伯旁;抽菸的人是他;但這在我們學校基本上就等同自己違反校規。)母親痛恨香菸。她父母是一對和藹可親的馴馬師──我很喜歡聽母親說他們的故事,但很不公平地,我還沒來得及認識,他們便都已與世長辭──常往返於西部各地,以培育摩根馬維生,愛喝雞尾酒、打橋牌,每年一定參加肯塔基的賽馬大賽,家裡隨處可見銀製的菸盒。但有一天,當外婆正要從馬廄回屋時,忽然彎腰劇咳,甚至咳出血來。此後,在母親的青春歲月裡,氧氣筒成為長駐前廊的風景,臥房的窗簾再也不曾拉開。
但是──正如我所恐懼,而且並非毫無來由的恐懼──湯姆抽菸的事只是冰山一角。我在學校麻煩纏身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事情是從幾個月前,父親拋妻棄子、離家出走那時開始的,或該說像滾雪球般越滾越大。我和母親向來不是太喜歡他,而且少了他,我們的日子其實過得更開心,但其他人似乎都對他毫無預警的出走大為震驚與痛心(他沒有留下任何錢財、扶養費,或聯絡地址)。我在上西城的學校老師十分同情我,急於提供最大的諒解與支持,以至於給我──一個拿獎學金的學生──各種特別的補助金、延長我的作業期限,並一而再、再而三地給予我改過的機會。他們不停將繩子越放越長,直到幾個月後,我發現自己已然垂降到一個深不見底的深淵。
因此,我們兩人──母親和我──接獲學校通知,請我們過去會面。會議十一點半才開始,但反正母親早上都得請假,我們就想提早到西城──吃早餐(還有,展開一場嚴肅的談話,我想),順便替她同事買生日禮物。她前一晚凌晨兩點半才睡,電腦螢幕的光芒映在她神色凝重的面孔上,手指不停敲打鍵盤,撰寫電子郵件,為早上的請假做準備。
「我不知道妳怎麼想,」阿金對母親說,語氣有些激動,「但我已經受夠了這春天和濕氣,一天到晚都在下雨,下雨──」他打了個哆嗦,做出拉緊領口的樣子,瞥向天空。
「我想下午應該就會放晴了。」
「是啊,但我已經準備好要迎接夏天了。」他搓了搓雙手,「人們一個個離城,他們不喜歡夏天,老是抱怨那高溫,但我呢──我是隻熱帶鳥,天氣越熱越好。夏天你就放馬過來吧!」他拍拍雙手,踏穩馬步,擺出準備接招的姿勢。「而且──我最喜歡的,就是城裡會變得好安靜。到了七月啊──哪裡都人去樓空,整座城市昏昏欲睡,大家都離開了。妳知道嗎,」他彈了下手指,計程車呼嘯而過,「那就是我的假期。」
「但留在這兒不會覺得很熱嗎?」我那個性冷漠的父親就討厭她這點──老是喜歡和女侍、門房或乾洗店裡氣喘吁吁的老頭閒聊。「我的意思是,冬天裡你起碼可以多加件大衣──」
「欸,妳有在冬天守門過嗎?我告訴妳,那可不是普通的冷。不管妳穿了幾件外套,戴了多少帽子,只要一、二月裡站在這裡,吹著從河上灌來的寒風?呼──那真的是冷翻了。」
我心浮氣躁,一面啃著自己的大拇指指甲,一面看著計程車無視阿金高舉的手臂呼嘯而過。我知道在十一點半的會談開始前,這將會是一場煎熬的等待,而我所能做的,就是動也不動站在原地,不要脫口而出任何會自找麻煩的問題。我不曉得我和母親踏進辦公室後,他們會送上什麼出奇不意的驚喜。「會談」這兩個字隱含有威權、指控、擊垮,或許還有驅逐的意味。如果我失去獎學金,那將會是一場天大的災難。父親離開後我們就破產了,只能勉強付出房租。最糟的是,我擔心畢曼先生已經從某處得知我和湯姆.蓋伯一起去漢普敦過夜時,曾闖入無人居住的度假別墅。雖說是「闖入」,但我們沒有破壞任何門鎖或損壞任何物品(湯姆的母親是房屋仲介,我們用從她辦公室架上偷來的鑰匙開門),主要只是看看衣櫥裡有些什麼東西,翻了翻梳妝台的抽屜而已。不過我們確實也拿了點東西:冰箱裡的啤酒、一些Xbox的遊戲和一片電影光碟(李連杰的《鬥犬》),以及一些些現金,總共大約是九十二塊──都是從廚房罐子裡掏出來的皺巴巴的五元鈔和十元鈔,以及從洗衣間換洗衣物口袋中撈出來的大把零錢。
只要想起這件事,我就一陣反胃。我去湯姆家已經是幾個月前的事,但即便我拚命告訴自己,畢曼先生絕不可能知道我們私闖民宅──他怎麼可能知道?──我的想像力卻依舊飛馳,驚慌失措地瘋狂亂竄。我已經打定主意絕對不會告發湯姆(即便我無法同樣肯定地說他沒有出賣我也一樣),但那卻令我進退維谷。我怎麼會如此愚蠢?強行入侵是違法的,是要坐牢的。前一夜,我在床上躺了好幾個鐘頭,遲遲無法入睡,心裡煎熬萬分,輾轉反側,只能看著一波又一波的雨水擊打窗戶,思忖自己該怎麼回答他們的質問。但如果我連他們知道什麼都不曉得,又能怎麼替自己辯解?
阿金重重嘆了口氣,放下手臂,倒退走回母親佇立之處。
「真不敢相信。」他對她說,一眼仍疲憊地留意馬路,「蘇活區那淹了大水,妳有聽說吧?卡洛斯說聯合國總部那兒有幾條街都封了。」
我悶悶不樂地看著一群工人走下市區巴士,猶如成群的黃蜂般冰冷陰鬱,毫無欣喜之色。若是再往西走一、兩條街運氣可能會好些,但我和母親已經學乖了,知道如果我們自己去招車,阿金會不開心。但就在這時──事出突然,我們都嚇了一跳──一輛亮著空車指示燈的計程車硬切過巷子,朝我們疾駛而來,濺起一大波透著下水道味的水花。
「小心!」計程車猛然停靠路邊,阿金出聲示警,往旁跳開──隨即發現母親沒有雨傘。「等等。」他說,舉步就要走進大廳。他將失物招領的雨傘收在壁爐邊的一只銅桶裡,到了雨天就重新分發給需要的住戶。
「不要緊。」母親高喊,在包包裡翻找她那把糖果色的條紋小折疊傘。「別麻煩了,阿金,我這兒有──」
阿金跑回路旁,替她關上車門,然後彎腰傾身,敲了敲車窗。
「祝妳有個美好的一天。」他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荷蘭文,意指「凶殺懸案」。
2 荷蘭文,意指「未知」。
3 荷蘭文,意指「美國前科犯」。
第一部
荒謬並不帶來自由,而是束縛。
──卡繆
第一章 捧著骷髏的男孩
1.
仍在阿姆斯特丹時,我夢見了母親,那是許多年來的第一次。當時我已在旅館裡躲了超過一週,不敢打給任何人,也不敢出門。即便是最細瑣尋常的聲音都令我心驚膽戰,惶惶不安:電梯的叮鈴聲、哐啷作響的飲料推車,甚至是教堂大鐘的報時。在那宏亮的鐘鳴聲中,德維斯特圖倫飯店與聖方濟各沙勿略堂猶若一抹幽影,一幅末日童話的織錦繡帷。白天時,我坐在床尾,絞盡腦汁想要解讀電視上的荷蘭新聞(但完全是白費力氣,因為我一句荷蘭...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7收藏
7收藏

 18二手徵求有驚喜
18二手徵求有驚喜



 7收藏
7收藏

 18二手徵求有驚喜
18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