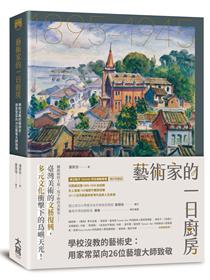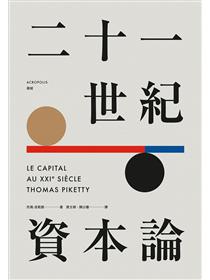人要經過多少時間才能放下過去?
《行過地獄之路》曼布克獎得主、澳洲作家理查‧費納根又一暢銷代表作。
榮獲澳洲文壇最高榮譽維多利亞總督文學獎
作者親自擔任導演搬上大銀幕,入圍柏林影展正式競賽
如果悲傷沒有理由,世界上就沒有受苦的理由
真相,真的值得用人生去換取嗎?一九五四年,坡匠‧布羅決定帶著妻子和女兒離開斯洛維尼亞當地的戰後難民營,來到澳洲南方塔斯馬尼亞山區,協助當地興建水壩,從頭開始新生活。某個嚴冬夜晚,他心愛的美麗妻子獨自離家後再也沒回家,留下他獨自照顧三歲女兒松婭。坡匠滿腹痛苦無人可以傾訴,只能夜夜借酒澆愁,酒精卻徹底壓垮了父女間的橋梁,終於女兒也一去不回。多年以後,長年在雪梨一人生活的松婭,在工作的電視臺觀賞水壩興建紀錄片時,竟認出了畫面中那個發狂猛揮大錘的身影,正是自己的父親。母親不告而別後父親總是那樣悲傷的臉,那張臉曾經像一堵牆,幾乎令松婭窒息,如今那道牆遠遠看上去像一扇門,而門後那個人多年來守住一個祕密在等著她回家。
「我的媽媽是蕾絲。我的爸爸是木頭。
我是被撕成兩半的蕾絲。裂成兩半的木頭。」我是什麼呢?孤伶無助的女兒半生苦思,不勝悲抑。如同前作書名取自「奧之細道」,本書書名援引日本禪師白隱慧鶴的知名公案「隻手之聲」──兩手拍掌可以發出聲音,一隻手發出什麼聲音?寓意人生中面臨到無解,其實是無能為力的問題。作者藉由書寫一對固執又不知變通的父女,經歷家庭悲劇,無法相互諒解,任數十年時光蹉跎。從蕾絲、木頭等一般物件,作者展露海明威「冰山理論」的修辭技法,透過象徵去揭示人物性格並豐富內涵,書中「象徵」無所不在,亦如浩大的水壩工程,以及書中提到一九六七年塔斯馬尼亞叢林大火。其實理查‧費納根用情極深地透過書寫這本小說,去關注二次大戰後,短短十五年內湧入澳洲多達一百五十萬人的歐洲移民,他們水深火熱的窘迫生活。以簡潔、含蓄而詩意的象徵手法,一筆舉起這群小人物,他們人生中的失落的時光,與對愛的堅毅執著。
「要不害怕,就得去想像沒有經歷過的世界。」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暴力史。這是一部悲愴的小說,如同《行過地獄之路》,本書主角同樣「在時間中漸漸失去愛的能力,產生了日後影響一生的錯亂和痛楚。」然而,平凡怯懦之人,也有充滿慈愛光輝的時候,比如坡匠滑稽的示愛木作,再現作者擅長的「頓降法」,藝術終會在絕望時出手拯救。親人的愛有時很痛,像一個謎。轉身離開,還是重逢互擁?掩卷之際思緒如浪濤淘湧,心跳搏動難以撫平。從一個家庭的悲劇,作者有意圖帶領讀者從漠不關心,到更開闊地去沉思人類的創傷和同理心,真相往往比謊言傷人,但記憶終會尋回正義。反覆讀下去,更加驚覺這部小說的偉大。
「不快樂的人,除了過去,什麼也沒有。」──《行過地獄之路》
如果痛苦依舊每天早上都會重新出現
人,不應該任由更大的命運所擺布。作者簡介:
理查.費納根 Richard Flanagan
一九六一年出生於澳洲塔斯馬尼亞省,是澳洲頂尖文學家。他的小說《Death of a River Guide》、《Gould’s Book of Fish》(大英國協作家獎作品)、《The Unknown Terrorist》、《Wanting》、《行過地獄之路》、《First Person》獲獎無數,在四十二國印行。他的父親死於費納根完成《行過地獄之路》那天,是泰緬死亡鐵路的存活戰俘。《行過地獄之路》於二○一四年獲得曼布克文學獎殊榮。
譯者簡介:
高紫文
臺師大工業科技教育系畢業,熱愛翻譯,譯有《阿垂阿斯家族》、《永恆的懷疑》、《塔樓》、《失控的正向思考》、《馬特洪峰》、《1940法國陷落》、《狼哨》、《美國狙擊手》、《神鬼交鋒》、《納粹獵人》、《原子城女孩》、《雜碎:美國中餐文化史》等二十餘本譯作。
各界推薦
得獎紀錄:
榮獲澳洲文壇最高榮譽維多利亞總督文學獎
作者親自擔任導演搬上大銀幕,入圍柏林影展正式競賽
媒體推薦:
一部必須被聽見的故事。──CNN
心碎的故事。──《洛杉磯時報》
難忘的。──《坎培拉報》
迷人的。──《泰晤士報》
深情動人。──《衛報》
鐵定成為經典。──澳洲《太陽先驅報》
揪心啊。──《文學評論》
得獎紀錄:榮獲澳洲文壇最高榮譽維多利亞總督文學獎
作者親自擔任導演搬上大銀幕,入圍柏林影展正式競賽媒體推薦:一部必須被聽見的故事。──CNN
心碎的故事。──《洛杉磯時報》
難忘的。──《坎培拉報》
迷人的。──《泰晤士報》
深情動人。──《衛報》
鐵定成為經典。──澳洲《太陽先驅報》
揪心啊。──《文學評論》
章節試閱
第一章
一九五四年
這一切你終將會理解,但是永遠無法明晰。這一切發生在很久很久以前,那個世界在一個很少人聽聞過的島嶼上,後來在一個被遺忘了的冬天裡,化為泥炭。事情開始發生的時候,雪還沒徹底掩蓋足跡,無法挽回。當時烏雲遮蔽了星星與被月光照亮的天空,陰影無法遮蔽的黑暗降臨到低聲細語的土地上。
就在那一刻,時間達到頂點,瑪利亞.布羅的紫紅色鞋子走到屋外最底下的第三階臺階,上頭覆滿了粉末狀的雪。就在那一刻,瑪利亞.布羅把臉朝屋子撇開,她知道自己已經走太遠了,沒辦法再回頭了。
有人說那天晚上她是被狂風暴雪吹出鎮外;說是猛烈的暴風將她吹起,她隨風飛起,像天使一樣,飛進鎮外的森林裡,像鬼魅一樣,飛進荒野。那個地方像皮肉上剛被子彈打出來的洞一樣,熱燙燙的。但是四面八方都是荒野。
當然,事實並非大家訛傳的那樣。
甚至有人說,她化成了風,變成狂風,要詛咒他們所有人。不過這種可怕的風,可不是夢裡那種人可以乘馭的風。遇到這種風,人們要小心防備,瑪利亞.布羅正是那樣做,因為畢竟她是個理智的女人,不管別人怎麼說,她絕對不是個魯莽的女人。她小心逆風而行,好像風是一道牆似的,隨時會倒塌壓到她身上。她拉著鮮紅色外套,那件鮮紅色外套破破爛爛的。她緊緊拉著,包覆住瘦小的身軀。不過就這個故事而言,現在談那個動作是太早了,因為幾乎是等到她走出小鎮之後,風才吹得強勁。她必須走好一段路,才能走到那麼遠。
「媽媽,」瑪利亞.布羅聽到一個小女孩的聲音從屋子裡傳出來,一會兒過後,聲音又傳出來,這次比較像在啜泣——「媽媽⋯⋯」
瑪利亞.布羅站在臺階上,試著安撫留在屋子裡的孩子。她四處張望,就是不轉頭去看身後的屋子。瑪利亞.布羅低頭看著酒紅色的鞋子,看著那雙破舊的鞋子在剛飄下來的雪中呈現出美麗的模樣,發現上面那兩階木階上,足跡漸漸消失在新飄落的雪中。她思索著美的本質,思索著是不是所有美好的事物短暫出現之後就會消失。「aja,aja。」瑪利亞.布羅試著安撫孩子,在她的故鄉,母親都是這樣哄孩子入睡,「aja,aja。」
她走了,沒有回頭看屋子,任由目光往上飄,任由目光飄過亂七八糟的聚落,進入黑暗的森林。看著漆黑的夜空。看著雪落入一道道錐形的黃色燈光裡。看著雪迴旋落到地上。雪花在空中旋轉,彷彿時間似的,但是不是不斷流逝,而是不規律地流逝。瑪利亞.布羅看著雪飄落的模樣,發現空氣從來就不是靜止的,空氣裡有許多雜七雜八的東西,無盡地繞圈飛旋,可能存在著無數難以理解的優美動靜。
就在那一刻,瑪利亞.布羅認為自己應該仔細看看這一切,包括她自己,彷彿自己是在電影裡,而這裡是電影裡的場景。她就這樣想著,沒有聽到遠處傳來女兒從她剛離開的那棟小屋哭喊著她。那聲音好陌生。不過她沒有聽到。
「媽媽。」孩子哭喊著,但是她的母親沒聽見。
「aja,aja。」瑪利亞.布羅用安撫的語氣說,不過她這句話到底是說給自己聽的,或是說孩子聽的,或是說得完全沒有理由,沒有人知道,因為她已經離木屋很遠了,雪已經讓所有聲音都變得微弱。「aja,aja。」
她繼續看著眼前的景物:全部重新再看一次,彷彿一切都跟她沒有關聯似的。她看見整片黑白的景象被亮眼的燈光照亮,在被認為是街道的道路上,街燈沿街而立。街道兩邊有簡陋的垂直木板屋,屋頂和煙囪都是瓦愣鐵皮搭建。她不禁想,對於某些住在那裡的居民,這個畫面可能會令他們想起痛苦萬分的記憶,想起在烏拉山或西伯利亞的勞動營。不過她知道這裡不是史達林的蘇聯;知道這裡不是科雷馬或裸島或比克瑙;知道這裡根本就不是歐洲;知道這裡是水力發電委員會的一座施工營區,被雪覆蓋,叫作管家谷(Butlers Gorge),座落在雨林裡的荒野裡,活像個瘡口。
在這片無邊無際的土地上,小木屋全都建造得緊密靠在一起,好像那些屋子面對不可知的力量、重量與寂靜,嚇得全擠在一起瑟縮發抖,其實那些未知的事物有可能是有益的,甚至可能根本不在乎居民。只是居民經歷恐怖的過往,因此不由得心生恐懼。幾百年殘酷恐怖的歷史,記載在他們收藏著的一些蕾絲桌墊和捲翹的照片裡,還有他們養成的古怪習慣和特別的吃飯方式裡。
要不害怕,就得去想像沒有經歷過的世界。
但是沒有人辦得到。
在那些擠在一塊瑟縮發抖的小屋裡,一定住著工人,因為這個偏遠的高地鄉村位於塔斯馬尼亞這個偏遠的島嶼,距離澳洲本土很遙遠,在方圓數里內,沒有其他的人類聚落。只有蠻荒的河流,更蠻荒的山脊,雨林無所不在,占據大部分的土地,只有偶爾會出現長滿鈕扣草的曠野,或在比較高的地方有高沼地。
這就是她看見的景象。
她什麼聲音都沒聽見。
此時興建大水壩的熱潮正興起,新澳洲人紛紛來到這些荒郊野地,幹外國移民幹的興建水壩工作,因為雖然新澳洲人比較喜歡在都市裡工作,但是都市裡的工作都被澳洲人占據了。不過瑪利亞.布羅,也就是坡匠.布羅的妻子,松婭.布羅的母親,並不是要來管家谷。
她是要離開。
永遠不會再回來。
於是瑪利亞.布羅繼續沿著空蕩蕩的街道走,一名年輕婦女穿著舊外套,拎著一個小型硬紙板手提箱,鞋子留下的足跡立刻把那座陰森溼冷、受到風雪吹襲的營區劃分成兩半,在不斷飄落的雪中,她的形體彷彿鬼魅一般。
一臺小引擎噗噗接近,撕開了雪罩在村落上的那層寂靜。一道小車頭燈照出黃色的漫射光,在紛飛的雪花中,看似一灘移動著的尿色水坑。接著,一個駝背的機車騎士出現,邊車裡空空的,在一片白色空無中浮現輪廓。騎士沿著街道騎向瑪利亞.布羅,快速騎過她身旁,騎到距離約莫五十碼,放慢速度,往右轉,扭轉車身,在一家餐廳外頭停了下來。瑪利亞.布羅停下腳步,轉頭盯著看。
餐廳正門口有一道雙百葉木門,她看見木門前面有十幾個女人,聚集在一個用油桶作成的火盆,燒著熊熊烈火,寧願在如此嚴寒的地方跟大夥聚在一起,也不要獨自到溫暖一點的地方避寒。她們的穿著搭配古怪,夏季洋裝配上厚重的冬季外套,頭上戴著各種造型奇特的帽子,有幾個人戴貝雷帽,有一個人戴垂邊軟帽,有兩個人戴草帽,有一個人戴五顏六色的毛帽。在正門附近,有幾個女人站著,有幾個坐在空的啤酒木桶上,一邊聊天,一邊喝著她們的男人——丈夫、男朋友和調情對象——從只有男人可以進入的餐廳裡拿出來給她們的啤酒。每當門打開要讓男人進出時,熱烈的談笑聲和玻璃摔破的聲音就會傳到那些女人的耳裡,傳到大街上。
一名穿著皮夾克,戴著安全帽,跨下摩托車的人,故意大模大樣走進餐廳,大步走過那群女人。坐在木桶上的那些女人立刻被這個引人注目的陌生人吸引住了。她們聽見他洪亮的聲音從滿座的餐廳裡傳了出來。「我叫艾瑞克.普雷斯頓。」他扯嗓大聲說,「我是澳洲工人工會的籌辦人,我是來幫歐洲難民解決問題的。這裡誰作主?」
不過他刺耳的說話聲被嘈雜的說話聲蓋過去,餐廳裡大家一邊喝酒一邊聊著往事。女人們也轉移了注意力,改看著那個形單影隻的女人,拎著一個手提箱,在這樣險惡的夜晚,走出小鎮,不知道要去哪裡。那個孤獨的女人也盯著她們看,看穿她們,好像她們雖然看起來像在那裡,但是其實從來就沒有在那裡;好像她看見了近似過去的未來,她們全都再度被風吹散,這個可怕的時間和地方都將不復存在。她的臉(很年輕,非常年輕,現在看起來像一臉震驚)簡直就像東方人的臉孔:骨頭的構造和大大的眼睛都跟澳洲人的不一樣;還有皺紋——雖然只有一些,但卻很深——似乎不是過往歲月留下的,也不是太陽照射生成的,比較像是雕刻師刻到她臉上的,凸顯出一種奇特的異域美感。
後來有人說她錯了,不該批判她們無法理解的事。或許正是因為這樣的批判;抑或許是出自相反的情緒,有點同情可能發生在她們任何人身上的悲劇;抑或許是因為她們沒人想得明白的某些原因,當瑪利亞.布羅那樣看著她們的時候,她們用手肘推了推彼此,停止聊天。她們所有人或瑪利亞.布羅都只聽得到餐廳裡頭男人們持續發出的嘈雜聲。
瑪利亞.布羅轉過身,再度舉步走離小鎮。她聽見餐廳裡傳出非常微弱的旋律,留聲機播放著一首新的美國西部鄉村歌曲。那首歌似乎燉煮著眼淚,像是用悲傷燉煮出來的燉菜牛肉。瑪利亞.布羅朝黑暗的森林走去,餐廳裡的嘈雜聲漸漸變小。歌聲消失在輕輕落下的雨和雪中。瑪利亞.布羅的臉上沒有任何情緒。沒錯,就是那張臉——美麗,沒錯;年輕,沒錯;但是還有別的東西。是什麼呢?就是眼淚——雖然只有幾滴——滑落眼眶,讓她的臉上閃著淚光,但這似乎讓她永遠成了神祕的女子。
在瑪利亞.布羅的身後,足跡往回延伸到她來的地方,在飄落的雪中,就在她製造足跡的同時,足跡也逐漸消失,消失在白色之中。早在很久以前,那片白就好似想要遮蓋住那座陰森的小村莊裡的每個人和一切事物。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餐廳打烊了,吵鬧結束了,打牌的人也體力不支,回家睡覺,對著戴著毛帽睡覺的女人的背打呼,口氣滿是酒味。強風刮了起來,開始尖聲呼嘯,讓那片潮濕的荒地也不禁感到寒冷。
aja,aja。風似乎這樣呼嘯著,aja,aja。
可以聽到巨大的老樹劈啪作響,發出吱嘎聲。新的電線在廣闊的夜空中晃動,發出詭異的哨音。那天晚上女人們躺在凹陷的床上睡不著,聽到那些聲響,心裡更加驚惶不安。
第一章
一九五四年
這一切你終將會理解,但是永遠無法明晰。這一切發生在很久很久以前,那個世界在一個很少人聽聞過的島嶼上,後來在一個被遺忘了的冬天裡,化為泥炭。事情開始發生的時候,雪還沒徹底掩蓋足跡,無法挽回。當時烏雲遮蔽了星星與被月光照亮的天空,陰影無法遮蔽的黑暗降臨到低聲細語的土地上。
就在那一刻,時間達到頂點,瑪利亞.布羅的紫紅色鞋子走到屋外最底下的第三階臺階,上頭覆滿了粉末狀的雪。就在那一刻,瑪利亞.布羅把臉朝屋子撇開,她知道自己已經走太遠了,沒辦法再回頭了。
有人說那天晚上她是被狂風暴...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5收藏
5收藏

 10二手徵求有驚喜
10二手徵求有驚喜



 5收藏
5收藏

 10二手徵求有驚喜
10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