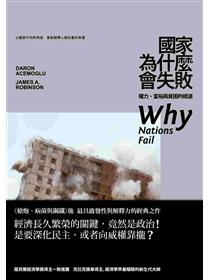《社會契約論》又譯為《民約論》,是探討政治權利原理的政治哲學著作,當中的主權在民的思想,為人民民主主權的建立奠定理論基礎,是現代民主制度的基石,影響了逐步廢除歐洲君主絕對權力的運動,以及18世紀末北美殖民地擺脫英帝國統治、建立民主制度的鬥爭。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宣言》及兩國的憲法即體現了《社會契約論》的民主思想。
作者簡介:
讓-雅克‧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06.28.-1778.07.02)
出身於日內瓦,是哲學家、政治理論家和作曲家、也是18世紀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先驅,啟蒙運動代表人物之一。代表性著作除本書外尚有《愛彌兒》及自傳《懺悔錄》等。盧梭也擅長作曲和樂理,有歌劇及其他形式的作品。
著有《科學和藝術的進步對改良風俗是否有益》及《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對哲學發展極其重要;其中《社會契約論》所論述的人民主權及民主政治哲學的思想影響近代的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以至現代的政治、哲學和教育思想。他認為不論是傳統和現代的公民社會,都一樣始於私人財產。
盧梭撰有小說作品《愛彌兒》(Émile)是關於全人公民教育的哲學論文,自傳體作品《懺悔錄》更是現代自傳的開端。
譯者簡介:
李平漚(1924.3-2016.7)
四川仁壽縣人。翻譯家,對法國18世紀偉大的啟蒙思想家、哲學家盧梭及其論著深感興趣,為盧梭問題研究專家。畢業於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曾任國務院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法文翻譯;1958年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力學研究所任法文和英文翻譯、北京對外貿易學院(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前身)法語教員、教授。
章節試閱
第七章 主權體
從這方式我們看出社會結合的行為是包含公共和個人間的相互關係;每個契約的分子—可以說和他自己訂約—都具備雙重負責的身分;對個體而言為主權體的一分子;對主權體而言,為國家的一分子。但在這裡我們不能應用民法上的原則,任何人無須遵守自己和自己所訂約的拘束,因為受自己的拘束和受自己為其一部分全體的拘束,二者有很大的區別。
我們更要注意:公共的決定,雖因分子的雙重身分之故,足以使一切國民受主權體約束,但不能依反面的理由,使主權體受其自身約束。故主權體若是以一種法律來拘束其自身,便是違反 政治社會的本質。因為主權體只具一種身分,它的情形正與個人和他自己訂約的情形相同。由此 可見沒有亦不能有什麼根本的法律能約束人民的集體,雖社約亦不能約束它。但這並不是說,這 種政治社會不能和別的團體訂立契約,只要不違犯社約就可以。因為就其對外的關係來說,它是 個單純的人,是個個體。
但這種由神聖社約產生的政治社會或主權體,不能—即使對外也不能—約束它自己去做有損於原約的行為,例如:讓出它自己的任何部分或屈服於別的主體權之類。破壞它所賴以存在的條款,便是毀滅自己;本身毀滅視為無物,便不能產生物。
眾人結合成為團體之後,損及其分子必然會侵及團體,而損及團體,更不能不使分子憤恨。利益和義務都同樣使訂約的雙方必須互助。人們必會就這兩重關係,結合所有的利益。
主權體因為是純由各分子共同組成的,故沒有亦不能有什麼違反他們利害的利害;所以,主權體對於其人民不須有什麼保障,因為團體絕不願損害其一切分子的;我們以後將看見,它亦不會損害任何一個分子的。主權體因為是主權體,便始終是它應該是的模樣。
至於國民對主權體的關係卻不是如此。雖是有關公共的利益,但除非主權體能設法保證國民盡忠,否則不能保證他們能履行義務。
事實上,每個個人作為人來說,各有其特有的意志,和公共意志(他以公民的資格具有的公 共意志)相反或相異;他私人的利害所指示他的,也許與公共的利害所指示的完全不同。他自己 絕對的,和自然獨立的存在,或許會使他把他該替公家做的事看作原無義務的善舉,認為他不做 這事而使他人所蒙的損失,不及他做這事而使他自己所受的煩累。又因為構成國家的精神人格不 是真的人,他便以為那是幻想的東西,只想享受公民的權利,而不盡國民的義務。這種不公平狀 態徜若繼續下去,將毀去政治的組織。
所以,社約為了免為空泛的儀式,隱含著這麼一項條款:任何人如不遵守公共的意志,則 得由全體迫其遵守。有了這條款,其餘條款就都能生效。這條款只是要使人自由,因為它把各個 國民連結於國家,保證他不必依靠任何個人;它使政治機構運用,使政治行為公正合法。沒有了 它,政治行為則將淪為荒謬專制,易陷於不堪的腐敗之中。
第八章 國家
從自然狀態過渡至國家︵即有政治組織的社會︶狀態,在人的方面產生極重要的變化:行 為是以正義代替本能,而取得原來缺乏的道德性。只有當義務觀念代替衝動,權利代替情慾的時 候,才會使一向只顧自己的人們,覺得必須依別的原則去行為,必須在依從本能的傾向以前,加 以理智的考慮。在這種情形之下,他雖然失去一些他於自然狀態下所得的利益,但他所得的報償 是很大的,他的才能是引起並發展了,他的觀念是擴大了,他的情感是高尚了,他整個的靈魂是 提高了:如果不是這新情形的腐敗使他墮落,墮落到比他從前原有的狀況還不如,他必須要繼續 不斷地慶幸這快樂的日子,使他永遠脫離自然狀態,並使他成為有理智的東西,成為一個人,而不再是愚昧無思的動物。
讓我們用易於比較的詞來總結此帳。人們在社約上所喪失的是自然的自由,和隨心意所欲地取其所能的無限權利。他所獲得的是社會的自由,及其保有物的所有權。我們如欲避免較量上的錯誤,必須把自然的自由(即受限於個人的力的自由),和社會的自由(即受限於公共意志的自由),加以區別;再把占有(即是力之效果或最先占領者的權利),和所有權(只能依正當權源 而享有的),加以區別。
此外,社會結合後的獲得,我們還可舉出道德的自由,這使人成為真正自己的主人;因為循 情慾的衝動是奴隸,而依從自己所定的法則是自由。但我對於這題目已說得很多,「自由」一詞 的哲學意義現在不再討論了。
第九章 不動產
在社會初成立的時候,每個分子都把自己連同他所有的一切—包括他所有的東西—交與社會。這種行為改變了保有者,而未嘗改變保有的性質,未嘗變為主權體的財產。但國家的權力比個人的權力,是大得無可比擬,故公共的保有是較穩固不變的。但公共的保有也並沒有變為較合法,至少從外人的觀點看來是如此。因此國家對於其國民而言,依照社約︵社約在國家裡是一切權利的基礎︶是其國民的一切財產的保有者;但對於別國而言,國家是依據先占權(這先占權是國家從其國民取過來的)而成為保有者。
先占權雖較強者權實在些,但只在財產權成立之後才變為真正的權。每個人本來都有權利取得對於他所需要的物,但他既為其物之物主,就不能為其他一切物之物主。他既然分得了一物,便該保持它,而對於未分的公共財產,便不能再有什麼權利了。所以先占權在自然狀態下極不穩固;而在國家裡則得到各人的尊重,其故在此。我們在這種權裡,與其說是尊重他人的物,不如說尊重不屬於自己的物。
普通來說要確定一塊地的先占權,必須具備下面的條件:第一,該地須尚未有人居住;第 二,個人只能占據維持其生存上所必需的面積;第三,除形式的占有外必須以勞力經營開墾。這 勞力才是所有的標記,即使沒有法律的名義,亦應受他人尊重的。
如果先占權具備了﹁必需﹂與﹁勞力﹂兩元素,我們是否可以盡量擴張該權呢?是否對於該權可以不加限制呢?僅僅落下足跡到了一塊公共的土地,是否可以宣告自己為該地的所有主呢? 是否一時有逐去別人的力量,便可永遠剝奪別人回至該地的權利呢?如果不是可處罰的霸占,一個人或一個民族怎麼能占據一片極大的土地而不許別人同享(自然給他們共享的居住和維持生存的權利都被剝奪了)呢?昔巴爾波亞(Nunez Balbao) 【1】 站在海岸上以卡斯提爾(Castile) 【2】 國王的名義宣稱占領太平洋和南美洲全部,試問這是否可以逐去該處的居民,並排斥別國的王占有該地呢?如果可以的話,則種種儀式都可不必舉行,該國國王—天主教的國王—不妨在他的私室裡先宣告把全世界占有,然後把別國的王早已占有的土地除去,不就好了嗎?
國家成立後,原有互相連接的個人土地變成公共土地,國家主權從對人民伸至對人民所有的土地,於是變為對人而又對物的主權。因此土地所有者不復如從前的自主,其所有的力乃因此保證其忠實。這種好處似乎古代的專制君主沒有察覺到,他們稱自己為波斯人的王,斯基泰人 (Scythians) 【3】 的王,或馬其頓人的王,他們似乎把自己看作人們的統治者,而不看作國土的主 人。現代的專制君主較聰明地自稱為法國的王、西班牙的王,或英格蘭的王;他們以為保有土 地,便是保有居民。
這種轉變的特質是:國家接受個人的產業,不是剝奪個人的產業,只是保證他們合法地保 有,使占據變為真正的權,用益變為所有權。又所有者被認為是公共產業的保管人,他們的權受國家一切分子所尊重,亦受國家的權力維持,使其不受外國侵占,他們彷彿由於一種有利於公共,同時更有利於他們自己的讓渡,獲得他們所已放棄的一切。這種似非而是之論,我們以後可 以知道,若把主權體對於地產之權,和業主對於地產之權分別清楚,便不難解釋明白。
人們也許在保有任何地產之前,即互相連結起來,後來占領了一塊足以供大家利用的土地,便共同享用,或把它分派—或是平均分派,或是依照主權體的規定而分派。無論地產是怎 樣獲得,總之,個人對於其地產的權是居於社會對於整個地產的權之下的,否則社會的連結便不 能穩固,而主權的運用亦沒有真正的力量了。
我指出現今整個社會制度應根據的一件事實,以結束本章和本編。即是:根本的社約並不毀 去自然的平等,且以道德的、法律的平等,代替自然所加於人們的體智上的不平等;使人們在體 力智力方面的不平等,而依契約法權,大家一律平等 【4】 。
註釋
【1】 Nunez Balbao︵1457-1517︶,西班牙的探險家,為太平洋之發現者。
【2】 Castile西班牙區境內的一個王國。
【3】 Scythians昔亞細亞北部及中部之Scythia的人。
【4】 在不良的政府下,這種平等只是表面的、虛幻的;它只是維持貧者於其貧窮狀態,富者於其所掠奪的富有
狀態。實際上,法律才是利於富者,不利於貧者的。故社會的狀態,要當大家都有些所得,而沒有人過於
富有的時候,才有利於人類。—原註
第七章 主權體
從這方式我們看出社會結合的行為是包含公共和個人間的相互關係;每個契約的分子—可以說和他自己訂約—都具備雙重負責的身分;對個體而言為主權體的一分子;對主權體而言,為國家的一分子。但在這裡我們不能應用民法上的原則,任何人無須遵守自己和自己所訂約的拘束,因為受自己的拘束和受自己為其一部分全體的拘束,二者有很大的區別。
我們更要注意:公共的決定,雖因分子的雙重身分之故,足以使一切國民受主權體約束,但不能依反面的理由,使主權體受其自身約束。故主權體若是以一種法律來拘束其自身,便是違反 政治社...
推薦序
換上另一套「枷鎖」來跳現代文明的自由舞曲?
——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導讀/ 國立政治大學 政治學系副教授 葉浩
既然沒人有支配其同類的天然權力,而且暴力並不能產生權利,那麼契約便是人與人之間正當權力的基礎了。
——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
一、前言:關於本書的三個閱讀脈絡
1749年夏季,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狄德羅(Dennis Diderot, 1713-84)因為公開懷疑上帝的存在而被囚禁於凡森城堡(Château de Vincennes,巴黎古監獄)之中,當時還是他好友的本書作者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某天在步行前往探視的途中,看到了狄戎學院(Academy of Dijon)的有獎徵文比賽廣告,題目是:「科學與藝術的重建是否了道德的淨化?」如果他那本檢討別人比自己還多的《懺悔錄》(Les Confessions, 1770)所言屬實,這是他人生最重要的轉捩點 。在此之前,盧梭做過不少荒唐事,包括棄養了三個親生孩子(之後還有兩個)。但他心中不曾懷疑過自己的善良以及回歸純真的可能性。剎那之間,他先是千頭萬緒,然後靈光乍現,意識到了人是天生善良的,而變壞全是社會制度使然。1762年,盧梭的《社會契約論》(Du Contrat Social, 1762;以下簡稱《社約論》)正式出版,隨後他寫了一封信給巴黎大主教波蒙(Christophe de Beaumont, 1703-81),不僅信誓旦旦地說,本書提出的理論可用以解決日內瓦的憲政危機,也再次強調人性本善乃所有道德的根基,並說那是貫穿他所有著作的核心信念。
日內瓦是盧梭的故鄉,而本書不但讓盧梭得以和現代西方政治哲學奠定者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以及開創了西方自由主義(liberalism)政治思想的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平起平坐,《社約論》也從此和他們分別撰寫的《利維坦》(Leviathan, 1651)和《政府論》(Two Treaties of Government, 1689)並列為「契約論」(contractarianism)政治思想傳統的三大經典著作之一,對日後的「憲政」與「民主」之理論發展與政治實踐,影響甚巨。
契約論作為一種論證方式,結構上包括了底下四個元素組成之推論:(一)關於人類進入社會之前的「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之描繪,(二)解釋人們欲離開那狀態的根本理由,(三)列舉人們藉以離開的「社會契約」之內容項目,以及(四)據此所提出的一套政治制度。
以上四個元素整體構成了一個獨特的論證方式,並以一個關於人們何以離開自然狀態的邏輯貫穿其中,一方面說明政治社會的基礎與根本樣貌,一方面藉此確立人民與政府的應有關係,以及國家體制將如何維繫。由於契約論預設了政治權威之基礎在於被統治者的自主意願,且政府的統治正當性取決於能否提供人民特定的保障,此一論證方式本身足以威脅到前現代的「君權神授」之說或其他基礎不在契約關係之上的國家。因此,在盧梭撰寫本書之前,契約論已在理論與實踐上挑戰並某程度上形塑了現代政治的發展。
當然,偉大政治思想家的過人之處在於提出一個既能回應自身時代所需,又具有普世意義的理論。霍布斯書寫《利維坦》時英國正處內戰,思索政治權威如何建立、維持和避免戰亂是時代的必要,而洛克的《政府論》某程度上已針對正在生根的民主制度提出反思,且如火如荼進行中的北美洲殖民也需要一套能賦予擴張行動正當性的論述。及至盧梭開始構思本書的十八世紀中葉,契約論已是歐洲許多思想家所熟知並參與爭辯的政治思想傳統,因此有不同於英國契約論的關懷脈絡。
商業社會(civil society)和新興中產階級的崛起,是本書寫作的主要歷史脈絡特徵。方興未艾的啟蒙運動不僅提倡線性的進步史觀,相信科學與理性會獲得最終的歷史勝利,其推動者也見證了伴隨中產階級興起而來的消費文化和通俗娛樂。雖然這或許更應該歸功於盧梭的蘇格蘭友人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 1711-76)和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90)兩人分別倡議的自由貿易和市場自由,以及提倡炫耀性消費的盧梭勁敵,亦即法國啟蒙運動大將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但英國契約論高舉的個人權利以及獨特的國家概念,也是動力之一。開始爭取個人權益的政治思想正在劇烈改變人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同時也撼動著現代社會的凝聚基礎。
另一方面,正如他在序言中提及《社約論》原是另一個大型寫作計畫的一部分。其構思始於1743年當作者被派駐在維也納,擔任法國大使秘書的期間,當時他企圖完成的是一個完整的政治制度設計。該計畫並不順利,但盧梭似乎並未真的放棄,而本書內容基本上是作者取材於此間的手稿所編寫而成。
未收錄於當中的其他手稿,其實有部分也進了1755年出版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es),以及同年撰寫關於政治經濟學的文章。前者基本上是盧梭對自然狀態最詳盡的描述,而關於人類曾經如何自由但後來卻活在層層枷鎖當中,以及進入社會之後的種種契約又如何讓人淪為奴隸的部分,亦是理解《社約論》所不可或缺的文本。至於三年後以《論政治經濟》(Discour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專書出版的後者,不但盧梭政治思想體系儼然成形,更可見本書當中至關重要的「公共意志」概念。此外,關於人性本善最詳盡的說法,則是在那本與《社約論》出版時間相距一個多月的《愛彌爾》(Émile, ou De l’éducation, 1762)當中,其主旨為教育,而社約論的核心就是該書的政治教育綱要。
本文以盧梭人生轉捩點的頓悟為線索,在兼顧上述契約論思想傳統的發展和中產階級崛起這兩個歷史脈絡同時,以及他本人對「重拾純真」這命題的看重,提供一個如何閱讀《社約論》的方向。
二、盧梭論天然自由與新自然狀態
無疑,盧梭的思想既反映生命經歷,也回應時代變遷。頓悟只是確立問題的開始,而本書才是他思索十年所提的因應之道,其要旨正如底下這段話:
「問題是在找出一種結社(association)的方式,能以共同的力量來捍衛並保護每一個成員及其財產,並讓每一個人在完全與整體合一的同時,不僅只服從於自己,且跟過去一樣地自由。」這是社會契約所給予解決的根本問題。
讓我們首先聚焦於此一段話為核心,特別是「跟過去一樣地自由」這想法之上,來掌握盧梭的問題意識。關鍵關鍵在於,既然社會契約作為一種解決方案,是為了建立一個和過去同樣自由的社會,那麼:(一)究竟是什麼樣的一種自由?(二)為何唯有社會契約才能恢復或重建那一種自由?
盧梭在本書提出的「天然自由」(natural liberty),是問題(一)的簡答,但申論則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關於人類演化史的論述當中,據其臆測:
漫遊在森林的原始人,他無須工作、無需談話、居無定所、不與人爭、不與人交、不需同類,也無意加害他們,甚至可能從來也不曾認識哪一個個別的人。他僅受制於很少的熱情,因此是自足的,並僅具備在自然狀態中所需的感覺與啟發,感受真正的需求…… 藝術隨著發明者而消失,既沒有教育,也沒有進步可言。
倘若此一描繪為真,尚未進入社會以前的「自然人」雖然過著未開化的生活,也沒有人際關係的牽絆,看似野蠻卻反而有不依賴他人的獨立、自足堪稱高貴的自由。
不可否認,他們也無處不在危險當中,因此必須靠本能來生存,也具備求生本能。盧梭稱那是所有動物共有的「自保之愛」(l’amour de soi),但人之所以為人乃因對同類的受苦亦能感同身受,或至少會產生一種強烈的反感。天生憐憫心不僅能讓人互認彼此異於禽獸,從而以「平等」方式相待,其運作也足以克制原始的攻擊性並避免戰爭,發揮一種道德與法律之於社會的規範功能。如此一來,自然狀態並非霍布斯筆下那個人人彼此交戰,過著「孤獨、貧困、齷齪、殘暴、短命」的慘況,而是一個人人平等、自由,幾近烏托邦的自然狀態。
不僅如此,盧梭強調此時的自保之愛絕不同於唯有在複雜人際關係當中才會浮現的「自重之愛」(l’amour proper)。那是一種與他人比較的心理,為的是想從中他人的角度來確認自我價值,或從他人的羨慕眼光來提升自尊。看在盧梭眼裡,那是一種墮落。原本的高貴野蠻人將從此喪失獨立性並開始依賴他人,然後跌入一種永劫不復的爭奪、嫉妒、怨恨之循環當中。
這說法的另一面是:霍布斯的理論根本倒果為因。他藉以說明戰爭必然性的自利、虛榮、聲名等動機乃社會產物,絕不可能出現於社會化以前的原始狀態。於是,盧梭意有所指地說,過往契約論者在「論及需求、貪婪、壓迫、慾望與傲慢的同時,已經把存在於社會當中的概念轉移到自然狀態中,他們談論野蠻人,想的卻是文明人。」
除此之外,盧梭也批評了霍布斯主張的出走邏輯。該邏輯基本上假定:政治權威的闕如等同沒有實際約束人們彼此行為的規範力量,所以人們會「自由」地為了生存而不擇手段,包括奪人性命,而且因為所有人都處於同樣情境,且能威脅他人的生命,全都「平等」。當然,他們並非喪失理性,只不過理性會告誡自己,在缺乏保障底下去服從自然法,等同開自己生命的玩笑。於是,不堪其苦的人們將會決定集體放下武裝來締約成立社會,然後將原先的權利讓渡給一人當做主權者,從此以守法來換取安全。
對此,盧梭提出了兩個反駁。首先,社會在「歷史上」的真正起源其實是一連串漫長的演變過程,而非誕生於特定時間點的契約關係,更不是霍布斯所設想一群人當中每個人和每個人彼此簽約而成。亦或,如果真有那麼一刻,盧梭認為那應該是當一個人圈起了一塊土地並宣稱『這是我的!』,而竟然也有人單純到信以為真的時候。當然,這樣的「公民社會始祖」會不只一個,且這種同意也不是契約關係,而是正在慢慢成立制度的一種互動。更重要的是,盧梭感也說,倘若此時有人大聲疾呼:
『注意聽這個欺騙人所說的,若是你們忘記了樹上果子是大家的,大地不屬於任何特定的人,你們將全盤皆輸』,那麼所有發生在人類的罪行、戰爭與謀殺,以及悲慘和恐怖都能避免 。
不幸的是,沒有人這麼做。其他人不但信以為真,甚至還紛紛效仿。於是世界有了私有財產概念,之後催生了保障財產的法律,不僅承認了私有財產權,更以政治權威來保障了,從而演變成一個有法律規範的社會,其功能是:
給了弱者新的絆繩,又給了富人新的力量,卻不回頭地破壞了天然自由,永遠設定了財產與不平等的法律,一個精緻的霸佔變成了一種無可挽回的權利。從這時開始,為了一些野心人的利益,將所有的人類至於勞動、服侍與悲慘的情境之中。
盧梭強調,原始人根本沒有「原則上」必須走出自然狀態的理由。他們的自保並不妨礙他人,方式也平和。反之,自重之愛卻一步步替人類套上了心靈與制度的枷鎖,直到社會最終成了所有人和所有人戰爭的「新自然狀態」 ,人才真的非離開不可!
三、從英國契約論邁向一個「規範性」契約概念
以上對霍布斯的批評翻轉了契約論的基本邏輯。並非因自然狀態讓人苦不堪言,才選擇出走,而是原始狀態某些人的自愛墮落成自重之愛,才讓自然的烏托邦變成人為的失樂園,並美其名曰「現代文明社會」,其法律功能不外是為了保障人們爭先爭先恐後取得的財物以及以交易賴以進行的契約。後果則是,(一)原先不加入爭奪的高貴自由人,在社會中卻成了沒有財產的窮人;(二)自由人在地位翻轉之後,可能開始學會你爭我奪,所有人的自愛終將被自重之愛所取代。
眼尖的讀者當可發現,盧梭的眼光似乎從契約論方法預設和推論邏輯轉向了契約與財產權對於現代社會的實際影響。就某程度而言,這等同矛頭指向了洛克。洛克當然也仰賴了類似的出走邏輯,亦即以讓渡權利換取更好保障的基本思維。但他援引了基督教神學並將自然狀態理解為一個上帝允許人類享受其創造的世界,不僅可以藉勞動來累積財產,也懂得運用自然法於待人接物和交易之上。不過,人們也因為詮釋與運用上的判斷差異而終日紛爭不斷,極其不便,所以也會想要一個政府。其職責主要在於擔任自然法最終詮釋者並據此制定法律,保障人們在自然狀態底下即享有的自由、平等和財產。為了善盡此責,政治權威絕不得違背個人基本權利,而為了防範濫權也必須有所限制,甚至分散權力使其彼此制衡。
洛克的理論是「法治」(the rule of law)概念以及「憲政民主」理論之原型,鑲嵌於此一論述當中的「代議政府」更是讓後世自由主義者奉為理想的政體,亦即現代社會當中唯一能捍衛自由、人權乃至財產權等普世價值的可行方案。然而,盧梭卻在本書第三卷第十五章說:
英國人自以為是自由,實在大錯特錯。他們只在選舉議會議員時才是自由的。當議員一經選出,他們變成了奴隸,不算什麼了。但他們能利用短時期的自由,亦足使其喪失自由有相當代價了。
此處重點並非英國人的自以為是或虛偽,也不是理論與實踐的落差,而是如果「民主」兩字指的是人民當家做主的話,那代議政治根本配不上這名稱,因為,以選舉制度為基礎的民主,不過是讓強者(富人)繼續奴役弱者(富人)的另一種方式,畢竟,唯有富人才會有錢有閒參與政治,為生計奔波勞碌的窮人不可能競選,行使起來只會強化了既有的不平等,甚至將不正當的強權出頭政治「實然」轉化為一種「應然」。另一方面,其所仰賴的「代表」(representation)概念本身亦有問題;一來掩蓋了上述事實,讓人以為選出的代表將會為民喉舌,製造錯誤的期待,甚至以為自己在投票時即行使了主權,所以是國家的主人,但其實不過是再次將個人主權讓渡了出去。
無論如何,如果選舉這算是一種契約,那必然是「不平等」契約。據此觀點,代議民主理論充其量乃高明的政治修辭,嚴格說是騙術,其倡議者不過是自由幻象的製造者。言下之意,洛克似乎是霍布斯式新自然狀態的幫兇,一如許多人視其財產權論述終究是為北美殖民甚至帝國主義服務。是故,盧梭於是大聲疾呼:「主權不許代表,其理由正如主權不可讓渡一樣。」
不過,比起契約雙方的不平等作為一種事實必須予以批判,盧梭更在意的是任何處於不對等的兩方皆不可能進入一種真正的「契約」關係。進一步解釋,固然盧梭認為:
既然沒人有支配其同類的自然權力,而且暴力不產生任何權,那麼契約便是人與人之間合法權利之基礎。
但,這並不意味任何兩方同意的約定都是「契約」,例如自願為奴——因為當我們這麼做的時候其實已失去了簽約的資格,畢竟:
放棄自由,便是放棄做人,便是放棄做人的義務和權利。對於放棄一切的人是不能有補償的。這種放棄是違反人性。
嚴格說,人在意圖出賣自己的時候已人間失格,當然不可能是締約的道德主體。於是盧梭強調,出賣自己是一件極其荒謬甚至瘋狂的事,但「瘋狂是不能生權利的」!
此一說法當然也呼應了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中所說的這一段話,因此我們知道此處所說的「自由」指的是自然人在自然狀態時的獨立與自足:
放棄生命,等於是否定個人存在;放棄自由,等於是毀滅內部心靈。在世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作為這兩者相互之間的補償,所以若將它們與任何代價作交換,等於同時否定了自然與理性。
至此,我們知道盧梭真正仰賴的是以天然自由作為基礎來提出對「契約」的規範性(normative)界定。其要旨為:雙方不平等或單純圖利(或犧牲)其中一方的約定,既稱不上真正的契約,更不能構成權威,且不論當事人是否如此感受。正如戰勝者與戰敗者可以締結臣屬之約,「但這種約定並非結束了戰爭狀態,而是隱含著戰爭狀態的延續」。即使簽訂和平協議的臣服者可能「不停地炫耀他們在鐵牢中所享受的和平與安逸」,甚至會「稱呼一個悲慘和奴役國家,為一個和平國家」 ,但那終究是一種奴隸的生存狀態。
「以另一種方式延續的奴役」是獨具慧眼的盧梭所在意。雖具備了「憲政主義」色彩的霍布斯理論是一例,畢竟那意味著「絕對王權」。但洛克提出的「二次契約」也是,因人民與政府締約不過是臣屬關係的再確認。
四、換一套枷鎖來跳文明的舞曲
至此,我們方能面對盧梭開啟本書的這段話,並思考為何社會契約是恢復或重建原本自由的方法,且不會是另一種延續奴役的方式:
人生而自由,但卻無處不在枷鎖當中。好些人自以為是別人的主人,其實比起在人來,還是更大的奴隸。怎麼會變成這樣呢?我不知道。是什麼能令其正當 (legitimate)呢?這問題,我想我能回答。
讀者當然明白他並非不知道為何變成這樣,第二句也無需解釋。在此他想聚焦於第二個問題之上,亦即什麼才能讓「枷鎖」成為正當。換言之,目的並非在於解除所有的枷鎖,畢竟,在現代社會當中那幾乎是不可能,重點在於如何讓人們只受到「正當」的束縛。更精確地說,如何讓套在我們身上的束縛是那唯一能「重獲自由」的束縛?
社會契約正是那唯一具正當性的枷鎖或說規範,畢竟法律是其實踐方式,而法律之目的不外是自由與平等,正如盧梭說:
如果我們追問什麼是全體最大的善,應成為一切立法系統的目的——我們發現可以歸結為兩個主要目標:自由與平等。
有一種束縛是為了自由。乍聽之下頗為弔詭,不過,這卻是盧梭的真正想法。欲對此有更好的掌握,讓我們繼續洛克的相關討論來細究上面第二句話。從前文可知,盧梭對洛克私有財產的捍衛頗不以為然,甚至給人一種印象:雖然他來不及阻止歷史上第一個圍起籬笆的騙子,此時決定起身對抗合理化那騙行的(洛克)契約論。既然代議政府不過是延續奴役的另一種方式,自由主義不過是高明的政治修辭,甚至是騙術,那洛克似乎是霍布斯式新自然狀態的幫兇,一如其財產權論述終究是為英國殖民者甚至帝國主義服務。亦或如二手文獻所常見,盧梭是有感於人類文明之路一開始就走錯,社會化無異於墮落過程,中途更讓英國契約論以財產權保障強硬地限制住了未來走向,所以才必須挺身而出力挽狂瀾,將人類將一切的枷鎖中解放出來,恢復天然自由。
不,倘若如此,那真正的解決方案必須重新打造一切人為制度,其規模之大將超過革命,近乎重建新天新地乃至新人類。
誠然,盧梭認定制度使人腐化,不是天性或其他自然因素——更嚴格說,社會制度始於人性墮落,也是進一步鞏固人類不平等的力量。無論是人類演化史或個人從小到成年的社會化經歷,都是墮落過程。先有自重之愛的心靈枷鎖,再有法律與財產乃至市場作為制度性枷鎖。所有在現代社會當中的一切契約,包括君主立憲、勞動契約、選舉制度甚至各種家父長制的政治想像,全是建立在某種不同位階的不平等關係之延續。甚至連啟蒙人士高舉為人類希望的科學與理性,也不例外。事實上,他回應前文提及的徵文比賽當中所振臂疾書的論點,也徹底反駁了科學與藝術對道德有淨化作用之說。徵文題目本身其實以法國正在重建人類偉大文明為背景,亦即一度讓中世紀「黑暗時代」所遮蔽的科學與藝術,因此必須重獲光照或「啟蒙」(enlightened),然而盧梭卻對這重建大業不以為然。一如他在《愛彌爾》也感嘆地說:「萬物在造物主手上時一切都美好,一但離開來到了人類的手中,就全開始敗壞!」
不過,走錯路畢竟是歷史(經驗上)的實然而非(未來也必須如此的)必然。力挽狂瀾也並不一定是將所有制度打掉重練,退回原始狀態重新開始。盧梭真正批判的對象不是歷史,而是「現代性」(modernity)及其讓我們所能想像的未來進步方式。其敏銳在於他不僅意識到了腐化的無所不在,也在於理解到進入社會之後的不可逆,以及人類希望之所在:那曾被制度誤導但尚未徹底泯滅的良善天性!
無論如何,正如盧梭他在闡釋本書問題意識時提及了對財產的保護,社會契約作為解決方案並不意圖取消私有財產,也不反對財產權,畢竟,那的確是現代公民社會之基石。關鍵在於如何限制其不平等使用。另一方面,盧梭終究也肯定那些制度是「從人類自然本性,經由理性的發展,逐步衍生而成」 ,不僅是一種心靈「進步」,更是人類所獨有「追求自我完美的能力」之展現 。如果放棄生命或自由,等同否定了自然與理性,那麼,作為自然本性與理性相互運作的結果,也不該全盤否定,更何況,追求自我完美的能力意味著:人類的本性必然會與自然本性決裂——亦即唯有在脫離野蠻人狀態時才最像一個不同於禽獸的人。
是故,道德與社會的不平等乃人為之事實,並不意味著文明本身必須被撤銷。一來,人類的文明進程來到了現代,不可能退回到前社會的狀態。二來,進入社會化之後的人類文明也並非一無可取,例如,「自愛」本身不是一件壞事,政治也可以是實現自由的前提現實條件。
既然當時公認為最能捍衛自由與平等的代議民主,實則另一種延續奴役的方式,所以「跟過去一樣地自由」絕不能仰賴現有法律制度,必須另起爐灶。另一方面,文明進程也不可逆行,因此那種歷史上僅出現於人類進入社會以前的自由,必須以另一種方式在現代社會當中來重建。盧梭在診斷了現代性之後於是替自己設定了一個難題:如何在承認基本現代世界設定(例如自我意識、財產權、集會結社與政治制度的存在的不可逆)之下,恢復原初那種獨立、自足?他思索了二十年後提出的解方是,換上另一副「枷鎖」來繼續跳這一支文明舞曲!
五、新國、新民、新自由以及新民主
這一副枷鎖必須是現代人能根據自主意願替自己套上去的法律規範,且是為了重獲自由的緣故,其方式就是所有人共同簽訂一份契約,創造一個新的國度以及運作方式。誠然,鑑於天然自由不可能真的「再現」,契約論者提出的個人自由與法律保障也不過是奴役的另一種方式,但財產權與法律制度本身又不可廢除,那唯一能做的事似乎必須找到以另一種制度來重建真正的自由,且重建的過程本身不得以讓渡權利或他人代為行使主權的方式進行,否則仍是一種奴役,而奴役之路絕對通往不了自由,因此出路必然是涉及了所有人親自參與的行動。在盧梭替自己所設定如此嚴苛的理論與實踐之條件底下,那唯一解方似乎是:
我們每一個人把自身的一切權力交給公共,受「公共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 /general will)之最高的指揮,我們對於每個分子都作為全體之不可分的部分看待。
雖不若上帝那樣創造新天新地新人,但社會契約本身也的確創造了一個集體,亦即盧梭稱為「共和國」(Republic)的「政治體」(body politic):靜處時是一個「國家」(state),主動作為時則是一個「主權」(sovereign),若與其他國家較量時則是一個「強權」(power);另一方面,實際參與簽約的人則從此在集體上統稱為「人民」(people),個別時是「公民」(citizen),而在專指是否受到國家法律管轄時則稱為「國民」(subject)。
基本上,盧梭的社會契約是一個徹底轉化政治社會的龐大工程,人們關於「自由」、「財產」和「民主」的理解,在此也重新界定。首先,關於財產,相較於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中對私有財產的根本性批評,認定那不但起源於自私,當國家以法律來保障的時候更是造成了難以撼動的不平等社會結構,盧梭在本書卻大抵同意了洛克關於自然狀態底下「先佔權」的說法。那是一種出自於「必要」與「勞動」才能保有的權利,其理據則源自人所能擁有的自己身體。缺乏政治權威的自然狀態底下這種財產沒有保障,因此並不穩固。盧梭的社會契約提供了保障,但方法是讓個人的所有產業由全國家接收保有。之所必須如此,一來因為簽約所產生的新主體,也就是作為主權者的人民全體,才是真正的財產的真正擁有人。二來,也唯有共同保有一個人的產業才能有效確保不被他人所侵佔。更重要的是,國家的建立所包括的領土畢竟包括了許多尚未被個人所佔有的「公共」土地,個人產業由國家接收並保有並不吃虧,畢竟,個人也因此而能享有更多。是故,這種接收絕非是一種剝奪,而是強化其所有和使用的權益,並恢復了人類最原初的平等。
這當然也是盧梭接受現代性特色的證據之一,亦即認同的以領土為基礎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體制。另一方面,不論是個體或集體,社會契約的簽訂也讓人重拾人類曾一度有過的自由,不過,那種自由在公民社會底下必須是以結合政治制度才能體現,因此盧梭稱之為「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猶記盧梭對英國代議制度的主要批評是,人民唯有在投票時才是自由,一但議員選出旋即回歸奴隸狀態,那麼,唯一能讓人民永遠自由的似乎是得「天天」行使主權。解套方式是所有人民共同參與立法,而政府則不過是執行人民意志的機構。參與立法工作,才不讓自己受制於他人制定的法,正如盧梭底下所說:
法律是把意志的普遍性和事物的普遍性連結起來,故個人不論為誰憑其權威所下的命令都不是法律。即使主權者對某一個個別事物所下的命令也不是法律。
也唯有如此,人民才是真正的主權者,而政府是公僕。因此,盧梭並不徹底否定讓公僕代勞的所有機制,例如草擬法條或提案預備工作,但唯有人民全體擁有最後的決定權。
進一步解釋,前文提及的「公共意志」亦可譯成「普遍意志」。之所以如此乃因「普遍性/générale」指的是法律之權威普及至國家的每一個成員,包括政府官員在內,而盧梭此舉也賦予了「法治」(the rule of law)概念一個特定且明確的內涵,亦即讓法治與(人民)主權成為「民主」的一體兩面。換言之,法治再也不能以人民被動地受憲法保障來落實,而是一種公民的主動性立法行動,畢竟人民才是國家真正的主權者,不替自己立法等同活在他人的意志底下。如果民主的核心要義果真為「人民當家做主」,那參與式政治似乎是唯一的解套。
一反霍布斯的邏輯讓人民徹底把主權讓渡出去,也不同於洛克倡議的代議政治底下立法權座落於國會議員手中,盧梭筆下的人民才是主權者而政府是其意志的執行者。其具體作法是讓人民定期召開人民議會,並在每次開議時針對兩個提案作出表決:(一)是否贊成維持現有的政治體制?以及(二)是否贊成將行政權交付現在的執政當局?據此,我們知道盧梭嚴格區分了行政權和立法權,後者歸人民全體所有且不得讓渡,而前者乃政府職責,包括了行政官員的制度設計與人事任命。而在此區分之下,我們也看到了人民主權的行使,採取的是針對身為意志代行者的政府全盤式評估。如果對上述兩個提案做出否決,那麼人民便可進一步開始進行關於政治體制選擇的商議。
如此一來,貴族制、君主制亦或全民共治皆是選項之一,本身並不具絕對優先性。政體乃至財產制度的具體細節,最終決定權仍在人民手上。本書第三篇旨在闡釋這一種社約論意義上的盧梭式民主。
六、強迫自由和盧梭的論證特色
關鍵在於,怎麼讓公共意志來指揮人民?比這更為根本的問題則是:我們如何確認何為公共意志?盧梭在本書中對「公共意志」概念的解釋並不詳盡,但要旨倒也不難掌握。第一步是理解它和「全體意志」(the will of all)和「個別意志」底下的根本差異:
全體意志和公共意志常有很大差異,後者只看公共利益,前者則為私利,且只是個別意志的總和。不過,如果把這些個別意志相互抵銷的較多或腳少成分減除,剩餘的差額便是公共意志。
根據盧梭的闡釋,公共意志所意欲的對象就是公共利益。通常人們以簡單計算題來解釋這一段話。例如,倘若此時天上掉下來一張千元大鈔在十個人當中,而此時有六人想獨吞,兩人想要平分,另外兩人則根本不想要,其全體意志的滿足必須有六千兩百,但極端個別意志的加減結果則是每人各得一百元,即是公共意志。
不過,姑且不論這是否在嚴格意義上可理解為一道數學習題,此處有三點必須注意。第一,盧梭明白公共利益不一定是每一個人真的想要,也不是所有人想要的總和,但卻是所有人應該致力於追求的事。因此,他在本書第四篇提出了許多措施來拉近現實與理想,例如公民教育、愛國心的培養亦或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的全面推動,甚至必須禁止具有偏私的黨派組織,無一不是為了讓多數人的個人意志能等同公共意志,甚至到最後全體意志也和公共意志吻合一致。
第二,無論其計算方式是把最極端的想法全部去除之後所取得的平衡或中間值,亦或減去人們的自重之愛之後的結果,盧梭認定每個立法情境當中都存在一個公共意志,也就是一個潛在的標準答案等待找尋。因此,他如此說道:
公共意志永遠是公正,永遠傾向公共利益的實現;但這並不是說人民的實際決策過程都是同樣公正無私。每個人都想追求自己認為好的事物,但並不一定都能看清楚什麼是好——個人無法讓人民腐化,但卻經常誤導它,而一但如此發生時,人民會看起來像是在追求邪惡的事物。
第三,正因為公共意志永遠公正,所以違背者必然是受到腐化或偏見蒙蔽的結果,所以「倘若有人不遵守公共意志,得由全體迫其遵守之」,且這麼做其實是:
為了迫使他自由,也唯獨把每一個公民交給國家,才能讓他不再依賴任何人。
盧梭強調,這種不得已的必要措施乃社會契約本身的隱藏條款。缺之,則契約的落實恐淪為空談。
上述第三點日後在文獻上被簡化為所謂的「強迫自由」(forced to be free)概念,不但成了日後革命人士的進步口號,也是常見於獨裁政權的一種反動修辭,甚至讓盧梭在二十世紀背負了「極權主義始作俑者」的罵名。本文礙於篇幅不能深入討論此一爭議,只能進一步從方法論角度提出四點供讀者藉以判斷。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盧梭的整體政治思想存在一個從「實然」(is)推出「應然」(ought)的特色。更具體地說,他的推論奠基於曾經存在過的事實(自然狀態底下的自由人),從而試想,倘若沒有社會化的墮落過程,人們現在應該將會有的樣子。換言之,現實世界當中勾心鬥角、爭得你死我活的現代人,反而是一種人格被扭曲了的存在,不是真正的自己。此一想法預示了二十世紀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和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藉以批判現代社會弊病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本真性」(authenticity)概念,也讓盧梭得以主張:自由並非自由主義底下「公民」享有的消極權利,而是身為「人」就當努力去實踐的積極義務。盧梭的直接民主說到底爭不只建立於一個規範性契約概念,而是整個體系維繫於一個關於「人之所以為人」的理解——或說具規範色彩的人論。
另一方面,鑑於盧梭的想法乃根據歷史(過去的實然)來推出當前(現在實然)當中「應該存在但卻不存在」的獨立與尊貴(應然),所以嚴格說並非一種用來進行因果推論或探索未見可能的「反事實思維」(counterfactual thinking),而是一種「目的論式」(teleological)思維。類似一顆麥子如果落在適當的土壤當中,加上必要的水與養分,當可發芽茁壯,個人在適當的制度底下將能發展成獨立且高貴的公民,而社會整體乃至人類文明亦可走向真正美好的自由境界。
藏在目的論背後的其實是一種關於「潛力」有機式(organic)想像,正如盧梭當年的頓悟意味著:人具有向善的天性,只要給予適當的(社會制度)條件,將能發揮出來,而社會契約旨在提供此一條件。然而,雖説潛力是一種潛藏於實然當中的應然,但這不能讓我們可以遊走於實然與應然之間,甚至因而喪失了現實感。例如,當盧梭主張新公民社會的新自由人不僅必須關心公共事務,戮力於實現象徵公共利益的「公共意志」,並盡可能戰勝代表自尊之愛的「個人意志」的時候,他一方面把應然與實然的兩種意志塞進去了一個人的意志當中,認定人人都有兩個自己,因此必須—以《愛彌爾》的用語來說—讓「高階的自我」來主導「低階的自己」,否則不僅義務未盡,權利也將一併喪失。
與此同時,盧梭似乎也忽略了當社會集體在強迫一個人自由時,不但仰賴了上述的比喻,更藉由將社會「類比」為具有單一意志的個人那樣,因此迫使他接受多數人的決定不過是強迫他接受了(不被私利所蒙蔽的)真正自己。那實際上也許是一群自認為代表公共意志的人在強迫他們所認定為受困於個人意志的人,或說多數暴力。
七、結語
從方法論角度來看,相較於霍布斯與洛克在以「社會契約」來說明國家起源亦或政治權威的基礎,某程度上合理化了現狀,盧梭在強調參與之必要時,反而讓契約論作為一種政治理論方法不僅能「解釋」過去起源,「批判」現在的不平等結構,同時也提出一個「規範性」民主理論,以及如何打造一個「直接民主」未來的具體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盧梭的理論也突顯了「立憲主義」與「民主政治」的潛在衝突。社會契約並不單指一次性的政治工程,其「奠基」成分在於所有當事人所共同簽訂那呼喚出一個共和國的首次契約,但此後公民針對公共事務的立法相關工作,也是不可或缺的政治日常,否則同樣會在立國之後淪為受制於他人制定的法律之奴隸。無論如何,新共和國底下的新自由人必須是勤於關心公共事務的公民,且自由的獲得與維持都得以親身參與作為代價。走出自然狀態的人必須放棄天然自由以換取新的公民自由,從此讓自己的意志接受公共意志的指揮。
然而說到底,盧梭的社約論所欲捍衛的是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所謂的「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亦即成為自己的主人,並以回復本真的自己作為自主的理想,而非洛克以降的英國自由主義想以憲法來保障的那種不受他人(尤其是政府)干涉的「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作為一種積極自由,「公民自由」是必須且應當付出努力才能取得的一種成就。也正因如此,以此為基礎的直接民主實踐起來相當不易。
盧梭的歷史感與現實感讓他設想了許多用來提升公民素質並防範社會更加墮落的機制。不過,當付之實踐的時候,直接民主的決策方式幾乎等同多數決,且難以避免多數暴力的可能性。除非我們有另一個外在且獨立的方法可確認公共意志的內容,否則我們難以斷定那是多數暴力或果真迫使了一個反對者從私心當中解放自己,成就更高階的自我。更讓論者陷入兩難的是:如果我們有投票之外的另一種方法,那全民投票的意義在哪?又,萬一如果多數決其實是不過是違背公共利益的全體意志,那我們又該如何?
另一方面,鑑於盧梭的性善論與基督教「原罪」(original sin)有根本的衝突,當他提出公民宗教並高舉基督教,其實是採取了工具性角度來看待宗教,而非其內在價值或人類對神聖的追求。就此而言,公民宗教實施起來其實也無異於愛國教育,且是一種以國家來填補上帝空缺的方式。也許那是因為他意識到了法國即將進入的嚴重社會分裂,所以才設想了此一方式來凝聚追求私利的人民和黨派,但此一功能取向的宗教觀,讓人難以不聯想到國家意識形態的灌輸。
事實上,正如同樣捍衛人類本真性的加拿大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曾指出,盧梭的思想在兩方面促成了法國大革命走向致命之路:一是公共意志概念讓人相信所有政治衝突皆有達成「和諧一致」的可能,二是高舉公民精神的結果讓人將愛國視為一種「美德」 。置於二十世紀的脈絡,不意外前者將允許社會集體隨時準備強迫少數人接受多數意見,而後者則給予了國家正當理由來進行愛國教育灌輸,甚至將為國犧牲高舉為一種個人的最高榮耀。
這當然不是盧梭本意。畢竟,盧梭爭的是一種人應當有的樣子,也就是他認定人之所以為人的尊嚴。這根本想像來自他對自然狀態的理解,但也指向了一個社會應當改革與個人心理必須發展的明確方向。《社約論》的書寫既不是為了回歸自然狀態,也非抒發烏托邦情懷,更不想等著科學來推動人類走向進步的未來,而是真切地期待理性之光可以引導人們去認識公共意志,而良心則能教會人們如何去愛它,最終重拾過往的純真與自由。然而當這理論落入追求私利的人們手中,似乎比任何貶抑人性的理論更加危險,更容易合理化多數決甚至是獨裁政權。如果說柏拉圖的「哲君」(philosopher-king)理論不該為日後獨裁者假裝哲學家來統治國家,那或許我們也不能將受到盧梭啟發的政治野心家採取的迫害措施,全歸咎於本書。
換上另一套「枷鎖」來跳現代文明的自由舞曲?
——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導讀/ 國立政治大學 政治學系副教授 葉浩
既然沒人有支配其同類的天然權力,而且暴力並不能產生權利,那麼契約便是人與人之間正當權力的基礎了。
——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
一、前言:關於本書的三個閱讀脈絡
1749年夏季,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狄德羅(Dennis Diderot, 1713-84)因為公開懷疑上帝的存在而被囚禁於凡森城堡(Château de Vincennes,巴黎古監獄)之中,當時還是他好友的本書作者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某天...
目錄
換上另一套「枷鎖」來跳現代文明的自由舞曲?——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導讀 / 葉浩
譯序
序言
第一編
第一章第一編的問題
第二章原始的社會
第三章最強者的權利
第四章奴隸
第五章溯究最初協約的必要
第六章社約(社會的契約)
第七章主權體
第八章國家
第九章不動產
第二編
第一章主權是不能讓渡的
第二章主權是不能分割的
第三章公共意志能否錯誤
第四章主權者的權限
第五章生死權
第六章法律
第七章立法者
第八章人民
第九章人民(續)
第十章人民(續)
第十一章 各種法制
第十二章 法律之分類
第三編
第一章政府通論
第二章各種政體的原理
第三章政體之分類
第四章民治政體
第五章貴族政體
第六章君主政體
第七章混合政體
第八章非任何政體適合任何國家
第九章良好政府之標記
第十章政府之妄為及其墮落之傾向
第十一章 政治社會之滅亡
第十二章 主權怎樣維持
第十三章 主權怎樣維持(續)
第十四章 主權怎樣維持(續)
第十五章 代表
第十六章 組織政府非契約行為
第十七章 政府之組織
第十八章 怎樣防止政府篡權
第四編
第一章公共意志不能毀滅
第二章票決
第三章選舉
第四章羅馬民會
第五章護民官
第六章迪克推多制
第七章監察制
第八章宗教
第九章結論
盧梭年表
換上另一套「枷鎖」來跳現代文明的自由舞曲?——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導讀 / 葉浩
譯序
序言
第一編
第一章第一編的問題
第二章原始的社會
第三章最強者的權利
第四章奴隸
第五章溯究最初協約的必要
第六章社約(社會的契約)
第七章主權體
第八章國家
第九章不動產
第二編
第一章主權是不能讓渡的
第二章主權是不能分割的
第三章公共意志能否錯誤
第四章主權者的權限
第五章生死權
第六章法律
第七章立法者
第八章人民
第九章人民(續)
第十章人民(續)
第十一章 各種法制
第十二章 法律之分類
第...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收藏
1收藏

 8二手徵求有驚喜
8二手徵求有驚喜




 1收藏
1收藏

 8二手徵求有驚喜
8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