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 子
聽著錄影機裡不斷傳出「嗡嗡」的聲音,李瀚心裡不知怎麼,開始緊張起來。
錄影帶裡的內容很快顯示了出來,李瀚的手心已經有些發汗,螢幕呈現一種黑白的狀態,就像是二十世紀初的那種黑白相片。
畫面被王允定格了,黑白的畫面上彷彿有一個虛影,看不出是人還是什麼,也看不出具體年代,虛影像是在吃著什麼東西,動作有點急切,很激動的樣子,有點像餓狼撲食。
李瀚重新打量錄影機上的畫面,年代久遠的黑白畫面,看不出是人是鬼的虛影,侷促的空間,讓他漸漸感覺全身的雞皮疙瘩都起來了,莫名的壓力彷彿要將他的心臟從胸膛裡擠壓出來。
這台錄影機是王允剛剛從舊貨市場挖回來的,所以機身上還滿是灰塵,裡面不斷發出一些「哢哢」的噪音。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緊張,王允不小心按到電源鍵,螢幕一下子就黑了,再打開的時候,錄影機卻讀不到錄影帶,連模糊的黑白畫面也沒了。
李瀚忙了半天,手心裡全是汗,甚至連後背的衣服都微微汗濕,卻依然沒有任何進展。王允將錄影帶再次裝進去,也許因為他更熟悉這台錄影機,也許是剛才李瀚的努力終於有了效果,王允只是拍了兩下,寂靜無聲的黑白畫面、模糊不清的虛影,便再次呈現在螢幕上。
這次的畫面有了一點點變化,剛開始,畫面是白色的,帶著些黑點,想來應該是帶子上的廢片。王允還是不斷拍打著錄影機,畫面上的黑點也開始有規律地跳動起來。
黑白的畫面大概持續了五分鐘,螢幕上卻依然沒有任何變化。
李瀚有點著急了,手心裡的汗也更多了,不知道是這台年久失修的錄影機的問題,還是錄影帶本身的品質就不好,這樣的黑白畫面根本不能給他們帶來任何有用的資訊。
正當他擔心錄影帶後面的內容還能不能播放出來的時候,一行字在螢幕上一閃而過。王允愣了一下,停住手,將畫面慢慢往後退,把那行字倒了出來,最後將它定格在螢幕上。
這是一行極為潦草的漢字, 看起來應該是手寫的, 李瀚雖然一時沒看出來寫的是什麼,但還是看出這應該是一句嚴厲的警告,末尾醒目的驚嘆號讓他心裡為之一顫。之後,黑色的字跡漸漸變得清晰起來:「特情08絕密*工程部隊」。 「絕密」兩個字讓李瀚剎那抬起了頭,身為鑑識學的高材生,他自然知道「絕密」這兩個字的嚴肅性。國家祕密等級一般分為祕密、機密、絕密,而絕密是最高等級,不知道這卷模糊不清又歷經多年歲月的錄影帶,到底埋藏著怎樣的祕密。
「工程部隊」這個詞聽起來非常奇怪,可能是沿用了以前的名稱,至少他在C市從未聽過這種名稱。更令他奇怪的是,這一行字看起來還是手寫的,
不像是電腦打字,反而像是拍完了,再寫到錄影帶上,而後每十年再翻錄一次。那行字很影機。幾秒之後,畫面再次回到之前觀看的地方,兩人再次屏住呼吸。
「絕密」兩個字讓李瀚漸漸覺得呼吸都有點困難。他想到了一些可能,但都是臆測。
連續出現的畫面長短不一,除了那個模糊的虛影瘋狂吃東西的畫面,其餘都是零散的資料,之後就是漆黑一片。可以確定的是,那漆黑的畫面裡其實是有內容的,可能是當時拍攝光線不足或年代太過久遠,讓人根本看不清楚是什麼,只是偶爾閃過的一些白點,讓李瀚知道錄影帶的內容還在繼續。
兩個人安靜了足足十幾分鐘,王允看了李瀚一次又一次,卻始終沒有說話。
李瀚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思考裡, 眉頭緊緊地皺著, 坐在沙發裡的身體一動不動。錄影帶的品質不高,看起來年代又很久遠,綜合分析,這卷錄影帶應該拍攝於二十世紀。可能是因為當時技術和設備的限制,畫面一直晃動得很厲害。又經過了歲月的洗禮和多次的翻錄,所以很多畫面早已模糊不清,連聲音都沒有,不知道它本來就是部默片,還是因為錄影機的音響壞掉了。唯一值得慶幸的是還能看清楚一些東西,勉強能分辨出裡面的山石和人物。顯示出來的內容很少,也很簡單,一開始沒有任何鋪陳氣氛,側重於表現裡面的細節和人物。
錄影機上顯示出來的第一段畫面就是那個虛影在瘋狂地吃著什麼東西。
第二段畫面是白天,能看到晴朗的天空,有十幾個人在搬運東西。鏡頭拍攝到一個女人,還沒等他們看清女人的身高和長相,鏡頭就又轉掉了,改成拍一個年輕人。這樣來回重複了好幾次,畫面不斷切換,給人一種很急促的感覺,也使得這卷錄影帶顯得更加神祕,更加令人疑惑。畫面中的年輕人像是在講解什麼。因為沒有聲音,李瀚也不知道他到底說了什麼。漸漸地,連嘴型都變得模糊起來。接下來,鏡頭自上而下拍攝,依稀能看到一路上的山石、河流…
接下來錄影機的螢幕裡就是一片雪花,等再次出現畫面時,已經變成了黑夜,所有人都隱沒在黑暗中,圍著一個火堆。所有人都低頭不語,身形隨著攝影鏡頭不斷晃動,看起來極為疲憊。 這些畫面看起來似乎沒有什麼意義,再往後就是一些碎石,還有一些躺在地上的人,似乎跟吳離暴力殺人一點關係也沒有。之後,鏡頭不再抖動,李瀚看到畫面上出現一張男人的臉,讓他心裡有點發毛。那個男人一副披頭散髮的模樣,臉上掛著笑,神情中透著一種說不出的怪異。他穿著軍裝大衣,突然就跪了下去,頭直直地磕在地上,再也沒有站起來,他全身有點抽搐,彷彿是受了驚嚇,又彷彿是在哭泣。 鏡頭像是被人固定在了這裡,停留了很長時間也沒有其他畫面出現。李瀚看了看王允,意思是錄影帶是不是播放完了。王允搖搖頭,指了指螢幕上的時間,大概還有一分鐘。這時,畫面終於有了變化,一個女人走進鏡頭。這個女人談不上漂亮,身材修長,也穿著軍裝大衣,鏡頭拍到了她的臉。李瀚感覺她的表情同樣有些怪異,可是又不同於剛才那個男人的感覺。他的腦海中閃過一些奇怪的想法,但還沒等他細想,這個女人的畫面又一閃而過,那個跪著的男人和站著的女人都消失了,螢幕又重新回到漆黑的狀態。李瀚覺得這幾段畫面處處透著不尋常,可是又遲遲抓不住關鍵點。
畫面已經停止了,螢幕上的時間也顯示播放完畢,王允剛想倒回去再看一遍,螢幕突然再次亮起。李瀚看到鏡頭晃動得厲害,像是被人打倒了,一個光球出現在畫面上,有臉盆那麼大, 光球裡好像有什麼東西在不斷湧動。 他不明白那是什麼。 太陽?又或者是月亮?
畫面再次定格,還是那個女人的臉,卻讓李瀚第一次感覺到了恐懼,以至於他不敢直視。
良久,王允才輕聲問道:「你覺得這卷錄影帶跟那件兇殺案有沒有關係?」
李瀚沒說話,他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他腦子裡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該如何反應。他低著頭指了指螢幕,聽到「啪嗒」一聲關掉錄影機的聲音,這才張了張嘴巴:「應該沒關係。」
王允坐回李瀚身邊,沒有吭聲。他深吸了一口氣,努力讓自己的情緒平靜下來。
「難道吳離還有前科?」李瀚試探性地問了一句。如果這些畫面都是真實的,那吳離可能真的有犯罪前科。李瀚越來越懷疑,畫面裡那個吃東西的人就是吳離,而他吃的東西是…
「看樣子應該是幾十年前的事了,即使有案底也不好查。」 李瀚點了點頭,錄影帶裡的內容應該發生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就算有案底也不好查,需要動用大量的人力物力。
第一章 風雨欲來
C市,銅鑼區。 眼前是一棟老式結構的磚混矮樓,以前是某機械廠的員工宿舍。在福利分房的年代,這棟樓算是當時少有的多層建築,只不過時過境遷,城裡的高樓越蓋越高,越建越多,這棟聳立了三十年的老樓就顯得很是破敗。案發現場位於三樓的三○二室,已經被先前趕到的員警們封鎖了。雖然警戒線早早地拉了起來,可樓前依然圍滿了人,幾個技術人員和法醫正忙著拍照、驗屍、勘驗現場,樓內顯得擁擠不堪。一個先到現場的員警告訴王允,這是一間出租房,死者獨居多年,是一個典型的單身漢。 屍體頭朝南腳朝北,呈仰臥狀,頭頸處被人用利器砍傷。 「怎麼樣?」王允拍了拍一個法醫的肩膀問道。
「死因是機械性死亡,兇器應該是一把生鏽的菜刀,已經被勘驗組的人收起來了,據現場偵查的情況來看,推測死亡時間不超過五個小時。」「也就是說死亡時間是凌晨五點左右?」「對。」
王允點了點頭, 轉身對李瀚說: 「過來啊。 」李瀚下意識地點點頭, 邊走邊環視上下。昏暗骯髒的走廊、面色凝重的警員、法醫手裡冰冷的器械、樓下醒目的警戒線,以及面前散發著濃重血腥味的屍體,一時間讓他胃裡翻江倒海,扶著牆就吐了起來。李瀚知道自己早晚有一天會親眼見到這樣的凶案現場,可是他沒料到會這麼快,也沒有料到自己會這麼丟臉。要冷靜,不能影響判斷,李瀚暗暗提醒自己。 作為鑑識學的高材生,這個時候,李瀚絕不允許自己丟臉。 「你被嚇到了?」他的耳邊響起王允有些不耐煩的聲音。
他強忍著噁心,慢慢靠近眼前這具屍體。男性,年齡五十歲左右,上身是一件汗衫,滿是烏紅的血跡。面部扭曲,屍斑融合成大片,出現全身屍僵,嘴唇已經開始皺縮。挑開他的眼皮,角膜混濁,確認已經死亡至少四個小時以上。法醫正在仔細勘驗男屍脖頸處的創口,小心扯動著被切開的皮膚和肌肉組織,最後在肌肉組織中成功提取出少量鐵鏽。「兇器確定是現場的那把菜刀。」一個年輕的法醫說。
王允盯著他,幾秒鐘後忍不住開口問:「就這些?」 「對,就這些。」年輕的法醫自信地回答。王允嘆了口氣,顯得有些失望。從現場遺留的那把生鏽菜刀來看,確實是兇器無疑,殘留在死者脖頸處的鏽跡也可以證實這一點,但在菜刀上並未採檢到任何指紋。另外,屋內整潔而不亂,表明兇手並未與被害人有過激烈搏鬥。
「小子,你看出什麼來了嗎?」王允轉而看向李瀚。
李瀚蹲下身去,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將菜刀從證物袋裡取出來,放到被害人的脖頸處。
菜刀上血跡斑斑,甚至有一些卷刃的現象,按理說這是兇手在砍向被害人的脖頸時,刀口自然微微卷起,然而一旁的地板上卻有著幾道不起眼的溝壑,應該是利器砍向地面時留下來的痕跡。雖然那些淺淺的溝壑已經被凝固的血液覆蓋,但是地面上那微微的凹陷卻是無法掩蓋的。
「能借你的鑷子用一下嗎?」
眼前的年輕法醫顯然沒有想到李瀚會忽然提出這個要求,顯得有些手足無措,鑷子順勢從他手裡掉到地上。李瀚拿著鑷子,將地上凝固的血液一點點地撥開,漸漸露出帶著新色的溝壑來。李瀚指了指死者的姿勢,又揮了揮菜刀,王允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
「你是說兇手故意砍了地面幾刀?」
「對,從死者死亡時右手在其身下,可以推測死者被砍傷後,未死前曾有翻身的舉動,但是兇手並未追著砍,而是在原地砍了幾次地面後再次行兇。」
一旁蹲著的年輕法醫小聲嘀咕道:「那也有可能是兇手在砍死被害人之前,失手砍到了地面上啊。」
王允冷著臉說:「屍體的血跡全部流向死者的右側,而左側的血跡只可能是死者第一次被砍傷時留下的。」
年輕法醫低著頭不再說話,王允繼續看著李瀚:「小子,你繼續。」
「兇手為男性,年齡在四十五歲至五十五歲之間,身高不會超過一百七十公分,不太講衛生,身體羸弱,並且是個左撇子。」王允盯著李瀚,問:「就這些?」「就這些。」王允微微皺起眉道:「身高、體重可以從現場的腳印推斷出來,年齡也相差無幾,但兇手不太講衛生,還有是左撇子好像跟本案無關吧?」
「你們看死者的面部、頭髮都很乾淨,唯獨衣服上留下了一些污漬,而室內並沒有任何打鬥的痕跡,表示這些污漬很可能來自死者與兇手的身體接觸。還有,死者脖頸上的致命傷並不是一條平的直線。假設我是兇手,站在被害人的左側,用右手拿刀砍死被害者,那麼刀口應該是向下傾斜才對,而死者脖頸的切口明顯是向上傾斜,所以兇手只可能是個左撇子。」李瀚說道。
「你說得都很對,可是不太講衛生,又是一個左撇子,這樣的人並不少。」王允說道。
「另外,我感覺這個人精神上有些問題,至於是什麼問題,我不能肯定。」
「傻子都能看出來這個人精神有問題,不然在這大白天揮刀砍人,不是變態是什麼?」年輕法醫嘟囔道。
「變態跟精神障礙是兩回事,兇手應該屬於後者。」
王允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立刻吩咐手下的警力開始在全市調查患有精神障礙、不太講衛生又是左撇子的人。而李瀚卻愣在原地,心裡久久不能平靜。
一個有精神障礙並失去自控能力的嫌犯暴力入室殺人—這是李瀚對這起案件的分析。然而兇手並非死者的熟人,體格看起來也並不屬於強壯的類型,他是怎麼做到令死者乖乖引頸受戮的呢?
死者租屋處的門窗並沒有任何被破壞的痕跡,一個陌生人是如何順利進入屋內並說服死者自願被殺害?為什麼兇手會在死者翻身之後繼續砍地面,而不是立即上前繼續砍殺?
「在想什麼?」王允遞了一根煙過來。
李瀚回過神,接過煙,搖頭說沒事,就一個人往死者家裡的廚房走去。廚房的煤氣灶旁擺著一個木製刀架,一共有四個位置,上面插著水果刀、剔骨刀、削皮刀,加上之前的那把菜刀,均是鏽跡斑斑,證實菜刀確實是兇器無疑。
屋內的足跡顯示兇手目的明確,進入屋子後徑直到廚房拿刀,沒有多走一步,這樣頭腦清晰的人為什麼會在殺死死者時刀碰到地面,並且連續朝著地面揮了三、四刀?難道他在殺人的時候恍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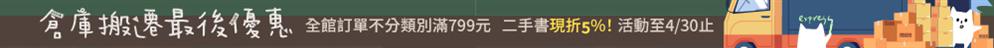













 二手徵求有驚喜
二手徵求有驚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