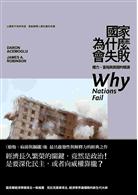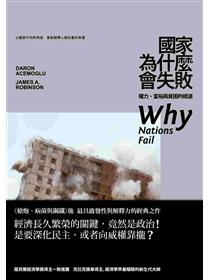《天若有情天亦老》是旅法作者安琪《痛苦的民主》系列之一。在世紀之交的歷史大背景下,側重人物專訪與政論分析,通過對吳國光、趙紫陽、劉賓雁、蔣彥永、達賴喇嘛、高行健、章詒和、趙無極、司徒立、嚴家祺、羅孚、燕保羅、牧惠、劉達文、戈揚、鐘文、程映湘、許良英、余英時等各界人士的思辨性訪談和述評,揭示在東西方文明的碰撞中,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到底發生了怎樣的裂變、他們走向世界的姿態是怎樣的,以及在中國一黨專制體制下、在共產黨意識形態「觸及靈魂」的洗腦過程中,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及人性異化的真相,令人扼腕。著名流亡學者嚴家祺說:這是「新聞」,不是「舊聞」,是不可磨滅的記憶。
安琪在書中以具體的人與事,詳實記錄了「共產時代」個體的覺醒和反叛。他們中不乏有人堅守對真理的承諾,承擔著責任和道義的重負,用生命揭穿謊言,還原歷史真實,創造未來。他們是推動中國向憲政民主轉型的先行者。書中談及戴安娜、密特朗、溫丁等「他山之石」,從不同角度探討全球範圍內新聞自由場域的變遷和挑戰,以及現代社會價值重建可期借鑑的思想資源。
作者簡介:
安琪,祖籍中國浙江,生於蘭州。資深媒體人。自1989年10月定居法國巴黎,為獨立記者和自由撰稿人,並從事新聞研究。先後任香港、美國等地多家中文報刊特約記者和主筆。出版文集:《痛苦的民主》卷一(1994),《中國民族站起來了?》(2002)。
自1996年4月至今,為巴黎「自由談」沙龍主持人。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嚴家祺序:歷史是不可磨滅的記憶——重返法蘭西〉
1989年是中國和世界歷史的大轉折,六四大屠殺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至今沒有結束,六四也導致了蘇聯帝國的解體和20世紀兩極世界的消失。六四的許多流亡者來到了法國,這本書多篇文章記述了六四流亡者和六四後中國國內知識分子的抗爭,這也是歷史。
在這本書裡安琪說:「當時流亡者中的許多人,從一開始就沒打算留在法國」,「這讓法國方面非常惱火。據說,時任法國駐香港副總領事的孟飛龍,聽說我(安琪)已收到美國某大學的邀請函和某報社的工作機會,有可能去美國時,他激動地將手中的打火機扔向天花板。」我也提出去美國,幫助我們在法國定居的艾麗斯協會的一位成員對我說,我們把你們一個個都安排在法國,你們一個個都到美國去了,你不要走了。於是,我就留在法國。幾年後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請我擔任訪問學者。這樣,我還是離開了法國,到了美國。
我經歷了三次人生大轉折,第一次是1989年六四後逃亡香港並到法國,第二次是在華盛頓一週內三次全身麻醉下的心臟手術,第三次就是最近重返法蘭西。這三次大轉折,不是自主行為,而是被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驅動的。
人類不同於動物,在於人有高度的理性和深厚的情感。理性賦予人以想像力,使人可以認識宇宙中的規律,創造出有益於人類而自然界中沒有的物質環境和社會環境;理性也可以製造罪惡,發動戰爭,危害人類和世界。對人來說,理性計算的利益決定人如何行為,而情感決定人行為的方向和道路。
2023年10月31日,我與妻子高皋乘法蘭西航空公司AF55從美國回到巴黎。我一家七口,有法國人、中國人、美國人。「一家三國」,這一天終於團聚。我82年人生經歷了許多事,一件一件都沒有受到多少困難都過去了,重返法蘭西,是遇到最多困難、也得到很多幫助,最後平安實現。
安琪是香港《前哨》特約記者,巴黎「自由談」沙龍主持人。這本書收集了她在香港《前哨》月刊和其他報刊的多篇文章,書名來自於她十年前在香港《前哨》月刊上寫的一篇紀念法國外交家燕保羅的文章。題目是:〈天若有情天亦老——「黃雀行動」與燕保羅的人道情懷及其他〉。我也是《前哨》月刊的作者,有幾年,幾乎每期都有我的文章。十年前,我讀安琪這篇文章時,才具體地知道,經燕保羅接納安置的中國「六四」流亡者有兩百多名。燕保羅和法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馬騰、法國駐香港副總領事夢飛龍,為法國接納六四流亡者作出了巨大努力。回憶起1989年多次見到燕保羅的情景,感到他對我們這些來到法國的流亡者十分關懷和友好。我不知道他的父親也是「流亡者」,更沒有聯想起,從香港來到法國,我的登機證上的英文名字YIPPAUL就是燕保羅。當時我改名為「朱豐」,而不是「保羅」。由於YIP與PAUL之間沒有分開,我想不到YIP是燕字,多年中不知道YIPPAUL就是燕保羅。
讀這篇文章的當時,我給安琪回信說她這篇文章,「不是舊聞,而是新聞,是不可磨滅的記憶」。1989年,我保存了這張登機證,記錄了當時的逃亡過程。
在地球上,物理物體不能記憶。在浩瀚的宇宙中,星球、星系不能記憶。只有動物和人類能夠記憶。對動物與人類來說,許多行為沒有經過大腦,是自主神經系統(又稱「植物神經系統」)的「自律(自主)行為」,如心跳、呼吸、消化、新陳代謝。記憶是動物和人作為「個體」的自主行為的基礎和指南,但動物的記憶轉瞬即逝,只有人類的記憶可以長期保存、不可磨滅。歷史就是不可磨滅的記憶。人工智能的發展將會證明,理性只是一種「演算法」,而機器人只能按預定程序模擬人類的情感,不能「創造情感」。
1989年6月19日,香港友人林道群、李志華把我與妻子高皋、以及社科院的甘陽,安排快艇從廣東穿越大亞灣飛馳到香港。我們到香港的第四天,6月22日,香港《明報》頭版頭條刊出了〈喬石李鵬覬覦總書記,楊李力主處死嚴家其〉的報導。這一天上午10時,一位中文名叫方文森的法國駐香港領事館的官員把我們三位「偷渡客」帶到港英政治處的一個機構。我們被告知,不得在香港再停留下去,因為我們是「非法入境」,必須到其他國家去,法國政府歡迎我們三人去法國。
我們沒有其他選擇,在港英政治處,當時就照他們的安排,我們三人改了姓名,我改名為「朱豐」,換上了一身他們要我們穿的衣服。港英政治處的警察將帶著我們三個「假警察」在機場「執勤」,我們每人手裡拿一個「對講機」,做四處巡視的樣子。經過一個單向轉動門、一個鐵門,就到了機場。所謂「執勤」,不過是從港英政治處去機場登機前的路上,如果有人詢問或要檢查,要求我們擺出的姿態。實際上,一路十分順利,我們並沒有扮演警察。
安琪的這部新出版的書,除了燕保羅外,還寫了二十多位大家都熟悉的人,從法國總統密特朗、中國總理趙紫陽、達賴喇嘛、趙無極、高行健、程映湘、余英時,到英國的戴安娜、緬甸的溫丁,許多內容,都會留在人們的長期記憶中。
安琪的這本書,在許多地方談到自由問題。一個人有沒有自由,不僅與他所處的社會環境有關,而且與他有沒有自主行為意向和努力有關。當一個人有強烈信仰時,他的被迫行為,就成了自主行為。宗教是一種信仰,虔誠的宗教信徒可以把信仰作為自主行為的指南。意識形態也是一種信仰,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都是意識形態信仰。作為中華文明基礎的儒家,不是宗教,可以說是一種廣義的意識形態信仰。除了宗教信仰和意識形態信仰外,世界觀也是一種信仰。人類社會中還有一種根深柢固的信仰,這就是迷信。自由出創造,為了爭取思想自由、創作自由,這本書談到吳國光、劉賓雁、蔣彥永、高行健、章詒和、趙無極、司徒立、劉達文等人,在不同環境中,為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以各自特有的方式追尋自由的艱難歷程。
讀這本書,使我想到,人類的各種文明實際上是幾千年中形成的思想文化、行為習慣、像「印刻」一樣,只能以千百年為尺度非常緩慢地改變,而經濟制度,可以在十年、幾十年中發生改變,政治則是轉瞬即逝的行為,可以在幾月、幾年內發生重大變革。這是千年、百年、十年不同「數量級」的現象。一個國家,關心政治的人愈多,這個國家政治問題就愈大;政治愈好的國家,關心政治的人愈少。在一個國家大變革的前夕,人人都關心政治。戰爭把所有人捲入政治。政治不是行政,不是管理,而是用智慧、用妥協的方法消除戰爭和大規模暴力的國家行為。國際關係不是人際關係,全球化有助於消除全球戰爭,全球化是全球性的政治經濟變革,是21世紀、22世紀以至整個第三千紀的大趨勢。最近幾年,出現全球化的局部倒退,只是短期波折。「全球化」,就是一步一步地用幾年、幾十年時間,按照經濟發展的共同路徑,按照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逐步改變一個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政治結構。為改變經濟結構,在保留各國貨幣基礎上建立全球單一貨幣或全球總帳本;在政治結構上,在保留國家的基礎上,建立全球聯邦。全球化,就是在這一經濟政治變革下的全球各種文明和平共存的偉大歷程。
嚴家祺 2023-12-15寫於巴黎
名人推薦:〈嚴家祺序:歷史是不可磨滅的記憶——重返法蘭西〉
1989年是中國和世界歷史的大轉折,六四大屠殺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至今沒有結束,六四也導致了蘇聯帝國的解體和20世紀兩極世界的消失。六四的許多流亡者來到了法國,這本書多篇文章記述了六四流亡者和六四後中國國內知識分子的抗爭,這也是歷史。
在這本書裡安琪說:「當時流亡者中的許多人,從一開始就沒打算留在法國」,「這讓法國方面非常惱火。據說,時任法國駐香港副總領事的孟飛龍,聽說我(安琪)已收到美國某大學的邀請函和某報社的工作機會,有可能去美...
章節試閱
〈要民主主義,還是共產主義?——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悲劇啟示錄〉(節選)
在民主社會生活的經驗告訴我們,當整個社會指望一、兩個「良心」的時候,其禁錮和愚昧造成的民心萎頓可想而知。人們更樂意推崇某個良心,而不去考慮自己應該擔當的社會責任。這樣一種「民意」推舉出來的所謂「良心」是否真的具有普遍意義,值得質疑。另外,正如密爾所特別指出的那樣;「若是哪個國度裡有著一個占優勢的階級,那麼一國的道德必是大部分發自那個階級的階級利益和階級優越感。」在這一前提下,當專制獨裁者用道德說教來束縛人們的精神自由的時候,「良心」與「道德」的對話就像在同一個酒席上行酒令,有一定的規則和「套數」,旁觀者聽起來很熱鬧,實際上都是「套中人」的「政治術語」。因為,「現代統治者要與大眾對話,所以,才不得不顯示自己是道德家、把自己的行為與道德、形而上學、神話聯繫起來。」(班達語。下同。)
舉例來說,當年初任總理的朱鎔基豪言帶100口棺材去闖地雷陣,99口給貪官,最後一口留給自己。此舉不由分說地激起了人們的感情波瀾,沒有誰能夠冷靜理性地去思考這種情形所能產生的後果及其本身的意義。即使朱鎔基的生死委實「重如泰山」,亦不過一泰山而已,豈能壓過九州民生?一國總理的大任,豈可呈匹夫之勇、是幾具棺材就可以擔負的?取悅民意的最好辦法,是改變不合理的制度,而不是以突顯個人道德的特殊性來惑眾,這種做法只能進一步愚昧百姓。奇怪的是,這樣一種封建遺留的傳統土方炮製的「軍令狀」,竟如一張民意通行證,在朱鎔基任期,無論他政績如何,都不會影響他的正面形象。在「棺材」面前,朱鎔基永遠是高大的,致使可以發言的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態處於弱勢,並「陷入道德的荒蕪之中。」以「英雄之媚」馴服人民,這也是一種在極權國家仍然行之有效卻經不起推敲的「權術」。
〈極權中國的良心符號——劉賓雁〉(節選)
•「中國特色」的良心悖論
劉賓雁是作家,更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記者。無論從五○年代在《中國青年報》,或是七○年代末乃至幾乎貫穿整個八○年代在《人民日報》,劉賓雁只要身在其位,就「未敢忘憂國」。他持著新聞記者的「輿論之劍」,針對專制制度下的各種「重點題材」,以一顆赤誠之心,行使自己寫陰暗面和干預生活的權利。
筆者在「中國的良心」這一「通稱」中加了限定詞「極權」和「符號」,在於說明「這一個良心」的特殊性。劉賓雁是在「極權專制中國」的特殊歷史背景下出現的。在那樣一種萬馬齊瘖,「黨指揮槍」,「槍口」瞄準一切「筆桿子」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他那無畏的獻身精神,無異於飛蛾投火,具有悲壯而宏偉的美學意義。
這裡的「良心」,是拒絕承認專制壓迫下的謊言。是說出「皇帝的新衣」的客觀真相。在中國社會結構和政治語境發生很大變化的今天,我們仍能強烈感受到劉賓雁「良心」的道德力量。因為他在「黨的喉舌」的絕對控制下,指明了一個平凡的和基本的常識,即:真理的存在。
劉賓雁曾援引德國著名心理學家、哲學家埃里克‧弗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另譯埃里希‧佛洛姆)在《為自己的人》(Man for Himself: An Inquiry into the Psychology of Ethics,臺灣版譯名為《自我的追尋:倫理學的心理學探究》)一書中的話說:「人的內心裡同時有兩種良心,一個是權威主義的良心,一個是人本來的良心。權威——家長、國家或任何其他權威,可以把它的聲音輸入到人的內心,使外在權威內在化」(劉賓雁〈走出幻想〉,下同)。
對此,劉賓雁的內心體驗是痛苦的和深刻的。他說:「你以為你自己的思想在指導你的行動,你自己的良心在判斷善惡是非,作出取捨,其實,那原本是代表中國共產黨或毛澤東之需要的那些思想、意志和是非判斷標準在起作用,而你卻認為是你本人的,並且常常以這種聲音壓倒你作為人的那個真正的良心。」
這裡道出了一個關鍵的真實——良心的真偽。從心理學角度分析,這樣一種「外在權威內在化」,不可避免地混同或者模糊了「作為人的那個真正的良心」。在這種難以覺察的、受到內在不自覺迎合的「外在權威」影響下所展示出來的那個良心,就會有真有偽,真偽難辨。它的表現形式為:或真中有偽,或偽中有真,或真偽參半。其結果,個人難免陷入他所執著的那個「良心誤圈」,並常常會因為事與願違而感到內心痛苦和困惑。
這似乎是專制極權統治下具有人格理念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普遍體驗。這也是筆者稱之為「極權中國的良心符號」的第二層含義。
〈朝聖者的里程碑——記百年華人首席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節選)
•法蘭西的光榮
高行健的主要創作都是來到法國以後寫的,從數量和作品的質量上講,都遠遠超過他在國內的寫作。
為什麼選擇了巴黎?
高行健說:「首先語言上沒問題。另外,我認為巴黎對藝術家來說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地方,既和平適宜,又有充分的國際性。」這應該是高行健最關鍵性的一次選擇。
高行健到法國伊始,就受到了法國文化藝術界的歡迎和尊重。法國文化部幾乎每年都向他預訂一部戲,並提供所有的演出所需。所謂預訂,只是時間上的限定,沒有任何對內容和形式方面的要求,完全聽憑作家自己作主,全然沒有大陸作家所無法避免的條條框框,這種幸運自然是大陸作家所可望而不可求的。
同時,為了表彰和鼓勵作家的貢獻,法國文化部1992年授予高行健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1995年《靈山》出版後,法國秋季藝術節隆重推出高行健和他的作品。高行健自編自導的《對話與反詰》一劇,由法蘭西戲劇學院著名表演藝術家龍達勒(Michel Lonsdale, 1931-2020;臺灣譯名為麥可‧朗斯代爾)主演,成為重新修復的法國大革命遺址——巴黎莫里哀劇場的開幕式。法國最大的連鎖書店FNAC在巴黎、馬賽、里昂等八個城市以及外省的十多個書店舉行了《靈山》討論會和作家簽名活動。法國各新聞媒體均以罕見的篇幅對此進行了報導。法國《世界報》(Le Monde)評論《靈山》「是一部關於納入大自然的總體循環的生命的偉大的小說。1990年代的中國文學——不如說是被壞死病折磨的中國文學,從此可以指望高行健的創作力與勇氣」。法新社全天播出《靈山》的出版消息及作者專訪,稱《靈山》是「本世紀末中文的一本鉅著」,「既涉及中國的現實,又追述中國的遠古歷史」。法國音樂電臺還破天荒舉辦了長達三小時的「會見高行健」、討論《靈山》音樂語言的專題節目,並同時舉行了高行健喜歡的作曲家現場音樂會。各種形式的高行健作品朗誦會,如《夜遊神》、《周末四重奏》和《逃亡》,以及詩歌等,也在巴黎和外省多個城市舉行。自此,高行健這個名字,代表著一種文化品質,為熱衷藝術的法國文化人所樂道。他的作品,成為每年一度的法國各地藝術節的代表作。
高行健在法國定居十餘年來,一共寫了中文劇本六個,其中三個戲是同時用法文寫的。完成了兩部長篇小說《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出版新論文集《沒有主義》、作品集《周末四重奏》、《高行健戲劇六種》等。辦了三十餘場個人畫展,導演了六部戲,他的戲用不同語言和風格製作演出,遍及世界各地,劇作也被譯成英、法、德、義、荷、日、瑞典、匈牙利、波蘭等多種文字出版。其中,《夜遊神》於1995年獲比利時法語共同體戲劇創作獎。2000年的新劇《叩問死亡》是應法國文化部之約而寫的法文版。
作為一名中國作家,高行健在自己的母國與所在國所經歷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境遇,實在令人深思。通過高行健,法國這個歷史悠久的藝術王國,再次顯示了其豐厚的人文精神和自由、平等、博愛的傳統理念,以及無償接納世界優秀文化藝術的博大胸襟。正是在這塊土地上,高行健獲得了自由無羈的創作生命,「重新再活了一次」。
高行健走上諾貝爾文學獎的聖壇,是作家藝術生命的悲壯與永恆的莊嚴宣言,是法蘭西民族值得驕傲的光榮。
〈章詒和的力量〉(節選)
•「是文學讓人還保持人的意識」
花甲之年開始寫作的章詒和,一開始就將自己的餘生與「用筆發言」結成了「生死戀」。她說:「我拿起筆,也是在為自己尋找繼續生存的理由和力量,拯救我即將枯萎的心。」(《往事並不如煙》自序。)這樣一種寫作理由,唯一的,也是全部的支撐點自然是真實寫作。對此,「經歷了天堂、地獄、人間三部曲」的章詒和是有心理準備的。她說:「許多人受到傷害和驚嚇,毀掉了所有屬於私人的文字紀錄,隨之也抹去了對往事的真切記憶。於是,歷史不但變得模糊不清,而且以不可思議的速度被改寫。這樣的『記憶』就像手握沙子一樣,很快從指縫裡流掉。從前的人什麼都相信,相信……後來突然又什麼都不信了。何以如此?其中恐怕就有我們長期迴避真實、拒絕真實的問題。」(同上)
我們看到,章詒和面對的真實,既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對於「往事」的敘述,章詒和筆下的所有人物都是具有獨立人格和鮮明個性的「這一個」。他們在人為的悲劇社會的大背景中掙扎、求索。命運的跌宕起伏,伴隨著人的卑微和迷茫,事業的輝煌與失落。讓人掩卷慨嘆的,是個體生命的痛苦與無奈。是生命的追求與被踐踏的人生。這樣一件件人物卷宗,正是我們所親歷時代的社會生活場景——這是一幅怎樣的煉獄之旅啊?!
「是文學讓人還保持人的意識」。可以說,章詒和的寫作,也是生命的寫作。她以人為本,敘述中充滿對生命的敬畏,以及對人的權利和尊嚴的捍衛。她的文筆深邃優雅,犀利洞察,筆之所觸,有情有義,情義並重,悲傷中不盡悲傷,憤慨中不盡憤慨。這樣一種樸素深沉的真實寫作,呈現給世人的,是浩氣長存的生命篇章。在飽受共產文化浸淫的中國社會,在「去聖已遠,寶變為石」(章詒和《伶人往事》自序)的消費年代,章詒和的寫作,簡直是一個奇蹟!她出手不凡,一本書,幾個人物,就把長達半個多世紀的「講話精神」解構了。不僅如此,這樣一種「對個體生命的確認」的真實性寫作,讓我們見證了「文學之為文學而不可動搖的理由」。「在這裡,真實不僅僅是文學的價值判斷,也同時具有倫理的涵義。作家並不承擔道德教化的使命,既將大千世界各色人等悉盡展示,同時也將自我袒裎無遺,連人內心的隱祕也如是呈現,真實之於文學,對作家來說,幾乎等同於倫理,而且是文學至高無上的倫理。」
在這裡,章詒和的寫作,宛如一股穿越時空的清泉,給業已荒蕪的中國當代文學注入了生機。她用「換代之際的人物」(指國民黨政府與共產黨政府的不同統治期),在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之間的溝壑上,架起了一座橋梁。那斷裂的殘垣斷壁處,盡是荒唐言和辛酸淚。從中我們依稀可見中國人的脊梁—— 一個遭強權百般蹂躪、踐踏的不屈的人的脊梁!!!
前不久,我在給國內一位受人尊敬的詩人的信中寫道:
節日期間,除了忙活,我讀的就是章詒和的《伶人往事》,她寫得真好,道理說得非常透澈,常常讓人從心裡喝采,也為主人公流淚。她筆下的伶人,是中國藝術的靈魂,也是受盡凌辱的悲劇人物。多虧有個章詒和,才讓這些人的靈魂得以復活,讓這些人和事,讓他們的命運來鞭打製造噩運者,警醒已然麻木的人們。
感謝章詒和,她一個人的力量,頂得上一個軍隊……
果然,章詒和的力量引起了當局的驚惶。
〈無極的世界——用繪畫闡釋存在的自由與「無法澄清的生命」〉(節選)
現代派抽象繪畫藝術大師趙無極(Zao Wou-Ki, 1920-2013),是20世紀第一位躍居西方現代派藝術主流的法籍華裔繪畫大師,也是藝術生涯最長、最完整的來自中國大陸本土的藝術家。時間跨度從國民政府時期到21世紀——期間避開了共產黨執政期最黑暗的年代。
何以強調這一點?因為這個「時間差」,對於趙無極這一「個體」來說,非常重要。是生與死,存在與否的關鍵所在。現代派藝術,源於西方19世紀末的現代主義文藝思潮,旨在突顯人的自由與解放。「五四」時期的中國文人,或多或少都受到這一思潮的影響。三○年代含有「租界文化」元素的上海都市文化現象,通過對個性的張揚,肯定自我的存在,被視為中國文人試圖衝破傳統束縛、嚮往自由的一種現代性追求。
然而,這一具有普世價值的現代性,自1949年以來的數十年間,被執政中國共產黨視為「異端」,遭到嚴厲批判和排斥。「政治掛帥」、「階級性」排除現代性,現代派所涉及的任何領域,都是禁忌。凡與「舊時」沾邊的一切,都被視為封資修而被整肅。「適時」離開的趙無極,得以「避難」。而他的父親、家人卻深陷困境,難逃一劫。瞭解了這一點,才能更好地理解,趙無極這個倖免於被「共產思想」毒化和汙染的「中華民國人」,之於中國乃至中國人的意義;才能略知趙氏獨有的「無極的藝術」之於世界的價值與啟示。而這些,遠不是他的畫作之「天價」所能概括的。
趙無極生時不做西方人眼中的「中國畫家」,死時安葬於距他的畫室「一箭之遙」的蒙巴拉斯公墓(Cimetière du Montparnasse,另譯蒙帕納斯公墓)。懷有「強國夢」,卻罕與中國人來往。躋身於法國主流藝術圈,卻「咬斷舌頭」埋頭畫畫,執意不受任何流派所限。父親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的「盡孝之道」則是回國講學,為了父親那「無法澄清的生命」〔無極的摯友、詩人勒內‧夏爾(René Char, 1907-1988)〕。他的藝術成就於法國,卻被大陸媒體視為「國寶」,成為「引進國門」的「先世界、再中國」的外籍藝術大師。
這一切,構成了趙無極具悲喜劇色彩的傳奇人生。個中傳達著中國人的百年滄桑與榮辱,傳達著趙無極這一個體生命及其藝術的存在之祕。而趙無極在身後「被回歸」——這一來自「大中國」的「殊榮」及各種報導,則暴露出對趙無極的「關注錯位」,顯示出深刻的文化衝突——不單是一般意義上文化認知層面的衝突,而是包含人文的和教養的心理衝突。反映出經歷政治、經濟雙重壓迫的中國社會形態下,人的情感道德的失落和價值精神的整體匱乏。
〈天若有情天亦老——「黃雀行動」與燕保羅的人道情懷及其他〉(節選)
•接力「黃雀行動」內幕
1989年北京發生六四鎮壓,一大批被通緝或人身受到威脅的學生領袖、知識分子、工人、企業家等民運人士被迫走上了逃亡之路。一水之隔的香港,以香港支聯會(港支聯)為首的各種社會力量總動員,成為史無前例的大批中國流亡者的首要「通道」。當他們逃到香港,通過港支聯尋求第三國庇護時,或許出於某種不為他人所知的「策略」,美國緊閉大門,除了點名要被中國政府首批通緝的嚴家祺、陳一諮、萬潤南、蘇曉康等人外,其他一概拒之門外。英國緊隨美國之後,嚴守邊關。(最近坊間所謂法、英、美三國的聯手行動,不知從何談起?)而法國則張開雙臂無條件地迎接這些被理想和悲情衝擊的人們,「始作俑者」,是在香港「第一線」的法國駐港副總領事孟飛龍(J. P. Montagne, 1952-2021)。據知情者透露,孟飛龍以「先斬後奏」的方式,當機立斷,解了港支聯的「燃眉之急」。
是時,社會黨黨魁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 1916-1996;總統任期1981-1995)統領的法國,在國際社會頗具大國風範。剛剛三十出頭的保羅,作為一名忠實的社會黨員,是外交部副部長的內閣成員。因了這個「便利」,保羅接應了港支聯轉到法國駐港副總領事孟飛龍那裡,再由孟飛龍送往法國的流亡者。據說支持這一切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幕後人物,就是時任法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的馬騰(Claude Martin)。1989年6月3日,他正好在中國旅行,住在比鄰天安門廣場的北京飯店,與六四屠殺擦肩而過。他們三人的共同點是,喜歡中國,熱愛中國傳統文明和文化,都講一口流利的中文。
同年7月14日,法國政府邀請首批抵達巴黎的中國流亡者參加法國國慶大典,賦予這一行動以正義性和合法性,充分彰顯了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
〈要民主主義,還是共產主義?——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悲劇啟示錄〉(節選)
在民主社會生活的經驗告訴我們,當整個社會指望一、兩個「良心」的時候,其禁錮和愚昧造成的民心萎頓可想而知。人們更樂意推崇某個良心,而不去考慮自己應該擔當的社會責任。這樣一種「民意」推舉出來的所謂「良心」是否真的具有普遍意義,值得質疑。另外,正如密爾所特別指出的那樣;「若是哪個國度裡有著一個占優勢的階級,那麼一國的道德必是大部分發自那個階級的階級利益和階級優越感。」在這一前提下,當專制獨裁者用道德說教來束縛人們的精神自由的...
目錄
嚴家祺序:歷史是不可磨滅的記憶—重返法蘭西
代序一 逝者如斯夫?——人的存在與生命流的詠嘆
代序二 巴黎「自由談」沙龍紀要與述評:我們在哪裡,中國就在哪裡——政治學者吳國光提出「亞流亡」概念及對華人族群命運的思考
【第一編 思辨篇】
要民主主義,還是共產主義?——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悲劇啟示錄
極權中國的良心符號——劉賓雁
衝破思想牢籠,走出六四悲情——也談蔣彥永上書的思想內涵
中國知識分子應該懺悔——兼論知識階層依附性的惡果
最後的達賴喇嘛—— 一介僧侶對峙共產強權的神話與思考
西藏問題「回歸」本土,拷問中國良知
【第二編 自由篇】
朝聖者的里程碑——記百年華人首席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
章詒和的力量
無極的世界——用繪畫闡釋存在的自由與「無法澄清的生命」
尋找事物的祕密——司徒立的繪畫藝術
永遠的巴黎,生命流的詠嘆——記原首任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首屆民陣主席嚴家祺
香港新聞自由現狀與前景——「九七」前夕與老報人羅孚對話
【第三編 祭祀篇】
天若有情天亦老——「黃雀行動」與燕保羅的人道情懷及其他
牧惠——絕不缺席的中國知識分子
堪回首,滄海桑田度有涯——從報界同人劉達文父親的一生談起
摒棄六四衣缽,維護流亡者回家的權利——謹此悼念病逝他鄉的劉賓雁先生
戈揚——翱翔的自由鳥
那個叫鐘文的人,走了!
超越者的智慧——記第一代流亡人士、文化使者程映湘
【第四編 他山石】
從「世紀婚禮」到「世紀葬禮」——戴安娜悲劇與現代社會的整體精神匱乏
失衡的天平——從密特朗私人醫生大揭密風波說開去
緬甸「無冕之王」溫丁
【附錄】
民族主義與反西化的輿論導向——訪致力於中國人權、民主事業的科學史家許良英
民族主義與中國政治傳統——專訪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余英時
心靈自由與獨立人格——訪自由撰稿人安琪女士/亞衣
謝辭
嚴家祺序:歷史是不可磨滅的記憶—重返法蘭西
代序一 逝者如斯夫?——人的存在與生命流的詠嘆
代序二 巴黎「自由談」沙龍紀要與述評:我們在哪裡,中國就在哪裡——政治學者吳國光提出「亞流亡」概念及對華人族群命運的思考
【第一編 思辨篇】
要民主主義,還是共產主義?——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悲劇啟示錄
極權中國的良心符號——劉賓雁
衝破思想牢籠,走出六四悲情——也談蔣彥永上書的思想內涵
中國知識分子應該懺悔——兼論知識階層依附性的惡果
最後的達賴喇嘛—— 一介僧侶對峙共產強權的神話與思考
西藏問題「回歸」...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收藏
收藏

 二手徵求有驚喜
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