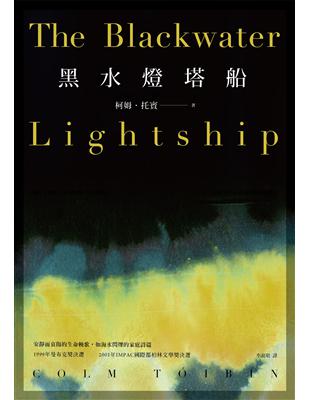「人世多苦難啊,我們都無可奈何。」
大師柯姆.托賓一鳴驚人成名作
安靜而哀傷的生命輓歌,
如海水閃爍的家庭詩篇
「這本小說探索了人們生存在清晰世界中的模糊感受。」
──重量級評論家 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
1999年英國布克獎決選
2001年IMPAC國際都柏林文學獎決選
※台大外文系教授曾麗玲_專文導讀
一九九○年代初期的愛爾蘭,罹患愛滋病的男子狄克倫將不久於人世。他終於打破沈默、決定將病情告訴自己的姊姊海倫,並表示希望從都柏林回到外婆在家鄉黑水鎮的房子靜養。二十年來,海倫與她的母親莉莉、外婆朵拉早因為種種心結避不見面,如今狄克倫返鄉養病,家族中的三代女人才重新聚首。狄克倫的兩個同志好友保羅和賴利,也一起來到濱海的房子裡,加入這群女人之中,共同照料病痛中的狄克倫。這一段回家的時光,窗外的海水依然堅硬孤獨,但當他們不再沈默,才逐漸化解了彼此間的冷漠和恩怨。
本書是托賓第四部長篇小說,一九九九年出版後,贏來廣泛的國際聲譽,並入圍英國曼布克獎決選。他卓越而靈巧的文風此際已展露無遺,閱讀它就像一腳踏進愛爾蘭的家庭生活。此外,全書背景設定在愛爾蘭同性戀除罪的九○年代初期,作者勇敢碰觸愛滋病議題,從個人、家庭到政治面去勾勒他心目中的當代愛爾蘭社會,也因此《黑水燈塔船》在托賓歷年作品中有著最強烈卻最自在的感受。這是一部情感豐沛的小說,在安靜而哀傷的輓歌式故事中,傳達出「家」的複雜關係與愛的本質。縱使韶光易逝,人生無常,家永遠是家。
「與其說《黑水燈塔船》是一部典型的LGBTQ小說,倒不如說它也是一部重省(愛爾蘭)『母親』角色的小說。在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中,母親經常被視為受苦的、被殖民的愛爾蘭的象徵,這本小說由性取向酷異的男同志族群取代,不啻是托賓頗具當代性的願景。托賓全書以近似海明威風格的散文體,即去蕪存菁、不濫情聳動、但鏗鏘有力的文采,勾勒出他心目中擁有跨性別與跨世代的新愛爾蘭,洞穿秘密與創傷之後的療癒,才是『家』之所在。」
──台大外文系教授,曾麗玲,摘錄自推薦序《黑水燈塔船──跨性別與跨世代的創傷療癒》
作者簡介:
柯姆.托賓
COLM TÓIBÍN
一九五五年出生於愛爾蘭。著有九部長篇小說,三度入圍布克獎決選,包括處女作《黑水燈塔船》、《大師》、《馬利亞的泣訴》,其中《大師》榮獲IMPAC國際都柏林文學獎。《布魯克林》榮獲柯斯達文學獎。另有兩本短篇小說集。
托賓作品授權超過全球三十多國,內容多描繪愛爾蘭社會、移民生活,探索角色個人認同、性別認同。先後在史丹福大學、德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以及曼徹斯特大學教授寫作。定期為《倫敦書評》、《紐約書評》、《倫敦書評》供稿,撰寫時事及文學評論。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多年後,於二○一七年起接任利物浦大學校長。
譯者簡介:
李淑珺
台大外文系畢業,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碩士,英國劍橋大學,蘇格蘭聖安德魯大學進修。曾任新聞翻譯,於實踐大學教授翻譯課程,現為自由譯者,專職翻譯書籍,譯作橫跨心理學,文學,建築,藝術,歷史等範疇。
譯作累積二十餘種,包括《與切.格瓦拉的短暫相遇》、《波特貝羅女巫》、《滅頂與生還》、《幸福的托斯卡尼花園》、《時間不等鼠》、《瑞普利遊戲》、《哥白尼博士》、《克卜勒》、《牛頓書信》、《躁鬱奇才》、《巫婆一定得死》、《非零年代》、《神奇城堡》、《巧奪天工》、《心理治療的道德責任》、《生命的哲思》等。
譯者email:sarali@aptg.net
各界推薦
得獎紀錄:
1999年英國布克獎決選
2001年IMPAC國際都柏林文學獎決選
《紐約時報》《泰晤士報》暢銷榜
名人推薦:
「《黑水燈塔船》絕非狹隘的作品。托賓在意的並非簡單的對立,也不企圖追求這類主題敘事普遍會有的、顯而易見的解套,他敏感而睿智地利用這個令人尷尬的情境,以大師的筆觸描繪出當代愛爾蘭在個人的、家庭的,跟政治上的演變。《黑水燈塔船》同時是一部成熟的,哲學的作品,在對話、內省與客觀的敘事之間巧妙地轉換游移,令人連想到維吉妮亞.吳爾芙的《航向燈塔》,而本書的書名肯定也企圖向之致敬。托賓看似模稜兩可的哲學與對他筆下角色的感受專橫權威的刺探,更讓人想起早期的艾瑞斯.梅鐸,兩人有著一樣的尖酸而幽默。這部小說肯定的東西也許很少,除了海倫一生都將愛與失落適得其所地連結在一起之外。但是它詩意的憂鬱卻是誠實又老練的,也確認了托賓的文壇地位。這部作品值得你的注意,更值得你的喝采。」──理查.康寧(Richard Canning),《獨立報》(Independent)
「以托賓的優異與犀利,他絕非那種平凡說教的作家,只懂得將一切複雜事物包裹成一個溫馨的訊息。反而書中每個角色所作的妥協都是困難的、片段的,遍佈舊傷口。這是一部狡猾的小說;它以簡單的開頭引誘你,逐漸擴展到形成一個複雜的故事,跟托賓處理過的任何故事同樣複雜。人物的描寫是不完整的,解答也是如此;托賓有種技巧,總是站在後頭,讓讀者陷入先入為主的評斷,然後他再將之推翻。但也就是這種不加評斷與沈默的技巧將這部小說提升到超乎平凡的境界。」──貝拉.巴瑟斯特(Bella Bathurst),《格拉斯哥前鋒報》(Herald, Glasgow)
「閱讀這部入圍布克獎的小說的樂趣之一,是觀察柯姆.托賓如何發揮他的寫作技巧與才華。他揭露了愛爾蘭的家庭生活,那是由罪惡感跟糾結的愛編織起來,交雜著義務與沈默的網,透過卓越的文筆來呈現。書中狄克倫的病形塑出戲劇張力,並迫使情節前進,灼熱的傷口交錯著辛辣的黑色喜劇,但心理上的核心地帶卻是女性之間的憎恨與敵意。托賓刻劃出鄉村生活的緊密,讓讀者對此有更深刻的了解,更強烈感受其中的侵犯性,街坊鄰居對左鄰右舍的窺探,帶來道德上的幽閉恐懼。他的寫作方式宛如在夢遊間徹底的警醒,特別挑出真正重要的細節來描述(描述態度與姿態,而非外表上的細節,讓每個角色栩栩如生)。他對所有人的同理心,既尖銳又溫和,一針見血地描繪出他們的缺陷,以及足以扳回一成的優點。在托賓的多部小說當中,《黑水燈塔船》擁有最強烈卻最自在的感受,毫不誇示而自由的對素材的運用。閱讀它就像是一覽無遺愛爾蘭的生活,但除去了其中的喧譁騷動與嘻笑怒罵。」──湯姆.艾達爾(Tom Adair),《蘇格蘭周日報》(Scotland on Sunday)
「托賓的《黑水燈塔船》是布克獎最後入圍名單中最完美的作品﹍設定在今日愛爾蘭的,安靜哀傷的輓歌式故事﹍他的文風簡約而靈巧,而書中充滿了各個角色對其他角色透露的,令人著迷的故事。」──保羅.李維(Paul Levy),《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媒體推薦:
「令人震驚的寫作,抒情的情感,簡約的結構﹍托賓雕琢出一部不可錯過的傑作。」──《周日先鋒報》(Sunday Herald)
「托賓以他情感豐沛的編排,顯現自己是個不可多得的作家。海倫與她母親跟外婆都已經形同陌路,托賓─以美麗的方式幫助她們達成和解。」──《周日電報》(Sunday Telegraph)
「他的文筆簡約而力量強大,而且他對家庭關係刻畫入微,因此閱讀他的故事有時候會讓人感到難以想像的痛苦。但這真是一部美麗的小說。」──《貝爾伐斯特新聞報》(Belfast News)
「我們將在二十年內持續閱讀黑水燈塔並生活其中。」──《周日獨立報》(Independent on Sunday)
得獎紀錄:1999年英國布克獎決選
2001年IMPAC國際都柏林文學獎決選
《紐約時報》《泰晤士報》暢銷榜名人推薦:「《黑水燈塔船》絕非狹隘的作品。托賓在意的並非簡單的對立,也不企圖追求這類主題敘事普遍會有的、顯而易見的解套,他敏感而睿智地利用這個令人尷尬的情境,以大師的筆觸描繪出當代愛爾蘭在個人的、家庭的,跟政治上的演變。《黑水燈塔船》同時是一部成熟的,哲學的作品,在對話、內省與客觀的敘事之間巧妙地轉換游移,令人連想到維吉妮亞.吳爾芙的《航向燈塔》,而本書的書名肯定也企圖向之致敬。托賓看似模稜兩可的哲學與...
章節試閱
她外婆坐在窗邊。在來自海上的蒼白光線消退,而陰影加深時,海倫專注地看著這個老婦人;她看著她的白髮與長而瘦的臉孔。她外婆開口時,那聲音尖銳而堅決。
「我看到你們從車上下來時,」她對保羅說,「我看到你的時候,心裡對自己說───又來了一個。」
「外婆,你在說什麼?」海倫問她。
「你明知道我在說什麼,海倫,」她說。
「她是在說同性戀,」保羅說。
「外婆,你不應該這樣講別人。」
「我看到他下車的時候」───這老婦人講話的樣子像是在自言自語,像要努力記起什麼事───「大概是他走路的樣子或轉身的樣子,然後我想,他現在是過什麼樣的生活,當什麼樣的人。」她抬起頭,看著房間對面的海倫。
「現在這個時候,我們所有人都很難過,」海倫說。
「他們會很難過,海倫,而且永遠都會。」
「我想她還是在指同性戀,」保羅說。
「嗯,我很幸福,」賴瑞說。「我在這裡不太幸福,但我的人生很幸福。」
「『幸福』,這個字眼很蠢,」保羅說。
沈默在此刻籠罩下來。他們四個人就在幽暗中坐著,而燈塔開始發出光芒。她外婆望向窗外,彷彿聽到聲音或什麼人接近。然後她回頭面向房間裡面。「海倫,我老了,我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海倫明白了她還是會怕她的外婆,也明白她無法對抗她或違逆她。她看著房間對面的她,知道這老婦人看不出她的厭惡或憎恨。她外婆轉向保羅跟賴瑞,她的兩個客人。
「狄克倫從來沒告訴過我們他的事。我們一直以為他在都柏林過得很好。沒有人知道他生病,也沒有人知道他是你們這種人。」
她有一會兒沒說話,但很顯然她只是停下來休息一下,才有力氣說接下來要說的話。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我已經知道一年了,但是我沒有告訴任何人,沒說任何話。狄克倫去年夏天來過這裡。他把車停在很遠的地方,所以我沒聽到車聲,但是因為某種原因,我還是走到巷子去,望向懸崖的方向,然後看到他向我走來。他一定是經過屋子前面,沒有叫我,又或許他是從麥克.雷蒙的房子那邊下去,然後經由海灘走過來。他朝我走來,但他並沒有預料會見到我,大概也不想見到我,我想如果我沒有出來到巷子時,他就會經過我的房子過門不入。我從之前那個聖誕節後就再也沒有看過他了,而且我想他也超過一年沒來過這裡了。當他走向我的時候,我看得出來他先前哭過,而且他好瘦好陌生,像是他根本不想見到我。他一直都是很親切的人,從小時候就是這樣。所以他進來屋子以後,就努力想要彌補。他一直微笑,開玩笑,但是我永遠忘不了看到他的樣子。他在這裡喝了茶,而我們兩個都知道一定出了什麼很可怕的事,很糟糕的事。我知道他有了麻煩,但是我壓根不會想到愛滋病,我什麼壞事都想到了。」
海倫在燈塔啟動時的昏暗中屏住呼吸。她不懂為什麼她外婆從沒跟她說過。
「我知道狄克倫來過這裡,」賴瑞說。「他以前常會單獨開車離開都柏林,通常是去威克洛,去山上;他會沿著公路開好幾英里。他也開車去過威克斯佛好幾次,去他母親的房子,但每次時間都很晚,所以他從來沒有進去過。我猜他希望她會發現他,就像你一樣。但是他始終沒有見到她。然後他又會開回都柏林。」
「我知道一定會發生什麼事,所以我一直等著,」戴沃荷太太說,彷彿她剛剛根本沒有在聽。
海倫希望她外婆不要再說了,於是她對賴瑞跟保羅發問。「你們都知道自己是同性戀嗎?」她問他們。
「講這件事,比經歷這件事更難。」
「繼續說啊,」保羅說。
「反正,我就站在那裡,我母親一直問我到底有什麼事,但是我說不出口。我父親坐在沙發上看著我,好像覺得我瘋了。我明白我對我母親可能說不出口,但我對我父親是絕對不能說的。所以我說我需要跟我母親獨處一下。我父親說他可以出去,但是我叫他不要出去,因為我相信他一定會遇到有人看到我在電視上。或者他會去酒吧,然後發現真相。」
「你兒子其實是個女生,」保羅說。
「你閉嘴,保羅,」賴瑞說。
「所以發生了什麼事?」海倫問。
「他走去廚房,我卻還是說不出話,於是我母親看著我,突然說:『你想加入愛爾蘭共和軍』嗎?我簡直不敢相信。你可以想像我加入愛爾蘭共和軍嗎?我想愛爾蘭共和軍裡從來沒有來自圖拉摩的人吧?他們都是無聊透頂的人。我說不是,然後我就告訴她了。」
「那她說什麼?」海倫問。
「她說無論我做什麼,我永遠是她的兒子,但是她要我立刻回車上,開回都柏林,由她來應付我爸爸,然後她晚一點再打電話給我。她迫不及待地要我出去。她臉色蒼白,一臉憂慮。我想如果我是加入愛爾蘭共和軍,她還會比較高興一點。」
「別這樣說,」海倫說,「事實不是這樣。」
「好吧,這樣說對愛爾蘭共和軍不公平,」賴瑞說。「我想她只是很震驚,很意外。你知道,在我們家裡,我的兄弟姊妹們───甚至包括那些已經結婚的───都還沒告訴我父母說他們是異性戀。我們從來不談性。她後來對這件事很貼心,到現在也還是接受,但是我爸就跟以前一樣,看到我只是咕噥一聲。如果我真的加入愛爾蘭共和軍,至少我們有話可說。會比較正常。」
「所以你跟保羅是伴侶?」海倫問。
「他嗎?你開玩笑吧,」賴瑞說。
「鐵定是發瘋了,」保羅說。
「你是說跟你在一起嗎?還是跟他在一起?」海倫問。
「跟他在一起,」保羅說。「又或許跟我們哪一個都是。」
「所以你有伴嗎,賴瑞?」海倫問。
「你說嘛,賴瑞,」保羅說。
「我有,海倫,」賴瑞說。「但是我無法跟你多說。」
「說嘛,賴瑞,」保羅說。
「我相信戴沃荷太太已經不想聽了,」賴瑞說。
「喔,不用擔心我,」老婦人說。「沒有什麼事會讓我震驚了。等你們像我經歷過這麼多事,世界上就沒什麼你沒聽過的事了。」
「奇怪,在黑暗中講這些好像比較容易,」賴瑞說。「感覺就像去告解,只是告解廂裡不會有燈塔。」
「快說吧,我們都在等,」保羅說。
「我們待會再來聽保羅的,」賴瑞說。
「跟他們說那件事,」保羅說。
「如果我講得太囉唆,就阻止我講下去,」賴瑞說。「我小時候,跟我們家隔幾個門,有一個大家庭。他們家有五個女孩子,四個男孩子。我爸媽跟他們的父母是朋友。他們家的父母信教很虔誠──父親是文生.德.保祿慈善會的會員,母親老是把九日經掛在嘴上。他們都是很親切的普通人。他們最小的兒子住在都柏林,我現在就跟他在一起。我們已經在一起好幾個月了。唯一的問題是,我也跟另外三個人在一起,我是說另外那三個兒子。其中兩個人結婚了,但是這似乎不影響他們。很有趣的是,他們全都不一樣。最年輕的那個真的很棒。」
他說完時,大家一片沈默。海倫可以看到窗戶透進來的些許光線痕跡,但是此刻房間裡已經完全黑暗了。
「他們是很棒的一家人。一定是基因的關係,」保羅在幾分鐘後說。
「關鍵確實在他們的基因裡,」賴瑞說。「但也在他們的褲子裡。」
「這下我真是什麼事都聽過了,」老婦人說。她的聲音很僵硬,也不必要地很大聲,彷彿在跟某種崇高的力量說話。「他們四個人!顯然你找到對的一群人了。」
「我想我媽現在已經夠心煩了,」海倫說。
「我說過你不會想聽的,戴沃荷太太,」賴瑞說。
「喔,你最好守護好你的心,這是我給你的忠告,守護好你的心,小心你自己。」
就在這時候,燈打開了,海倫的母親站在門口。「你們幹嘛全都坐在黑暗裡?」她問。
海倫眨了下眼,遮住眼睛,抵擋刺眼的電燈光線。
「狄克倫剛吐了,但是沒有太嚴重,」她母親說。「我已經清理乾淨了,沒事了,但是我想他現在可能睡了。希望是睡了。你們全坐在黑暗裡,到底在幹嘛?」
「我們在聊天,莉莉,我們在聊天,沒發現天都黑了,」外婆說。
「我走進來的時候你們在說什麼?」海倫的母親問。
「我剛好在跟這幾個男孩子說,現在這麼困難的時候,有他們陪真的很好,」外婆說。海倫看到她把臉轉向賴瑞,彷彿要示意他別想反駁她的話。「我剛才就是在跟他們說這個,莉莉,」她說。
老太太這時候站起來,望向夜色’之中。她把椅子往後拉,然後開始慢慢地拉起窗簾,直到賴瑞過來幫她。他接近她時,她舉起一隻手像要打他。他笑著閃開。
※※※
大約八點時,狄克倫跟她母親回來了。海倫透過餐廳的窗戶,看著她扶他下車。她跟保羅走到前門。
「他想去廁所,」她母親說。
「之前有什麼問題嗎?」保羅問。
「之前都沒事,一直到我們開車回來時,他才在車上吐了。」
「我來清理,」保羅說。
「抱歉了,保羅,」狄克倫說。他開始步履蹣跚地爬上樓去廁所。
「今天真的很讓人難過,海倫,」她母親說。「我們先前講的那間房子跟花園,都是我老早為他計畫好的,希望他週末過來,對這裡感興趣。他只來過一次。但是他今天都看到了,而且他真的好好。我帶他去辦公室;重新整修後都還沒看過。我得去交代一些下禮拜的事。」
狄克倫對著樓下叫說他需要乾淨的內褲跟衣服,他母親就去拿了。海倫還在驚訝當中,幾乎是震驚,震驚她母親剛剛對她說話的口氣,那樣毫不猶豫的坦白與親密。那種感覺就像是嚐到你長大後就再也沒有吃過的東西,或者聞到你已經二十年沒有再碰到的味道。那帶來焦慮,同時也帶來安心。
在廚房裡,她外婆坐在窗邊往外看,兩隻貓坐在她膝上。牠們一看到海倫就立刻跳起來,坐到餐具櫥上方,儘管之前賴瑞一直都在房間裡。
「有些人喜歡貓,貓也喜歡有些人,但兩者不見得一樣,」她外婆說。
「你在威克斯佛有買什麼東西嗎?」海倫問。
「喔,我們現在什麼都有新鮮的了,新鮮的麵包、新鮮的雞蛋、新鮮的魚跟新鮮的肉。全都在超市買的。在回來的路上,我跟賴瑞說:『我們簡直可以說我們就住在海邊的農場上。』」
保羅進來,站在門邊。「狄克倫說他想去巴利康尼格散步一下。他說他想乾脆一次吐光算了。他媽媽要一起去。」
賴瑞跟海倫決定他們也一起去散步。
「跟他們說我會待在這裡,」戴沃荷太太說,「還有問他們晚餐要吃鮭魚還是羊排。要跟他們說每樣東西都是新鮮的。」
狄克倫說他應該吃不了多少,但他想試試看鮭魚。這老太太過來看海倫、她母親,還有狄克倫坐上狄克倫的車,然後賴瑞跟保羅坐進賴瑞的車。她對著在院子裡迴轉的他們揮手。
「海倫,」她母親從車後座說,「我希望你叫她好好照顧自己。就算只是裝個管用的電話,這種小事也會有很大的改善。」
「我丈夫說我們家的女人都說不通的,」海倫說。
「他又不認識我們,」她母親說。
我跟他說過你,」海倫說。
突然間,她抬頭,在後視鏡裡看到她母親的臉;她的眼睛似乎放大了,顯得毫無防備而脆弱,緊張地看著她。她有一秒鐘真的很想減速,也許是後照鏡讓她母親的眼睛看起來像那樣,或者當她直視著她的眼睛時,也會是這個樣子。但是海倫再抬頭看時,她母親已經低下眼睛。
他們抵達巴利康尼格並在停車場停下來,賴瑞跟保羅停在他們後面的位子。他們下了車,走過那座小小的木橋,在已經消退一半的光線中往南走。塔斯卡燈塔已經開始啟動,他們站定,看著一道族轉中的光束朝他們而來。
「以前這裡曾經有兩座燈塔,」她母親說。「我不知道另外一座要用來做什麼,但是我猜那時候愛爾蘭海面上很忙碌,而且有些地方很危險吧。它就在那邊───不,在更北一點,往庫許跟你外婆家的方向。海倫,你記得嗎?」
「我記得,媽,但那是我們小時候的事。」
「愛爾蘭燈塔委員會把它除役了。我不確定是什麼時候,」她母親說。
「它叫什麼名字?」保羅問。
「它叫黑水燈塔。它的光線比塔斯卡弱。塔斯卡建在岩石上,所以比較耐久,我猜。但是我還是喜歡有兩座燈塔。我想可能是科技進步了,而且也許現在航行的船也沒有以前多了。黑水燈塔船。我以為它會一直屹立不搖的。」
他們慢慢地走向巴利伐魯。海倫緩緩靠近她母親。其他三個人往前走,賴瑞跟保羅當中夾著狄克倫,默默地保護他。海倫注意到那燈塔的光束都不會按照她計算的時間照過來。每次她算得太早。
「我小時候,躺在你外婆的房子裡時,」她母親說,「都一直相信塔斯卡是男的,而黑水是女的,而且它們都在對彼此,也對其他燈塔放出訊號,就像求偶的叫聲一樣。他強壯而強硬,她比較柔弱,但也比較穩定,而且有時候她會在黑暗真正降臨之間就開始發光。我總是覺得它們在互相召喚,那讓人覺得好滿足,他那麼強壯,而她那麼忠誠。你可以想像嗎,海倫,一個小女孩躺在床上想著這些?結果根本不是這樣。你知道,我本來以為你爸爸會永遠活下去。所以我學到了非常慘痛的教訓。」海倫往下看時,才發現她母親緊握著拳頭。「我真希望此刻能在這裡見到他,你知道,見到你爸爸,一分鐘也好。即使他只能在這裡的海灘跟我們擦身而過,在這裡,現在,在黑夜快來的時候。不用說話,只能用他的眼睛看到我們。我真希望他能知道,或看到,或用他的眼神肯定我們身上發生的事。這都是我胡言亂語,別理我,但是我每次看著塔斯卡燈塔時,都會想到這些。
「我們應該回去了,」她母親繼續說,「我想大家都餓了吧,我跟狄克倫今天過了漫長的一天,我相信你們也是。」
他們五個人回頭,走向那條每年都會在沙地上改變河道的小河。此刻海灘上已經沒有別人;對散步或游泳的人而言都太晚了,所以停車場上只有他們的車。海倫很意外狄克倫要跟他朋友一起坐,而讓她單獨跟她母親坐一輛車。他一定跟他們的媽媽談到了她的事,她想,他一定在試圖讓他們和解。現在她們在一起了,海倫想,但是真尷尬。她發動車子,然後等賴瑞的車子發動。她緩緩開在他的車後面,大燈全開,在夜晚逐漸降臨時往庫許開回去。
他們一回到家,海倫就變得煩躁不安,想著能否找個藉口,現在就開車回都柏林。她母親散發出全新的柔和態度讓人不可能抗拒。她覺得她母親正等著再度接近她,帶著撫慰的聲音跟自然親近的口氣。她受不了。她拿了狄克倫的車鑰匙,溜出房子,開進黑水鎮。
她在村子裡的公用電話亭撥了修夫的號碼。他母親接起電話時,感覺海倫要修夫來聽電話的口氣格外緊急,於是她立刻叫他過來,完全沒跟她寒暄。
「都還好嗎?」修夫問。
「不,不好。我好想離開這裡。」
「狄克倫還好嗎?」他問。
「沒什麼變化。」
「孩子們都睡熟了,」修夫說。
「我沒跟你去真是瘋了。我再也不會這樣了。我以後再不會這樣丟下他們。」
「海倫,只有幾天而已。」
「你怎麼知道他們是不是還好?」
「我當然知道,」修夫說。「他們很好。他們很開心地在度假。他們知道很快就會看到你了。」
「我爸爸生病的時候,他們也都覺得把我們丟在這裡沒關係。」
「這有很大的差別,」修夫說。「我是他們的爸爸,我跟他們在一起。你講得好像我不存在的樣子。我整天都看著他們啊。」
海倫聽著,沈默不語。
「你需要做的,」修夫繼續說,「是想像多年前,如果你爸爸跟你們在一起的話,會是什麼模樣。而且你跟兩個孩子講話時也不要流露出很擔心的樣子,不然他們也會擔心。他們現在無憂無慮。而且如果有任何問題,我都會告訴你的。」
「也許我擔心的是我自己。也許我只是不敢告訴你這一點。」
「我一直都在這裡,如果你要我下去,我隨時都可以下去,即使只去一天也行。」
「最糟的是,我媽現在對我好溫柔。」
「這聽起來是好消息。」
「不要把每件事都說得這麼好。」
「那你要怎麼辦?你要留下來嗎?」
「我會再待一天,」她說。「我早上再打給你。跟你講話真好。」
(未完待續)
她外婆坐在窗邊。在來自海上的蒼白光線消退,而陰影加深時,海倫專注地看著這個老婦人;她看著她的白髮與長而瘦的臉孔。她外婆開口時,那聲音尖銳而堅決。
「我看到你們從車上下來時,」她對保羅說,「我看到你的時候,心裡對自己說───又來了一個。」
「外婆,你在說什麼?」海倫問她。
「你明知道我在說什麼,海倫,」她說。
「她是在說同性戀,」保羅說。
「外婆,你不應該這樣講別人。」
「我看到他下車的時候」───這老婦人講話的樣子像是在自言自語,像要努力記起什麼事───「大概是他走路的樣子或轉身的樣子,然後我想...
推薦序
導讀
《黑水燈塔船》──跨性別與跨世代的創傷療癒
◎曾麗玲 台大外文系教授
托賓完成於1999年的小說《黑水燈塔船》,雖以一位年僅27歲、罹患愛滋病三年、疾病已屆末期的狄克倫為核心人物,但小說更細寫由於男同志的罹病而牽扯出一家人祖、母、女三個世代之間二十年懸而未決的情結與衝突。小說採取第三代女兒海倫、也就是男同志狄克倫唯一的姊姊、第三人稱的敘述觀點,讀者透過她的見聞與回憶得知她與母親、母親與外婆有著世代傳承喪失男性親人的創傷,以及這三位女性即將面臨家中另一位男性親人、即狄克倫的病體將要逝去、正要發生的創痛,故小說除了直接呈現同志族群於九○年代初愛爾蘭的處境外,更明顯是想藉機將傳統的母親與家庭角色做「酷兒」(queer)式的翻轉與「歪讀」(queering)。
愛爾蘭於一九九三年將同性戀除罪,《黑水燈塔船》剛好也將故事背景設定在同年(小說以賴瑞及其他男女同志受到當時愛爾蘭人權女總統瑪麗.羅賓森在總統府的接見、吸引大批媒體關注愛爾蘭即將更動法律,來暗示此重要事件),除了反映九○年代承襲八○年代愛滋病流行高峰的實況外,應該更是呼應並傳達愛爾蘭社會對即將緩步追上此股政治正確脈動的同志族群的新觀感。小說裡的同志主人翁平常獨自生活在都柏林,並與居住在歐洲其他大都市如布魯賽爾的同志朋友交好,所以,小說呈現的同志新景象是以(大)都會為中心的,也就是說,托賓這本小說與其他美國、歐洲同性質的LGBTQ(指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酷兒/性身份疑惑者)小說擁有相似的物質條件觀。不過,有趣的是,托賓讓都會的新同志族群與愛爾蘭在這本小說以燈塔船為表象的海邊偏鄉背景產生衝撞,因為當主人翁狄克倫病重在都柏林入院治療時,他透過也是同志的密友保羅接洽大他三歲、平時疏於聯絡、也住在都柏林、擔任一所綜合中學校長的姊姊海倫,並表達他的遺願,希望能回到外婆臨黑水鎮、位在庫許鎮海邊的老屋,並與在另一城鎮(威克斯佛)獨居的母親重聚,還希望由姊姊海倫向她們宣布狄克倫患有愛滋病的消息。於是,小說便是藉由狄克倫與看顧他的兩位友人保羅與賴瑞之間並無血緣關係但卻情濃於血的友情,來對照狄克倫與海倫兩姊弟他們與原生家庭家人的隔閡。
例如,小說令人動容地描寫著保羅嫻熟地處理狄克倫因嘔吐、在床上腹瀉而需要更換衣褲、床單的需求,他獨攬此看護、甚至清潔的工作,連狄克倫的母親與姊姊也只能作壁上觀,目視保羅無微不至地照護狄克倫無助的病體。另外,保羅在與海倫分享他發覺自己同志身份認同的心路歷程時,提到他的同婚伴侶馮斯華曾說過欲領養狄克倫為他們的義子,在他們布魯賽爾的住家常準備一套睡衣提供狄克倫療癒情傷時過夜用,這些情節都是托賓利用同志族群建立另類的「家」與家人,藉之挑戰異性戀家庭結構的手法,職是,《黑水燈塔船》在此主題上的鋪陳與LGBTQ文學寫作的要旨若合符節。
雖然小說故事發生的年代為愛爾蘭剛通過同志除罪的一九九三年,但愛爾蘭人對同志接受的程度其實還非常有限,小說裡清楚地傳達即便在法律修改過的此時,愛爾蘭人風聞同志議題時,比聽到愛爾蘭共和軍(IRA)一向惡名昭彰的恐怖活動還令人畏懼的情形,這是當眾人坐在日暮時、逐漸暗去的客廳裡,賴瑞對著海倫及外婆陳述,他雖然想趁著社會觀感有所改善之際,意圖向母親出櫃,但無論如何話仍是說不出口,此時,他母親解讀兒子支支吾吾的狀態是他想加入愛爾蘭共和軍而不敢承認,賴瑞感慨的說「如果我真的加入愛爾蘭共和軍,至少我們還會有話可說,那會比較正常」,托賓此舉其實正式將恐同的議題與愛爾蘭恐怖主義劃上(令人錯愕但也無奈的)等號,也同時鋪陳同志=犯罪=他者這一連串等號背後所透露出的愛爾蘭國內政治與道德二層面複雜的問題性。
除了同志議題外,《黑水燈塔船》還鎖定愛爾蘭社會裡另一顯著的「他者」──女性。與其說《黑水燈塔船》是一部典型的LGBTQ小說,倒不如說它也是一部重省(愛爾蘭)「母親」角色的小說。小說利用海倫受弟弟之託,不得不與母親、外婆重聚,而逐漸披露貫穿在三代母女間一直無法言喻的創痛,面對創傷,海倫慣性反應就是沈默與噤聲,但由於弟弟與其同志友人另類替代家人的新連結,顛覆了性別與異性戀家庭結構的刻板印象而得到釋放。原來,二十年前海倫母親莉莉需在都柏林看顧罹癌入院的丈夫,將不知情的兒女海倫與狄克倫安置在海邊外婆家達三、四月之久,但莉莉的丈夫終告不治,當莉莉再與兩個子女相聚已是在丈夫的喪禮中,海倫無法接受父親過世的事實,更心驚於母親在喪禮中「莊嚴而遙遠」、及「高傲」的姿態,從此與母親形同陌路,早早離開後來也被母親迅速賣掉的老家,獨自到都柏林求學及就業,就連與修夫結婚、生了兩個兒子,都與母親再無聯絡,獨居在另一城鎮、但本身也是職業婦女(她擔任威克斯佛電腦有限公司的執行長)的母親當然也從未見過女婿及外孫。小說藉由照顧生病丈夫、但仍無從挽回丈夫性命的母親莉莉二十年後的告白,揭露在愛爾蘭文化裡女性普遍需承受的性別包袱。莉莉與其母親都是早年就喪夫的寡婦,莉莉最後終於對海倫坦承,當她從都柏林回到一家人位在安尼斯科息的舊居時,因她無力保住丈夫性命而感到內疚、且因自己成為失敗的配偶而感到羞恥,這番糾結、更毋寧是創傷,當然是當時只有十一歲的海倫無法感同身受的,莉莉可以說是從那個時候就壓抑、拒絕承認她喪偶悲傷的真正原因,其實與社會對於女性做為配偶及母親多所期待、而她因不稱職而犯了這個社會的大不諱息息相關,而海倫也自絕於了解母親沈默的真相,兀自陷溺於失去父親的沈痛之中,多年來只知道以避免見到彼此、也就是以更多的沈默及空白,做為母女倆封存創傷的唯一憑藉。
非常具有基進意義的是,《黑水燈塔船》安排讓狄克倫的男性友人釋放海倫母女三代的噤聲,讓她們有機會坦承過去對彼此的不諒解,這是托賓具有關鍵性的性別翻轉策略──父權社會習於讓女性消音,但在這部小說裡,男性反而促使讓順應社會期待、被動的女性角色得以發聲,所以,溫柔照顧著狄克倫宛若其母的保羅,其實積極扮演著催生解開海倫與莉莉禁錮情結的助產士的角色。母親的角色在十九世紀末即開啟深具民族主義色彩的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Celtic/Irish Literary Revival)裡經常被視為受苦的、被殖民的愛爾蘭的象徵,但在托賓這本小說裡,由性取向酷異的男同志族群取代長期獨佔象徵愛爾蘭的母性天職,不啻是托賓頗具當代性(相對於崇古的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的願景。托賓在《黑水燈塔船》裡以近似海明威風格的散文體,即去蕪存菁(spare)、不濫情聳動、但鏗鏘有力的文采,勾勒出在他心目中(如果仍有民族主義傾向的)新愛爾蘭「國」家的形象,那就是擁有跨性別與跨世代的、能被如(曾一度屹立的)「黑水燈塔船」所發射燈光洞穿秘密與創傷之後的療癒,才是愛爾蘭國「家」之所在。/完
導讀
《黑水燈塔船》──跨性別與跨世代的創傷療癒
◎曾麗玲 台大外文系教授
托賓完成於1999年的小說《黑水燈塔船》,雖以一位年僅27歲、罹患愛滋病三年、疾病已屆末期的狄克倫為核心人物,但小說更細寫由於男同志的罹病而牽扯出一家人祖、母、女三個世代之間二十年懸而未決的情結與衝突。小說採取第三代女兒海倫、也就是男同志狄克倫唯一的姊姊、第三人稱的敘述觀點,讀者透過她的見聞與回憶得知她與母親、母親與外婆有著世代傳承喪失男性親人的創傷,以及這三位女性即將面臨家中另一位男性親人、即狄克倫的病體將要逝去、正要發...
購物須知
關於二手書說明:
商品建檔資料為新書及二手書共用,因是二手商品,實際狀況可能已與建檔資料有差異,購買二手書時,請務必檢視商品書況、備註說明及書況影片,收到商品將以書況影片內呈現為準。若有差異時僅可提供退貨處理,無法換貨或再補寄。
商品版權法律說明:
TAAZE 單純提供網路二手書託售平台予消費者,並不涉入書本作者與原出版商間之任何糾紛;敬請各界鑒察。
退換貨說明:
二手書籍商品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二手影音商品(例如CD、DVD等),恕不提供10天猶豫期退貨。
二手商品無法提供換貨服務,僅能辦理退貨。如須退貨,請保持該商品及其附件的完整性(包含書籍封底之TAAZE物流條碼)。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
退換貨原則、
二手CD、DVD退換貨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