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现代人对别人和自己的变幻莫测的心灵世界,产生了越来越浓烈的兴趣。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人的心理活动是“地球上最美的花朵’。人们由关注故事型小说、以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转向关注心理型小说,以获取人的内心世界的信息,乃是一种合乎规律的转变。西方小说理论家奥泰迦说得十分明确:刻板的写实本身是不会吸引我们的,单纯的模仿就更不会使人感兴趣;而真正能够吸引我们的是“想象的心理活动”,是小说人物的“虚构的内心世界”。而中外许多作家也日渐意识到,研究和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是小说家的首要任务,也是作品吸引读者、震撼读者心灵的重要途径。如印度心理小说家阿葛叶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缩小了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却把人们心灵的距离拉开了,而文学可以沟通人间的感情”。所以他强调现代小说要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描绘,要有意识地让读者观赏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变化过程。
由于心理小说的内容,侧重于表现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即包括意识与无意识两方面的各种心理要素的组合及其演变过程,因此,作家的表现手法必然随之而更新。意识流、内心独白、心理分析、心理时伺、时空交叉等等艺术手法,就是心理小说家为了表现特定的心理内容而精心设计的;没有这些必要的、特定的手法,心理小说的内容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真实、生动的体现。
确实,心理小说是小说艺术发展的产物,是一种崭新的小说形态。它适应于人们认识自身的需要,适应于现代社会审美观念的新变化。不过,心理小说与传统小说各有自己的地位与作用,彼此只能互补,而不能相互取代。心理小说的长处,果然弥补了传统小说的短处;而传统小说的长处,恰恰是心理小说难以克服的短处。这种互有长短的现象,是不容置辩的客观事实。况且,现代小说的读者群是十分复杂的,审美层次是大相径庭的,他们的审美需要也是无限多样的。因而心理小说和其他小说样式一样,只享有周存共荣的权利。
詹姆斯对自己所找到的这一叙述方法无疑是十分欣赏的,他后期的作品越来越精心于观察角度的选择,《梅西所知道的》、《使节》,都是体现这一创作原则的杰出样板。而当他的18篇序言问世以后,“意识中心’成了现代小说理论家最为关心的问题,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小说叙事艺术的最佳模式。平心而论,这一叙述方法在忠实、客观地反映人物复杂心理经验方面,确有其长处,能给读者带来一种生动、自然的逼真感;但如果刻意追求,就会走向反面,精细的内心观察与感受将会牺牲在“高妙莫测”的祭坛上,使读者不胜重负。经过20世纪意识流小说家的挖掘与扭曲,“意识中心”说更富有深度,同时也陷入了歧途,便是一个明证。
总而言之,詹姆斯是一位建立了一套明确小说理论的杰出作家,他对心理小说传统作出的贡献是卓著的。诚如他的传记作者里昂·埃代尔所说的:“他使整个‘小说之家’秩序井然。”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他的理论过于讲究“井然的秩序’,为小说创作设置了众多条条框框,就显得呆板而缺乏灵气。这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他的创作——当詹姆斯刻意求工时,文体就难免做作。同时,他从自己的理论角度出发衡量同时代作家的创作实践,有时会欠公允。例如,他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为大而无当的怪物,事实上,这两位大师的作品,是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两座高峰,他们所达到的高度,是詹姆斯无可企及的。
在英国,女作家多萝茜·理查森(1873—1957)是这种创作新趋向的第一名开拓者。她在1915年至1938年间接连出版了十二卷本系列小说《人生历程》。这部小说也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故事情节,直接记叙了女主角米丽安·亨特森流动不已、飘忽不定的情绪和感觉,她对周围人与事的主观印象;外部世界只是为人物丰富而旺盛的精神变化提供诱因和原料。作家在序言中说,她要用一种“女性现实主义’来反对巴尔扎克、贝内特为代表的“男性现实主义”,“只要求被沉思默想的现实一独立发言”,以“发现个人思想和信仰的真实”。也即是说,她要表现的是人物意识活动本身。
多萝茜·理查森自以为是小说技巧革新中的一个“孤独的探索者”,回首一瞥,却惊喜地发现自己仅是采用意识流方法创作的“一群人中的一个’。这一群人的代表,在英国,便是詹姆斯·乔伊斯与弗吉尼亚·沃尔夫。
乔伊斯在1916年完成了艺术手法从传统到革新转变期的作品《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以后,在1922年和1939年分别发表了《尤利西斯》和《芬尼根们的觉醒》,把意识流方法“推到了顶峰”。
沃尔夫的艺术实验从短篇小说开始。写于1917年的《墙上的斑点》,堪称意识流短篇名作。1922年出版的《雅各的房间),是她用意识流方法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沃尔夫在《日记》中谈到这部小说的创作计划时,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一种崭新的形式:“没有框架.,几乎看不到一块砖头;一切都朦胧莫辨,但是心灵、激情、幽默,所有这一切光亮耀眼,犹如雾霭中的篝火。”①如果说,这是沃尔夫创作新试验的开端,那么,而后出版的三部小说:1925年的《达罗威夫人》、1927年的《到灯塔去》、1931年的《海浪》,不断强化意识流表现手段,作家独特的文学风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通常被称为“典型的意识流小说”。
在美国,威廉·福克纳于1929年与1930年接连出版了《喧哗与骚动》与《我弥留之际》。两部小说均以时序颠倒、多角度叙述、内心独白等手法,深刻地发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为作家赢得了“意识流大师”的称誉。
普鲁斯特、乔伊斯、沃尔夫和福克纳的上述作品被公认为意识流小说的“经典著作’,也是这一创作流派进入全盛时期的标志。然而,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从全盛到衰落,几乎没有时间的间隔。40年代初,这一流派就自然而然地解体了。那些“正宗”的意识流小说,也就只是作为历史的过去而被载入文学的史册,成为高等学府的教材,专家学者们研究的对象。虽然它的影响并没有烟消云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种现代主义创作流派风起云涌,意识流作为一种艺术手法,被各派作家广为吸收,并且超出了小说领域,进入戏剧、电影各个部门,丰富着对人物进行心理剖析的手段。但是,很少有作家再用纯粹的意识流手法来进行创作了。 为什么意识流小说显赫一时,却又衰落得如此迅疾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直接的原因,是由于它的晦涩朦胧,并且往往不惜用冗词赘句来铺张篇幅,令人读来不仅索然无味,甚至不堪消受,难以卒读。究其根源,问题还是出于意识流小说家的真实观上:过分的偏向于表现内在的心理真实,而忽略了、乃至摒弃了对心外世界的描绘,最终把文学技巧的变革试验推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超越了合理的范围,从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也走到了尽头。应该承认,早期的意识流小说尚有一定的可读性。一般说来,这些小说还没有脱尽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对于人物和事件,还保留着某些客观描述,还赋予人物一定的性格特征;记录人物意识流动的轨迹,也是从人物经由外界事物所获得的印象入手,可以找到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并不过于散乱;整部作品的主题与寓意也比较明确。但是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开始,包括沃尔夫成熟期的三部作品,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都越来越超乎现实。为了最大限度地揭示所谓的心理真实,他们人为地隔绝了人物与客观现实的联系,任凭主观意识自由流淌。生活的历程,现实的遭际,都被人物内心深处错乱而复杂的感受与无意识的冲动所取代;并且不惜用神秘莫测的梦幻语言和象征主义手法强化人物的非理性意识。在无穷无尽的任意性后面,存在着怎样的一种秩序?“意识流”和“生活之流’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一种关系?扑朔迷离的意象中蕴含着怎样的一种寓意?一系列谜点和难题都留待读者自己去发掘、解答。而读者阅读这样的作品,就像闯入一座没有任何路标的迷宫,除非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和理解力,加上反复研读的高度忍耐力,一般人是难以走出迷阵的。无法读通、读懂,当然也就谈不上品味与欣赏了。就如乔伊斯在给朋友所写的信中说:“我在书中留下了许多谜和难题。这些谜和难题究竟用意何在,这将使教授们忙碌几百年,而这正是一个作家得以永垂不朽的惟一途径。”对乔伊斯作品争论之激烈,确是堪称世界之最,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与评论他作品的书籍足可摆满一个图书室。然而晚年的乔伊斯,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试验是该偃旗
息鼓了,转而打算“写一些非常简单又非常短小的东西”。
常言道曲高和寡。一种艺术样式“高深”到“叵测’的地步,要靠专家学者潜心研究诠释去破译谜点难题,普通读者就必然只能望而生畏、敬而远之了。而一部作品如果只能供少数人摆弄,失去了基本的欣赏者,不能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读者群,它的存在价值势必大大降低。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生产媒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
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生产与消费的一般规律。它适用于物质生产与物质消费,同样也适用于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之间的关系,便是这样一种辩证关系。生产媒介着消费,艺术创造不仅生产出消费的对象——作品,而且生产出能消费它的主体——“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另一方面,消费媒介着生产,艺术欣赏实现着艺术创造。这是“因为只是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就像“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能成为现实的房屋”一样,一件艺术作品只有通过欣赏,才能成为有价值的艺术存在。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恐怕没有什么事情会比读者不想读完他的作品更令他烦恼、痛苦了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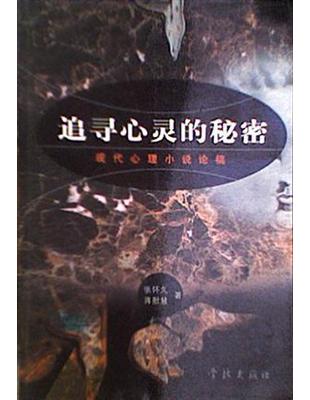


 收藏
收藏

 二手徵求有驚喜
二手徵求有驚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