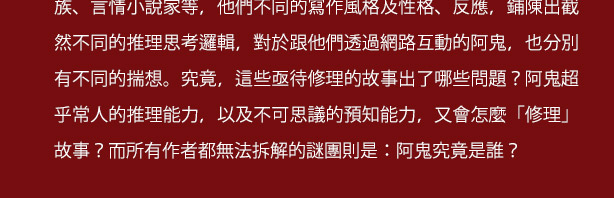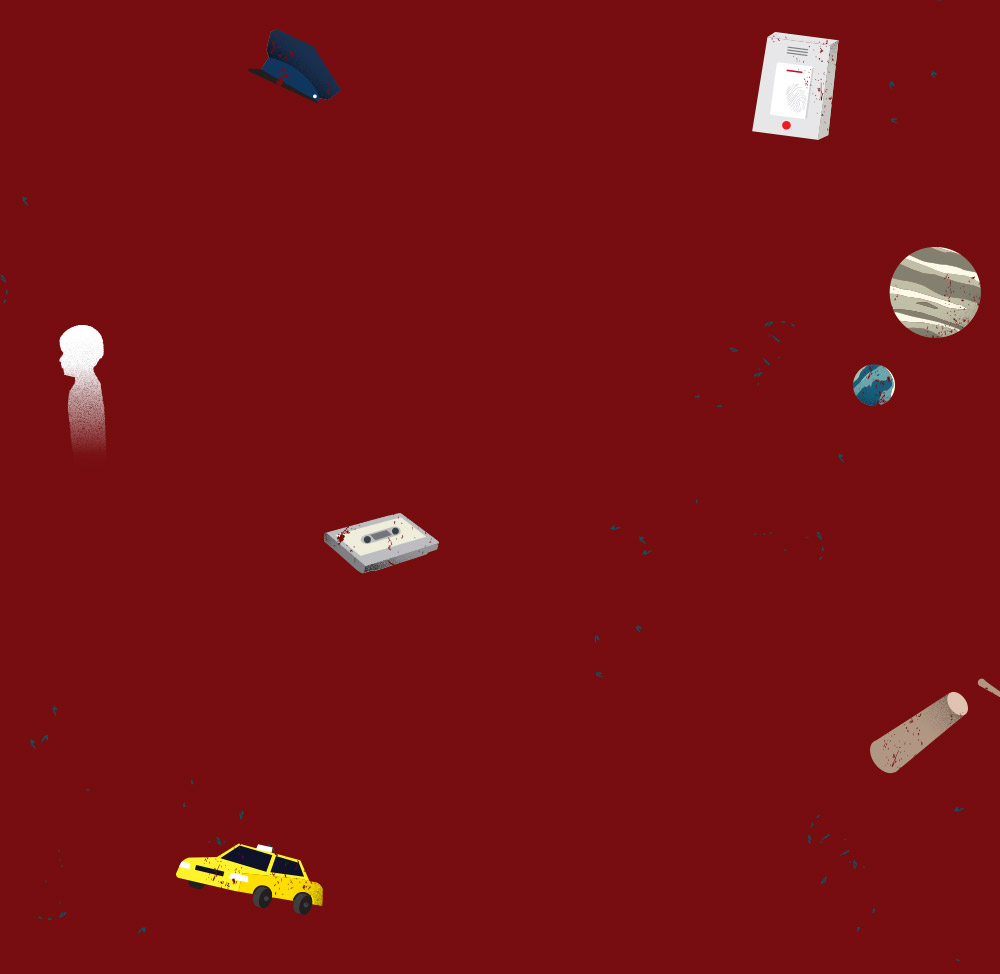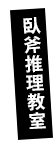FIX:修理、補齊、校準,以及牢記
※本文涉及《FIX》情節及成書經過,請自行斟酌閱讀
近年有些公開談小說創作的機會,我大約都會從構成故事的五個基本元素講起;時間夠就多舉點例子、講細一點,時間不夠就列出元素、只講重點。倘若講的是「推理小說」創作,那麼對基本元素的認知就更加重要,因為推理小說的創作者有時太過執著於情節中的謎團安排,容易忽略其他元素設定,以致於在構成謎團、解釋謎團,甚或其他情節轉折的時候,出現生硬、不合理等等作者明顯介入干預劇情的狀況—對故事而言,這不是件好事。
不過,就我自己的經驗來說,創作技法的精進主要來自兩個部分,一是大量練習,二是大量閱聽—我喜歡從各式創作裡分析理解創作時的種種方法,不大喜歡只讀教條理論。
是故,我曾與編輯朋友聊過一個故事構想:某甲寫了篇小說想參加推理徵文獎,先找朋友閱讀,不同朋友指出小說裡與謎團無關的不同問題,某甲因而開始──補足或修改基本設定,最終讓小說變得完整。如此主軸,加入一些轉折設計,就成了一個「講創作的故事」,創作者可以從中獲得一些關於小說創作的討論,一般讀者也能讀到有趣的故事。
這構想當時也就是聊聊。原訂要寫的作品還在排隊,加上有時出現的稿約或合作計畫,公餘時間大致已經滿檔;這構想有趣,也有意義,不過當時認為暫時還不會用上。
二○一六年初,我寫完長篇小說《抵達夢土通知我》的初稿,正與衛城總編輯莊瑞琳討論修改細節;某日,瑞琳問我,有沒有興趣瞭解一下鄭性澤的案子?因為彼時這個案子重審的進度有點遲滯,而我對社會議題有一定的關注,如果能就這樁案子寫點什麼,或許能夠幫得上忙。
我憎惡冤案。冤案像是寫壞了的推理小說,硬把一個角色塞進犯人的位置,瞧著彆扭,讓人懷疑作者的智商、寫作技巧,以及被稱為「作者」的資格;更糟的是,冤案裡的「犯人」並非活在小說當中,無論面臨哪種他不該接受的刑罰,都會耗損、摧折他的真實人生。
日本曾任法官、現任律師的森炎,在他的著作《冤罪論》裡就簡單直接地指出:「冤罪是最大的不正義。」
鄭案是國內有名的冤獄事件,我先前已約略讀過相關紀錄,當然有興趣深入瞭解;問題是,實際事件的追蹤或相關人物的訪談,先前已經有不少資料,至於書籍,也已經有張娟芬的《十三姨KTV殺人事件》這本詳細、好讀,從不同角度切入討論的作品—所以,我還能做什麼?
雖然不確定自己究竟能幫什麼忙,但我仍經瑞琳介紹,與臺灣冤獄平反協會的羅士翔律師及臺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的林欣怡見面;討論當中,我提及因為日常工作的緣故,我的寫作時間有限,而且作品大多聚焦在小說,接著想起:或許我能做的,就是以小說描述這樁案子的疑點,例如鑑識證據的疏失,或者推理環節的問題?
士翔和欣怡都認為這個方式行得通,我們進一步聊到:或許我可以多寫幾篇,除了鄭案之外,再多談幾樁有爭議的冤案。
討論結束,瑞琳與我走向捷運站時,我突然想到:先前那個一直沒動筆的寫作構想,其實和這個合作計畫可以相互連結。
這樣吧;我站在路邊,把那個構想告訴瑞琳:我把實際案件的部分疑點,放進某甲的推理創作當中,再經另外一人指出它們。如此一來,這些短篇表層是推理小說,中層是講「怎麼創作」的故事,而底層則有呼籲讀者關注真實冤案的意義。
《FIX》裡的七篇故事於是如此開展。我希望盡量展現不同主角在不同情境下開始創作的經過、自以為沒問題實際上不對勁的故事設計,並以一個各篇主角都不認識的奇妙角色針對問題提出建議,最後一篇再揭露奇妙角色的真實身分。如此一來,每個故事都可以視為推理短篇獨立閱讀,合在一起讀到最後,也會有某種推理趣味。
〈敲木頭〉選擇的題材自然是鄭案;這樁案件的審理過程當中疑點甚多,創作時只聚焦在發生槍戰的KTV包廂中的鑑識證據處理過程,刑求及因刑求而產生的自白部分約略帶過。我挪用了歡快的爵士樂曲〈敲木頭〉為篇名,定下與實際案件沉重內幕截然不同的輕鬆基調,並且在其餘數篇裡維持相同氛圍—我希望讀者在還不知道實案內裡的時候,先以閱讀大眾小說的心情面對故事。
〈沒有你我無法微笑〉使用了后豐大橋墜橋案。這樁案件的調查過程乍看仔細但缺失不少,原來的墜橋悲劇,因而轉變成殺人案件。我在故事裡重新設定了相關角色的性別,挪用The Carpenters溫柔的曲名,敘述愛情關係裡的悵然。
〈英雄們〉選的是邱和順案。邱和順已經服刑多年,在退休警員出面表示當年曾經刑求取供之後仍未獲釋;寫作過程中,邱和順因故送醫急救,提供了這個故事發生的舞臺,我也把這件事寫進情節當中。篇名〈英雄們〉來自David Bowie的同名歌曲,歌詞中的「We can be Heroes, just for one day」常讓我有各種思索。
〈我們和他們〉原型是杜氏兄弟案。這樁案子發生在中國,是故牽涉到兩岸之間的敏感狀況,我方檢調並未拿到實證就緝捕了杜氏父子,杜父在漫長的訴訟期間過世,杜氏兄弟也在二○一三年遭到槍決。我讓故事主角從娥蘇拉‧勒瑰恩的科幻小說《一無所有》中得到相關靈感,並以Pink Floyd的〈我們和他們〉為篇名,凸顯在不同政治實體間跨國辦案時必須注意的問題。
〈大大的小黃〉談到林金貴案,著重在證人及證據可能隱藏的缺漏。Joni Mitchell的同名歌曲提供了角色身分設定及必要的情節元素,而當年因冤入獄的林金貴,被關押將近十年後,終於在二○一七年四月平反獲釋。
〈比蒼白更蒼白的影〉講的是謝志宏案,除了提到角色設定對情節的影響之外,也談到現實偵查當中不能完全倚賴證詞但卻常過度倚賴證詞的狀況。篇名〈比蒼白更蒼白的影〉取自Procol Harum的經典曲目,幽微隱晦的歌詞,很適合故事裡把祕密壓在心底的角色。
〈被感染的愛〉當中埋設的實案是呂金鎧案,此案最大的癥結在不夠嚴謹的法醫證據及粗心大意的證物保存。我篤信科學,但這份信任奠基在科學對各種細節存疑與探究的精神上,粗略的鑑識結果不僅缺乏專家應有的專業態度,也無助於釐清事實。The Four Preps的歌曲〈被感染的愛〉指出箇中角色心態,也指出在偵辦過程裡去除雜質的必要。
必須強調,《FIX》當中收錄的全是小說創作,雖然基底來自真實案件,但創作時並未納入所有偵辦過程的疑點,部分細節也在創作時做過修改。是故,倘若您在讀完全書後有興趣瞭解這些案子,理應查找實際資料,而非單看小說情節。
以我創作時查閱、研讀的資料判斷,這七樁案子無庸置疑,都是冤案。但《FIX》的創作初衷,除了提供閱讀樂趣、利用故事講述創作時該注意的事項及相關技法外,並非指出偵辦案件過程中種種有心或無意的疏忽,而是讓您關注這些真實案件。倘若您在自行參閱相關資料後,得出不同結論,那也沒什麼不好—我相信愈多人注意這些刑案、愈多人討論這些刑案,真相就愈可能被挖掘或拼湊出來,司法與檢調體系也愈可能更加完備。
士翔、欣怡,以及李佳玟、尤伯祥、邱顯智、涂欣成等律師整理的資料,在創作過程中提供了極大的助力;瑞琳、吳芳碩與甘彩蓉等出版社工作夥伴,也在初稿完成後提供了重要的意見;大家一起討論出書名之後,設計師廖韡做出簡約但充滿巧思的封面—《FIX》的成書,上述諸位功不可沒,在此致謝。
當然,我也要感謝七樁案件的受刑人。撰寫本文時,他們有的在多年牢災之後獲釋,有的仍在獄中等待平反,而有的已然辭世。入獄之前,他們並非全是安善良民,但入獄之後,他們全因自己沒犯的罪狀受苦。他們的際遇黯淡,但卻是映照出系統漏洞的亮光;我誠摯地希望,《FIX》可以讓更多人開始審視這些洞孔,將我們的社會制度朝更完備的方向推進。
「FIX」這個單字,指的既是故事裡對創作者的「修理」,也是對故事的「校準」與「補齊」,同時,它還有「牢記」的意義—透過觀察、思考、書寫以及閱讀,作者與讀者可以一起從現實穿行到虛構之境,並且將在該處獲得的體悟與感想,帶回現實,面對世界與自己。
這也是「故事」最要緊、最無可取代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