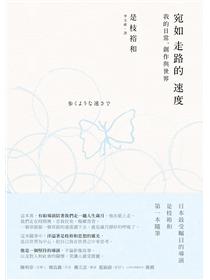「笑話只有好笑不好笑,
誰管他媽政治不政治,正確不正確。」
引人拆解,再三玩味,一頭霧水……
向文學大師、經典巨作致敬的奇異之作!
堪比《黑色追緝令》、《鬥陣俱樂部》;
荒誕可笑之中埋藏大疑問,
真正的哲學,藏在低俗笑話的背後。
「笑話,尤其是真心好笑的那種,不是左派就是右派。」好友板哥的這番話,讓專為教科書編寫笑話的出版社職員也開始為所有笑話分類。最後面對好友的死亡,他唯獨在意的是:他上吊時頭是往左偏,還是向右擺?死亡,要算是左派還是右派呢?……
新銳小說家羅士庭以八則風格各異的短篇故事向品欽、愛倫‧坡等文學大師致敬,我們將在書中看見當今難能可貴的、只有羅士庭能寫出的荒誕幽默,同時又有讓人屏息的淒美與絕望。他的文字像是一幕幕節奏緊湊的短劇,翻開第一頁,就只能任其揪著我們的衣領奔過快速輪轉的場景,在惡趣味橫飛、線索橫溢(卻未必有意義)的故事中,一邊陷入瘋狂,一邊嘴角失守喊過癮。
(別再問封面的倒楣老兄是誰,天知道!)
文壇齊推
吳明益(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李依倩(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副教授)|專文作序
李奕樵、沈嘉悅、邱常婷、林育德、馬翊航、陳夏民、葉佳怡、顏訥|不俗推薦
這本小說裡的寂寥、荒謬、笑鬧與哀傷(這些實質「長」在他身上的事物),是士庭該寫下去,你應該打開的理由。作為一個具有天賦的年輕寫作者,他選擇在形式上跟諸位小說家致意,但實質內容已在向自己的人生致敬、迴響,這是我看好士庭的原因。
──吳明益(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惡俗小說》可以視為某種士庭在經典文學課後開設的私人講座,和我們當年在講桌前拼起來的四張課桌椅不同,士庭的講座是座寬廣無邊際且時空多元的迷宮、遍布插曲、軼事、笑話、譬喻、典故、哲思的奇花異草;到處都像是出口,每個角落都可能藏有線索或寶物。
──李依倩(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副教授)
因為羅士庭,研究所時我第一次知道何謂天才。天知道作為他的同學,我們等這部作品多久了。
──邱常婷(作家)
本書特色
1.《惡俗小說》取名自昆汀‧塔倫提諾的經典電影 Pulp Fiction(指通俗、低俗、媚俗的廉價小說。台譯片名為《黑色追緝令》)。羅士庭以這本短篇集向多位文學大師、經典巨作致敬,卻也充分展現他獨特且幽默的敘事魅力。每篇故事都暗藏符號,引人無限猜想,讀著讀著,彷彿也能見羅士庭賊笑又帶點肅穆地,在向遠方的致敬對象們行禮。
2.〈淺色的那條〉獲聯合小說新人獎評審獎、時報文學獎小說評審獎。
3.吳明益:「如此這本小說已顯露羅士庭作為一個年輕小說家的數種可能性。」
作者簡介:
羅士庭
1987年生,花蓮人。清華大學電機系肄業,東華大學華文所創作組畢業。作品曾獲聯合小說新人獎評審獎、時報文學獎小說評審獎、臺中文學獎小說組佳作。其餘作品散見報刊、《創世紀詩刊》、《力量狗臉》詩刊等。
章節試閱
〈維也納的死亡與慈悲〉
有段時間我十分熱衷於收集笑話。那是因為我在任職的教科書出版社負責了一個新企劃,要在每個學習單元末的一方小框框裡寫上一個輕鬆的笑話,給學生調劑調劑。主編和召委願意將這個神聖的工作委派給我令我非常感動,這無疑是全書最富有教育意義的篇章,所以我非常認真從事,還隨身帶著錄音筆和一本紅皮小記事本,狂熱到了逢人就問有沒有新笑話的地步。
板哥告訴了我一個右派的笑話。笑話是這樣的:去年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把他抓進去體檢──他的原話如此。也就是說,這個笑話一開始就注定不可能放進教科書裡了,我們得避開有政治傾向的用語。除此之外,這個笑話也太長了,我得分五個單元連載,這在教科書笑話學界可是前無古人地大膽。組長表示──他是教育學碩士,對於教育心理還有孩童成長學什麼的十分內行──我們要考慮學生的記憶能力,以及將他們的注意力引導到正確的方向,笑話只是知識的延伸,得做到不偏不倚。
對此,板哥嗤之以鼻:「笑話,尤其是真心好笑的那種,不是左派就是右派。不信的話,你褪褲襤看看自己胯下的小指南針好不好笑?」
「那它指向北邊的時候怎麼辦?」
「你是不會倒立嗎?」
就組長的觀點而言,笑話不過是昆蟲的觸角,像是蟑螂鬚之於蟑螂。作為政治主體,蟑螂那往前方未知世界的觸鬚探索當然是種政治行為。只可惜蟑螂非常對稱,既不左也不右。(板哥反駁:「見你個鬼,你下次仔細看,共產黨的蟑螂只爬左傾的水溝。」)這是昆蟲的優點,牠沒有辦法政治化;也因為相同的緣故,根據板哥的分類學,昆蟲天生就不具笑點。
言歸正傳,板哥繞過幾道排著長長人龍的關卡,專挑沒幾隻菜兵的隊伍。他找上一個滿臉豆花,臉色臭得像是便祕了一個禮拜的醫官。醫官要他伸出腳來,踩在一個小木盒上頭驗足弓的角度,他不鳥指示,逕自伸出左手,舉到醫官面前甩了甩,秀出一截斷指──板哥五歲的時候,有次在家裡的工廠玩耍,不幸當場被液壓機輾碎了一截左手食指。從此他玩剪刀石頭布永遠只出右手。
醫官滿臉不耐,拿出手冊翻出規章,指著上頭的規定逐行解釋給他聽:按規定,除非斷了任一手指的兩支指節以上,又或者斷的是右手食指第一指節,否則皆不算免役體位。
板哥抗議:「為什麼有左右手的分別?這是歧視。」
醫官解釋:「國軍規定,射擊時要用右手扣扳機;你沒辦法扣扳機,我們才會判定無法服役。」
「如果我是左撇子呢?」
「一樣。規定要用右手開槍。」
「規定就是規定?」
「法律是這樣說的。」
「國家法律規定我們只能用右手殺人?」
話說到點子上了,醫官避而不答,不耐揮揮手要他快閃。
「所以那天我發現了一個天大的祕密,」板哥湊近我,神祕地說:「原來我們的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是個不折不扣的大右派!」
右派的笑話到此為止。但更好笑的在後頭:後來板哥走回量測身高體重的隊伍中,五分鐘後,他因為體重過輕驗退了。
我們笑得前仰後合,又劈啪開了兩瓶啤酒,攪得滿嘴口水泡沫。啃泥跟著忘情地狂吠起來。大約三、四年前──那時我和板哥還住在一起──一個大雨的大半夜裡,板哥像是冷戰片裡的間諜一樣,乒乒乓乓地撞開家門,懷裡抱著一隻烏克麗麗大小的小黃狗,一人一狗都濕到了骨子裡。喇叭裡Kenny G(啃泥的名字就是這麼來的)的薩克斯風吹到最高潮,啃泥聽見了,像是接上插頭似的忽然電力飽滿,在板哥的懷裡奮力掙扎,和他濕答答的毛衣摔角。我們花了好大力氣,她才稍微安生,滿地泥水狗毛。停戰後,雨也停了,於是兩人一狗一起出門吃了早餐。上下左右不知哪戶的鄰居傳來抗議聲,板哥甩上窗戶,我們繼續歡了半小時。忽然有人摁門鈴,一位管區員警上門關切,他拿出分貝計,板哥卻對著儀器呼氣,又在阿Sir耳邊咯咯笑著,不知道說些什麼。我簡直快笑瘋了,阿Sir只能無奈地繼續道德勸說。臨走前,板哥大聲說了個一百零八分貝的笑話──這是個大家都聽過的三字笑話,笑點在於說笑者本身之自我實踐精神的自嘲。
阿Sir豎起眉毛,或許在考慮要不要發作。
「阿Sir啊,你說講笑話犯法,這就不對了嘛。講笑話妨害安寧,那發明笑話的不就是恐怖分子?」
板哥斜睨了我一眼,我冷汗直冒。我算個啥?現行犯,預備犯,還是思想犯?
「我跟你說,這屋子裡犯法的只有一個人。」他舉起左手食指,瞇起右眼,準備用不存在的指節扣下不存在的扳機。不知為什麼,一瞬間大家都被那不容質疑的模樣說服了。砰。「那個人妨害自由。他妨礙我們慢性自殺的自由。」
*
我點開檔案,如果說笑是種慢性自殺,那錄音檔裡頭的吃吃竊笑聲無疑像是某個前一晚吃壞肚子的三流小提琴手拉出的安魂曲前奏。小蕙第七次皺著眉頭起身,走進茶水間的陰影中,啪答啪答,外頭下起了大雨。錄音第八號,一個四處尋找愛情的少年變成了驢子,最後愛上了胡蘿蔔的故事。這是個爛笑話,但我還是笑了。只要看著小蕙的剪影,我就會忍不住笑出聲來,不知道是因為某種制約反應,還是我自己體質敏感。
小知識(收錄於國二下健康教育):絕大多數的人沒有辦法搔自己癢,聰明的你知道為什麼嗎?因為啊,我們的腦袋裡頭有個模擬自體反應的系統,在搔自己癢時,系統預先模擬了即將到來的搔癢感,從而發出訊號抵銷了強烈的笑意。
對於職業逗自己笑的人來說,這知識真令人消沉。
小實驗:試著搔自己癢試試看。接著再和鄰座的同學互相搔癢。觀察並記錄結果。
有時我會想,如果能把小蕙偷渡進教科書裡就好了,有了小蕙大家都能心情愉快。但事情可沒那麼簡單。
請問要怎麼把長頸鹿放進冰箱裡呢?
第一步,把冰箱打開。第二步,把長頸鹿放進去。第三步,關上冰箱。
排容定理,高二下數學課程,大考命題率一顆星。這個笑話還有後續:
請問要怎麼把大象放進冰箱呢?
第一步,把冰箱打開。第二步,把長頸鹿拿出來。第三步,把大象放進去。第四步,關上冰箱。
許多學生經常忘記把長頸鹿拿出來,即使我們打上了星號,又換了五種科學證明能有效引起注意的色號,依然有人忘記。我想這是因為他們青春期的冰箱裡早就塞滿其他的東西,動輒得咎,所以既拿不出長頸鹿,也放不下大象。言歸正傳,我沒辦法把小蕙放進教科書,是因為我沒辦法把既存於教科書裡頭的小蕙拿出來,當然也放不進真正的、好笑到不行的小蕙。版權頁上的美術編輯小蕙就像是豌豆公主──床下的豌豆。
我打開休憩區的冰箱門,茫然頹坐,想像躺在床上的豌豆,和躲在床墊下的公主。寬闊的床面就像片無邊寂寞的,只停了台孤伶伶小車的停車場。掉了鑰匙的公主無法離開,在午夜倒數的同時躲著哭花了她的妝。我張開大口試著笑出聲來,壓縮機猛地轟隆運作,掩蓋住我的笑聲。
七點半,板哥打了電話給我。我嗯嗯喔喔了兩句,斜對面的組長投來懷疑的眼色。雨還在下著。八點,我抓準一個所有人都低著頭的時機悄悄摸出公司,臨過打卡鐘,忍不住回頭瞥了小蕙一眼。她看起來一臉幸福,右手支著額頭,左手在繪圖板上無意識地摳挖,鏡片上跳動的光芒和眼神同步閃動。我嘆了口氣,她上禮拜才因為東憲歐巴失憶的衝擊導致潰瘍,照了胃鏡。而從她鏡片反光裡上映的最新一集進展看來,歐巴從九死一生的手術中活下來了。這會讓小蕙心情好上半天。但矛盾的是,這代表明天的編輯會議我八成得交白卷了。小蕙開心的時候,我連一個笑話的靈感也沒有。……
〈維也納的死亡與慈悲〉
有段時間我十分熱衷於收集笑話。那是因為我在任職的教科書出版社負責了一個新企劃,要在每個學習單元末的一方小框框裡寫上一個輕鬆的笑話,給學生調劑調劑。主編和召委願意將這個神聖的工作委派給我令我非常感動,這無疑是全書最富有教育意義的篇章,所以我非常認真從事,還隨身帶著錄音筆和一本紅皮小記事本,狂熱到了逢人就問有沒有新笑話的地步。
板哥告訴了我一個右派的笑話。笑話是這樣的:去年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把他抓進去體檢──他的原話如此。也就是說,這個笑話一開始就注定不可能放進教科書裡了,...
推薦序
【推薦序一】
俗聖並存的所在
◎吳明益(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但凡經過彆扭青春期的人都知道,有段時間我們會刻意擺出傲慢無視他人的姿態,但另一些時候,會自縮回自我的殼鞘之中,偶爾也會以自我貶抑來爭取認同或避免受傷。我一直認為,靠字面來揣測人的真實心意是困難的,特別是創作者。某個角度來說,創作者很像是永遠沒有離開過青春期,這類人的身上虛榮與懦弱並存,是孔雀和兔子的綜合體。
神祕又獨特的作家品欽(Thomas Ruggles Pynchon)曾在一九六五年寫給他的經紀人,宣稱自己正在寫一部「potboiler」(混飯吃,騙錢的)的小說。當時品欽已經寫出《V.》這部證明他的博學與奇特思考的傑作,這話當然不能直接理解他真的就是希望寫一部混飯吃的小說。如果你看過昆汀‧塔倫提諾的《黑色追緝令》(Pulp Fiction),當你從電影院出來時,很清楚地知道,這部Pulp Fiction並非等於Pulp Fiction,或者可以這麼說,昆汀.塔倫提諾讓我們見識到Pulp Fiction的力量。
我第一次讀到士庭的作品不是小說,而是在「論創作」(on writing)的課程裡,見識到他迴圈式的論述。往往你以為他準備放蹄飛馳,進行激烈的辯證,須臾定神,才發現實際上是在原點徘徊。他會自我設問,接著引用馮內果、費茲傑羅、《戀夏五百日》、《老人與海》、大江健三郎、《哈利波特》、愛特伍、《三國演義》……而後持續虛懸問號。有時候你甚至會懷疑,那些引用是必要的嗎?
不,這麼說並非貶意,我只是想說,士庭從一開始根本就是一個小說家,一個善於歧出、跑馬,善用離心力,跟你說想寫一部Pulp Fiction,實際上卻和品欽一樣,想寫的是裡頭「藏著大問題」的敘事者。
我第一次讀士庭的小說感到心動是〈他就這麼掉了下去〉。在這個故事裡,敘事者開著車來到了工業區,想起了一個家裡做大理石加工的國小同學,因此試探性地撥了電話。電話通了,名叫白告的小學同學在工廠門口迎接「我」。老同學見面第一件事是,打開門口那對石獅子眼睛的雷射光,兩人看著光爬過樹梢與天空。迎接「我」的還有重重往事,包括此刻已罹患肺腺癌的阿嬤、名喚波波的狗、一幢未完成的一○一大樓積木,以及他們都刻意不再提起的,一件關於「就這麼掉了下去」的事。
這篇小說敘事單純,可以看出士庭成熟的敘事與寫景功力。與其他刻意「擬仿」名家的作品相比,有著吸引我的質樸小說特質──我竊以為它暗示了一件事──士庭的本質可能是一個面帶憂容的說故事人,而不是他想要假扮的輕浮、媚俗的小說家。
我並不曉得為什麼士庭要宣稱自己寫了一本「惡俗小說」,我也很感好奇,士庭作為一個在虛榮與懦弱間擺盪的年輕作者(我不負責任地假設每個年輕作者都有一樣的經驗,就像每個人一定都要感冒過一樣),為什麼刻意在他的第一部作品,扮演「多面寫作者」的角色。
我一直認為,「多面寫作者」是對年輕作家的錯誤褒揚,一旦把時間軸拉長,你會發現很少作家真能多面,即使是士庭崇拜的品欽亦然。一個能長期寫作的作家通常在第一本小說就會顯露本質,一開始讓人炫目的面目,會在接續的作品裡褪去大半,唯有最後留下的那個本然面目,才能讓一個作家成為有風格的作家。
但士庭就是要在這本小說集裡嘗試各種寫法,他不避諱於使用品欽《維也納的死亡與慈悲》(Mortality and Mercy in Vienna)來做篇名,刻意也寫一個和「維也納」無關的故事來討論死亡。為了向羅貝托‧博拉紐(Roberto Bolaño)的〈克拉拉〉(Clara)致意,他寫了他的〈徐敏敏〉。而為了模仿「拿腔拿調」的複合句,我們讀到了〈技術施作細則〉……凡此種種都讓我很想再次問士庭(或也曾經這麼做的我自己),進行這些原作者不會知道的「致意」,是為了練習?像體操選手模仿對手高難度動作的炫耀與自信?還是有更深沉的什麼含意──比方說,那些作家沒有完成的,有一天由我來完成?問題是,在漫漫的小說史上,還有什麼敘事技術是沒有「完成過」的?
在「論創作」的課程裡,士庭後來寫了一封信來「論虛構」。他說:
沒有經驗絕非虛構之害,相反地,虛構反而能幫助真實輕盈。我曾經覺得,所有大作家的生命中都會遇到一件無論他的心靈如何巨大,總沒有辦法消化的大事件(通常是巨大的荒謬)。昆德拉遇到的是布拉格之春,馮內果則是二戰。當時馮內果淪為德軍的戰俘,被抓到德勒斯登一間屠宰場的地下室關起來。大轟炸後,他在嗆鼻的焚燒氣味中看見的是被聯軍轟炸過的整座廢墟,反射地笑了。我曾經不理解這個微笑,第一次讀到這裡的時候我十足覺得馮內果又在開玩笑了,怎麼可能?就像一位記者等了許久終於遭逢了夢寐以求的大獨家,他處理起來卻似乎不那麼莊重。直到幾年後我才明白,這個笑可能才是真的。馮內果插科打諢寫了整本書,種種怪力亂神、時空穿越云云,這些荒唐的虛構情事可能只是為了幫助這個微笑成立。當一個罹患創傷症候群的老人回想起往事──這些巨大的荒謬──他只能如此雜亂地錯置彼此的因果關連藉以稀釋傷慟,而當回憶走到他踏出屠宰場的第一步時,他再一次地「在場」,他還能怎麼辦?馮內果本人當時有沒有笑我們不知道,但小說人物的「再度在場」給了他一種後見之明的眼光,面對如此巨大的、無以抗力的荒謬,他當然只能笑了。這不「真實」嗎?
我在往返台北香港的飛機上,反覆看著這段話,它幾乎已經是從事小說創作的人遇到藐視虛構文類論述時回應、辯解的基本話語。不過我感覺裡頭似乎潛藏著遺憾:偏偏,偏偏我們這一代的小說作者,就是沒有在年輕時遇上這類「無法消化的大事件」。那麼我們的笑聲會不會變成是一種矯情?我們寫的虛構只是虛構?
我不禁想起這本小說集另一篇打動我的〈青春記〉。雖然士庭刻意用另一種「拿腔拿調」的語氣來敘事,卻有著「大問題」與「真感情」流動其間。那就是士庭在口試時提到的,關於他的父系家族從「大陳島」撤退的故事。那即使是間接聽聞的殘磚碎瓦,也會使得一篇作品有神。
在一次信件往返中,士庭提到這第一本小說是他的嘗試,有點像傑夫.代爾(Geoff Dyer)說的「看到好文章後,非得寫一篇回應它的衝動」產物,是對那些影響他的作家的回聲。我絲毫不懷疑這點,就像我並不懷疑士庭的才能,更不懷疑讀者能在這些不同類型的小說中,獲得閱讀的樂趣──這本小說已經顯露他作為一個年輕小說家的數種可能性。
這本小說裡的寂寥、荒謬、笑鬧與哀傷(這些實質「長」在他身上的事物),才是士庭該寫下去,你應該打開的理由。我一直認為,是寫作這個行為形塑了人、故事與哲學,卻不是一個人完成了生命、學會了什麼技巧或理解了什麼以後才去寫作。一個小說家在拓荒時最為迷人,成就後就只能走下坡了,不是嗎?
不過這數種可能性,最終得靠士庭找出一條真實之路。作為一個具有天賦的年輕寫作者,他選擇在形式上跟諸位小說家致意,但實質內容已在向自己的人生致敬、迴響,這是我看好士庭的原因。士庭說或許他還需要數十萬、百萬字的練習,才能進入寫作「大陳島」故事的狀態,我也把它當成是一種話術──因為我很明確地感受到,大陳島就是他未來寫作「無法消化的大事件」,不管是不是有讀者支持,他都應該試著往前走。
我想士庭一定知道,昆汀.塔倫提諾在當導演之前曾是錄影帶出租店的員工,在那裡,他完成了Pulp Fiction的熱身準備。(這世界上還有什麼地方擁有比錄影帶店更多的Pulp Fiction?)不過,真正讓他形成「內裡」的可是這個世界。
據說大陳島撤退之後,解放軍上岸只見到一個老人與一條狗,我想,這對年輕的小說家士庭來說,是個他不得不寫的理由。還有我在口試場上,曾聽他講述過的,壯麗又哀愁的海上賽鴿……只有我能寫這個、只有我看到這個,是每個年輕小說家走向第三本小說的重大動力。
我相信在完成《惡俗小說》後,士庭會繼續走向真正俗、聖並存的所在,那會是他成為小說作者的意義,也是你願意打開這本小說的意義。
【推薦序二】
課後私人講座
◎李依倩(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副教授)
初識羅士庭,是因為他和另一位同學想選修我在東華華文所開設的文學批評。課沒開成,但他們兩個還是積極地想學點什麼。我找了一位當時正準備寫碩論的指導生一起過來,在下午五點我某門課結束後,利用原教室進行私人講座。
說是講座,其實也不過就是講台前四張拼起來的課桌椅。前一堂課的學生離開沒多久,六點那堂他系課程的同學們就三三兩兩進來了。我們在前面討論羅蘭巴特的符號學原理,他們在後方或吃便當、或趴桌睡、或看書。我們聊得太起勁忘記時間,總有人會上前來口氣平和地說他們要上課了。
私人講座後那學期,士庭正式修習我所開設的敘事學,並成為我的指導生。接下來幾年我們舉行多次晤談,通常是請他和另外一兩位同學發表與評論各自的新作,短篇小說居多。
有件事始終令我困惑。士庭所發表的多篇小說,就像這本集子裡所顯示的:明明故事是他自己的原創,卻帶有某位名家的腔調(甚至某篇名作的輪廓):艾德格‧愛倫‧坡、羅貝托‧博拉紐、湯瑪斯‧品欽、朱天文……有時候,那語氣惟妙惟肖到令人懷疑這是不是影子寫手的職業訓練。
我其實挺羡慕士庭這種能力,因為這顯示他擁有敏銳的文字感知與強大的應用能力。透過這些習來的技法,文字像魔術師的球般在他指間靈活地滾動,變出一個又一個把戲。觀眾眼花繚亂,不知道球在哪根手指間,不確定總共有幾顆球;球有時在指掌間輪轉,有時似乎騰空,有時卻又消失無蹤。
某個時間點,我終於忍不住問士庭:「對你而言,文學是什麼?」
他用《惡俗小說》回答了這個問題。
透過對經典作品的學習與運用,士庭嘗試導演昆汀‧塔倫提諾式的「致敬」,一方面重新觸發經典所帶來的感動,另一方面探索什麼是他自己所特有的。
以致敬博拉紐〈克拉拉〉的〈徐敏敏〉為起點,旁及《惡俗小說》的其他短篇,我試著發掘什麼是士庭所特有的。雖然他應該比較希望讀者們將不同短篇各自獨立看待,但為了幫士庭的寫作勾勒出一些輪廓(這些輪廓是不是僅存於我眼中的幻影姑且不論),還是得穿梭與聯繫各篇作品,暫時把它們當作某種有機整體。
〈徐敏敏〉和〈克拉拉〉一樣,第一人稱男性敘事者與篇名女性維持時密時疏的關係、藕斷絲連的通訊,其中有著時空、心理、際遇造成的落差與隔閡。兩位女性都曾罹患身心疾病,歷經數度婚姻/感情波折;兩對男女的人生都在偶爾交錯、大多分離的情況下前進。
博拉紐的〈克拉拉〉簡潔流暢、彷若直白,羅士庭的〈徐敏敏〉繁瑣細緻,將各種不確定性擺上檯面,並帶有類比宇宙星辰的長串譬喻,以及即使得到正解也未必能接近「答案」的謎題。
〈徐敏敏〉和〈克拉拉〉一樣帶有懷舊基調,但《惡俗小說》中其他篇章也常回顧過往而非關致敬:〈青春記〉裡童年時的大陳一村、〈他就這麼掉了下去〉裡小學時的生活片段與事件、〈耳洞〉裡的數段戀情與搖滾明星生命史。
回望過往的段落常帶有溫情與感傷,細節豐富、場景鮮明:〈青春記〉裡榮民之家混置流刺和碎玻璃的矮牆、市場裡用竹枝棉線罐頭做成個小鑼吆喝的豆干小販、有著暈人黃燈泡和大雨鞋的豬肉攤/販;〈徐敏敏〉裡,喜宴上徐敏敏頭髮上的亮粉在霓虹燈的照耀下反射多彩燐光,像多年前第一人稱敘事者某夜在住處看見、也不知為何對徐敏敏提過的:中庭噴水池底L E D光線所投射出像是雪靜靜地由地面往天空下的景象……
懷舊的同時,《惡俗小說》還有著各種崩壞與墜落。多篇小說中人物或病或殘──身體的、心理的:〈徐敏敏〉裡女主角的自殘與子宮切除、某位朋友胰臟方面的罕見疾病;〈維也納的死亡與慈悲〉裡板哥爸爸中風、板哥斷指與自殺;〈技術施作細則〉裡科技廠員工吸入過量氯氣、〈耳洞〉裡搖滾明星嗑藥、殺人與自殺;〈淺色的那條〉裡「詩人」被診斷為人格解離妄想症;〈青春記〉裡爺爺的糖尿病與阿茲海默症;〈他就這麼掉了下去〉裡白告阿嬤和第一人稱敘事者姨丈的肺腺癌……
此外還有或許可視為某種崩壞的各種有形與無形的墜落:名為〈他就這麼掉了下去〉的那篇就不用說了:殭屍、一○一模型、大理石切片、小慧、白告阿嬤的塑膠湯碗還有阿嬤自己紛紛墜落;〈青春記〉裡的爺爺「漸漸掉進了奇怪的地方,先是身體,再來記憶,最後是年歲」;〈維也納的死亡與慈悲〉裡,第一人稱敘事者看著蹲跨在輸送履帶間的工人,想著「他們如果掉了下去……」;〈一個記憶中的場景〉裡,第一人稱敘事者處於掉進愛倫‧坡小說中的「可笑情境」。
在人事物陸續崩壞墜落的《惡俗小說》中,也有某些巨大、穩固、不可動搖的事物,姑且稱之為體制好了,像是〈淺色的那條〉的軍隊與〈技術施作細則〉的科技廠。小說中對這些體制不乏諷刺,但任何顛覆的可能都在其後各種如枝葉般蔓生的荒唐突梯中消解。在〈維也納的死亡與慈悲〉中,那些政治的、社會的、體制的與個人的,從頭到尾都是某種左派的或右派的笑話,沒有出路也沒有救贖。
那麼,在遍布崩壞墜落荒謬的《惡俗小說》各作中,讀者是否能尋獲某種主題或意義?不是不可能,但有點困難。士庭的小說中,場景與地點繁多且跳躍,時序通常混亂──在順敘、倒敘與凝滯間往返不定,情節常多線並行或交錯。清晰、明確而線性的故事主軸少見,但總有像是遍布於迷宮花園的分岔枝節,姿態各異、奇趣橫生;其下潛流的曖昧含混卻始終是難以掌握的,儘管某些篇章有著表面可解的謎團或看似結局/真相的末尾。
尤有甚者,故事中還埋藏著抗拒因果與意義的機制,像是層層疊疊的修辭、多重內外部互文或指涉(尤其是對近現代文學與文化的)、既像開放又似封閉迴路的哲學式思索、繁複而隱晦的譬喻、有如豎起「禁止進入」或「探究無益」警告牌的各種「無理由」標籤:〈徐敏敏〉中不明就裡的打火機交換儀式、敘事者不知所以的無對象憤怒、徐敏敏不知為什麼的簌簌發抖;〈一個記憶中的場景〉裡對圖書館結構的無來由領悟;〈他就這麼掉了下去〉裡不知為何建造的、眼睛會發光的石獅……
士庭這種對主旨、意義、因果的抗拒或「非必要」觀點,有時候或可由故事中第一人稱敘事者的口中反身映照,像〈一個記憶中的場景〉中:「我不認為每一篇小說都有,或都該有所謂的『中心思想』」、「人類的智力設計永遠也無法比及自然之萬一,偶然亦是美妙絕倫的。」
〈徐敏敏〉中,敘事者對徐敏敏言談方式的描述與評論:「她的語速愈來愈急,像是要填補這些年來意義的空洞」或是「她的思緒顯然陷入了最混亂的漩渦,許多地方含混不清,許多地方又觸目驚心地詳實」,似乎也可以用來側寫《惡俗小說》的部分特徵:不斷增殖但不知導向何方的敘事、細膩動人但卻未必有益於意義建構的諸多細節、像是要傳達什麼深奧哲理卻又混沌不明的思考與譬喻……
上述這種形貌的《惡俗小說》中,難道沒有流露一絲對所謂確定性、中心或意義的懷舊感?這些東西也都和歲月、情境、記憶、身體等一起崩壞墜落了嗎?抑或像〈他就這麼掉了下去〉所說的,我們還是「需要一個阻尼器,需要一顆鐵球穩住我們,否則下一個掉下去的就是我們」。
回到一開始的問題,在士庭這些常源自於向經典致敬的作品中,是否發展出什麼屬於自己特有的?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上述種種不僅是出自我的誤讀或建構。
到頭來,《惡俗小說》可以視為某種士庭在經典文學課後開設的私人講座,只不過現在他打開大門,歡迎大家一起來共學。
和我們當年在講桌前拼起來的四張課桌椅不同,士庭的講座是座寬廣無邊際且時空多元的迷宮,遍布插曲、軼事、笑話、譬喻、典故、哲思的奇花異草;到處都像是出口,每個角落都可能藏有線索或寶物。然而,訪者可能還是在迷宮中徘徊不已,或許是流連忘返,或許是兩手滿滿的寶物和線索,卻不知其各自意義、彼此關連與終極用途。不習慣這種小說/講座/迷宮型態的訪者,可能有點忿忿不平,覺得作者高高在上、睥睨眾生,自娛自樂地玩著凡人看不懂的戲法,在書頁間、講桌後或牆角邊嗤嗤低笑,嘲弄愚鈍的人們──雖然就我一向所看到或讀到的,我可以保證他絕對是謙遜誠懇的。
【推薦序一】
俗聖並存的所在
◎吳明益(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但凡經過彆扭青春期的人都知道,有段時間我們會刻意擺出傲慢無視他人的姿態,但另一些時候,會自縮回自我的殼鞘之中,偶爾也會以自我貶抑來爭取認同或避免受傷。我一直認為,靠字面來揣測人的真實心意是困難的,特別是創作者。某個角度來說,創作者很像是永遠沒有離開過青春期,這類人的身上虛榮與懦弱並存,是孔雀和兔子的綜合體。
神祕又獨特的作家品欽(Thomas Ruggles Pynchon)曾在一九六五年寫給他的經紀人,宣稱自己正在寫一部「potboiler」(混飯吃,騙錢的...
目錄
【推薦序一】俗聖並存的所在 ◎吳明益
【推薦序二】課後私人講座 ◎李依倩
維也納的死亡與慈悲
他就這麼掉了下去
徐敏敏
青春記
淺色的那條
一個記憶中的場景
耳洞
技術施作細則
【推薦序一】俗聖並存的所在 ◎吳明益
【推薦序二】課後私人講座 ◎李依倩
維也納的死亡與慈悲
他就這麼掉了下去
徐敏敏
青春記
淺色的那條
一個記憶中的場景
耳洞
技術施作細則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8收藏
8收藏

 10二手徵求有驚喜
10二手徵求有驚喜




 8收藏
8收藏

 10二手徵求有驚喜
10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