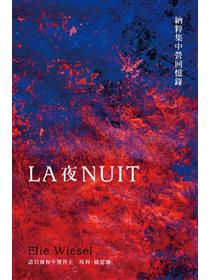◎「知日者」的日本文化物語北京上海廣州東京一路開專欄最有人氣的旅日華人隨筆作家居酒屋本來是庶民的小酒館。只要打出「居酒屋」的看板,就是為了號召大眾,排闥直入。價錢瞭然於胸,一樣的水酒,一樣的小菜,有如歸之感。自斟自飲,連明月也不邀,待喝出孤獨,便發現了自己的存在,唯我獨尊,達到獨酌的最高境界。李長聲旅日二十年,眼冷心熱看扶桑,動手動腳寫文章,大至中日文化比較,小至江戶糞尿浴桶骨壺掌故;遠至春帆樓歷史恩怨,近如地鐵痴漢小說。無不嫻於心,落諸筆下。此書輕鬆風趣,見多識廣,讀來如沐春風。茶酒伴讀,長夜一瞬,東方已白而不自覺也。◎名家聯手推薦茂呂美耶(作家)陳浩(『中天書坊』主持人)莊裕安(作家)楊照(作家、文化評論者)◎精彩內容摘錄東京有什麼好?到處是一樣的招牌,一樣的燒鳥或刺身,一樣燈火通明的「扒金庫」。但走在街上,也有我看見就要進的,那就是舊書店。日本人把散佈大街小巷的書店叫作「文化的街燈」,賣新書的書店是,賣舊書的當然也是,只是昏暗些。~〈文化的街燈〉落日是日本文學中常見的景色。小說家藤澤周平偏愛寫夕陽,或金光鋪滿原野,或又紅又大地掛在櫛比的房屋上,而人影是黑的,在餘暉中動搖。他記得自己小時候看著紅極了的晚霞而哭了起來。~〈日本海的落日〉同樣是凋零,櫻花被武士欣賞,山茶花卻遭到厭惡。因為山茶的花是整朵花「吧嗒」一聲掉下來,武士看著一激靈,好似被砍了頭,就覺著晦氣,以致現今人們也不拿山茶花探望病人。~〈路邊開著山茶花〉日本人吃魚,一生二烤,該丟不丟的用鍋煮,通常就是煮蘿蔔。蘿蔔怎麼吃也不會中毒,那就像拙劣的藝人再怎麼演也不會有人「中毒」,跑來充當她或他的追星族,此等藝人在日本就叫「大蘿蔔」。~〈別有風味蘿蔔泥〉
章節試閱
別有風味蘿蔔泥(1393)
我不愛吃蘿蔔。
周作人說︰「明人王象晉稱蘿蔔可生可熟,可菹可齏,可醬可豉,可糖可醋,可臘,乃蔬之最有益者。」雖然吃法多樣,但若天天多樣地吃,像東北改革開放前那樣,吃它一冬,不厭才怪呢。似乎清人李笠翁就不像周作人那樣覺得蘿蔔「頂有意思」,只寫到「生蘿蔔切絲作小菜,伴以醋及他物,用之下粥最宜。」糖醋蘿蔔絲,清涼爽口,用之最宜的是下酒,這倒是我向來對蘿蔔唯一能另眼看待的。現而今餐館把蘿蔔洗吧洗吧端上來給人懷舊,黑土地,大豐收,食客盡開顏,那是闊起來的意思——需要去油膩了——卻終歸一噱頭耳。
孰料,飛機一起一落來到日本,竟好似落在了蘿蔔地――走遍四島,種植面積最大的蔬菜就屬它,而且那愛吃勁兒,簡直是沒有蘿蔔不成席。日本叫「大根」,我國最古老的辭書《爾雅》裡面就有這個叫法。老早從中國傳來,被他們栽培出繁多品種,為世界之最,不過,東京的菜場裡常見的是又長又粗的白蘿蔔。我們東北也種的,它長出地面一大截,宛如章子怡露出凝脂的肩頭,人走進地裡絆絆磕磕,但趙本山的鄉親說話逗,卻叫它「絆倒驢」。(編按,趙本山,大陸著名喜劇演員,東北人。)
日本古時候用蘿蔔比喻美女的白皙,但後來人糞尿施得足了,越種越茁壯,就用來嘲笑女腿粗,險乎絆倒驢。日本人吃魚,一生二烤,該丟不丟的用鍋煮,通常就是煮蘿蔔。蘿蔔怎麼吃也不會中毒, 那就像拙劣的藝人再怎麼演也不會有人「中毒」,跑來充當她或他的追星族,此等藝人在日本就叫「大蘿蔔」。還有一說,說是江戶年間,農家挑擔子進城收人尿,報以蘿蔔,滿街高喊「大根――小便――」,喊臭了蘿蔔,轉而用來罵藝人臭手臭腳。
日本每年盛產的蘿蔔一半醃鹹蘿蔔,另一半有種種吃法,例如「關東煮」,就是把整個蘿蔔逐刀切成月餅似的圓片,和豆腐、芋頭、魚糕(編按,即台灣所稱的「魚板」。)等物一起用醬油煮,大概與周作人「最愛的和尚吃的那種大塊蘿蔔燉豆腐」差不多。我覺得日本最獨特的吃法是蘿蔔泥,當作佐料,與芥末、生薑比類齊觀。一條烤魚,旁邊一小堆蘿蔔泥,調以醬油就著吃;油炸魚蝦或蔬菜,叫「天麩羅」,蘸著吃的汁液裡也要放蘿蔔泥。吃河豚用的蘿蔔泥一團粉紅,叫「楓葉蘿蔔泥」,那是加了紅辣椒。
做蘿蔔泥有專門工具,過去也寫作「山葵擦」或「薑擦」,想來當初是研磨山葵或生薑的,後來興起吃蘿蔔泥,也不曾改口叫「大根擦」。「山葵擦」一般為陶製:四周帶圍堰的碟子,當中佈滿小凸起,像研墨一樣在上面研磨。高級的「山葵擦」是鮫皮的,把沙紙似的鮫皮貼在木板上,據說用它磨出來的綠芥末味道就是不一樣。整根的新鮮山葵比較貴,自磨也麻煩,如今人家都是買現成的,擠牙膏一般便利。日本吃蕎麥面,嘴裡能淡出鳥來,佐料之一是綠芥末,有的麵館落座後自己動手磨,我磨過多次,還不曾遇到鮫皮「山葵擦」。研磨蘿蔔泥的工具以銅為好,銅板的一面翹然鑿起一排排小尖刺,經久耐用,很容易就把一段蘿蔔磨成一攤泥水,手指卻不免根根自危。
去年游廣州,見學南越王墓博物館,意外地發現「山葵擦」,卻原來我們也有過,叫作「礤」,而且是鐵製。孔夫子不撤薑食,可能就用它研磨。查《辭海》:「礤,刨刮蔬果使成絲狀。」這是另外一種礤,比較後世的,現在日常也使用,刨刮蘿蔔絲、土豆絲。蘿蔔絲,日本叫「千六本」,其實是中國「纖蘿蔔」仨字的音譯。蘿蔔絲常用來給生魚片墊底,團團銀絲,既增量感,又增美感,再配上紫蘇葉、柳蓼苗,去腥健胃。
日本菜寡淡,用蘿蔔泥佐之確也別有風味。
俏皮的川柳(1863)
日本狹長,從南向北,櫻花一路開過去,不留痕迹,緊接著梅雨又從沖繩壓將過來,壓得人心更其鬱鬱。據文部省(職司教育與文化)調查,日本人活得很不安,那種不可一世的勁頭兒正在喪失之中。若謂不信,有詩爲證:
•哪個吊環都固定了,上班族。(按:乘車上班,每天是那個鐘點那個位置,車上的人都成了熟面孔。)
•走時還睡著,回來早睡下。(按:起早貪黑上下班,竟然和妻子動如參與商。)
•比饅頭皮還薄的,脖子皮。(按:日語裡「脖子」有「解雇」之意,源自「馘首」,即砍頭。)
•還沒擔心下崗,公司先倒了。(按:這真叫人哭笑不得。)
•別抱奢望,那是你的孩子。(按:丈夫譏諷「教育媽媽」。)
•年收的五倍,總算能買塊墓地。(按:購房置地,在日本難乎其難。)
這就是川柳,世界上最短的詩型,但只能譯出個大意,難以成詩。和俳句一樣,僅有十七個音,按五、七、五分作三句,印成鉛字也只是鬆鬆散散的一行。日語並非一音一字,所以按漢字計算,比我國宋代的俳諧詩體「十七字詩」更短小。日本詩歌不講究押韻,靠音數和句式營造節奏感。川柳的作法頗似文革年間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表演的三句半。俳句有季語(能反映季節時令的詞語)、切字(用於斷句的語氣詞,計二十二個)之類的格律,而川柳則像中國「順口溜」,極盡自由,以至有人說:俳句是憋氣,川柳是吐氣。「我心憂矣,我歌且謠」。近年經濟不景氣,上班族處境慘澹,拿它來吐吐一肚子怨氣,也就是文人之所謂「塊壘」,而被稱作「上班族哀歌」。
在網路上常讀到一些流行於民衆口頭的順口溜,大概也屬於作家摩羅在《自由的歌謠》裡說的,「一切歌謠,一切巫咒,都是弱者的靈魂的呻吟,是無奈而又無力的呻吟。」不過,古語有云,「天高聽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吟者無奈,但一旦天聽到了,像電視劇裡演的,就算是有了力量吧。文化大革命終焉之際,感慨萬千,我也寫過一首順口溜:「旗手扒手吹鼓手,十年喪盡十億心,大王嘗聞布衣怒,載也民來覆也民。」雖爲民之一口,但溜而不順,居然好意思拿出來,都因回頭想來,載舟是民,誰覆舟就難說了,民也不要太托大了。總之,可發一噱。
順口溜,更文學的叫法是「民謠」(民間歌謠)。清人杜文瀾編《古諺謠》,從古籍中輯錄上古至明代的民謠民諺,計三千二百首。劉毓崧爲之序:「誠以言爲心聲,而謠諺皆天籟自鳴,直書己意,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言有盡而意無窮。」這些話完全可以用來說川柳。川柳的歷史比短歌、俳句淺。某韓國人論說日本人的秉性,一言以蔽之,是一個「切」字,倒可以從日本詩歌發展史得到支援。
俳句和川柳都是從俳諧連歌切下來的,就好比我們從律詩切下來四句,獨立爲絕句。連歌是一種集體性文藝活動,類似我國近體詩的聯句,並且跟作詩要練習對仗一樣,連歌得練習寫「前句附」。「前句附」指的是「前句」和「附句」的附和,有點像賦得體,「前句」是題,按題作「附句」,各逞機敏,互競俏皮。「世上玩弄前句附,以至樵翁牧童,無不事之。」(《俳諧高天鶯》,一六九六年刊),以文化傳統悠久的京都、大阪爲中心勃興的這種文藝遊戲,最後也波及新城江戶(東京)。大家都來寫,自然就有人評點。江戶出了個評點高手柄井川柳(1718∼90),投到他名下的作品,一年間多至七萬首。他的評點使江戶市井更樂此不疲。一七六五年他去掉「前句」,單把「附句」的佳作合編刊行,從此「附句」定型爲獨立的藝術形式。這種小詩有過種種稱呼,到了明治年間,始定名為「川柳」。
後世稱江戶時代的川柳爲古川柳。川柳獨具娛樂性,誰都能湊趣,向來爲庶民所喜聞樂見。當今日本報刊幾乎沒有不開設川柳欄目的,行家主持,讀者投稿,其樂融融。不過,順口溜似的川柳從藝術上被正統川柳家看低。他們強調署名,理由是事關著作權,但無名氏們只求一吐爲快,署名之處往往被用來點題,妙趣橫生。
柄井川柳評選,把川柳分爲三類,大致是時事、生活、情話。川柳的發想構思極自由,只可惜不能把陳寅恪的話――「無自由之思想,則無優美之文學」――反過來說。自由就帶有批判精神,難免政治壓迫。二戰期間,一位號鶴彬的工人作川柳反戰,被警察逮捕,死於獄中,年僅二十九歲。更多的人搞過「敬神愛國,勸善懲惡」的川柳。「體察物理人情,直寫出來,令人看了破顔一笑,有時或者還感到淡淡的哀愁。」這樣的川柳被周作人視爲上品。次之是「找出人生的缺陷,如繡花針噗哧的一下,叫聲好痛,卻也不至於刺出血來。」古川柳多是笑他人,而當代川柳偏於自嘲,發出無奈而又無力的苦笑。中國人喜好笑駡,怒也怒得亮堂堂,順口溜基本沒那種「淡淡的哀愁」。
似乎拿平民百姓的哀愁扯淡,街上又開始賣夢了――彩票,獎金翻一番。中頭彩的機會比精子在子宮裡撞上卵子大得多,不妨一試,就作了一首川柳:
早中啦,最難的頭彩,在娘肚子裡。
文化的街燈(1476)
在北京街頭遇見一個舊書攤,攤了些舊而破的書刊。翻檢一過,想:中國舊書業不發達,看來原因之一是書刊質量差,如此髒而破,誰願意把垃圾買回家。坦言:我在東京的垃圾堆裡看見成綑的書刊,必折腰檢閱,時而感歎書腰帶居然還完好無損;當然,收穫之餘,給人家重新捆好放好,這是揀破爛的仁義。
東京有什麽好?到處是一樣的招牌,一樣的燒鳥或刺身,一樣燈火通明的「扒金庫」(編按,台譯「柏青哥」。)但走在街上,也有我看見就要進的,那就是舊書店。日本人把散佈大街小巷的書店叫作「文化的街燈」,賣新書的書店是,賣舊書的當然也是,只是昏暗些。舊書店多,不正是東京乃至日本的一好麼?按:高行健還沒拿到那筆諾貝爾文學獎金以前,就去過斯德哥爾摩,在大學裡講話,其中有這樣幾句:
漢語詞和片語大可直接聯綴,毫無必要的「的」、「地」、「著」,前置詞或虛詞濫用,句子長而不當,或本可點斷卻莫名其妙連綴一起,凡此種種,把漢語弄得不倫不類,文學作品中病句也比比皆是,就更不用說了。
此說有理,似乎我這裡就必要「的」他一下:新書「的」店、舊書「的」店,以免被誤解爲新或舊的書店。
東京有八百來家舊書店,其中百餘家集中在神田一帶,鱗次櫛比,據說密度爲世界之最。街燈每年都熄滅不少,但也點燃一些。興亡半個世紀,據一位店家說,舊書店數量幾乎沒有變,著實令破字當頭、橫掃一切的友邦驚詫。逛舊書店,魅力首先並不是便宜,而是想邂逅已從新書店裡消失了的書,彷彿走進上一個時代。我愛讀昭和四十年代的書,即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五年所出版者,關於這一段時期的日本,很值得我們補課,只是當時的出版物大都只能在舊書店尋尋覓覓。
舊書,日語寫作「古本」,也寫作「古書」,兩者並無明確界定,但通常「古書」偏於指久遠或孤存之類的古籍,專家學者藏書家趨之。三、五十年前的舊書就叫它「古本」,即便絕了版,升值也有限。給舊書標價是店主的本事,他懂書,也懂市場需求,根據資料性、文化性、稀少性什麽的決定「舊」的價值。新書店則只許按出版社定的價銷售,這是日本的法律。新出版的書、暢銷書、長銷書在舊書店裡不值錢,新書店和舊書店是互補的關係,相安無事。但近年新生了一個事物,叫「新古本店」(編按,台灣譯成「新舊書店」,一般或以最大連鎖店「Book Off」稱之。)成爲出版流通的問題,以至被出版行業列爲二○○一年十大新聞之一。
傳統舊書店多數是一家一戶的小店,陳舊昏暗逼仄,店主埋沒在書堆裡,霉頭霉腦。「新古本店」是新型舊書店(可否譯作「特價書店」?),打出廢物利用的旗號,更類似便利商店,店堂敞亮,連鎖店遍地開花。它按定價的百分之五至十收購無限近乎新上市的書,用機器修整一新,半價出售,就搶了新書店的生意。出版不景氣,退回出版社的圖書堆積如山,送去裁化紙漿到底不如賣幾個錢。但作者不幹了,因爲這麽賣,他們拿不到版稅。讀者上「新古本店」買書,幾乎和上圖書館借書一樣,妨礙多賣書,影響作者的收入。於是幾百位漫畫家在六十八種漫畫雜誌上聯名發表聲明,抗議把圖書單純當作商品處理。可是,天下哪有不希望書價便宜再便宜的讀者?
把書買回家,有兩大用處,一是讀,不讀就要被中國學者譏諷;二是查,這是日本社會評論家大宅壯一的主張。多多收藏,以免書到用時方恨少。他身後留下一座大宅文庫,讓人們受用。可是,那些大量生産、大量消費的圖書哪裡有收藏價值?讀了就趁熱賣才是。中國舊書業不發達,另一原因就在於中國人的藏書情結。日本人也有過這種情結,但經濟高速度發展以後一家叫「角川書店」的出版社在電視上做廣告:年輕人開著私家車,「啪」的丟出一本書。日本人真就養成這習慣,紅火了舊書店。
別有風味蘿蔔泥(1393)我不愛吃蘿蔔。周作人說︰「明人王象晉稱蘿蔔可生可熟,可菹可齏,可醬可豉,可糖可醋,可臘,乃蔬之最有益者。」雖然吃法多樣,但若天天多樣地吃,像東北改革開放前那樣,吃它一冬,不厭才怪呢。似乎清人李笠翁就不像周作人那樣覺得蘿蔔「頂有意思」,只寫到「生蘿蔔切絲作小菜,伴以醋及他物,用之下粥最宜。」糖醋蘿蔔絲,清涼爽口,用之最宜的是下酒,這倒是我向來對蘿蔔唯一能另眼看待的。現而今餐館把蘿蔔洗吧洗吧端上來給人懷舊,黑土地,大豐收,食客盡開顏,那是闊起來的意思——需要去油膩了——卻終歸一...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9收藏
9收藏

 4二手徵求有驚喜
4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