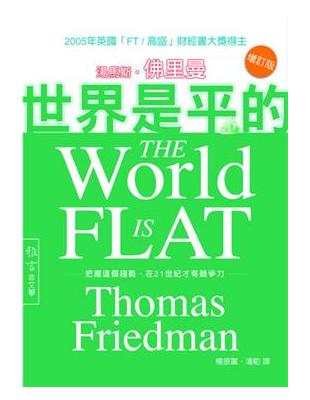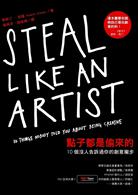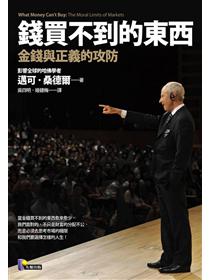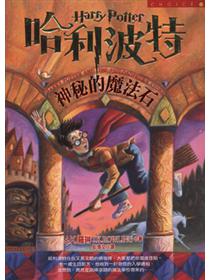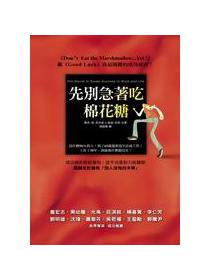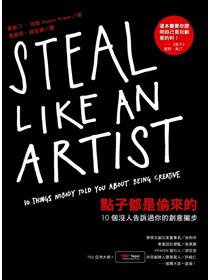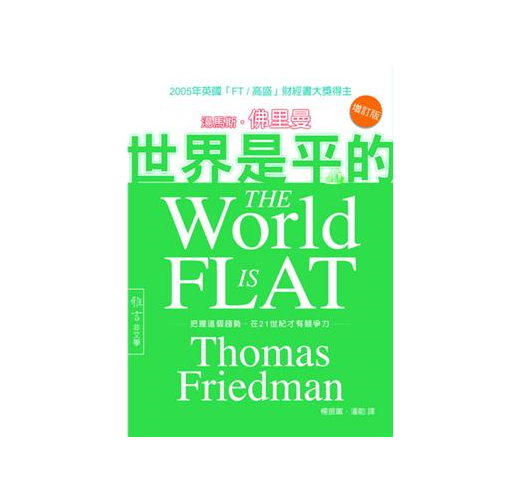第7章:「世界是平的」時代需要的教育理念
這兩年我有機會到美國各處演講,講全球化與「世界是平的」,聽眾形形色色,有加州棕櫚泉的退休人士,有馬里蘭州貝詩達的中學校長,有大城市郊讀書會的爸爸媽媽。我最吃驚的,是民眾對教育與競爭力所表現的關切之情。那種焦慮可以這麼說:我們的上一代都認定他們可以比上一代過得更好,我們這一代當然也會比他們那一代更好。如今,唉,我們這一代卻愈來愈憂心,我們的退休歲月會不如我們的上一代,下一代則可能更糟。我看到大家好像都在找可拯救下一代免於沉淪之苦的仙方。竟然有兩次,有人問我:「我女兒正在學中文。她將來會好好的,對吧?」
我答:「哦,不盡然。」
為什麼不呢?因為天底下根本沒有競爭力的仙方。我覺得像現在,應該要退一步,深呼吸一下再問:假如第六章裡所討論的策略,的確是男男女女要在「新中間」佔得一席之位的最好方法,那麼下一代該受什麼樣的教育呢?誠如普林斯敦經濟學家布蘭德指出的,「顯然,美國等富裕國家的教育必須改頭換貌,才能造就出適任本國工作機會的工作者。單單提高教育的量,總體來說是不無小補,因為勞動人口教育程度愈高,彈性就愈大,更能因應非重複性的任務,轉職的適應力也會更好。但是,光只有更多的教育絕非萬靈丹。未來,可能教育的方式會比教育的量來得重要。」
我明白地問過雇主還有教育工作者:「有競爭力的特質到底有哪些?下一代的白領階級需要什麼樣的教育?教育該做什麼樣的改變?」他們跟我講的不是什麼特定課程,而是某些技能和態度的組合。本章的重點,就是我從他們所學到的東西。我集中講四點,對任何想在「新中間」佔有一席之地的人都很重要。
在「世界是平的」時代,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學習力。你必須不時地吸收、自己教自己,怎麼用新方法做舊事情,或用新方法做新事情。許多的工作機會,不是部分就是全部,被數位化、自動化、外移去別國,新產業、新的工作機會冒出的速度愈來愈快,在這種年代,每個工作者都該養成學習力。在這樣的世界,脫穎而出的已不止是你懂什麼,還有你怎麼學。因為,今天你懂的,可能明天就沒用了。
我在明尼蘇達州的聖保羅演講就有挑明這一點,之後接受發問,二樓聽眾席有個少年舉手,他說他是九年級生,然後問說:「佛里曼先生,假如學習力這麼重要,那麼這個能力要怎麼學?我該去上什麼課?」
誰說童言無忌。
這個問題很合理。當時我還沒想透,所以只隨口答,現在回想方向卻是正確的。我說:「去找你的朋友,只問他們一個問題:『你最喜歡的老師是誰?』然後一一去上那些老師列的課,不管他們教的是什麼,不管是什麼課。」是希臘神話、微積分、藝術史或美國文學,都不重要,就是去上他們的課。因為我回想我最喜歡的那些老師,他們教我什麼,我都記不得了,但我鐵記得當時在學習時的興奮感受。一直伴我的,不是他們教的課業,而是他們所啟發的學習熱情。要有學習力,你必須先熱愛學習,至少要在學習中得到樂趣。學習有一大部份,是要具備自己教自己的動力。有些人似乎天生就有那種動力,其他人則要培養,或由適當的老師(或爸媽)來賦予。
CQ+PQ>IQ
再來就要講到兢爭力的第二項,P 是 passion,也就是熱情,C則是curiosity好奇心。不管過去還是未來,對事物的好奇與熱情都是一大競爭優勢。只是,世界抹平之後,對工作、成功、某個領域,甚至某種嗜好的好奇與熱情就比以前更重要了。世界是平的,代表你會擁有更多工具,可以更進一步、更深入地探索你所好奇的事物。
《Linux Journal》的主編席爾斯(Doc Searls)是一位在美國很受敬重的科技寫作者,為本書初版寫書評時就有寫到:「在抹平的新世界裡,教育機會是無限的,甚至無需學校、政府、教會、企業的協助也可以。你有必要知道的一切,很多都已經存在於網上某處。你若是搞科技的,更是如此。沒錯,網路並非無所不在。但只要已抹平的地方都有網路,而抹平的地方正快速拓展。當然,庸才傻瓜還是很多,不用懷疑。但是換一下這種想法試試:庸才傻瓜都是被造就的。造就出他們的是舊教育。自工業時代發韌之初,教育就只有一個目的:要為金字塔形、底寬頂尖的企業組織生產員工。在工業時代,如果不想進這種金字塔,除了務農及一些孤單的職業,可以選擇的很少。但現在可以選的已經很多,就跟有寬頻的人一樣多。」
所以我的結論是:抹平的世界裡,IQ還是很重要,但CQ與PQ,也就是好奇與熱情的商數,則更為重要。我堅信CQ+PQ>IQ這個公式。一個有學習熱情、充滿好奇心的小孩,一定會贏過一個空有IQ卻沒熱情的小孩。熱愛學習的好奇小孩能自我教育、自我驅策,總能找到學習的管道,尤其是在可上傳又可下載的抹平世界平台上。席爾斯說:「用功很重要,但好奇更重要。好奇的小孩最用功。」
依我所見,每一家學校的大門都應該刻上這句話:「好奇的小孩最用功。」
有些小孩的好奇是天生的。很多卻不是,要天生並不好奇的小孩愛上學習,最好的方式是運用優秀的教學把好奇心灌輸給他們。不然就是把「世界是平的」這個平台的一切科技提供給他們,激發出他們的內在好奇心,所以他們可以用五花八門的方式做自我教育。2005年4月24日,《紐約時報•教育專刊》有一則關於亞利桑納大學學生施蜜特(Britney Schmidt)的報導。報導中說,她對自己在上的課感到好煩,最大的原因是教授們的興趣都似乎只是來授授課,然後就走人。
施蜜特接受紐時記者訪問時說:「我修的課都拿A,只是我沒遭遇挑戰,沒在想新東西。」話雖如此,有一個學期,她必須修一門自然科學的課,教授跟助教群都很優秀,點燃她求知的欲望。她說:「我很幸運,修到一門老師真正用心的課。」結果,一名科學家誕生了。修了更多門科學的課之後,洛杉磯加大的行星物理所跟芝加哥大學的宇宙化學所都想收她當研究生。
老師沒熊熊的熱情,就無法點燃學生的。馬里蘭州蒙哥馬利郡的雷頓斯維小學校長倫妮(Hilarie Rooney)一天聽完我演講,來跟我講,她聘僱老師只看一點:「愛不愛小孩」。她說,假如你沒孩子緣,你講的東西他們就聽不進去。沒音樂感的人,也絕對無法演奏不出音樂來。
她說:「但假如你愛小孩,讓他們感受到,那麼就算你懂得不是那麼多,小孩也會受到激勵,自己努力去學。我能做教學策略上的指導,卻無法教人怎麼愛小孩。我一走進教室,就可以感受到老師愛不愛小孩。小學生都很愛老師,只是,愛小孩的老師是看得出來的。他們可以激勵出小孩的持續努力,為老師做到最優異。小孩的用功事實上是為自己,但假使他們曉得老師真的在意真的投入,小孩的熱情就會永不熄滅。那才是真正的學習。」
沒有老師或父母刺激,也能生出高PQ嗎?當然可以。只要回想一下你小時候,拿到第一台玩具消防車、洋娃娃、玩具醫生診療組或太空人頭盔,你就跟人講,將來長大要當消防隊員、時裝模特兒、醫生或太空人。那種無邪的熱情,想做某種工作,根本不曉得薪水、工作時數或該怎麼做職前準備,正是你該回頭尋覓的東西。我們都該重新發現的,正是那種孩子氣:「我想做,因為我想,不必解釋原因。」簡單講,就是找回你心中那輛玩具消防車。我們都有的,你一發現就會曉得的。
第三點其實只是倫妮校長說法的變奏:你必須喜歡人。你必須擅長處理人的事情,懂得和人相處。好的人際技巧在職場向來是一大資產,在抹平的世界裡更是。我不曉得課堂上要怎麼教這個東西,最好快把它研究出來吧。
誠如前一章指出,未來有很多「新中間」工作都要牽涉到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需要與人互動的工作是絕對無法外移或自動化的,價值鏈裡幾乎總是需要這麼一個環節。布蘭德形容得最好,也最引人深思:「或許,跟近幾年的想法正相反,未來搞不好人際技能會比電腦技能更重要。科技人是不會整個主宰地球的。」
第四點是開發右腦。平克(Daniel Pink)著有《新心智:由資訊時代走向概念時代》一書,他認為,假如你想要有一份「電腦或機器人無法做更快,外國人才也無法以更低薪做得一樣好」的工作,也就是做我所謂的「碰不得的人」,你就必須不時開發你的右腦,「比如不止於做交易,還要培養關係;要迎向新挑戰,而不只是解決例行問題;要縱觀全局,而不只是做單點的分析。」
平克主張:「外國人既然已經能更便宜地做左腦工了,我們美國人一定要把右腦工做更好。」對我而言,這正是要點。
只是,怎樣才能開發右腦呢?方法是要做你最愛的事,至少也要是你喜歡做的事。這樣你才會投入某種不可捉摸的什麼,某種你右腦所產生的東西,無法輕易複製、自動化或外包。誠如平克形容:「如今最重要的職能已經變成要先具備內在動機才能培養出來的那些。很少有人是為了內在動機而去做會計的。但把人變成創造者、感受者、設計師、說書人、輔導老師、企管顧問的,正是內在動機。隨時一個週末都會有會計師在自家車庫裡畫水彩,有律師在寫電影劇本。但我敢向你保證,絕沒有彫刻師傅會在週末,把替人免費報稅當做一種休閒娛樂。換句話說,做其所愛又能帶來經濟收入,這樣的情形會愈來愈多。
所以,平克的結論是,如果你爸媽告訴你,或畢業典禮的致詞貴賓說,「去做你愛做的事」,那可不是什麼沒營養的甜言蜜語。他們是在給你一種求生策略。
低音管與試管
現在倒推回去想。假如「新中間」工作要的是一流的合作力、槓桿操作力、調變力、解釋力、整合力,懂得怎麼做模型,怎麼在地化,用有個性的方式做事情,這些又全都要用到學習力,要在工作時投入好奇心與熱情,跟人相處和諧,那麼,我們的教育該怎麼做?
再次強調,我不是教育家,所以面對這個問題我必須謙虛。只是,我是記者,我可以報導說,真實的世界已經有好多真正的教育家正針對這個問題提出解決方案。我在美國許多大學都有看到他們為了培養未來的「新中間」所進行的教育試驗。我在此只提一所,即亞特蘭大的喬治亞理工學院(Georgia Tech)。
喬治亞理工的校長克洛(G. Wayne Clough)所做的課程重整,純是因為非做不可。他在1994年接任校長,他說:「想當初在六○年代,我進這所大學當新鮮人時,校方在新生訓練時就告訴我們:『看看你左邊,再看看你右邊,你們三個中只有一個能畢業。』」
當時要進喬治亞理工很容易,能不能畢業則是憑達爾文式的優勝劣敗,完全看成績。當時校內的社交與學術環境都很冷酷,不怎麼好玩。即使到九○年代初,大學部的畢業率也只有六成五。學生無法完成學業,原因是課程及學風都很陰鬱。他們的學業成敗,校方也不怎麼看重。
克洛認為,美國迫切需要更多的優秀科學家、工程師、創業者,大學是不該在畢業日前就失去三分之一的可能畢業生的。克洛了解,要把課程弄正確,而不只是量加多,「才能吸引更多高中應屆畢業生申請,並念到畢業。」
克洛回想他自己當工程師的經驗。他共事過的第一流工程人才當年讀書時成績倒不是最好的。他說:「他們曉得創意思考。他們解微積分等式的能力可能不比人強,但是,他們界定那種必須用到微積分的問題,能力卻比誰都強。他們有一種特殊性格,一種只能意會的東西。」
漸漸,克洛注意到,「好多有才華的學生對課外的創意活動比對課業更感興趣,」像電影製作、音樂創作等不務正業的嗜好。「跟他們聊天,會發現這些學生都很有意思。我開始想,嘿,校園裡如果有更多這種有趣的人,不是很棒嗎?校園會更有樂趣,興趣偏狹的學生多多接觸一些不一樣的同學,也能擴展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