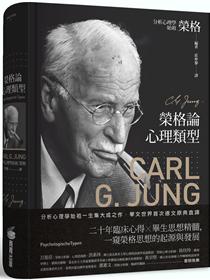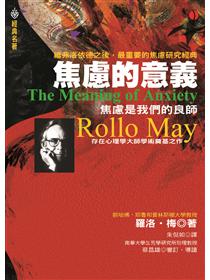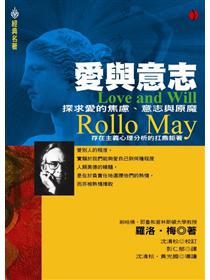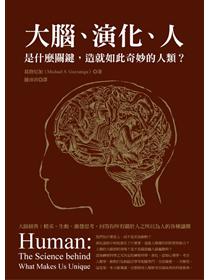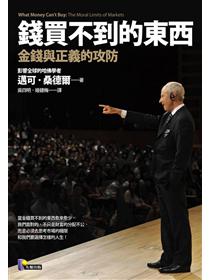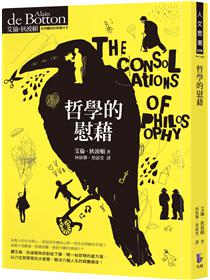‧焦慮是西方文明最耀眼的心理特質。
‧如果我們能穿透政治、經濟、商業、專業或家庭危機的表層,深入去發掘他們的心理原因,或者試圖去了解當代藝術、詩歌、哲學與宗教的話,我們在每個角落幾乎都會碰到焦慮的問題。
引述 文化評論學者劉森堯教授關於焦慮的短文如下
「我焦慮,故我存在。」這是我新近所建立的格言。有人會問:你在焦慮什麼呢?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我不焦慮,我就不是活著的了。
哲學家洛克說過:「我一輩子都活在焦慮和恐懼之中。」焦慮是人的心理生活必不可少的一種自我防衛機制,同時又因此衍生出恐懼,可是,焦慮和恐懼什麼呢?我們知道,根本什麼都未曾發生,還是活得好好的,仔細推敲,原來焦慮的源頭竟然是死亡,如羅洛.梅在「焦慮的意義」一書中所說:「我們無時無刻面臨非存有的威脅,所以焦慮。」
焦慮,人類處境的本質
正面處理焦慮,才可能有真正的自覺
十七世紀是數學的年代,十八世紀是物理科學的年代,十九世紀是生物學的年代,二十世紀呢?詩人奧登寫下《焦慮的年代》,卡繆則命名為「恐懼的世紀」,而我們也常指稱為「心理學的世紀」。焦慮、恐懼不獨現代社會才有,只是更為凸顯罷了。
羅洛. 梅在此經典研究中,檢視不同的焦慮理論,並逐一檢視其文化、歷史、生物和心理的面向,加以審度。他尋求這些理論的公分母,評估其中的分歧觀點,儘可能將不同的觀點綜合成一個整全的焦慮理論。他也挑戰「精神健康就是沒有焦慮」的流行信念,並堅稱焦慮是人類處境的本質,面對焦慮可以讓我們免於無聊困乏,鍛鍊我們的機智聰敏,同時開創人類存在所必需的張力。羅洛. 梅告訴我們,焦慮不是只有負面的癱瘓作用,它也可以是我們正向轉變的動力,因為只有正面處理焦慮,才可能有真正的自覺。另外,恐懼與心理學之間是否有必然的關聯,以及恐懼是否就是驅使人們去檢視他們自己心靈的力量,都是本書所要探討的疑問。
原本,焦慮與生俱來,人不可能沒有焦慮,而其中最大的主題是「死亡」,與其壓抑、忽略焦慮的存在,不如去認識它,學習如何共處。透過本書的案例研究,您將進一步看清焦慮的因由,並可對此展開尋索的旅程。
作者簡介:
羅洛‧梅(Rollo May)
美國存在心理學家,1909年生。幼年命運多舛,雙親長期不合,終至離異,姊姊曾不幸精神崩潰。大學因參與激進學生刊物遭退學。另行入學畢業後,赴希臘三年,任大學英文教席,並隨阿德勒(Alfred Adler)短期研習。返美後,旋入聯合神學院,與存在主義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以師友相交,深受其思啟迪。
梅年輕時甚為結核病所苦,不得不入療養院靜養三年,然此病反成為其生命轉捩點。面對死亡、遍覽群籍之餘,梅尤其耽讀存在主義宗教思想家齊克果(Kierkegaard)之著作。出院之後,入懷特學院(White Institute)攻讀精神分析,遇蘇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與佛洛姆(Erich Fromm)等人,終於1949年獲得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首位臨床心理學博士學位。
他是一位受歡迎的演講者,同時在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大學任教,並曾擔任懷特學院的訓練兼主任分析師。畢生致力於將存在心理學引入美國,1994年病逝於加州。
章節試閱
焦慮的現代詮釋
Modern Interpretations of Anxiety
我們見到了敵人,他就是我們自己。
二十世紀中葉的焦慮
Anxiety in Mid-Twentieth Century
當現代人被困在……兩個不同的年代,以及二種不同的生活模式中,他們了解自身的能力便全然喪失,
沒有標準、沒有安全感,也沒有最起碼的共識。
──赫塞(Herman Hesse),《荒野之狼》(Steppenwolf)
每一位機敏的社會公民,從他自己的經驗以及對同胞的觀察中,都明白焦慮是二十世紀普遍而深刻的景象。自一九四五年原子彈誕生以來,焦慮由潛藏的問題,轉變成公開的問題。機敏的公民不僅覺察到某些顯然會產生焦慮的處境,如不受控制的原子戰爭、激進的政經動亂等,更可以在自己和身邊其他人的身上,注意到某些較不明顯,但卻更深刻的個人焦慮來源。其中個人焦慮的部分包括內在困惑、疏離、心理混亂,以及價值和行為標準的不確定。因此,努力去「證明」當代焦慮的無所不在,就像晴天打傘一樣,顯然沒有必要。
既然大家都清楚社會中焦慮潛藏的來源,我們在這章導論中的任務,便在於指出焦慮浮現的過程,並說明它如何成為我們許多不同文化領域中的顯性問題。我們可能會感覺到,當此二十世紀中葉的時節,在完全分歧的科學、文學、宗教、政治領域中,都共同關切焦慮這個問題。二、三十年前,我們或許還可以稱它為「隱性的焦慮年代」──本章稍後將做說明 ──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就成為奧登(W. H. Auden)和卡繆(Albert Camus)口中所謂「顯性的焦慮年代」了。焦慮問題的浮現從隱性而顯性,從只是一種「情緒狀態」,變成我們必須不計代價試圖澄清界定的緊急議題,的確是意義重大的現象。
焦慮不僅在了解和處置情緒紛擾及行為失序時,被認為是弗洛依德所謂的「關鍵問題」(nodal problem),即使在文學、社會學、政治與經濟思想、教育、宗教和哲學等不同領域中,也都同樣被認為是關鍵的課題。我將從這些領域中引證案例,從比較一般性的問題開始談起,然後再進一步論及把焦慮視為科學研究問題的特殊考量。
文學
如果我們探究一九二○或三○年代美國文學中呈現出的焦慮,我們所關注的必然是焦慮的症狀,而不是顯性的焦慮本身。儘管在那個時期,公開和外顯的焦慮徵兆並不太多,但是研究者還是可以發現許多潛藏焦慮的症狀。譬如,像湯瑪斯.吳爾夫(Thomas Wolfe, 1900-1938,譯註:著名美國南方詩人)這樣的小說家作品中,所宣稱的孤寂感,以及永恆追尋的特質──亦即強迫式的瘋狂追尋,但卻總是受挫──便是。我們可以從本書說明焦慮的案例中看出,焦慮在本質上往往是根植於吳爾夫的小說標題──《你回不了家了》(You can’t go home again
)──所象徵表達的那個議題上的。我們看到書中眾生相,因為無法接受回不了家的心理意義,也就是失去心理上的自主,所以產生了神經官能的焦慮。人們感到好奇(因為文藝家以象徵手法表達文化中的無意識假設和衝突,往往令人深信不疑)的是,吳爾夫書中的象徵,是否意味著美國在一九二○與三○年代的許多人,已經開始了解到,我們不僅回不了家,也不可能再依靠過去的經濟、社會和倫理準繩來維繫安全感了?這個體認的核心便是,顯性焦慮逐步浮現變成人們意識得到的一個問題,以及一種「無家可歸」的感覺。如果我們把這個現象視為是針對家鄉和母親核心象徵的揣測,或許便以更清楚的形式,提出了一個我們在這項焦慮的研究中,將不斷面對的問題。
到了一九五○年代,焦慮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已經成為顯性的陳述。奧登認為自己的詩題──《焦慮的年代》(The Age of Anxiety)──最精確地呈現出該時期的特性。儘管奧登對詩中四位人物的內在經驗詮釋,是設定在戰爭時期──亦即「恐懼成為必然,而自由卻窮極無聊」的時期──但是他清楚地表明,詩中人物和其他同時代的人之所以會感到焦慮的潛藏因素,必須在比戰爭更深刻的層次尋找答案。詩中的四個人物,儘管出身背景與氣質皆不相同,卻共同具有某些當代的特徵:孤寂、做人無意義的感覺,以及無法擁有愛人與被愛的體驗;儘管我們有共同的需求,共同努力,同時也都有酒精提供的短暫喘息。對奧登而言,如果焦慮的來源可以在我們某些文化的基本趨勢中找到的話,便是向崇尚商業與機械價值的世界靠攏的壓力:
我們隨著巨輪的轉動前行;革命影響無所不在,無論是世事浮沉還是商業買賣……
……這個愚蠢的世界精品巧器主宰一切,我們喋喋不休說東道西,卻仍舊孤獨,
存活卻孤獨,歸屬──在哪裡? ──像無根的野草一般。
而詩中四位人物可能要面對的處境是,他們也將被捲入這無意義的機械化常規之中:
……我們所知的恐懼是未知。夜晚的降臨是否會為我們帶來可怕的境遇──在小鎮經營五金行……以教職謀生教新教的女孩學科學──?為時已晚。
我們有被徵詢過意見嗎?我們是否根本不堪聞問?
他們失去的是體驗的能力,以及自己是具有獨特價值個體的信念。這象徵我們每個人的四位角色,同時也不再對其他同胞懷抱信念,更無法與他們獲致有意義的溝通。
與奧登的詩題相似,卡繆將這個年代命名為「恐懼的世紀」,而稱十七世紀為數學的年代,十八世紀為物理科學的年代,十九世紀為生物學的年代。卡繆知道這些特性在邏輯上並不對稱,也知道恐懼並不是科學,但是「科學必定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因為當完美的科技即將造成地球毀滅的威脅時,科學的最新理論發展,便已經走到否認自己的地步了。此外,儘管恐懼本身不能被視為是一種科學,但是它確實可以被認為是一種技術。」而我們的時代也常被指稱為「心理學的世紀」。恐懼與心理學之間是否有必然的關聯,以及恐懼是否就是驅使人們去檢視他們自己心靈的力量,都是本書所要探討的疑問。
另一位沉痛表達出本世紀的焦慮,以及人們有類似焦慮狀態的人,便是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譯註:捷克作家,代表作有《變形記》〔1912〕、《地洞》〔1923〕、《審判》等)。卡夫卡在一九四○和五○年代的作品中大量湧現的寫作旨趣,對於本書的寫作目的極為重要,因為它所呈現的正是變遷中的時代氛圍。如果有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卡夫卡所言對自己是有意義的,這就表示他所傳達的乃是社會大眾普遍經驗中的某些深刻層面。在卡夫卡的小說《城堡》(The Castle)中,故事主人翁一生奮鬥不懈的乃是,致力與城堡中全面控制村民生活的權威當局溝通;這個城堡當局有權決定他所從事的行業,以及他的人生意義。卡夫卡的平民英雄(non-hero)之所以反抗,乃是受到「生命最原始要素,植根於鄉土與心靈召喚,以及成為社群一員等需求」所驅策的。但是城堡中的權威當局仍然莫測高深、不可親近,故事主人翁的人生失去了方向、無法整合,也不能融入社群之中。雖然城堡究竟所指為何是可以深入辯論的問題,但是就城堡當局以權力壓制個人自主性和有意義的人際關係這點而言,很清楚地便是官僚科層組織效能的縮影。我們堅定地認為,卡夫卡所描寫的正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產階級文化的諸般面向;由於科技效能的大幅提升,以致個人的價值幾近摧毀。
相較於卡夫卡,文學象徵處理來得較少的赫塞,卻更明顯地指出當代人焦慮的來源。二十世紀在美國發生重大的社會變革之前,歐洲已經歷過了這個創傷,因為對此社會形勢有所覺察,所以赫塞所寫的內容,比起一九二七年的《荒野之狼》,就更貼近美國一九四○年代社會所顯現出來的問題。他以海勒(Harry Haller)為主人翁的小說故事,做為我們時代的寓言。赫塞主張,海勒及其時代同袍的孤立與焦慮,是來自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中產階級文化,因為它強調的是機械和理性的「平衡」,卻以壓制經驗中動態的非理性質素做為代價。海勒克服自己孤立寂寞的方式,就是將自己先前受壓抑的感官與非理性衝動(亦即書名中的「狼」)解放出來。但是這種反應式的方法,只能帶來短暫的情緒紓解。赫塞的確沒有針對當代西方人的焦慮問題,提出徹底的解決方案,這是因為他相信當前的時代正是「整個世代被困在……兩個不同年代」的情況。換言之,中產階級的標準與自制已經崩解,但是取而代之的社會標準卻尚未形成。赫塞視海勒的行徑為時代的記錄,因為就我所知,海勒的靈魂之病不是某個人的變態行為,而是整個時代生病了,是海勒所屬的整個世代都患了神經官能症……這種疾病……正是要嚴懲那些精神堅強、天資聰穎者的疾病。
社會研究
焦慮在社會研究的領域中,也浮出了檯面。如果我們接受琳德夫婦在「美國小鎮」(Middletown)這二篇研究中所比較呈現的結果,那麼焦慮成為一個顯性的社會問題,便是在一九三○與四○年代。(譯:琳德夫婦在二十世紀初,以社會人類學為進路,在美國印地安納州的曼希〔Muncie〕鎮,研究典型美國小鎮的日常生活,前後出版了二冊珍貴的社會學文獻,後來並有以這二冊書為本的六集電視影集問世)在一九二○年代完成的第一次研究中,焦慮對小鎮居民而言,並不是一個顯性的問題,而且焦慮這個主題甚至沒有出現在該書的索引內。但是如果我們從心理學的角度來閱讀此一研究就會懷疑,小鎮居民的許多行為已經是隱性焦慮的病症了──譬如,強迫式地不停工作(「工商人士似乎都以追逐金錢的方式,來追求美好的生活」)、普遍有屈從規範的掙扎、強迫式的熱愛交際(非常強調所謂的「參加」社團),以及瘋狂地想用活動把自己的休閒時間填滿(諸如「飆車」)等,也不管這些活動本身是多麼沒有意義。到了週日下午,許多人都會固定地跳上車,開個五十哩,然後再駛回來。這讓我們聯想到巴斯卡(Pascal)對某些隱性焦慮症狀的描述:人們不斷分散自己的注意力、逃避無聊、避免孤獨,直到「困擾」本身成為問題為止。在第一本書中只有一個人──琳德夫婦形容他為「敏銳的」觀察者──透視到這些症狀的底層,並感受到潛在的憂慮。他注意到他的同鎮居民「都有所恐懼;那是什麼呢?」
但是對同一社區在一九三○年代的第二次研究,卻呈現出非常不一樣的圖像。顯性的焦慮出現了。琳德夫婦注意到,「美國小鎮居民共通的地方,是在面對複雜世界時的不安。」當時外顯的焦慮場景,可以確定就是經濟大蕭條。但是如果立即下結論說,經濟不安是焦慮浮現的全部因素,並不正確。琳德夫婦把「美國小鎮」的不安,跟那個時代個人所經驗的角色混淆相連結,是十分準確的看法。他們寫道,「鎮民陷入衝突模式的混亂中,這些模式並非全然不對,但是也沒有哪一個模式清楚地得到認同,或能夠免於困惑;換言之,基於團體的制裁而要求男分女歸的角色扮演,乃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是個人在面對文化的要求時,卻無法做出合於標準的回應。」
美國小鎮這種「衝突模式的混亂」,所呈現的乃是美國文化中無所不在的社會變遷,它們和我們時代中四處瀰漫的焦慮密切相關,這點我將在後面的章節中提出來。琳德夫婦注意到,既然「多數人無法容忍生活各層面的變遷與不確定完全爆發」,美國小鎮便傾向撤退到更嚴厲、更保守的經濟與社會意識形態中去。此一焦慮症狀和抗拒焦慮的不祥發展,預示了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主題,也就是焦慮與政治極權主義之間的關係。
社會心理學家立富頓(Robert Jay Lifton, 1926-)已為我們提供許多有關洗腦過程的洞見;而洗腦已是一九五○年以來,全球顯著的社會動亂形式。我在此不會從許多相關面向切入討論立富頓這項深具潛力的研究,只引述其中談到焦慮主題的地方做為參考:
著名的天主教神學家鄧恩(John S. Dunne)認為「所謂的『逾越』(passing over)現象」,乃是當代的新宗教。鄧恩對這個過程的描述是,「先是過渡到另一種文化的標準,另一種生活的方式,另一種宗教……接下來就是所謂『歸返』(coming back)的過程,帶著嶄新的洞見歸返自己原來的文化、生活方式和宗教。」
然而,這個過程也有其陰暗面。「逾越」過程的千變萬化,以及所謂的普羅修斯風格(Protean style),將產生大量的焦慮。因分散現象而引發的焦慮,反而會帶動人們對安定的追求,這個情況我們在當前基本教義派和許多集體靈修運動中一覽無遺。
所謂的「普羅修斯人」(Protean Man)是立富頓對當代人格的分析,他們不斷地改變自己的身分認同。希臘神話中的普羅修斯(Proteus,譯註:普羅修斯在荷馬史詩《奧德賽》中是海神波塞頓的助手,善於形變)能夠不斷轉變自己的外形──「從大野豬、髯鬚雄獅、龍怪、大火到流水。 ……但是,除非他被抓住用鐵鍊鎖起來,否則就沒有辦法不改變他的外形。」這種戴上不同面具、不斷變遷、持續反映環境,而「不知自己歸屬之處」(某位年輕的現代普羅修斯的形容)的驅力,所顯示的乃是變動得令人暈眩的文化處境。不論我們對此讚許或失望,此情此景所顯現的無疑正是我們社會的動盪不安。
立富頓把恐懼原子戰的當代焦慮,比擬為一種麻木不仁的過程。此一防衛機轉是一種情緒的縮斂,人們除了以此麻痺感覺、切斷威脅的知覺外,無可奈何。萎靡自己的意識作用似乎可以暫時防阻焦慮。至於個人日後是否要為此付出代價則是個未知數;對於帕布洛事件(Pueblo)的生還者而言,他們確實付出了代價。某位研究過此一事件的學者說道,「因為明顯的壓抑和否認,而做出短期調適是可能的,但是事後一定得付出代價」,例如,後果可能會以自殺或精神性的抑鬱症表現出來。
政治場景
政治與焦慮的理想關係,在史賓諾莎(Spinoza)對「免於恐懼」的政治層面意涵解讀中表露無遺。他認為國家的目的在於「讓每個人免於恐懼,使個人因此可以在沒有安全顧慮下生活與行動,不會傷害自己與鄰人。」但是當我們轉向實際的政治舞台時,我們卻發現焦慮正若隱若現地展露出來。我們不用深入法西斯主義的複雜成因,就會注意到它的誕生和攫取權力,都是發生在普遍充斥焦慮的年代裡的。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曾親身經歷納粹在德國的興起,他如此描述德國法西斯主義發展背景的一九三○年代歐洲處境:
首先是一種恐懼感,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種不確定的焦慮感到處瀰漫。不只在政經層面,文化與宗教亦復如是,人們似乎失去了安全感。個人失去可以信賴的基石;一切也都沒了根底。災難性的崩解隨時會發生。因此,對安全感的渴望遂與日滋生。伴隨著恐懼與焦慮的自由已喪失價值;於是人們寧可要安全的權威,也不要恐懼的自由!
焦慮的現代詮釋
Modern Interpretations of Anxiety
我們見到了敵人,他就是我們自己。
二十世紀中葉的焦慮
Anxiety in Mid-Twentieth Century
當現代人被困在……兩個不同的年代,以及二種不同的生活模式中,他們了解自身的能力便全然喪失,
沒有標準、沒有安全感,也沒有最起碼的共識。
──赫塞(Herman Hesse),《荒野之狼》(Steppenwolf)
每一位機敏的社會公民,從他自己的經驗以及對同胞的觀察中,都明白焦慮是二十世紀普遍而深刻的景象。自一九四五年原子彈誕生以來,焦慮由潛藏的問題,轉變成公開的問題。機...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25收藏
25收藏

 46二手徵求有驚喜
46二手徵求有驚喜




 25收藏
25收藏

 46二手徵求有驚喜
46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