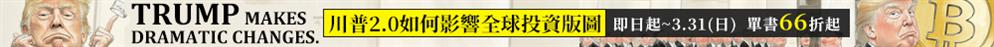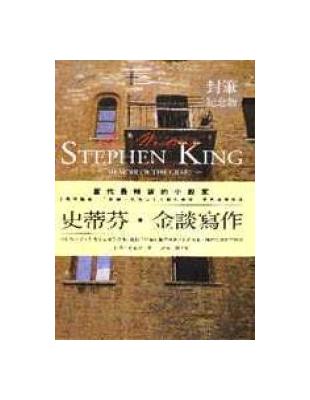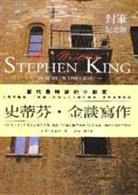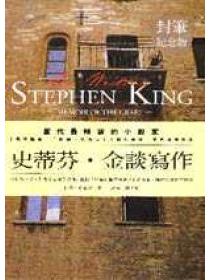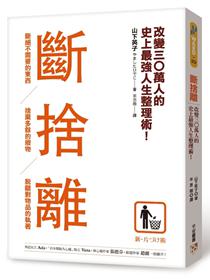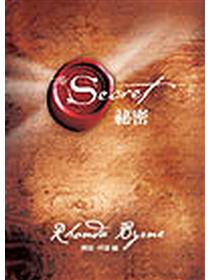序一
九○年代初期(可能是九二年吧,當日子過得不錯的時候,時間總是記不太清楚),我加入了一個大部份由作家組成的搖滾樂團。搖滾本質庫存樂團(Rock Bottom Remainders)是凱西•卡門•高德馬克一手創建,他是一位來自舊金山的書評家和音樂家。樂團成員有吉他手大衛•貝瑞,貝斯手雷利.皮爾森,鍵盤手巴巴拉•金蘇佛,曼陀林手羅柏•福羅漢,我是負責節奏吉他。還有個仿傚三人一組「俏妹歌手」南方之杯(Dixie Cups,編按:美國黑人樂團,由三個表姊妹組成)的樂團,成員(通常)有凱西、泰德•巴迪摩斯以及譚恩美。
樂團本來有意來個僅此一次的表演,在全美書商大會上做兩場演出,搏君一笑,重拾三、四個小時虛擲的青春時光,然後即分道揚鑣。
結果這樣的事情並沒有發生,因為樂團從來就沒有真的解散。我們發現我們實在是太愛在一起玩音樂,以至於欲罷不能,還有好幾個「槍手」樂師擔任薩克斯風手和鼓手(加上我們早期的音樂宗師阿拉•古柏,在我們的樂團核心),我們的音樂聽起來相當不錯。你會願意付錢來聽我們的演出,不是太多,不像U2或E街樂團(E Street Band)那樣的票價,但也許是早期說的那種在小酒館現場演出的「走唱價」(roadhouse money)。我們四處巡迴演出,出了一本書以茲紀念(我太太負責拍照,興起時也會跳支舞,其實她還蠻常跳的),並持續的偶爾表演幾場,有時是以庫存樂團的名義,有時則是稱作雷蒙.布爾的腿。樂團裡的成員來來去去——專欄作家米契•艾爾柏取代芭芭拉擔任鍵盤手;而艾爾不再隨團演出,因為他和凱西處不來。但是核心人物仍然是凱西、恩美、雷利、大衛、米契•艾爾柏和我……,加上鼓手喬許•凱力和吹薩克斯風的艾爾斯莫•帕洛。
我們因為音樂而聚合,但我們也因為友誼而聚在一起。我們彼此互相欣賞,也高興有此機會聊聊彼此真正的工作,那些別人總叫我們不可以輕言放棄的正職。我們都是作家,但從不過問彼此靈感從何而來;因為我們很清楚我們自己也不知道答案。
某一晚,當我們在邁阿密海灘演出前吃著中國菜時,我問恩美每次在作家講壇後幾乎都緊隨而來的「答客問」時間裡,有沒有哪一個問題是她從來沒有被問過的——那種當你站在一群對作者痴迷的書迷面前,假裝你不是那種一次只能從一邊褲管開始穿起的一般人時,從來沒有幾會回答的問題,恩美停了半?,仔細地想了一下然後說:「從來沒有人問過措辭的問題。」
我對她的答案抱以萬分的感謝.當時,我想要寫一本和「寫作」有關的小書己經超過一年多了,之所以遲遲未動筆是因為我不相信自己的動機——為什為想寫一本和寫作有關的書呢?是什麼內容讓我覺得值得我書寫?
答案很簡單,要是有人和我一樣賣了這麼多本小說,他必定有值得一提的事情可以寫,但是這顯而易見的答案卻未必是事實。山德斯上校(Colonel Sanders,譯按:肯德基炸基的創始人)的炸雞廣受好評,但我不確定有人會想知道他是如何製作炸雞。如果我冒昧到要告訴大家如何寫作,那應該要有比「我受歡迎」更好的理由。換言之,即使像這本書一樣短,我也不想寫一本會讓我覺得自己像個文學的吹牛者,或是一個自命不凡混蛋的書。市面上已經有夠多諸如此類的書——和作家了。
但恩美是對的:沒人問過措辭。大家會問狄尼洛(Don DeLillos,編按:美國當代作家,得過國家書卷獎,以《美國》一書聞名)、厄普代克(John Updikes,編按:美國當代作家,以短篇故事以及《野兔子》系列書聞名)和史提洛斯(Willian Styrons,編按:美國當代作家,長期遭受憂鬱症的困擾,小說主題也多以此為主題),但就是沒有人會問暢銷小說家。但我們這些無產階級作者也以我們謙虛的方式關心語言的表達,並且熱切地關注在紙上說故事的藝術及技巧。接下來,我嘗試用簡單扼要的方式,表達我如何獲得寫作技巧,我現在所知道的技巧;以及它們是如何運作。這是關於我的工作,這也是關於措辭。
僅將本書獻給譚恩美,是她以非常簡單直接的方式告訴我,可以去寫一本這樣的書。
序二
這是一本薄的書,因為大部份教寫作的書都滿紙胡說八道。小說家們,包括現今的那群人,通常都對他們自己做的事一知半解——做的好的時候是哪裡做的好、做的不好的時候又是為什麼做的不好。因此我領悟到這本書要是寫的越短,就會越少一些胡說八道。
小威廉•史湯克和懷特(E.B.White,編按:《夏綠蒂的網》作者)的《風格元素》(The Elements of Style)是這堆胡說八道慣例裡唯一著名的例外。那本書裡幾乎沒有任何明顯的廢話。(當然,它很薄,八十五頁的頁數比起本書還薄得很。)我現在告訴你,每一個有理想抱負的作家都應該去看《風格元素》。在「作文的原則」那一章裡的第十七條原則是「刪除不必要的文字」。我將在此試著去身體力行。
序三
有一條規則將不會在本書的其他部份直接點明:「編輯永遠是對的。」自然而然的是沒有作家會完全採納編輯的忠告;為此,他們總是違背和短缺了編排上的完美。換言之,寫作是人,編輯如神。查克•威瑞爾是本書的編輯,我的許多小說也是出自他手。依照慣例:查克,你是上帝。
第四章
……
我以兩個理論逐漸接近本書的核心,它們都很簡單。首先,好的寫作包含了對基本功夫的掌握(字彙、文法、風格元素),然後把你的工具箱第三層放滿正確的工具;其次,在一個不可能把壞作家弄成有能力的作家,以及同樣一個不可能把好作家變成偉大作家的情況下,加上大量的努力、投入、和適時的幫助,把一個還算可以的作家轉變成一個好作家,是有可能做到的事。
恐怕這樣的想法會被許多評論家以及寫作老師們否定,他們當中有許多人的政治理念自由,但在他們所選擇從事的專業領域裡卻像披了甲殼般的保守。那些會從當地鄉村俱樂部裡走上街頭,抗議對非裔美人和美國原住民(我可以想像史川克先生會對這些政治立場正確,但卻不甚優雅的稱呼說些什麼)不平等待遇的男人和女人們,通常也就是那些會告訴他們班上的學生,寫作能力是固定而不可改變的同一群人;一旦是個庸材,就永遠是個庸材。就算一個作家在一兩項具影響力的評論中得到較好的評價,他還是得永遠背負著他早期獲得的名聲,像是一個曾經在青少年時期瘋狂過的正直已婚婦人一樣。有些人是永遠不會忘記這種事的,如此而已,而大部份的文學評論也只是用來加強一種排他性的社會階級系統,而這種系統和培育出文學評論這東西本身的智能式俗氣勢利一樣古老.雷蒙.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也許在今日看來是個二十世紀美國文學中重要的人物,一個早期描繪二次大戰後混亂失常城市生活的聲音,可是還是有許多評論家會無法控制的否定這樣的評論。他是個庸材啊!他們憤怒地叫喊,一個自負的庸材!是最糟糕的那種!是那種自以為可以超過我們任何人的傢伙!
試圖從這種智能上動脈硬化惡境中突圍而出的評論通常獲得的成功有限,他們的同行也許可以接受錢德勒名列偉大作家的行列,不過卻傾向於把它放在名單的最下面.而且永遠都會有那種耳語:「從廉價科幻小說發跡的嘛,你知道的……,對那種人來說算是發展挺好的,不是嗎?……你知道他在三○年代有幫《黑面具》寫稿……,對啊,真令人惋惜……。」
甚至查爾斯.狄更斯,小說界中的莎士比亞,都得面對持續不斷的評論攻擊,這肇因於他那通常太過聳人聽聞的才能,他那愉快的多產量(當他沒在創作小說時,他和他的妻子就在製造小孩),以及當然,他在他自己和我們的時代裡贏得廣大閱讀群眾的成功。評論家和學者總是對於廣受歡迎的成功抱存懷疑,而他們的猜疑時常是調整過後的。在一些其他例子裡,這些存疑被用來當作是不用思考的藉口,沒有一個人可以在才智上如此的懶惰卻又顯得如此的聰明;給聰明人一半的機會,他們就能駕駛著他們的小艇漂流……,你也許可以這麼說:一路打著盹就到了拜占庭。
所以是的——我預期我會被某些人指責我是在鼓吹一種不用大腦,快樂的霍雷肖.阿爾傑(Horatio Alger,美國作家,以他創造出那些充分體現美國夢的角色們受到推崇)式白手起家哲學、強為我仍自擁有的那點小得快看不到的名聲加以辯護、並且鼓勵那些「非我族類的老傢伙們」去申請鄉村俱樂部會員卡.我想我應該可以忍受這些指控。但是在我們繼續下去之前,讓我再重述一次我的基本論點:如果你是個壞作家,沒有人可以幫你變成一個好作家;如果你寫的不錯但想要成為偉大的作家……,還是算了吧!
接下來的部份是我所知道如何寫出好小說的所有東西。我會儘可能的簡單厄要,因為你的時間很寶貴,我的也是,而且我們都瞭解我們花在講寫作的時間,也就是我們沒有在實際寫作的時間。我也會儘量鼓勵你,因為那是我的本性,而我也喜歡這份工作,我希望你也能夠同樣的喜愛它。不過,如果你不想拼了老命的工作,你是不可能有機會寫得好的——就退回到尚能勝任的程度去,並心存感謝你還有那麼點東西讓你做靠山。靈感之神繆思是存在的,不過他不會降臨你的寫作室裡和你閒聊,並在你的打字機或電腦上撒滿創作的魔粉;他是住在地下的,是個地下室型的人,你必須下降到他的層級,而一旦你到了那下面,你就要幫他整理出個小公寓給他住。換句話說,當繆思坐在那抽著雪茄、讚嘆著他的保齡球獎座、以及故意裝作沒看到你的時候,你得要做所有的勞力工作.你覺得這事公平嗎?我認為很公平。那個傢伙可能不怎麼起眼,而且他也或許不是個容易交談的人(我從我的繆思那得來的東西大部份都是些垃圾,除非他有認真工作),不過他卻會為你帶來靈感。你理當做所有的工作而且熬夜奮戰,因為這個抽著雪茄,有對小翅膀的傢伙擁有一個神奇的盒子,那裡面有些東西是可以改變你的人生的。
相信我,我真的知道。
如果你想成為一個作家,在所有事情之上有兩件事你一定要做:多閱讀和多寫作。就我所知除此之外別無他法,沒有捷徑。
我的閱讀速度很慢,不過我通常每年會讀七、八十本書,大部份是小說。我並不是為了研究寫作技巧而閱讀;我讀書是因為我喜歡閱讀,這是我晚上做的事,坐在我那張藍椅子上讀書。同樣地,我並不是為了學習小說技巧而去讀小說,而是單純地因為喜歡故事,然而這還是有一種學習過程在進行著。每一本你所選擇的書都有它值得學習的某個地方或某些地方,而且不好的書反而通常比好書有更多值得學習的東西。
當我八年級時,我碰巧讀到一本多產科的幻小說家莫瑞.藍斯特的小說,他大部份作品都發表在四、五十年代,那個時候,像《驚奇故事》這種雜誌稿費才一個字一分錢。我之前也讀過藍斯特其他的作品,足以理解到他寫作的品質不怎麼平均。而這本有關在小行星帶上開礦的故事,就是他不太成功的作品之一。這樣說還太仁慈了,事實上這本書糟透了,故事裡的人物淡薄如紙,情節發展又古怪可笑。最糟糕的是(或是在我當時看來),藍斯特愛上了「熱情的」這個字。書中主角以「熱情的笑容」注視著逐漸接近的帶有礦產的行星群;書中主角以「熱情的期待」在他們的採礦船上坐下來用晚餐。故事接近尾聲時,書中的英雄以「熱情的懷抱」擁住故事裡那個豐滿的金髮波霸女英雄。對我而言,這本書在文學價值上等同於一劑天花疫苗:就我目前所知,我從來沒有在任何一本小說或故事中用到「熱情的」這個字。若上帝同意的話,我以後也絕不會用。
以讀者的身份來看,《行星礦工》(雖然不是書的標題,但也很接近了)是我生平很重要的一本書。幾乎每個人都能夠記得自己失去童貞的第一次,而大部份作家也能夠記得第一本讓他(她)把書放下並思考著:「我能寫得比這本更好。見鬼了,我現在就寫的比這好!」的書。還有什麼比讓掙扎中的作家了解到他(她)的作品,毫無疑問地比某位實際上讓人為他作品付錢的作家還要好這件事,更能激勵人心?
從閱讀一本劣質作品中最能清楚學習到什麼東西是你不該做的——一本像《行星礦工》的小說〔或《娃娃谷》、《閣樓之花》,以及《麥迪遜之橋》等這類的作品〕,就值得放在一間好的寫作學校中用上一學期來討論,甚至還可以邀請到超級明星級的客座主講人。
另一方面,優質作品教導學習中的作家有關作品風格、優美的敘事方式、情節發展、具可信度的角色人物塑造,以及事實陳述。像《忿怒的葡萄》,這種小說也許能夠讓一位新進作家充滿了絕望感覺和老式的妒嫉情懷——「就算我活了一千歲,我也不可能寫出這等佳作」——但這種感覺也可以是種刺激,驅使作家去努力工作和設定更高的目標。被一個優美的故事和傑出文筆的綜合體當面掃過——事實上是擊倒在地——是每個作家必經的過程.你不能期待有人會被你的作品的力量給掃倒,直到這樣的事發生在你身上為止。
所以我們用閱讀去體驗所謂普通和劣質的作品;這種經驗幫助我們在類似的情形悄悄出現在自己作品中的時候,能夠清楚地辨別出它們,並且斷然的掃除它們;我們也透過閱讀去檢測自己和佳作或經典作品之間的距離,藉此瞭解究竟有什麼是我們可以做的.而且我們透過閱讀去體驗不同的寫作風格。
……
如果說「多看、多寫」是成為作家重要的準則——而我向你保證它是——那要寫多少才算是多呢?這當然就不一定了,隨著各作家因人而異。也許傳言的成分勝過事實,對此我最喜歡的故事之一,和詹姆士•喬伊斯有關。根據這故事,有天一位朋友前去拜訪他,發現這位偉大的作家正以一種全然絕望的姿勢張開雙手地趴在他的寫作檯上。
「詹姆士,你怎麼了?」朋友問道。「是工作嗎?」
喬伊斯示意,連頭都沒有抬起來看他朋友一眼。當然是工作的問題;不是一直都是嗎?
「你今天寫了多少字?」朋友追問。
喬伊斯(仍然覺得沮喪,仍然低著頭趴在桌子上)回答:
「七個。」
「七個字?可是詹姆士……,那不錯啊,至少對你來說啊!」
「是啊。」喬伊斯說,終於把頭抬了起來。「我想是這樣吧……。可是我不知道這七個字順序要怎麼排進去!」
在相反的那頭,也有著像安東尼.特洛勒普是個不錯的例子;對今日的讀者來說,這本書也許應該改名叫《你有可能讀完它嗎?》,而且他還以不可思議的規律性不斷地寫出來。他白天的工作是英國郵局職員(散佈全英國的紅色公共郵筒就是安東尼的發明);他每天早晨出門上班前寫二個半小時。這個作息安排如鋼鐵般嚴謹,如果當這二個半鐘頭的時間到了,而他句子只寫到一半,他會把那未完成的句子留到隔天早上再寫。如果在還剩下十五分鐘的時候他剛好完成他那六百頁的巨作之一,他會寫上「結束」,將原稿放在一旁,然後開始寫下一本書。
約翰.克里西,一位英國著名懸疑小說家,用了十個不同的筆名寫了五百本小說(是的,你們沒看錯)。我寫了三十五本左右——有些是特洛普式的長度——就已經被當作多產作家,可是我看來確定是佔住了儘次於凱克里西的紀錄。有些其他的當代小說家(他們包括了魯絲.藍黛兒/芭芭拉.法恩、尹凡.杭特/艾德.麥可班恩、狄恩.昆玆、以及喬伊絲.卡羅.奧茲)創作的數量都輕而易舉地和我旗鼓相當;有些還比我多寫了很多。
另一方面——詹姆士•喬尹斯那一方面——還有個只寫了一本書(出名的《梅崗城故事》的哈波.李.其他任何一個類似的作家,包括詹姆斯.艾吉、麥爾肯.勞瑞,和湯瑪士.哈里斯(目前來講),都寫不到五本.這也是可以啦,但我總是對這些人有兩件事覺得好奇:他們花多少時間來寫那些他們已經寫了的書?以及他們除此之外的時間都做了些什麼?編織阿富汗地毯?組織教堂市集?奉敬梅子?我這樣子可能討人嫌惡,但我也是,相信我,真的覺得很好奇。如果上帝給你一些天賦去做某些事,那你為什麼不就去做它呢?
我自己的時間表是劃分的非常清楚,早上屬於任何新工作——手邊正進行著的創作;下午用來小睡片刻和寫信;晚上的時間則是給閱讀、家人、觀賞電視上紅襪隊的比賽,以及任何無法等待的文章修改。基本上,早晨是我主要的寫作時間。
一旦我開始一項作業,除非逼不得已我不會停止,也不會放慢速度。如果我不每天寫作,故事人物就會在我心中漸漸走味——他們開始讓人覺得像是小說中的人物而不是真實世界的人。而故事結構不再分明,我也開始失去對故事情節和步調的掌握。最糟糕的是,所有編織新故事的興奮感會開始褪色,工作開始覺得就像個工作,對所有的作家而言這是個死亡之吻。最棒的寫作發生在——總是、總是、總是——當它對作者而言是一項靈感之啟發的時候。必要時,我可以很冷血地寫作,但我還是最喜歡在想法仍然新鮮、幾乎握不住般燙手的時候寫作。
我曾經告訴採訪媒體我每天寫作,除了聖誕節、獨立紀念日和我的生日之外。那是個謊言。我之所以會那麼說是因為一旦你答應接受訪問,你就必須得說點什麼,如果可以說些至少有點小聰明的東西,效果又會比較好。同時,我也不想讓人家聽起來覺得我是一個有工作狂的怪胎(我猜我就是個工作狂)。事實是我在寫作時,我就每天都寫,不管是不是像個有工作狂的怪胎。這包括了聖誕節、獨立紀念日和我的生日(反正到了我這個年紀,你會試著去乎略那該死的生日)。而我不工作的時候,我就完完全全的不工作,雖然在這種全面停止下來的時刻裡,常常覺得自己神志不清而且睡不好覺。對我而言,不工作才是真正的工作。當我在寫作時,一切都像是遊樂場,就算是我在寫作時所遭遇過感覺最糟的三個小時,其實都還是蠻快樂的。
我過去的寫作速度比現在快;我其中一本著作〔《跑步的男人》,後來改編成電影「魔鬼阿諾」〕就是在一星期內寫完的,是個約翰.克里西也許會很欣賞的表現(雖然我曾經讀到過克里西有幾本懸疑小說是他在二天內就寫完的)。我想是戒煙讓我的速度變慢;尼古丁真是刺激神經傳導的好東西。不過問題當然是,它在幫助你寫作的同時,也在致你於死地。我仍然相信完成一本書的初稿——即使是長篇作品——都不應該超過三個月,也就是一季的時間。任何比那久的時間——至少對我來說——故事就開始有種奇怪漠生的感覺,像是從羅馬尼亞公共事務部寄來的快遞,或是在強烈太陽黑子活動期間內在高頻段短波廣播播放的東西一樣。
我喜歡每天寫十頁,字數最多可到二千字左右,三個月下來就有十八萬字,對一本書來說是很好的長度——如果故事情節寫的不錯而且維持住新鮮感,這樣的長度可以讓讀者快樂地悠遊其中。有些日子裡,寫個十頁是輕而易舉的事;我起床、出房門,早上十一點半以前就可以結束我的工作,生龍活虎的像是一隻在義大利臘腸堆裡的老鼠。最近隨著年歲漸長,我發現我在書桌上吃午餐,直到下午一點半左右才完成一天的工作。有的時候腸枯思竭,一直到喝下午茶時仍在四處瞎晃。不管哪種狀況我都可以接受,但只有在最糟的情況下我才會允許自己在寫出二千字之前就關機休息。
對規律式(特洛普式?)寫作最好的幫助就是在安靜的氣氛下工作。即使是個天生多產的作家,也很難在老是有著警報聲和撞擊聲的吵雜環境下工作。當我被問到「我成功的祕訣」時(一個荒謬但不可能逃得過的問題),我有時會回答說有兩個:我保持健康的身體(至少是直到一九九九年夏天一部休旅車把我從路邊撞倒為止),還有美滿的婚姻。這是個好答案,因為它不但打發了這個問題,也含有真實的元素在裡面。健康的身體,加上和一位不接受我、或其他任何人影響的獨立自主女性有著穩定的關係,使我的工作生命得以持續不斷。而且我相信這樣的關係就算反過來也是事實:我的寫作和我在寫作中得到的快樂有助於維繫我的健康和我的家庭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