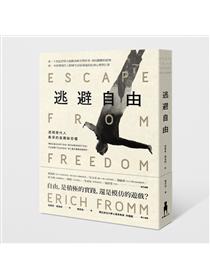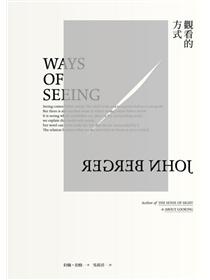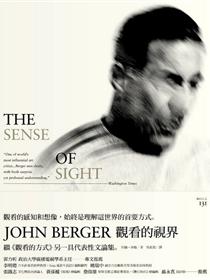◎被視為「哲學家的哲學家」梅洛龐蒂的經典之作
在普羅旺斯鄉下離艾克斯(Aix)不遠的托洛內(Tholonet)住了兩三個月,他沉浸在這個具有濃厚深居氣息的地方,特別是日日得以樂享塞尚(Paul Cézanne)之眼曾經投注的景色,在此,他重新探問視覺,重新探問繪畫。他再一次尋求發端之語詞,譬如,那些能夠命名人類身體造化奇蹟的語詞、命名身體那無以解釋的生氣活力的語詞、命名身體那即刻能與他者、世界與自身建立連結的語詞,同時,也找尋那些命名此一奇蹟的脆弱性的語詞。
全文共5大節:
第一節的主題是科學與藝術。
第二節討論的是可見性的條件。
第三節可以說是對笛卡兒視覺哲學肢解了視覺作用的批判。
第四節集中在現代繪畫史對於深度、色彩、形、線條、輪廓、運動的多重探索。
簡短的第五節,回到了藝術所特有的喑啞歷史性力量。
作者簡介:
梅洛龐蒂(Merleau-Ponty)
梅洛龐蒂(Merleau-Ponty,1908-1961)
法國哲學家,在現象學運動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闡發了一種獨到的「身體哲學」。
1945 年以《行為的結構》(La structure du comportement,1942年出版)、《知覺現象學》(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1945年出版)兩部重要著作獲得博士學位。1945年10月與沙特等人創立《現代》(Les Temps modernes)雜誌。
本書《眼與心》原為梅洛龐蒂生前發表過的一篇長文,最終以單行本形式聞名於世,這是 梅洛龐蒂最著名的現象學藝術論。
譯者簡介:
龔卓軍
國立台灣大學哲學博士,現任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現象學與當代法國哲學,長期關注身體哲學、美學、現象學心理學,以及精神分析的相關議題。著有《身體部署》、《文化的總譜與變奏》,譯有《人及其象徵》、《拉岡》、《空間詩學》,合譯有《自由與命運》、《夢的智慧》、《傅柯考》。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最完整翔實的中文譯本
長篇導讀、豐富譯註、延伸閱讀
引領您進梅洛龐蒂的哲學世界,哲學家隱晦艱澀的謎語有了一絲線索──
名人推薦:最完整翔實的中文譯本
長篇導讀、豐富譯註、延伸閱讀
引領您進梅洛龐蒂的哲學世界,哲學家隱晦艱澀的謎語有了一絲線索──
章節試閱
譯序 旋進的身體影像
文/龔卓軍
未定域
1961年《眼與心》(L’Œil et l’Esprit)刊行於期刊《法蘭西藝術》(Art de
France)創刊號,1962年春天,梅洛龐蒂死於心臟病。所有後續言說的中斷,將這篇文章推向了一個未定域。至今我們仍可以查到1962年的美國藝術文獻評論The Burlington Magazine上,某位評論者認為:「梅洛龐蒂教授討論藝術家的視覺時,哲學行文風格如此有意隱晦艱澀、如此雜亂無章地呈現,使其論點不知所終。」 表達了對這篇處於未決狀態的文章極其不滿之意。就像是一個死前留下的謎語,像是電影<大國民>(Citizen Kane)裡面的密碼,沙特在1965年說:梅洛龐蒂此書「說出了一切,如果人們懂得解碼的話。」 人們對此議論紛紛,正面與反面的解讀,交錯在這一片未定域之上。
約翰生(Galen A. Johnson) 在《梅洛龐蒂美學讀本》中指出,梅洛龐蒂在此書中闡述其原創的存有學,同時隱然與海德格思想形成對話。
但我們隨即在同一個讀本中讀到來自後現代哲學家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的猛烈攻擊。他不滿梅洛龐蒂在《眼與心》對馬黑(Marey)、杜象(Duchamp)所做的藝術實驗的惡評,認為這正是他隱藏的一神論形上學、將形體與話語(discours, figure)絕對區隔的理論缺陷。 故事並未就此結束,同一本書,杜夫海納(Mikel Dufrenne)在同名文章<眼與心>中,反駁了李歐塔對話語在先、無話語則無視覺經驗的強調,把焦點拉回原初視覺經驗的絕對差異中。
讓故事回到了原點。在現代與後現代之間,在現象學與後現代之間,《眼與心》這本小書帶來的並不是傳統美學理論的論辯,而是傳統美學理論的某種諧擬(parady)狀態,它並不呈現為某種系統性的、解決方案式的美學理論,毋寧是一個令人難以釐清、難以決定其意義的事件。
這個事件的暴風眼,也就是無言的、靜默的畫家之眼。再次回到塞尚(Cézanne)視覺的未決定狀態嗎?梅洛龐蒂在《眼與心》中對於塞尚的討論,比重上遠不及他在1945年發表的<塞尚的疑惑>(Le Doute de Cézanne)。塞尚在《眼與心》中,被置入了偏向梵谷(Van Gogh)、羅丹(Rodin)、賈克梅第(Giacometti)、克利(Klee)、恩斯特(Ernst)、馬蒂斯(Matisse)這樣的系譜中,進行現代繪畫史所隱含的繪畫形上學的相關討論,而非<塞尚的疑惑>一文中,以現象學的意向性描述與生活世界還原法操作,對比於弗洛依德(Freud)以精神分析所進行達文西繪畫詮釋。那麼,《眼與心》的問題場域(problématique),在早期的現象學之後,是否有所移轉?許多研究者都指出,對於《眼與心》的閱讀,必須重新置入梅洛龐蒂從1959年到1961年去世前的最終轉換,或者最終的搖擺,或者是在現象學界限上的最終搖擺。鷲田清一在評論梅洛龐蒂的現象學理念時曾說:
這反映了梅洛-龐蒂思想的搖擺:一方面,作為從忘卻中的覺醒,不斷地要探索本源性事物、原始性事物,另一方面,卻又反覆談論本源性事物的炸裂與散亂,暗示本源性事物的失敗。
這種思想上的搖擺未定,其中一個重要的參照文本,就是《可見與不可見》。《可見與不可見》(Le Visible et l’Invisible)是梅洛龐蒂1959年開始書寫,去世時留下150頁的大開面未完成手稿。 經過克羅德.勒佛(Claude Lefort)編輯遺稿成書,於1964年出版。此書由五篇文稿與自1959年1月至1961年3月的101則工作筆記組成,成為梅洛龐蒂晚期思想的重要文獻,許多關鍵而尚未釐清的理念,都可以在可見與不可見這本書當中找到。同時期的文獻還包括:1960年出版的《符號》(Signes)文集的前言,集中討論了政治哲學與歷史哲學的問題,以及其他相關的課程講稿,譬如:1959-1960年討論胡塞爾《幾何學起源》的課程講稿《現象學極限上的胡塞爾》(Husserl aux limites de la phénoménologie)、1959-1960年討論「自然概念」的法蘭西學院講稿<自然與邏各斯:人類身體>(“Le concept de nature, 1959-1960; Nature et logos: le corps humain”)、1960-1961年的《黑格爾以降的哲學與非哲學,1960-1961年課程》(Philosophie et non-philosophie depuis Hegel. Cours de
1960-1961)等等,這三種晚期課程講稿目前均有英文譯本。但是,本文關切的問題是:梅洛龐蒂的思想是否恰好在此走到了某種思想搖擺的極限?
所謂的極限,必然相對於界限而產生。梅洛龐蒂出版於1945年的現象學心理學代表作《知覺現象學》(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不僅提出了身體主體的理論,也為他自己的哲學思想畫下了第一道界線。身體主體是肉身化的主體性,它雖然侷限了吾人的觀點,卻是形構出「在世存有」(être-au-monde)的根本出發點,藉由身體主體的「運作意向性」,梅洛龐蒂企圖破除了意識哲學的框架,在病理經驗的對質下,重新闡明身體主體形構出「在世存有」之時空感受、欲望活動、意義指向的存在完形結構。雖然梅洛龐蒂此書致力於走出笛卡兒身心二元論的格局,但評論者認為他仍陷於「反思/辯證」、「意識/對象」與「主客二分」的語言對立項之中,甚至他晚期在《可見與不可見》筆記中亦對此提出了自我批判。
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可以視《眼與心》是他嘗試運用畫家、詩人與作家的創作經驗──亦即追尋與創建嶄新語言的經驗,一方面藉由畫家的「視覺式思考」來擴大「語言」的一般概念內涵,另一方面將哲學工作導向某種嶄新語言的探問與創作,使它不再受現象學心理學的「科學實證性」要求所限制──在意識與對象之間搖擺,而企望在藝術創作的「超反思」(sur-réflxion)經驗中找到「藝術實證性」的存有學根基,將現象學的超驗還原與海德格的朝向「非思」之思一舉結合在對於現代藝術的「肉身思維」及其所蘊含的「肉」形上學中。
這個時候,梅洛龐蒂把焦點指向了「影像」(image)的問題,身體問題的某種最終轉換,或搖擺。「影像這個聲名狼藉的概念」 ,在梅洛龐蒂從身體主體的現象學心理學到肉形上學的終局路上,這個概念如何可能跳脫含混不清的概念夾纏,走出意識哲學、主體性哲學的死巷?首先,影像與身體,在慣常的中文脈絡中並沒有任何關聯,但是在法文的脈絡中,卻牽涉到梅洛龐蒂思想的一個相當重要的背景:柏格森(Henri Bergson)思想中的身體影像(image du mon corps)。為了要解決觀念論與實在論對於真實的看法,柏格森在《物質與記憶》(Matière et Mémoire, 1896)這本書的導論即聲明,「我們所謂的影像,是某種存在,多於觀念論所謂的再現表象,又少於實在論者所稱的事物,這種存在位於事物與再現表象之間。」
如果說,我們身處的當下就是在我的感官開放時被種種的影像所環繞,在我的感官關閉時這些影像隨即消逝,這些影像與影像之間按照柏格森所謂的自然法則而相互作用,於是我們依據當下、或者在過去的當下所呈現過的種種影像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預測未來種種影像所可能產生的變化。麻煩的是,有一個影像在種種的影像之間特別突出,「我沒有辦法單單從外在的知覺中認識到它,還要從內部的欲動(affections)才能認識到它:這個影像就是我的身體。」
如果世界就是許多影像聚集所產生的狀態,那麼從客觀的角度來說,這些影像不可能發生嶄新的變化,除非有某些特定的影像中介,由它來造成影像內容與聚集方式的改變,這種類型的影像中介,它本身又可以再被影像化,變成外在影像當中的一員,這也就是作為種種影像核心的身體影像所具有的優位。
就身心關係問題來說,柏格森一生不斷與身心平行論(parallélisme)進行論戰,他說:「衣服跟它掛上的鉤子相互關聯,如果有人拿掉鉤子它就會掉下去,鉤子動它也動,如果鉤子的頭太尖銳,它就會被刺穿、裂開,鉤子的一舉一動怎麼影響它,它就怎麼受影響。鉤子與衣服一點都不相等,更不要提鉤子與衣服會是同一件事物了。」
他所要反對的身心平行論認為,身心關係因身體受到某些化學物質的作用而產生聯結,但柏格森認為這是「抽象下的混淆」(confusion dabstractions) ,他認為大腦是精神或心智的工具,讓它能夠認識世界、處理自己的問題。所謂的化學物質,無法影響到精神,而只會影響到它的工具,也就是身體。譬如,對於身體在空間中的定位感,柏格森認為這是任何論述都不可能掌握的,與精神心智層面的活動完全不同,身體是透過空間影像而運動,而身體自身的影像即成為這一切空間影像的核心。就此而言,作為身體與精神之間的中介表象活動,身體、影像與精神層面的思考活動,形成了極為有趣的複雜關係。
從柏格森的角度來說,身體的知覺成果只不過是兩種影像系統中的一環,知覺作用無異於幻象效果,折射出存有者的虛擬狀態,就好像一種特殊的銀幕,存有者的真實活動會穿越而過,但是它們的虛擬活動會成為影像投射在這道銀幕上。但是在純粹的視覺影像之外,它們所圍繞的中心,一個可變的、能夠運動的中心,卻是一個未定域(zones d’indéterminations)
,它讓我們能夠依據自己特定的身體影像能夠去選擇知覺中的其他影像進行互動,使得我們的身體得到運動上的未決定空間,實際上,未定域指向了意志的未決狀態,這也就是並存的兩種影像系統的另外一端:從意志、大腦、神經、身體動作,一直到與外在世界影像接榫在一起、外在世界影像環繞著它而存在的的身體影像。如果我們反過來從生成的角度來看身體影像的出現,我們會發現身體影像剛開始是一種無人稱狀態(impersonnelle) ,透過許多再現表象的環繞,我們才慢慢的適應,將我們的身體視為運動中心,其他的影像不斷的環繞著它而變化,但是它本身卻成為各種影像所參照的中心影像,成為各種影像的聚集之所、行動的中心,本身保持不變。自此衍生出人稱與人格。
在這裡,影像自身、身體影像、身體與影像的關係,成為環繞著「身體影像」這個未定域而形成的運動星座。用梅洛龐蒂的話來說,這是身體影像或視覺的旋進狀態:「依據我們所見與促成之所見,形成了存在者的旋進(précession)狀態 ,再依據存在者,形成我們所見與促成之所見的旋進狀態,這就是視覺自身。」
不論我們說它是陀螺傾斜轉動時造成的迴圈狀態(circuit)、是地球自轉時自己有一條傾斜的自轉軸同時又有另外一條鉛直線做旋轉軸,身體影像的旋進現象──而非身體自身,顯然成為晚期梅洛龐蒂思想發展所投影出來的一條重要軸線,這條軸線不僅指向了現象學界限之外的哲學或存有學,甚至指向了哲學的界限之外:繪畫、視覺、藝術,指向了梅洛龐蒂思想的極限。
所謂思想極限,同時也指向未決定、未區分的思想流變狀態。就此而言說,勒佛雖然在本書序言中強調,胡塞爾的觀念論為梅洛龐蒂所拒絕,但梅洛龐蒂在《知覺現象學》著名的前言中,又肯定胡塞爾現象學還原的方法目標是回到生活世界,而不是離析出來一個孤立的形構意識。同時,收錄在《符號》的<哲學家和他的影子>一文,梅洛龐蒂亦肯定形構活動與被形構者之間的靜態關係,最終已為胡塞爾所放棄,代之「主體間性」(intersubjetivité)、「身體間性」(inter-corporéité)和肉身主體性與自然間的交互關係。最後,透過運作意向性之被動性(passivité)與無人稱性的探討,梅洛龐蒂亦以身體與世界的「肉」(chair)的可轉圜性(reversibilité)呼應了胡塞爾將超越主體性等同於「主體間性」的做法。凡此種種,並不能簡單的說梅洛龐蒂拒絕了胡塞爾的觀念論。然而,梅洛龐蒂對美學經驗──特別是繪畫與文學藝術的重視,使得他的晚期思想走向了現象學的界限狀態,這種界限狀態與胡塞爾思想的關係,特別是與胡塞爾在<幾何學起源>一文中所強調的觀念化作用湧現的歷史性條件:「符號身體」與書寫之關聯,值得依據梅氏的晚期講稿再加以深究。
非美學
如果從當代美學的觀點來看,《眼與心》開闢的問題場域(problématique),傾向一種前藝術、前美學的思考,也就是藝術尚未被界定、被定位,美學尚未成論述、成體系的未區辨混搭狀態,用David Carroll在Paraesthetics: Foucault, Lyotard, Derrida一書中的概念來說,就是「paraesthetics」──可譯為悖謬美學、逆美學、反美學、擬美學或類美學,或者直譯為不倫不類、無法分類的「趴拉美學」,它「意指類似於美學回轉過來反對它自己、超越它自己或在它自身之外側生出去……悖謬美學描繪出一個批判的美學進路,認為藝術是一個尚未論定的問題……在其中,藝術並沒有被決定好的位置或確切的定義。」
這種藝術存有學式的反身提問,與梅洛龐蒂在《眼與心》透過「肉」的弔詭現象所提出的逆美學思考更為相應:對科學、對理論界限本身的質疑態度。《眼與心》透過繪畫來論證一種「非思考的思考」的關鍵態度。Carroll說:「美學可以被用來指向理論的、思辨的、道德宗教的界限,而不重新落入到一個取代它們的位置,本身又變成一種超越秩序嗎?」
就此而言,傅柯、李歐塔與德希達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們挑戰且模糊了哲學與文學、藝術、政治的界限,也就是將哲學與它所想要論述、想要了解的「他者」的界限,做了逆轉性的物質條件批判,用哲學的「肉」的複雜來源與構成,顛倒、破除哲學自身所以為的身世同一性。
從非美學的問題場域,讓讀者可以輕巧的掌握《眼與心》這本書的構成。
第一節的主題是科學與藝術。梅洛龐蒂發展了《知覺現象學》以來所強調的運作意向性,將運作與操作的概念重新置入科學與藝術兩個脈絡當中。宛如回應柏格森所謂的雙重影像系統,科學的操作主義立基於知覺作用所形成的影像系統上,卻脫離了知覺影像,成為純粹概念模型的操作主義;透過藝術的操作,特別是以繪畫視覺影像的操作為例,梅洛龐蒂認為繪畫史不斷的重新回到另外一個具有能動地位的影像系統──身體影像,在這個未定域不斷重新輻射出嶄新的、多樣的、特異的世界影像,以此成為科學中的科學,一種致力於未定域的非思考的思考。
第二節討論的是可見性的條件。梅洛龐蒂透過身體影像系統的多樣性與多重向度性,提出了多重向度之間的混搭侵越(empiétement)的現象。可見性的基礎條件讓我們不得不思考某種絕對的內勢力量(puissance d’immanence),這種力量介於身體運動、視覺、觸覺與既有的世界影像記憶的相互侵越混搭之間,它是推動、選擇所有不可見者以某種力量線成為可見者的力量核心,它是居中者(moyen)。繪畫史上的中種種努力讓我們看到的,不僅僅只是再現外在世界的影像,還指向了這個是外在世界影像系統變現為可見、也使得內外的分野得以出現的不可見者中的不可見者。
第三節可以說是對笛卡兒視覺哲學肢解了視覺作用的批判。梅洛龐蒂把攻擊火力集焦於與笛卡兒《曲光學》(La Dioptrique, 1637)的對質,突顯截然不同、潛藏已久的視覺哲學,突顯用視覺模式來思考視覺與用觸覺模式來思考視覺經驗的差異,這種哲學所認定的思考型態與思考基礎不同於笛卡兒的觀念論──必須從清晰而分明的觀念來建立我們對世界與自我的認識和存在方式,必須以觸覺的幾何學來取代視覺幾何學以及所有視覺經驗。梅洛龐蒂認為,至少現代畫家──或絕大多數的畫家都在探索既有的維度之外的維度,以此多重維度中的流變影像來認識世界或面對自我。透過這一節的論辯與立場區辨,確立第四節以後所要闡述的身體影像哲學思考、一種完全不同的知識論與存有學。
第四節集中在現代繪畫史對於深度、色彩、形、線條、輪廓、運動的多重探索。梅洛龐蒂的哲學書寫的搖擺與極限狀態,特別是在這一節展現了高度張力。一方面,他企圖將現代藝術史上追尋線條、明暗、色彩、輪廓、材質、多重維度上的突破表現,匯歸於一個大寫的感性邏各斯(Logos),一個大寫的存有;另外一方面,又隱然將此大寫存有在身體影像上的流散表現等同於繪畫與雕塑,而對於攝影影像、定格影像、運動影像的種種創作實驗採取批判性的態度,認為它們毀壞了時間的越出(dépassement)、混搭(empiétement)和「變形」(métamorphorse)。恰恰是在這裡,將原本的未定域給出了隱然的決定,梅洛龐蒂呼應了柏格森的時間形上學,給予時間以存有學上的優位,大寫存有讓位給了繪畫式藝術創作的非思性思考,也讓後來的傅柯、李歐塔、德勒茲──特別是德勒茲──的時間切片、事件思考和運動影像哲學,領有了當代法國哲學之「當代性」資格的思想反叛地帶,繼續在此非美學、未定的誤區進行對「時間性」哲學的反叛。
簡短的第五節,回到了藝術所特有的喑啞歷史性力量。梅洛龐蒂在未能總結的總結中,提示了一種新型態的開放迴圈無言理性:「這種喑啞的歷史性(historicité
sourde),藉著迂迴、踰越、侵越混搭與突然的推進,在迷宮中前進。」 用畫家克利的話來說,視覺與可見性並不是「肉」,而是「火」一般的存在:「某種火焰想要活起來,它甦醒了,隨著手的指揮吐著火舌前進,火焰到達了畫布,進佔了畫面,然後,一顆火星跳出來,在它想開闢出來的環圈上合攏:回到眼睛,回到更遠之處。」
這樣1種開放迴圈的無言理性,是從身體影像的旋進狀態中、從未定域中、前人類狀態中皺折出來的喑啞歷史性,它以空間影像方式,插入到大寫存有的運動中,從而改變了、甚至瓦解了我們對於人、對於世界、對於存有的既定理解,而終將推演至「大寫存有」的廢黜,當它流佈為1種力量的多重名稱。
科學與藝術:從完形到雙曲線視覺模型
從旋進的身體影像這多軸線的中心來看,梅洛龐蒂所關心的雙重影像系統,可以用科學與藝術這兩條軸線的影像操作模式來理解。梅洛龐蒂在早期著作《行為的結構》(La structure du comportement, 1942)中「導論」的第一句話就表明,「我們的目標是理解意識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包含身體性的、心理上的、甚至是社會性的自然層面。」
他運用了完形心理學的完形概念與黑格爾式(Hegelian)「從最底層開始」的辯證法,闡明行為的完形「結構」在知識論與存有學上較直接的機械性刺激反應模式更具優位,同時又反過來批判完形學派把「完形」(Gestalt)加以自然化、外在化了,那麼,如果說這種科學是個世界影像結構既不是外在、也不是內在於先驗主體──他不願走回康德式的主體先驗構式的哲學,他該如何解決這個辯證上非內亦非外的困境呢?
在物理序列、生命序列與人類序列之間,他認為人類序列的完形有一特殊現象:語言概念,使得意識與自然有了超越辯證的中介,換句話說,有了語言概念──如果說這也稱得上是一種特定的影像類型的話,物理完形、生命與心理完形、社會與人類完形都有了具體的綜合完形介面,有了語言,我們的行為的結構的各個層面都得以有所定位與整體意義的掌握依據,我們的心理活動、其他生命的活動、一直到人類互動的各種模式,都有了可以被明確中介出來的完形介面,這是古典行為主義與機械論生物學所未考量的層面。但是,這種想法要求有另一種哲學構想,以提出這種思想在知識論與存有學上哲學意涵。我們可以看到,梅洛龐蒂一直到遺稿《可見與不可見》的工作筆記中,還在思考這個「完形」帶來的哲學問題。
從柏格森的脈絡來看,如果把「完形」理念視為未定域的身體影像,我們當可以了解,梅洛龐蒂的「完形」理念涉及到科學思考模式所無法掌握的虛擬影像創造工作,這種虛擬影像的最佳範例就是語言和繪畫創作,涉及到所有人類成為人類、人文化為人文的原初歷史狀態。
胡塞爾在<幾何學起源>(1936),透過質問幾何學起源狀態,提出了由幾何學原初直觀、觀念化,進入幾何學具體歷史的「原初歷史性」論題。胡塞爾認為要重新活化幾何學的原初直觀,不可能不處理意識如何「活躍而創造性地涉入意義第一次成形的過程。」就此過程而言,他要談的幾何學不是意義已化為具體觀念,「被傳衍下來的既成、已歸檔的幾何學語句。」也不是某個歷史上具體的個人如何在大腦中閃現出幾何學的原初直觀。重點在於語言如何做為歷史性的具體、肉身條件。換言之,幾何學觀念在任何第一個直觀到它的人的經驗中、在它被直觀到後,如何透過製圖、語言化、書寫的影像化過程將它變現在具體歷史與生活世界中,就成為問題的重點,這也就是發生現象學與動態形構的問題。
如果我們在此將幾何學的起源直觀狀態,置換為繪畫史中,畫家的「主題」(motif)凝視,在前無古人表象的第一次視覺直觀出現後,如何可能在具體歷史中掌握此直觀而給予落實的表達方式,就成為梅洛龐蒂自<塞尚的疑惑>以來即關注有加的繪畫存有學問題了。
這是詩人與畫家所面對的歷史緊急狀態,也是讓歷史得到具體轉換介面的危險狀態。梅洛龐蒂對於畫家不顧現實歷史的發展,將虛擬的繪畫影像創作視為其存在的唯一要務,讓我們想到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在<詩人所為為何?>、<關於技術的追問>兩篇文章中所討論到的危險狀態、上帝缺位狀態。在命運中,詩人與藝術家面對著這種危險、深淵,冒險進入沒有基礎的深淵破碎之處,展現其語言道說的存在歌聲。相形之下,這種緊急狀態與科學的思考或戰爭的緊急狀態實不可同日而語。就此而言,畫家塞尚在梅洛龐蒂哲學中的位置,實堪與海德格哲學中的詩人賀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相比擬。
在塞尚之外,梅洛龐蒂《眼與心》一書中所不斷引用的畫家克利,也是「緊急狀態」下的視覺詩人。1933年,克利被納粹認定為「頹廢藝術」的創作者,在頹廢藝術目錄中,甚至將克利的作品稱為「病態心靈的作品」。從《思考中的眼睛》一書來看,可以說他有一種冷的浪漫主義傾向,雖不接受當時的人智學的想法,卻仍保留了德國觀念論形上學的思考傾向。對克利而言,畫家不是在人的世界或活人的世界思考與創作,而是與死人、與未來的人的創作狀態共存。這樣說好了,畫家是一隻創作的動物,卡夫卡筆下的科學院猴子,在不一樣的眼睛與感受基礎上面對這個世界,表現出以機智和嘲諷為能事的另類心靈。在「歷史哲學論綱」第九條,班雅明曾經以克利1920年的作品<新天使>(Angelus Novus)為題,談到一種新的歷史哲學,新的精神狀態,這位歷史天使面對著現代性的「進步」帶來的風暴與災難、一種常規化了的緊急狀態,把這位天使吹離了現場,離開了塵世俗物。就此而言,《眼與心》的第四章多次引用克利的話,包括最關鍵的「使之可見」(rendre visible),甚至引用克利的墓誌銘,恐非偶然。
然而,即使回到最實證的觀點來看,從這種詩意的緊急狀態到科學操作的模式之間,仍然保有藝術與科學的自由關聯。依據梅洛龐蒂的現象學詮釋學與現象學心理學觀點,Patrick A. Heelan曾經運用非歐幾何雙曲線原理的視覺研究,結合藝術史的材料,重新詮釋梵谷的畫作空間配置並不只是內心激情的表現。
梅洛龐蒂在<塞尚的疑惑>中所提出的「生活透視」,除了可以用視覺完形心理學詮釋塞尚畫作如「坐在黃色沙發上的塞尚夫人」(1888-90)背景牆上不相平行的橫條、「古斯塔夫.吉弗瓦肖像」(1895)前景中向下延伸翹曲的書桌、以及「靜物與有抽屜的衣櫃」(1883-87)那顯然不平行的桌子前沿,Heelan還致力證明人以雙眼球凝視一定距離內的物件或一定距離外的風景時,都會在眼睛自動的調整下,造成某種視象上的結構性扭曲效應,所以,在凝視這幾幅畫的時候,本來不連接、不平行或過度往外往下翹曲的平面,會在眼睛的實際觀看經驗與一定的聚焦狀態時,變現為連接、平行或不再過度翹曲的凝視結果。運用同樣的雙曲線模型,Heelan證明梵谷的畫作「梵谷在亞耳的房間」(1888, 1889)、「夜間咖啡店」(1888)的不尋常透視──某種距離過近所造成的發散性的雙曲線透視,就呈現在畫面上。這種詮釋說明了藝術創作的虛擬影像與科學知覺的影像系統之間所可能產生的交纏關係,同時也隱含了本文的一個基本命題、基本追問:那麼,畫家的秘密科學是什麼?畫家在平面幾何學之外苦苦追尋的「維度」是什麼?
可見性 的存有學條件:肉
從晚期梅洛龐蒂的思想脈絡來看,「可見性」的討論無所不在,我們可以從這個概念掌握《知覺現象學》中與身體影像相關的「身體圖式」發展到晚期《可見與不可見》的基本線索。如果我們平行閱讀梅洛龐蒂在《自然:法蘭西學院講稿》(La Nature: Notes cours du collège de France)<自然概念,1959到1960年,自然與邏各斯:人體>的「第一草稿」中的講法,會發現他再一次的談到了從身體主體發展到「肉」存有學的基本線索,在召喚一門感性學的思考背景下,我們可以更好的理解「可見性」做為一重要迴圈的理論關鍵地位:
再度考慮這個理念,讓身體呈現為運動的主體、感知作用的主體,如果這不只是口頭說說,它意味著:身體是作為觸與被觸、看與被看、一種反射迴響的場所,透過它,將自身關聯於某種不同於它自己的物質團塊的能力、將它的迴圈連接上可見者、連接上外在的感覺物的能力才會展現出來。基本上:肉的理論(théorie de la chair),把身體視為可感知性(Emfindbarkeit),而將事物視為是蘊含在其中。這與意識下降為身體客體毫無共同之處。相反的,它會將身體客體的糾纏環繞在它的周邊,或者說,它是種種隱喻的休息區。它並不是透過意識對身體與世界的全面考察概括論述,而是我的身體介入到在我面前的東西與在我後面的東西之間,我的身體站立在直立的事物的前面,與世界成為一個迴圈(circuit),成為對世界、對事物、對動物、對他人的身體感性的移置(Einfülung,就像是同時擁有一種感知的介面),透過這樣的肉的理論才能夠讓這一切得到理解。因為「肉」乃是原初無呈現(Nichturpräsentierten)本身的原初可呈現性(Urpräsentierbarkeit),不可見者的可見性——(我們需要一個)感性學(esthésiologie),來研究感官本身的這種奇蹟。它讓不可見者在可見者當中的是形象化作用「能夠變得明白」。
從可見性到肉的存有學,梅洛龐蒂仍然把「我的身體影像」置放在這個迴圈的中心。值得注意的是,「肉」本身是作為「原初無呈現本身的原初可呈現性」,也就是說,把它視為不可見的感性內勢力量,並不為過。如果說在科學的客觀思維之外,柏格森哲學關切的是形上的生命創造力、生命衝動(élan vital),那麼,梅洛龐蒂晚期思想的極限可以說是要穿越視覺的屏幕世界,走向無人稱的感性發用狀態。但或許是揮之不去的現象學科學要求的影響,從知覺作用、可見性到肉的存有學,梅洛龐蒂始終停留在身體感官的基本模式來思考可見性問題。《眼與心》雖然已經觸及了繪畫界面作為一種影像存在自身,不同於身體影像的發用狀態,但身體主體的陰影仍然盤繞在上空,影像自身的運動空間尚待打開。
這種思考極限上其中的一個例子,就是「交纏」。「交纏」(entrelacs)這個理念是晚期梅洛龐蒂的系列關鍵概念之一,也是《可見與不可見》所收錄遺稿其中一章的標題。我們用這一章的其中一段討論觸覺與觸覺本身、觸覺與視覺的複雜關係,來闡明「交纏」這個理念如何限定在人類身體的旋進作用──而非身體影像的旋進作用:
關於「觸摸」,我們已經發現了三種特出而互為基礎的經驗,三種交疊但互異的維度:對於質料粗精的觸摸、對於事物的觸摸——身體及其空間的被動感受(也就是肌肉空間運動時的內觸覺)——最後是對觸摸的驗證性觸摸,當我右手去觸摸我正在觸摸事物的左手時,其時,「觸覺主體」轉而落入到被觸摸者的位階、滑轉成為事物,觸摸形成於世界的氛圍環境中,也形成於種種的事物當中。我左手對這只皮包所產生的厚實感,與右手運用在左手時所行的外部檢驗,兩者間有很大的差異,就如同我的眼部動作造成所見的變化與我的眼部動作本身,兩者亦不可相提並論。相反的,對於可見者的任何經驗,總是在觀看的動作脈絡中向我給出,而可見的景象與「可觸知的性質」卻共同隸屬於觸摸當中。我們必須讓自己習慣這樣去想,所有可見者在可觸者中都被安排過,而所有可觸的東西都以某種方式許配給了可見性,這中間的混搭侵越(empiétement),不只存在於受觸者與觸摸者之間,也存在於可觸者與在其上形成外殼的可見者之間,反過來說,就如同可觸者本身並不是沒有可見性,也不乏其視覺上的存在。既然是同一個身體去看和去摸,可見者和可觸者便屬於同一個世界。這是個長久被忽略的奇蹟,我的眼睛的每個動作,甚至是我身體的每個動作,在我運用它們詳審地探索出來的同一個可見世界(univers)裡,都有它們自己的位置,反過來看,就好比每一個視覺都發生在觸覺空間的某個位置。這裡有一種雙重交叉的定位(relèvement double et croisé),可見者在可觸者當中,可觸者在可見者當中;兩張版圖皆屬完整,卻不曾和合為一。兩個局部都涉及整體,卻無法疊合為一。
就上一段的引文來看,「交纏」至少涉及到感性介面本身的多維度與不同感性介面之間的「混搭侵越」與「雙重交叉定位」的多種間距關係。但是,就《眼與心》所批判的笛卡兒觸覺模式下的幾何學世界觀來看,這一段引文所引用的觸覺模式,相對於影像自身的存在而言,兩者之間的不可共量性卻突然消逝,因為梅洛龐蒂採用的是整體性的大寫存有話語、讓所有間距都化為大寫間距的存有學論述,這個時候,影像運動自身的問題就被解消了。視覺性的影像介面和觸覺介面最大的不同,在於影像介面本身具有共時性,這種共時性呈現,使得梅洛龐蒂所謂的混搭侵越(empiétement)、交錯(écart)、交纏(entrelacs)、可逆轉性(reversibilité)單單在影像介面內部就得以完成,而不必然需要涉及大寫存有的巨型論述來支撐它。這也就是為什麼梅洛龐蒂在《眼與心》選擇了視覺、繪畫、影像與圖象的問題來延伸他對身體主體、身體圖式、甚至是身體影像的討論,這也正是畫家或影像創作者的創作狀態不同於純粹觸覺模式的創作之處。影像介面本身的共時性、公共性、可重複性、可複製性,甚至是當今世界影像存在的遠距可延伸性,都使得觸覺模式在相形之下更具有私密、個別、無可言說的特質。
在觸覺模式與視覺模式的交纏、混搭之下,究竟梅洛龐蒂的「肉」存有學能不能夠像柏格森的影像哲學那樣,區分出影像的未定域與既有的影像之間的差異呢?梅洛龐蒂的確掌握了交錯層疊的身體感受(sensations),但是對於這些身體感受基礎上不可見的欲動(affections)卻保持天真的、避而不談的保留態度,換句話說,他對中性的存有學論述語言建構的關切,對於大寫存有的關切,要遠遠大於對大寫存有的裂縫中展現出來的差異的關注。我們可以在他的「肉」的理論論述中掌握到這種理論特質。
@
「肉」(chair)是梅洛龐蒂晚期另一個重要的關鍵理念。我們在此同樣採用《可見與不可見》<交纏>這一章的一段文字,讓讀者參照「肉」的基本意涵:
這種大寫的可見性(Visibilité),在其自身的大寫可感者(Sensible en soi)的這種普遍性(généralité),這種天生對我自己就有的無人稱狀態(anonymat),我們先前稱之為肉(chair),大家知道在傳統哲學中沒有任何名字來指涉它。肉並不是物質,它不是存有者的微小粒子,只要彼此不斷增加就可以形成存有者。肉也不是某種可見的心靈物質,就像我自己的身體那樣,透過事實上存在的事物和它們作用在我實際上的身體而產生的心靈物質。一般而言,它並不是事實,也不是物質和精神事實的總合。肉也不是心靈的表象:心靈不可能被它自己的表象所捕捉到,它會背叛這種插入到可見者的狀態,這是能見者的重要本質。肉並不是物質、並不是心靈、也不是實體。如果要指出它,我們會需要一個古老的詞彙「培元素」(élément),就我們談到地水火氣的意義而言,它是某種普遍的事物,在時空個體與觀念之間存在,某種具有肉身化的原理,只要是有存有者的碎片存在,它就會帶出某種存有者的風格。就此而言,肉就是大寫存有的「培元素」。
這裡的「培元素」並不等於化學性的元素的意思,而是像中國古代「金、木、水、火、土」五行那樣的形上物質條件,不過,「肉」這種物質條件涉及五行之外的「肉」與「交錯層疊的身體感受」的特質,它使得可見者成為可見者,亦使得不可見者得以有物質條件轉化為可見者,所以被稱為「大寫的可見性」。梅洛龐蒂致力於將這個理念轉化為他的存有學基本概念,而無意於去展現其徹底的差異性。但是,在《眼與心》的搖擺中,又選擇了個別的視覺與繪畫問題成了展示「肉」之存有學特質的焦點,帶入了現代繪畫史的整體存有問題,然而,就此搖擺的另一端,詳細的繪畫史與繪畫史「問題場域」的轉化,卻未能得到應有的充分討論。當然,如果我們了解梅洛龐蒂的哲學手勢,與其哲學傳承,或許可以對這種愮未決的哲學姿態得到某種理解。梅洛龐蒂所認定的哲學問題場域,除了柏格森與現象學之外,我們可以再舉出一個名字,來勾勒其隱而不顯的傳承。
馬勒布朗許(Malebranche)這個名字就像柏格森的名字,經常出現在梅洛龐蒂的著作當中,從《行為的結構》到《可見與不可見》,以及1959到1961課程筆記皆然。對梅洛龐蒂來說,馬勒布朗許是17世紀最重要的理性主義思想家,梅洛龐蒂一生不斷回到馬勒布朗許的思想,在1947-1948年的課程講稿《馬勒布朗許,比朗與柏格森論身心統合》(LUnion de lame et du corps chez Malebranche, Biran et Bergson)第四講他說:現象學觀點下討論過的身心統合問題,「我們今天看到的問題,馬勒布朗許早已經看到」 ,梅洛龐蒂這這裡所指的問題是在觀念論和實在論之外的第三種選擇,它是在為己(pour soi)和在己(en soi)之間或之外、在身心之間和之外、在自我和世界之間和之外的一個介面,也就是知覺作用。在300年前,馬勒布朗許便已透過他的自然判斷學說嘗試找出這個介面。馬勒布朗許和比朗(Biran),長久以來被認為是法國哲學的經典,在梅洛龐蒂還在當學生並成為新科中學教師時,仍有許多相關的討論。譬如1920年代的辜伊葉(Henri Gouhier)、德伯斯(Victor Delbos)、布朗士維克(Leon Brunschvig)等相關著作;1934年勒華(George Le Roy)出版了討論比朗的重要著作;1939年居耶胡(Martial Gueroult)出版了高度肯定馬勒布朗許的重要著作。柏格森在1941年去世時,已被認為是法國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1946年柏格森重要的《物質與記憶》(Matière
et Mémoire)已經出至62版,梅洛龐蒂在1939年出版的《行為的結構》最後一章的標題「身心關係和知覺意識的問題」,已經很明白點出了梅洛龐蒂整個哲學道路的主要焦點,以及這個論題與當時相關討論氛圍之間的緊密關聯。
梅洛龐蒂在《馬勒布朗許,比朗與柏格森論身心統合》講稿一開始便指出法國哲學在這個問題上的兩個傳統。笛卡兒的傳統認為,心靈與身體的關聯必須藉由心靈與上帝的關係來釐清;巴斯卡(Pascal)的傳統認為,心靈(或靈魂)與上帝的關係必須藉由心靈(或靈魂)與身體的關係來釐清。梅洛龐蒂認為馬勒布朗許是屬於笛卡兒傳統,而比朗和柏格森則是屬於巴斯卡傳統。但是兩個傳統都要從對於笛卡兒思想的陳述作為起點。譬如:如果我們對照第三節與《屈光學》的內容,會發覺梅洛龐蒂所討論的「光線」、「折射」、「眼睛」、「感官」、「在眼睛基礎上形成的影像」、「視覺」、「幫助眼睛更加完美的方法」、「切磨鏡片的方式」等,與《屈光學》的討論重點形成完整的批判對立面。於是,《眼與心》所呈現給讀者的,即是回到笛卡兒的起點,進行最根本的論辯,而不是去呈現身體影像所給出的差異化運動。
然而,梅洛龐蒂的論述,並不是沒有留下差異化思考的線索。譬如,寫作<靈視者書信>的詩人韓波 ,既同時要求詩人讓自己成為無比崇高的博學的科學家和最激進的唯物論者,又要求這種科學精神通過長期、廣泛和推理思考的過程,打亂所有的感覺、道德和社會秩序,以求達到一種藝術性的「不可知」(arriver à linconnu)狀態。這裡不僅呼應了他參與巴黎公社時所抱持的理想,也突顯出一種他為自己設下的不可能的文學任務:「我是他人」(Je est un autre),「我」的存在是以成為第三人稱的他人存在為目標,一種以讓自己「成為任何人」、「生活在他方」為目的的分裂生命。這裡的身體影像未定域,無非是強調「自我」影像與「他人」影像間透過文字創作,可以形成一種無法想像、尚不存在的反轉關係。若把這種「自我」與「他者」間的反轉,轉換到畫家的眼睛與所見間進行的「使其可見」反轉工作,即成為《眼與心》所要闡述的重點。
反轉閱讀:混搭侵越與感覺邏輯
在《眼與心》中,混搭侵越(empiétement)、潛伏性(latence)這兩個概念的關鍵程度,可與「肉」相比擬。但是,這兩個概念的難解程度,並不比「肉」來得低。經過前面四節的討論,本文提議採用一種「後遺」的反轉閱讀來理解它們,也就是從這些概念的作用後效,回過頭來理解它們。其中一個可能的線索,就是用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影像哲學來看待此中潛藏的問題。德勒茲曾經在《何謂哲學?》(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當中說:
胡塞爾與他的許多後繼者那兒所發生的是,他們發現在他者(Autre)、或在肉(Chair)當中,在內勢(immanence)本身當中存在著超越者的隧道深掘機在工作……在現代時期,我們不再滿足於透過某超越者來思考內勢,我們想要透過內勢者的內部來思考超越,也就是我們等待著內勢展現出斷裂……猶太基督宗教的話語取代了希臘羅格斯的話語:我們不再滿意於把超越歸屬於內勢,我們將要讓內勢處處排除掉超越(transcendence)。
這段話明顯將矛頭之一指向了梅洛龐蒂(另一位當然就是列維納斯(E. Lévinas)),而他所謂的「超越」,也就是在《眼與心》不斷出現的「大寫存有」。但我們的問題是,從「影像」存有者的討論脈絡來看,梅洛龐蒂在整個文脈中的「大寫存有」,真的如德勒茲所言是個「超越者」嗎?首先,我們可以反觀德勒茲對於「內勢」──也就是形成某種「皺折」與「個別力量線」的純粹力量狀態──如何得到界定:「內勢只就其本身顯現其存在,並自此理解所有一切、沉浸於整體之太一(Tout-Un),不留下任何可以支持任何東西成為內勢存有物的東西。無論如何,每當我們要將內勢詮釋為與某於關聯的內勢時,我們可以肯定,這裡的某物把外在的超越物搬了進來。」
在《何謂哲學?》的這段文字中,「整體之太一」或「全一」(Tout-Un)又當如何理解呢?內勢在定義上是否也是在肯定某種超越性的整全狀態呢?不!在阿岡本(Giorgio Agamben)的詮釋下 ,對德勒茲來說,內勢湧現時,早已隨身帶著冒號;它一湧現就即刻收住它自身,這種噴出並不會流現在它自身之外,它會馬上並令人暈眩的將之保留在自己身上。這也就是為什麼德勒茲可以這樣寫。他用的表達方式已經顯示了他的寫作思考的整個狀態已經被內勢這個概念所充滿:「內勢恰恰是哲學上的暈眩。」從這個角度來看,混搭侵越(empiétement)、潛伏性(latence)這些對於身體影像、肉或事物的內部力量狀態的描述,同時也包含梅洛龐蒂對「第三維度」的討論,不僅沒有讓我們到其存有學上的「超越」地位,反而是在視覺經驗、繪畫經驗中,我們讀到梅洛龐蒂不斷在哲學上企圖逼近一種「肉」的凹折的狀態、「肉」的侵越混搭、「肉」的轉圜現象與無止境發散與凝聚的複本化運動力量──身體影像的力量只是這種內勢的一個例子,它讓哲學思考進入暈眩狀態,因為內勢永遠以一種潛伏態與具體的顯現隔開來,無法定於任何具體的影像與概念中。
不過,搖曳在這種哲學的暈眩中不久,梅洛龐蒂又忍不住似的開始強調大寫存有的種種特質,以及「肉」做為大寫存有的化現。於是,對於「肉」的存有學「超越」論述便已成形。梅洛龐蒂雖然批判笛卡兒古典存有學對大寫存有的認同,批判笛卡主義自認為人可以擁有絕對超越者的無限視覺與無限視點,但弔詭的是,梅洛龐蒂又憑什麼認定人們有或是沒有大寫存有的無限視覺呢?難道他的哲學自認為可以站在一個制高點上,看到別人的視覺限制嗎?
就《眼與心》的論述角度而言,不如說他的「肉」存有學早就肯定了哲學思考也只不過是在「肉」之中的一種語言混搭的結果,沒有絕對的外部制高點,而只有無人稱的先驗(transcendantal)場域,和與之相對立的超越(transcendant)大寫存有。先驗並不蘊涵著意識,先驗場域的界定可以說是「逃脫了所有的主體超越與客體超越」,到達一種無主體、無客體的無人稱狀態。《眼與心》明確指出,從視覺經驗來說,畫面影像當中安排凸透鏡的「前人類(pré-humain)的注視方式,正是畫家注視的徵象。」
換句話說,畫家對待影像的方式,正是必須以一種無人稱的、非主非客的態度,才能進入到影像的先驗場域中重新凹折出新的實證可能。但正是在此處,我們發覺梅洛龐蒂哲學話語上走向失去事件性、失去特異性的平板化思考。梅洛龐蒂雖然頻頻向繪畫史的既有板塊回首,去找尋驗證其存有學命題的例子──於是,這些例子就只是例子,在《眼與心》全書中,並沒有任何繪畫史上的事件,突顯出梅洛龐蒂一再宣稱的繪畫的「思考」究竟如何具有特異性?如果我們同樣拿德勒茲討論畫家培根(Francis Bacon)的例子,我們會發現培根不止是哲學論述中的「例子」,德勒茲還特意打造新的概念語彙,然後從繪畫史的內部運動(而不是大寫「肉」的運動)與某種未來性,來面對這位畫家的「繪畫性思考」。接下來,請讀者容許我們引用一長段德勒茲的《培根:感覺的邏輯》英文版的作者導論,做為這種混搭哲學或非美學論述的「例子」:
培根是個善用色彩的畫家。對他來說色彩關聯到許多不同的系統,其中有兩個特別重要,一個是畫像/肉的系統,另外一個是色場/區段系統。就好像培根已經重新規定了塞尚之後繪畫的整個問題。塞尚的解決方案基本上是透過個別的筆觸來調整色彩,按照光譜的秩序來進行,這讓兩個問題產生出來:一方面如何保留同質性或基礎的統整性,就好像它是一片垂直的盔甲,讓整個色彩的推進可以產生;而另外方面也要保留在知覺變樣當中形態本身的特定性與獨特性(singularity)?對梵谷和高更(Gauguin)一樣,這都是個新問題。這個問題帶著兩種迫在眉睫的危險,因為基礎不再被允許保持呆滯沈悶的狀態,而型態也不被允許變得陰暗黝黑或者成為灰色裝飾畫。梵谷與高更重新發現了肖像的藝術,『透過色彩的肖像』,透過保留基礎的大片單色場域,朝向無限定狀態,同時透過為肉發明新色彩,『與自然大大不同』,這些色彩看起來像在窯內被烤過,可以比得上陶器。第一種向度為現代繪畫帶來許多新穎的實驗:那些巨大明亮的單色色場,並不是透過色調的變化而得到生命,而是透過鄰接的區塊所決定的張力與飽和感的細微變化而得到生命。這就是培根的道路:這些鄰接的區塊要不然就是透過色場的區段而被引發出來,要不然就是透過一條白色延伸出來的繩帶或跨越色場的大的色帶所引導出來的。
另外的向度,肉的色彩,培根是沿著高更所鋪設出來的路線得到解決:藉由創造出破碎的色調氣氛來達成,就好像在爐子裡面烤或是被火燒透了皮。培根在色彩運用方面的天才同時存在於這些觀念之中,但是大部分的現代畫家都把心力集中在第一個方面。培根卻以一種嚴格的方式讓這兩個向度相互關聯:大塊色場的明亮純粹色調氣氛,伴隨著高度張力的演出;肉的破碎色調,伴隨著爆炸火焰和碎裂的程序,不可或缺的補充混合起來。就好像繪畫能夠透過色彩用兩種方式征服時間,一方面是在色場的無限定當中的永恆與光線,身體在墜落並且經歷著它們的步法;另外一方面是一種驅動著這些身體的通道、是一種新陳代謝的可變化性,存在於這些身體的肉裡面和皮膚上面(有三個大的男性背後請有變化著的裂縫)。這是一種色彩的時間(Chronochromie)……現代繪畫放棄了簡單造形(figuration)是一個普遍事實,任何時代的繪畫其實都在這樣做。但有趣的是培根所做的事與造像工作完全決裂:它並不是印象派、不是表現主義、不是象徵主義、不是立體派、也不是抽象主義。從來沒有任何人(或許除了米開朗基羅之外)像他這樣優秀的與造像工作決裂的把它提昇到體態(Figure)。就是在體態與色場的對質中,它們孤單的在淺薄的深度(swallow depth)中角力,讓繪畫與所有的敘說決裂,與所有的象徵化決裂。在敘說或是象徵當中,造形的工作只是保留了再現表象或意指的假造暴力,卻沒有表現任何感覺的暴力,換句話說,並沒有表達繪畫行動本身的暴力。
當梅洛龐蒂把所有的繪畫哲學敘說收斂到「肉」的存有學語言皺折界面時,德勒茲已藉由現代繪畫存中的「問題」流變,直指培根繪畫的特異性所給出的繪畫「問題場域」的新形體,也就是從繪畫史內部指出培根繪畫特別帶有的外部性「感覺的暴力」。藉由培根的繪畫,德勒茲的哲學思考似乎得到了新的外部語言混搭界面,換句話說,這是一種發散、延伸、游牧、流佈式的哲學概念思考,讓德勒茲的思考「內勢」一遭遇到不同的特定對象,即由「整體之太一」或「全一」(Tout-Un)流變出新的語言概念。我們要問:難道這種給出體態(Figure)的流變式思考方式,不是更接近繪畫式的、無人稱式的「思維」嗎?
然而,再把這裡所進行的哲學對質拉回現實的歷史與哲學的當下。我們驚覺,兩位哲學家不過是各自突顯出了他們的當下:雖然塞尚去世後40至60年左右,梅洛龐蒂還在寫他 (1945年、1961年),但是,立體主義、克利、恩斯特、昂利.米秀(Henri Michaux)不正是梅洛龐蒂非美學的「當代性」所拉出的事件、力量線嗎?以這些現代與當代畫家的思考狀態做為其哲學思考的類比,在當代美學的發展史上,可以說是胡塞爾(片段談論杜勒)與海德格(片段談及梵谷)的現象學與詮釋學往視覺哲學領域的激進行動,也可以說是波特萊爾1863年的《現代生活的畫家》之後,一個重大的哲學事件。但是,這個哲學事件的特異性,要等到德勒茲將繪畫的特異語言與哲學思考上的特異語言配對成一種勢均力敵的混搭狀態之後,也就脫離了梅洛龐蒂所採用的法國式「隨筆」(essai)、現象學與柏格森唯心論的哲學書寫傳統之後,一種新的、極度混搭的、來自影像的力量啟發的哲學書寫狀態才噴發出來。
德勒茲在培根去世前11年,也就是1981年(英文版導論是1984年)畫家72歲時,出版了《培根:感覺的邏輯》,事實上只是見證了梅洛龐蒂不可能經歷到的68年以後的精神狀態與哲學問題的遞變。「身體」、「肉」都已成為哲學場域中的老問題,被納入了德勒茲的常用語與既成問題之列,而進一步的「尖叫」、「神經纖維」、「歇斯底里」、「感覺」、「眼與手」、「前繪畫的繪畫」、「後現象學」、「後語言學」方興未艾,正在成為「當代」、「當下」與未來的哲學問題場域,不論它們是否早已在60、70年代的藝術場域中被藝術家的行動與作品所思考、以無言或過度喧嘩的方式提出。
新型哲學部署的宣言:欲望與內勢
旋進的身體影像,面對突然臨現的死亡,遂戛然而止。相較之下,我們可以說《眼與心》第四節潛藏著一種新型哲學部署的宣言:偶然、肉身、事件結構、藍圖效能、詮釋上的多元可能,但是在實踐層面上的可能,梅洛龐蒂則仍然停留在宣訴某種未來哲學思考的遙指,停留在透過視覺和繪畫經驗而提出普遍存有學論述的書寫模式,未能更進一步進入具體可見世界的「問題」中。這已經是梅洛龐蒂的思考或搖擺或暈眩的極限。畫家馬格力特(René
Magritte)曾抱怨他在閱讀《眼與心》時,感到「他談論繪畫的方式,就像藉著研究哲學家的筆架和用紙,來討論一本哲學著作。……唯一值得注目的繪畫,其存在理由與世界的存在理由沒什麼兩樣──奧祕。」
然而,如果我們從《眼與心》的行文結構來看,梅洛龐蒂在第五節一開始已明確指出,第四節或前四節針對的是「深度、色彩、形狀、線條、運動、輪廓、面貌」這些現代繪畫在繪畫過程中所「思考」的「問題」叢結,只不過,這些概念除了做為大寫存有的影像裂變例證外,欠缺進一步的理論語言反轉或非美學化、非單一語言中心的存有學的書寫行動。
當然,雕塑家摩爾對藝術的看法,或許也會讓馬格力特再次感到不耐煩。在回答他的一位姪女問他作品的標題為何都如此簡單時,摩爾說:「所有的藝術都應該有某種神秘,引發觀者的問題。如果一件雕塑或繪畫太明顯要去除了神秘,觀者就會移步往下一件事物,不會駐足努力估量他剛剛看到的東西有什麼意義了。每人個會思考他或她在看卻沒真的看見的東西。」但是,畢竟摩爾並不是哲學家。梅洛龐蒂在《眼與心》第四節文中所提到的摩爾作品型態,可以舉<帶有觸點的卵形>(Oval with Points, 1969-70)為例,更典型的是<斜靠的體態>(Reclining Figure, 1952),一個抽象的女人體態,轉切出許多開放洞眼。可惜梅洛龐蒂在此無意討論繪畫作品所呈現的視覺特異力量,使其哲學宣言停留在宣言的階段,無法深入繪畫史的「肉」與「神經纖維」內部。
但同樣是在第四節,梅洛龐蒂運用煉金術士的例子討論到「光的尖叫」,卻與德勒茲在《培根:感覺的邏輯》第五章一開始所討論的「肉頭」與教皇「尖叫的嘴」有一種奇怪的呼應(或不呼應)的關係。從「尖叫」到「歇斯底里的笑」所形成的肉與神經的無器官身體體態(Figure),似已更進一步推進了「光的尖叫」的問題。無論如何,雖然梅洛龐蒂的身體影像問題重心與德勒茲透過培根繪畫所推出的「體態」問題仍有所差距,但把兩種文本對比閱讀,或許可以掌握到偏向現象學哲學以降的「身體哲學」或存有學式的「肉」的非美學論述,與以「體態」為焦點的內勢論述的差別。如果用簡單的方式來分判這兩者的歧異點,我們可以說,當梅洛龐蒂仍以第三人稱的語言描述第一人稱的中性身體知覺與畫家的視知覺經驗時,德勒茲已經進入到運用多人稱或去人稱化的創新語言來描述第一人稱的欲動與欲望指向。
梅洛龐蒂習於把「欲望」的問題扭轉為「思考」與意義的問題。他在1945年發表的<塞尚的疑惑>(Le Doute de Cézanne)一文後半部,用現象學的觀點批判地閱讀弗洛依德(S. Freud)的<列歐納多.達文西與他的一樁兒時回憶>(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主張達文西生活在接近非人稱狀態的絕對理性精神中,如同塞尚投注其全部生命在接近純粹視覺界面的非人世界中,而超越了精神分析病理上的意義,但反過來說,梅洛龐蒂亦認為弗洛依德精神分析的詮釋方法──法國哲學家傅柯(M. Foucault)早年視之為「意義神學」的方法──有其非自然科學性的存在效力、語言效力,因為就存在上而言,任何經驗都可能充滿了「意義」。寫作<塞尚的疑惑>時的梅洛龐蒂,尚未接受語言學的影響,如果我們對照《眼與心》中達文西出現的脈絡,會發現梅洛龐蒂的關注焦點不再是主體的「兒時回憶」,而是視覺與繪畫界面中的「畫論」──圖像思考問題,是某種「運作意向性」的問題,而不是直指身體影像未定域的「欲望」運動問題。換句話說,柏格森的身體影像論背後隱藏了一個創造精神的唯心論形上學,梅洛龐蒂欲將其唯心論的形上學去除,以「肉」的運動來取代之,然而,德勒茲更進一步將「肉」的運動納入到身體影像運動的流變中,同時也轉化了柏格森的精神,成為一種純粹的內勢能量。
有趣的是,第四節末尾的採用誤譯──將「Ici-bas, je suis insaisissable.」譯為「Je suis inssaisissable dans l’immanence......」,反而引發了我們從柏格森與德勒茲所聯結的「身體影像」星群來解讀梅洛龐蒂的另一種趣味。"Ici-bas"與梅洛龐蒂採用克羅索夫斯基的法譯本"immanence"的譯法差別在於,前者中文可以譯為「此世、塵世、當世」,後者則可譯為「內勢」。如果我們採用梅洛龐蒂原來的譯法,克利的墓誌銘的意味就比較複雜了。如果略去本來的句子與顯然較為正確譯法不談,單單討論梅洛龐蒂所採用的「內勢」(immanence)譯法,克利的日記文句:「Je suis inssaisissable dans l’immanence......」可以有兩種讀法。第一種可能的讀法是:「我」無法在「內勢、內在狀態」中被理解、被掌握,如果我們把重讀音放在這個開放結尾句子的中間,強調其「insaisissable」,那麼,這種「內勢或內在狀態」當可以理解為:我無法以內在於此世間、當世的內在力量狀態被理解。但是,如果我們把加重讀音放在句首的「Je」上面,也就是句子的前半部,那麼,另一種讀法就出現了:「我」是無法被掌握的,在「內勢與內在狀態」中、在純粹的視覺經驗與其延展出來的內部力量與內在狀態中,「我」被消解了,變得無法加以理解或掌握,如果這裡還要硬說有「我」,這個「我」恐已非今世之人所能了解的「我」。那是某種「非我」之我、「無我」之我,某種視覺動物狀態的、無人稱的「我」──在未定域中旋進的身體影像。
「我要傳達給你們的是更神秘的東西;它就交錯纏繞在存有者的根柢中,交錯纏繞在種種感覺之無法觸知的源頭中。」
──加斯奎(J. Gasquet),《塞尚》
一
科學操縱事物,拒絕棲居於事物當中。它給定事物的種種內在模式(modèles),透過這些指標(indice)或變數(variable),運作出其定義範圍內所允許的變體,它只能與現實世界進行越來越遙遠的對質。科學是──而且從來就是──這樣一種思維,令人驚嘆地活躍、機智、從容而灑脫,而且早已打定主意把所有的存有者當作「對象一般」(object en général)來看待,好像它們對我們既不關痛癢,卻又註定要為我們的人工巧計(artifice)所用。
不過,古典科學對世界的曖昧不明性(opacité)仍帶有情感,過去,它情願透過自己的建構(construction)與世界重新結合,為此之故,古典科學感到有必要為自己的操作(opération)尋找超越或先驗的基礎。今天,不是在科學之中,而是在一種相當流行的科學哲學之中,我們發現一套全新的做法。建構式的科學實踐鍥而不捨地裝出自律自主(autonome)的樣子,所謂思想,不過是精巧地將自身化約為它自己發明出來的蒐集與取材的技術總合。思考就等於測試、操作、改造,唯一條件是此活動必須在實驗的控制下進行,只允許最高度「加工過」(travaillés)的現象出現,於是,這些現象比較像是由儀器生產出來,而非由儀器紀錄下來的。由此以降,展開了五花八門、飄忽無根的企圖。科學對於知識模式的敏感,莫有勝於今日者。當一種模式(mode)在某個問題序列內獲得成功時,科學就將它們到處試用。譬如:我們今天的胚胎學和生物學,充滿了各種「梯度」(gradients),我們看不出來這些梯度與古典科學所謂的「序列」(ordre)和「整體性」(totalité)有何不同,然而,這問題卻不見有人提起,甚至它不允許被提起。梯度如同一張網,撒向海裡,卻不知道它要撈出什麼。或許,梯度就像一些細微的分枝,上面將形成一些不期然的結晶。只要人們不時加以定位,不時自問一下,為什麼機具在這裡行得通,在別處卻沒有用,就可以了,只要這種流動的科學自己了解自己,只要它了解到自己的建構基礎是在於一野性(brut)、變現為存在(existant)的世界,而不是像一套觀念論哲學中所可能擁有的「自然概念」一樣 ,自認為其盲目運作具有形構的價值,那麼,操作(opération)的這種自由,當然將超越許多徒勞無益的兩難推理(dilemmes)。就唯名式的定義而言,說世界是我們所操控的對象X,就等於把學者的知識處境(situation de connaissance)視為絕對,就好比在說所有存在和曾存在的事物,都只是為了要進實驗室一樣。「操作式」思考變成了一種絕對的人工技巧論(artificialisme),如同我們在模控論的意識型態(idéologie cybernétique)中所見到的,人類的創造是由訊息的自然過程所衍生出來的,而這種意識型態又是在以人類機器(machines humaines)的模式上構想出來的。如果這種思考想要將它的勢力擴張到人和歷史中來;又如果它刻意忽略我們透過接觸交往和立場觀點對於人和歷史所獲得的知識,而如同某種在美國發生的沒落的心理分析和文化主義般,要在一些抽象指標的基礎上動手建構人和歷史,既然人真正變成了他所想成為的操縱者(manipulandum),那麼,我們便進入一個涉及人和歷史時真偽不分的文化制體(régime)當中,進入一場再不會有任何東西可以將之喚醒的沈睡或夢魘當中。
應該讓科學的思維--凌越式(survol)的思維、對象一般論的思維--重回對我們的身體來說已先行的「有」(il ya)處,重回其位所(site),亦即在我們生命中可感的、已成形的世界土壤(sol)裡。而我們的身體,指的不是那種可能的身體──亦即我們可以視之為一具訊息機器的身體,而是被我稱之為「我的」的當下身體,這個默默在我言語和行動指揮下執勤的哨兵。透過我的身體,必須與相聯的身體(corps associés)相互喚醒,所謂「他人」,不僅是動物學者所稱的我的同類,而是纏繞著我(qui me hante)、被我所纏繞的他人,我與他們又一同交纏出一個單一、當下和現實的大寫存有 (Être),而沒有任何動物曾經如此與牠的同類、領域、棲息地這般交纏。在這個原初的歷史性(historicité primordiale)
當中,輕迅敏捷、即興而發的科學思想,將學會堅決強調其自身與事物自身,將再度變為哲學……
但是,藝術,特別是繪畫,就從這一大片野性的意義中汲取養料,對於此種意義,行動主義(activisme)是不願有任何了解的。甚至,也只有藝術與繪畫以全然的天真來從事於此。我們希望從哲學家和作家那兒獲得些許意見和建議,而不允許他們讓世界置於懸而未定之中,我們期待他們採取立場,他們不應當拒絕做為發言人所該負的責任。相反的,音樂太過侷限於世界及可指涉的事物此岸,以致僅能具象描繪大寫存有的某些輪廓--它的漲落、增長、突爆與迴旋,而不及於其他層面。唯有畫家有權在注視萬物時,不帶有評價的義務。幾乎可以說,在畫家面前,知識與行動的口令失去了效力。激烈攻擊繪畫「頹廢腐敗 」的那些政體,卻很少真正去毀壞作品,他們把畫藏起來秘不示人,這種「眼不見為淨」的心態本身幾乎就是對繪畫的一種承認(reconnaissance)。人們也很少責備畫家的逃避主義。自從尼采說過「哲學無法教我們成為偉大的生命」,連最差的學生都斷然放棄哲學之後,人們卻不願責難塞尚在1870年戰爭期間避居在艾斯達克(Estaque),大家仍然懷著敬意引用他的話:「生命是令人畏懼的」。似乎在畫家的事業當中,有一種超乎其他緊急狀態之上的緊急狀態。在生活當中,無論畫家是強者還是弱者,在對世界的反覆思考當中,他卻是至高無上的。除了眼睛與手的「技術」讓他拼命去看、去畫之外,他沒有什麼別的能耐,他奮力從那個承載著歷史榮辱的喧囂世界中提汲「圖畫」(toiles),這些畫布對人類的憤怒和希望幾乎無濟於事,卻沒有人抱怨。那麼,畫家所擁有或正尋找的這種秘密科學是什麼?梵谷(Van Gogh)想要依憑著它走得「更遠」的這個維度是什麼?繪畫、或者整個文化的這個根柢又是什麼?
譯後記:
本書書名L’Œil et l’Esprit的譯法,涉及到幾個關鍵詞的脈絡理解與詮釋,譯者認為,「esprit」這個語詞必須回到這個脈絡來了解。這幾個關鍵詞就是:âme、esprit、cœur。首先,「âme」的首要意涵是靈魂、良心,較趨近思想道德的範疇,雖然「âme」也有精神、內心的意指,同時也指向感覺、意志的力量,但就《眼與心》對笛卡兒思想傳統的挑戰而言,本書的關注焦點毋寧更接近「esprit」,也就是心靈、心智、精神與思想的問題。依據Le Robert辭典的分析,在17世紀的古典生理學中認為,向動物體內各器官輸送生命和情感的東西,就叫做esprit,故有esprits vitaux(生氣、生命精氣)或esprits
anmiaux(動物精氣)的說法。譯者認為,本書的esprit包含了與笛卡兒形上學與知識論論辯和涵蓋古典之「心神、精氣」的雙重意涵,較少偏向道德意涵上的靈魂與意志問題,換句話說,《眼與心》討論的焦點是另一種「思維」、另一種「生命形式」,以視覺經驗與感覺經驗為邏輯的生命狀態,而不是以「科學概念」、「科學模型」的運作為邏輯的生命狀態。最後,「cœur」這個語詞的主要意涵是「心臟、心境、內心情感」的意思,同時也包含了道德意涵上的「心腸、心地」的意指,單就這個部分,譯者感覺到cœur缺乏本書所關注的知識論與存有學上的主要意涵,但中文的「心」這個字無疑卻能夠涵蓋esprit所帶有的知性與存在意涵。或許Le Robert辭典上的一個例子,可以很簡潔地呈現這三個詞的意涵微差:esprits élevés, mais âmes basses; bonnes têtes, mais méchants cœurs.(才智傑出,但靈魂卑劣;頭腦精明,但心腸惡毒。)基於以上的理由,譯者沿用了劉韻涵與楊大春兩位譯者的書名譯法。
「一切翻譯都是對付語言的外來性或異已性的權宜之計。」班雅明曾經這樣表明譯者的任務,這份工作的目標是為詩人「創造出原作的回聲」,他也同時認為,詩人賀德林一生中最後作品──索福克利斯的翻譯,使他「從一個深淵跌入另一個深淵,直到像是丟失在語言的無底的深度中。」
不是因為內容的表面訊息,而是文字與形式(或者中文說的「氣韻」)難倒了他。從1993年動念翻譯《眼與心》,也為此與友人組過讀書會,至今,慢慢明晰的是,梅洛龐蒂在本書中的哲學語言特質很難以說是散文或訊息性的,它是一篇濃稠的哲學長詩,似乎梅洛龐蒂一生所有的哲學思維都壓縮編碼,成為一堆堆的文字團塊。如此熟悉的陌生經驗。十幾年來,面對這樣團塊,從英文到法文,我的翻譯目標漸漸從追索作者的意向性,轉向了小說家大江健三郎所說的三角關係:「對我而言,處於法語原文(英語原文)、日文譯文和我自己的語言這三者構成的三角關係中,是一種充實的、知識的、情感的體驗。」
這個工作,或說這個翻譯的習慣,已成為我的思考語言的靈感重要來源。這份執拗──有太多人提醒我在台灣從事學術翻譯是傻子的行為──究竟是為了什麼?我想修改班雅明的警句,來說明我對語言翻譯的感受:「翻譯是對付一切語言的外來性或異己性的權宜之計。」我認為,一切語言都是外來的,當我被包覆在現代中文裡,我便失去了與我的非中文存在對話的機會,但是,如果我的思考都變成法語式的,當然我也就失去了我的中文式的生命。然而,在中文、英文、法文之間,我掙扎著與原本不存在的我講話,在不同語言三角關係之間,我自己的外來性與異己性才慢慢得到生存的領地。如果說,這本小書也是為了與我自己的對話而譯,那麼,它無異包含了過去的我、現在的我、未來的我,有一些對我而言既有的語彙,但還不至於成為陳腔濫調,另一些是正在接觸、或完全陌生的語言,最幽微者,莫過於歷經錯誤與創傷才能懂得的私密語碼,或風格。它們從柏格森、梅洛龐蒂、德勒茲的歐洲世界裡,各自拖拉著冗長的歷史,唸著喃喃密語向我走來,我解碼、再以中文編碼送往迎來,中間一晃就過了十多年。語言憔悴處,終得說再見。這才知道,譯者的任務,不過是安安心心的窩在他的三角關係裡,在字裡行間抱著希望推敲,游走,等待自己的語言扣門、應門,或所謂有朝一日,能從異鄉、深淵,從語言破碎之地,蹣跚歸來。
譯序 旋進的身體影像文/龔卓軍未定域1961年《眼與心》(L’Œil et l’Esprit)刊行於期刊《法蘭西藝術》(Art de France)創刊號,1962年春天,梅洛龐蒂死於心臟病。所有後續言說的中斷,將這篇文章推向了一個未定域。至今我們仍可以查到1962年的美國藝術文獻評論The Burlington Magazine上,某位評論者認為:「梅洛龐蒂教授討論藝術家的視覺時,哲學行文風格如此有意隱晦艱澀、如此雜亂無章地呈現,使其論點不知所終。」 表達了對這篇處於未決狀態的文章極其不滿之意。就像是一個死前留下的謎語,像是電影<大國民>(Citizen Kane)裡面的...
目錄
1. 出版緣起
2. 主編的話/潘示番
3. 推薦序/林保堯
4. 譯序/龔卓軍
5. 前言
6. 內文(含原註、譯註)
7. 譯後記
8. 延伸閱讀
9. 索引
1. 出版緣起
2. 主編的話/潘示番
3. 推薦序/林保堯
4. 譯序/龔卓軍
5. 前言
6. 內文(含原註、譯註)
7. 譯後記
8. 延伸閱讀
9. 索引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25收藏
25收藏

 72二手徵求有驚喜
72二手徵求有驚喜




 25收藏
25收藏

 72二手徵求有驚喜
72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