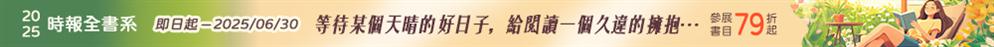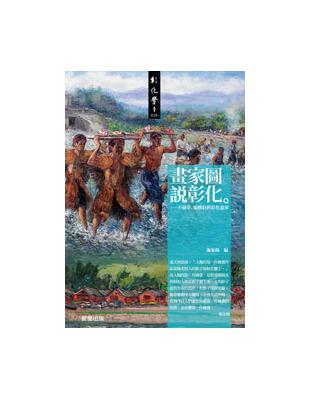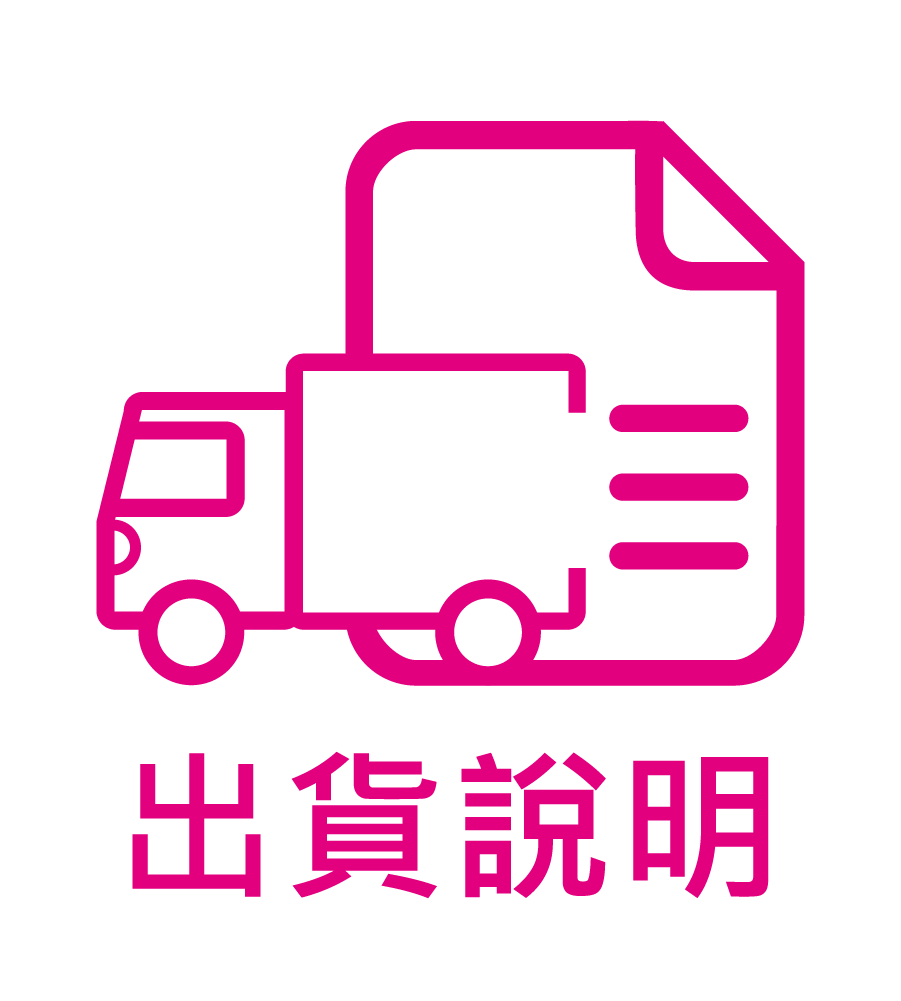名人推薦:
大地有美有感傷──施並錫的土地新傳
李欽賢 美術史學者
1.唯一不變的是「常變」
跨世紀的台灣面臨政治、經濟、社會的空前巨變,傳統詩詞常讀到的「景物依舊人事已非」之類的人文嘆息,已無法適合當今的時代觀照。敏感的藝術家絕不想依憑既有的吟詠山水、展現技巧之本領,繼續討好世俗與市場。畫家施並錫更發現「常變」反而是世事唯一不變的現象。他否定了過去他自己的慣性與類型,細心觀察大地生命存亡的訊息。
敏感,是藝術家發人之所未省者;感受,是藝術家喚出創作的痛苦與狂歡。這樣的作品窄看滿目瘡痍,卻是藝術家所看到的事實,亦即施並錫畫筆下「常變」的生態寫實。
「流嬗大地」主題屬施並錫跨世紀的力作,幾乎全是百號以上的大畫面,涵蓋了世紀末台灣接受大地反撲的震盪以及迎接新世紀台灣的陣痛。時代大變遷,大地大翻滾,山河大動搖,無奈的台灣越過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地震,再度站起來,展現浴火重生的希望。
施並錫的心痛是痛定思痛,從痛處反思,於是土石流的禍首─檳榔、肆虐美麗島歲月的天災─地、水、火、風四連作,還有八掌溪事件人為疏忽所造成的悲劇,以及高屏溪大橋斷裂事故,都上了施並錫巨大的畫幅。其所產生的震撼已非單純的報導性圖像可堪比擬,施並錫以探究真相的原理,把他的感受畫出來,讓人們面對畫作勾起史詩的衝擊。施並錫探究事件真相有治史的宏觀,還有對土地一貫的深情,只有這樣的藝術家,才有敏銳的時代嗅覺於先;表達強烈悲鳴的感受於後,建構了施並錫「流嬗大地」之與時代無法脫勾的系列巨作。
高屏溪大橋斷裂於公元二千年八月廿七日,這座橋齡不長的水泥公路大橋,事實上仍抵不過一九一四年竣工的高屏溪鐵道橋。斷裂紀事搬上畫面,施並錫的感觸是橋下「流水依舊景物流變不已」,橋斷的成因包藏了盜採砂石、偷工減料的嚴重性。是以作者畫斷橋紀事也要揪出禍源,甚至所有「流嬗大地」系列大畫幅,皆以顛覆福爾摩沙舊圖像,提出新觀照、新詮釋,一切思惟的基礎,在於深入究明台灣「常變」的生態現狀。
2.台灣美的焦慮圖像
施並錫「流嬗大地」系列巨作頗有今人觸目驚心的畫面,是作者道盡台灣之美前的憂心。憂心下的土地新傳統換成圖像,傷痕累累,作者以歷史情懷和地理認知,尋索焦慮中的台灣,呈現不同角度的台灣美術。
台灣美術已然走出唯美的、山光水湄的尋常焦點,注入爭議論題,借力使力,突顯風景的人文性與社會性,擴張繪畫版圖無限上綱,台灣之美脫離純欣賞,接近了反覆思考的地步,這就是施並錫新作的時代意義。
台灣美術的焦慮圖像極少出現於美術史上,有一陣子模仿西方超現實主義手法呈現的哲學式焦慮,並沒有與土地共生詠嘆的情緣,那畢竟是彼時新生代青年的感時傷懷,是白色恐怖時期的心靈出口。今天施並錫所拋出的焦慮圖像,都是近年來台灣發生過的血淋淋事實,從八掌溪四名待救的工人到「賽龍舟」乃至「民意如流水」的萬頭鑽動,作者以人作議題,隱喻生命的尊嚴與人性的浮躁,其實這也是現代台灣人的寫照。
選舉與慶典已成為今天台灣人心沸騰的另類舞台。「飛龍在人間」,作者藉龍圖騰諷喻封建霸權,畫中背景選在同具權威性的建築物大門,依線條走勢營造龍騰與飛簷絞結的筆力,刻劃龍威盤據咱土地的反諷場景。
至於人潮是盲從的、不由自主的,施並錫視民意也是一種流水,賽龍舟是群策群力順水而流,都是很現實、很俗民化的集體行動。時間一到人群流逝,期待下回再聚。
台灣美術也很少有此般熱鬧場面,本來可以用歡笑的嘉年華會來處理,但是施並錫卻以冷眼省視群眾中的個人意志,都捲進浪潮裏去了。
現階段台灣美的焦慮圖像,是施並錫「流嬗大地」的創作主題,放大開來就是台灣跨世紀的大紀事。這樣肯與時代共嚐滋味的藝術家不會很多。焦慮圖像也許不美,但也非完全醜陋,它是台灣美的時代經驗,端看藝術家怎麼轉化,怎樣表達。
施並錫選擇平面性的油畫,以畫與畫的呼喚,人與畫的對語,為維護台灣美,期待台灣要更美,面對大畫布坦誠告訴大家:大地有美也有感傷。
什麼都變了,只有流水不變。流水好比光陰,時間過去,世間無常一直持續。「常變」是以成為不變之理。跨向廿一世紀的台灣,承受遽變,浴火鳳凰,未來土地傳記勢將重寫。
處理流變時代繁華都會,車流亦如流水,「川流不『熄』一作就是我們習以為常的城市夜景。快速、華燈映照出一幅流光似水的畫面,夜間行車交錯奔馳,是回家或赴約,交代了現代人生活的律動。車子擦身而過,人的距離愈來愈遠,也是現代人的寫照。作者畫車流燈光以彩管代筆,宣洩如柱,一氣呵成。
台灣美的焦慮圖像可以說是施並錫的土地新傳,對台灣跨世紀提出福爾摩沙圖像的新詮釋,舉凡生態破壞、土石流禍首、大地震現場、水火災變的無情等等,珍惜大地之美,痛陳現實感傷,施並錫為台灣美術留下傷痕美感,留下記錄,留下見證,一切都為這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