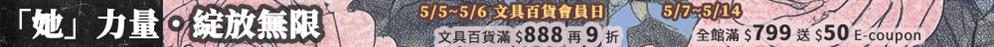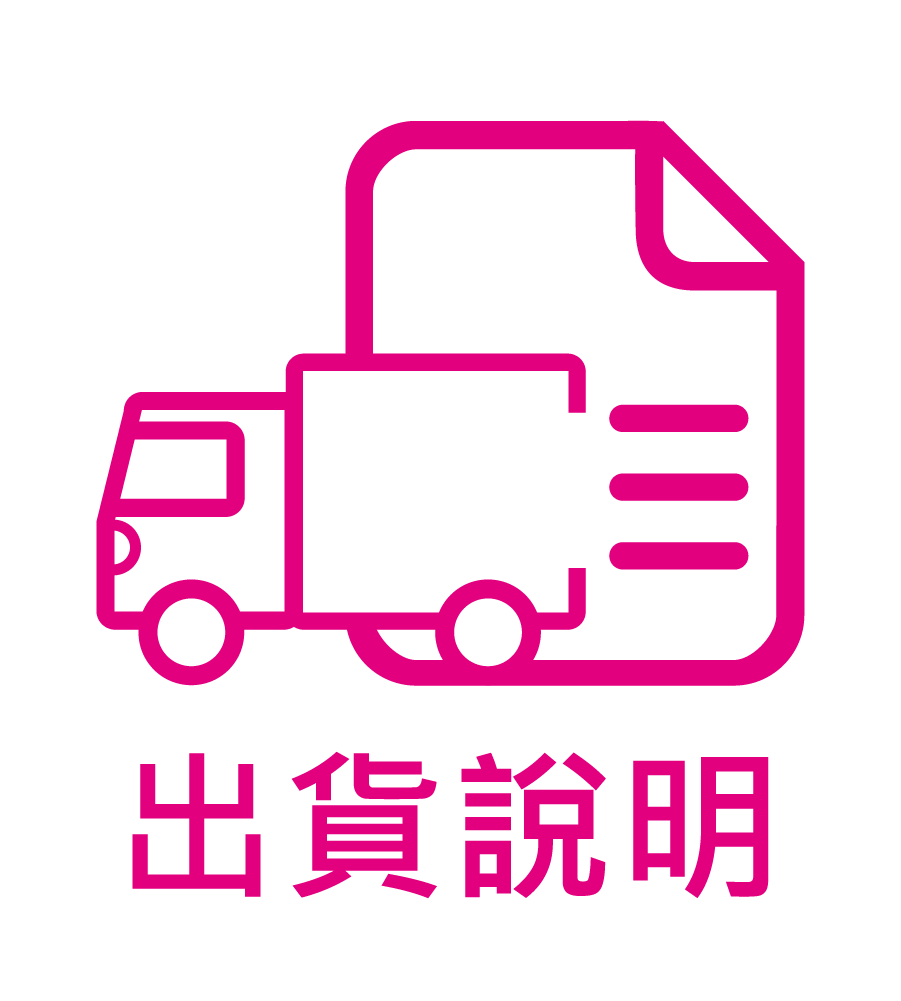「儘管臺灣已經民主化,但至今因內部存在不同的歷史記憶而爭辯不已,也因資源配置、國家目標差異,不時引發衝突。民主化之後新生的臺灣共同體仍須戰戰兢兢、努力維繫認同與向心:包括如何增進臺灣這塊土地上先來後到不同族群之間的相互理解;如何對一起走過的苦難與變革形成集體記憶、產生共感;如何使不同群體的權益都能獲得確保、人們得以安身立命,並珍視由此而來的幸福感與成就感。當人們不僅滿意並珍惜現在的生活,且願意為未來攜手打拚、挺身護衛,臺灣共同體才能夠堅定凝聚、屹立不搖。」
何謂「臺灣人」?這是一九二〇年代臺灣知識分子提出的問題,百年來不斷迴盪,鋪展出一條追尋認同的崎嶇道路。本書將帶領我們回溯從日治中期到戰後初期,臺灣國族認同逐步確立的曲折歷程。
故事始於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與文化協會的誕生。知識分子喊出「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試圖透過政治與文化運動激發臺灣人的集體意識。這些努力雖取得顯著成果,但範疇局限於菁英階層,未能廣泛滲透大眾生活。
作者隨後探討了日治時期臺灣認同與祖國情懷的糾葛,尤其是吳濁流等知識分子的「祖國想像」。他們對中國懷抱理想化情感,儘管親眼目睹其貧困與混亂,仍為之辯護。這種感性壓倒理性的矛盾心理,為戰後的幻滅埋下伏筆。
中日戰爭爆發後,戰爭體制進一步加深認同的複雜性。割臺世代的林獻堂在中國情懷與現實政治之間苦苦掙扎;大正世代的吳新榮努力平衡順應與抗拒;戰爭世代的葉盛吉起初深受帝國教育影響,積極同化,最終仍轉向認同臺灣。在鋪天蓋地的皇民化宣傳下,三代人都沒有「成為日本人」,反而對鄉土的愛日益深摯。
戰後,國民政府接管之初曾讓臺灣人充滿期待,但腐敗、壓迫與歧視很快摧毀了這些幻想,二二八事件更宛如覺醒的催化劑。作者指出,正是日治時期累積的反殖民抵抗經驗,使戰後臺灣人面對再殖民情境時迅速奮起,更在遭遇殘酷鎮壓後凝聚出「非靠自己不可」的國族意識。
《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1920-1950)》橫跨日治與戰後,精心勾勒被忽略的歷史連續性軌跡,並結合多樣史料與個體經驗,細緻還原臺灣認同從萌芽、擺盪到成形的動態過程。這段從挫折中奮起、在失望中重塑自我的歷史,絕對是我們思考當前認同議題與未來集體方向的重要基石。
作者簡介:
陳翠蓮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博士,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曾任《自立晚報》記者,後任教於淡江大學、政治大學。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臺灣政治史、戰後臺灣政治史。主要著作有《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自治之夢:日治時期到二二八的臺灣民主運動》、《政治檔案會說話:自由時代公民指南》(合著)、《重探戰後臺灣政治史:美國、國民黨政府與臺灣社會的三方角力》等。
各界推薦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導論
一九八〇年代臺灣政治社會運動風起雲湧,衝擊威權體制,長期受壓抑的臺灣史研究因體制鬆動開始活絡,青年研究生更一馬當先投入日治時期研究,尤其有關日本統治評價與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受到矚目。接著,一九九〇年代以來在民主化、本土化趨勢下,有關「臺灣認同」、「臺灣民族主義」成為人文社會學界最熱門的學術研究課題。
事實上早在一九七〇年代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危機時,臺灣就曾出現一波回顧日治時期歷史文化熱潮。當時有一批知識分子、文學家與政治運動者,開始關注日治時期新文學運動、政治社會運動,他們以中國民族主義抗日框架理解日治時期的運動,要求重視臺灣本土歷史,從事政治改革,而被社會學者蕭阿勤稱為「回歸現實世代」。
雖然兩波臺灣史研究的興起都與時代背景有關,但一九九〇年代這波熱潮與前者明顯不同:一則臺灣剛剛擺脫威權體制壓迫,不需再受由上而下的中國民族主義框架限制,得以在較為自由開放的條件下貼近歷史事實,從事探索與思考。二則因為民主化、本土化啟動,人們對於臺灣未來發展充滿樂觀期待,相應之下更熱切希望瞭解我族的身世、共同體形成的歷史,藉以自我定位、凝聚共識與展望未來。第三,前一波熱潮以文化界人士為主,後一波則因為威權管制解除使學術環境鬆綁,學界青壯代研究者大量投入,開展了與過往不同的研究路徑,使得臺灣認同研究得以在國際經驗下進行理論性的探討。
由於新生政治共同體對自身歷史的探索焦慮與集體需求,一九九〇年代臺灣史研究的重心集中在日治時期,有關「臺灣認同如何形成」、「臺灣人是一個民族嗎」、「臺灣人是否追求獨立」等成為核心議題。
筆者的學術研究工作正是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展開。一九八七年六月筆者以日治時期臺灣文化協會為主題取得碩士學位後,仍無法回答以下問題:一九二〇年代臺灣政治社會運動被總括為「臺灣民族運動」,但是這些運動並未公開訴求建立自己的國家,這樣可以稱為「臺灣民族主義」嗎?甚至,日治時期政治社會運動也不曾明確訴求與中國的關係,這樣可以算是「中國民族主義」?既非臺灣民族主義、也非中國民族主義的運動,可以稱得上是「民族主義運動」嗎?
一九九四年六月,筆者完成以二二八事件為主題的博士論文,心中更大的困惑是:戰後初期批判國民黨政府統治的人們,與日治中期政治運動者高度重疊,日治時期他們抵抗殖民統治,戰後迎來了中國政府不久,卻爆發更大規模、全島性的反抗行動。從日治到戰後,臺灣人一再反抗,究竟他們在追求什麼?
長期以來臺灣史的分期習慣以統治政權為依據,近四百年來的臺灣史被分為荷治、明鄭、清領、日治與國民黨統治時期,這顯然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來看歷史,統治政權一換手,就開啟了新時期。此種歷史分期與臺灣社會割離,並未考慮人民生活變化、經濟發展型態、都市化程度、社會整合狀態等各方面的轉變,也未關照到土地上人群集體意識的形成與發展。因此,以統治者作為政治史分期標準的作法並不合宜,有重新考量的必要。
日治中期一九二〇年代以來,知識分子所帶領的臺灣政治社會運動,抗議日本殖民帝國統治,標舉「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並對集體未來進行討論。二戰結束後,殖民者戰敗離去,新統治政權到來,在短短時間內就爆發全面性抵抗,糾葛已久的認同問題受到劇烈衝擊。筆者認為,從日治中期到戰後初期,大約一九二〇至一九五〇年代,是臺灣政治史上國族主義形成的重要階段。
一九八七年解嚴以來,臺灣有關國族認同爭議一波又一波,從國會全面改選的代表性疑慮、臺北市長選舉的「中華民國滅亡」恐懼,到《認識臺灣》教科書的親日反華指控,每每引發臺灣社會激烈衝突、對立。值得注意的是,臺灣認同相關問題並非解嚴以後才出現,只是戰後戒嚴近四十年期間遭到強力壓制、掩蓋,民主化之後終於得以重見天日、公開被討論。
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們,何時開始出現以全臺灣為規模的集體意識?為何以「臺灣人」自我命名?又如何思考群體的政治處境與未來歸屬?這在任何國家的政治史上都是最核心的議題。重新爬梳一九二〇到一九五〇年代土地上人們的集體思維與情感,追溯臺灣認同形成的過程,將有助於廓清戰後臺灣國族認同問題的來龍去脈,提供不同族群間相互理解與對話的基礎。
(中略)
【三、本書各章節與內容】
本書以國族認同與反殖民抵抗為主題,筆者認為,日本帝國與殖民地臺灣不能以簡單的日本/臺灣、殖民╱被殖、壓迫╱反抗、抵抗╱協力等單純的二元對立觀點視之,而是在「西洋─日本─臺灣─中國」的多重關係與脈絡下,其間的認同與抵抗複雜交錯,必須更加細膩的進行剖析與觀察。
本書由一系列論文所組成,各篇論文環繞著國族認同與殖民抵抗的共同焦點,並依時間順序列論。導論部分針對本書的問題意識、研究範圍、主要概念與架構加以說明,全書主體七章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探討一九二〇年代臺灣人的抵抗運動,分別包括三章。第一章〈自治主義的進路與局限〉探討一九二〇年代以來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為主的自治主義路線政治運動,其揭櫫的訴求、理念與運動推進,藉此觀察殖民者與被殖者之間相互滲透的錯綜關係。自治主義運動展現了殖民地人民的自主意識,也標示出臺灣人共同體的範圍與自治目標,並穿透殖民者陣營尋求助力;但自治主義運動受日本內地大正民主運動影響甚深,臺灣人自我形象認知也受統治者所建構的殖民論述限制,體制內抵抗路線終有難以突破的困境。第二章〈以文化作為抵抗戰場〉,透過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七年《臺灣民報》中有關臺灣文化的論述,來分析文化協會分裂前知識分子對臺灣文化的想像與建構。此時期的臺灣文化論述跳脫出本土主義或同化主義的兩極窠臼,追求自由、尊嚴、平等、進步等近代價值與精神文明,隱含著超越殖民母國、直接取法其背後更高位階文明的企圖,並希望透過自主的語文工具與近代文明接軌。但語文工具的選擇涉及共同體想像與便利性等問題,存在實際困難;又,偏向菁英主義、激進型態的文化改革取向也與傳統文人及普羅大眾出現緊張關係。第三章〈菁英與群眾:文化協會、農民組合與臺灣農民運動〉鑿討論抵抗運動中不同階級的思考取向與行動落差。一九二〇年代以來的臺灣文化協會反殖民抵抗運動固然開拓了社會氛圍與行動空間,但因菁英所訴求的政治社會運動目標與農民的現實生活需求未必一致。從史料與數據檢證,農民運動的發展並非來自知識菁英的介入或遵循菁英的指導,而是依據農民自身的理性邏輯行動,進退之間實保有高度的自主性。
第二部分析臺灣認同與漢人認同的糾葛,參考史密斯所提示「先在族群情結」在國族想像中不能忽視的重要性,分析臺灣認同形成過程中「祖國情結」的影響。臺灣社會組成以漢人為主,此一先在族群差異經常成為抵抗運動者主張無法同化於日本的理由;同時,日本政府的殖民壓迫更讓臺灣人寄情期待於「祖國」。第四章〈想像與真實:臺灣人的祖國印象〉,以謝春木、黃旺成、吳濁流、鍾理和四人的遊記與文學作品為文本,探討一九三〇至一九四〇年代知識分子所懷抱的祖國情懷。族群情結帶有強烈的情感特性,日治下的臺灣人並非沒有機會認識中國,例如四人的祖國之旅都不約而同地發現中國的落後性與遲滯性,但卻又都一廂情願地為祖國辯護,顯現情感取向壓過理性思辨、感性期待凌駕於眼見真實的現象。臺灣人對祖國的情感、包容與期待,是日本戰敗戰後臺灣社會歡迎中國統治的主要原因。第五章〈戰爭、世代與認同:以林獻堂、吳新榮與葉盛吉為例(1937-1945)〉,透過不同世代三人的日記檢視戰爭體制下臺灣人的生活實況、進退選擇與國族認同變化。戰爭局面迫使臺灣人在日本與中國之間做出抉擇,割臺世代林獻堂與大正世代吳新榮都各有應付時局要求的對應方法與生存之道,自幼受帝國教育戰爭世代葉盛吉,則有鮮明的日本認同,不同世代間出現呈現認同差異。本章也指出,戰爭時期的官方宣傳固然影響局勢判斷,決戰局面也迫使殖民地人民與母國利害與共,但臺灣人與總督府的協力關係仍存在明顯的權宜性質,戰火下保全鄉土的意志與本土認同則明顯增強。
第三部探討戰後初期的認同衝擊。第六章〈「新生臺灣」的頓挫:延平學院創立始末〉以「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與延平學院的創立經過,梳理戰後初期臺灣知識分子積極建設臺灣的熱情如何遭受挫折與打擊。臺灣菁英原本以為祖國重光,從今而後可以重做主人,繼而熱心建設鄉土,以此奉獻於國家。但是中國政府不信任臺灣菁英,不但阻撓他們插手高等教育,並藉二二八事件加以清除,延平學院的遭遇是戰後初期臺灣菁英處境具體而微的縮影。第七章〈戰後初期臺灣人的祖國體驗與認同轉變〉,透過對比戰後初期的官方作為與民間期望,呈現政治從屬化、文化汙名化的再殖民現象。戰後初期的祖國體驗,令臺灣社會大眾強烈感覺如同日本統治下的殖民情境,日治時期出於反殖民抵抗而形成的臺灣人認同重新被喚起,追求臺灣自治的政治目標、文明進步的文化理念再度登場,有關臺灣前途的各種方案陸續被提出。在此脈絡下,二二八事件並非突如其來的偶發意外(accident),而與日治以來的反殖民抵抗經驗有著密切的歷史關連。
結論部分將總括本書的發現。筆者將以國族主義理論作為參照,指出一九二〇年代臺灣人共同體意識形成的原因、特性;此些特性在戰後初期如何被延續,並形成對新統治者的另一波抵抗行動;最後提示一九二〇至一九五〇年代臺灣人認同形成與抵抗行動所呈現的重要意義,作為思考臺灣社會當前認同議題與未來集體方向的基礎。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導論
一九八〇年代臺灣政治社會運動風起雲湧,衝擊威權體制,長期受壓抑的臺灣史研究因體制鬆動開始活絡,青年研究生更一馬當先投入日治時期研究,尤其有關日本統治評價與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受到矚目。接著,一九九〇年代以來在民主化、本土化趨勢下,有關「臺灣認同」、「臺灣民族主義」成為人文社會學界最熱門的學術研究課題。
事實上早在一九七〇年代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危機時,臺灣就曾出現一波回顧日治時期歷史文化熱潮。當時有一批知識分子、文學家與政治運動者,開始關注日治時期新文學運動、政治社會運動,他們...
章節試閱
結論
一九二〇年代是臺灣政治史上無法忽視的重要年代,儘管殖民體制日益穩固、帝國權力深入掌控臺灣各處,但就如同安德森所指出的,殖民地知識分子到殖民母國學習而引發殖民地民族主義運動,臺灣知識分子也是從帝都東京出發,開始了自我發現之旅。一戰後威爾遜總統的殖民地自決主張帶起風潮,接著,朝鮮三一獨立運動的劇烈衝擊,刺激臺灣知識分子思考自身的處境,進而自問「我們是誰」?「我們該如何解放」?日本內地多元思潮交織激盪,普選、婦女、無產運動多重展演、俄國與第三國際的革命路線引領,也使臺灣知識分子得以貼近國際脈動、與世界接軌,從殖民母國取得近代思想武器的他們,迫不急待點燃啟蒙之火、號召同胞,開始了豐富而奇妙的文化構築與共同體認同追尋旅程。
這是臺灣歷史上首次以近代式社會運動模式進行媒體宣傳、策略動員、論述建構的經驗,範圍所及不僅在政治抵抗層面,更擴及社會動員、文化建構。知識分子們認真面對統治關係、殖民體制,盱衡情勢提出具體政治訴求,並透過組織動員說服、號召一般大眾。他們也急切地引入西方文明價值,構思理想臺灣的圖像,並以「世界的臺灣」自我期許。日治中期反殖民運動撐開了相對自由空間,也為底層農民大眾營造有利條件,農民抗爭行動蓬勃一時。日治中期政治社會運動的高峰雖然只有短短十年,即因中日戰爭迫近橫遭壓制,但因反殖民運動凝聚而來的共同體意識,卻留下深遠影響。
然而在臺灣人共同體意識形成的同時,漢族血緣意識緊緊相隨。臺灣社會的主要構成來自漢族,即使近代知識分子也難以擺脫血緣意識,不斷影響集體的未來想像。
好不容易熬過戰爭考驗,臺灣人終於喜見光明,期待「出頭天」。戰後,知識分子欣喜返鄉、企盼建設「新臺灣」,臺灣社會則熱烈歡迎祖國政府、慶祝光復。不料,走在與臺灣不同歷史道路上的祖國,無法理解臺灣人的集體情感與熱切期望。八年抗戰的祖國以日本為敵,不但拒絕任用受日本統治五十年的臺灣人,更認為必須清洗深受「奴化毒素」的臺灣社會。臺灣人敏銳地察覺到戰後的「再殖民」情境,儘管異族離去、卻換來同族的再殖民。於是,日治時期因反殖民、反壓迫而形成的集體意識被喚醒,知識分子們的自治主張再次上場,在官民無法相互溝通理解的情況下,最後並爆發全島性的抵抗行動。
本書梳理一九二〇至一九五〇年有關「臺灣人」的出現、政治共同體認同,以及當時人們對於集體命運與未來方向的思考,這些課題有助於增進臺灣社會的自我認識,更對當代臺灣具有現實意義。以下是本書的幾項主要發現。
【一、反殖民、反壓迫而形成的臺灣集體認同】
一九二〇年代是臺灣人共同體意識形成的起點。日本帝國在殖民地所建立的有效統治、交通電信建設、媒體流通、教育與語言等近代性工程,為共同體形成提供了基礎條件;但更明確而言,臺灣總督府為了確保帝國利益所採取的殖民體制、差別待遇、壓榨掠奪而引發的反殖民運動,才是促使臺灣人區別「我者」與「他者」的動力。臺灣知識分子到母國留學,見識到內地相對平等開放,並面對國際殖民地自決風潮,強烈感受殖民地臺灣處境堪憐,必須奮起改變,因此訴求「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主張設立以臺灣為規模的民選議會。反殖民、反壓迫,是臺灣人抵抗運動的起因,也是「臺灣人」意識形成的起點。
值得注意的是,臺灣人的反殖民運動有其特殊之處:其一,在文化上,異於許多殖民地以本土文化對抗殖民文化,殖民地臺灣與帝國日本之間並非二元對抗關係,而是呈現「西方─日本─臺灣」的階序關係。其二,在政治上,臺灣人並不像許多殖民地那樣以獨立為目標,而是一方面在承認帝國統治的前提下,希望提升臺灣人參政權利;一方面又基於漢族血緣而對中國存在情感上的憧憬,形成「日本─臺灣─中國」的三角關係。
先談文化層面,臺灣知識分子的世界文明圖像中存在「西方─日本─臺灣」三層階序概念,臺灣處於世界文明的最底層,人民蒙昧未開,尚待啟蒙方能重新打造文化。他們並不以臺灣文化對抗日本文化,而是借重更上位的西方文明作為武器,批判日本帝國的落後性。帝國/殖民地之間並非同化/對抗關係,臺灣知識分子直接取法西方價值,藉以超越日本媒介的二手文明,用「近代化」抵抗「日本化」,展現出激進改革傾向。在近代性的基礎上,臺灣知識分子更構想多元融合、吸收創新、貢獻於世界的臺灣文化,而充滿高度建構色彩。
【二、臺灣人政治性格中的務實面向】
日治時期的反殖民運動追求體制內改革,相較於日本另一殖民地朝鮮以追求獨立為目標,並為此付出慘烈代價,臺灣的抵抗運動溫和許多。
一九一九年三一獨立運動被鎮壓後,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對「朝鮮問題」也不予理會,朝鮮志士企圖透過外交途徑尋求獨立的努力也完全失敗,民族主義運動陣營因此出現分化,溫和派的朝鮮自治路線與激進派的朝鮮獨立路線分裂。朝鮮總督府拉攏自治派作為懷柔手段,一九二五年提出朝鮮自治論,規劃「朝鮮大」的地方議會。但是,朝鮮自治運動被視為親日、妥協的運動,遭到輿論批判、同胞唾棄,在敵對的社會氛圍中,無法公開論述,力量相當微弱。主張朝鮮人盡速同化為日本人以獲取國民權利的「朝鮮國民協會」會長閔元植,甚至遭到朝鮮青年刺殺身亡。
與朝鮮抵抗運動比較,臺灣人的反殖民運動具有高度務實性格。目睹朝鮮的重大犧牲,臺灣知識分子們權衡得失,放棄激烈的獨立運動,但又不願接受統治當局的同化政策,於是提出確保臺灣特殊性的第三條路──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灣議會運動並不像朝鮮一樣遭到內部批判、反對,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三四年持續進行,成為一九二〇年代反殖民運動的主要路線。但是,當議會請願運動以「反殖民運動統一戰線」的型態出現、成功凝聚臺灣人的抵抗意志時,臺灣總督府終究無法容忍,而施以各種手段分化、圍堵、打壓。
臺灣人為何選擇此一溫和的抵抗路徑?對大多數人而言,臺灣沒有自己的國家經驗,缺乏朝鮮一樣激烈的國族主義抵抗熱情,何況面對日本帝國強大的近代軍事武力,手無寸鐵的人民如何以卵擊石?朝鮮三一獨立運動的血跡斑斑是最好的教訓。所以,一九二〇年代臺灣知識分子採取議會設置請願的溫和路線,正是在上述條件下理性抉擇的結果。
其次,因為理性務實,臺灣人的政治運動往往流露事大主義傾向。一九一五年臺灣士紳曾經呼應日本民權運動板垣退助倡議,組織「臺灣同化會」,以接受同化的前提換取平等地位。臺灣同化會所追求的參政權與平等待遇目標,引起在臺日人的高度戒心,遂與臺灣總督府聯手打壓、解散該會。一九二八年日本實施普選,殖民地參政權仍未開展,蔡培火出版《日本本國民に與ふ》一書,企圖說服日本內地人民理解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回應殖民地朝鮮與臺灣人民的請求。蔡培火說,清廷割讓臺灣時,大多數臺灣民眾只視之為兩國國勢變化所造成的「莫明所以的命運」而已,並未有亡國的屈辱感。臺灣人的反抗運動其實是始於日本統治的實際體驗,因為總督府的壓迫、他族侵害,才激使我族奮起自我保衛。他強調,「政治是講究實感的東西,安身立命是第一要務」,因不滿總督府的「同化政策只是榨取的別名」,臺灣人在強烈反感下不得不抵抗;相反的,如果日本政府能保障殖民地臺灣平等安定,就算不鼓勵同化,人們自然會去達成。蔡培火露骨地表達了政治現實主義者的想法:其一,臺灣從來只是帝國邊陲,主權移轉只被視為「莫明所以的命運」而已,誰來統治並無強烈好惡;其二、政治講究實際利益,只要日本統治者能讓臺灣人安身立命、保障平等權利,同化為日本人不是問題。但日本統治五十年終究難以做到一視同仁,同化政策難竟其功。二戰結束,殖民母國戰敗,臺灣人並未訴諸自力更生,而是再度將希望寄託於祖國,希望成為戰勝國的「一等國民」。
臺灣人事大主義的形成,除了因為利益權衡,恐怕也與殖民體制弊害難脫干係。本書第二章指出,在統治者的建構下,臺灣人素質低下、落後無能、貪財怕死等殖民論述深植人心,扭曲了殖民地人民的自我認知。臺灣人缺乏自信、自我禁錮,未曾想像能夠成為自己的主人、自我統治,戰後迎來了新統治者,繼續遭到高高在上的祖國文化鄙視貶抑。從日治到戰後,這種統治者/高尚vs.臺灣人/低俗的霸權論述輪番荼毒,歷經多重殖民經驗的臺灣人深受其害。
難得的是,儘管臺灣人的抵抗運動溫和、務實,但卻也充滿韌性。日治時期透過體制內的折衝、跨越、你退我進、討價還價,持續與強者周旋;日常生活中損傷有限的邊緣戰鬥有助於持久抵抗。此種彈性務實的抵抗策略也展現在農民運動中,蔗農、佃農反抗的目的在尋求生活改善,並非你死我活的零和賽局。一九四〇年代,即使在戰時體制與皇民化運動高壓下,臺灣社會仍有其應對之道,以拖延、應付、轉化,抵銷同化收編的作用。直到戰後威權體制建立,臺灣人的日常抵抗仍舊上演,雖然大多數民眾為了生活與工作必須妥協、叮囑子弟遠離政治,但人們的沉默並非等同於馴服,許多人私下小心翼翼傳遞二二八記憶、閱讀禁書與黨外雜誌、挹助民主運動。此種日常的、非正式的、邊緣的、持久的抵抗行動不曾間斷,終於在一九八〇年代有利國際結構下獲得翻轉體制的機會。
(下略)
結論
一九二〇年代是臺灣政治史上無法忽視的重要年代,儘管殖民體制日益穩固、帝國權力深入掌控臺灣各處,但就如同安德森所指出的,殖民地知識分子到殖民母國學習而引發殖民地民族主義運動,臺灣知識分子也是從帝都東京出發,開始了自我發現之旅。一戰後威爾遜總統的殖民地自決主張帶起風潮,接著,朝鮮三一獨立運動的劇烈衝擊,刺激臺灣知識分子思考自身的處境,進而自問「我們是誰」?「我們該如何解放」?日本內地多元思潮交織激盪,普選、婦女、無產運動多重展演、俄國與第三國際的革命路線引領,也使臺灣知識分子得以貼近國際脈動、...
目錄
新版序
舊版序:在困惑中前行
導論
【第一部 一九二〇年代臺灣人的抵抗運動】
第一章 自治主義的進路與局限
第二章 以文化作為抵抗戰場
第三章 菁英與群眾:文化協會、農民組合與臺灣農民運動
【第二部 臺灣認同與漢人認同的糾葛】
第四章 想像與真實:臺灣人的祖國印象
第五章 戰爭、世代與認同:以林獻堂、吳新榮與葉盛吉為例(1937-1945)
【第三部 戰後初期的認同衝擊】
第六章 「新生臺灣」的頓挫:延平學院創立始末
第七章 戰後初期臺灣人的祖國體驗與認同轉變
結論
注釋
參考書目
索引
新版序
舊版序:在困惑中前行
導論
【第一部 一九二〇年代臺灣人的抵抗運動】
第一章 自治主義的進路與局限
第二章 以文化作為抵抗戰場
第三章 菁英與群眾:文化協會、農民組合與臺灣農民運動
【第二部 臺灣認同與漢人認同的糾葛】
第四章 想像與真實:臺灣人的祖國印象
第五章 戰爭、世代與認同:以林獻堂、吳新榮與葉盛吉為例(1937-1945)
【第三部 戰後初期的認同衝擊】
第六章 「新生臺灣」的頓挫:延平學院創立始末
第七章 戰後初期臺灣人的祖國體驗與認同轉變
結論
注釋
參考書目
索引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