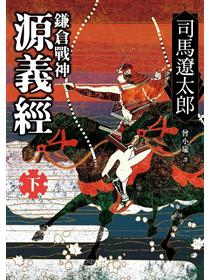若使讀書人只知歌功頌德,仰權貴之鼻息,為官府之走狗鷹犬,則是諸夏亡矣!
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
執掌西夏邊防要務的外戚高遵裕,多年浮報軍費、坐吃空餉。無意間掌握到確切證據的段子介與向安北,原想向上舉報卻被官官相護的陋習所阻,反被構陷迫害。瞬間成為了亡命之徒的二人,決定分頭通風報信,但他們前是荒漠絕境,後有同袍追兵,正義真能伸張嗎?
大宋與西夏鏖戰再起,西北硝煙滿佈。但西夏國內的政權長久以來在梁太后為首的外戚把持下與少主秉常的新派之間,卻開始因戰事而開始產生嫌隙與矛盾,石越如何利用母子兩人之間的齟齬,派遣細作見縫插針來達成分化西夏的目的。而來到陝西軍事邊鎮仍能屢建奇功,所經之路百姓必是夾道歡呼,偶爾也忍不住沾沾自喜的石越,如何能在權勢與名利中得到平衡?能堅持住最初的理想嗎?這個人人自危、心機四伏的官場又容得了他嗎?在內政與外交上都同時面臨艱鉅挑戰的石越又該如何逢凶化吉?
本書特色
《新宋》歷史背景是北宋熙寧年間王安石變法前,內容描述一個熱愛歷史的現代大學生石越穿越時空,試圖運用數千年後的歷史知識與文化涵養試圖改變這個世界,以現代觀點改革宋朝弊病,見地精深,史料綿密,對北宋王朝的各個方面進行改革的故事。主人翁以當代人的身份,去接觸歷史上的各種傑出人物,一步一步試圖扭轉歷史的車輪。掩卷之餘,總是讓人有一種思考,歷史是不是倘若真能那樣,會將是有如何重大的改變?
這個現象同時也反映出對岸當代年輕人對於未來的茫然與夢想的渴望在現實環境的壓力與劇烈變動之下,無從發揮自己的理想,只好寄情於歷史小說,細膩的心理情境描寫與真實的史實具象交構,在歷史小說中這是個創舉,也是當代青年會有的共同感受。
故事中的主角石越和改革派王安石、呂惠卿針鋒相對,與蘇軾一同品酒煮茶、談政論學,創立書院與二程子、沈括一起研究發明,並結識蘇杭名妓楚雲兒、世家之後桑梓兒,引進棉花紡織技術發展商業,使用活字印刷術開始立書傳世,從此改變北宋的變法革新……。
《新宋》的內容包羅萬象,涉及北宋各個層面,帶領讀者置身於當時的大宋江山,舉凡科技(建築、印刷術、火藥、紡織)、政治(兩黨制、議會制度、新舊黨爭)、權謀(權力分割、分化、抹黑構陷)、情感(朋黨、愛情)都有相當程度的描寫,作者阿越本身為歷史博士研究生,對於歷史非常考究,也因此在大陸出版時引起一派歷史小說的風潮,也開創歷史小說全新的格局與定位,因此擁有新歷史小說盟主與網路二月河的稱號,甚至受邀到北京大學與北京師範大學作專題演講。
新宋系列共有三部,共計十三卷,陸續出版中。
作者簡介:
阿越
文理兼修的創作才子,理工科畢業後,曾任火車維修技師,後轉為攻讀中國古代史,創作新宋的緣由起於碩士班入學考試的試題中有關於宋代史的題目,竟發生答題不遂的窘境,因而耿耿於懷要再深入研究宋代歷史。現為湖南師範大學歷史碩士。
2004年開始動筆撰寫長篇小說《新宋》,歷經數載完成《十字》、《權柄》、《燕雲》三部長篇小說,近240萬字。目前是大陸第一線的網路作家,有網路二月河的美名。
阿越的作品思想深刻,文風嚴謹,於正確詳實的歷史氛圍中創造出歷史想像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是新歷史小說的代表作家。《新宋》開創了新歷史小說的新境界,與《隋亂》的作者酒徒在歷史小說界有著極高的人氣,也正因此而有南阿越、北酒徒的稱號產生。
《新宋》系列也在新浪官方博客長期維持超高人氣和「越迷們」的關注。百度網的「新宋吧」也成為評論歷史小說的第一大討論區。更有讀者特意尋書中文字著成〈新宋詩詞考〉、〈新宋地理考〉。甚至有學者也專門討論「新宋學」這股新歷史小說的風潮。
各界推薦
得獎紀錄:
中國作家協會主辦1999~2008年「網絡文學十年盤點」十大優秀作品
07年度新浪原創小說風雲榜
08年新浪原創最具暢銷潛力的小說
08年新浪年度網路十大人氣作家
起點中文網 幻劍書盟 鮮網 17K文學網 各大文學網讚譽
數千萬網友好評追文
《新宋》的內容包羅萬象,舉凡科技(印刷術、火藥、紡織)、政治(兩黨制、黨爭)、權謀(權力分割、分化)、情感(朋黨、愛情)都有相當程度的描寫,作者阿越對於歷史非常慎重考究,也因此在大陸出版時引起一派風潮,擁有新歷史小說盟主的稱號。
名人推薦:
對岸一線網路名家 一致好評讚譽:
一切歷史其實都是攸關現代。阿越以極其嫺熟的筆法,將我們帶入了一場有關北宋的歷史劇。將王安石、司馬光、蘇軾、呂惠卿,這些耳熟能詳的歷史人物,還有很多被歷史遺忘的市井草民、販夫走卒,都一個個從紙上走出,走到你我身邊。在幕起幕落之間,卻依舊能隱隱找到現代社會的投影。
——《隋亂》酒徒
如果不是因為偶然。歷史說不定就會變成了另外的模樣。這本書的作者顯然是想再呈現另外一種形式的歷史,他將那個時代描寫得如此真實。以至於我的確認真想了很久,歷史是否真有可能那樣發展?
——《崑崙》作者鳳歌
回到過去的小說有很多,但不同的是回去做些什麼是替換掉歷史人物自己來呼風喚雨,還是把千年前的美人搶回二十一世紀?《新宋》沒有掉進戲謔與狂想之中,相反,回到宋朝的主角很認真地開始思考與探討政治和經濟,並通過他的視野,把北宋熙甯年間的風雲時事再現於讀者面前。
——《悟空傳》作者今何在
我們站在已知歷史的前面,可是作者卻試圖為我們描繪可能存在的歷史的背面。
——《誅仙》作者蕭鼎
小說將讀者帶到曾經繁華的宋朝,帶著讀者去探詢歷史上影響最深遠的變革。
——《中華再起》作者中華揚
當愛麗絲站在魔鏡面前的時候,她對鏡子那奇妙的另一面充滿了好奇。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書,也是一面魔鏡,它所映照出的是歷史的另一面。
——《天行健》作者燕壘生
得獎紀錄:中國作家協會主辦1999~2008年「網絡文學十年盤點」十大優秀作品
07年度新浪原創小說風雲榜
08年新浪原創最具暢銷潛力的小說
08年新浪年度網路十大人氣作家
起點中文網 幻劍書盟 鮮網 17K文學網 各大文學網讚譽
數千萬網友好評追文
《新宋》的內容包羅萬象,舉凡科技(印刷術、火藥、紡織)、政治(兩黨制、黨爭)、權謀(權力分割、分化)、情感(朋黨、愛情)都有相當程度的描寫,作者阿越對於歷史非常慎重考究,也因此在大陸出版時引起一派風潮,擁有新歷史小說盟主的稱號。
名人推薦:對岸一線網路名家 一致好評讚譽:
一...
章節試閱
摘文一:
「有欠謹慎!」戶部尚書司馬光的額頭上,幾乎就差直接刻上這四個大字了。
「若是發行,日後想要多少錢就可以印多少錢……」尚書右僕射呂惠卿心中的想法,也不經意從嘴角的笑容中流露出來。
剩下的宰輔們,有幾位被這前所未有的大膽計劃所震撼,腦海中短暫性出現空白的現象;其他尚屬清醒的大臣,則在心中反覆衡量著韓維提出來的計劃的利弊,包括對大宋朝的利弊,也包括對自己利益可能產生的影響,一時之間竟然難以下出判斷。
韓維提出來的計劃,表面上真的是充滿了誘惑力。
但是拋開派系之間的立場不提,政事堂中許多大臣,還是從這種誘惑當中,直覺的感受到了危險,雖然他們並不清楚究竟會有何危險。
「旁門左道!」司馬光心中十分排斥發行交鈔這種危險的想法。他始終相信,真正理財的王道,就是朝廷的君臣厲行節儉、輕徭薄賦,使百姓們種好地、生產出足夠的糧食,這樣國家自然會上下富足。其他所有的理財方法,在本質上都屬於歪門邪道。「天下的錢財有限,不在官便在民,官多自然民少!」雖然司馬光並不懂得什麼叫做「零和遊戲 」,然而他卻固執的保持著這樣的信念:其他所謂的「理財之術」,都不過是「零和遊戲」而已。
而呂惠卿猶疑的,則是提出這個計劃的人—韓維是眾所周知的「石黨」!他的計劃便是脫胎於石越的構想,他有必要替風頭正健的石越再添新功嗎?石越與高遵裕在陝西取得勝利讓朝野為之振奮,一時間譽聲如潮,但是真正要為補給、財政操心的,卻是他呂惠卿!
呂惠卿心中頗覺憤憤不平。
當然,他自動忽略了司馬光等人的工作。
呂惠卿望了各懷心事的政事堂宰輔們一眼,似乎感覺過於長久的沉默並非解決問題的辦法,便輕輕咳了一聲,說道:「諸位大人以為此策如何?」
「某以為不妥!」司馬光絲毫不留情面的說道,「無論金、銀、銅、鈔,皆為無用之物。於世間有用之物,乃是糧食與絹布。天下農夫每歲所耕之地不變,則所產之糧不增多;天下農婦所種之桑麻棉不變,則所織之布不增多。而朝廷卻要發行所謂『交鈔』,此是以此無用之物,奪天下農夫農婦所產之糧布,與加稅又有何異?」
戶部尚書所說的,是一種樸素的經濟道理,立時贏得在座大部分人的認同。
但是太府寺卿顯然也有他的理由,韓維立時向司馬光欠身說道:「非也!某以為,司馬公所言,只見其一,不見其二。」
「願聞其詳。」說話的是尚書右僕射呂惠卿。雖然韓維與石越本質上都是他的政敵,但相比而言,他更願意見到有人讓司馬光難堪。
自從司馬光入朝之後,呂惠卿與司馬光之間在皇帝面前公開的互相攻訐,就超過三十次;至於在政事堂的互相批評,更是家常便飯。然而奇怪的是,雖然呂惠卿曾經數次用計,試圖激怒司馬光,逼性情剛強的司馬光主動請辭,但是司馬光卻似乎頗覺其意,哪怕在政事堂爭得面紅耳赤,卻絕不肯辭職。呂惠卿自然不知道司馬光有重重原因而不敢輕易言退,且一方面,因為受到太皇太后的重托,讓忠君觀念極強的司馬光有了一種肩負重任的感覺;另一方面,卻是因為當年王安石雖然與司馬光政見不合,但是司馬光潛意識中,對王安石還有一種信任,懷著一種僥倖認為王安石也未必不能成功,但是對呂惠卿,司馬光卻是認定了他不過是一個奸佞小人,司馬光自認為如果自己離開朝廷,將會成為國家的罪人,因此雖然屈居呂惠卿之下、哪怕與呂惠卿爭得怒發衝冠,司馬光始終不敢放棄自己的責任。
但是司馬光的這些心理,呂惠卿哪能理解。他始終希望借用一切機會,來拔掉政事堂的這根眼中釘。
韓維並不知道自己此時已經成為呂惠卿打擊司馬光的工具,他注視司馬光,朗聲說道:「司馬公當知慶歷間事,慶歷之時,江淮之地便有錢荒,其因便是朝廷需調集銅錢應付西夏元昊之邊患。直至熙寧以來,東南錢荒,依然如故。熙寧二年呂相公便曾建議坐倉收購軍兵餉糧,而令東南漕運糧改納現錢,當年司馬公曾上章論之,以為如此則會加劇東南錢荒……」他這句話說出來,政事堂中呂惠卿與司馬光都表情尷尬,馮京、吳充等人卻面露笑容。韓維沒有覺察到自己失言,兀自繼續說道:「此後朝臣論東南錢荒者甚眾,直至熙寧九年夏,張方平相公亦曾言東南六路錢荒,道『公私上下,並苦乏錢,百貨不通,萬商束手。』且言『人情日急』。是故石越為杭州守牧,便曾上章論之,請朝廷於秋收之時,許農夫納米不納錢,以免使農人同時賣米,加劇米賤錢貴,重傷農夫。後其入朝,又數論之,天子恩德,於熙寧九年秋頒詔許之,天下稱頌之聲,今日尤不絕於道。然則東南錢荒,卻並未完全解除。」
韓維說到此處,連司馬光都暗暗點起頭來,因為韓維提及的,實是宋朝經濟領域面臨的一個死結!大宋君臣,對此都束手無策。果然,便聽韓維繼續說道:「天下錢事,一面是東南錢荒,致使米賤傷農,百貨不通,萬商束手;一面卻是銅貴錢賤,銅禁未開之時,天下銷錢鑄銅器者已不可勝數,自王介甫相公開銅禁後,更是風行天下。蓋銷鎔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物,即可獲利五倍甚至十倍,天下誰不願為?遂使錢荒愈重。石越論及此事,以為以銅鑄錢與以銅鑄器,利潤相差如此,是銅錢之值賤也!若依常理,則既有錢荒,則當錢貴,錢貴則鑄錢監當有重利,而今日之事實,卻是各地鑄錢監,因銅價貴於錢價,若能不虧,已是萬幸。」
韓維說的,的確是當時的怪現象,一方面東南錢荒,流通市場缺少銅錢,導致錢貴米賤,傷害農業;另一方面,卻是銅錢的市場價值低於它的實際價值,導致官府鑄銅錢不能獲利甚至是虧本,大量的銅錢被鎔鑄成銅器流出海外,因為宋錢在海外的購買力,數倍於在本國的購買力!由此更加劇了錢荒的現象。
這是宋朝人難以解釋的現象,更無法理解為什麼會陷入這樣的惡性循環中。他們鑄造的銅錢,既是貴的,又是便宜的!哪怕就在缺少銅錢的東南諸路也是如此,那裡的銅錢一方面缺少,一方面卻除了傷害到米價之外,並沒有導致物價暴跌,甚至是米價,也處於一個相當的水準,使得銅錢不斷的外流。曾經有來自倭國的商船,一夜之間將一座城市的銅錢全部買走!也有非法的海商,載著滿船滿船的銅錢出海,去海外購買超過這些銅錢在大宋境內的價格一百倍的貨物!
這也許可以解釋成宋朝政府在平準物價方面做得多麼出色,哪怕是虧本也在不斷鑄造銅錢,使東南地區雖然看起來永遠都在缺錢,但是至少不是不斷的缺錢,流入量抵銷流出量,從而維持了一種相對的平衡;也可以解釋成因為宋朝的經濟水準遠高於鄰國。
但無論如何,對於宋朝來說,這始終是個難題。連石越都無法解釋清楚這種現象,更不用說設法解決了。雖然這只是一種局部現象,但是對大宋東南地區的工商業,卻有十分大的影響。因為錢荒,導致東南地區的市場被限制在一定的規模之內,無法擴大;又因為錢在大宋境內價賤,從事海外貿易的商人唯有以物易物,才能得到最大的利潤。從海外運回銅錢,那是傻子才做的事情,因為哪怕是將銅錢運回來鑄成銅器,在算上運輸費用之後,其利潤相比海外貿易的利潤,也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每個商人,都務求將手裡的每一文銅錢都換成貨物運回大宋。但是東南諸路的市場規模,卻無法吸納這過多的貨物,大部分的貨物,只能運往汴京。一旦汴京也吸納不了時,與其降價賣到其他地區,商人們更願意削減貿易的規模來保證利潤。
大宋東南地區的發展,就這樣被限制了。
整件事情雖然引起了宋朝精英的普遍關注,但是在當時的人們而言,很難從更深的層次來理解這個問題。儘管如此,韓維還是憑藉著自己粗淺的理解,以及在太府寺卿任上所得到經驗,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法。雖然他的認識並不深刻,考慮的問題也並不周全,但實際上卻很可能有效。
所謂的「瞎貓撞上死耗子」這種事,有時候也是存在的。
這位太府寺卿在政事堂上繼續著他的慷慨陳詞:「所以,某以為,目前便有一劑良方,可以解決東南錢荒與鑄錢虧損的問題!」
他說到此時,眾人都已漸漸明白他的理由。
「某以為,在東南諸路發行二百萬貫的交鈔,便可以有效的解決東南錢荒,交鈔不懼外流,不懼銷鑄,只要將最新出現的彩色套印技術收歸官有,控制住幾家最好的造紙坊,盜印的問題也可以抑制在相當小的範圍內。而且相比銅錢而言,交鈔攜帶也更為方便。此外,朝廷還可以在川陝發行一百萬貫的交鈔,其目的一方面是為陝西路興修水利提供資金;另一方面,則可以在川陝地區,逐步回收鐵錢,停止鐵錢監鑄鐵錢導致的虧損。川陝停用鐵錢,尚有一個意外的好處,便是可以使墨吏在收稅之時,少了用鐵錢與銅錢之間的兌率來剝刻百姓的機會,於川陝百姓而言,無疑亦是一大德政。因此,某以為,川陝的交鈔,甚至可以發行更小面額的!」
吏部尚書馮京聽到韓維興致勃勃的說完,不由試探著問道:「一旦東南六路與川陝諸路發行成功,交鈔是否要推行天下?」他問出了所有人的心聲。
「自然要推行天下!」韓維毫不遲疑的說道,「交鈔相比銅錢與鐵錢,方便而不費。銅礦產量始終有限,諸君皆知日後朝廷尚有一個地方需要大量用銅,若是找不到取代之物,只恐錢荒越來越嚴重!」
摘文二:
這是清河郡主的聲音!
但這是清河郡主?
武釋之此時也無暇思索究竟是不是被傳言所誤,還是剛才過去的根本不是清河郡主。他只是更加堅定的證實,那馬車有鬼,但是他也沒有餘暇去思考,為何「清河郡主」要幫助一個叛將。只待馬車衝過,他立時從巷子中衝出,繼續追趕起前面的馬車,他沒有時間與「清河郡主」糾纏。
然而這樣一折騰,他與前面的馬車又拉開了距離。而「清河郡主」的馬車,也不依不撓的掉頭跟了上來。
「我非追上這廝不可!」武釋之拚命抽打著戰馬,他與馬車之間的距離,終於慢慢拉近了。
突然,馬車轉了個彎,駛進了一條大道。
追上去的武釋之怔住了!
大宋陝西路安撫使司!
前頭的那輛馬車,駛向的地方,竟然是陝西路帥司衙門!
「叛將?」「調虎離山?」一瞬間,武釋之的腦海中,充斥著各種各樣的念頭。
安撫使司衙門的衛隊截住了那輛馬車,一個熟悉的身影從馬車中走了下來—段子介!不管心中有多少不解,武釋之還是策馬上前,既然段子介自投羅網,那麼他從安撫使司的衛隊手中接收這個「叛將」,自然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來者何人?」安撫使司的衛隊也發現了靠近的武釋之,有兩個護衛迎了上來,大聲喝問。
「衛尉寺宣節校尉武釋之。」武釋之亮出了自己的腰牌。
驗過武釋之的腰牌,那兩個護衛客氣很多。「武大人來此何事?」
「下官追捕叛將至此。」
「叛將?」
「正是。段子介便是叛將。」
「啊?」那兩個護衛都吃了一驚,其中一個小心翼翼的問道:「段大人是衛尉寺駐安撫使司監察虞侯副使……」
「不錯。不過二人有所不知,段子介與其上司致果校尉向安北叛國,據報向安北已經逃出東門,新任監察虞侯王則校尉已經出城追拿;某奉命來追捕段子介。」武釋之的聲音大得滿街都能聽見。
正在與段子介說話的衛隊長聞言也怔住了,懷疑的望著兀自被綁著段子介。
「我並非叛賊,一切待石帥回來,自然可見分曉。」段子介急切的辯白道:「在下只求待在帥司衙門的大牢中,等待石帥回京兆府。卻千萬不可將我交給衛尉寺。」
雖然不明白為什麼段子介這麼害怕被移交到衛尉寺—也許是石越更加寬容而章惇要嚴酷許多—但是武釋之認為自己的要求並不過份:「軍中武臣犯法,當由樞府或衛尉寺審理。段子介身為軍法官,理所當然要由衛尉寺處置。既便石帥回來,亦是一樣,還請諸位能夠體諒在下。」
「我辛辛苦苦將他送來此處,可不是為了交給衛尉寺的。」一個動聽的聲音從武釋之腦後傳來,不過此時對武釋之而言,這個聲音可一點也不動聽。
「清河郡主!」武釋之的聲音嚴厲起來,「國家章程,並非兒戲!」
「清河郡主?」
「清河郡主?」
安撫使司衙門前的大街上,無數的人忍俊不住。很多人雖然不認識柔嘉縣主,但是卻有不少人曾經見過清河郡主的。
「武大人認錯人了。」一個護衛好意的提醒道。
「認錯人了?」武釋之愕然回頭,卻見柔嘉笑意盈盈的望著自己,竟是無絲毫害怕之意。不由怒道:「妳是何人?怎的敢冒充宗室?」
「她本來就是宗室!」從更遠的地方傳來景安世氣喘吁吁的聲音,雖然武釋之無法理解為何他騎馬趕來也會喘氣,但顯然這些事情如今已經並不重要。只見景安世策馬到柔嘉跟前,下了馬來,凝視柔嘉半晌,忽然厲聲問道:「柔嘉縣主,妳如何會出現在京兆府?!」
「你管得著嗎?」柔嘉卻是膽大包天,壓根不知大禍已將臨頭。
景安世又看了柔嘉兩眼,冷笑兩聲,冷冷說道:「本官管不著,自有人管得著。本官只奉勸縣主,莫要恃寵而驕,禍及父母!」
說罷,雙手正了正獬豸冠 ,向段子介走去。
柔嘉從未見過有人對自己說話如此無禮,怔了一下,卻權當是危言聳聽,只搶先幾步走到那衛隊長跟前,說道:「先莫把這人交給他們,待我去見見夫人,自有分曉。」說罷,也不管衛隊長答不答應,大搖大擺的往安撫使司衙門闖了進去。
景安世望著柔嘉的背影,卻只不停冷笑。
「察院大人?」武釋之見景安世並不說話,忙低聲呼道。
景安世擺擺手,淡淡說道:「不要急,她要見魯郡夫人,便讓她見。便是石子明親來,若是與朝廷章程不合,亦不敢放肆。本官現在只想見識一下魯郡夫人的見識!」
「我只是朝廷的命婦,豈能幹涉外事?」京兆府中喧嘩了半夜,梓兒直到現在才知道原來是出了兩個「叛將」,而出人意料出現在這裡的柔嘉竟然還要她出面來保護其中一個「叛將」。
「眼下京兆府中,說得上話的大都出去了。若是妳也不管,便沒有人管了。妳去看看那個御史和那個什麼武釋之的囂張樣……」柔嘉心裡其實也清楚清河是將一個燙手山芋交到梓兒手中。但是眼下的情勢,的確也只有安撫使司衙門有這個能力保住那個什麼段子介,而只有段子介保住了,她之前所做的一切,才是有意義的。否則的話,清河想不受連累都不可能。而眼下顯然只有梓兒有能力影響安撫使司衙門的衛隊。
「妳方才說,那兩個叛將叫什麼名字?」梓兒沉吟了一會,突然問道。她老覺得其中有個名字似曾相識。
「一個叫向什麼,一個叫段子介。」
「段子介?」梓兒轉過頭,向阿旺問道:「阿旺,你可聽說過這個名字?」
阿旺也怔住了,「似是有點相熟。」
柔嘉卻不明白梓兒為何在這當兒,想起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但又拿她無可奈何。
「是不是被開封府抓過的那個段子介?」梓兒突然間靈光一閃,想了起來。
「對。」阿旺雖然沒有經歷過,但是卻也常聽人提及。
「他被開封府抓過?」柔嘉卻怔住了,「難道他真是叛將?」
「他決不可能是叛將。」梓兒淡淡的說道,語氣卻十定堅定,「其中定有蹊蹺!」
柔嘉一時沒有弄明白為何被開封府抓過反而不會是叛將,但是梓兒能認可自己的判斷,無論如何是一件好事,當下笑道:「那夫人妳快去救他。」
「我不能出面。」梓兒溫和的笑了笑,雖然出身不高,她卻是非常懂得輕重的。要知道,甚至連相州韓家那樣的世家大族的姑嫂們,都挑不出她的毛病來。
「那怎麼辦?」
梓兒垂首想了一會,突然想起一個人來,卻是剛剛因為侍劍的推薦,被調到安撫使司來的李旭,此時名喚「李十五」。梓兒聽石越說過他的底細,當下又細細想了想,道:「阿旺,妳去將李十五叫來。」
「是。」
景安世與武釋之在外面等了約小半個時辰,才見有一隊衛兵從安撫使衙門中舉著火把走了出來。
外面的衛隊長見到為首的是個年輕人,卻不見梓兒,也不見柔嘉露面,不由奇道:「十五郎,如何是你?」
李旭走到衛隊長跟前,低聲說了兩句什麼,便見那衛隊長點頭應了,他於是徑直走到段子介跟前,上下打量了一下,眼中忍不住露出一絲笑意;段子介望著李旭,也是一怔,嘴唇微微動了動,卻是忍住了沒有出聲。
李旭徑直走到景安世前面,欠身說道:「察院大人,魯郡夫人言道:婦人不當干預外事,這邊廂的事情,夫人不便參預。」
景安世見他如此回答,不禁微覺失望,但是口裡卻讚道:「魯郡夫人果然是明曉事理。」
「不過……」李旭的話卻沒有說完,「魯郡夫人說,這個段子介本是朝廷任命的駐安撫使司監察御史副使,雖說他是叛將,可他此時硬要來帥司衙門,寧在這兒坐牢亦不願意去衛尉寺。似乎……嗯,只怕其中多有蹊蹺之處。若真是另有苦衷,他來到帥司門前,還被人截走,日後張揚出來,難保不成笑話,這個罪過卻也不好擔當……」
景安世與武釋之聽到這話,臉色不免都變得有些難看,這話中之意卻是明明白白的表示了對他們的懷疑。
李旭卻沒有去看他們的臉色,只在心中暗暗佩服梓兒的聰慧,「因此魯郡君說,或可以有個兩全其美的方法,想來衛尉寺定是人手不足,否則也不至於讓他們跑了,石帥與章衛尉同殿稱臣,都是在為朝廷辦事,所以不妨由帥司衙門派一隊護衛,協助衛尉寺的武大人押送這位段大人去京師。到了汴京後,我等便齊將這位段大人送至樞密院,衛尉寺若要人,直管問樞府要便是。如此一來,大家都不用傷了和氣,衛尉寺的事也辦好了,我帥司衙門亦不擔關係,這位段大人若真有什麼苦衷,文相公自是不會冤枉他的。不知景大人與武大人意下如何?」
他如此一說,景安世與武釋之不由都怔住了;段子介卻不免喜出望外。
但是不管怎麼樣,梓兒提出來的這個方案,絕對是讓人無話可說的。的確,安撫使司若要強留衛尉寺的犯人,自然是說不過去的,但是它懷疑其中有疑點,要送到樞府去,卻也是理所當然的。若是景安世與武釋之還要說什麼,倒顯得他們真的是居心不良了。
不過真正讓景安世佩服的是,這位石夫人口中謙遜著說不干涉外事,實際卻把外事全部干涉光了,還讓人無話可說,女流之中,也算得厲害之人。
「如此,也甚好。不過帥司衙門要派誰去?」武釋之訝然之後,便也覺得這個提議不錯,既可不直接得罪石越,也不能算違命。
「便是在下與這八位兄弟。」李旭笑著指了指身後的八人。那八人向前一步,朝武釋之欠身一禮,便走到段子介身邊,所站的位置,竟是團團的將他護住。因為他們接到的命令是:從此時開始,到將段子介交到文彥博手中為止,必須與他寸步不離,必須絕對的保證他的安全!
喧囂了一個晚上的長安城終於平靜下來,啟明星也已經開始出現在天空之中。
而此時此刻,心情沉重的王則卻帶著向安北的屍體在衛尉寺陝西司的衙門裡等待著天亮。他用顫抖的手指,翻動著那份沾滿了鮮血的報告,心中情不自禁的充滿了洗刷不盡罪惡感—這份報告,本來他也應當直接交給武釋之,讓他帶回京師的,但……
而陝西路安撫使司衙門前面的街道上,一什輕甲衛士則押送著一個被五花大綁的軍官,跟在一個沉著臉的武官後面,緩緩而行。而被綁的軍官,臉上反而不時的漾出笑容,似乎這樣被綁著倒是如何開心的一件事。
而在西北方向的一條小巷上,正騎在馬上的監察御史景安世,嘴角亦不時露出得意的笑容。他此時的心裡,正在構思著最新的奏章—這必然是一份能掀起驚濤駭浪的奏章!在這份奏章中,將涉及到一個與皇帝有著近系血親的公爵、一個極受寵愛的郡主、一個無法無天的縣主、一個似乎正在失寵的郡馬、還有一個如今炙手可熱的安撫使,無論如何,他的老師呂相公,一定會非常喜歡這份奏折的。
摘文三:
「樞府以為五年內造十二門重炮防衛汴京,並在陳橋驛以北建築裝備克虜炮的十四座石寨,契丹對汴京的威脅可以減至最輕。萬一有事,汴京完全可以堅持至援軍的到來……樞密會議甚至以為,憑現在的軍力再加上火炮,汴京城絕非契丹所能撼動。」大宋禁宮後苑的一片草地上,趙頊雙手握著「鷹嘴」,比劃著桿下的小球,一面和石越「閒聊」著軍國大事。
石越頗有點哭笑不得,這種在宋朝被稱為「捶丸」的運動,非常類似於後世的高爾夫球。捶丸在宋朝的王公貴族中十分流行,特別得到宮女們的鐘愛,但是石越對高爾夫球卻缺少必要的興趣,不幸的是,皇帝看起來興致盎然,完全不容他拒絕。好在石越不用擔心自己打得太差,比面前皇帝更差的球技,絕對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他使勁握了一下自己手中的桿子,笑道:「京師乃大宋之根本,加強防衛自無不妥,只是臣以為不可操之過急。天下安危,在德不在險,昔秦始皇修長城而陳涉起於大澤,隋煬帝征高麗而翟讓興於瓦崗,此皆前車之鑑。」
「卿言甚善。」趙頊的心情看起來非常不錯。「砰」的一聲,趙頊手中的鷹嘴揮出,彩球優美的飛過空中,可惜,失之毫釐,差之千里。趙頊放下桿子,尷尬的笑了笑,將球桿扔到草地,轉身向附近的亭子走去。
石越忍住笑意,忙將球桿交給一個內侍,跟了上去。
「此次一共鑄了六門克虜炮,兩門運至朱仙鎮,四門率先裝備禁軍,安置在汴京城牆上。朕料定這城牆,遲早要改了。」為了掩飾自己球技的失敗,趙頊繼續起之前話題,內侍們則小心的在石凳上鋪上錦墊,遞上茶水。
「臣之愚見,以為炮兵若不操練,恐怕誤事。」
「王韶亦是這般說。」趙頊笑道:「諸臣之中,王韶、郭逵,最重火炮。王韶巡視兵研院後,盛讚火炮是不餉之兵,不秣之馬。郭逵亦道火炮可恃為天下後世鎮國之奇技。」
「臣亦頗以為然。」
「朕已下旨,賜封趙岩男爵,賞宅院一座,田三十頃。」趙頊曾經親自檢閱過火炮的威力,亦是十分得意,「唯一美中不足者,是青銅造炮,耗費太大。」
「此事不過循序漸進,欲速則不達。」
「嗯。卿言甚是。」趙頊點點頭,似乎又想起什麼,向石越問道:「卿聽說過李格非其人嗎?」
「李格非?李文叔?歷城人?」石越下意識的反問道。
「卿果然認識。」趙頊笑道,「卿以為此人學問如何?」
「臣並不認識李格非。」石越未及細想,信口便答道。
趙頊大奇,詫道:「那卿如何又知道他字文叔,是歷城人?」
石越這時才驚覺過來,他自然不可能不知道李格非,李格非倒也罷了,他的女兒李清照,卻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人物。不過算其年歲,李清照現在還未出生呢,石越可沒辦法對皇帝說他聽說過李格非女兒李清照的才名。
「臣是聽說過此人,據說文章極好……」
「文章極好?」趙頊似乎頗覺驚訝,「以卿之材,而許之文章極好,則這個李格非當非一般人物。他文章極好,為何不試進士科,反入了白水潭格物院?」
「啊?」這下輪到石越目瞪口呆了,李格非雖然沒他女兒出名,可也是赫赫有名的「蘇門後四學士」之一,現在居然學了格物……
「卿不知道嗎?」趙頊道:「李格非在熙寧十年以白水潭格物院第一名畢業,入兵器研究院,協助趙岩造火炮,多有發明……」
石越此時滿腦子卻只有一個念頭:「李格非學格物了,那李清照怎麼辦?」
趙頊接著說道:「郭逵曾遞了一份奏章,論及火炮之事,以為火炮此物,士卒非經訓練,不曉幾何算術,不能善其用。並附上一本著述,書中論火炮諸事甚詳,署名便是歷城李格非,惟其書言語淺白不文。朕召郭逵詢問,郭逵只言李格非其人甚聰穎,此番隨克虜炮及藥彈一道運來城中者,用於測量瞄準之工具規、尺、矩度等物,皆是李氏所造。」
石越對這些卻也不太懂,只得附和道:「想見其見識才幹亦不差。」心裡卻依然忍不住在擔憂哀嘆李清照的命運,雖說明明知道歷史已經改變,人們的命運也一定會發生巨大的變化,但是對於李清照將來可能成為女科學家這一點,石越依然覺得難以接受。特別是,以他的壽命,極有可能目睹,石越對李清照的生平知之甚詳,知道如果李清照能夠出生的話,也就是幾年後的事情了。但問題是,李格非的命運改變了,李清照究竟還能不能出生?
石越突然間覺得煩惱起來。
「朕已准了郭逵所請之事。」趙頊喝了口茶,渾然沒有注意到石越的心不在焉,又說道:「郭逵本欲延請李格非去講武學堂教授炮兵,不料被他所拒,沒幾日,朕便聽說此人去了洛陽。」
「洛陽?」石越下意識的問道。
「嵩陽學院請他做教授。」趙頊苦笑道:「朕的講武學堂,竟比不上嵩陽學院。」
到底是李清照沒能出生更糟,還是李清照變成女科學家更糟?石越的思維此時和皇帝卻沒有一點交集。他竟然發起呆來……
在石越為李清照未知的命運出神的時候,數千里之外,西夏的君臣們,卻都在為自己的命運而緊張的策劃著。
大宋熙寧十一年,是西夏的大安四年。
幾個月以來,興慶府都一直顯得有點死氣沉沉。
熙寧十年的幾場戰爭,其實宋朝與西夏都有些準備不足,無論對哪一方來說都稱得上有點冒險的戰爭,最後卻是宋朝取得了勝利。西夏在這一年的戰爭中,損失了四成的精銳,橫山地區控制權的易手眼看也是早晚之事,沒有人提得起興致來,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所有的人都明白,若非因為老天保佑,結果一定會更糟。
而最糟糕的是,在西夏國,幾乎每一個握有權力的人,都能嗅到某種不祥的味道。
這是個真正只剩下沙漠的白上國。
西夏王宮。
「太后。」嵬名榮的臉上,有著掩飾不住的焦慮。
梁太后瞥了他一眼,緩緩說道:「天還沒有塌下來。」
「太后,遣使向宋遼同時稱臣,是迫不得已之法,但若接受遼主的要求,與遼主夾擊楊遵勖,卻一定會激怒宋朝。我大夏兵力已疲,士氣低下,豈堪再戰?」
「結遼抗宋,是唯一選擇,宋朝欲亡我之心,路人皆知。他們若有餘力攻我,我們便是不激怒他們,他們也會找藉口來打。」
「但畢竟可以拖延時日,恢復實力,靜待有變。只要能拖過幾年,遼主英武,必然平定楊遵勖,他又豈能容宋朝來亡我大夏?至少宋軍也須忌憚契丹,不能出全力與我作戰。若此時激怒宋軍,其舉國來伐,契丹亦無能為也,請太后三思。」
「待遼使來後再說吧。」梁太后沒有興趣再繼續討論這個問題。「我聽說外間有人上表,要相國罷相?」
嵬名榮遲疑了一下,道:「確有此事。」
「那他們想讓誰代相國為相?」梁太后冷笑道。
「以仁多澣呼聲最高。」
「仁多澣?」梁太后譏諷的笑出聲來,「他敢來興慶府嗎?」
「是……」
梁太后的臉色突然一變,怒道:「若非仁多澣貽誤軍機,石越都已成擒!又豈會有敗軍辱國之事?!」
嵬名榮的嘴唇動了一下,卻終於沒敢替仁多澣說話。
「他若敢來興慶府,我必取他人頭。」梁太后冷冰冰的說道:「遼使來國之事,你親自去迎接,莫要聲張出去。」
「是。」嵬名榮雖然不贊同梁太后的意見,但是他也知道,此時此刻,遼國是萬萬得罪不起的,而接待遼使,也是絕不能出差錯的。
「再派人去董氈那裡,若是他肯答應和親,我願意將康樂公主許給他兒子。」
「是。」嵬名榮欠身應道,一種屈辱的感覺從心裡頭冒了出來。不要說康樂公主是梁太后最疼愛的女兒,單單是女方主動要求和親,便已經是極大的恥辱。這哪裡是和親?這分明是獻女!
但這一切,都必須忍受。
李清府。
李清一身戎裝,在府前翻身下了馬,親兵家將們連忙上前牽過馬匹,迎他入府。
「將軍,你回來了。」一個帶著點怯意的柔軟聲音,向李清問候道。
李清停下腳步,循聲望去,卻是史十三寄在府中那個喚作「嘉君」的女孩,正低頭斂衽向自己行禮。他上下打量她一陣,見她手中提著個小籃子,點點頭,道:「妳要出門嗎?」
「是,想去東市買點東西。」
李清掃了她一眼,皺眉道:「府中若是缺什麼,問夫人要便可,自會著人去買。這段時間,妳不要出門。」
「是。」嘉君的身子微微抖了一下,又向李清行了一禮,轉身往內院走去。
李清凝視她的背影,若有所思。
「將軍,禹藏駙馬求見。」門房過來稟報。
李清回過神來,問道:「是駙馬一人,還是還有別人?」
「只是駙馬一人。」
「快請!」李清一面吩咐著,一面快步往中堂走去。
「李郎君。」禹藏花麻在客位上屁股尚未坐穩,便迫不及待的開口說道:「國中如今流言四起,人心惶惶。有人在傳說,宋朝不僅要全面停止互市,還要嚴查私販,茶葉等物品價格飛漲;又有人在說,國中有人想聯遼制宋……興慶府與靈州又開始嚴格執行宵禁,靈州已有十幾個百姓因為冒犯宵禁,被就地處斬……」
李清靜靜的聽著。
「明人面前不說暗話,我來是想問問李郎君,有無救時之良策?」
李清望著禹藏花麻,笑道:「這等大事,駙馬如何來問我?」
禹藏花麻冷笑道:「李郎君,我是個粗人,不會怕這怕那的!如今這事,若是合我心意,殺頭滅族我亦做了;若是不合我意,我大不了帶了親兵家將回老家去!誰又能奈我何?」
李清笑道:「不知何謂合駙馬之意?何謂不合駙馬之意?」
「讓皇上親政!皇上親政,他要聯遼便聯遼,要附宋便附宋,我都隨主上幹了。」禹藏花麻大聲嚷了起來。
摘文一:
「有欠謹慎!」戶部尚書司馬光的額頭上,幾乎就差直接刻上這四個大字了。
「若是發行,日後想要多少錢就可以印多少錢……」尚書右僕射呂惠卿心中的想法,也不經意從嘴角的笑容中流露出來。
剩下的宰輔們,有幾位被這前所未有的大膽計劃所震撼,腦海中短暫性出現空白的現象;其他尚屬清醒的大臣,則在心中反覆衡量著韓維提出來的計劃的利弊,包括對大宋朝的利弊,也包括對自己利益可能產生的影響,一時之間竟然難以下出判斷。
韓維提出來的計劃,表面上真的是充滿了誘惑力。
但是拋開派系之間的立場不提,政事堂中許多大臣,...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收藏
收藏

 二手徵求有驚喜
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