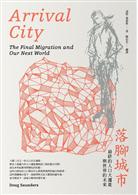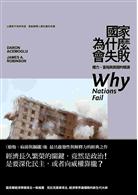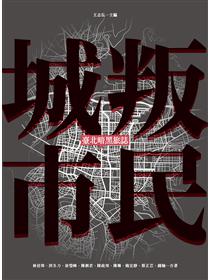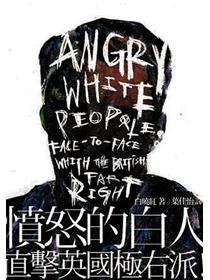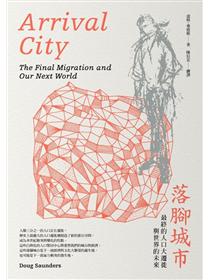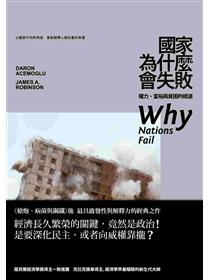推薦序
事事關心 余英時/作
最近我有機會和吾爾開希長談,又拜讀了他的論文集-《為自由而自首》,十分欽佩他二十多年來的進步和成就。開希要我為他的文集寫一篇序文,紀念「六四」民主運動的二十四週年,我覺得義不容辭。
開希流亡差不多己四分之一世紀了。在這一漫長的時期中,他不但一直在繼續著民運的大業,而且也通過閱讀、觀察、生活體驗等等管道成長為一個極其卓越的政治評論家了。從談話和文集中,我深切認識到:他的知識面廣闊、批判力鋒銳、判斷力精準,無論是推動民主還是評論時事,都是如此。
但是追究到底,這些特色是和他的基本人格取向分不開的。我覺得他的基本人格中一個最重要的向度便是「關心」。明末東林學派的領袖們留下了「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名言。文革時迫害致死的鄧拓寫過一首廣為傳誦的詩,其中兩句說:「東林講學繼龜山,事事關心天地間」。
可知「關心」早已進入中國知識人的傳統了。開希「從小喜讀古書」(〈「識正書簡」之我見〉),我相信他的「關心」必輾轉從這一傳說中得來。
由於「事事關心」,他在中國便關心中國,在台灣便關心台灣;他既出於維吾爾族,當然更不能不關心新疆。推而廣之,他對西藏人的遭遇也同樣抱著無限的關懷。他說,他是維吾爾人,也是台灣人,只有中國自由了,他才自由。這些話都發乎內心,我是深信不疑的。
「事事關心」便不能有限制。所以他對狹隘民族主義深惡痛絕。因為民族主義一旦走上狹隘之路,人們「關心」的範圍便越縮越小,二戰前義大利的法西斯、德國的納粹和日本的軍國主義便提供了典型的例證。如何防止狹隘民族主義的復燃在今天的中國尤其是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正如開希在〈狹隘民族主義形成的原因〉和〈抗戰勝利該給我們的啟發〉兩文中所說的,中共為了維護其一黨專政的統治,「採取了和當年納粹、法西斯、軍國主義一樣的模式,宣傳虛擬的外國威脅來凝聚國民對國家的支持,並蓄意模糊和混淆國家、政府及執政黨之間的分界。」其結果則是「今天在中國一些網站上充斥著和當年,戰爭爆發之前與東京、柏林、羅馬相同的言論。」
同樣的,由於他的「關心」是沒有限制的,自一九九六年定居台灣以後,他始終能超越於一切黨派觀點之上。他因為喜歡台灣而自覺地成為一個台灣人。他在〈我也是台灣人〉告訴我們:
因為喜歡,自然關心,而進一步就有了承擔。…從關心教育,關心治安,到進一步關心政治,都不再僅僅是以外人的身份。
但我們一讀集中「關心」台灣的政論,便會立即發現,他的批判完全以理性為依歸,不問國民黨或民進黨,不管在朝黨或在野黨,不分藍或綠,甚至也不考慮和他個人關係的親或疏。很顯然的,在寫這些文字時他「關心」的是整個台灣。
不必諱言,「關心」中國大陸一定是他時時刻刻不能去懷的隱痛。二十四年了,他日夜思念著雙親而中共則下定決心不讓他有任何可以和父母相見的機會。他的父親一向害怕共產黨,但開希告訴我們:有一次父親竟然,用激動的語氣說出了他這幾年在電話中最無懼的一句話:「祝你們爭取一個沒有恐懼的社會的努力早日成功。」(〈爭取一個免於恐懼的社會〉)我讀了這句話非常感動。「免於恐懼」是羅斯福總統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所提倡的「四大自由」之一(”freedom from fear”),現在連最怕共產黨的人也「無懼」地說出這句話來,「中國自由」的日子應該不遠了。二十多年來,開希為爭取「中國自由」作了無數的努力,最近竟三次「為自由而自首」。諷刺的是,二○○九年中共駐澳門的聯絡處、二○一○年東京駐日大使館和二○一二年華府駐美大使館都不敢接受他的報案。這次是輪到中共「恐懼」了。「中國自由」離我們更近了。是為序。
二○一三年五月十五日
寫於普林斯頓
推薦序
與時俱進的六四思索者 蔡詩萍/作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吾爾開希寫書,必成焦點。
他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要角之一,是學運領袖,是六四事件後流亡海外的最知名人士之一,他談中國,談中國的未來,比他見解深廣的人一定不少,但比他感受深刻的人卻決不多見。
只因為,他始終是個積極的參與者,是個日常生活的實踐者。
但,他始終沒出書。
沉默這麼多年,吾爾開希選擇在台灣,在六四事件相隔了二十四年之後的台灣,出版他的第一本書,這份沉默的堅持,反而更讓人好奇:他在等什麼?
六四事件對所有關心中國未來的人,都是一大震撼,對身涉其中的學運領袖,尤其是一輩子的震懾。他們或被關,或及時逃出流亡異域,但不管何種際遇,他們畢竟還活著,看似比死去的罹難者幸運些,卻無疑要揹負著更為艱苦的責任:怎樣持續的堅持信念,保證自己不辜負生者的期盼、死者的託付?又怎樣在事件高潮退卻後,面對人生舞台上的孤寂,以及漫漫長路上,必須生活、必須時時柴米油鹽醬醋茶、必須三不五時迎來一雙雙好奇的眼光:喔,你就是那個六四學運領袖喔,那你,現在在幹嘛呢?
而或許,最最艱困的挑戰是,當年決意對付他們的頑固老頭鄧小平固然與世長辭,去見馬克斯了,但他堅持的改革開放路線並未停下腳步,歷經了江澤民、胡錦濤,如今到了「太子黨」的習近平當家,二十幾年來,三代領導人交棒,中國仍然是共產黨一黨掌握政權,完全沒出現六四民運人士曾期待的民主變革,當然更沒垮台。相對的,中國卻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世界工廠,也是世界最被渴望的內需市場,中國的巨變圖像,不僅是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伊始,「摸著石頭過河」時所難以想像,即便六四事件的參與者,若今昔相較,恐怕亦不免要驚嘆:中國何以變化(進步)如此之劇?不但中國沒有崩解,或陷入六四後有一段時期在國際間所瀰漫的一股「中國前途堪憂論」氣氛,反倒是更昂揚、更雄心勃勃的繼續走「中國夢」呢!對六四參與者而言,「中國怎麼辦?」固然仍是關切重心,然而,「自己怎麼辦?」卻尤其是個大問題了,畢竟,每個活著的六四參與者,都得繼續在日常生活裡面對現實,自己的,中國的。
六四事件之後,我親身接觸的民運、學運參與者還算不少,其中不乏代表性人物,有些沉潛向學,成為學者;有些繼續扮演專業批判者,提供世界觀於中國的祕聞與內幕;有些消失了,消失在日常生活的關注裡,消失於對中國巨大成長的陰影下。吾爾開希的個案,是有點特別。
隨著時光的流逝,伴著中國的壯大,以及我自己不時前往中國的個人閱歷與長期閱讀心得,我尤其會注意這些六四流亡者,他們自身的成長與性情的變化,當然,他們對中國的觀察角度,更會成為我比對現實、比對我自己觀點的一些座標。我必須說,有些六四流亡者確實陷溺於昔日的光環,觀察變得喃喃自語;有些基於西方世界的需求,觀察變得自圓其說;當然也有些,繼續理直氣壯,卻不免脫離了中國當下的現實。
當中國度過六四事件的陰影,一路向上成長時,昔日年輕的六四鬥士,如何讓自己維持高昂的信念,繼續在漫漫人生路上,保有「與時俱進的成長鬥志」?我始終好奇著。
六四之後,吾爾開希走的路,不管是自己的抉擇,或是命運的安排,都可說是一條頗堪玩味的小徑。他逃亡赴美,完成學業,巧遇台灣女子,變成台灣女婿,定居台灣,成為新台灣人;當時,還是一個年少輕狂的大孩子,如今已進階成為兩個孩子的中年爸爸,連體型都很中年了。唯一不變的,是他持續對家國的關切,持續對公共事務的參與興趣,只是,「家國」裡有了台灣,「公共事務」裡有了台灣政治。吾爾開希的身分,更多樣了,他的人生圖像也更豐富了。我每每與他相遇,都能充分感覺,他對自己、對周遭事物的熱誠,始終沒變。當然,中國巨變的歷史現實,他從未逃避亦從未放棄過關切的責任。
做為民運一分子,吾爾開希對中國政治的關注,理所當然。他顯然知道,今日之中國,已非當年他站在天安門前呼喊自由的那個中國,中國富有了、強大了、自信了,但共產黨對自己統治的信心與不安全感,卻與日並進,這實在是極其矛盾的困局。吾爾開希流亡海外的經歷,使他有更寬廣的視野,來看待中國與共產黨的歷史處境。吾爾開希也因為具有維吾爾族的身份,他又比一般漢人民運者,多了幾分少數族裔的敏感智慧,對思索中國的出路,多添一道「他者」的警醒。尤有甚者,他也是台灣人了,站在台灣這一端,華人民主最前進的基地,他既以「新來者」(既來之)的視角,對台灣民主進程做參與式的觀察批判,亦可以「安之者」(則安之)的角色,對中國富裕之後,如何民主化的可能性,以台灣經驗做最好的推估與建言。
我理所當然地以為,此時此刻已然中年的吾爾開希,當是他人生最好階段的進行式。他有多重身分,他有多樣視野,他有用不完的熱忱,他有對家國最深沉的愛。雖然他說「希望」二字,對一位流亡者來說是多麼奢侈的字眼!但他自己,不就是一路抱持著希望,才能化險為夷,安然於日常生活的險關與單調重覆,成為許多中國人渴望民主、自由的希望之化身嗎?
我希望他快樂的活著,繼續認真思索中國與台灣的未來,「流亡者」最好的命運,是遇見愛,遇見真誠,遇見夢想。也許,這是他此刻才出書的理由吧。
自序
流亡者的五個名詞
——希望˙堅強˙責任˙理想˙自由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兩點,日本廣島的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高峰會在經過上午的開幕式後進入正式會程。大會司儀宣佈會議開始後介紹第一位上台的演講者:「天安門學生領袖,吾爾開希。」我在全場起立鼓掌歡迎聲中走上講台,開始我的發言:「很榮幸受邀在如此重要的場合表達中國異議分子的聲音,雖然,我更希望站在這裡的不是我,而是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劉曉波,我的好友,我的導師」。
我演講的題目是「希望帶來變革」,劉曉波是個富有理想的人,同時又是一個願意抱持希望的人。他在被以「陰謀顛覆政府」罪起訴,宣判當日,在法庭上所作的那篇著名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中,甚至對中國的監獄以及司法程式的一步步規範化也表達了讚賞。這是一個對中國的專制抨擊多年,為此第三次身陷囹圄的人,是一個從二十多年前就立志為推動中國的社會變革而全力以赴、萬死不辭的人,他當然絕對不是一個鄉愿到認為中國的今天有所進步就該受到讚美、收到接納、收到擁護的人;他在最後的陳述中表達對中國在共產黨統治的一點點進步的肯定是在表達希望,是在表達只要對中國的未來抱有希望,無論你的政治立場為何,都可能因為這點希望而帶來變化,而這些變化最終會給中國帶來我們夢寐以求的自由、民主以及現代文明。
然而,「希望」這個名詞對於一個流亡者來說是多麼奢侈!
這一天的十七個月之前,二〇〇九年六月三日,我從台北搭上長榮班機前往澳門。澳門是我持台灣護照,無需簽證,可以合法進入中國國境的唯一地方。雖然那裡仍然是特別行政區,但這已是我能夠在這一天到達的中國最近的地方。更何況,那裡有中國政府機構,我的計劃是在第二天,「六四」屠殺二十年週年當天,走入中聯辦,向我遇見的第一個中國政府官員大聲宣佈,我是中國政府通緝犯,前來自首,請安排我回到北京受審!
我已在臨行前委託在台北的朋友,在登機後替我發表聲明:
今天是二〇〇九年六月三日,我是吾爾開希,流亡的中國異議分子。
一九八九年,中國政府血腥鎮壓了發生在北京的民主運動,也就是「六四屠殺」,鎮壓之後,我受中國政府通緝,名列二十一個學生領袖第二名,被迫逃離中國,開始了我的流亡生涯。
今天,我決定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向中國政府駐澳門聯絡辦公室尋求投案。
二十年來,中國政府奉行流放民運人士的政策,相當一批異議分子被迫流亡海外。流亡者追求回家權力的抗爭從未停止,而中國政府對我們的這扇門則始終緊閉。
我不能回到中國而我的父母又受到中國政府限制出境,其結果,我已二十年未得與家人相見,我和我的父母為此受到極不公平的磨難。這是一個中國政府極其殘酷而無恥的行為,即不符合人類文明基本準則,也不符合中國人的傳統價值,更不符合包括中國憲法在內的各種保障公民權利的法律公約。
經過多年努力斡旋而沒有結果,我今天決定以投案這樣一種方法爭取回家。
我的投案絕對不應被理解為我承認自己二十年前的行為是違法和錯誤的,我在此重申一九八九年中國發生的慘劇,中國政府負有完全的、不可推卸的道義、政治及法律責任。我在投案之後,將利用中國法庭這樣一個表達平台,與中國政府對此進行爭論。我希望在二十年後,中國政府在「六四屠殺」這個歷史問題上能夠有新的立場,承認罪行,向全國人民道歉,追究相關人員責任,並向受難者家屬乞求寬恕。
我已於今日下午四點二十分,搭乘長榮BR805班機前往澳門,澳門是我持台灣的護照可以免簽證而進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我將於明日,六月四日,國殤日二十週年當天,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聯絡辦公室,尋求安排投案及引渡相關事宜。
感謝大家的關心與支持。
吾爾開希 |
流亡二十年不得回國,這是精神酷刑;二十年見不到父母家人,這不僅對我,更對我父母來說,已超過精神酷刑,他們受此折磨只是因為他們的兒子二十年前的言論和行為不見容於中國政府,這是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所無法容忍的野蠻原始的行為。我要以投案自首強烈抗議!我要回家,哪怕這回家意味著牢獄;我要見到日漸年邁的父母,哪怕這見面將是以探監的形式;我要繼續尋求二十年前中國大學生在街頭提出的與中國政府的「對話」,哪怕這對話以起訴和答辯的方式進行!
然而,我在澳門機場被扣留,並於第二天被強行遣返回台灣。那天晚上,我在澳門機場的移民局拘留室狹小的房間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時鐘到達十二點,六月四日,二十年了!難道我們將來都會是在海外紀念這一天嗎?難道我們離中國最近的就是這澳門機場小小的拘留室嗎?
在這一天,「希望」這個概念,離我好遠。
如果說流亡是精神酷刑,那麼流亡中失去返國的希望,則使得這一酷刑變得幾乎一分鐘也無法再承受!
演講結束,我與幾位我極為崇敬的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會晤,並召開記者會,繼續呼籲中國政府釋放劉曉波,容忍和傾聽不同的聲音。當晚,我回到廣島王子飯店二十層樓的房間,憑窗遠眺,夜景非常迷人。我看著廣島灣中的燈火,說不定,那移動中的某條貨輪,即將前往中國的上海港?這時突然意識到,我流亡的時間已經超過二十一年又四個月——也就是說,我流亡的時間已經超過我在中國生活的時間!
一股已經很久不曾感受的巨大的悲傷情緒湧上我的心頭。
很久不曾感受絕不是因為遺忘,流亡是不可能被遺忘的,即使在心情最為愉快的哪一天,比如兒子的出生,那流亡者的感受也從來不會真的消失,那是一種憤怒加上更多是思念的酸楚的複雜情感,每當希望的感覺低落,這感受中就會多出悲傷。但二十年的時間,我們也早已學會承擔起這些複雜的情感,懷著理想,堅定地抱持希望。如果要用一個詞來形容,那就是「堅強」:不需時時想起,也絕不會一夕忘記。學會堅強是每個流亡者的基本功課,學會堅強,就不會常常受到悲傷情緒的衝擊。
在我來到廣島五個月之前,又是六月三日,也是在日本,我試圖從成田機場搭機,經北京前往曼谷。我的計劃是在飛機抵達首都機場時,再次向中國官員聲明,我是中國的通緝犯,現在中國領土上尋求投案自首。儘管這次我的行程保密到家,機票也是在前兩天才在網路上購得,我在成田機場試圖搭機時,地勤的日本小姐一臉訝異、一臉狐疑地看著螢幕告訴我,這張看來一切沒問題的機票,被中國政府Cancel(撤銷)了。我投案自首的努力再度挫敗。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四日當天,我在中國大使館門前參加「六四」紀念活動,一躍翻過日本員警圍欄,試圖闖入中國大使館,再次向大使館「自首」尋求引渡回國。我記得那天站在大使館門口的心情,應該比起一年前在澳門更加憤怒、更加悲傷、更加絕望。
日本機動隊五、六個訓練有素的警察在幾秒鐘之內牢牢抓住了我,我再一次離中國領土幾步之遙而不得其門而入,之後的兩天,我在東京拘留所渡過,在囚室中渡過六四當天似乎要成為我獨有的紀念方式了。而此時的中國除了在天安門廣場一定是非常肅殺,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嚴防民運分子、訪民、藏人或其它受迫害的中國人借這一天國際媒體剩餘不多的對中國人權、政治話題的關注「滋事」,其它地方沉浸在剛剛成功舉辦過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並在風雨飄搖的國際金融風暴中屹立不搖,甚至要扮演頹敗西方的拯救者的角色,當政者是躊躇滿志、志得意滿的嗎?
再過了幾個月,十月八日,挪威奧斯陸,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宣佈,深陷獄中的中國異議分子,零八憲章的起草人,八九學運的參與者,我的好友和導師劉曉波為二〇一〇年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
兩天後,諾貝爾和平獎得獎人高峰會找到我,希望在劉曉波繫獄且無法聯絡其妻子劉霞的情況下,邀請我到廣島與會,發出中國異議分子的聲音。
當在廣島的兩天,日本以及國際媒體把正在日本參加亞太經合會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美國總統歐巴馬,日本首相菅直人,再加上達賴喇嘛和我的合照並列排出,並提出中國人權與政治改革這個議題時,呼籲釋放劉曉波時,我感受到二十多年前我在北京走上街頭時所受到的全世界的支持,這種久違的感受使得「希望」這個概念又似乎再度走近了我。
今年,二〇一三年,本書出版時,六四紀念日又屆,我們仍然在海外,同時我們學會的堅強和希望也已深植我們的心中。
這希望到底是什麼呢?除了最終我能夠回到中國,進入中國的一刻親吻久違的土地,擁抱我的父母,祈求他們的原諒,回到天安門廣場向「六四」英靈報告這二十多年來我們的努力。這希望總是要具體到能夠讓六四英靈感受到當初為之犧牲的理想實現有日吧?
如果說二十世紀的世界歷史僅有兩頁,它一定會記載兩件事:兩次世界大戰及之後幾十年的冷戰,也就是反法西斯和反專制,而這兩大戰役都在「自由、民主」的旗幟之下,這就是二十世紀歷史的主軸。二十四年前在柏林牆倒塌,東歐、蘇聯共產黨國家一個個走入歷史的時刻,整個世界因為感受到期盼千年的和平與文明正在降臨而歡欣鼓舞,自由、民主戰勝專制,完成了二十世紀的歷史使命。中國的大學生雖然在八九年走上街頭,啟動了這場戰役最後一場勝利戰鬥的序曲,卻在這場全世界參與的嘉年華中缺席,全世界也為中國傷痛也扼腕。
「六四」屠殺,令成百上千個家庭破碎,母親悲傷;中國沒有走上民主與自由的路,卻走上了員警統治、權貴專制。「六四」把我這個當初二十一歲的初生之犢變成了經過流亡二十多年的中年人,今天的我是一個堅定的自由主義者、堅定的異議分子堅定的民運人士。我們學會了希望,我們學會了堅強,我們更需思索二十四年前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以血腥的方式收場,把我們造就成為異議分子這件事對我們的意義為何?
我們要謹記另外一個名詞:責任。
我堅信,中國即將進入一個新時期,在這個時期,專制將褪去,自由與民主即將落地生根,中國人將面對一個在自身歷史中未曾經歷的轉型過程。而歷史進程剛剛走過的這幾十年,共產黨專制對人性進行了無情的摧毀,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因素在中國一旦誕生即受扼殺,在這些使得對民主以及對於公民意識的呼喚將會是一個嚴峻的課題;此時民族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都會在中國找到土壤而萌芽,而成為一個現代文明國家所需的自由民主價值要怎樣或者說能不能在中國順利誕生?傳統文明中的社會和諧、榮譽、忍讓等精神與現代文明中的個人權利、表現等精神如何找到相容的根基?幾十年共產黨殘暴統治所遺留的社會正義課題如何解答,民族之間的仇恨如何消解?
二十多年來,仍然願意以「天安門一代」以「民運人士」自稱的夥伴們,一直都在思考。每個人可能都有自己面對這些嚴峻的題目的方式和角度。我流亡,使我失去回到祖國的自由,卻也宿命般地把我拋向這世界最為自由的地方,我先後在法國、美國和台灣生活,如飢似渴又如魚得水地汲取自由民主的養分。我,在流亡中學會永遠胸懷希望,永遠堅強,永遠牢記責任。而要學會作到這些,必須找到源源不絕的動力,我的動力來源是我的理想。
我的理想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