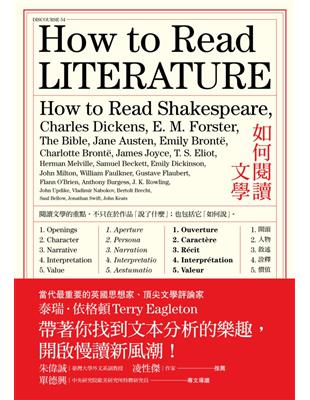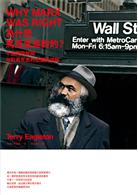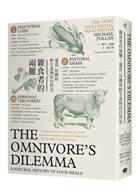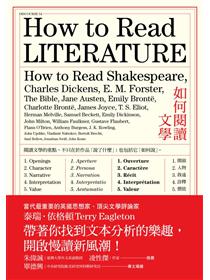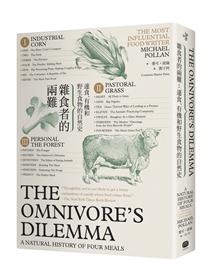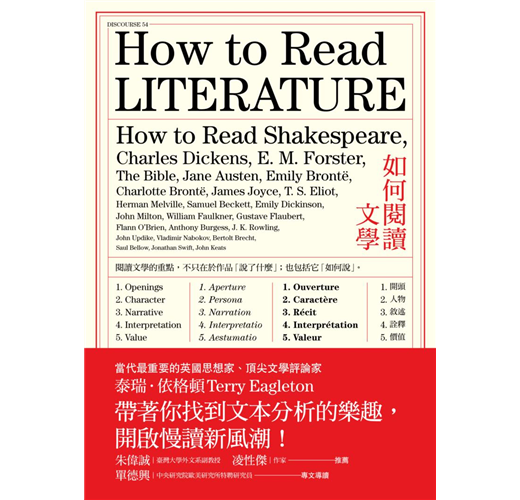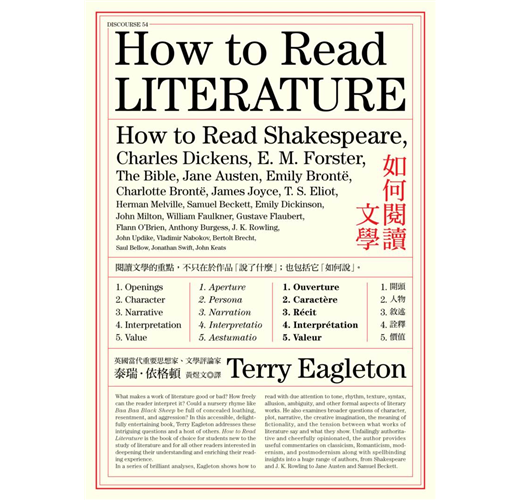當代最重要的英國思想家 & 頂尖文化評論家 泰瑞‧伊格頓
帶著你找到文本分析的樂趣,開啟慢讀新風潮!
◎ 朱偉誠(臺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凌性傑(作家)推薦
◎ 單德興(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專文導讀
☆閱讀文學的重點,不只在於作品「說了什麼」,也包括它「如何說」。☆
這是一本寫給初學者與文學愛好者的指南。當代最頂尖的文化評論家泰瑞‧伊格頓以一連串精彩的分析手法,為讀者示範了從敘述、情節、角色、文學語言、詮釋、小說的本質、價值判斷等各個面向的分析方法,並引用了從莎士比亞到 J. K‧羅琳等大量英文文本,是一本生動有趣的文學「伴讀」之書,也是最翔實有用的文學分析入門。
開頭 Openings
創世記的開頭、白鯨記的開頭、咆哮山莊的開頭……各有其不同的特色與筆調。文學作品的開頭,除了負責捉住讀者的目光,其實也暗示了作品的情節展開、格局與人物的性格。
人物 Character
文學人物的生命只存在於文本之中,唯有閱讀,才能讓他們持續存在。不同流派的角色會有不同的呈現方式,他們所帶給讀者的,是想像與體驗另一種生活的可能。
敘事 Narrative
敘事是文學作品所採取的觀點。敘事者的設定,將決定作品的特色、限制與是否可靠。而情節則是書中內容的概述,是敘事的一部分,當人們問我們故事在說什麼時,他想知道的就是所謂的情節。
詮釋 Interpretation
文學的存在不是為了告訴我們事實為何。當小說被置入某個特定的脈絡中,其真實或虛假就不再是重點。要緊的是,小說如何在想像的邏輯裡行動,而我們如何對之做出詮釋。
價值 Value
文學作品的好壞如何判斷?洞察的深度、與真實人生的貼近程度、形式的連貫、普世性的訴求、道德的複雜性、語言的創造性、想像的視野……這些都曾被視為評估作品的指標,而世代不間斷的詮釋與閱讀,將賦予文學作品新的價值。
作者簡介:
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
英國蘭開斯特大學英文系傑出教授、聖母大學英文系傑出客座教授。是英語世界中最具影響力的文學評論家之一。他撰寫了超過四十本關於文學理論、後現代主義、政治、意識型態與宗教的書。現居於愛爾蘭。
譯者簡介:
黃煜文
台大歷史所碩士,專職譯者,譯作包括《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氣候變遷政治學》、《鴨子中了大樂透》、《為什麼是凱因斯?》、《歷史的歷史: 史學家和他們的歷史時代》、《最近比較煩:一個哲學思考》、《閱讀蒙田,是為了生活》、《世界史》等多部作品。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看到伊格頓對於西方文學名著信手拈來,旁徵博引,精讀細品,不時夾雜著英國人特有的幽默,透露出個人的立場,即使讀者不見得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也會折服於他的博學,欣賞他的評論與個性,油然生出『斯人也而有斯文也』之感……(本書)除了注意文本細節(微觀),闡明不同文學主義與流派的差異(宏觀)之外,也透露了伊格頓的左派觀點與英式幽默。」──單德興(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卓越、眩目以及其他書評家的形容詞都不足以形容《如何閱讀文學》。而且這本書──容我斗膽這麼說──還很好笑。顯然你應該讀讀泰瑞‧伊格頓剛完成的這部作品,因為你可以從中學到很多東西。不管怎麼說,這個人可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批評家與老師,他以福爾摩斯的技巧抽絲剝繭,同時也揶揄句子乃至於某個單字的意義。但《如何閱讀文學》真正特出的地方,在於伊格頓個人的機智與幽默,他的隨和與親切躍然紙上。這不只是一本值得研讀的書,也是一本床邊書,一本充滿樂趣的書。」──麥可‧德達(Michale Dirda),《悅讀經典》(Classics for Pleasure)作者
「這不只是一本娛樂書,而是一本重要的書。在尼采之後,伊格頓提到「慢讀」這項人類活動正遭受嚴重的威脅。在本書中,他引領我們回到最基本的元素,透過一連串敏銳的分析,將閱讀的核心面向融入其中。我喜愛伊格頓輕鬆的筆調,如此容易理解而具體;但他並未因此而喪失了細微或巧妙。這是一本適合每個讀者閱讀的作品,不只限於初學者。而且也非常適合在課堂上講授。」──傑‧帕里尼(Jay Parnini),《詩為何重要》(Why Poetry Matters)作者
大師小烹,金針度人──序伊格頓《如何閱讀文學》
單德興
去年(2013)六月,我赴愛爾蘭參加《格理弗遊記》(Gulliver’s Travels)的作者綏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就任聖帕提克大教堂總鐸三百週年慶,向文學大家致敬。我特地取道倫敦,走訪一些名勝古蹟與文教之地,著名的書店街查令十字路(Charing Cross Road)當然是參訪的重點,尤其是以學術書籍聞名的黑井書店(Blackwell Bookstore)。當我在書架上看到伊格頓的新書《如何閱讀文學》(How to Read Literature)時,既驚又喜:驚的是這位歐美的文學理論與批評大師竟然願意寫這麼一本入門書;喜的是他為了提升文學教育、培養讀者「對於語言的敏感」(sensitivity to language)而拔筆為文。一想到「大師為了普渡眾生而出手」,我不禁會心一笑。
我站在書架前翻閱,先從序言了解作者撰寫此書的良苦用心,再從目錄認識全書架構,並閱讀內文中對一些古今文學名著的品評,尤其是我曾譯注的《格理弗遊記》。看到伊格頓對於西方文學名著信手拈來,旁徵博引,精讀細品,不時夾雜著英國人特有的幽默,透露出個人的立場,即使讀者不見得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也會折服於他的博學,欣賞他的評論與個性,油然生出「斯人也而有斯文也」之感。
其實華文世界對伊格頓並不陌生。一九四三年出生於英國曼徹斯特的他,是第三代愛爾蘭移民,來自工人家庭背景,家境寒微。但他聰敏好學,得以就讀劍橋大學,從學於文化批評大家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先後任教於牛津大學、曼徹斯特大學、蘭開斯特大學、愛爾蘭國立大學等。伊格頓的著作等身,至今已超過四十本,至少有下列幾本譯成正體字流通於華文世界──《文學理論導讀》(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1983;吳新發譯,書林,1993)、《馬克思》(Marx, 1997;李志成譯,麥田,2000)、《文化的理念》(The Idea of Culture, 2000;林志忠譯,巨流,2002)、《理論之後》(After Theory, 2003;李尚遠譯,商周,2005)、《生命的意義是爵士樂團》(The Meaning of Life, 2007;方佳俊譯,商周,2009)、《散步在華爾街的馬克思》(Why Marx Was Right, 2011;李尚遠譯,商周,2012)。尤其是《文學理論導讀》一書自問世以來便風行全球,譯成多種語文,研讀當代文學理論的學者與學子幾乎人手一冊,售出逾百萬冊。該書合法授權版中文正體字譯本出版至今二十年,已增訂二版九刷,售出逾萬冊,讀者以英/外文系的大學生為主,也有中/台文系所的大學生與研究生,更普及一般社會人士。
如果說《文學理論導讀》因為討論的主題是文學理論所以顯得內容較深奧,風格較抽象,寫作態度較嚴肅;那麼《如何閱讀文學》則是文學導讀,不僅解說文學作品與賞析的重要因素,並針對特定文本加以批評示範。相形之下,《如何閱讀文學》的文字更簡單,風格更具體,寫作態度更為平易近人。全書提綱挈領,娓娓道來,內容豐富,舉重若輕。從史詩、詩歌到童謠,從聖經、莎士比亞到《哈利‧波特》……有如大師小烹,談笑風生,左右逢源,揮灑自如,處處展現了作者的學養與見地,也不時流露出性情與幽默。
在二○一二年六月四日《牛津人評論》(Oxonian Review)的訪談之中,伊格頓透露自己有一本書即將出版,書名有些老調(當時提到的書名是《如何研究文學》〔How to Study Literature〕)。撰寫此書的動機,在於他擔心「文學批評幾乎死了」,當年在劍橋大學所學的,像是「仔細分析語言,回應文學形式,道德嚴肅感」已邈然無蹤,而他「很珍惜的對於語言的敏感」也消逝了。他之所以有此慨嘆,起因於二○○一年在曼徹斯特大學任教時,驚覺學生閱讀文學的能力低落,「能對一首詩的背景深入了解,卻不知如何就詩論詩」。他坦言「明年要出的這本書,其實就是試著把我心目中的文學批評重新納入自己的行動方針」,並提到該書要「討論的問題就是價值、好壞、形式、主題、語言、意象諸如此類的事」,而這些是他「往昔不假思索就在做的事」。
身為當代文學理論的代表性引介者與推廣者,竟然會如此關切「喪失細讀的傳統」(the loss of the close reading tradition),也許令人覺得反諷。但他指出,理論與閱讀之間的對立其實並不成立(照他的說法是「偽對立」〔a false opposition〕),因為「一眼望去,偉大的理論家,從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克莉絲特娃(Julia Kristeva)到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幾乎都是很仔細的讀者──對一些人來說,德希達是太過仔細的讀者。」在他看來,問題與其說是出在理論,不如說是出在「媒體、後現代主義、一般文化的變遷、書寫文字的狀態等等」。這位立場鮮明的左派文學批評家並不諱言,只要有人支持「回歸對於語言的敏感」,即使彼此政治立場南轅北轍,也都能在精讀細品文學中找到共通點。
伊格頓在簡短的序言開宗明義指出,「尼采所稱的『慢讀』(slow reading)傳統正面臨逐漸消失的危機」,正是這種危機感促使他寫這本書,希望它不僅「可以充當初學者的指南」,也能對文學研究者或愛好者「有所幫助」。他自言「希望提供讀者與學生一些基本的批判工具」,增加他們對於一些作家、作品與文學思潮的認識。依他之見,感性的喜好與理性的分析、批判不僅不矛盾牴觸,反而能相輔相成,令人對文學作品既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而且說得出一番道理。換言之,他是抱持著「欲將金針度與人」的動機,將數十年閱讀文學與鑽研理論的心得與功力,以淺易的文字傳授給讀者,目標在於提升文學評論技巧與語言敏感度。這個動機與目標,與多年大力提倡並躬身實踐精讀、慢讀的我國作家王文興如出一轍,而後者對於慢讀的要求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理想的速度為「一小時一千字,一天不超過兩小時」,以深入體會一字一句的好處。
序言中表明此書「將試著說明各種問題,例如敘事、情節、人物、文學語言、小說性質、批判性的詮釋問題、讀者的角色與價值判斷的問題。」全書五章,第一章「開頭」(Openings)討論文學作品如何起頭,接著論述文本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Character)以及吸引人往下閱讀的「敘事」(Narrative),繼而說明「詮釋」(Interpretation)的作用與意義,歸結於作品的「價值」(Value),其架構基本上由淺入深,由具體而抽象,舉證豐富,文字平易。
第一章「開頭」強調作品的文學性,指出除了要留意文學作品「說什麼」(內容)之外,也要留意「怎麼說」(表現方式),接著針對一些著名的小說、戲劇、詩歌以及聖經的開頭,以文本分析來示範文學批評的手法,剖析各文本開頭的技巧、意義與作用,因為作者都在「開頭使出看家本領,希望藉此讓人留下印象,吸引住讀者飄忽不定的目光。」
第二章「人物」指出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只存在於文本中,於讀者閱讀時才存在,接著列舉 character 一字的不同意涵,說明文學作品中的不同人物與類型,人物與語言、環境、脈絡的關係,特別著墨於寫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不同的人物觀與呈現方式:前者的典型「通常合理而穩定,前後一致」;後者則複雜、深邃而不穩定,並更著重於語言本身。
第三章「敘事」論述小說中不同的敘事觀點、特色與限制,可靠與不可靠的敘事者,戲劇則透過劇中人來表達不同的觀點,敘事與人物的關係,作者與作品的關係,顯示(showing)與訴說(saying)之別,寫實主義、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不同的敘事觀與對結局的看法,說故事的昔今之別,敘事與情節的不同等等。
第四章「詮釋」強調文學的特色在於虛構性而且是「可攜帶的」(portable,也就是不限於特定的時空與脈絡),文本的意義必須藉由讀者參與創造,既非一成不變,也不能隨便強加,而解讀與詮釋文學時固然要運用想像,也必須依照邏輯與文本證據,然而文學作品並「沒有唯一與正確的詮釋」,只要持之以據,言之成理,便可存此一說,增加文本的豐饒繁複。
第五章「價值」列舉評斷文學作品好壞的一些普遍的假定(如原創性、真實的描述、普世的主題、深刻性與複雜性、形式的統一、語言的創新),接著以作品來說明這些假定雖然合理,卻不是毫無問題,並證諸新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不同的藝術觀與評價,而偉大的文學作品的價值雖很難說是「永恆」或「普世」,但藉由一代代的閱讀與詮釋可使文本不斷產生新意,獲得新生,穿越不同的時空,感動不同的讀者。然而,全書結尾時留下一個「陰魂不散」的問題讓讀者去思索。此處由於篇幅所限,僅能略述,細節有待讀者閱讀全書,仔細體會。
《如何閱讀文學》除了注意文本細節(微觀),闡明不同文學主義與流派的差異(宏觀)之外,也透露了伊格頓的左派觀點與英式幽默。在左派觀點方面,如「狄更斯晚年讚美擁有實作技術的人,輕視那些靠股票與股份生活的人。體力勞動是真實的,紙上富貴是寄生在別人的勞動之上」;「在十九世紀,文學對工人階級來說是一種感受方式,它讓工人有機會想像騎馬帶著一群獵犬外出打獵是什麼樣子,或嫁給貴族是什麼感覺,因為這些事情現實上不可能發生。因此詩與小說值得閱讀的理由又多了一個。」在英式幽默方面,如「許多文學作品會回溯過去,但很少有比《創世記》還要遠古的。想比《創世記》更往前回溯,恐怕會從世界的邊緣掉落」;「像簡‧愛這樣的女主角,自以為是、愛說教、稍微帶點受虐狂傾向,恐怕很少有人願意跟她一起共乘計程車」;「馬克白夫人到底有幾個孩子,數目是不確定的,這或許可以讓她便於申請兒童福利給付。」
這類大師現身說法之作及其翻譯自有用意與效應。傅月庵在〈2013開卷好書獎──非文學類/評審報告〉中,便語重心長地指出,每年台灣的數萬本出版品中,相較於中文創作,翻譯作品「相對豐饒多元,深入淺出,類皆佳作」。他進一步指出這些外國作者的背景主要有二:一為學術界,一為新聞界。後者是「長期關注、調查某一主題,用心寫成」;前者的特色則是「學有專精的學者或各行各業的專家,放下身段,以簡白的文字,舉重若輕地闡述專門學科或一己之見,造福普通讀者。」《如何閱讀文學》顯然屬於後者,藉由專家學者的投入,甚至大師的加持,讓一般讀者能對特定的議題具有基本的認識。
伊格頓以資深讀者的文學喜好、批評家的敏銳功力與理論大師的豐富學養,回歸到作品本身,根據特定的文學與批評因素,解讀文本細節,彰顯作家的巧妙與作品的特色,並置於更寬廣的文學與文化脈絡,大力推動博雅教育,藉此培養讀者對於語言的敏感以及批判的能力,進而將這種識讀能力(literacy)運用於人生各方面。此書特意以簡易的英文寫成,讀者閱讀中譯之餘,若有興趣也可直接閱讀英文原本,欣賞其文字風格,當更能體會作者的用意,而有另一番感受。
基於上述種種特色,本書值得肯定與推薦。不容諱言的是,每位批評家都有其背景、特色與限制。伊格頓所舉的例證為西洋文學,主要是英國文學,讓讀者能透過他深入淺出的解說進入文學殿堂,獲得一些解讀語言與文本的技巧,領會這些文學作品微妙之處,既「看熱鬧」,又「看門道」,進而如法炮製,運用於其他文本。若讀者讀過這些作品,正可印證自己的閱讀經驗;若尚未讀過,希望書中的觀察與評論能引發讀者的興趣,進而閱讀這些文本,嘗試自行品評。
伊格頓在《文學理論導讀》〈中文版前言〉結尾特地提到,「台灣的社會一定可依自身的方式辨識出許多此類問題。這些都是普受關注的問題,我樂於有此機會與更廣泛的讀者分享個人在這些問題上的看法。」《如何閱讀文學》也可作如是觀。有鑒於此書的寫作動機、呈現方式與目標效應,至盼華文世界的大師級學者/讀者也能懷著廣結善緣、金針度人之心,針對普受關注的文學議題,根據華文文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脈絡,寫出類似的作品,讓華文世界的讀者有機會分享資深讀者多年精讀、鑽研文學的心得與看法,與此書參照,以培養文學興趣,精進閱讀技巧,磨練批判工具,拓展視野,提升眼界,共同為「文學共和國」開疆闢土,貢獻心力。
二○一四年一月十六日
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名人推薦:「看到伊格頓對於西方文學名著信手拈來,旁徵博引,精讀細品,不時夾雜著英國人特有的幽默,透露出個人的立場,即使讀者不見得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也會折服於他的博學,欣賞他的評論與個性,油然生出『斯人也而有斯文也』之感……(本書)除了注意文本細節(微觀),闡明不同文學主義與流派的差異(宏觀)之外,也透露了伊格頓的左派觀點與英式幽默。」──單德興(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卓越、眩目以及其他書評家的形容詞都不足以形容《如何閱讀文學》。而且這本書──容我斗膽這麼說──還很好笑。顯然你應該...
章節試閱
第二章
人物
要檢視劇作或小說的文學性,最常見的一種方式是把劇作或小說中的人物當成真實人物來看待。就某個意義來說,確實是如此,我們幾乎不可避免會這麼做。形容李爾王(Lear)的恃強凌弱、易怒與自欺,免不了讓人聯想到現代報紙報導的某個富豪鉅子。然而,李爾王與富豪鉅子的差異,在於前者只是印在紙上的黑字,至於後者,遺憾的是,他並非簡單的幾個記號。富豪鉅子在我們遇見他之前就已真實存在於這個世界,文學角色剛好相反。在戲上演之前,哈姆雷特(Hamlet)並非真實存在的大學生,即使戲是這麼告訴我們的。哈姆雷特其實根本不存在。在步上舞臺之前,黑達‧加布勒(Hedda Gabler)從未存在過一秒鐘,我們對她的認識完全是易卜生(Ibsen)的劇作告訴我們的。此外,我們沒有其他的資料來源能知道黑達。
希斯克里夫(Heathcliff)神祕地從咆哮山莊(Wuthering Heights)消失了一段時間,小說並未告訴我們他去了哪裡。有一種說法認為他回到了利物浦,也就是他幼年首次被發現的地方,並且在當地靠奴隸貿易致富,另一種可能則是他在里丁(Reading)開了美髮沙龍店。事實上,希斯克里夫並未停留在地圖上的任何地方。相反地,他居無定所,四處漂泊。他去的地方在真實生活中並不存在,即使他提到了印第安納州的蓋瑞,但那也是虛構之物。或許,我可以問希斯克里夫有幾顆牙齒,但我們得到的答案將只是不確定的數字。我們可以合理地推論他有牙齒,但我們無法知道他有幾顆牙。著名的批評文章〈馬克白夫人生了幾個小孩?〉提到,我們可以從劇作的描述來推斷,她或許至少生了一個孩子,但我們不知道她是否又繼續生了其他孩子。因此,馬克白夫人到底有幾個孩子,數目是不確定的,這或許可以讓她便於申請兒童福利給付。
文學人物的生命只存在於文本之中。據說,一名劇場經理在演出哈洛德‧品特(Harold Pinter)的劇作時,曾向作者請教,希望能得到演員在上臺前該做什麼的建議。但品特的回答是:「不要多管閒事」。愛瑪‧伍德豪斯(Emma Woodhouse)是珍‧奧斯汀(Jane Austen)的小說《愛瑪》(Emma)的女主角,但只有當人們閱讀到她時她才存在。如果沒有任何人在任何時間閱讀到她(鑑於這部小說的精采程度,以及全世界有數十億英語讀者閱讀,這種狀況幾乎不可能發生),那麼愛瑪將不存在於這個世界上。愛瑪在《愛瑪》一書結束後就消失無蹤。她活在字裡行間,而非活在富麗堂皇的鄉村宅邸裡,文本是文本與讀者產生交流的地方。書籍本身是個有形體的物質,即使沒有人翻開書本閱讀,書本也依然存在。但文本的內容是由意義構成的類型,這些意義類型不像蛇或沙發一樣,它無法獨立存在。
有些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會在末尾以溫柔的眼神遙望小說人物的未來,想像他們年事漸長、頭髮斑白,被一群嬉鬧的孫子孫女所圍繞,所有人都沉浸在快樂的氣氛裡。小說家很難放下小說人物,就像父母有時很難放下對兒女的牽掛。當然,以溫柔眼神遙望小說人物的未來也可說是一種文學技巧。文學人物沒有未來,他能擁有的希望甚至比不上關在牢裡的連續殺人犯。莎士比亞在《暴風雨》末尾以美麗的詩句表達這一點,至於另外一段我們先前已經看過:
高興起來吧,我兒。
我們的狂歡已經終止了。我們的這一些演員們,
我曾經告訴過你,原是一群精靈;
他們都已化成淡煙而消散了。如同這虛無縹緲的幻景一樣,
入雲的樓閣、瑰偉的宮殿、
莊嚴的廟堂,甚至地球自身,
以及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將同樣消散,
就像這一場幻景,
連一點煙雲的影子都不曾留下。構成我們的料子
也就是那夢幻的料子;我們的短暫的一生,
前後都環繞在酣睡之中……
隨著戲劇接近尾聲,人物與事件也消失在稀薄的空氣裡,因為在虛構的情節中,他們已無處可去。他們的作者也即將從倫敦的戲劇院消失,返回斯特拉特福(Stratford)的老家。耐人尋味的是,普洛斯彼羅(Prospero)的一席話,並未讓舞臺的不真實,與真實男女有血有肉的現實生活對立起來。相反地,他口中戲劇人物的不堪一擊恰好成了一種隱喻,足以反映現實人生虛幻不真實的一面。因為不光只有莎士比亞想像了一連串虛構人物,如愛麗兒(Ariel)與卡利班(Caliban),就連我們也一樣做著夢。即使是實際聳立在地上的入雲樓閣與瑰偉宮殿,充其量也不過是舞臺布景罷了。
戲劇可以教導我真理,不過這個真理說的卻是我們的存在其實帶有虛幻的性質。戲劇提醒我們人生如夢,人生短暫、多變、缺乏堅實的基礎。因此,藉由提醒我們人生是有限的,可以讓我們培養出謙遜的美德。這是個寶貴的體悟,因為我們有許多道德難題來自於某種無意識的假定,我們很容易以為自己會長生不死。事實上,我們的人生就像《暴風雨》的末尾一樣戛然而止。這聽起來或許讓人感到沮喪。如果我們接受自身的存在就像普洛斯彼羅與米蘭達的人生一樣,脆弱而短暫,我們或許能從中得到一些領悟。我們也許不會像過去那樣以過度戒慎恐懼的心情看待自己的人生,而是更加放鬆地享受人生,停止傷害他人。或許這正是普羅斯彼羅──他在戲裡是相當奇怪的角色──要我們高興起來的原因。世事變化無常,因此不需要感到扼腕。如果愛情與夏多諾夫杜帕普(Châteauneuf-du-Pape)的好酒均有消逝的一日,那麼戰爭與暴君也是一樣。
「characeter」這個字在今日可以指符號、字母或象徵,也可以指文學裡的人物。它源自古希臘文,意思是指銘刻的工具,可以留下特定的記號。推而廣之,character也可以指一個人的特徵,就像一個人的簽名一樣。character就像今日的字元參照一樣,它是一種符號,一種對男女樣貌的刻畫與描述。之後,它又直接用來指稱男女。原本用來代表個人的符號,現在成了個人本身。記號的獨特性也成為個人的獨特性。「character」這個字因此成為比喻的一種,稱為提喻法,也就是以部分來代表全體。
以上的說明不光只是一種技術性的陳述。character從個人的獨特記號轉變成個人本身,這段變化的過程與整個社會歷史息息相關。簡言之,這種轉變與現代個人主義的興起有關。個人是透過自身的獨特性來界定,例如自己的簽名與旁人無法模仿的人格。個人用來區別彼此的特點,要比個人彼此之間的共通點來得重要。湯姆‧索亞(Tom Sawyer)之所以是湯姆‧索亞,在於他的一切特質都與哈克‧芬恩(Huck Finn)不同。馬克白夫人之所以是馬克白夫人,在於她那殘暴不仁的意志與勇往直前的野心,而非她的痛苦、笑容、悲傷與噴嚏。因為這些是她與其他人共有的性質,所以這些表現實際上就不能說是她特質的一部分。如果我們把這種說法推到極端,男人與女人這種相當耐人尋味的概念,顯示男人與女人是什麼以及男人與女人做什麼,不盡然真的能代表「他們」。因為他們是什麼與他們做什麼並不是他們特有的;而且由於性格或人格被認為是不可比較的,因此他們是什麼與做什麼就不能說是性格或人格的一部分。
今日,character(性格)這個詞指的是個人的心智與道德特質,如安德魯王子評論的,他說在福克蘭戰爭槍林彈雨的環境下,「對於性格的建立非常有幫助」。或許他想讓自己的性格多受一點錘鍊。當然,character這個字也可以指小說、劇作、電影這類作品裡的人物。然而,我們也會用character這個字來指稱實際的人,例如,「在梵蒂岡溫德爾飯店外頭嘔吐的那些人(characters)是誰?」character也可指某個特立獨行的人,例如,「我發誓,先生,他是個人物(character)!」 令人好奇的是,character比較常用來講男性,而非女性,它反映出一種非常英式的對怪癖的喜好。英國人讚賞脾氣不好、不迎合流俗的類型,這些類型的人總是與身邊的人格格不入。這些怪人跟誰都處不來,只能一個人獨處。出門肩上停著一隻白鼬,或者頭上套著牛皮紙袋的人,據說也可以稱為character,表示他們的脫離常軌予人一種親切的感受,因而獲得大家的縱容。因此,character這個字蘊含著寬容的精神。我們因此不會專斷地將某些逸脫常軌的人置於保護管束之列。
在狄更斯的小說裡,有些怪人討人喜歡,有些則討人厭。狄更斯筆下的人物也有介於這兩個極端的,他們可能有著讓人覺得有趣的怪癖,而這些怪癖也使人隱隱感到不安。他們似乎無法站在別人的視角來看世界,只是一味固執自己的想法。這種道德斜視症使他們充滿喜感,但也可能使他們做出不道德的事。精力充沛的獨立心智,與拒人於門外深鎖在內在自我之中,兩者的差異只在一線之間。封閉內心太久,很可能造成精神失常。「characters」與瘋狂相隔絕不遙遠,這一點可以從薩繆爾‧約翰生(Samuel Johnson)的人生看出。迷人與怪異只有一步之遙。
沒有規範,就沒有偏差。特立獨行的人頑固地堅持自己的行事作風,並且沾沾自喜,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們任性的基礎其實來自於現實上存在著一群「正常」男女。能稱得上古怪,主要是因為對照著標準行為。還是一樣,這種狀況在狄更斯的世界裡看得最明顯,他的人物總是分成兩種,慣常的與特異的。只要有小奈兒(Little Nell)──她是《老古玩店》(The Old Curiosity Shop)裡令人感到煩悶的美德典範──這樣的人存在,世間就免不了出現一個奎爾普(Quilp),一個野蠻的侏儒,他嚼著點燃的雪茄,威脅著要咬他的妻子。只要有尼可拉斯‧尼克比(Nicholas Nickleby)這樣的年輕紳士,就會有威克佛德‧斯奎爾斯(Wackford Squeers)這樣的獨眼怪獸,惡棍般的校長,他從不教導這些受欺凌的學生拼「窗戶」這個字,反而要他們把學校的窗戶擦乾淨。
問題是,如果正常的人物具備所有的美德,則怪異的人物擁有美好的生活。如果能跟費根喝啤酒,誰還會跟奧利佛‧崔斯特共享柳橙汁。為惡不悛要比受人尊敬更吸引人。當維多利亞時代的中產階級把正常界定為節儉、謹慎、耐心、貞潔、順從、自律與勤勉時,邪惡顯然鼓吹的就是其他令人舒服自在的面向。在這些德行重重束縛下,脫離常軌自然成了一種選擇。因此,後現代對吸血鬼與哥德式恐怖、對反常與邊緣的著迷,在今日儼然成了正統,就像節儉與貞潔在十九世紀大受標榜一樣。《失樂園》(Paradise Lost)的讀者幾乎沒有人喜歡彌爾頓筆下的上帝,祂說起話來就像便祕的公務員,反倒欣賞鬱鬱不平而叛逆的撒旦。事實上,這可能是英國歷史上首次出現美德令人厭煩而邪惡反而受人喜愛的現象。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十七世紀中葉的作品中讚揚英雄或貴族的特質,如勇氣、榮譽、光榮與寬大;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在十七世紀末則宣揚中產階級價值,如勤勉、節儉、冷靜與穩健。
第四章
詮釋
近年來,英國文學最受喜愛的孤兒是哈利‧波特。哈利小時候寄居在討人厭的德思禮(Dursley)家中,他的遭遇跟皮普的經驗,以及簡‧愛小時候在里德(Reed )家的遭遇沒什麼不同。然而,在哈利的例子裡,卻出現了佛洛伊德的家庭羅曼史症候群。哈利出身的家庭遠比德思禮家來得顯赫。事實上,在《哈利波特──神祕的魔法石》中,哈利‧波特首次進到霍格華茲學院時,他發現自己已是一個名人。哈利‧波特出身巫師家族,他們的地位不僅高於德思禮家族(這並不困難),也高於麻瓜(沒有魔法能力的一般人)。他的父母不只是傑出的巫師,也受眾人尊敬。與《遠大前程》相反,這裡的幻想都是真實的。與皮普不同,哈利不需要成為特別的人,因為他「本來」就特別。事實上,有許多關於哈利是彌賽亞的傳言,這個地位恐怕不是想往高處爬的皮普所能企及的。雅各斯告訴皮普不利他日後發展的消息,反觀頭髮蓬亂、身形巨大的海格則是向哈利透露他的真實身世,顯然他將有個不同於凡人的未來。哈利是個謙遜的男孩,絲毫沒有野心,與盛氣凌人的皮普相比,哈利更惹人同情。他的好運早已擺在他的面前,毋需費心就能取得。
哈利有個差勁的代理父親,那就是粗野的德思禮先生,但他也因此獲得補償,他有了一堆好代理父親,如睿智的長者鄧不利多、海格與天狼星布萊克。他與德思禮一家人同住,但那不是他真正的家。他還有個幻想的家(霍格華茲),那是他真正的歸屬之地。哈利‧波特小說因此對現實與幻想做出區別,但也讓這些區別遭受質疑。鄧不利多告訴哈利,事情在腦子裡發生,不表示在現實上不存在。幻想與日常現實匯聚在寫作之中,而寫作往往盤旋在現實主義與非現實主義之間。哈利‧波特小說描繪的現實主義世界往往會發生極不可能發生的事件。讀者必須認清小說中的現實,然而才能享受現實被魔法力量改變的樂趣。由於絕大多數讀者是兒童,而兒童通常沒有地位或權威,因此當他們看到其他孩子擁有強大的力量時,無疑能產生極大的滿足。現實主義與非現實主義的交融成了哈利‧波特小說的核心,即使每一頁都出現熟悉與奇異的東西突兀地結合在一起也沒關係。例如,你看見穿著藍色牛仔褲的人物施法念咒。掃帚柄降落之後,會吐出塵土與小卵石。食死人與牡丹姑婆同時並存。不真實的生物進出真實的門。哈利曾經使用魔杖把他的手帕變乾淨,他因為擦爐子而把手帕弄髒了。為什麼不乾脆用魔杖把爐子清乾淨呢?
如果魔法可以解決人類所有的問題,那麼就不需要敘事了。我們知道故事要吸引人,裡面的人物必須遭遇不幸、啟示或命運的變化。在哈利‧波特小說中,這種崩解不可能來自魔法世界與現實世界的衝突,因為魔法一定能輕鬆戰勝現實,如此一來就不可能出現冒險犯難的情節。所以崩解一定要來自魔法世界內部的分裂,也就是好巫師與壞巫師的鬥爭。魔法的力量如同雙面刃,可以為善,亦可以為惡。唯有從這個地方出發,情節才可能展開。然而這也意謂著善與惡並非截然二分,因為善與惡似乎來自於同一個源頭。《哈利波特──死神的聖物》中的「聖物」(Hallows),其字源的意思是祝聖,因此當它與形容詞「死神的」牢牢結合在一起的時候,令人感到些許不安。它提醒我們,「神聖的」這個詞原初的意思包括祝福與詛咒。我們看到小說把幻想與現實對立起來,但也看到小說讓這兩個領域彼此融合。同樣地,小說堅持光明與黑暗的力量(無私的哈利與邪惡的佛地魔)存在著絕對衝突,但同時也讓這個對立一直遭受質疑。
我們可以從幾個地方看出這點。首先,具有好父親形象的人物,如鄧不利多,也有可能是壞父親。與《遠大前程》的馬格維奇一樣,鄧不利多為了拯救哈利而暗自謀畫;但是,想到馬格維奇為皮普擬定的計畫,不禁讓人懷疑,鄧不利多的計畫是否完全出於善意。鄧不利多是善的一方,但卻帶有瑕疵,而這使得原本單純的善惡對立變得趨於複雜。石內卜曖昧不明的行徑也是如此。此外,佛地魔不完全是哈利的敵人。他也是哈利象徵性的父親與醜惡的他我(alter ego)。哈利與佛地魔的爭鬥讓人聯想到《星際大戰》中路克‧天行者(Luke Skywalk )與達斯‧維達(Darth Vader)的衝突,而這兩個惡棍的名字開頭都是V。
的確,佛地魔並非哈利的親生父親,他們不像達斯‧維達與路克一樣是真正的父子;但佛地魔最重要的部分在哈利的體內,正如我們的父母把基因留在我們體內一樣。因此,為了消滅黑魔王,哈利也必須與自己戰鬥。真正的敵人總是來自於內心。哈利一方面憎恨這名野心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與他維持緊密關係,他的內心因此遭到撕裂。「我痛恨他可以進入我的內心,」哈利不滿地說。「但我會利用這一點。」哈利與佛地魔就某方面來說是同一個人。與許多精采絕倫的對決一樣,這兩個人是彼此的鏡中影像。但哈利利用自己也能進入這名惡棍內心的機會,削弱了對方的力量。
佛地魔呈現的父親形象是殘酷而壓迫的,相較之下,哈利的親生父母不僅給予哈利生命,也充滿感情。佛地魔的父親形象是禁制的法律或超我,對佛洛伊德來說,這股力量來自於內心,而非外在權威。佛洛伊德認為,父權形象的黑暗面連結著傷害與閹割的威脅。如果哈利額頭上的疤痕使他與佛地魔之間產生心靈感應,那麼我們的心中應該也帶著某種精神上的疤痕,使我們與類似的人產生類似的感應。佛地魔希望哈利成為自己的一部分,哈利因此必須在自己的內心進行一場光明與黑暗的鬥爭。事實上,整篇故事差一點就演變成一場悲劇。與許多救贖的人物一樣,哈利如果想挽救其他人的生命,他必須犧牲自己。哈利不死,就無法消滅佛地魔。然而孩子的故事傳統上都是喜劇,以免打發孩子上床時,孩子充滿創傷全身發抖,因此敘事用上了所有的魔法,終於讓哈利免於一死。小說的最後一句話正是所有喜劇最後說的:「一切都好。」
文學批評家還能從這些故事裡找到什麼?政治面向。一名法西斯主義菁英巫師仇視其他有麻瓜血統的巫師,因此與其他較為開明的巫師展開一場戰爭。這引發了幾個重要問題。一個人如何「與眾不同」而又不感到優越?少數人與菁英要如何區分?與大多數人區別開來(如巫師與麻瓜區別開來)的同時,如何還能與大多數人維持連帶感?在這裡,關於孩子與成人的關係存在著一個難以言喻的問題,巫師與麻瓜的關係正可用來諷喻這點。孩子代表一種難題,他們類似成人,卻不是成人。就像霍格華茲的居民一樣,他們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但仍與成人的領域有所交集。孩子要想受到重視,不被當成「異類」,他們與成人的差異就必須獲得承認。維多利亞時代的福音派(Evangelical)就犯了這樣的錯誤,他們把自己的子女視為任性而無可救藥。這種傾向也出現在現代的恐怖片裡。孩子有一些異於常人的性格總會讓人聯想到外星人或惡靈,如《E.T.外星人》(ET)與《大法師》(The Exorcist)。我們現在說孩子讓人毛骨悚然,猶如過去說孩子有罪(sinful)一樣。佛洛伊德會為一些既陌生又熟悉的事物取個古怪名字。然而,如果看到孩子的嘔吐物五顏六色便大驚小怪是錯誤的,那麼把孩子當成小一號的成人也同樣錯得離譜,偏偏以前的人就是這麼想的。童年這個詞是相當晚近的產物。(英國文學中真正出現兒童的概念,始於布萊克〔Blake〕與華茲華斯〔Wordsworth〕。)同樣地,種族之間的差異固然應該注意,但不是用來刻意強調,而忽略了種族之間的共通性其實遠超過彼此的差異性。
哈利‧波特小說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主要人物姓名的音節數。在英格蘭,上層階級要比工人階級更傾向於取長音節的名字。大量的音節意謂著另一種形式的富裕。如果有人名叫Fiona Fortescue-Arbuthnot-Smythe,那麼我們實在難以想像在利物浦的後街會有人大聲呼喊這樣的姓名,John Doyle倒很常見。妙麗‧格蘭傑(Hermione Granger)的名字在英國中上階級相當常見,她的姓原意是指大農莊(grange)。妙麗‧格蘭傑這個名字在小說的三位重要人物裡是最雅緻的,總計不少於六個音節。(有些美國人把Hermione這個字念成三個音節。)哈利‧波特(Harry Potter)是典型的中產階級主角,他的名字有四個整齊均衡的音節,既不過度也不侷促。至於工人階級出身的榮恩‧衛斯理(Ron Weasley)則只有少得可憐的三個音節。他的姓讓人想起黃鼠狼(weasel)這個字,意指狡猾與欺詐。黃鼠狼並非體格龐大的野獸,因此相當適合榮恩這種來自底層的角色。
我們還可以舉出許多跟佛地魔(Voldemort)一樣是V開頭,而且都具有負面含意 的字彙:惡棍(villain)、邪惡(vice)、禿鷹(vulture)、破壞者(vandal)、惡毒的(venomous)、邪惡的(vicious)、腐敗的(venal)、虛榮的(vain)、無味的(vapid)、謾罵的(vituperative)、空虛的(vacuous)、貪婪的(voracious)、吸血鬼(vampire)、劇毒的(virulent)、壞心眼的女人(vixen)、偷窺狂(voyeur)、嘔吐(vomit)、風險資本機家(venture capitalist)、暈眩(vertigo)、憤怒(vex)、粗俗的(vulgar)、卑鄙的(vile)、毒蛇(viper)、潑婦(virago)、暴力的(violent)、南非頑固的種族主義者(verkrampte)、報復的(vindictive)、害蟲(vermin)、復仇的(vengeful)、保安團員(vigilante)與(對熱心於傳統愛爾蘭音樂的人來說)凡‧莫里森(Van Morrison)。V這個符號帶有侮辱的意味與閹割的象徵。佛地魔,法文的意思是「逃離死亡」,但也有「小田鼠」(vole)的意思,同樣是體積嬌小的生物。或許也暗示著「墓穴」與「黴菌」。
有些文學批評者認為哈利‧波特小說不值一哂。在他們眼裡,哈利‧波特小說還不夠格稱為文學。然而談到好的文學與壞的文學,我們倒是可以把這部作品拿出來討論一番。
第二章
人物
要檢視劇作或小說的文學性,最常見的一種方式是把劇作或小說中的人物當成真實人物來看待。就某個意義來說,確實是如此,我們幾乎不可避免會這麼做。形容李爾王(Lear)的恃強凌弱、易怒與自欺,免不了讓人聯想到現代報紙報導的某個富豪鉅子。然而,李爾王與富豪鉅子的差異,在於前者只是印在紙上的黑字,至於後者,遺憾的是,他並非簡單的幾個記號。富豪鉅子在我們遇見他之前就已真實存在於這個世界,文學角色剛好相反。在戲上演之前,哈姆雷特(Hamlet)並非真實存在的大學生,即使戲是這麼告訴我們的。哈姆雷特其實根本不...
目錄
導讀
作者序
開頭
人物
敘事
詮釋
價值
導讀
作者序
開頭
人物
敘事
詮釋
價值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