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讀《清晨的人》(代序)
丁邦殿
隱地筆下的西元一九七五年,那是充滿焦躁且有希望的一年,政治的、文學的、藝術的,多采多姿的開展著。那也是文學的「爾雅出版社」誕生的一年︱一家小而美卻影響無數人的出版社。
「爾雅」出版的第一本書是王鼎鈞的《開放的人生》。套用隱地的話,「是一本使我們成長的書,也是一本給我們智慧的書。」我不但自己閱讀也曾經推薦給學生,想來他們也一定會介紹給子女,那是一本影響深遠的書,許多人的生命從此不同。第二本書是琦君的《三更有夢書當枕》,如今它還是我案頭書堆中的一本,當心情低落時,當對人性失去信心時,我能從中找出一些美好,有一股暖流撫慰心頭。
今年適逢爾雅四十周年,四十年來它出版了八百種文學叢書,秉持著興趣理想與信念,在文學的花園中勤耕不輟。可是大環境的變遷,人們早已遠離書本,每天在手機上滑來滑去,寫著沒有營養的短句,點送著各式的貼圖,只有浮光掠影,細細想來當真蒼白無味,再也沒有往昔書中雋永低迴的文句,也缺乏苦澀中的甜美,哀愁中的美麗了。難怪隱地感嘆「只有演戲的人,已經沒有看戲的人」。
許多的作家,許多的作品,一一的在《清晨的人》︱「爾雅四十周年回顧散章」裡出現,那些我們曾經仰望的作家,親切的出現在我們眼前,那些讀過的或者失之交臂的作品,重新被提起被介紹,一切都鮮活過來,許多文學花園中的參天巨木,似錦繁花,讓人心生嚮往,好像聽故事一樣,嘆息一千零一夜太短了,還不停的在心中問著:然後呢?然後呢?
已經深夜一點多,爾雅的故事來到一九八五年,十年間「爾雅」出版了兩百多本書,好書不厭百回讀,多麼燦爛輝煌的十年!時間從不為誰停留,而一心投入文學出版的「爾雅」,除了個別作家的作品,也盡心在「年度短篇小說選」、「年度詩選」、「年度文學批評選」,為現代文學留下精采的紀錄。
四十年來,「爾雅」八百種書,和新詩有關的書竟有一百三十五種之多,這是怎樣的一位出版家,竟有如此勇氣,出版擺明難銷的詩集。原來是因為「人生無詩會無趣」,更神奇的是,後來連出版社老闆自己都跳進去成了詩人,五十六歲才寫詩的出版人,一樣可以大放異彩。詩人說「詩是大地上的花樹。詩是日月之光。大自然的風雪雨露,都是詩。」詩人說「任何人只要肯走進詩裡去,都會採到鮮花和陽光。」所以當「人人都有困境」的年代,隱地又丟出一本詩評集《讀一首詩吧!》。
夜裡兩點多了,「爾雅」也邁入一九九五年,社會氛圍一團混亂的一年,幸好還有一本本的好書伴我們度過長夜漫漫,「在有限的生命裡,種一棵無限的文學樹。」外在的環境再喧囂,書中自有一片靜謐的天地;外在環境再污濁,書中自有一方清淨的所在。
看看時鐘三點十五分,《清晨的人》︱「爾雅四十周年回顧散章」,也進入成立三十周年的二 五年。儘管這一年地球失控,氣象反常,但是過去的十年間,還是有許多有使命感的作家。出版家繼續努力著,寫好書、出版好書,挽救著苦惱困惑的靈魂,寫人生的悲喜,訴說生命的故事,不斷地送著禮物給苦難的人類(隱地原句是「文學藝術是老天送給苦難人類最好的禮物」)。
天快亮了,現在是二 一五年八月,我正讀著隱地《清晨的人》︱「爾雅四十周年回顧散章」的最後幾頁,臺大博士生李令儀和隱地對談「文學興旺」的年代;徐開塵訪隱地,說「爾雅五書」的故事,還有書後附了無數爾雅叢書的封面書影,往事歷歷,是一本寫不完的書。書中更強調「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余秋雨「文化苦旅」及圖文版「新文化苦旅」六冊都是值得一讀再讀的好書。
掩卷沉思,那些我讀過的,還有正準備讀的,曾經豐富了我的人生,也將繼續增添靈魂的厚度。對於想要出版「全家人愛讀的書」的編者,一位作家,一位詩人,一位「生命中每一天的清晨永遠是清醒的」出版家,四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執著,是最值得尊敬的人。掌聲,要的;喝采,要的;更重要的是作為讀者的我們不要忘記,要永遠支持讀好書,買好書,贈人以好書。
終於,我也成了一位清晨時「還清醒著的人」。
關於作者
丁邦殿,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為臺北市立松山高商退休教師。曾任教臺北市永春國中、成德國中。現為爾雅書房讀書會生活寫作班學員。愛好旅行、閱讀。
和二 一五年說再見(後記之後的後記)
二○一○年曾是我的豐收年,一年裡居然出版了三種書︱《朋友都還在嗎?》、《讀一首詩吧!》和詩集《風雲舞山》,隔了五年,沒想到自己再一次豐收,今年我也出版了三種書︱《清晨的人》、《隱地看電影》和《深夜的人》。
這三種書,讓我年初到年尾,比二○○二和二○一二那兩年天天要寫日記的日子還忙。
忙,讓日子過得更快,幾乎上午才到辦公室,怎麼就到了下午下班時間,而清晨才醒,怎麼又到了深夜必須上床,日子和日子排著隊,二○一五年又要和我說再見了!
二○一三年是我生命中特殊的一年,先是因靜脈血管阻塞,引起眼睛玻璃體出血,接著牙病登場,又因一生都在「寫字」,得了職業病,於是拉筋整骨推拿……一整年都在進出中西診所和各大醫院,後來情況稍有改善,到了年底,寫了一本《生命中特殊的一年》,在那本書裡我也提到了透過讀汪其楣在《文訊》上的一篇文章,我認識了寫《繁花不落》的藍明姊︱當年正聲電台「夜深沉」的節目主持人,於是我們開始通信,當年一個守在收音機旁聽藍明說話的高中生,想不到超越時空,隔了五、六十年通起信來,生命確有奇蹟,我們成為年紀最大的筆友,最奇特的是,我保留學生時代到南海路參觀美新處的一張照片,照片裡西裝筆挺結著領花的帥哥副處長,竟然就是藍明姊的老公司馬笑先生。
二○一四年是我們通信最勤的一年,但二○一五年,因我日以繼夜不停地寫,以致於未能每封信都回,還好藍姊能諒解,但我心裡還是過意不去。
非但如此,許多老長官、老朋友、老同學我都忽略了,寫作讓我忘了禮數,還有,讀者的信,以往也總設法回覆,如今年紀大了真的沒有力氣,只能說力不從心。
現在,我身上尚餘的一些力氣,都給了寫作。看來我已經中了寫作的毒,戒不掉,而我,也不想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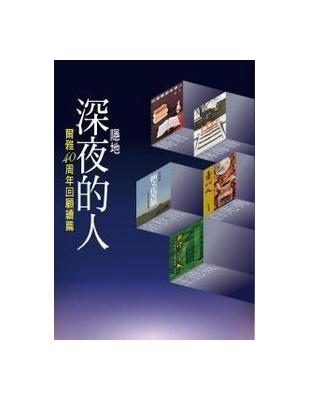


 收藏
收藏

 二手徵求有驚喜
二手徵求有驚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