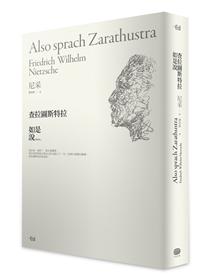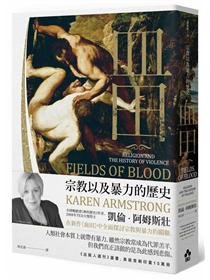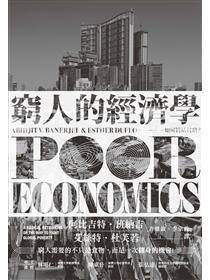因為卡爾‧馬克思,人類歷史變得不一樣!《資本論》從寫作到誕生的歷史,反映了世界文明的進程與發展。
一位巨人,一套思想,一部改變人類歷史的鉅著
共產主義的幽靈,自此從歐洲遊蕩到全世界各地
了解馬克思、《資本論》,改變看待世界的方法本書由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萬毓澤審訂
1844年8月,正值23歲的恩格斯來到了馬克思在巴黎的公寓。他們是如此完美地互補:馬克思有知識上的財富,而恩格斯有關於財富的知識。在毫無抱怨或嫉妒之下,恩格斯接受了自己的使命:在經濟與思想上支持馬克思的寫作。「我完全不了解」,他寫道,「誰能妒忌天才呢?天才如此特別,我們這些沒有天分的人最初即明瞭,這是我們達不到的。只有心思狹窄的人才會妒忌天才。」
馬克思是19世紀大思想家中,最受磨難的巨人之一,因而在接近他的傑作之前,我們有必要事先尋找其困厄與靈感的諸多來源。在《遊蕩世界的幽靈:馬克思,《資本論》的誕生》中,法蘭西斯‧昆恩細緻鮮明地描述了馬克思為了完成《資本論》所經歷的奮鬥過程,並淺顯易懂地闡釋這部鉅著的內容、影響以及為人類文明灌注的精神價值。
資產階級的衰落與無產階級的勝利尚未實現。從誤讀、勿讀到務必要讀,《資本論》對於支配人類生命的那些力量及由此而生的不穩定、異化與剝削的生動描繪,將永遠不會失去共鳴,也不會失去將世界置於其焦點之下的能力。馬克思從未被歷史埋葬,他依然可以成為21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
作者簡介:
法蘭西斯‧昆恩(Francis Wheen)
生於1957年1月22日,畢業於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英國記者、作家和廣播員,曾為《獨立報》、《鏡報》、《新社會主義》等知名刊物撰寫過文章,現在執筆《衛報》「昆恩世界」定期專欄,並曾被評選為年度專欄作家。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孕育
一八四四年八月,正當燕妮去特利爾探望母親的時候,正值二十三歲的恩格斯來到了馬克思在巴黎的公寓。他們之前曾經在《萊茵報》的辦公室有過短暫的會面,之後不久,馬克思對恩格斯提交《德法年鑑》的一篇文章〈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產生極深的印象。其中的原因很明顯:雖然他現在已相信社會與經濟的力量是驅動歷史的主因,然而他對於資本主義還沒有實際的知識。在這方面,恩格斯正好可以指導他,他是一個在曼徹斯特(Manchester)擁有工廠的德國棉花製造商的兒子與繼承人。曼徹斯特位於工業革命的心臟地帶、同時也是「反穀物法聯盟」(Anti- Corn Law League)的創始之處。在這個城市裡,充滿各式各樣的憲章運動活動者(Chartists)、歐文主義者(Owenists)和社會主義的活躍分子。恩格斯在一八四二年秋天搬到蘭開夏(Lancashire),表面上,是要熟悉家族事業,但實際的目的卻是觀察維多利亞時代的資本主義對人類的影響。白天,他是一個棉花交易所的勤奮經理;幾個小時後,他便改變位置,開始探索發掘這個城市的無產階級街區以及貧民窟,為他早期一部經典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1845)搜集材料。
雖然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巴黎一起度過了十天,但是所有有關那一次盛大會面的交談內容,僅僅記載於四十年後恩格斯的一句話:「一八四四年夏天,我在巴黎拜訪馬克思時,我們在所有理論領域的意見都完全一致,從此就開始了我們共同的工作。」他們是如此完美地互補:馬克思有知識上的財富,而恩格斯有關於財富的知識。馬克思寫得很慢,也很痛苦,往往伴隨著數不清的修改塗抹痕跡;恩格斯的手稿卻條理清楚、優雅明淨。馬克思的一生大多處於混亂與貧困;恩格斯卻一輩子擁有全職工作,還持續產出豐富的著作、書信和報章文字,甚至還有閒暇享受資產階級上流生活的樂趣,在馬廄飼養馬匹,在地窖藏有紅酒。然而,儘管他表面上占有優勢,從一開始他就知道自己不會是主導的一方。在毫無抱怨或嫉妒之下,他接受了自己的使命:在經濟與思想上支持馬克思的寫作。「我完全不了解」,他寫道,「誰能妒忌天才呢?天才如此特別,我們這些沒有天分的人最初即明瞭,這是我們達不到的。只有心思狹窄的人才會妒忌天才。」
他們之間沒有祕密,也沒有禁忌:他們的通信尖刻地混雜了歷史與八卦、晦澀的經濟學和小男生的玩笑。對馬克思來說,恩格斯代理著一種類似母親的角色──寄給他零用錢,擔憂他的健康,並且不斷警告他不要忘記做功課。最早留存下來的信件是從一八四四年十月開始的,恩格斯催促馬克思趕緊把政治學和經濟學的筆記整理成書:「快把你收集的資料公諸於世,你早該這麼做了!」三個月後,他更耐不住性子:「你還是先試著完成政治經濟學書籍好了,就算你有不滿意的地方,不要緊!人民已經成熟了,我們要打鐵趁熱……所以請嘗試在四月前寫完。要像我這樣,給自己設定一個時限,告訴自己在這個時限內一定要完成。」然而這卻是一直無法實現的希望:直到二十年後,《資本論》第一卷才付印。
事實上,恩格斯也並不是全然無可指責。就在他與馬克思的巴黎會面不久後,他便提議馬克思一起合寫一本不超過四十頁的小冊子,來批評那些更激越的青年黑格爾派。幾天後,當恩格斯完成他自己的那二十頁後,他「一點都不驚訝」馬克思在幾個月後,已把它膨脹至三百頁。馬克思是那種無法抗拒干擾的作家,比起無聲地為那本鉅著付出晦暗苦功──當時暫定的題目是《政治學與國民經濟學批判》(Kritik der Politik und Nationalökonomie)──他更喜歡在小冊子和單篇文章中獲得立即的滿足。儘管他已答應要在一八四五年夏季結束前,將這本經濟學著作的手稿交給德國出版商列斯凱(Karl Leske),但他寫完目錄就把它丟在一邊了。「我認為在發表正面的立論之前,先發表一部反對至今所有德國哲學與德國社會主義的論戰性文章,是很重要的」,他向列斯凱解釋:「這是為了使讀者對我的經濟學觀點有所準備,我的觀點在根本上是與德國迄今為止的學術思想對立的……如有必要,我可以提供從德國、法國寄來的許多信件,向您證明讀者們正迫切期待這部著作的出版。」類似的故事不僅於此:一直到一九三二年,上文說的這本論戰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Die Deutsche Ideologie)才找到出版商。馬克思寫道:「既然我們已經達成了我們的目的──澄清自己的問題,我們就讓原稿留給老鼠的牙齒去批判了。」
然而他依舊無法、或不願意全神貫注在他這本經濟學著作,接下來的幾年又出現更多論爭上的干擾:《哲學的貧困》(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是一部百餘頁的著作,主要是為了批評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流亡中的大人物》(Die großen Männer des Exils)是一部冗長的尖刻之作,主要是為了嘲諷流亡的社會主義者當中一些「更值得注意的蠢貨」以及「民主黨飯桶」;《十八世紀外交史內幕》(The Secret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是一部反俄的長篇大論;而在《帕麥斯頓勛爵》(The Story of the Life of Lord Palmerston)中,他試圖證明一名英國外交大臣是俄國沙皇的特務;另外,《福格特先生》(Herr Vogt)則猛烈抨擊一位波恩大學自然科學教授,後者因為將馬克思稱為騙子、譏諷他白吃白喝而激怒了馬克思。「以牙還牙,報復讓世界運轉。」他喜孜孜地哼唱著,儘管他已花了一年中大好時間與福格特鬥爭。
國內局勢的持續動盪也進一步阻礙他的工作進度。一八四五年一月,普魯士駐巴黎公使為了一篇文章向國王路易腓力提出抗議,馬克思在文中奚落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於是法國內政部長立即關閉了這份雜誌,並下令把作者驅逐出境。歐洲大陸僅剩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一世(Leopold I)還願意接納馬克思,條件是他得提出不會再發表「任何有關政治局勢」文章的書面聲明。馬克思認為這並不妨礙他參與政治,於是他請求恩格斯到布魯塞爾與他會合,在那兒,他們成立了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Communist Correspondence Committee)以保持與西歐社會主義團體的「持續來往」,到了一八四七年,這個委員會轉變為倫敦新成立的共產主義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的一個分支,這個同盟邀請馬克思起草一份宣言。後來馬克思交給他們的就是《共產黨宣言》,可以說是歷史上讀者最多也最有影響力的小冊子。
一八四八年最初幾個星期,當馬克思正在寫《共產黨宣言》時,他認為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Bourgeois capitalism)已完成其使命,即將被自身的矛盾埋葬。現代工業把孤立的工人趕到工廠,已經創造了條件,讓無產階級能夠團結為一股無可抗拒的力量。「因此,資產階級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由於他認為他是在排練一幕喪禮,所以他對失敗的敵人表現得雍容大度。有評論者曾經將這個宣言描述為「對於資產階級的一場抒情詩慶典」,第一次讀它的人可能會被馬克思給予對手如此慷慨華麗的溢美之辭感到驚訝:
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係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於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別的任何聯繫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的神聖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交換價值……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係,從而對全部社會關係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
他將在《資本論》中更深刻與複雜地回應這個主題,不過現在沒有時間詳述。在《共產黨宣言》開頭第一句話(「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及其同樣著名的結尾(「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證明了這是一篇鼓動文章。雖然是一篇在起義發生前匆匆寫就的文稿,但其中卻蘊含著無比才智。
一個令人欣喜的巧合的是,一八四八年二月,就在這本小冊出版的當週,革命真的爆發了。革命以燎原之勢橫掃歐洲大陸。隨著路易腓力的退位以及法蘭西共和國宣告成立,驚慌失措的比利時政府命令馬克思在二十四小時之內離境,永遠不許再回來。幸運的是,他剛剛接到巴黎臨時政府的邀請:「正直忠實的馬克思先生……暴政使你流放,如今自由的法國打開大門,迎接你以及那些所有獻身於神聖事業、為博愛奮鬥的人們。」然而他在巴黎僅僅待了一個月就旋即轉往科隆,希望能夠擴大在德國的革命。他選擇的武器仍然是文字:他創辦了一份新的日報──《新萊茵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這份報刊在短暫的生命中,不斷遭到官方的騷擾。七月時,他因「侮辱、毀謗檢察總長」而遭法官傳訊;九月頒布戒嚴令之後,科隆的軍事首長下令報社停刊一個月;次年二月,在任何革命的可能性消失殆盡之後,他被以「煽惑叛亂」的罪名起訴,但是他在法庭上的精彩演說卻說服了法官,使他獲判無罪。然而,最後在一八四九年五月,普魯士當局還是起訴了報社的半數成員,並建議將另一半成員驅逐出境,包括已喪失公民權的馬克思。
他在一八四九年六月回到巴黎,回去後卻發現,全城正處於霍亂流行病以及保皇黨人士的掌握之中。政府下令將他驅逐到位於布列塔尼(Brittany)的莫比昂(Morbihan),這個地區正有瘧疾肆虐,於是他前往歐洲唯一仍然願意收留流亡革命分子的國家避難。一八四九年八月二十七日,馬克思乘船赴英國,從此一直留在那裡,直到一八八三年過世為止。「你必須快點來倫敦一趟」,他寫信給當時正在瑞士遊覽的恩格斯:「我們在倫敦有事要忙了。」
第一章 孕育
一八四四年八月,正當燕妮去特利爾探望母親的時候,正值二十三歲的恩格斯來到了馬克思在巴黎的公寓。他們之前曾經在《萊茵報》的辦公室有過短暫的會面,之後不久,馬克思對恩格斯提交《德法年鑑》的一篇文章〈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產生極深的印象。其中的原因很明顯:雖然他現在已相信社會與經濟的力量是驅動歷史的主因,然而他對於資本主義還沒有實際的知識。在這方面,恩格斯正好可以指導他,他是一個在曼徹斯特(Manchester)擁有工廠的德國棉花製造商的兒子與繼承人。...
作者序
一八六七年二月,就在《資本論》(Das Kapital)第一卷付印前,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勸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讀讀巴爾札克的〈無名的傑作〉(The Unknown Masterpiece)。他說,這個故事本身就是短篇傑作,「充滿許多值得玩味的諷刺。」
我們不知道恩格斯是否聽取了他的建議。如果他讀過這篇小說,他肯定會注意到其中的諷喻,然而,他也可能會訝異於他老友從中體會到的樂趣。〈無名的傑作〉寫的是弗亨霍夫(Frenhofer)的故事,他是一位偉大的畫家,耗費了十年時間一而再,再而三地創作一幅肖像畫。藉由提供「對現實最完美的表現」,他要為藝術帶來根本性的革命。最終,當他允諾藝術家朋友普桑(Poussin)和波伯斯(Porbus)登門鑑定他那最終完成的油畫作品時,他們大驚失色。這兩人見到大量汙漬點點的形狀與顏色任意堆疊在一塊,簡直是一團混亂。「啊!」弗亨霍夫誤解了他倆的詫異之情,大聲說道:「你們從來沒想過會有如此完美的作品吧!」但後來,這位畫家不經意地聽到普桑告訴波伯斯,說他最後一定會發現真相的──那幅畫被反覆描繪了太多次,以至於什麼也沒留下。
根據馬克思的女婿保羅‧拉法格(Paul Lafargue)所言,巴爾札克的小說「讓馬克思留下極深的印象,因為在某種程度上,這正是他的心情寫照。」多年來,馬克思孜孜矻矻地專注於他那尚未面世的傑作。在冗長的構思期間,有些人要求一睹他那未竟的作品,對於這些人,他習慣性的回答就和弗亨霍夫相同:「不,不!我還得修飾幾筆,昨晚我以為完成了……沒想到今早攤在日光下,我才發覺我錯了。」早在一八四六年,當這本書已延遲許久,超過預定出版日時,馬克思寫信給他的德國出版商說道:「在我沒有重新修改內容與文字風格以前,我是不會交寄付印的。一個筆耕不輟的作家不可以把他六個月以前寫的東西原封不動地在六個月後拿去出版,這是毋庸置疑。」十二年後,這部著作仍未告成,他解釋:「進展實在很慢。我多年研究的某些題材對象,一旦最終想處置它們,往往又出現若干新的面向,於是需要進一步仔細思量。」身為固執的完美主義者,他永遠都在為調色板尋找新的色彩──研究數學、學習天體運行、為了能夠研讀俄國土地制度的書籍而自學俄語,或者,不如再次引述弗亨霍夫的話:「哎呀!曾經有那麼一會兒我以為作品已經完成了;但我肯定在某些細節上出錯了。在我清除疑慮以前,心思無法獲得平靜。為了將我的畫作與不同形式的自然進行比較,我決定要去旅行,要去見識見識土耳其、希臘、亞洲,尋找新的典範。」
為什麼當馬克思準備將其著作公諸於世前會想起巴爾札克的小說呢?難道他害怕自己也徒勞無功?擔心他「對現實最完美的表現」最終被證明為一部晦澀難懂的作品?毫無疑問地,他的確有過這種憂慮──馬克思的個性是一種奇怪的混合物,既極度自信,又往往痛苦地自我懷疑──他試著透過前言的警語事先防止那些針對他的批評:「當然,我指的是那些想學到一些新東西、因而願意自己思考的讀者。」不過,當他將自己等同於無名傑作的創作者時,最強烈打動我們的應該是:弗亨霍夫是一位藝術家──不是政治經濟學家,不是哲學家或歷史學家,也不是擅辯之人。
一八六七年二月,就在《資本論》(Das Kapital)第一卷付印前,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勸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讀讀巴爾札克的〈無名的傑作〉(The Unknown Masterpiece)。他說,這個故事本身就是短篇傑作,「充滿許多值得玩味的諷刺。」
我們不知道恩格斯是否聽取了他的建議。如果他讀過這篇小說,他肯定會注意到其中的諷喻,然而,他也可能會訝異於他老友從中體會到的樂趣。〈無名的傑作〉寫的是弗亨霍夫(Frenhofer)的故事,他是一位偉大的畫家,耗費了十年時間一而再,再而三地創作一幅肖像畫。藉由提供「對現實...
目錄
導論 無名的傑作
第一章 孕育
第二章 誕生
第三章 來世
導論 無名的傑作
第一章 孕育
第二章 誕生
第三章 來世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5收藏
15收藏

 56二手徵求有驚喜
56二手徵求有驚喜




 15收藏
15收藏

 56二手徵求有驚喜
56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