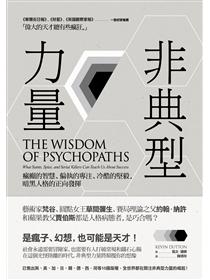毛澤東一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於是,應該繼續讀書的革命小將黃雙林帶著淳樸的政治理想、激情與希望,豪情滿懷地惜別家人、道別初戀、告別城市,跟著二千萬同伴大規模地「上山下鄉」革命去了。然而,進入農村後,匱乏的食物、費力的勞動、一場又一場的批判,偷偷摸摸的情愛,是否將一點一滴磨光知青的熱情與憧憬、精神與肉體……
「往事記憶三部曲」書寫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位武漢工人村出身的底層階級在中學時期,從成為紅衛兵到身陷上山下鄉的知青時代,最後招回武漢成為鋼鐵工人,以底層人民的故事拼湊文革十年的風雲詭譎。
本書特色
這世上最凶險的就是惡,沒有什麼能贏得了惡的
揭開文革時期知青上山下鄉的荒誕面紗
濃郁自傳色彩──「往事記憶三部曲」之二
作者簡介:
王繼
雖是生在湖北、長在湖北,因養父是東北人,在戶口簿上、居民身分證上,祖籍至今仍是東北。前三十多年一直生活在武漢,後遷居重慶,在重慶生活也已近三十年了。蹉跎中,年近古稀。
上世紀六○年代末,作為知青,下放到鄂西南的高山裡,做過幾年農民;七○年代初,招工到武漢鋼鐵公司煉鐵廠做了八年鋼鐵工人;雖是初中畢業,學生時代卻基本沒讀過書。或許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八○年末,考入武漢大學作家班,算是正兒八經讀了兩年書。
上世紀七、八○年代出版發表長篇中篇短篇小說若干,按字數計應在百萬以上。但羞於提到這些小說,因很大一部分是爲改變工人身分、為「稻梁謀」的利益之作。雖然其中也有可一讀的《我就是第三者——也是愛情的故事》(長篇小說)和《六個古怪的世界》(中篇小說)。
停筆二十幾年後,二○一七年,台灣南方家園出版社出版了長篇小說《八月欲望》,才覺得終於掙脫了利益、心靈的羈絆,寫出了一部令自己比較滿意、也不會受良心良知折磨的長篇小說。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王繼先生新著長篇《六月悲風》,是消失多年的知青文學的一次轉世暴動。這一曾經橫行八〇年代中國的文學流派,已爲世人遺忘許久。知青的凋零乃至知青文學的沉寂,都是眼前這個時代對歷史的遮蔽。當一代人的悲哀轉而又成爲某些人所謂青春無悔的頌歌時,當新的上山下鄉陰謀又在鼓吹時,我們是該來看看這部書了。這些事關我家鄉的記憶,這些我能旁證的往事,也許是這個日漸瘋狂時代的一針清醒劑……
─作家 野夫
王繼的小說有一個了不起的特質:每一個人物都充滿馬奎斯般的鮮活生命力。他們穿草鞋、餓肚子、做春夢、相信口號和理想、改天換地、不知畏懼,直到最後的悲劇來臨。他筆下的鄉村充滿野趣,崇拜陽具,萬物共生,卻被狂熱的政治摧動而扭曲變形。所有的夢想與青春就像那一根山中巨大的陽具,在大爆炸聲中,將所有的夢與希望一起埋葬!
王繼為一個逝去的時代,劃下不可忘卻的容顏。
─作家 楊渡
我認爲王繼的《六月悲風》對人物設計時所體現的「道德節制」,是我所欣賞的。雖然他意在展示他所生存的那個時代的殘酷,卻沒有讓譴責泛濫到不可收拾,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作家 冉雲飛
《六月悲風》在這裡顯示出它切入歷史的巧妙。我認為作者在構思作品的時候,是設定了一個有效的邊界的,不論是出於小說的敘述的需要,還是在於他對歷史的理解,他都讓他的人物簡單起來,事件也簡單起來,讓迷霧重重、渾然囫圇的歷史只呈現出具體可感或最為醒目的部分。
─文學評論家 唐雲
名人推薦:王繼先生新著長篇《六月悲風》,是消失多年的知青文學的一次轉世暴動。這一曾經橫行八〇年代中國的文學流派,已爲世人遺忘許久。知青的凋零乃至知青文學的沉寂,都是眼前這個時代對歷史的遮蔽。當一代人的悲哀轉而又成爲某些人所謂青春無悔的頌歌時,當新的上山下鄉陰謀又在鼓吹時,我們是該來看看這部書了。這些事關我家鄉的記憶,這些我能旁證的往事,也許是這個日漸瘋狂時代的一針清醒劑……
─作家 野夫
王繼的小說有一個了不起的特質:每一個人物都充滿馬奎斯般的鮮活生命力。他們穿草鞋、餓肚子、做春夢、相信口號和理想...
章節試閱
1
二○○○年初秋的一個上午,站在穿過高董子的機耕道上,望著周圍亂石如林,特別那已被碎石淹沒了大半截的印子石,我思緒萬端,心情有些沉重。一九八五年夏天我第一次訪舊回擔擔坪時,還沒有這條機耕道,和我一九六九年一月插隊落戶到擔擔坪當知青時一樣,要從金峒司爬山越嶺幾十裡,才能到達擔擔坪。有了這條連接省道的機耕道,從金峒司開車上擔擔坪,似乎也就是一、二十分鐘的事,但是,如果我知道這條機耕道要穿越高董子抵達擔擔坪,我情願把車停在金峒司,步行去擔擔坪……陪我同來的利川縣文化局的民俗專家老譚也下了越野車,他問我,這裡就是高董子?我點頭。他環望周圍黑鴉鴉連綿不絕的大山,又望望亂石聳立的高董子,笑著問我:「曉得那條雞冠蛇變成了龍沒有?」我跟老譚說過高董子的雞冠蛇想變成龍的故事。我搖搖頭,表示不知道。老譚俯身從路邊拾起一竹鞭(竹子生於地之下的橫莖),遙指峰巒疊嶂黑黝黝的大山,又指指身邊的高董子和我,像表演舞臺劇似的,很高聲、很誇張地對我說:「雙林,你是從這重重大山裡走出去的作家喲?不容易!真不容易喲。」老譚唏噓感嘆著。金剛坡那面扇形的絕壁消失後,從金剛坡至高董子,形成了一個亂石鋪就的約七八十度的斜坡。老譚的話音剛落,那面斜坡上邊就突然傳來了喊聲:「底下是雙林麼?底下是黃雙林麼?!」這陡然響起在亂石和寂寥大山裡的喊聲,嚇了我和老譚一跳,雖然這聲音嘶啞蒼老,但我仍聽出這是花妹,這是崔宗益在呼喚我,我有些激動,立即衝坡上也大聲呼喊:「是我,是我呀,我是黃雙林。上頭是花妹麼?」上頭馬上回答道:「是我,是我,硬是我嘛。」隨著呼喊聲,只見一人頭纏青帕,足蹬草鞋,手持柴刀,三步並作兩步,從亂石荒草中衝了下來,衝到我們面前「呼呼」地喘著粗氣……
花妹對知青、也就是對我們插隊落戶到擔擔坪,感到很稀奇,總覺得這裡面有個天的祕密。他問過我很多次:「你們那個廊場,沒得我們這個廊場好?」擔擔坪不通電不通汽車……從工業文明程度上講,擔擔坪根本無法與城市比。我說,「不是。」花妹又問:「你們那個廊場吃不飽飯?」城裡人有購糧本,糧食有定量,起碼餓不死。我回答說:「也不是。是毛主席指示我們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花妹更惶惑。他說,「我弟娃上個學也只走幾里路,就是到金峒司上中學也只走二三十里路嘛。你們啷個(註:「為什麼」之意)要跑這(註:讀嫩)麼遠來受教育呢?」花妹把我問得理屈詞窮。
在擔擔坪,最先和我們成為朋友的是花妹,江薇薇和龔曉萍住的就是他家的廂房,龔大平住在覃德清老漢的一間廂房裡,而我和韓三住在覃德清老漢那隔成兩間的吊腳樓上。花妹右臉頰上那道竪著的灼痕,窄窄的淺淺的紅紅的,像一朵艶山紅花的淺浮雕。花妹的父親已過世,他才十八歲,儼然就一家之主了,兩個小他兩三歲的弟弟見了他,如同他們家養的那條趕山狗一樣,搖頭晃尾,顯得十分服帖;就連他堂叔貧協組長崔廣安的大兒子、二兒子也一天窩在花妹家裡。花妹他媽給我印像最深的是她手中那近兩米長的旱菸桿,她遠遠坐著,嘴裡含著銅菸嘴,銅菸袋鍋卻伸到火坑裡就著炭火點菸。磕掉菸鍋巴,重新裝菸葉時,宛如漁夫釣到魚收攏釣竿,把菸桿一寸寸地扯回去。我們跟花妹親近,還因他要學我們一樣生活。我們早起要站在屋沿上刷牙,把漱口水吐到院壩裡。花妹買不起牙刷牙膏(或捨不得買),就用筷子醮上鹽在牙上搓一搓,把鹽口水也吐到院壩裡。這讓我們那種城裡人的優越感,會不知不覺流露了出來。不過,覃老漢很看不起花妹的做派,花妹用筷子刷牙時,他問花妹:「你在掏蛆呀?」他捎帶著把我們也駡了。
過了陰曆正月十五,我們好像才進入了正常的生活。所謂正常的生活,就是我們知青自己開火做飯了。一九六九年的冬天特別冷,幾場大雪飄落下來,覆蓋了連綿不絕的大山,皚皚白雪讓嵯峨雄壯的大山失去了稜角,突然變得圓潤變得細膩婉約了;山林中連鳥兒也不叫,天地間靜悄悄的,只有屋外的竹林裡的竹子常被冰雪墜壓得「吱嘎吱嘎」響,偶爾,也有冰凌從大樹的樹丫上落下,傳出幾聲悶悶的如放屁一樣的聲音。大山的空寂,更讓我們幾個知青覺得清寒陰冷逼人。我和韓三除了吃飯解溲,基本就偎在被子裡捱時光。當花妹邀我們到他家火坑烤火時,我和韓三一骨碌就從被子裡爬了出來。花妹一直不能明白,我們這些人為什麼要從大城市到大山裡來,無論怎樣解釋,都不能使他滿意,似乎他總覺得這裡邊一定有個天大的祕密。他親近我們,或許為了探究我們自己也無法明白的祕密吧。這時,我並不知道,在這隆冬的農閑時節,當我和韓三整日還偎在被窩裡的時候,魏文武已走遍了擔擔坪的山山水水。後來有人告訴我,只穿了幾天草鞋的魏文武的腳上,皸裂出許多大大小小的口子,有些還滲著血,他仍然堅持穿草鞋。那人不無讚嘆地說:「這是個狠角色。」
我們居住的這幢「∏」型木屋裡,那一橫槓的堂屋和屋外的院壩,應是公共區域。院壩裡雜亂地堆放著各家的柴垛,而堂屋裡最顯眼的,除了正面板壁上張貼的毛主席畫像和大紅「忠」外,就是擺放在堂屋側面的覃老漢那具柏木棺材了。我們誰都沒有想到,這個院子向毛主席畫像早請示、晚彙報的儀式,會因覃德清老漢這具棺材而消解。大山裡的冬日早晨,寒氣逼人,哈口氣猶如從嘴裡飛出了一團白雲,但我們不得不爬起來對著毛主席畫像和大紅「忠」字三鞠躬,祝他老人家萬壽無疆。實際上並沒有人強迫我們這樣做,但人人都開始這麼做的時候,似乎就演變成了一種必須和責任。我和韓三掙扎著起了床,口不漱臉不洗,匆匆忙忙早請示後,又匆匆忙忙鑽進被子裡睡回籠覺。只要我和韓三一站在毛主席畫像前,不出一分鐘,江薇薇必定站在了我們身邊。早請示、晚彙報不是必須的集體活動,可以單獨進行,比我們起得早的江薇薇沒必要等我們。當她早請示,特別是天將黑時的晚彙報,她緊緊依靠著我或韓三,游移而驚恐的目光,卻不由自主瞅向那具被生漆刷得黑亮黑亮的柏木棺材時,我知道她等我們是因害怕這具棺材,不敢單獨面對這具棺材。這是覃德清老漢為自己準備的棺材,他稱之為壽材。覃德清老漢孤獨一身,是隊裡的五保戶,我和韓三住的吊腳樓,龔大平住的那間小屋,就是他騰給我們的,而吊腳樓下那頭被他喚為黑娃子的大水牛,就歸他飼養。他的全部生活內容好像只有兩件事,餵養黑娃子和擦拭他的壽材。在覃老漢精心擦拭下,即使在暗夜中,那棺木偶爾也會跳躍出幾縷光亮。面對黑沉沉的棺材,別說江薇薇,我也時有畏懼。
黑棺材在覃德清老漢心裡是歸宿,在江薇薇眼裡就是死亡。誰不畏懼死亡?終於,無法容忍的江薇薇直接找覃老漢交涉,請他把棺材移走,覃老漢不肯移走,說沒得地方移。一怒之下,江薇薇就給覃老漢扣帽子,說他的棺材放在堂屋裡,既影響了早請示、晚彙報,也是極不尊重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敬愛的毛主席。覃老漢被江薇薇一番話噎得只翻白眼,嘴脣哆嗦著說不出一句話來,他返身「撲通」一下,跪倒在毛主席畫像前,他這一跪,好像就會說話,也有話說了。他帶著哭聲說道:「毛主席,我先向您老人家請罪,再祝您老人家萬壽無疆!毛主席呀,我們這些小民總歸是要死的嘛,死了嘛,總歸要入土嘛,入土嘛總不能沒得棺木嘛,有個棺木嘛,總得有個地方擱嘛……」覃老漢跪著,時而仰頭面對毛主席畫像、時而垂頭朝下絮絮叨叨地說著,他那撮花白的山羊鬍子,生硬倔強地戳在他尖瘦的下巴頦上。而此時,江薇薇卻早已被覃老漢富有邏輯色彩、因果關係的話氣走了。這天,江薇薇沒晚彙報,第二天早晨她也沒去早請示,第二、三天也如是。懈怠也是具有傳染性的,先是我和韓三,再是龔氏兄妹……後來,這院裡就沒人早請示、晚彙報了。我們這個院子不早請示、晚彙報了,似乎也沒人指責和追究。再後來,這種向毛主席表忠心的儀式在擔擔坪無形中消失了。這種儀式在全公社全縣全省全國怎麼消失的,我無從知道,就像我不知道它怎麼會像燎原大火燃遍全國一樣。但這儀式在擔擔坪消失,肯定與覃老漢那具沉重而黑得發亮的棺材有直接關係。
很多年以後,我特意搜集了國內許多研究巫和巫術的學術文章、專著來讀,甚至通讀了中文版的弗雷澤的《金枝》和馬林諾夫斯基的《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我沒有想成為這方面專家或學者的意思和意願,我只想從中找到巫師的法術被毀,與斑鳩、女人生殖器相關的案例。但我一例也沒有找到。覃老漢跟我說他的「掌心雷」失靈,是因為他的手觸碰了女人的生殖器。巫和巫術中有數不清的禁忌,有很多禁忌甚至流傳至到了民間。比如江薇薇、龔曉萍把內衣內褲、月經帶晾晒在院壩裡,招來了花妹他媽的雷霆大怒,像趙子龍揮舞長槍似地搖著她那長約兩米的菸桿、破口大駡,逼著江薇薇和龔曉萍收起她們的內衣內褲、月經帶,從此,這些東西她們只敢晾在她們自己的房間裡。而這些東西恰恰又是最需要太陽光照射的;又比如擔擔坪的男人們,絕不允許任何女人從他們放在地下的扁擔上跨過去。這些,或多或少都與女人生殖器有些關聯,也就是說,在中國巫術中,女性生殖器是大禁忌,那求偶時垂下頭、翹起尾巴「咕~咕,咕~咕……」叫個不停的斑鳩又是為什麼成為了端公禁忌的呢?
1
二○○○年初秋的一個上午,站在穿過高董子的機耕道上,望著周圍亂石如林,特別那已被碎石淹沒了大半截的印子石,我思緒萬端,心情有些沉重。一九八五年夏天我第一次訪舊回擔擔坪時,還沒有這條機耕道,和我一九六九年一月插隊落戶到擔擔坪當知青時一樣,要從金峒司爬山越嶺幾十裡,才能到達擔擔坪。有了這條連接省道的機耕道,從金峒司開車上擔擔坪,似乎也就是一、二十分鐘的事,但是,如果我知道這條機耕道要穿越高董子抵達擔擔坪,我情願把車停在金峒司,步行去擔擔坪……陪我同來的利川縣文化局的民俗專家老譚也下了越野車,...
目錄
序 冉雲飛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序王繼《六月悲風》
正文
六月悲風
附錄 「剝棗詩社」集體創作
〈巴人創世紀〉
跋 唐雲
一切都將無可追憶─讀《六月悲風》後的冥想
後記
序 冉雲飛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序王繼《六月悲風》
正文
六月悲風
附錄 「剝棗詩社」集體創作
〈巴人創世紀〉
跋 唐雲
一切都將無可追憶─讀《六月悲風》後的冥想
後記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