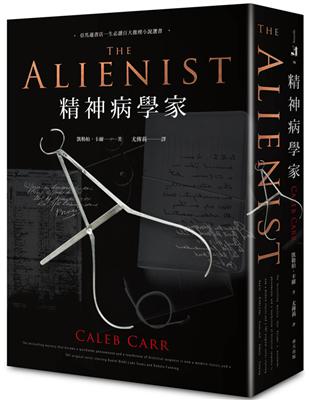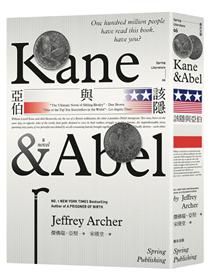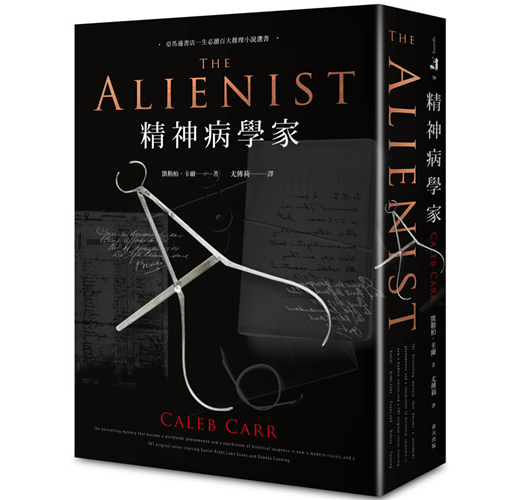亞馬遜書店一生必讀百大推理小說選書
NETFLIX熱門影集《沉默的天使》原著小說
風靡全球暢銷書 完美融合歷史及推理的經典小說
●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榜,售出24國版權
●獲頒安東尼獎最佳首作獎
●獲頒法國偵探文學大獎
●獲頒美國浪達同志文學獎
●獲頒丹麥Palle Rosenkrantz獎(丹麥年度最佳犯罪小說獎)
●改編影集由丹尼爾・布爾(Daniel Brühl)、路克・伊凡斯(Luke Evans)及達科塔・芬妮(Dakota Fanning)主演
●自1994年初版、2006年出版平裝本至今,現仍居亞馬遜暢銷懸疑驚悚小說榜
「有個人三年前謀殺了那兩個小孩,現在又有個模仿的神經病也喜歡毀損屍體。我們該怎麼辦?」
「你剛剛所講……幾乎沒有一樣是正確的。我一點也不確定他是神經病,也不太相信他喜歡毀損屍體。但最重要的是──這一點我恐怕要讓你失望了……我非常確定這不是模仿者,而是同一個人。」
一八九六年,紐約。興建中的威廉斯堡橋上發現一具男孩的屍體,屍身被殘酷毀損。報社記者摩爾被他的好友克萊斯勒──一名精神病學家──邀請前往現場勘驗,意外發現此案與三年前尚未偵破的水塔兄妹命案應是同一人所為,在找出真兇之前,兇手還會繼續犯案……
那三具屍體就像文字一般清楚,我們可以閱讀出他竭力呼喊著要我們找到他。而且要快──因為我猜想,他殺人的時間表非常嚴格。而這個時間表,也是我們務必要學著破解的。
一半像福爾摩斯,一半像《沉默的羔羊》,《精神病學家》呈現出鍍金年代的曼哈頓,有著廉價租屋和富貴豪宅、腐敗的警察和囂張的幫派份子、華麗的歌劇院和骯髒的酒館。這本書證明凱勒柏.卡爾的大師手筆,精采刻劃出日常生活之下潛藏的種種不安力量。
作者簡介:
凱勒柏.卡爾Caleb Carr
小說家、軍事史學家。得獎暢銷書《精神病學家》、《黑暗天使》作者,同時著有眾多小說作品,最近一部是Surrender, New York。他的歷史著作包括備受讚譽的The Lessons of Terror: A History of Warfare Against Civilians以及The Devil Soldier: The Story of Frederick Townsend Ward。在紐約市出生、成長。現任《軍事史學報季刊》(MHQ: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特約編輯,以及「現代戰爭叢書」編輯。目前定居紐約州北部,任教於巴德學院(Bard College)。
譯者簡介:
尤傳莉
生於台中,東吳大學經濟系畢業。現為專職譯者。著有《台灣當代美術大系:政治、權力》,譯有《達文西密碼》、《天使與魔鬼》、《依然美麗》、《過得還不錯的一年》、《骸骨花園》、《喀邁拉空間》、《外科醫生》等小說與非小說多種。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追獵的方法和截然不同的獵人團隊,讓整個故事超越優秀驚悚小說的水準──超過太多了……一部融合歷史小說和心理驚悚小說的出色組合。
──《水牛城新聞報》(The Buffalo News)
凱勒柏.卡爾這本豐富的驚悚小說帶著我們回到歷史上的那一刻,我們初次見識到現代觀念中的連續殺人兇手……看著一群有遠見的調查團隊熱誠努力要解開一連串駭人聽聞的謀殺案──引人入勝……充滿懸疑……令人滿足。
──《弗林特日報》(The Flint Journal)
太了不起了……帶領讀者進行一場鍍金年代大都會的旋風之旅,登上廉價租屋的樓梯,爬過屋頂,見證午夜的驗屍解剖……一部令人屏息、寫作技藝絕佳的推理小說!
──《里奇蒙時代快報》(Richmond Time-Dispatch)
不但是出色的推理小說,同時還讓讀者透過虛構的社會歷史場景如臨現場。
──《科克斯書評》
《精神病學家》不但是別出心裁的推理小說,凱勒柏.卡爾同時也熱切地將舊時代的紐約歷歷呈現於讀者眼前。
──安東尼.昆(Antohony Quinn),《獨立報》
凱勒柏.卡爾的卓越之處是他極為嚴謹的佈局,以及高度的想像力。尤其在描寫克萊斯勒為什麼向前探索時總可以依循許多龐大的科學脈絡而得以成功……凱勒柏.卡爾說故事的氣魄對他的小說幫助頗大,其敘述能力讓讀者在每章節結束時感受到驚險的高潮,欲罷不能!
──史蒂芬.阿米頓(Stephen Amidon),《星期天泰晤士報》
雖然故事的素材不容易處理,但是故事卻憑著正確的歷史感和緊湊情節,直到最後才公開殺手的身分,而贏得讀者的一致讚賞。其實凱勒柏.卡爾的小說並不只是局限推理小說上,而是立基於更開闊的文體。
──基爾柏.泰勒(Gilbert Taylor),《書目》雜誌
第一流的罪與罰故事。
──《娛樂週刊》(Entertainment Weekly)
讓讀者一頁接一頁,過了睡覺時間許久還欲罷不能!
──《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
恐怖,令人著迷……《爵士年代》和《沉默的羔羊》的粉絲們會很喜歡。
──《弗林特日報》(The Flint Journal)
令人沉迷其中。
──《新聞週刊》(Newsweek)
情節設計出色……一場美好的黑暗之旅。
──《亞歷桑納每日星報》(The Arizona Daily Star)
故事的前提安排巧妙──背景和角色塑造部分極為細緻,比書店裡成排的一般驚悚小說要強太多!
──《華盛頓郵報》書之世界(The 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令人入迷!
──《底特律自由報》(The Detroit Free Press)
名人推薦:追獵的方法和截然不同的獵人團隊,讓整個故事超越優秀驚悚小說的水準──超過太多了……一部融合歷史小說和心理驚悚小說的出色組合。
──《水牛城新聞報》(The Buffalo News)
凱勒柏.卡爾這本豐富的驚悚小說帶著我們回到歷史上的那一刻,我們初次見識到現代觀念中的連續殺人兇手……看著一群有遠見的調查團隊熱誠努力要解開一連串駭人聽聞的謀殺案──引人入勝……充滿懸疑……令人滿足。
──《弗林特日報》(The Flint Journal)
太了不起了……帶領讀者進行一場鍍金年代大都會的旋風之旅,登上廉價租屋的樓梯,爬...
章節試閱
一八九六年三月三日凌晨兩點,在我祖母位於華盛頓廣場北路十九號的大宅裡,一陣窮凶惡極的捶門聲響起。先是吵醒一個女僕,接著是我祖母,兩人先後走到各自的臥室門口。我躺在床上,處於不再酒醉、卻也沒完全酒醒、且還需要睡眠的狀態。雖然知道來敲門的人大概是要找我,而不是要找祖母的,但我只是在亞麻布套的枕頭堆裡鑽得更深,希望那個敲門的人可以放棄而離開。 「摩爾太太!」我聽到那女僕喊。「好吵啊,我該去應門嗎?」 「不要,」我祖母清脆且堅定的聲音回答。「去叫醒我孫子吧,哈麗葉。一定是他的賭債忘了還!」 然後我聽到腳步聲走近我的房間,心想自己最好有所準備。自從大約兩年前,我和華府的茱麗亞.普瑞特小姐的婚約取消之後,就搬回來跟我祖母同住。這兩年來,我祖母愈來愈懷疑我怎麼消磨自己的下班時間。我已經跟她解釋過很多次,身為《紐約時報》的社會記者,我必須去很多比較污穢的區域和建築物裡,跟一些比較不那麼體面的人物打交道;但她清楚記得我年少輕狂的種種,不肯接受這個顯然太過勉強的說法。我搬回來後每天晚上的行為,又加強了她的猜疑,認定我老跑去「里脊肉區」的舞廳和賭場並不是出於職業責任,而是因為我愛去;這會兒我聽她跟哈麗葉提到賭博,才發現應該表現出我是清醒男人、認真負責的形象。於是趕緊穿上一件黑色睡袍,把頭上的短髮撫平些,然後高傲地打開了門,剛好哈麗葉來到我房門前。 「啊,哈麗葉,」我冷靜地說,一手放在睡袍裡。「不必大驚小怪。我剛剛正在看一篇報導的筆記,發現還需要一些辦公室的資料,於是派了人去拿。一定是那個跑腿的小弟幫我拿來了。」 「約翰!」正當哈麗葉困惑地點著頭時,我祖母大喊。「是你嗎?」 「不是,奶奶,」我說,踩著厚厚的波斯地毯下樓。「是賀姆斯醫師。」H.H.賀姆斯醫師是費城一位殘酷不堪的騙子謀殺犯,此刻正關在牢裡等著被吊死。而出於莫名其妙的原因,我祖母最大的夢魘,就是賀姆斯可能逃離跟絞刑官的約會、跑來紐約殺了她。我來到她臥室門邊,吻了一下她的臉頰,她毫無微笑接受了,不過顯然還是很開心。 「別這麼沒禮貌,約翰。這是你最不討人喜歡的特質。另外別以為你英俊的魅力就能讓我比較不生氣。」捶門聲又開始了,隨之一個男孩的聲音喊著我的名字。我祖母的眉頭皺得更深了。「到底是誰啊,有什麼事情這麼急?」 「我相信是報社派來的跑腿小弟,」我繼續撒著原來的謊,但也很想知道這位如此堅定猛敲著門的人是誰。 「報社?」我祖母說,一個字都不相信。「好吧,那你去應門。」 我迅速但謹慎地走到樓梯底端,才意識到我其實聽過這個喊我名字的聲音,但想不起到底是誰。儘管我確定這個聲音很年輕,但還是不放心——我一八九六年在紐約所見過各路最兇惡的盜賊和兇手,有一些都只是未成年人。 「摩爾先生!」那小夥子又喊道,敲門之餘還用腳用力踢了大門幾下。「我要找約翰.司凱勒.摩爾先生!」 我站在門廳的黑白大理石地板上。「是哪一位?」我問,一手放在門鎖上。 「是我,先生!史蒂威,先生!」 我放鬆地吐出一口氣,打開沉重的木門。外頭,站在一盞煤氣燈—全屋子內外所有燈都已經換成電燈泡了,只有這盞我祖母堅持不肯換—黯淡燈光下的,是史蒂威.塔格特,綽號「史蒂威菸斗」。史蒂威才十一歲時,就成了十五分局的禍患;但接著我的好友拉茲洛.克萊斯勒醫師讓他改過自新,現在這男孩成為這位著名內科醫師兼精神病學家的馬車夫與跑腿小弟。史蒂威倚著門外的一根白石柱,努力喘著氣——顯然嚇壞了。 「史蒂威!」我說,看到他長長的褐色頭髮被汗水沁溼。「發生了什麼事?」然後我看到他身後克萊斯勒那輛小小的加拿大輕馬車。黑色的上掀式車篷收起來了,拉車的是一匹黑色的騸馬,叫福瑞吉克。那匹馬和史蒂威一樣渾身是汗,在三月的凌晨空氣中吐著白霧。「克萊斯勒醫師沒跟你來嗎?」 「醫師叫你跟我走!」史蒂威匆忙喘著氣說。「馬上!」 「可是去哪裡?現在是凌晨兩點——」 「馬上!」他顯然沒時間解釋了,於是我叫他等我換衣服。回房時,我祖母在我臥室房門外大聲說,不論「那個古怪的克萊斯勒醫師」和我在凌晨兩點要去做什麼,她都確定不會是什麼體面的事情。我盡量不理會她,換好衣服回到外頭,拉緊我的粗花呢大衣,跳上馬車。 我都還沒坐下,史蒂威就揮動長鞭抽打福瑞吉克。我往後倒向深栗紅色的皮革座位,本來想責罵那小鬼,但他臉上的恐懼神情再度鎮住了我。我撐穩身子,同時馬車搖晃著駛過華盛頓廣場的鵝卵石路,速度快得有點危險了。馬車轉入百老匯大道的俄羅斯石板路面時,那種搖晃和震動也只稍微減輕一點。我們駛向下城、往東的方向,來到的曼哈頓這一帶是拉茲洛.克萊斯勒工作的地方,而且是愈進入深處、生活就愈廉價且骯髒的區域:下東城。 有那麼片刻,我以為或許克萊斯勒出了什麼事。當然,這是因為史蒂威焦躁地鞭打並驅趕福瑞吉克的方式,因為據我所知,史蒂威大部分時間都對這匹馬非常和善。史蒂威對任何人不是咬一口就是打一拳,唯一的例外是克萊斯勒,而且他絕對是這個小夥子沒待在蘭德爾島那所美其名為「少年收容所」的唯一理由。以紐約市警局的說法,史蒂威除了十歲前就是「小偷、扒手、醉鬼、有菸癮、騙人牌局的攬客小弟,以及天生有破壞性的討厭鬼」之外,外加攻擊過蘭德爾島的一名警衛至嚴重傷殘,還說是因為那警衛想攻擊他。(在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報紙上所謂的「攻擊」,幾乎毫無例外就是指強暴。)因為那警衛有老婆、有小孩,因此史蒂威的誠實度、甚至精神正常與否,就頗受質疑了。此時克萊斯勒以當時法庭精神病學界最厲害專家之一的身分,進入了那個收容所。在一場為了判定史蒂威精神健全與否的聽審上,克萊斯勒出色地描繪出這個男孩從三歲被母親棄養、從此在街頭流浪的生活。(他的母親為了鴉片癮而拋棄兒子,後來成為一名華人鴉片商的情婦。)法官對於克萊斯勒的敘述印象深刻,也很懷疑那位受傷警衛的證詞;但直到克萊斯勒提出要收留這個男孩,並為他未來的行為擔保,法官才同意釋放史蒂威。當時我覺得克萊斯勒太瘋狂了,但毫無疑問,才剛過一年,史蒂威就變得截然不同。而且,就像幾乎每個幫克萊斯勒工作的人一樣,這個男孩對主子忠心耿耿,儘管克萊斯勒情感上保持距離的古怪特質,讓很多認識他的人覺得費解。 「史蒂威,」我在馬車輪子撞擊俄羅斯花崗岩石板破損邊緣的嘈雜聲中大喊,「克萊斯勒醫師人在哪裡?他沒事吧?」 「在學園裡!」史蒂威回答,藍色的眼睛睜得很大。克萊斯勒工作的總部是一所學校與研究中心的混合物「克萊斯勒兒童學園」,由他一手在一八八○年代創辦。我正要問起他這麼晚了還在那裡幹嘛,馬車就衝過依然繁忙的百老匯大道和郝士頓街交叉口,於是我把問題吞回肚裡。曾有人睿智地說,你可以站在這個十字路口,拿一把霰彈槍朝任何方向開火,都不會射中一個誠實正直的人;史蒂威很樂於把那些醉鬼、法老牌戲莊家、嗎啡和古柯鹼成癮者、妓女和她們的水手恩客,以及行乞的遊民嚇得朝人行道飛奔。大部分人安全後,都在我們後頭叫罵著粗話。 「所以我們也要去學園了?」我喊道。但史蒂威只是扯著韁繩,在清泉街猛然左轉,打斷了兩三家歌廳外頭的人潮,這些歌廳其實是幽會的撮合地點,裡頭的妓女打扮成舞者,跟通常是城外來的不幸笨蛋在此挑好對象,稍後再去廉價旅館。清泉街走到底後,史蒂威轉入迪蘭西街——這條街正在拓寬,以容納新的威廉斯堡橋(最近剛開始興建)落成後預計將會增加的車流——然後我們飛快掠過幾座黑暗的戲院。一路經過的每條小街,我都能聽到絕望、發狂的聲音從廉價酒館內傳來:這些污穢的小店裡只有一塊骯髒的厚木板權充吧檯,賣的那些劣等烈酒裡摻的從石油醚到樟腦,各式各樣都有可能,一杯只賣兩毛五。史蒂威沒放慢速度,我們似乎直衝曼哈頓島的最邊緣。 我又最後一次試圖溝通:「我們要去學園嗎!?」 史蒂威只是搖頭,然後又揮動長長的馬鞭。我聳聳肩,往後靠著車廂邊緣坐好,很納悶會是什麼把這男孩嚇成這樣—他短短的一生中,已經看過紐約的許多恐怖場面了。 我們沿著迪蘭西街往前,經過一家家關閉的水果攤和衣服店,進入了下東城那些擠滿廉租屋和簡陋棚屋的最糟糕貧民窟之一:柯立爾岬北邊的水濱附近。一大片由小棚屋和粗糙新建廉租屋形成的悲慘海洋,就在我們兩邊延伸。這個區域是不同移民文化和語言的大燉鍋,愛爾蘭人獨霸迪蘭西街以南,匈牙利人則佔據了靠近郝士頓街的北端。偶爾可以看到某個宗派的教會,點綴在一排排淒慘的住屋間,而那些住屋外的曬衣繩上頭,連在這寒冷的凌晨都還掛著溼衣服。有些衣服和床單都快結凍了,在風中僵硬地扭動,形成非常不自然的角度;但老實說,在這樣的一個地方——鬼鬼祟祟的人從沒有燈光的門內溜進黑暗的小巷,一身破爛衣服,赤腳踩在馬路表面冰凍的馬糞、馬尿、煤灰上——沒有什麼真能稱之為不自然的。我們來到的這一帶沒有什麼法律或規則,無論訪客或居民,只有在逃離這裡之後,才能感到愉快。 快到迪蘭西街盡頭時,海洋和新鮮海水的氣息,混合著岸邊居民每天倒進海裡的垃圾臭味,製造出這個潮水灣——我們稱之為東河——獨一無二的氣味。很快地,一個巨大的結構物在我們前方傾斜升起:那是通往初期威廉斯堡橋的斜坡通道。令我驚訝的是,史蒂威毫無暫停地衝上了那條木板斜坡道,馬蹄和車輪在木頭上敲出的嘈雜聲,遠比敲在石頭路面要響亮。 那條斜坡道由一片迷宮般錯綜複雜的鋼製樑柱撐起,帶著我們往上爬了幾十呎,進入黑夜空氣中。正當我納悶著此行的目的地到底會是哪裡—因為威廉斯堡橋的橋塔才剛開工,還得好幾年才能完成——就開始搞懂聳立在前方、貌似大型中華廟宇壁面的東西是什麼了。這座奇特而雄偉的建築物,就是大橋在曼哈頓這端的錨座,整個結構由巨大的花崗岩石塊構成,頂端有兩個矮而粗的瞭望塔,每個塔的周圍環繞著一圈窄小的鋼製走道。整座橋將會有一組巨型懸吊鋼纜支撐中央橋跨,而這些鋼纜最後就是固定在橋兩端的錨座上。不過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它像一座廟的印象也不算太離譜:就像布魯克林大橋(我往南還可以看到它夜空下哥德式拱頂橋塔的輪廓),這座跨越東河才剛開工的新橋,建造時曾有許多工作人員的性命為之犧牲,而且完成後的十五年間,也引發全曼哈頓各地的極大驚嘆。但我當時不知道的是,那一夜在威廉斯堡大橋西端錨座頂端獻祭的鮮血,性質是非常不同的。 在錨座通往頂端瞭望塔的入口附近,幾個巡邏警員站在幾盞電燈泡和手持提燈所發出的微弱光線中,他們身上小小的黃銅佩章顯示屬於十三分局(不久前我們在迪蘭西街上,還經過了這個分局)。另外還有一位來自十五分局的警佐跟他們在一起,這件事立刻讓我覺得很反常——在《紐約時報》負責跑犯罪新聞兩年,更別說從小在紐約市長大,我已經知道這個城市的每個分局都嚴守自己的地盤。(在十九世紀中期,各種警界派系還都公然彼此鬥爭。)十三分局找來一個十五分局的人,顯示一定出了非同小可的事情。 接近這群穿著藍色長大衣的警察時,史蒂威終於勒住馬,然後跳下座位,抓住馬銜,把那匹猛喘的馬拉到路旁,靠近很大一堆建築材料和工具。史蒂威看著那些警察,帶著慣有的不信任眼神。來自十五分局的那個警佐是個高大的愛爾蘭人,蒼白的臉上唯一特色就是沒有一般警察唇上厚厚的小鬍子,他往前走過來打量著史蒂威,臉上帶著威脅的微笑。 「這可不是小史蒂威.塔格特嗎?」他說,一口明顯的愛爾蘭腔。「局長大老遠把我找來這裡,你想,應該不是為了要搧你這個小屁蛋的耳光吧?」 我下了車廂,走向史蒂威,他狠狠瞪了那警佐一眼。「別在意,史蒂威,」我盡可能體諒地說。「愚蠢是跟著皮革頭盔而來的。」史蒂威露出虛弱的微笑。「不過麻煩你告訴我,我來這裡是要做什麼?」 史蒂威朝北邊的瞭望塔點了個頭,然後從口袋裡掏出一根壓扁的捲菸。「在上頭。醫師說你要上去。」 我正要走向花崗岩牆上的一個入口,但發現史蒂威還是站在馬旁。「你不來嗎?」我問。 那男孩打了個冷顫,別過身子點了菸。「我看過一次了,可不想再看第二次。我就在這裡等你,摩爾先生,我會送你回家。醫師的指示。」 我心裡愈來愈擔心,轉身走到入口,那個警佐伸手攔住了我。「請問你是哪位,讓史蒂威菸斗三更半夜載著你到處亂跑?這裡是犯罪現場,你知道。」我說出我的姓名和職業,他一聽就咧嘴秀出一顆醒目的金牙。「啊,媒體的記者先生——而且還是《紐約時報》!唔,摩爾先生,我也是剛趕到。他們緊急打電話找我來,顯然沒有其他信得過的人。敝姓弗林,先生,拼法是F-l-y-n-n,另外可別把我寫成了巡查警官。我是正警佐。來吧,我們一起上去。你給我乖一點,小史蒂威,否則我馬上把你送回蘭德爾島!」 史蒂威轉身回去面對那匹馬。「你一邊涼快去吧。」他喃喃說,大聲得讓那警佐聽得見。弗林猛地轉身,惡狠狠的雙眼充滿憤怒的殺意,但是又想到我在場,於是忍住了。「無可救藥,那小鬼。摩爾先生,真無法想像你這樣的紳士怎麼會跟他在一起。想必是利用他當下流社會的線民了。我們上去吧,先生,另外提醒你一聲,這裡可是黑得像礦坑!」 於是就這樣,我磕磕絆絆地走上一段高低不平的階梯,爬到頂之後,我看出了另一個皮革頭盔的形影,是十三分局的一位巡查警官,他轉身喊著另外一個人: 「是弗林,長官。他來了。」 我們離開階梯,來到一個小房間,裡頭散佈鋸木架、木板、鉚釘桶,還有金屬和電線碎片。幾扇大窗使得各個方向的視野一覽無遺——我們後方的市區、我們前方的東河和局部完成的橋塔。小房間裡有一道門通向橋塔外環繞的走道。靠近門邊站著一個細長眼睛、蓄著絡腮鬍的刑事警佐,他是派屈克.康納,我以前去茂比利街的市警局總部跑新聞時就認識的。站在他旁邊、雙手在背後交握、正踮起腳往下眺望著東河的,則是更熟悉的身影:西奧多.羅斯福。 「弗林警佐,」羅斯福說,沒有轉身。「我們找你來,是因為有很可怕的狀況。非常可怕。」 然後羅斯福轉身過來時,我的不安感忽然更強烈了。他的外表沒有任何不尋常之處:一套昂貴而有點浮華的格子西裝,就是他那些年最偏愛的;戴著的夾鼻眼鏡就像他的雙眼,對他粗獷、四四方方的腦袋來說太小了;大鼻子底下是濃密的小鬍子。只不過,他的臉卻是極其反常。然後我想到了:他的牙齒。他那一口整齊、通常很顯眼的牙齒,現在卻完全看不到了。他的下巴緊繃著,看起來似乎非常生氣,或是自責。顯然有什麼事情讓他非常震驚。 看到我之後,他似乎更加驚訝了。「什麼——摩爾!你跑來這裡做什麼?」 「我也很高興見到你,羅斯福。」我不安地開了口,伸出一手。 他握了,不過難得一次,他沒有握著一直猛晃、晃得我手臂都快脫臼。「什麼——啊,對不起,摩爾。我——我當然很高興見到你了。很高興。不過是誰告訴你—?」 「告訴我什麼?我是被克萊斯勒的跑腿小弟硬拉著跑來這裡的。他只下令讓我來,根本什麼都沒解釋。」 「克萊斯勒!」羅斯福有點急切地喃喃道,看了窗外一眼,眼神困惑,甚至是有點恐懼,完全不像平常的他。「是的,克萊斯勒來過這裡。」 「來過?你的意思是,他離開了?」 「我到之前就走了。他留了一張字條。還有一份報告。」羅斯福讓我看他抓在左手裡的一張紙。「總之,只是一份初步報告。他是他們能找到的第一個醫師。雖然當時狀況已經沒有希望了……」 我握住他一邊肩膀。「羅斯福,到底怎麼回事?」 「局長,為了確定一下,我也很想知道,」弗林警佐也說,那種老派的奉承口吻讓人很受不了。「我們十五分局那邊最近都忙不過來了,我也才剛趕——」 「非常好,」羅斯福說,打起精神。「你們兩位的胃不會太差吧?」 我什麼都沒說,弗林講了個荒謬的笑話,提到他這輩子見過很多可怕的場面;但羅斯福的雙眼無動於衷,只是指著通往外頭走道的門。康納刑事警佐讓到一邊,然後弗林帶頭走出去。 儘管很擔心,但出了那道門之後,當時我的第一個想法,就是走道上的視野比塔樓窗子還要驚人。水面盡頭就是布魯克林的威廉斯堡地區,那裡一度是平靜的鄉間小鎮,但現在已經迅速轉變為一個繁華的地帶,而且幾個月後,就會正式納入大紐約的一部分。往南,則是布魯克林大橋;西南邊的遠方是印刷廠廣場上幾棟高聳的大樓,而在我們下方,則是滾滾流逝的黑色河水。 然後我看到了。
一八九六年三月三日凌晨兩點,在我祖母位於華盛頓廣場北路十九號的大宅裡,一陣窮凶惡極的捶門聲響起。先是吵醒一個女僕,接著是我祖母,兩人先後走到各自的臥室門口。我躺在床上,處於不再酒醉、卻也沒完全酒醒、且還需要睡眠的狀態。雖然知道來敲門的人大概是要找我,而不是要找祖母的,但我只是在亞麻布套的枕頭堆裡鑽得更深,希望那個敲門的人可以放棄而離開。 「摩爾太太!」我聽到那女僕喊。「好吵啊,我該去應門嗎?」 「不要,」我祖母清脆且堅定的聲音回答。「去叫醒我孫子吧,哈麗葉。一定是他的賭債忘了還!」 然後我聽到腳步聲...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