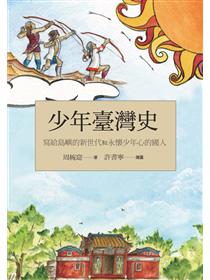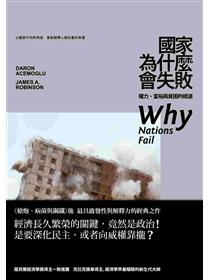當以暴易暴看似成為不得不的選擇,
非暴力的主張還有什麼意義?
「現代政治理論中最有影響力的聲音」、「當代最重要的女性主義理論家」茱蒂斯・巴特勒
反思國家暴力與全球政治狂潮之作在公民不服從運動於各地風起雲湧的當代,
誰有權來界定什麼是暴力、什麼是非暴力?
當你是一名為了爭取社會平等的政治抗爭者,在什麼情況下,你覺得你可以行使暴力?
反過來說,又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下,國家權力能夠「合理」行使暴力?
思考這些問題,就是政治的倫理學。
*********************************************************************************************
當代非暴力政治的難題在於:對於到底該如何界定一種行動是否暴力,往往看法分歧,從而導致了國家在行使暴力上的獨佔權。本書集結了茱蒂斯・巴特勒近年對政治倫理、國家暴力與抗爭運動的關懷與思索成果。針對暴力與非暴力的界定問題、人與人之間相互依存的必要,以及我們保衛他人的義務,都提出了獨到而深刻的剖析。
暴力與非暴力的界定遠比我們所想的曖昧,在本書中,巴特勒取徑傅柯、班雅明、法農、巴里巴等人的理論,拆解暴力所隱含的話語陷阱,也探討了為何這種壓迫往往行使在難民、少數種族與特定性別身上。此外,也分析了「種族幻象」(racial phantasms)如何形塑了國家的正義以及行政上的暴力
非暴力常被誤解為出自冷靜靈魂的消極手段,巴特勒則賦予它全新的政治想像,她認為非暴力與憤怒、仇恨,甚至毀滅都並不相違,是一種充滿憤慨、激情與攻擊性的表達形式。透過肉體抗爭與不合作,抗爭者向當權展現其存在;當弱者受暴力斲傷而催折,他人則透過悲慟與紀念賦予其生命存在價值。從而超越了個人主義,一種新的、全球性的平等理想也就此誕生。
專文推薦
黃涵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共同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序)
紀大偉(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張小虹(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萬毓澤(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國外好評
「茱蒂斯‧巴特勒是當代最具創意和勇氣的社會理論家,且一直持續寫作。」──柯尼爾‧衛斯特(Cornel West),著有《種族議題》(Race Matters)
「做為一種抵抗和抗議的手段,非暴力通常被視為消極的個人主義。而巴特勒的哲學則認為,這實際上是一種精明甚至激進的集體政治策略。」──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非暴力的力量)引導我們踏上一條從未嘗試過的解放之路,但在開始追求的那一刻,似曾相識與熟悉之感便湧上心頭。」──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書評LSE Review of Books
「茱蒂斯‧巴特勒是當代最有洞見、最勇於挑戰且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理查・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美國哲學家,著有《論暴力:思無所限》(Violence: Thinking without Banisters)
作者簡介:
茱蒂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1956年生,耶魯大學哲學博士,美國後結構主義學者,研究領域涵蓋女性主義、酷兒理論、政治哲學以及倫理學。目前任教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修辭學與比較文學系。
巴特勒為女性主義理論代表人物,其著作《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一書,更是女性主義的必讀經典。她近年的研究關懷,則轉向政治、暴力與倫理問題,被稱為「現代政治理論中最有影響力的聲音」和「最有影響力的女性主義理論家」。
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巴特勒參與了學術界連署,讉責香港警察的暴力行為,並促請香港政府捍衛學術自由,以及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譯者簡介:
蕭永群
臺灣大學中文系101級,美國加州聖塔芭芭拉分校東亞研究所畢業,專攻臺灣日治時期文學語言暨翻譯研究,現任美國德州媒體業新聞記者兼主播。譯有臺灣詩人杜國清《翻譯與譯詩》(英譯)。鍾愛羅曼•雅各布森的翻譯理論以及其「創譯」觀,堅信翻譯即是一次次對於自我經驗之修正與認同。
章節試閱
前言
非暴力議題在政治光譜各端上都飽受爭議,左翼分子主張暴力本身就可以為社會與經濟帶來徹底轉型,而也有人較保守地認為,暴力僅應做為我們實現這種轉型的策略之一。不論是主張非暴力、或選擇手段性或策略性地使用暴力,唯有在對「暴力」和「非暴力」的構成要件上有所共識後,這些論述才能被搬上檯面。非暴力支持者所面臨的一大挑戰在於,「暴力」和「非暴力」本身就是具有爭議的詞彙,比如說,有些人將傷人的話語視為「暴力」,然而也有人主張除了明確的威脅以外,把語言本身冠上「暴力」的形容並不恰當。另外有人堅持「暴力」的概念應有侷限,認為實質上的「身體攻擊」才能算數;還有人堅信經濟和法律結構是「暴力的」,它們會作用於身體之上,即便往往不是採用肢體暴力的形式。實際上,攻擊的形象(figure)已經悄悄地形塑了一些關於暴力的重要辯論,顯示出暴力往往發生於對峙的兩方人馬。將物理攻擊視為一種暴力無庸置疑,但我們也可主張社會結構或系統是「暴力的」,系統性種族主義(systemic racism)即是一例。確實,有時頭部或身體遭受物理攻擊,也算是系統性暴力的展現,但在這種狀況下,必須先釐清行動與結構或系統間的關係。要了解結構性或系統性的暴力,必須跳脫正面論述,因為它會限制我們理解暴力運作的方式。此外,我們必須找到一個更全面性的論述框架,而不是固守一方打人、一方被打的二元框架。當然,任何關於暴力的論述,如果無法解釋毀滅、攻擊、性暴力行為(包括強暴),或者無法理解暴力如何在親密二元、或面對面衝突的關係中運作,便是描述層面和分析層面上的失敗,無法闡明暴力到底是什麼。當我們在辯論何謂暴力與非暴力時,就是陷入了這種狀況[詳見 “The Political Scope of Non-Violence”, Thomas Merton, ed., Gandhi: On Non-Violence,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5, 65-78.]。
表面看來,宣稱自己反對暴力、表明立場,似乎是再簡單不過的事。然而在公共辯論的過程中,我們會發現「暴力」一詞是不穩定的,其語意本身能挑起各種爭端。有時國家和機構會將持不同政治意見、反對政府或質疑當權者的聲音冠上「暴力」的形容。示威、紮營抗議、集會、抵制、罷工,全都可以視為「暴力」,即便抗議者沒有訴諸肢體衝突或上述任何形式的系統性或結構性暴力[欲觀更多非暴力行動,參見Gene Sharp, How Nonviolent Struggle Works, Boston: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 2013.]。國家或機構之所以這麼做,目的在於將非暴力行為扣上「暴力」之名,引發一場公共語義層面上的政治戰。若連為了支持言論自由而發起的示威,這種自由本身的展現,都能被稱作「暴力」,唯一的可能即是當權者要霸佔對「暴力」一詞的使用權,因此不惜透過誹謗反對者,並合理化警力、軍隊、防禦機構的調派,用這些力量打擊捍衛自由的示威者。美國研究學者堅登.瑞地(Chandan Reddy)便曾論及:美國所採取的自由主義的現代性(liberal modernity),將國家視為自由的應許之地,保護人民免於暴力侵害,但卻是透過對少數族群,以及被貼上非理性或違反國家規範標籤的人毫無顧忌發動暴力,以此達到這點[ Chandan Reddy, Freedom with Violence: Race, Sexuality, and the US Stat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他認為:這個國家是建立在種族暴力的基礎上,且對少數族群的系統性施壓仍未止息。因此,種族暴力被當成國家「自衛」的手段。 在美國等地,黑人和棕色人種被警方貼上「暴力分子」標籤,因而被逮捕或射傷制伏的事件層出不窮,即使他們手無寸鐵、只是剛好路過或跑過,或僅是試圖要抱怨,搞不好連睡個覺也有無妄之災[對於非裔美國人遭警「合理」兇殺案的統計數據,參見“Black Lives Matter: Race, Policing, and Protest,” Wellesley Research Guildes, libguides.wellesley.edu/blacklivesmatter/statistics.]。在這種狀況下,警方往往先將特定目標對象視作威脅、會帶來實際暴力傷害的一方,然後進一步將自身行動解釋為「自衛」,如此的操作手法,讓人不禁感到既離奇又震驚。即使目標對象未做出明確的暴力舉動,他們仍被視為暴力的化身,因為他們是那種暴力的人,或因為他們身上體現出純粹的暴力,後者更經常帶有種族主義的主張。
因此,「暴力」議題從最初「支持與否」的道德論證,一下子演變成定義上的爭辯,以及探討什麼人會被視作「暴力的」、又是在何種情況下會如此。當人們凝聚起來對審查制度提出反對,或指責國家缺乏民主自由,往往會被扣上「暴民」帽子,或被認為是造成混亂或毀滅的威脅,敗壞社會秩序,這群人便被塑造成潛在、甚至真正的暴力分子,如此一來,國家便有理由保護社會免於暴民威脅。而隨之而來一系列的暴力行為,比如監禁、傷害、或殺戮,即是一種國家暴力(state violence)。即使國家企圖用自身權力,將異議分子命名和詮釋為暴徒,仍然不改這是一種「暴力」的事實。同樣地,如果國家握有國營媒體,或對媒體進行充分控制,一場和平示威便很容易被描繪、塑造成「暴行」,舉例而言,二〇一三年在伊斯坦堡蓋齊公園(Gezi Park, Istanbul)發起的和平示威[參見 “Gezi Park Protests 2013: Overview,”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ibraries Guides, guides.library.upenn.edu/Gezi_Park.]、或二〇一六年土耳其一眾學者所簽署的和平協議信[參見“Academics for Peace,” Frontline Defenders官網:frontlinedefenders.org。]便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集會自由被認為是「恐怖主義」(terrorism)的體現,如此一來,國家審查、被警察棍打或噴水、裁員、無限期拘留、入獄、放逐等遭遇便接踵而至。
雖然透過開誠布公討論以及找出共識的方式,可以更容易討論出何為暴力並取得共識,然而這在政治場域中是行不通的,掌權者將指控反對者為暴力的權力視為一種工具,以此來強化國家力量、抹黑反對者的理念,趁機徹底褫奪其公權、監禁,甚至謀殺他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反抗這種虛假與不公的指控。但當語義混雜的狀況已經根植在公共場域裡,以致難以辨認出暴力的情況下,何談反抗?我們是否已經被各種混亂觀點淹沒,導致我們只能被迫接受這種寬泛的相對主義(generalized relativism)?或者,我們是否可以建立一種分辨方法,來分辨透過捏造事實以反轉暴力責任歸屬的手段,以及其他往往尚未命名而缺乏恐怖的結構性與系統性暴力?
如果想論證支持非暴力的主張,首先必須了解並估量暴力一詞在話語、社會和國家權力的場域中,是如何被描述、歸類的,此外還要了解暴力的策略型反轉(inversion),以及該詞本身在責任歸屬上的不定性。更進一步地,我們必須抱持批判態度,審視國家暴力是如何陰謀將自身合理化,並且要了解這種陰謀是如何壟斷「暴力」一詞的使用權。這種壟斷建立在命名行為上,它為暴力塗脂抹粉,偽裝成合法的高壓統治,或將自身的暴力轉移到外在的目標對象上,好似在他人身上重新發現了這種暴力。
不論是要支持或反對非暴力,我們必須儘可能地區別它與暴力的不同。但要確立這兩者的語義差異並非一蹴可及,因為這個差異經常被利用來掩飾或放大暴力的目標和行動。換句話說,我們非得從概念上了解這個術語在各種情境中的部署方式,並且得分析這些部署背後的意義,才能導出結論。對於被指控為暴力、實際上卻沒有犯下任何暴行的人們,若認為指控不合理想為自己辯駁,便須說明什麼才能構成「暴力」指控:不只是「說了什麼話」,還需要說明「這些話具有什麼效果」?在何種認知架構上的話術容易被相信?換言之,是什麼讓人產生信任?更重要的是,要如何去拆穿和破解這些具有「高可信度」的話語?
在進行討論前,我們必須先同意「暴力」與「非暴力」的用法是多變且矛盾的,而不是陷入一種虛無主義的思想,以為暴力和非暴力的分界只由當權者來決定。本書的任務之一,便是要接受一件事,即當暴力受限於工具性的定義,服膺於政治利益、甚至國家暴力本身時,要定義及確立「暴力」一詞是極為困難的。對我而言,這種困難不意味著我們的批判性思考任務將被這種混亂的相對主義削弱,使我們無法辨識出錯誤且有害的工具性區分。暴力與非暴力所進入的道德辯論和政治分析場域,都早已被先前的各種運作給詮釋、改造過。如果我們希望反對國家暴力,並審慎檢視左翼分子將暴力合理化的手段,就無可避免地必須面對詮釋、區分暴力與非暴力的需要。當我們涉入道德哲學的水域,會發現我們處於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兩者的匯流處,在雙雙交互作用下,最終將影響我們參與政治、打造世界的方式。
在支持策略性地使用暴力這點上,左翼人士最常見的論調就是:許多人早就生活在暴力之中了。承接這個論調,正因暴力無時無刻都在發生,一個人是否透過行動去涉入暴力,其中根本不存在真正的選擇:因為我們早已身處暴力的場域。從這個角度觀之,以旁觀者的立場去討論使用暴力與否,這種道德論證本身就是特權、奢侈的,罔顧了自身在權力場域中的位置。從這個層面上看,使用暴力不是一種選擇,因為當事人早已身不由己地活在暴力之中。由於暴力時時刻刻都在上演(對弱勢族群則是日常),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的反擊只是一種反暴力(counter-violence)的形式罷了[針對反抗以及其相悖公式之完整論述,參見Howard Caygill, On Resistance: A Philosophy of Defiance, New York: Bloomsbury, 2013.]。除了主張「暴力鬥爭」(violent struggle)之於革命的必要性這種較普遍和傳統的左派論調外,還有其他更具體的辯解:由於我們被暴力侵害,我們理應對:一、先使用暴力的那方,以及二、衝著我們來的人,採取以暴易暴的行動。我們是出於維護自身和行使權利的基準下,才這麼做的。
至於抵制暴力的行為應被視為反暴力的這番主張,我們也應提出各種質疑:縱使深陷暴力不曾終止的循環,我們難道有資格決定是否讓它繼續惡性循環下去?若暴力不斷運行,是否就代表這將是個無限循環?去質疑這種無限循環背後的意義又是什麼?主張以暴易暴者可能會以「別人做了,我們也應該這樣做」,或「別人針對我們,出於自衛,我們也針對他們」之主張辯駁。這兩種主張各有所異,但都十分重要。第一種說法秉持直接的相互關係原則,主張別人若對我們採取了什麼行動,我們就有資格採取同樣方式。然而,這種論調罔顧了對方的行動是否合理。第二種說法將暴力的概念與自衛、自保掛勾,在之後的章節會有更詳細的探討。目前我們先探討:所謂的「自我防衛」一語,要防衛的「自我」究竟指誰[Elsa Dorlin, Se défendre: Une philosophie de la violence, Paris: La Découverte, 2017.
]?要如何將這個自我(self)從他人的自我,或從歷史、土地或其他定義中劃分出來?那些被他人施暴的人,是否某種意義上,也屬於那個出於自衛而施暴的「自我」之一部分?就此層面而言,對一個人施暴就等於是對自我施暴,但前提是這兩者間必須從根本上有高度關聯。
上述第二種主張是本書的核心關懷之一。當執行非暴力的一方和施暴方有所關聯,那麼他們之間顯然就先存在了一層社會關係:他們是彼此的一部分,或是說他們各自的自我會彼此牽連。而非暴力便成了默認這層社會關係的一種方式,無論這有多麼令人擔憂,或強化(affirming)了從這種既存社會關係中所產生的規範性期望(normative aspirations)。因為如此,我們無法從個人主義的角度檢視非暴力倫理,反而要在倫理與政治的基礎上,對個人主義加以批評。談及非暴力的倫理和政治,就必須先解釋眾多的自我是如何與他人的生活相互交織,並受到一系列的社會關係約束,這些關係可能同時具備了破壞性或支持性。而被綁定和定義了的關係,乃是超越二元的人類衝突(human encounter)之上,也因此,非暴力的命題不僅存在於人際關係內,更存在於所有活生生的(living)、相互建構的關係中。
然而,欲進行關於社會關係的探討,必須先了解在暴力衝突當中,兩個主體間存在了哪種潛在或實質的社會連結。如果一個人的自我是透過與他人的關係而構成,那麼保有或否定自我,便也部分意味著去保有或否定所衍生出、用以定義自我和世界的社會聯繫。在反對以個人自衛之名,將自我使用暴力視為必然發生這種概念的情形下,我們在進行非暴力的探討時,便須對自我主義的倫理(egological ethics),以及個人主義的政治遺緒(political legacy of individualism)進行批判,才能將自我意識(selfhood)的概念開拓為充滿社會關係性(social relationality)的場域。此處所謂的關係性,自然在某種程度上是由矛盾、憤怒、侵犯等負面成分所定義的。人際關係中潛在的破壞性,並不會將關係性給全盤推翻,且關係的視角也無所遁逃於社會束縛中始終留存的潛在或實質破壞。因此,關係性本身並非什麼正面事物,既不是一種聯繫的象徵,也不是用來對抗破壞的倫理規範;相反地,關係性是一個爭議且矛盾的場域,在該場域中,有鑑於持續存在於結構上的潛在破壞性,必須優先解決有關道德義務的命題。不管「做對的事」最終導致何種結果,都取決於做出倫理判斷後,所需經歷的分裂和掙扎。這個課題不僅僅是自反的(reflexive),換言之,它並不是僅僅只關乎自己。事實上,當世界成了一個暴力的場域,非暴力的任務便在於替這樣的世界找出生存與行為之道,當暴力似乎要充斥整個世界、無所宣洩時,透過非暴力可能扭轉、制止或改變暴力的局面。身體在這個改變中,可以扮演載體(vector)的角色,然話語、集體行動、基礎建設、各個機構同樣也能擔綱此角。反對者認為支持非暴力根本不切實際,面對這類型反對聲浪,非暴力支持者應質疑何謂現實,並肯定反現實主義(counter-realism)在如此世道下的力量與必要性。也許要做到非暴力,必須一定程度上地超脫現實,如此一來將拓展更多可能性,建構出嶄新的政治想像。
許多左派人士主張他們信仰非暴力,但自我防衛時例外。要理解他們的說法,我們首先要釐清「自我」一詞的定義──它的涵蓋領域、界線和構成關係。如果我所捍衛的自我就是我自己、我的親屬,抑或是和我屬於相同族群、國家、信仰、語言的人,如此一來我便化身成同溫層中的社群主義者(communitarian),理想上我就應該要守護同路人的生命,而不是非我族類。此外,顯然這個「我」生活在一個很容易意識到「自我」存在的世界。當發現有些人的自我比起其他人的更值得捍衛,我們便以自衛之名合理化種種暴行,這樣難道不算是一種不平等的展現嗎?要解釋這種不平等,不能不把種族計畫列入思考,畢竟正是它對誰的性命比較珍貴(若失去了會令人悲慟)、誰的不值得做出詭異的劃分,這種由「可悲慟性」(grievability)之程度所造成的不公平,存在於全球族群光譜之中。
有鑑於自衛極易被視為執行非暴力時的合理例外狀況,我們必須考慮兩個問題:一、此處的自我指的是誰,以及二、這個「自我」涵蓋的範圍有多廣(是否涵蓋家人、族群、信仰、國家、故土、風俗習慣)?而那些被認定沒有悲慟價值的生命(好像有沒有他們都無關痛癢),便彷彿徘徊在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所說的「非存在區域」(the zone of non-being)中。若想突破這個圖式(schema),需要出現一個使人重新正視生命的宣言,「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社會運動即是一例。生命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生命於外在世界中呈現出的物理形式;生命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每個人都值得被平等對待。然而,自我防衛的主張,往往成了掌權者的防護盾,用來維繫力量、特權,以及其所假定與製造的不平等。在這些情況下,受到保護的「自我」可能屬於白種人、某個特定的國家,或是邊境爭執中的一方;如此一來,自我防衛一詞成了引戰的開端。此處「自我」的運作方式可以與政權相比擬,在這個膨脹的自我中,囊括了在膚色、階級或特權上具有相似性的一群人,而在這個秩序中被標註為異類的主體/自我,則會因此遭到驅逐。即使我們往往認為自我防衛是為了因應外來攻擊,但那些享有特權的自我卻不需要透過這種刺激,即能劃清界線、排除他者。「任何潛在威脅」──也就是任何想像出來的威脅、任何威脅的幻影,都足以釋放所謂暴力的本質。誠如哲學家艾莎.多林(Elsa Dorlin)所言,只有某一些自我被認為是有權自衛的[同上。]。舉例而言,在法庭上,「自衛」從誰的口中說出更容易取信於人?從誰的口中說出來較容易被打折扣、被駁回?換句話說,在法律的權力框架中,誰的「自我」更有辯護價值?誰的生命更值得存在、值得捍衛,不能任其逝去?
前言
非暴力議題在政治光譜各端上都飽受爭議,左翼分子主張暴力本身就可以為社會與經濟帶來徹底轉型,而也有人較保守地認為,暴力僅應做為我們實現這種轉型的策略之一。不論是主張非暴力、或選擇手段性或策略性地使用暴力,唯有在對「暴力」和「非暴力」的構成要件上有所共識後,這些論述才能被搬上檯面。非暴力支持者所面臨的一大挑戰在於,「暴力」和「非暴力」本身就是具有爭議的詞彙,比如說,有些人將傷人的話語視為「暴力」,然而也有人主張除了明確的威脅以外,把語言本身冠上「暴力」的形容並不恰當。另外有人堅持「暴力」的概念...
推薦序
非暴力:一種積極面對暴力的政治實踐
黃涵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目前任教於美國柏克萊大學的茱蒂斯・巴特勒,在政治哲學、倫理學、女性主義、酷兒理論等領域都是相當具有影響力的當代哲學家與行動者。巴特勒的學術著作從早期的《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GenderTrouble:FeminismandtheSubversionofIdentity,1990)和《要緊的身體:論性的言談限制》(BodiesThatMatter:OntheDiscursiveLimitsofSex,1993)開始,就已奠定她在當代學術界的重要地位。這些著作都挑戰了傳統二元對立的性別概念,把性別界定為一種建構和展演的過程。巴特勒在實際行動上除了為女同性戀和男同志平權運動發聲之外,也強力批判以色列的猶太復國主義。
巴特勒的學術著述豐富且多元,但不乏前後連貫的關懷,包括對於即身性(embodiment)的重視,而她的倫理學總是不離主體對於自身認知限制的體察。本書《非暴力的力量:政治場域中的倫理》(TheForceofNonviolence:TheEthicalinthePolitical,後文引為《非暴力的力量》)也延續了這些關懷,透過與班雅明、德希達、佛洛伊德等人思想的對話,深入探討政治與倫理領域中至關重要的暴力與非暴力的議題。但本書同時也為暴力研究提供了新的語彙和概念,包括可悲慟性(grievability)、展演性(performativity)、脆弱性(vulnerability)等等。
《非暴力的力量》的論述核心,在於暴力與非暴力之間模糊但並非不存在的區分,也正是這樣的模糊性或曖昧性,使得批判性思考顯得格外重要,以免暴力與非暴力落入虛假不實的區分甚至被誤用,畢竟暴力論述總是具有政治與情感的效應,會被用來合理化特定政策與利益。本書主張暴力總是經過詮釋的,也因為如此,本書企圖打開詮釋暴力的可能性。巴特勒並不贊成為了對抗體制暴力而訴諸策略性的暴力,同時巴特勒也在挑戰有關非暴力的預設。非暴力應該被理解為社會與政治實踐,而不是道德取向;非暴力不一定出自於平靜的靈魂,而經常是憤怒;更重要的是,非暴力是一種只能趨近但無法完全實現的理想。如本書書名所示,非暴力不是抗拒行動,而是一種積極面對暴力的力量;非暴力的重要任務不在於譴責個別暴力行為,而更應該是揭露和批判體制性的暴力與壓迫。巴特勒指出:「事實上,當世界成了一個暴力的場域,『非暴力』的意義便在於替這樣的世界找出生存與行為之道。當暴力似乎要充斥整個世界、無所宣洩時,透過非暴力的力量,可能扭轉、制止或改變暴力的局面。」
要反思暴力與非暴力的區分,我們必須打破與他人界線分明的「自我」的迷思。如果我們對於暴力和非暴力的思考侷限於自我的概念,我們可能因此無視體制性的或客觀性的暴力,因為我們無法清楚指認施行暴力的個人。這樣的迷思也可能讓「自我防衛」合理化暴力行為,沒有考慮(不管是個人或一整個族群、甚至國家的層次)「自我」的社會性,也就是個體之間的交互依存。當我們破除自我的迷思,每一個生命都將是值得保存的,每一個生命的逝去也都是值得哀悼的,這就是本書的核心概念「可悲慟性」(grievability)。必須強調的是,可悲慟性並非只是一種情感,更對於我們反思健康照護、戰爭、公民身份等,有積極的作用。「可悲慟性」同時是想像力和行動的倫理要求,我們被彼此、被每一個生命的逝去纏繞,我們對於構成暴力的所有現實和結構性因素不再習以為常。
《非暴力的力量》並沒有給出確切的行動步驟,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它企圖撼動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一切價值觀,挑戰我們關於暴力與非暴力的錯誤觀念,那是建構新的共存方式必要的第一步。如同巴特勒自己在後記所說的,「我們生活在無數暴行和死亡肆虐的年代」,更需要理解暴力的真相。在當前的時代裡,我們依然目睹著難民、無國籍者、有色人種、女性、跨性別者等群體遭受暴力甚至戮殺的日常,這些都不是個別事件,而是具有全球的連結性。同樣是在我們所處的時代裡,國家機器任意使用自己的媒體和武力將異議份子塑造成暴民,即便他們使用和平的手段。
當我們從媒體看到許許多多暴力的報導和影像,我們是否在感受短暫的驚嚇之後,便當作什麼事都沒發生,無視遺忘或抹煞系統性的暴力?要讓非暴力展現真正的力量,我們需要的是理論分析、倫理、認識論、社群網路、團結和行動的號召。除此之外,我們在某種程度上也必須要脫離現實,保持對於更多可能性的未來的政治想像。這些都是《非暴力的力量》給予讀者的。
非暴力:一種積極面對暴力的政治實踐
黃涵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目前任教於美國柏克萊大學的茱蒂斯・巴特勒,在政治哲學、倫理學、女性主義、酷兒理論等領域都是相當具有影響力的當代哲學家與行動者。巴特勒的學術著作從早期的《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GenderTrouble:FeminismandtheSubversionofIdentity,1990)和《要緊的身體:論性的言談限制》(BodiesThatMatter:OntheDiscursiveLimitsofSex,1993)開始,就已奠定她在當代學術界的重要地位。這些著作都挑戰了傳統二元對立的性別概念,把性別界定為一種建構和...
目錄
專文推薦│非暴力:一種積極面對暴力的政治實踐/黃涵榆
謝詞
導論
第一章│非暴力、可悲慟性及對個人主義的批判
第二章│為他者續命
第三章│非暴力的倫理與政治
第四章│佛洛伊德的政治哲學:戰爭、解構、躁狂與批判功能
後記│脆弱、暴力、抵抗之反思
專文推薦│非暴力:一種積極面對暴力的政治實踐/黃涵榆
謝詞
導論
第一章│非暴力、可悲慟性及對個人主義的批判
第二章│為他者續命
第三章│非暴力的倫理與政治
第四章│佛洛伊德的政治哲學:戰爭、解構、躁狂與批判功能
後記│脆弱、暴力、抵抗之反思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1收藏
11收藏

 38二手徵求有驚喜
38二手徵求有驚喜






 11收藏
11收藏

 38二手徵求有驚喜
38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