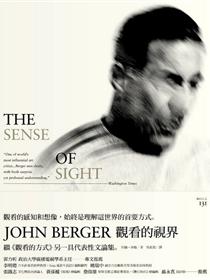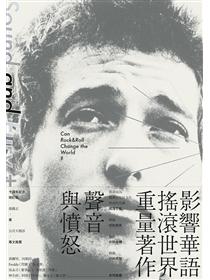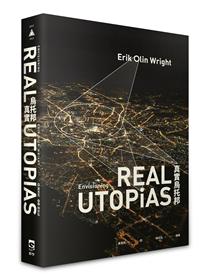「憂鬱」是個謎題。它和「失落」的關係是什麼?失去自己或失去別人,何者是憂鬱受苦的篇章?我們有「他是我愛人」的說法,何以「他是我恨人」這句話卻悄悄失聲了?失去「愛人」(名詞)會失志和憂鬱,那麼失去「恨人」(名詞)怎麼如此陌生呢?就算你不曾看過這三部電影,相信你也能從文字裡,窺見精神分析和電影巧妙互動的成果。
【薩所羅蘭】策展:「憂鬱三部曲」
「憂鬱三部曲」:
1. 撒旦的情與慾 (Antichrist)2. 驚悚末日 (Melancholia)3. 性愛成癮的女人 (Nymphomaniac)
不論你是否喜歡電影,是否看過這三部電影,這都不重要,我們會以有趣的方式來佈展它們;我們就是設定:「你不見得看過它們」來做準備的。
「佛洛伊德已死。」《撒旦的情與慾》女主角曾開精神分析的玩笑。這個玩笑太真實了,讓我們想喚醒佛洛伊德,回答謎題.......。
當我們談潛意識的情慾時,是什麼意思呢?說出來的性有多性呢?那麼電影演出來的情慾呢?它還是性嗎?它還隱身更撲朔的謎題?
我們談電影,不放映電影。薩所羅蘭邀請大家花一些些錢,來看我們創造不一樣的電影和精神分析的關係——不是用術語解剖或診斷電影人物,我們要在值得玩味的電影裡尋找出路,在臨床和非臨床之間,從診療室出發,走進電影世界,再走出來觀看臨床工作,替過渡空間創造出更多的想像。
與其說是「電影和精神分析」,或許說是「電影和臨床」更貼切。精神分析的論點,只是看事情的某種方式,這是我們的專業,但我們在此更要傳達的是,如何從電影學習看臨床,尤其是這三部以「憂鬱」為名的電影。
很多年前,精神分析領域曾有著一個疑惑,「在被分析前或被分析治療的過程裡,是否不能先閱讀精神分析的理論?」這個問題現在已經不是問題了,因為閱讀理論和實質體驗是兩件事,也就是,可以先看也可以不用先看,但是目前資訊取得便利,也許傾向是,大家都會先去閱讀相關資料。
而看電影這件事,我們將以精神分析的態度和理念,與它們對話,通常我們不會以正在上演的院線片作為對象,雖然我們不排斥這麼做。
你不必然得先看過這些電影,我們會說得讓你知道我們要說的,如果你事後想去看電影,那也很不錯,這或許代表我們已有了某種成功。我們在說故事的過程裡,一定會有一些些劇情爆雷,但是我們覺得,如果看電影只是因為某些爆雷就減損看電影的樂趣,這也怪怪的,難道電影只是劇情而已嗎?
作者簡介:
王明智|諮商心理師.小隱心理諮商所所長
陳建佑|精神科專科醫師.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師
王盈彬|精神科專科醫師.王盈彬精神科診所暨精神分析工作室主持人
吳念儒|臨床心理師.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師
陳瑞君|諮商心理師.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師
劉又銘|精神科專科醫師.台中美德醫院醫療部主任
劉玉文|諮商心理師.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師
蔡榮裕|精神科專科醫師.臺灣精神分析學會名譽理事長
章節試閱
《驚悚末日》:是喔,那麼情慾和什麼愛有關係嗎?
陳瑞君/諮商心理師
《驚悚末日》導演拉斯.馮.堤爾以幾個慢速而詭譎的畫面拉開序幕,女主角身上莊重的婚禮白紗是本片開場的主要意象,伴隨著背景音樂是華格納的《崔斯坦與伊索德》(Tristan And Isolde),連續不斷的「無限旋律」流轉出一幕幕同調性的召喚,低吟、低調、低沉,旋律緩慢且重複著懸疑氣氛,帶有近似音樂語言的「主導動機」(Leading Motive)。
「主導動機」,在樂理中指的是由人物、劇情及重複的概念運用,在樂曲當中,具有強烈戲劇暗示性的音樂片段不斷地襲捲重現,衝擊著聽覺的感受,因此,它總是帶有鮮明的「標籤」或「表徵」效應,用來暗示或揭示劇中,主角之情感發展,以及那不可見的地下情節。
第一樂章:女主角的「命運交響曲」,M(melancholia)小調激昂版
一開始,披著莊重優雅白紗的女主角賈絲汀慢速定調在一種永恆的意象裡,影片前奏的一幕像是女主角內在的一種魔幻寫實——遠遠的鏡頭,看到賈絲汀走在灰暗蕭瑟的杉木林裡,為了方便行走,她雙手撩高白紗的下緣,露出半截小腿大步邁前,看似正要趕往什麼重要的地方,賈絲汀堅定的心思意念在此刻全然顯露;然而,往下一看,白紗禮服下的小腿很快地被從地表竄出的粗壯如枯藤般的羊毛紗給圈住,愈來愈多的羊毛紗不留情的從四面八方而來,拉扯著賈絲汀的小腿、雙手,逐步延伸到勒住她的頸項,彷彿穿天遁地而至的強大力量,窒息般地阻止賈絲汀奔向幸福的企盼。
賈絲汀奮力想要掙脫羊毛紗,猶如拼著命想要逃離命運的枷鎖——在她與這個世界之間,似乎有一條難以言說卻緊密牽制的無形鎖鏈。在影片中的另外一幕,她好奇地伸出雙手端詳,雙手像是與宇宙中冥冥的什麼力量通電,一股電流好似暗示著,她與這個世界單獨且特別的關係。
那股拉扯賈絲汀的洪荒之力是什麼?又來自內在的哪裡?
賈絲汀愈是要邁開步伐,羊毛紗愈是像被觸怒的魔鬼,揮動著鋭利的爪子,愈狂怒地纏繞及吞噬;賈絲汀能遁逃出這個好似被咒詛的命運嗎?下一幕拉斯.馮.堤爾導演切換場景,跳tone轉換成宇宙中相互靠近的兩顆星球,代表Melancholia的藍色鬱星,在賈絲汀奮力逃離的同時,也逐步往地球端緩速靠進,終至與地球互相穿越而滲入地表;這個意象是否表徵身著亮麗婚紗、腳步堅定且加速前進的賈絲汀,邁向的不是幸福,反而是朝向對幸福的毀滅或侵蝕?
貝多芬的好友辛德勒,有一次問他說:「『命運交響曲』開頭的『登、登、登、登』四個音是什麼意思?」貝多芬回答:「那就是命運敲門的聲音。」在這裡藉用「命運交響曲」為標題,也同時在思考賈絲汀的命運又會如何被演奏和詮釋?劇中婚禮入場服務處,婚禮人員設計了「猜豆子摸彩」的活動,讓每位賓客報到後,抓一把豆子裝入一個瓶子中,賓客要提供一個數字,猜猜今天這瓶豆子最後的總數,婚禮結束前會公布最接近答案的人,優勝者並且可以得到獎項。賈絲汀當時瞧都沒瞧豆子就進入會場,但是,她就是知道答案——她一言不差的猜中,678顆。就好像賈絲汀也預知著自己的命運嗎?然而,誰會把命運設計成悲劇呢?難道如同伊底帕斯的故事,愈是奮力想要逃離的命運,卻每個選擇都再次帶自己進入命運的迴圈?賈絲汀找了一個高富帥又愛她的男友結婚,然而這個美好的企圖背後,為賈絲汀奏起的究竟是「命運交響曲」?還是「機會交響曲」呢?命運裡可以有機會嗎?
佛洛伊德曾說,「記憶」都是一種「遺忘」的變形,因為記憶常與「被禁止的慾望」有關,受到潛抑及喪失的,往往比真正記起來的還多,因而人持續性的精神生活總是用其它的型式來重新論述,就好像是常常變裝在重複那不知所以然的戲碼。人是不是很辛苦?佛洛伊德認為:
「人並不是因為他們的記憶受苦,而是因為遺忘而受苦,特別是以不當的方式去遺忘,這將會在行動中不斷的重回早期經驗的情緒場景,那是種喚醒心靈裡沉睡已久的部份,或許是段古老的回憶,一旦醒了,就無法再擺脫,只能不停地給予新的表達方式。」
如果人都像佛洛伊德所說的,透過行動不斷的重回早期經驗的情緒場景,那麼,賈絲汀要重回的是哪裡?想表達的是什麼?被羊毛紗圈住而難以逃脫的那一幕,宛如賈絲汀被動地接受命運擺佈的意象,她要重回的是這個場景嗎?人們一再重回早期的創傷場景,尋找受苦,如前文所述,是想再喚醒心靈裡沉睡的什麼。或許,賈絲汀受苦於不知從何而來的空洞及失落感的孤獨泥淖中,愈是努力掙扎,愈是無法逃脫而深陷;更像是早就失去了什麼重要東西而不自知,也不知如何找回——此刻的賈絲汀只能重複不停的悲傷了。
賈絲汀為何悲傷?佛洛伊德捕捉的場景 在《抑制、症狀和焦慮》(Inhibitions, Symp-toms and Anxiety, 1926)的附錄 C《Anxiety, Pain and Mourning》中,他這麼說:
「我們還不知道對失去某一客體的另一種情緒反應,那就是哀悼。但現在我們不再有任何困難來說明它。哀悼的發生受到現實感影響,因為後一種功能對失去客體的那些人,提出了絕對的要求,即他必須將自己與客體分離,因為客體已然不在。哀悼被委身一項任務,要在原先被那些客體高度貫注的所有情境中,將這種貫注撤回。與前面的觀點相吻合的是,這種分離會是痛苦的,因為,集中在對客體強烈渴望但卻不能滿足的貫注,失去客體的人必須在情境的重現中抵消(undo)他和客體連結的各種關係。」
由上面的論述來看,哀悼「需要撤回我們對失落客體的貫注,並重新抵消他和客體連結的所有關係。」然而,若早年的每一塊自我的形成都與主要依附對象有關聯,分離將會異常的痛苦,預告了這是一個無止盡的過程,因為人並沒有完全屬於自己,也沒有完全屬於他人,「人」本身的形成,基本上就是一種關係結合與變形的建構體,沒有人可以在不依靠他人的狀況下,長成獨立事件的自己,因而,可以視為是程度上的差別——生命早年的創傷可能不見得如一般預期的復原,甚至是難以完全康復,因此,我傾向假設,身而為人是無法有真正的哀悼(mourning),而是有著不同程度的憂鬱(melancholia)。
第二樂章:「英雄交響曲」A小調稍快版 /「堅定」的失誤
當年貝多芬的第三號「英雄交響曲」,原本是對拿破崙初期為法國革命的敬頌之曲,後來貝多芬得知拿破崙有稱帝之心,便大怒說:「他居然為了自己的權力慾望而藐視人權,想把自己抬升到萬人之上!」貝多芬憤而將此樂曲的標題頁撕成兩半扔在地上,並將曲名改爲:「紀念一位英雄人物」。
《驚悚末日》中的人物,若說到「堅定」,那個讓賈絲汀在古堡中舉行婚禮、面面俱到處理繁瑣事務、掌握所有婚禮進行流程的主持人——賈絲汀的姊姊克萊兒,看似也很堅定地想要掌握妹妹的人生節奏。當新娘與新郎姍姍來遲,到了結婚會場,所有賓客皆已入席久候,焦慮的克萊兒一見到下車的賈絲汀,便沒好氣的說:「我都懶得說你們遲到多久了。」她繼續急著數落:「你們還想要辦這場婚禮吧!」克萊兒堅定且急切地想讓賈絲汀順利完成婚禮,似乎希望將妹妹萬無一失地送入幸福的殿堂。既然是走向幸福,克萊兒為什麼會如此戒慎不安?克萊兒已經事必躬親,但她對賈絲汀的控制卻無法到位,因而讓她頗有微詞且慍怒,就像賈絲汀到達會場前,也有的許多小波折與插曲。克萊兒的堅定——在會場總是核對時程表、掌握著婚禮的進行、控制出場與換場秩序......,是否象徵她要在妹妹的婚禮上,尋找或創造自己曾經失去的東西?她要再度透過這個儀式,重新執政自己的人生?那些曾有的失落因此便能被撫平?然而過程是讓克萊兒一次又一次的帶來失望。而賈絲汀在婚禮上一連串的小失誤,只是因為不若姊姊般堅定嗎?
佛洛伊德在1904年出版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對「失誤」曾這麼說:
「生命中充滿了許多錯誤及意外,從性慾望的角度來看,確實都存在著意義,是由一種潛在的意圖充當主導者,以迂迴的方式達到被禁止的願望之目的。」
那麼,能說賈絲汀也如姊姊一樣的堅定,只是,她要堅定的走向失敗?而什麼是賈絲汀要重溫的失敗呢?
第三樂章:「田園交響曲」夢-熱情(Rêveries -Passions)/ 憂鬱又虛弱的序奏
貝多芬的第六號「田園交響曲」為「到達鄉郊,愜意的心情復甦了」,樂曲開頭的平靜、優美,漸漸變得積極、熱切,描繪了作曲家初到鄉間的感受。但曲子後面故意出現走調的音,此後速度加快,朝向奔放,隨即戛然而止,為緊接而來的風暴譜了前奏。
「想要幸福」的主旋律不只來自於姊姊,也來自於對眾人祝福的同聲嗎?被嚴重憂鬱籠罩的賈絲汀,也同樣地祝福著自己嗎?片中載著新人的禮車開往古堡婚禮的路上,加長型豪華禮車因車身過長而卡在前往的路徑,森林小徑的清幽與靜謐的田園,無法容下懷有巨大理想的幸福禮車?在一個小轉彎處,司機、新郎及新娘三人輪番上陣,接續握上這即將駛向幸福的方向盤;新郎下車認真用手勢指揮著車上正嘗試移動車頭的賈絲汀說,「哦!這裡......過來一點。」經過多次倒車、前進、指揮,花了多大的功夫,才抵達婚禮的會場。
隆重的加長型禮車是賈斯汀租的,困難地駛進田園小徑中,看似能計劃的方向,最後卻沒有被命運納入。新郎麥可隨後抵達婚宴會場,打情罵俏的向賈絲汀說:「又是誰說要租加長型禮車的?」
在名為「憂鬱」的主題下,賈絲汀的種種的矛盾選擇——加長型禮車、新人大遲到等等的跡象皆顯示著這是一場「難以抵達的幸福」的婚禮前奏,加長型禮車的場景像是一種戲謔,也帶來一種奇怪的愉悅?然而究竟是什麼理由,會使人不斷的從重覆錯誤中得到痛苦,並忍受它呢?佛洛伊德說「我們被迫要去思考自我中那神秘的受虐傾向。」(1920:14),這充滿著受虐般的荒謬。關於受苦,佛洛伊德《受虐的經濟學問題》(The Economic Problem Of Masochism)裡這麼說:
「回到受虐。我們觀察到受虐有三種形式:作為一種強加於性興奮的條件,作為一種女性本質的表達、作為一種行為規範。因此,我們加以區分為自體情慾的、女性的,道德上的受虐。第一種是自體情慾的受虐——在痛苦中的愉悅感——它亦是另外兩種形式的基底根源。這需要從生物學和體質上的路線來尋求其基礎,目前這個部份仍然如此無法理解,除非你決定對事物做出一些極其模糊的假設。第三種,在某些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受虐的表現形式直到最近才被精神分析確認為一種主要是潛意識裡的罪疚感;它已能被解釋,並與我們的其他的知識相吻合。另一方面,女性受虐是最容易被我們觀察到的,也是最不具爭議性的,它可以從所有關係中加以考察。我們將從它開始討論。」
第四樂章:「驚愕交響曲」(the Surprise Symphony)/ 定音鼓強奏恬淡的《田園交響曲》後,接下來賈絲汀的父母上場,我點一首海頓第94號《驚愕交響曲》呼應。據聞當年某些貴族為了附庸風雅前來聽音樂會,卻常常在演奏時睡著了,海頓於是譜了這首曲子,在前面弱起拍像是催眠的樂章,剎那間用定音鼓模仿驚雷般猛烈地敲擊,讓這些呼呼大睡的貴族猛然嚇醒。
「想要幸福」的主旋律是否不只來自於姊姊,也來自於她們的父母?或許她們的父母原先是這麼想的,因為他們都出席女兒的古堡婚禮,只是兩人是水火不容的仇家,即使已經隔著幾桌之遙,但劍拔弩張的氣氛一觸即發,失控似乎是必然的命運。兩人身為女兒的主婚人,然而他們顯然並不是那麼容易地能讓幸福買單。
看似玩世不恭的爸爸在婚禮會場,一焦慮起來就開始躁動不安,他在同桌女賓客的面前,故意弄掉一根又一根的湯匙,戲弄著服務生,一次又一次叫喚他們過來,指著旁邊的人說:「她們要湯匙。」他耍著令人難以理解的冷場把戲。賈絲汀的媽媽雖然不與前夫同桌,卻暗暗觀察著坐在別桌的前夫,一會兒,她終於忍無可忍,向賈絲汀憤怒且尖酸地發出牢騷,她冷冷地說:「賈絲汀,幫我甩妳爸一巴掌!」當媽媽對賈絲汀如此抱怨時,完全漠視坐在她們母女中間,小孫子Leo的存在;如果在小孩面前什麼難聽話都可以說,那麼,賈絲汀母親的心裡,是否有所謂的「小孩」存在?
對於媽媽這種舌尖上的毒辣,及關係的張力帶來心理上的興奮或潛在的愉悅,讓人想到法國思想家羅蘭.巴特的說法:
可能沒有什麼比愉悅(plaisir)更具文化性、因而更具社會性的了。在此,愉悅與痛快(jouissance,或譯「絕爽」)相對立。文本的愉悅與整個文化教養聯繫在一起,或者說,與一種契合、融入的情境聯繫在⼀起(一個深具代表性的片段:年輕的普魯斯特,把自己關在飄著鳶尾花香味的洗手間裡讀小說,他把自己與世界隔絕開來,籠罩在一種天堂般的環境當中)。相反地,文本的痛快,是反空間性、反社會性的;它以一種不可預期的方式發生在文化、語言的種種系列當中:沒人能解釋自己的痛快,沒人能對痛快進行分類。
或許在意識上,我們不容易從母親的憤怒中,指明她得到了潛在的愉悅,但難道不能說,這亦是一種沒能解釋的痛快嗎?這種高張力的氣氛,循著佛洛伊德對於「興奮」的定義是一致的,雖然外顯上是不愉快和生氣,但從神經學和能量學來說,都是在增添柴火,都是讓神經系統的刺激被增生而有神經興奮的傳遞,這有著生物學的基礎。
電影的另一幕,賈絲汀的父親為女兒證婚致詞時,話中總是藉機出言挑釁原本就怒火中燒的前妻,他對眾賓客說:「我該說些什麼才不會提到妳媽呢?不過這也不是什麼秘密,......她有時實在是很專橫跋扈!」父親似乎也等著這一刻,要好好地修理前妻。媽媽面對前夫公開羞辱,感到憤怒與不甘示弱,亦以主婚人的身份起身反擊,她也對著所有賓客說:「我不相信教堂,也不相信婚姻!」賈絲汀父母的證婚詞,在婚禮上註解了最尷尬、不堪與反諷的場景,所有的賓客毫無選擇地捲入了這風雨欲來、兩人角鬥的關係中。
賈絲汀在婚禮進行到了現在,又一次受到父母聯手帶來傷害,想必內心再度碎裂成片片,不過,這恐怕也不是她第一次被雙親摔碎吧?電影接下來,媽媽很快閃離會場,躲到樓上的客房去泡澡,直到被女婿約翰(克萊兒之夫)邀請下樓切結婚蛋糕。但是她憤然拒絕下樓,她對約翰冷淡且嘲諷地說:「賈絲汀第一次用便盆時我不在,她的性愛初體驗時我也不在,所以,少拿這些婚禮的鳥儀式來煩我!」
媽媽的這些話,陳述了她與賈絲汀的早年故事,或許對賈絲汀而言,「媽媽」這個重要客體一直都是缺席的;她一再地缺席/被缺席,跟賈絲汀缺乏連結。Adam Phillips在《調情》一書寫道:
「唯有透過缺席所造成的空間,才有可能理解自己的想像及渴望。當一個人缺席的時候,就是我們認識她的時候。」
這似乎也暗喻著「失落」——某種一個人在心裡上隻身的時刻,透過想像,反而是與缺席的客體最為靠近的位置;我們在心理上臨摹這個不存在者的存在,在心裡上描述一個客體經驗,我們開始用語言一字一句堆疊起個人的想像。克麗絲提娃在《黑太陽、抑鬱及憂鬱症》說:「如果我不接受喪失我的母親,我即無法去想像她,也無法為她賦名。」(p.164)
第五樂章:「復活變奏曲」(Resurrection)莊嚴的咏嘆調 / 來自荒野的呼喚
取於馬勒的第二號交響曲《復活》的典故,首段樂章為葬禮的場景並叩問:「有無死亡後的生活?」;第二樂章是已故者對生活快樂時代的回想;第三樂章則代表完全喪失信心,信任生活是毫無意義的。
被父母頻澆冷水的婚禮,賈絲汀是否可以在死亡後復活?「做自己」是一種復活嗎?這是內在荒野的呼喚!雖然賈絲汀走向的是,堅定地毀滅婚姻和投身工作之路,她一路無畏地走過去......。
當提到「失落」和「憂鬱」(melancholia)時,若將「受虐」的概念加進來思考,我們腦中浮現的可能是擔憂這樣的想法,是否會被視為在污名或攻訐憂鬱者?「受虐」一詞常帶有負面評價,有因果連結,讓人抗拒接受;當這樣的擔憂出現,「受虐」的概念便無法被納入溝通的語言,探索它存在的意義及現象也受限了。只有在不把它們當作是負面的意義時,討論的自由度才可能增加,讓「受虐」變成可以被溝通的概念,這尚有待我們努力發展。
樂曲分析中,所謂的「變奏」,意指在特定的主題或音樂素材上,以各種方式加以變化進行。賈絲汀原先在姊姊期待的「幸福主題曲」上相應和聲,享受嬌滴但品嘗起來極其虛幻的果實,這顯然沒有辦法讓她感到飽足。賈絲汀接下來蠢蠢欲動地加入不少個人的樂思——可以稱之為「賈絲汀的復活變奏曲」,樂曲從精巧到磅礡、恬靜到哀傷、節制到野放,或許這些才是滿足她個人心理現實的養份?
幸福的spy賈絲汀,她的內在的確有一股幻於無形的堅定,像是莫名地被揀擇的人選,接受指定交辦生命某個潛在的秘密任務。賈絲汀時而沐浴在粉紅泡泡中,努力地配合幸福人妻的主旋律,時而又像是被間碟植入某種惡意病毒的晶片,受許多暗示性的(潛意識)任務控制著——探測的是「幸福的不可能性」。
賈絲汀的無言行動,讓她像是個脫軌的新娘;在婚禮流程遲了2小時的狀況下,姊姊急迫地要將這對新人送進賀賓枯坐許久的婚禮會場,才快走兩步,賈絲汀突然拉著新郎轉向,她說:「我們先去馬廏,去跟亞伯拉罕打招呼。」到了馬廄,賈絲汀對著愛馬介紹著新歡,是否像是宣告著舊時代的結束,新世紀的來臨?賈絲汀輕撫著亞伯拉罕說:「麥可現在是我老公了。」這句話彷彿是在跟過去切割,跟自己的痛苦道別。
然而整場婚禮中,賈絲汀多次藉機離席,扮演落跑新娘的角色;她獨自默默離開婚宴,留下等待的賓客,也拋下尷尬的新郎,讓焦慮萬分的姊姊及姊夫硬著頭皮撐場。之後賈絲汀靜悄孤身回到樓上的新房,慢條斯理褪下那沈甸甸、綁綑著自我的禮服,她全身赤裸,悠哉地泡在浴缸裡,這場幸福的婚禮好似與她無關——她總在分離與融合間徘徊,在主動與被動間來去,結婚進行曲的主旋律奏起時,賈絲汀心裡奏起的是救贖還是毀滅?我們或許只能在賈絲汀的行動中,看到她暗暗以個人意志埋下的種子,作為演出的和絃,並且愈奏愈大聲,愈來愈搶拍......。馬勒的《復活變奏曲》也像是為賈絲汀而作:
「世界與生命成為雜亂的幻影,厭惡所有的存在與握緊拳頭,當您意猶未盡似地從第二樂章的夢中醒來,不得不回到錯誤複雜的人生時,你們常常會感到人生在不停地流動著,不時有莫名的恐懼向你襲來。那就像是你們從外面黑暗的地方,站在聽不到音樂聲的距離眺望時,看到明亮的舞會中舞者們搖動般。人生不知不覺地出現在你們眼前,這就像你們經常被惡夢驚醒過來一樣。」(林衡哲)
第六樂章:「悲愴交響曲」(Патетическая/Patetičeskaja)憂傷的慢板 / 暗淡絕望的音色
憂鬱的靈光閃現是音樂家最美的特權,「悲愴交響曲」蘊涵著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各種能語與不能語的壓抑與渴望,這是柴可夫斯基有生之年的最後作品。《悲愴》淒涼美麗,一路哀吟,與他的人生一同悲劇性謝幕。柴可夫斯基曾說,「悲愴」一曲是人世間共享的情緒......這同樣震撼著人們的心弦。
劇中,女婿約翰上樓尋找賈絲汀的媽媽,媽媽似乎和賈絲汀心意相通,也在自己的房裡泡澡。約翰受到丈母娘冷淡拒絕,她不願意參與配合婚禮正在進行的任何儀式。約翰悻悻然回到婚禮現場,怒不可遏的在妻子耳邊低語:「她們兩個賤貨都躲在房裡還泡起澡來......,你們一家都是神經病嗎?!」妻子聽了眉頭緊皺,脫序的樂曲已讓她不知如何是好。
相對於約翰的憤怒,賈絲汀與母親各自浸泡在自己的浴缸中,彷彿脫下一身不合宜的外衣,回到最原始的、最赤祼的狀態,沐浴在原初的自己裡。這樣的場景,恍若是媽媽懷著賈絲汀時,母女一同泡在同一個身體裡的羊水,是如此地的融合相近!諷刺的是,現實裡並非如此。
即使媽媽冷漠以對,像是被全世界拋棄的賈絲汀,最後還是跑到媽媽的房裡,沮喪垂淚對媽媽坦露說:「媽媽,我很驚恐。」媽媽冷冷回答:「這不是妳該來的地方,妳不該來,我也不該來。賈絲汀,妳別作夢了。」賈絲汀掏心掏肺,卻換來媽媽最後絕情的命令:「滾出房間!」
也許,在賈絲汀心裡仍是無法承受失去媽媽的事實,賈絲汀能做的,是以自己的方式選擇用「像她」來靠近她;賈絲汀保持泡澡的習慣來跟媽媽一樣,這樣她就可以像媽媽且忠誠於媽媽了。她用「像」,表達心裡上抗拒跟媽媽的別離及切斷。亞富尤的《當影子成形時》一書中提到:
「缺空激起了心靈的活動,使心智化、象徵化成為可能,以面對閹割焦慮。想像中的再度掌握和精神上分離經驗的轉化,促使再現的活動出現,從而取代了赤祼的、被現實迫使的、原本被動忍受的悲傷狀態。然後,各式各樣的幻想劇本啟動了,從被遺棄中得到一種被虐的滿足,這被遺棄的狀態本身成為了挹注客體,並取代了失落客體,甚至成為認同式的角色對調,以此確保能掌控分離。失敗的主體和失落的客體以某種方式交換了他們想像的角色和位置;被遺棄者使自己成為遺棄者。」(p.16)
受到媽媽強行拒絕推開的賈絲汀,似乎也不知要走到哪裡去?賈絲汀顯然是匱乏的,接近一種客體失落的樣態,包含了精神上及情緒上被擊潰的痛苦。當她回到眾聲喧嘩的舞會當中,與新郎攜手上樓,兩人火速地親熱了起來,卻在最後關頭,賈絲汀不知為何急踩煞車,她再次落跑,丟下身著內褲且頹坐在床邊的新郎在房裡守候。賈絲汀離開新郎後,大步往曠野走去,野放了自己,某一刻不知怎麼地,她突然在草地上推倒一個行進中的男人,粗暴地拉下他的拉鍊、掏出他的陽具,她抱著新娘禮服跨坐在這個男人身上,開始自顧自地搖晃起來;路過的男人彷彿無端地被賈絲汀充滿怨恨或悔恨的情緒,大力地凌辱。或許對賈絲汀而言,強暴的行動既是連結也是撕裂,她再度將自己留在一個陰鬱的空洞和黑影中,把性愛當作是一種對幸福之路的發洩與復仇。
從「愉悅」的概念來說,當潛在的刺激興奮被挑起來時,就需要宣洩。賈絲汀從小到大的憂鬱狀態,乍看好像是什麼都不在乎的行為,其實是充盈著受苦的經驗,那些因失落、空洞而存在的受苦,常是以潛在的罪惡感的型式變裝,這是一種源自於內在的刺激與興奮,因此,有時會以不可思議的方式來宣洩。賈絲汀和陌生人性交,不同於一般人是為了愉悅而做,她是為了解決因罪惡感所帶來的刺激後,以強力性交的方式來宣洩排解掉這樣的衝突,因此也可以說,賈絲汀是無情的。
賈絲汀親手破壞了自己的婚禮,這一切都達到了賈絲汀想要的了嗎?她終結這場如釋重負的自我逼迫,回到自己想要的,也是父母帶給她的失落和被遺棄的經驗?最終賓客不歡而散,心理上受到很大傷害的新郎也無言地走了,至此,殘破不堪的婚禮滿地碎片。賈絲汀此刻卻像是把所有事情辦妥了似的走向父親的客房,無人應門,父親在床上留下隻字片語:「有人要送我回家,我無法拒絕。」他一聲不響地離開了。爸爸的拒絕回應,使得賈絲汀的效忠沒有主人,她再度被遺棄。
阿莫多瓦的電影《痛苦與榮耀》中,主角薩瓦多描繪身體感受到失落和抑鬱的反應,可以作為我們想像賈絲汀的孤獨和受苦情境:
「『失眠、慢性咽喉炎、中耳炎、胃食道逆流、胃潰瘍、全身神經痛、尤其是坐骨神經痛,身體各部位的肌肉疼痛,腰痛、背痛、肌腱炎、雙膝雙肩疼痛。耳鳴、氣喘、哮喘。各種頭痛、長期背痛,還做過脊椎融合手術,後背一半以上不能動。脊椎與肌肉就像希臘諸神,需要彼此犧牲才能連結。』除了可以具體描繪感受的痛苦,也蒙受許多抽象的痛苦;如恐慌、焦慮,使心蒙受苦難,為我人生帶來煎熬與驚恐,因此憂鬱症與我共存多年。」
薩瓦多個人排山倒海的疼痛歷史,讓人不禁咋舌,各色疼痛宛若宏大的身心交響曲,鋪陳出主角獨特的生命史詩。他說:「在各種痛苦襲來的夜晚,我相信上帝並向祂祈禱,但僅有一種疼痛襲來的日子,我是個無神論者。」這讓人不禁玩味,究竟是哪一種痛苦呢?這種痛苦竟然超出神祇管轄的範圍,彷若被棄置,只能獨自承受,無人能知 、無人能解。
這種無人能知、無人能解的痛苦,是臨床常聽到的說法,也是臨床難解的課題。在這種感受下,個案很難描繪自己的感受,甚至也不知要表達什麼,好像「無人能知、無人能解」這個說法,就是最貼近心情的語詞。然而這種概念下,有著排斥他人的意味,讓周遭的人在他的心裡,輕易地變成了無人狀態。精神分析認為身心是個連續的光譜,會交互投射,容受彼此想要傳達的訊息。很多因為身體痛苦前來求診的病人,會被轉診至分析治療,即是意味著身體痛苦背後的心理訴求。
佛洛伊德在《記憶、重複與修通》(Remembering, Repeating and Working-Through)一書中寫道:
「病人不記得任何被他遺忘或潛抑的重複,他們以行動表現出來,以行動而非記憶的形式來再現,當然這些重複是他自己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進行的。」
最終回:「幻想交響曲」(Symphonie fantastique)女巫安息日的夜夢(Songe d'une nuit de sabbat)/怪物歡呼
賈絲汀想要效忠的人最後都離開了,最終留下來的是原初的離散與拒絕,她又再次回到那個熟悉的、空蕩蕩的,自我認同的客體失落感受裡,這也是自我的離散和失落。賈絲汀彈奏出那首被催毀殆盡的人生奏鳴曲,終至徹底捏碎了結婚進行曲的本質,改弦易轍,譜出個人另一個悲傷又傷人的魔幻樂章。
《驚悚末日》:是喔,那麼情慾和什麼愛有關係嗎?
陳瑞君/諮商心理師
《驚悚末日》導演拉斯.馮.堤爾以幾個慢速而詭譎的畫面拉開序幕,女主角身上莊重的婚禮白紗是本片開場的主要意象,伴隨著背景音樂是華格納的《崔斯坦與伊索德》(Tristan And Isolde),連續不斷的「無限旋律」流轉出一幕幕同調性的召喚,低吟、低調、低沉,旋律緩慢且重複著懸疑氣氛,帶有近似音樂語言的「主導動機」(Leading Motive)。
「主導動機」,在樂理中指的是由人物、劇情及重複的概念運用,在樂曲當中,具有強烈戲劇暗示性的音樂片段不斷地襲捲重現,衝...
作者序
【推薦序】
見血見骨,這是憂鬱?
李俊毅/高雄長庚醫院精神部身心醫學科主治醫師
若說「憂鬱」是情慾與激情堆砌而成,甚至充滿暴力與誘惑,這樣的說法有沒有顛覆大家熟知的「憂鬱」?拉斯.馮.提爾(Lars von Trier)大費周章拍了三部電影:《撒旦的情與慾》(Antichrist)、《驚悚末日》(Melancholia)以及《性愛成癮的女人》(Nymphomaniac),組成「憂鬱三部曲」(Depression Trilogy),用來述說一個駭人聽聞、簡直離經叛道版本的「憂鬱」;然而,驚悚(uncanny)倒是正好催促我們用更寬廣、更另類的視角,重新審視再熟悉不過的「憂鬱」。
在《驚悚末日》中,拉斯.馮.提爾讓華格納《崔伊斯坦與伊索德》的〈愛之死〉(liebestod)旋律不時響起,象徵相愛的兩人是透過一起死亡(dying together)才算永久結合。人的生命畢竟是生命本能與死亡本能之間的纏鬥或是纏綿的過程,代表愛與性的愛神(Eros)與代表痛苦與死亡的死神(Thanatos)經常換臉變身,幾度錯身而過,終究合為一體。
彭大歷斯(Jean-Bertrand Pontalis)這位內裡外在充滿文學涵養的精神分析學者,在最近發行的《潮起潮落》中提到一個奇特現象:夫妻兩人參加一位摯友的葬禮,心情沮喪得想跟隨好友長眠墓底,隨後又跟朋友一起喝酒追憶離世的摯友。晚上回到家,兩人卻被狂暴難耐的做愛慾望佔據。彭大歷斯說,交歡也許是為了驅退死亡,也可能藉此體驗死亡。不管怎樣,愛神(Eros)無論如何必須保持清醒,否則自我必將灰飛煙滅。這是詮釋?還是嘲諷?難不成憂鬱到了極致,便以性愛召喚愛神降臨?
類似的場景也出現在《撒旦的情與慾》。夫妻兩人失去意外身故的兒子,妻子陷入重度憂鬱,丈夫的自戀高漲,性愛竟成了兩人解決創傷性失落的方式。拉斯.馮.提爾在影片一開始就用慢動作將孩子墜地瞬間與夫妻性愛高潮同步,根本上已經將死亡與性愛緊緊環扣,接下來就是考驗觀影者有沒有能力解讀這個關聯性了。這情節不難讓人想起王爾德筆下的莎樂美為希律王跳完七紗舞後,狂舔作為恩賜的施洗者約翰鮮血淋漓的頭顱,那種死與愛交融的詭異畫面,令人不寒而慄。《撒旦的情與慾》的後半,當憂鬱的妻子轉而對丈夫行動化,她出現潛抑許久的閹割、暴力、謀殺等施虐本質的混亂行徑,此時我們才豁然開朗——憂鬱的本質果真是一種自戀性精神病態;這部份佛洛伊德已經在〈哀悼與憂鬱〉一文中剖析得淋漓盡致。
憂鬱的源頭畢竟是創傷,既然是創傷,必然是無可抗拒的強迫式重複。從影片中,我們無法真確得知《性愛成癮的女人》中的喬(Joe)早年受到何種創傷,但是從喬窮其一生陷入無限迴圈、無法自拔的性成癮,暗示喬在性的領域中試圖克服早年不易證實而且隱晦的創傷,早年「性創傷」的可能性因此浮上檯面。父女之間智性而曖昧的對話一再出現,正是一種誘惑,醞釀著日後亂倫幻想的行動化。憂鬱的喬,受虐與施虐特質交替出現在她的生命歷程,周遭所有人毫無例外成為滿足她性需求的客體,即使作為假性治療師(pseudo-therapist)角色的塞利曼,最終還是難逃潛抑一輩子的性衝動而遭致殺身之禍——飽讀詩書與滿腹經綸原來只是知識層面的防衛。同樣的,《撒旦的情與慾》中陷入精神病態的妻子,是否也可依此想像?當然,《驚悚末日》中的Justine又未嘗不是?
當年作為逗馬宣言一號作品《那一個晚上》(The Celebration),湯瑪斯.凡提伯格(Thomas Vinterberg)精心安排,在隆重的生日宴場合揭露家族性醜聞的手法,讓人驚嘆不已。如今,隱含著對凡提伯格的致敬,拉斯.馮.提爾採用更蒙太奇、更隱喻的手法拍攝《驚悚末日》,這次情節則是離異的雙親在女兒Justine的結婚喜宴中,行動化早年家庭衝突的情境,如此強迫性重複想必持續不斷地困擾著Justine,不斷將她拉回不堪回首的早年創傷情境中,讓慢性化的憂鬱活化又淡化,生生不息。當愛神火力全開,死神不會保持沈默,它的毀滅本能才會展露無遺。《驚悚末日》第二部的世界末日
情境,讓人想起佛洛伊德的史瑞伯(Schreber)案例,憂鬱者的內在世界原來也如妄想者般具有強烈的毀滅性!
不管愛與恨,生與死,施虐與受虐,佛洛伊德將人類本能(或是驅力)二元化(dualism),生命本能與死亡本能皆無法輕易與性能量力比多(libido)脫鉤。憂鬱狀態,力比多自客體撤回自我,形成一種次發性自戀,滿溢的力比多性能量,表現為性愛、攻擊、毀滅、施虐、受虐,有何不可?
【自序】
「憂鬱三部曲」:開場白
蔡榮裕/臺灣精神分析學會名譽理事長
其實是很暴力的過程。這種暴力的起源和目的是什麼呢?導演拉斯.馮.提爾(Lars von Trier)透過暴力和性的聯結所帶來的衝擊,也許可以說是某些人的內心戲,或者如夢的展現?只是夢不會如此完整,但電影裡的故事有完整嗎?劇中仍是破碎的經驗,如果我們依著導演的角度來談論「憂鬱」,是否會讓被如此診斷的人覺得污名化呢?覺得怎麼會有這樣的憂鬱呢?一般來說,憂鬱不是都顯得絕望和無力感嗎?我們假設導演的想像和演員的表演是廣義的「憂鬱」的一環,藉由這些電影,讓憂鬱的內心戲呈現在大家眼前。
如果要說,還是得說,這真的很暴力!就算平時我們會呼籲:「不要畏懼憂鬱、不要因此而害怕就醫。」只是什麼是憂鬱?從一般的情緒到嚴重到想要傷害自己而需要住院,這中間是如此寛廣,範圍如同光譜般,我們相信這是實情。
「憂鬱三部曲」:《撒旦的情與慾》、《驚悚末日》與《性愛成癮的女人》,它們是廣大光譜裡某段頻率的光吧?這個頻率可能如紅外線或紫外線般,是「之外」,是眼睛無法看見的光譜,它就存在那裡,我們嘗試以深度心理學做工具,親身來見證它們在吶喊。
我們不是只想定義它是性或暴力,而是想要跟它們對話,幫助我們了解我們的臨床實務。佛洛伊德說過,有些詩人對於人性的了解,可能勝過精神分析者。而我在這裡補充,有些電影導演、小說家、劇作家或其它的創作者的了解也可能如此,但是我這麼說時,一點也不覺得「精神分析取向者」會有被取代的擔心。
我們不是以「什麼是憂鬱」下診斷,而是以這是「人性一部份」的角度來書寫。導演在憂鬱症後拍攝的「憂鬱三部曲」電影,如同佛洛伊德在父親死後的自我分析而寫出《夢的解析》。我們就以「憂鬱三部曲」如《夢的解析》的平行想法,來寫我們的「憂鬱工作坊」——透過三部曲的影像、音樂和情節故事,讓我們了解和想像潛意識裡的某些層面。
佛洛伊德的知識生產有部份是以「症狀」和「夢」相互對話而建構起家,如果我們以臨床經驗跟電影裡的所見所想(廣義的『反移情』)對話,包括和臨床常見現象相同或不同之處,都是可以討論的——何以同?何以不同?是否還有什麼可以多思考的?
性活動是生之本能的驅動,但我們需要說明,何以有著不同的表達方式,以及何以有人會走到完全無力感,而變得性慾望全失?
比喻上,假設人都是從失落死亡的深淵裡回來,有人回不來了,而回來的人如何再活著和走下去?也許可以說這是溫尼考特(Winnicott)的「真我」(一堆活生生的能量),透過各式防衛的需要而不得不建構出「假我」,但「真我」也要滿足自己,那麼「真我」和「假我」的妥協是什麼?
請各位仔細品味以「憂鬱三部曲」為題材的文字宴席,我們從精神分析取向專業職人的角色,展開有趣的深度心理學探索之旅。就算你不曾看過這三部電影,我們相信你也能從我們的文字裡,窺見精神分析和電影巧妙互動的成果。
【推薦序】
見血見骨,這是憂鬱?
李俊毅/高雄長庚醫院精神部身心醫學科主治醫師
若說「憂鬱」是情慾與激情堆砌而成,甚至充滿暴力與誘惑,這樣的說法有沒有顛覆大家熟知的「憂鬱」?拉斯.馮.提爾(Lars von Trier)大費周章拍了三部電影:《撒旦的情與慾》(Antichrist)、《驚悚末日》(Melancholia)以及《性愛成癮的女人》(Nymphomaniac),組成「憂鬱三部曲」(Depression Trilogy),用來述說一個駭人聽聞、簡直離經叛道版本的「憂鬱」;然而,驚悚(uncanny)倒是正好催促我們用更寬廣、更另類的視角,重新審視再熟悉不過的「憂鬱」...
目錄
目錄
自序|【薩所羅蘭】精神分析的人間條件 薩所羅蘭
推薦序|見血見骨,這是憂鬱? 李俊毅
「憂鬱三部曲」:開場白 蔡榮裕
《撒旦的情與慾》誰的憂鬱周旋在情與慾裡浮沈? 王明智
《驚悚末日》憂鬱的心聲如何拐彎抹角說自己? 陳建佑
《性愛成癮的女人》這真的和憂鬱有關係嗎? 王盈彬
《撒旦的情與慾》好吧,讓我們一起來認識情和慾! 吳念儒
《驚悚末日》是喔,那麼情慾和什麼愛有關係嗎? 陳瑞君
《性愛成癮的女人》天啊,強迫式的重複竟是喧囂的癮! 劉又銘
「憂鬱三部曲」:我們談電影,為了臨床想像和認識自己 蔡榮裕
附錄一|浮沉在慾海中的天使在哭泣 劉玉文
附錄二|「憂鬱三部曲」工作坊文宣 薩所羅蘭
【薩所羅蘭】團隊簡介
目錄
自序|【薩所羅蘭】精神分析的人間條件 薩所羅蘭
推薦序|見血見骨,這是憂鬱? 李俊毅
「憂鬱三部曲」:開場白 蔡榮裕
《撒旦的情與慾》誰的憂鬱周旋在情與慾裡浮沈? 王明智
《驚悚末日》憂鬱的心聲如何拐彎抹角說自己? 陳建佑
《性愛成癮的女人》這真的和憂鬱有關係...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3收藏
3收藏

 9二手徵求有驚喜
9二手徵求有驚喜




 3收藏
3收藏

 9二手徵求有驚喜
9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