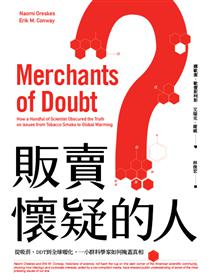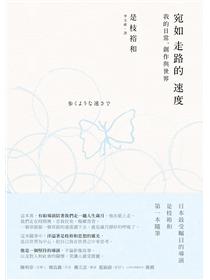當親耳聽見母親說:「如果我不值得活了,你要幫助我解脫。」
該如何抉擇?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思考死亡就是思考生命。」
面對「送母遠行」的生死之約,最後一段旅程該如何陪伴;
當生命僅餘痛苦,人們是否有自主善終的權利!中村醫師在《大往生》一書中以科學和理性的角度描寫了自然死亡的無痛與安詳,海倫.聶爾玲(Helen Nearing)在《美好人生的摯愛與告別》(Loving and Leaving the Good Life)中以智性和感性的筆觸描繪禁食而亡的平靜與自然。我在閱讀他們的作品中,體驗到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不再是令人恐懼、悲傷的,甚至可以欣然的去迎接,因為那是一個奔向自由的過程。
對所有家人而言,母親在她人生的最後一哩路,幫我們上了一堂寶貴的生死學課程。讓我們見證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死亡可以是安詳平和的,對死亡不再有未知的恐懼,懂得珍惜、善用活著的時光,不要有遺憾,勇敢面對死亡。
——畢柳鶯
●感動推薦
王美霞(南方講堂創辦人)
平路(作家)
江盛(婦產科醫師,安樂死立法推動者)
李崇建(作家,資深生命教育工作者)
周志建(資深心理師,故事療癒作家)
洪仲清(臨床心理師)
畢恆達(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陳耀昌(醫師,《傀儡花》、《島嶼DNA》作者)
賴其萬(和信醫院醫學教育講座教授)
蘇絢慧(諮商心理師)
(依姓氏筆劃排序)
●關於本書
藉著我的筆,母親繼續精采的活著。
母親擅長瑜珈,在家積極復健,於八十三歲時惡化到日常生活完全無法自理、不會翻身、進食容易嗆咳的地步。因為生命失去了意義,每日要忍受各種痛苦與不便,病情只會更急遽惡化,選擇斷食自主善終。經過三星期的漸進式斷食後,在家人的陪伴中安詳往生。我帶著忐忑的心情陪伴、照護……
——畢柳鶯
行醫超過四十年的畢柳鶯醫師,親耳聽母親說:當我不值得活了,你要幫助我解脫。
母親家族有小腦萎縮症病史,這是一種小腦退化的遺傳性疾病,目前尚無有效治療藥物。二○二○年冬天,畢柳鶯帶著行李,從台中自宅前往一小時車程的台北娘家,赴一個最遙遠的生死之約。六十五歲的她,展開行醫以來最奇幻的一趟旅程──陪伴八十三歲的母親斷食,走完人生最後一哩路……
這是母親教導她的最後一堂生死課。
現代社會有許多意外、疾病以及醫療的介入造成越來越多的人失去意識、重度癱瘓、依賴維生系統而沒有意義的歹活著。當生命僅餘痛苦,不再有樂趣,且造成家人和社會的重大負擔時,人們是否有自主善終的權利?
畢醫師說:死亡的過程也是醫療的一部分。
書寫此書的目的,是分享母親積極面對疾病的樂觀與毅力、豁達面對死亡的勇氣與智慧、斷食善終的過程以及家人支持的重要。斷食善終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凸顯尊嚴善終法立法的迫切性。……希望喚起更多民眾的注意,平時就討論死亡議題,為善終作準備。並督促政府以及醫界順應民意及世界潮流,通過尊嚴善終法案,讓台灣成為更具有人道自由的國家。
全書從畢柳鶯醫師母親的身世、母親家族遺傳的小腦萎縮症,到母親如何勇敢面對死亡;也從如何幫助母親斷食想法的由來、陪伴母親斷食善終的歷程,到探討台灣現階段有關善終議題的現況以及可以再努力的空間。畢醫師將這些歷程與思考,一段段特殊的學習經驗,以醫者和女兒纖細的觀察,娓娓道來……除了有感性的故事,更有理性的探討。
讓我們不只是讀一個感人的故事而已;從此刻起,讓我們一起為自己及家人的生命尊嚴,慎重思考,並且付諸行動。
●特別撰文推薦
這本書提供了有血有淚、有情有義的如何在「小我」的立場為摯愛的母親完成「善終」的心願,又能有條有理地整理出這麼豐富的國內國外的資料,影響「大我」的台灣社會。本書堪稱「情」、「理」、「法」三者兼顧的好書!——賴其萬
畢醫師這本新書,她的弦外之音,隱藏不能再浪費時間,不管是公投或立法通過死亡權利法案,尊重意識清楚,無法治癒,痛苦難受患者的自主願望與權利。——江盛
在有限的生命裡,活出有尊嚴、負責任的每一天。生是偶然,死是必然。母親對於死亡的坦然,實是寶貴的一課。——畢恆達
面對生死、臨終陪伴,很不容易。感謝畢醫師出這本書,我想,這本書會是將來無數個家庭去面對家人重病、臨終時,最好的臨終陪伴寶典。——周志建
這是一本生命教育之書,也是精采的家族歷史,從個人的生命遭遇,關注個人的生命史,充滿人性的關懷,將生命視為整體,充滿療癒的能量。對於台灣社會,對於生命的眼光,都是一本重要的書。——李崇建
作者簡介:
畢柳鶯
臺灣大學醫學系畢業。曾任台中市立復健醫院院長、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教授,目前擔任衛福部台中醫院復健科資深教學醫師。就讀小學時就感受到男女不平等、社會中的弱肉強食,因此喜好打抱不平。擔任復健科醫師是正確的選擇,養成不是只看見疾病而是全人照顧的素養。感謝所有我服務過的病人及家屬,他們的脆弱、受苦、堅強與韌性,給了我許多啟發與力量;也感謝復健團隊中所有成員無私熱情的協助。
喜歡藝術、旅遊、攝影與閱讀。二○一一年開始在部落格《阿畢的天空》撰文分享生活心得,累計五百篇文章,並著有《醫步醫腳印》一書。
阿畢的天空:http://bee1955.blogspot.com
Email: libih1955@yahoo.com.tw
章節試閱
引言/
思考死亡與面對死亡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思考死亡就是思考生命。
人從一出生,就是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終點。人終有一死,不過一般人很少思考死亡。也許這是一種自我保護作用,可以避免處於恐懼死亡的焦慮。
我第一次接觸死亡是十歲那年農曆七月半,宜蘭利澤村的冬山河邊有小朋友玩水溺斃,我帶著弟弟妹妹加入圍觀的人群中。當他的父母抵達時,小朋友突然流鼻血了。意外往生者見到親人會七竅流血的傳說,流傳已久,親眼目睹帶來永遠無法磨滅的印痕。這意味著人死以後,靈魂還在嗎?冬山河每年總有幾個人溺斃,通常是在七月半、八月半、春節前這些特殊的日子,傳說是溺水冤魂在找替死鬼。若此為真,也是死後有靈魂的印證嗎?我十二歲那年,也是農曆七月,父親夜晚騎腳踏車過橋,沒有發現橋樑修繕中,連車帶人落入河中,幸運被救起。沒想到第二天,一位深諳水性的人游泳溺水而死。全家人驚慌一場,對於替死鬼之說,印象深刻。
從小害怕靠近廟宇,因為廟宇牆上經常出現地獄裡上刀山、下油鍋等各種恐怖的畫面。為非作歹之人死後會下地獄,本是為了勸人向善,即使只是對父母不孝也要下地獄,對孩童而言,反而造成對死亡的恐懼。
我的長子從小學二年級開始,經常表示非常害怕死亡,問我死亡是怎麼回事?當時我雖然擔任醫師數年,上過解剖課,在醫院裡見過不少死亡案例,但是學校不曾開過死亡課程,醫院裡只把死亡病例當成醫療失敗的結果。定期召開死亡病例研討會,目的也是為了釐清死亡的病因。我未曾深思,死亡是什麼?臨終之人有何感受?
印象中我回答長子:「人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了,什麼感覺都沒有了,不用怕。」他覺得這答案更讓人覺得恐怖,活蹦亂跳的一個人,怎麼會變成什麼都沒有了?我換了一個答案:「人死了只是肉身毀壞,靈魂會永遠存在生者的記憶中。」最近與他核對此事,他記得的是我跟他說:「長大了就不會怕了。」
由此可見,雖然懂事之初,曾經恐懼死亡。之後二十幾年,我忙碌於學業和工作,即使比一般人見過更多的死亡,身為醫師的我並沒有認真思考過死亡,因此無法幫忙減輕兒子對死亡的焦慮。
美國精神科醫師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在《凝視太陽:面對死亡恐懼》(Staring at the Sun: Overcoming the Terror of Death)書中描述一位母親面對孩子提出相同疑問時的回答:「你眼前還有很長的人生要走,沒道理這麼小就煩惱這件事。」「當你老到快死的時候,你要不然是覺得死亡沒什麼,要不然就是有病在身,你會想快快解脫,不管是哪一種情況,那時候你都不會討厭死亡。」
聽起來這答案深具智慧,不過這個孩子雖然記得母親的話,即使長大成人,仍然為了死亡焦慮去找亞隆醫師做心理諮商。而亞隆八十五歲所寫的自傳《成為我自己:歐文.亞隆回憶錄》(Becoming Myself: A Psychiatrist’s Memoir)書中,還是用了不少篇幅述說他自己的死亡焦慮。
亞隆問過自己和病人:「對於死亡,你最害怕的是什麼?」常見的答案可分為兩類,第一:「無法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或無法看見自己關心的人之後的發展。」第二:「擔心自己的配偶、伴侶或者是子女,如何度過沒有他∕她的日子。」不論是哪個答案,最在意的無非是自己和所愛之人,那麼有生之年最重要的事情,不就是好好善待自己和所愛之人嗎?面對死亡時,所有的名利、物質皆可拋。
在《凝視太陽》書中,亞隆提到漣漪概念:我們每個人往往在不知不覺中,起了同心圓向外擴散的影響力,可能影響他人好幾年,甚至好幾代。唯有人的善行,唯有人對他人的德澤,能夠超越己身的有限而永垂不朽。我們一生中可能對陌生人有過善行、照顧了親友、工作中服務他人、指導或啟發過他人,甚至留下文字、音樂、藝術或科學的遺產。如果感到此生沒有白活、沒有遺憾,也許可以減少死亡的恐懼。
死亡的滋味,無人能知。畢竟沒有哪位亡者能夠回頭告訴我們死亡是什麼?然而,我們看過、聽過許多親人的死亡對生者造成的影響。朋友的母親已經八十幾歲,洗腎超過十年,在一次晨泳中意外溺斃。雖然其母在生前多次提到希望快速死亡,不要慢性臥病而死,自己受罪,也連累子女,但是母親突然的離去,這位朋友陷入了深沉而長久的哀痛。足足有兩年之久,她身陷陰鬱的情緒中,連說話的音調都與以往不同,也很難露出笑容。
我的外婆早逝,冬山阿姨長我母親十一歲,對我母親疼愛有加,我母親視她如母。家中三姊弟自然也最喜歡這位阿姨。但是阿姨的長子在十七歲的時候,死於工廠的意外。阿姨的眼睛差點哭瞎了,表哥的遺照被一頂帽子遮著,因為阿姨看到表哥的照片又要淚流不止。從此阿姨的面容如憂傷的聖母雕像,數十年沒有見到阿姨快樂的笑過,偶爾露出笑容,也像是石膏的臉,在眼角和嘴角有一絲絲肌肉的牽動而已。在國中的年紀,我見識到「白髮人送黑髮人」是人間至痛。
沒想到過了幾年,她的小兒子當兵回來,騎摩托車意外身亡。我們都擔心阿姨熬不過去,不知說什麼才好,只能默默的陪伴她。有一位師父開導她,她與兒子的緣分淺,只能陪伴那麼多年,她因此比較釋懷了。在復健科病房,除了腦中風的中老年人以外,最多的就是年輕男性的腦外傷和脊髓損傷者,病人多半是由母親照顧,我總把對阿姨的疼惜移情到這些母親身上。
冬山阿姨晚年得了血癌,遠從宜蘭到台大醫院接受治療,我母親也幫忙照顧。非常心疼她做骨髓穿刺、化療的艱辛。所幸治療後,症狀得到暫時緩解。但是三年後,血癌復發,治療無效,阿姨往生了。母親奔喪回來,興奮的告訴我,她從來沒有見過阿姨這麼美麗、這麼春風過,臉上甚至有淺淺的笑容。她覺得阿姨終於擺脫了喪子之痛,一定是在天上見到兩個兒子了。並且告訴我,若為了多活三年,吃那麼多苦,受那麼多罪,她覺得不值得。可見,我的母親對死亡無懼,害怕的是病苦!
一九八○年代,我在台大醫院擔任復健科住院醫師,植物人王曉民在父母照顧了二十年以後,情況不佳,其父母不忍女兒繼續受苦,提出安樂死立法的需求,引起社會廣泛討論。台大醫院就在立法院附近,我記得我在安樂死立法的連署單上簽了名,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安樂死的議題。當時我已經對「歹活不如好死」有所認同。
復健科經常要面對生活品質很差的嚴重失能者,看到病人餘生痛苦無邊,家人負擔沉重,心中非常不忍。許多女兒為了照顧父母,終身不婚,因為沒有機會交男朋友,也沒有餘力成家。許多母親或者妻子因為照顧臥病的子女或配偶,長期被困在病床邊,沒有自己的生活。當然,也有男性家屬作這樣的犧牲,這些男性在復健醫院裡面都被當作模範生一般讚揚。我覺得毫無尊嚴的終身纏綿病榻,對當事人及其家屬而言都極其殘忍。一直期待安樂死完成立法,倏忽四十年已過,可惜至今尚未成功。
一九九九年我閱讀美國生死學大師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Elisabeth Kubler-Ross)所寫的《天使走過人間:生與死的回憶錄》(The Wheel of Life: A Memoir of Living and Dying)才首次接觸到「臨終關懷」的觀念。她於一九六七年開始主持一種研討會,請疾病末期的病人來到會議現場,不是為了探討疾病的成因與治療,而是請病人訴說他們的內在感受、需求、遺憾或者是願望等等。在那人人避談死亡的年代,「臨終」、「死亡」等名詞在一般研討會裡都不會出現。事實上,病人從家屬與醫師的反應,對於自己將不久於人世已經心知肚明,醫師的不明說讓他們感到憤怒,家屬的逃避也讓他們覺得孤單。這個研討會提供他們吐露心聲的機會,也感受到有人關懷的溫暖。這樣的研討會對醫學生有很大的震撼與啟發,讓他們理解死亡乃是人生的一部分,讓臨終者身心靈得到照顧,沒有遺憾的離開,也是醫者的任務。然而多數把死亡視為醫療失敗的醫師同事們卻非常排斥,不來參加研討會,甚至故意不轉介病人給羅斯醫師。
羅斯醫師關懷臨終病人所思所願的觀念,也運用到了她父親的身上。她父親疾病末期,期望回家善終,但是醫師不放行。她從美國飛回瑞士,直奔醫院,和醫師理論。最後簽下「違反醫師建議自動出院切結書」,帶父親回家。在救護車上,她拿出預備好的香檳酒與父親乾杯,父親思念這美酒已經很久了。數日後父親在掛著瑞士風景畫的房間,聽著窗外熟悉的教堂鐘聲中安詳離開人世。這個案例凸顯諸多醫師只看見「疾病」,而未連結「病人」的感受與需求,實在是醫學教育的失敗!
羅斯醫師將研討會經歷彙整,於一九六九年出版《論死亡與臨終》《On Death and Dying》一書,得到很大的迴響,此書日後成為該領域的經典教科書。美國《生活》雜誌(LIFE)採訪報導了一場「死亡與臨終研討會」,讓她一舉成名。那次研討會的主角是一位二十一歲的年輕女性,她在研討會中不談疾病與死亡,卻是侃侃而談假若她能夠活下去,她有多少想做的事情、有多少抱負想要完成。羅斯從病人身上學習到,面對死亡是為了不要留下遺憾,是為了好好活著。然而院方還是對她非常不諒解,他們認為醫院是要救活病人的地方,羅斯把這家醫院變成名聞遐邇的死亡醫院。羅斯醫師被戲稱為「死亡醫師」。
羅斯醫師的觀念超越了時代,八○年代歐美先進國家陸續設立臨終安寧照護病房,台灣在一九九○年成立了第一個安寧照護病房,提供臨終病人舒適有尊嚴的善終服務。目前各大醫院都有這樣的服務,甚至有居家安寧照護的服務,病人可以在自己的家中善終。
日本的中村仁一醫師也可稱為另類的「死亡醫師」,他從一九九六年開始定期舉辦「思考自己之死」的集會。集會的標語是「要讓現在活得精采,就必須思考死亡」,與會人士自由溝通有關生與死的想法,討論末期醫療、癌症的宣告、腦死、器官移植、延命治療、尊嚴死、安樂死、生前意願等等議題,許多時候大家只是分享如何活得暢快。不只談論,還要行動,辦過「壽衣服裝秀」、「模擬葬禮」、「我要躺進棺材」等活動。在當時的日本社會,死亡還是一種禁忌,他的作為引起很大的爭議,但是這個集會每次都有數十人參加。至二○一七年時已經連續舉辦二十一年,有超過二百二十五次的聚會。
中村醫師甚至在家中放了一副可組裝拆卸的環保瓦楞紙棺材,每年除夕,他會在裡面躺上幾分鐘,回想這一生,反省過去一年做了哪些事情?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未來有什麼計畫?他從七十歲開始認為自己已經過了「賞味期」,隨時都可以沒有遺憾的離開人世,每一天都是老天爺額外給予的。
中村醫師於二○一三年出版《大往生:最先進的醫療技術無法帶給你最幸福的生命終點》,提倡傳統的在家「自然死」(natural death)。在日本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人在醫院死亡,許多沒有必要的醫療措施,延長了死亡的過程,造成人們死亡之前受到極大的痛苦。
他認為得癌症而死,是最好的死法。有充分的時間處理身後事,與親友告別。在他看來癌症是一種老化,癌症本身不痛苦,是治療癌症造成了痛苦。他已經過了七十歲,主張重病不叫救護車、不住院治療,在家自然死,死亡是留給晚輩最後的遺產。他對死亡的豁達,對生存的積極態度,令人讚賞。
達賴喇嘛對死亡的看法非常積極正面。他認為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不論我們喜不喜歡,它註定會來臨。害怕死亡而逃避它,還不如去瞭解它的涵義。覺知死亡之必然是一件好事,如此我們才會專注於此生的修行,善用這個已經獲得的特殊人生,多做利己和利他的善行,那麼死亡的時候將沒有遺憾。死亡可以是欣慰的事,人的靈魂將輪迴再生,死亡不過是換件衣服。這件衣服老了、舊了、破了就應該換掉,身體毀壞了也是如此。死亡如此簡單,不是神祕、黑暗的,那麼不需要恐懼它,需要的是努力過著有意義的生活。
註1│《凝視太陽:面對死亡恐懼》(Staring at the Sun: Overcoming the Terror of Death),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心靈工坊,二○○九。
註2│《成為我自己:歐文.亞隆回憶錄》(Becoming Myself: A Psychiatrist’s Memoir),歐文.亞隆,心靈工坊,二○一八。
註3│《天使走過人間:生與死的回憶錄》(The Wheel of Life: A Memoir of Living and Dying),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Elisabeth Kubler-Ross),天下文化,二版,二○○九。
註4│《大往生:最先進的醫療技術無法帶給你最幸福的生命終點》,中村仁一,三采文化,二○一三。
第一章
小腦萎縮基因篩檢記
二○○一年春節回娘家前,母親在電話裡說她走路越來越不穩了,上下樓梯都要用手扶。她抱怨走路不穩、容易跌倒好幾年了,但是平常除了照顧中風的父親以外,各項運動、家事樣樣來,手腳俐落得很,我想一定又是她多慮了。
沒想到,幾個星期沒見,她清瘦不少,兩腳併攏站立時身體搖晃得很厲害,更別提單腳站立了。
我的臉色一定露出異樣,母親頻頻追問:「我中獎了,是不是?我都這麼老了,怎麼還會發病呢?」我愣坐在一旁,腦中一片空白,說不出話來。
在此之前二十年,比母親小三歲的表哥由於走路搖搖晃晃,來到我擔任住院醫師的台大醫院神經內科看診,經過一系列檢查後主任給了一個罕見的診斷:脊髓小腦萎縮症(SCA: Spinocerebellar Ataxia)。他請我好好問清楚家族史,把資料交給他。
一路問下去才發現,原來舅舅從三十幾歲起,走路就像醉漢一樣,應該也是這種病。表哥確診的三年前舅舅因行動不良被診斷脊椎狹窄壓迫神經,脊椎手術後雙腳幾近癱瘓,無法解尿,就再也沒有下過床。外婆四十歲難產病故前身體無恙,但是外婆那邊很多房親戚都有人年輕時就走路不穩,日後行動不便長期臥床的。從密密麻麻的家族罹病分布圖看起來,男、女罹病機會相當,是一種顯性遺傳。只要父母中有任何一人罹病,每位子女都有二分之一的機率罹病。
這是舅舅一家人悲慘命運的開始,舅舅在臥床五年後利用衣物綁住脖子,身體滾下床自縊身亡。表哥在確診十年後,以塑膠袋悶住頭部,窒息掙扎而死。表弟二十幾歲發病,臥床七、八年無法言語、吞嚥,全身關節變形、壓瘡、瘦得皮包骨過世,得年才四十二歲。而表哥和表弟的孩子們已經多人發病,年齡不過十幾或二十幾歲。這疾病有個特徵,下一代會在更年輕就發病(anticipitation)。二表嫂因為女兒、兒子、丈夫先後得病,先是酗酒,後來得到憂鬱症,數年後不明原因猝死。
從此,家族有遺傳疾病的陰影,潛伏在我們的腦海裡。母親的多位姊姊當時好像都沒有發病的跡象,已經六十四歲的母親年紀早超過疾病好發年齡(三十至四十幾歲間),因此家人很少談及這件事。就連從事醫療工作的我,雖然知道幾年前已經可以做基因檢測,也沒想過要去面對這個問題,鴕鳥式的以為外婆把基因傳給兒子,女兒家人可以豁免。
看到母親明顯的平衡障礙,心知不妙,腦袋裡千頭萬緒,卻必須故作冷靜,安慰母親:「看了醫師再說。」先生得知此消息,萬分焦慮,覺得有如從雲端摔落,人生突然變色,夜裡輾轉難眠,又怕我承受不了打擊,頻頻勸慰。短短幾日白了頭!
陪母親到神經科看診,醫師做了理學檢查,平衡感有明顯障礙,安排我們到研究室抽血檢查,我知道八九不離十,劫數難逃了!不過還是要等基因檢查的結果,同時也安排了腦部磁振造影(MRI)以幫忙確定診斷。
照MRI要半個鐘頭,母親說感覺時間好長,全身不停地發抖,身上穿著薄薄的衣裳,蓋著一層薄薄的被子,在小小的密閉空間,好擔心機器會不會故障?機器不時傳來不同的聲響,不知道何時聲音會響起?也不知會響起何種聲音?恐怖又漫長的檢查!醫療人員很少知道,我們習以為常的檢查,病人這麼難受!
母親多半也看出端倪,不斷問我可不可能是別的病?我告訴她譬如感染、腫瘤也是有可能,所以要照腦部磁振造影。她說她希望她得到別的病,只要不是小腦萎縮症就好。她寧願是腦瘤,就算是癌症也沒有關係,開腦她不怕,死掉她也不在乎,只要不要遺傳給孩子、孫子就好。我心悽悽然!
我拿了磁振照影的片子,請教熟識的放射線科主任:「這像是多大年紀的MRI?」答約:「五十歲左右,只有看到一個很小的空洞,其他都正常。」我說病人有小腦萎縮家族史,目前已經有明顯平衡障礙。他說:「這樣的話,影像有符合小腦萎縮症。」病症早期,小腦的萎縮輕微,還在正常範圍內。和先生商量以後,決定瞞住所有家人,不要弟弟、妹妹和我們一樣面對這種煎熬。
我先生是婦產科醫師,利用產前篩檢,可以讓兒子和外甥不要生出帶著此遺傳基因的孩子,我們絕不能讓年紀輕輕的第三代面對這種生命之沉重。
電話裡我告訴母親她沒有小腦萎縮症,只是有些陳舊的腦中風,平衡感不好是因為年紀大了老化的關係。她雖看不到我(我住台中)因為撒謊而不自然的表情,但還是聽出來女兒沒有對她說實話,堅持要自己去看基因檢測的報告。
她去台北榮總看報告,檢查結果是台灣最常見的第三型小腦萎縮症。遺傳諮詢的技術員,很驚訝她怎麼無人陪伴,獨自來看結果,而且聽到結果還異常的冷靜,沒有驚慌、沒有悲傷,不斷稱讚她真堅強。母親當時正在學電腦,還告訴我她也許應該去學英文,免得將來跟外籍看護無法溝通。
母親希望我們三姊弟都去做檢查,她說她老了,生這種病沒有關係,然而她放心不下三個子女、三個外孫,萬一得病怎麼辦?她更不能接受外孫再生育有病的下一代。
我反對未發病者做檢查,這種病目前尚無有效的治療方法,提早知道了於事無補,只是影響心情而已。尤其是孩子們,年紀輕輕如何承擔這些?母親認為孩子假如帶有基因一定要知道,交女朋友時要告訴對方,不能像表弟這樣隱瞞女方,結果女方不能原諒,生下孩子就帶著孩子走了,一輩子怨恨他。(表弟的女兒,十歲發病,二十幾歲就過世了。)
我說孩子假如知道了,他還有機會交異性朋友嗎?欺騙對方,他們做不到,告訴對方,結果一定是把對方嚇跑的。唯一讓他們有公平與異性交往機會的就是他們真的不知道真相,他們才能自然的與人交往。母親說:「這樣對對方不公平!」我說:「你不是常告訴我『天下沒有真正公平的事』嗎?這是因為這個病現在可以提早檢查出來,一般人誰能保證自己將來不會得腦中風、癌症或者出意外呢?」
母親從舅舅和表哥、表弟身上,看到小腦萎縮症逐漸惡化的病程,看過表弟皮包骨、壓瘡、四肢攣縮、插著鼻胃管、無法言語的慘狀。主動和我討論起安樂死的問題,這一點我們很早就有共識。我們都認為假如身染重病,活著只是受罪的話,不要勉強救治,延長痛苦。我知道短期內台灣還不會通過安樂死,她希望我要謹記這一點,在必要時幫助她解脫!我是她三名子女中唯一的醫師,她把此願望寄託在我身上。
我反問她,疾病進展到什麼情況就是她所謂沒有必要活的時候呢?她說:「坐輪椅,不能照顧家人的生活,還要別人來照顧自己的時候!」我一聽,這可嚴重了,照這個標準,這世上不是有太多人不值得活了嗎?我們復健科的病人有多少人是終身坐輪椅的啊!趕忙安慰她,這個病年紀越大發病,惡化得越慢,她將來就像一般老人慢慢變得比較不方便而已,不要想這麼多!
這是安慰她的話,她從舅舅、表哥、表弟身上已經知道自己的未來:走路越來越不穩,繼而雙手不協調、吞嚥困難、講話口齒不清,最終坐也坐不穩,僅能臥床、靠鼻胃管進食。我絕對不忍心讓她走到最後的地步!
向先生轉述我與母親談話的內容,提起假如我得了這個病而嚴重癱瘓時,我也希望能夠早日解脫,不要痛苦而沒有尊嚴的活著。並交代先生,如果我先走了,有機會的話,他要再婚。先生急著說:「妳千萬不要做傻事,要做什麼決定的時候,一定要告訴我。我會一直陪著妳、照顧妳,若沒有妳在身旁,我只想一個人安靜的過生活,我對生活的要求很簡單。」
擔任復健科醫師多年,我照顧過許多嚴重失能的病友,早期常有病人尋死,或者關在家裡走不出來。以脊髓損傷者來說,現在多數病人都很快就能克服心障和身障回歸職場、回歸社會,心中對他們是由衷的欽佩。想了又想,自己豈能這麼軟弱,我告訴先生不要太擔心,我最近想了很多,在看到美麗的事物、聽音樂、閱讀的時候,還是可以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只要還能看、能聽、能閱讀,我想人生就值得活吧!
剛考上醫學系的大兒子,提到最近走路竟然撞到門好幾次,想起書上說早期症狀之一就是走路很容易碰到人或者撞到牆。夜裡輾轉反側想著,假如有小腦萎縮症平衡感不好,大兒子將來能當什麼科的醫師呢?讀國中的小兒子,也覺得滿腹狐疑,爸爸媽媽怎麼常常看到他進來,就停止了原先的話題,還要求他和哥哥做一些奇怪的動作(平衡測試),媽媽也在爸爸面前做過。
所有的事情都和原來沒有兩樣,但是我們夫妻倆的心境已經完全不同,覺得以往那種純粹的快樂好像再也喚不回來了!甚至覺得連好朋友也不想聯絡了,我怎麼能告訴朋友這些事、這些壓力,如果不能說,又怎麼能粉飾太平、戴著面具面對她們!我大哭了一場後,終於體會到:這個未知的煎熬,簡直如同自己已經得了病一般。那麼我不如去做檢查,還有一半的機會,若沒有得病,大家就得到解放了;萬一得病,也不過就是像現在的心情。
母親打電話來,說卜卦的師父告訴她,她只是老化,她將來不是因為家族遺傳的這個病而死的。她想安慰我,讓我不要太操心,因為師父告訴她:「你大女兒的壓力比你還大!」讓她擔心不已。我告訴她,我已經抽血檢查了,最近結果就快出來了!
我不希望這件事在自己工作的醫院曝光,所以請開業的先生幫忙抽血檢查。等待結果的那幾週,日子真的好煎熬。先生打電話到醫院來告訴我結果是「陰性」的那一刻,我高興得想告訴身邊所有人這個好消息!真是謝天謝地!趕忙撥了電話給母親,她說心中的六塊石頭,放下了三塊(我與兩個兒子),還有三塊!
事後先生告訴我,假使檢查結果是「陽性」的,他也會告訴我是「陰性」。我嚇得問他,到底我是陰性還是陽性?他說:當然是陰性的呀!假如我是陽性,他可能會偷偷幫兒子們抽血,但是不告訴他們結果。
我們覺得以前傻傻不知情的日子多麼單純、快樂,因此仍然不打算告訴弟弟、妹妹。但是我希望知道外甥有沒有帶基因,沒有當然最好,若有也不要告訴他,他的配偶懷孕早期我們會以產前檢查為名,幫忙做基因篩檢。
先生利用外甥來台中小住時,偽稱幫他抽血做生化檢查,實則是要驗小腦萎縮的基因。再度感謝老天爺,外甥的檢查結果也是陰性。這樣可以推斷妹妹有很高的機率沒有這基因。
我覺得既然第三代都很幸運的逃過一劫,已經中年的弟弟、妹妹,應該沒有必要接受檢查。母親仍然希望弟妹都去檢查,我想這是她身為人母的壓力,她一定覺得要所有子嗣都沒有得到遺傳,她才能完全去除這罪惡感吧!我分析我的想法給母親聽,並希望她完全摒除罪惡感,就像她絕不會怪罪外婆一樣,我們也絕對不會怪罪她。她不再堅持要告訴弟弟和妹妹。
幾個月以後,母親告訴我其實妹妹許多年來心裡一直被這個遺傳疾病的陰影所困擾,最近在媒體看到這疾病的報導,她詢問母親為什麼不去做檢查?到了這個地步,我們把真相都告訴了她,我以為她知道獨生子沒有帶這種基因,就可以放心,沒有必要再做檢查了。沒想到,她堅持要做,想到自己未做檢查之前的心情,好像沒有理由反對妹妹做。幸運的是,妹妹檢查結果也是陰性,母親和妹妹都大大的鬆了口氣。
最後知道實情的弟弟,他只擔憂親愛的媽媽,對他自己的事則完全沒有置評。母親建議他去檢查,他不為所動,他說眼前的事情都忙不完了,哪有時間去擔心以後的事?弟弟沒有兒女,我和先生也勸母親不要再要求弟弟去做檢查了,難得他看得開,何必預知未來,給自己找麻煩呢?人生有把握的只有現在,何苦拿未來的事情驚嚇現在的自己呢!弔詭的是,我自己當初可沒有辦法這麼想得開。
雖然這一路驚濤駭浪,最後有驚無險,然而我和先生兩人對人生的看法都有了很大的轉變。感到人類的渺小,生命裡無所謂理所當然,人生要珍惜、要付出!即使如此,我們無法想像,假如檢查結果都是陽性,我們現在會是什麼心情在過生活?
這整個基因篩檢的過程,由於身為醫師的關係,我運用了體制外的資源,依照我們夫妻認為對家人最好的方式來進行。從醫療人員的角度我曾對遺傳諮商的規範深信不疑,經歷此事件,才發現身為當事人時,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和看法。目前的規定是不幫未成年者鑑定,成年人一定要本人才能要求檢測,本人才能得知結果。胎兒可以接受檢測,需要時依優生保健法可以人工流產。有些已開發國家,認為此疾病中年才發病,反對墮胎。
在我等待基因檢測結果的時候,接到朱穗萍女士的電話,提到她與家人和一些小腦萎縮症病友、家屬將成立「中華小腦萎縮症病友協會」,邀請我擔任顧問醫師。經她說明,我才想起十年前報紙曾經刊登我談論小腦萎縮症的新聞。朱小姐閱報後來電詢問:「我的家族有類似情況,此病目前是否有治療的方法?」我回答她:「還沒有特效藥,做復健可以延緩病情惡化。」
她提到她母親多年前因為肢體癱瘓臥病數年後自殺,幾年後她的六位弟弟、妹妹相繼發病,有兩位先後被她接到家中自行照顧,非常辛苦。我在電話中提起脊髓損傷病友協會對病友以及家屬有很大的幫忙。沒想到她竟把成立病友協會當成人生目標,在十年後實現了她的願望。我真是太欽佩她了,也很驚訝十年前的一次電話,牽起這樣的因緣,自己的親人也從協會得到幫助。
二○○一年三月在台北舉辦病友協會第一次會員大會,我沒有得病的一位表姊擔任理事;大表哥的兒子、女兒是會員,二表哥的女兒才十三歲步態不穩由表嫂攙扶著出席,心中百感交集。我以顧問醫師的身分參加,多數人不知道我同時也是沒有得病的家屬。致詞時,我強調不要把小腦萎縮症視為絕症,這疾病只是小腦老化得比一般人快,利用復健可以延緩疾病的惡化,就像適當的養生及運動可以預防老化是同樣的道理。
之後,我工作的復健醫院照顧了不少小腦萎縮症的病友。因為罹病而運動不足的病友,可以在復健之後得到些許的進步,重要的是之後要在家中持續復健。不過病情還是會慢慢惡化,有些病友需再度來院復健,學習因為病情惡化而需要改變的運動方式和輔具處方。醫院的治療師們也經常到協會演講,並幫忙協會製作了衛教的手冊。
我的母親倒是從來沒有到復健科接受過治療。她從四十八歲開始學瑜珈以來,每天運動的時間超過兩小時。我推斷持之以恆的規律運動,延緩了她發病的時間,也能減緩病情的惡化。
註1│脊髓小腦萎縮症是因為基因的DNA多出來一段,製造出正常人所沒有的蛋白質。這種蛋白質沉積在小腦的神經細胞裡,使之提早死亡。多出來的DNA越長,製造越大量的蛋白質,破壞力越強,發病的年齡就越早,疾病惡化的速度也越快。
註2│沒有得病的家屬常出現一種倖存者罪惡感(survivor guilt),會有強烈的責任感想要照顧得病者。例如此文中的朱大姊、我表姊。
引言/
思考死亡與面對死亡
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思考死亡就是思考生命。
人從一出生,就是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終點。人終有一死,不過一般人很少思考死亡。也許這是一種自我保護作用,可以避免處於恐懼死亡的焦慮。
我第一次接觸死亡是十歲那年農曆七月半,宜蘭利澤村的冬山河邊有小朋友玩水溺斃,我帶著弟弟妹妹加入圍觀的人群中。當他的父母抵達時,小朋友突然流鼻血了。意外往生者見到親人會七竅流血的傳說,流傳已久,親眼目睹帶來永遠無法磨滅的印痕。這意味著人死以後,靈魂還在嗎?冬山河每年總有幾個人溺斃,通常是在七月半、...
目錄
﹝推薦序﹞
幫忙摯愛的母親達成生命的自主決定:「真情、勇氣、智慧」的結合/賴其萬(神經內科醫師,和信醫院醫學教育講座教授)
生命誠愉悅,死亡歸平靜/江盛(婦產科醫師,安樂死立法推動者)
好好道別、生死兩相安/周志建(資深心理師,故事療癒作家)
一本生命教育之書,精采的家族歷史/李崇建(作家,資深生命教育工作者)
自序:我們與善終的距離
引言:思考死亡,面對死亡
第一章:小腦萎縮基因篩檢記
第二章:坎坷人生孤女淚
第三章:愛要及時,牽手旅遊
第四章:自行復健,積極生活
第五章:父親往生,母獲自由
第六章:與看護相伴的日子
第七章:自主善終的抉擇
第八章:愛的極致是放手
第九章:斷食歷程
第十章:生前告別式
第十一章:三個葬禮,三樣情
第十二章:拔管善終的意外之旅
第十三章:善終權利立法進化史
第十四章:不得安樂死的自力救濟
後記/母親雖死猶生,與父親和解
最寶貴的一課:母親對於死亡的坦然/作者弟弟 畢恆達(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生與死的難題/作者先生 黃東曙(博生婦產科診所醫師)
母親與我們(母親與家人不同階段的身影留念)
附錄:
壹、讀者的迴響與疑問
貳、簽署「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辦法及表格
參、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辦法及表格
肆、《尊嚴善終法草案》(2020年3月13日提案)
﹝推薦序﹞
幫忙摯愛的母親達成生命的自主決定:「真情、勇氣、智慧」的結合/賴其萬(神經內科醫師,和信醫院醫學教育講座教授)
生命誠愉悅,死亡歸平靜/江盛(婦產科醫師,安樂死立法推動者)
好好道別、生死兩相安/周志建(資深心理師,故事療癒作家)
一本生命教育之書,精采的家族歷史/李崇建(作家,資深生命教育工作者)
自序:我們與善終的距離
引言:思考死亡,面對死亡
第一章:小腦萎縮基因篩檢記
第二章:坎坷人生孤女淚
第三章:愛要及時,牽手旅遊
第四章:自行復健,積極生活
第五章...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01收藏
101收藏

 104二手徵求有驚喜
104二手徵求有驚喜





 101收藏
101收藏

 104二手徵求有驚喜
104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