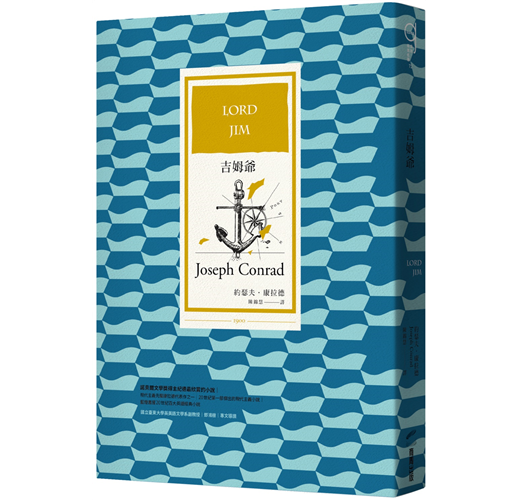名人推薦:
【密探】
〈導讀〉事物的真相/臺大外文系副教授 陳春燕
《密探》是康拉德豐實的寫作生涯中極不典型的作品──這是他少數並非以歐洲之外地區為場景的小說。
波蘭裔的康拉德出生於一八五七年,母親、父親在他年幼時相繼過世,他自十七歲起,便開始在商船上工作:青春盛年的大半時間,康拉德若非在海上度過,便是在海外的港口城市工作。時值十九世紀後半葉,他隨著不同的歐洲商船(尤以英國商隊為主)遠渡重洋,從澳洲、遠東到南亞,從中南美洲到非洲大陸,無數次的出海,恰恰勾勒出當時歐洲帝國勢力征服全球的軌跡。當他三十一、三十二歲之際開始嘗試寫作,這些海外經驗便成了筆下最實在的素材。從最為人熟知的中篇小說《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到《吉姆爺》(Lord Jim)、《碼頭老大》(Nostromo)等重要長篇,乃至於他多數的創作,都以他在世界角落的見聞為藍本。
《密探》則是少見的例外。
《密探》將鏡頭拉回倫敦,內容上則環繞十九世紀末歐洲各家政治意識型態在思想及行動上的角力。
小說所設定的背景時間為一八八七年,維多利亞女王登基五十週年,大英帝國盛景空前。但那也是英國內部紛爭四起的年代:財富分配不均,失業率居高不下,對愛爾蘭的高壓統治也日益引發民怨。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倫敦便曾發生大規模的民眾抗議活動,而政府採取的回應方式是以現代化的警力強勢鎮壓。
這個歷史時空也彰顯了,當時社會上不同的政治理念尚有機會相互爭逐。例如,社會不公,使得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有一定的擁護者;甚至無政府主義組織在當時都是合法的,也能在社會空間中維持一定能見度,出版書刊,爭取發言。而各式紛陳的政治選擇,構織了《密探》的內容肌理:小說中,我們看見不同的(男性)角色分別有機會長篇大論,各自發抒在政治光譜上或右或左、或自認比左更左的殊異立場。唯一例外恐怕是主角維洛克,而他的不願表態,與他選擇擔任雙面間諜,互為表裡。
與《密探》緊密相關的另一個時間點,則是小說情節核心──格林威治公園爆炸案──所參照的真實歷史事件。
一八九四年二月十五日,格林威治公園皇家天文台附近,法國籍無政府主義者波爾丹(Martial Bourdin)手持的炸藥突然爆裂,沒有傷及無辜,卻炸死自己。康拉德在一九二○年《密探》重印本的自序中,自陳小說的靈感確是一八九四年的爆炸案。其時,英國大眾傳媒頗有煽情八卦風氣,各報對爆炸案投注了高度關切,甚至在毫無證據情況下推敲出陰謀論,直指這是鎖定天文台的恐怖主義行動,只不過波爾丹行動有所閃失,誤炸了自己。簡言之,這在當時是起爆炸性新聞事件,但事件來龍去脈,事實上至今無解。
一八九四年對康拉德本人恰巧是個關鍵的時間座標。那年一月,他決定取消與一家商船的工作合約,也就此終結他將近二十年的海上生涯;二月十日,他的舅舅過世(舅舅是康拉德成為孤兒後的監護人,亦是主導他選擇船員工作的重要人物);這年,也是康拉德第一本小說被出版社接受的時間。換言之,這正是他人生重大的轉折點,他對寫作開始認真實踐。
《密探》撰寫於一九○六、○七年間,正式出版於○七年。當時,前述幾部後來堪稱他代表作的小說皆已問世,雖然康拉德尚未得到足夠的肯定,但他曾透露,一九○六年前後,他對於「事物的真相」極度敏感,卻總受到外在世界平庸、膚淺價值的干擾,深感孤立。那是個他稱為他「站定不動」、亟思改變的階段。
假使康拉德此刻正在尋索下一部小說題材,回望的是一八九四年(以及穿過一八九四年上溯的一八八○年代末期),這個動作,除了讓他得以反思日不落帝國時期英國的社會現況,更是他對自身創作志業初始點的一次回顧。
也因此,《密探》應被理解為康拉德希冀解決自己對「事物的真相」探求的過程。有趣的是,他所揀選的,卻是曾被戲稱為「波爾丹烏龍事件」這起看似如此靠近卻又難以解碼的新聞案例。而他處理的方式,不是企圖忠實仿製歷史上的波爾丹事件,而是藉由一個表面形似的情節,暴露出小說不同人物對故事中爆炸案緣由似是而非的各自表述,也就此暴露不同政治信仰各自的執迷。
這其中,有主張歷史是由生產、經濟活動所推動的唯物主義者(「假釋聖徒」麥凱里斯);有堅信無產階級革命即將到來的社會主義者(自稱為「恐怖分子」的揚德);也有打著客觀科學名號,以假醫學分析「中產階級墮落劣行」者(綽號「醫生」的奧西彭);還有身上隨時攜帶炸藥,隨時準備以身試法,以行動摧毀社會教條規範者(人稱「教授」的炸藥製造者)。此外,更有維洛克背後的金主,逼迫他製造驚天動地事件以喚醒中產階級的俄羅斯官員(瓦迪米爾);以及同情小偷卻無法憐憫無政府主義者的倫敦警探(錫特),對法律有一定的信心,卻需要收買維洛克這樣政治態度模糊的人,為他提供國際情報。
康拉德在《密探》中毫不避諱地對這些政治論述者的盲昧提出批判,而他批判的方式是從人物造型下手。康拉德從不害怕動用刻板印象,因為他有能力將刻板印象予以複雜化。而在《密探》中,他刻意採用十九世紀末流行的面相學(奧西彭即是這種偽科學的信奉者),讓角色的外觀透露他們的心性。因此,讀者應可留意小說中每位人物的外表形貌甚至衣著打扮:維洛克、麥凱里斯都被塑造成臃腫、蒼白的胖子,符合他們不事生產、寄生社會的個性;錫特則本有堅毅信念,但臉上肥肉讓他的矛盾性格露了餡。
維洛克的小舅子,智能不足的史蒂夫,是小說中難得面容清秀的男性,也的確不時展現對他人真誠的情感。然而姊夫的私心,終究導致了弱勢者史蒂夫的悲劇。
而如果小說表面上的微言大義多半聚焦於維洛克和革命分子這些欠缺自覺的男性人物,小說底蘊卻是不斷將重心拉往兩位女性人物。康拉德曾說過,維洛克的岳母,溫妮的母親,是小說中唯一有道德自省力者。他也曾指出,這部小說事實上是部溫妮的個人歷史。
後者這樣的說法,或有誇大之嫌,但若從小說篇幅編排來看,後半部確實將視角轉往溫妮,漸次鋪陳出她下嫁其貌不揚的維洛克背後的妥協(也因此,除了維洛克的雙面政治奉承值得注意,溫妮的表面順從與內心算計,也是某種雙面性)。而小說後半部的情節高潮以及結尾,更是全力鎖定溫妮的心理轉折。
《密探》事實上還有另一個主角:倫敦。如上所述,這是康拉德難得以倫敦為主場的故事,然他筆下的英國首都,不是繁華昇平,而是擁擠(大倫敦地區人口四百萬人)、失序(都市規畫糟糕到門牌號碼漫無章法),個人獨特性被壓抑,卻也沒有任何能帶來正面意義的集體性。康拉德在回想創作始末(即他那段「站定不動」的階段)時曾提到,他在構思小說的過程中,突然之間,一個巨大的城市的影像浮現在腦海:「一個人口甚至超過一些洲陸的恐怖城市……那裡,有足夠空間包納任何故事,有足夠深度接收各種激情,有足夠多樣性容許各式場景,也有足夠的黑暗埋葬五百萬條生命」。
《密探》除了在嚴肅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亦是當代英國大眾傳媒熱衷的題材。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自一九六七年以來,已四度將小說改編為影集。而英國媒體也總愛順勢將BBC每次的改編串連至不同年代的國際政局危機時刻,主要原因自是書中的恐怖主義元素──媒體總喜歡標舉《密探》如何遙遙預示了後世人的生活日常。
《密探》確實是歐美小說中最早開始探討恐怖主義的作品之一,不過《密探》首先在回應的仍是維多利亞時期英國的景況。炸藥發明於一八六六年,隨後不久便開始被用在政治運動中;光是一八八○年代的倫敦便出現過十數起炸藥攻擊。
其次,小說中所提出的恐怖主義信念,具有某種特殊性,倒未必能與我們這個時代多以伊斯蘭聖戰或反美、反西方為訴求的恐攻直接類比。《密探》中的恐怖主義傳聲筒,是俄羅斯駐英外交官瓦迪米爾,是他建議維洛克將攻擊目標鎖定在格林威治天文台,以製造一種純然的攻擊、毫無理由的褻瀆:他以為,科學正是當時幾乎帶有宗教地位的流行物件,攻擊科學,便能達到前述的純粹性,至於天文台(那裡有個標示格林威治標準時間的時鐘),便是當時科學神物化的象徵。
這是十分精準的觀察。一八八○年代,世界各國紛紛開始倡議將時間標準化;一八八四年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的國際會議,更是確認了國際時區制度,以英國自十八世紀中葉便建立的格林威治本初子午線作為基準。
時間的標準化,意味著生活秩序的標準化、工作節奏的統一,最終得利者,是那些需要工人按表操課、付出高效能勞力的資本家。於是,攻擊天文台,表面上是在打擊科學,骨子裡是在控訴資本制度對於人類生活的全面性掌控。
康拉德小說高妙之處便在於,這樣一個犀利的觀點,卻是由一個動機猥瑣的小人來提陳。小說家對於政治現實的論斷、他對人性的好惡,也因之難以黑白分明。《密探》一方面說了一個戲劇張力十足的故事,也拋給讀者一道關於作者道德曖昧性的難解之題。
【吉姆爺】
〈導讀〉背對高山憂鬱的暮光/鄧鴻樹(國立臺東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副教授)
一八七三年五月,瑞士弗卡山隘。一名十六歲的波蘭少年站在峰頂俯視阿爾卑斯山谷:山路蜿蜒,陡坡裸露的岩層如同浮雕,可見冰川懾人的刻痕。少年遠眺雄偉山景,逐夢雄心油然而生:他想暢遊七海,航向了不可見的海平線。
兩年後,年僅十八歲的他隻身前往馬賽,登上一艘法籍帆船成為見習生,開啟近二十年的航海生涯。他從船員一路做到船長;後來,他輾轉落腳英國,渡過三十年的寫作人生。他的作品捕捉各種人物的夢想、幻滅,與活下去的勇氣。他就是揭開現代英國文學序幕的船長作家康拉德。
充滿傳奇的兩段人生
康拉德是波蘭人,出生於波蘭南部一個小城(現烏克蘭西北部)。當時波蘭因列強瓜分而亡國,他父親參與獨立運動受到迫害,全家慘遭流放。艱苦的放逐生活重挫這一家:短短六年內,雙親相繼過世,小康拉德淪為亂世孤兒。
身為「異議份子」之子,康拉德很清楚唯有離鄉才能擁有自己的人生。他二十一歲踏上英國土地,加入英國商船服務。那時,他所知道的英文「不超過六個字」。他用第一份薪水買了《莎士比亞全集》,刻苦自學。莎翁精練的文筆深深影響康拉德;莎劇的悲情元素成為他日後寫作的一貫主題。
康拉德二十九歲歸化英國籍,順利取得帆船船長資格。跑船期間,他周遊東南亞、大洋洲等地,體驗異國文化。不過,他的航海夢過得並不順利。當時正值帆船航運沒落,穩定職缺難尋。康拉德三十七歲再次人生急轉彎:他決定回到陸地改行當作家。自學英文不到二十年便能以此外語專職寫作進而成為文豪,這項寫作成就在英國文學史上至今無人能及。
康拉德離鄉四十年後才再次踏上故鄉土地。或許因為長年漂泊異鄉,他終其一生寫下許多離散的故事,探究放逐與回歸的糾結。他於自傳寫道:「要解釋人性各種矛盾之間密切的依存關係,怎麼說也說不清:為何有時心中的愛會被迫以背叛的形態呈現。」《吉姆爺》正是一部把愛與背叛說個明白的傳世鉅作。
逐夢的代價
《吉姆爺》記敘一位流落異域的英國水手離鄉逐夢的故事。這部小說具有強烈的自傳色彩,是康拉德最知名的代表作。
吉姆從小嚮往成為冒險故事的英雄人物:「他永遠是盡忠職守的典範,跟書裡的主角一樣義無反顧」。然而,現實生活遠比冒險故事更為嚴苛。有次出航,吉姆服務的輪船遇上緊急事故,情急下他隨船員私下逃生。吉姆不僅當不成英雄,反而遭受吊銷執照的恥辱。這件海事醜聞讓他無顏返鄉,淪為「被放逐的海員」。他要如何扭轉失去榮譽的慘澹人生?一位歷盡滄桑的老船長徹夜說出吉姆不為人知的故事。
如莎劇《奧賽羅》所示,一個人若失去名節,生命將毫無價值;《哈姆雷特》則揭示,「要活,還是不要活,正是問題所在」。《吉姆爺》重溫莎翁大哉問:失去榮譽後,要如何保有尊嚴活下去?
吉姆在生死關頭選擇救自己,儘管有違職業操守,絕非懦弱無能。老船長很同情吉姆的處境:「坦然接受死亡的人不算少,卻很少有人會披上『決心』這堅不可摧的盔甲,在大勢已去的戰鬥中堅持到最後一刻」。吉姆身陷「物質世界生與死相互牴觸的訴求」,栽入自我救贖的深淵。這位青年的悲劇揭露一個殘酷真相:唯有「在毀滅的力量裡沒頂」,才能練就堅如磐石的生存意志「追逐夢想,直到永遠……」。
被夢想俘虜
為求谷底翻身,吉姆前往一處偏遠自治區擔任貿易代理人:
那片土地注定為他歌功頌德,從內陸的藍色山峰到海岸的白色浪花,無一例外。河流第一次轉彎後他就看不到大海了(大海辛勤的浪濤永遠升起又落下,消失再升起,正是勞苦人們的寫照),眼前是深深扎根在土壤裡無法動彈、迎著陽光賣力生長的森林。森林代代相傳的昏暗力量生生不息,就像生命本身。
吉姆在當地追剿盜匪、促進貿易,發揮武力征服的道德效益,成為傳奇人物。他的作為正如十九世紀中葉治理砂拉越的英籍「白王」(the White Rajah)布魯克(James Brooke, 1803-1868):以「白人主子」之姿爲英式殖民主義立下楷模。
吉姆在邊陲打造英雄國度的手段不僅「政治正確」,經濟行為也是如此。身為英國船員,吉姆很清楚當地農特產(燕窩、蜂蠟)極具經濟價值。他特別在當地開墾咖啡園。咖啡樹並非當地原生作物,十七世紀由歐洲人引入爪哇與蘇門答臘。該區高海拔山地所產之曼特寧咖啡(Mandheling)舉世聞名,成為重要輸出品。因此,從政治與經濟角度來看,吉姆的英雄大業有賴外界殖民體系庇護才得以實踐。
然而,如老船長指出,英國海員信奉一個核心價值:「必須堅定地相信我們自己種族的觀念是真實的」。同文同種的國族認同不可撼動:「我們必須在自己的族群裡奮鬥,否則我們的生命就沒有意義」。可是,吉姆遠赴「原始森林」,替他族奉獻青春。家鄉同胞該如何衡量吉姆的成就呢?老船長點出一個難題:「重點是吉姆沒有跟他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有所往來。所以問題在於,他最後有沒有接受某個比秩序與進步的規則更強大的信仰」。
吉姆能否超越強大的國族信仰,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老船長語帶保留:「他在那裡贏得的信任、名聲、友誼和愛情,既讓他成為主人,也讓他淪為俘虜」。吉姆在森林憂鬱的暮光下逐夢,了不可見的湛藍大海愈加遙不可及,歸鄉的衝動愈加徒勞無功。吉姆自始至終被白人的幻夢所擄獲,無法掙脫國族身分的詛咒。吉姆的掙扎令老船長不勝唏噓:「人的心夠開闊,裝得下整個世界。扛起重擔固然勇氣十足,但放下重擔的勇氣在哪裡?」。後來,吉姆再度被捲入愛與背叛的漩渦,最終被迫以激烈手段體現「放下重擔的勇氣」。
一九二四年八月,聲望如日中天的康拉德不幸與世長辭。法國作家紀德於悼文表示:「沒有人能像康拉德那樣瀟灑過活;也沒有人能像他那樣沉穩、敏銳、深具會意地將人生化為藝術。」紀德是一九四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非常崇拜康拉德。喜愛法國文學的康拉德晚年與紀德有密切的書信往來。紀德最欣賞的作品就是《吉姆爺》;長篇代表作《梵蒂岡地窖》第五部特引用《吉姆爺》名句作為卷首語:「只有一個辦法!只有一件事能讓我們治好自己」。康拉德逝世百年後,要如何治癒人生仍是無解的大哉問。故事結尾,吉姆「驕傲又無畏的短暫一瞥」看到了什麼答案?老商人揮別深山蝴蝶的手勢已默默道出一切。








 收藏
收藏

 二手徵求有驚喜
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