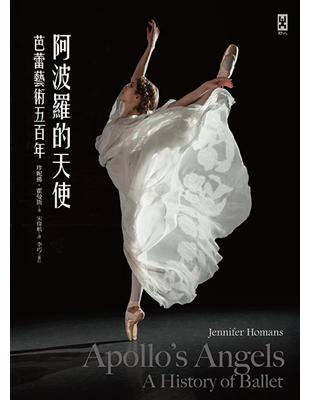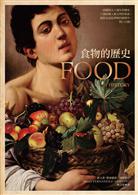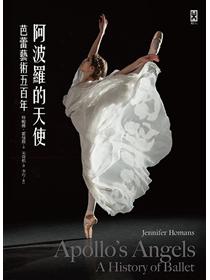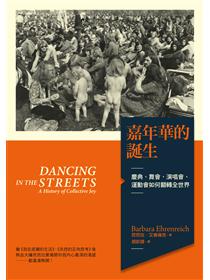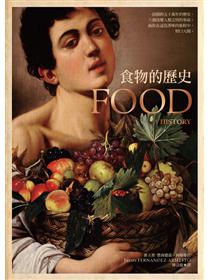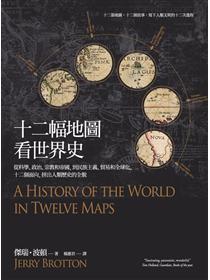章節試閱
【摘文1】
導言 名家和傳統
我的父母都在芝加哥大學任教,所以,我是在學術氣味濃厚的環境長大的。我不曉得當初我母親送我去學跳舞究竟是為了什麼,只知我母親愛看表演。說不定依她出身美國南方、注重禮節儀態的性子,芭蕾正合她的脾胃;而我家那一帶,也正好開了一所舞蹈學校,我母親自然送我過去學舞。那所舞蹈學校是一對老夫婦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有好幾支俄羅斯人的芭蕾舞團來到美國各地巡迴演出,他們便在其中一支舞團跳舞,順勢就留在美國。不過,老夫婦開的舞蹈學校跟一般常見的不同;沒有一年一度的《胡桃鉗》成果發表會,也看不到粉紅色的短蓬蓬裙和粉紅色的舞襪。老先生還罹患「多發性硬化症」,只能坐輪椅教課。所以,但見教室裡的他,耐著性子,強壓下火氣,用複雜難懂的辭彙詳述口令,學生則由老太太帶領,賣力做出老先生要的動作。芭蕾雖然也是人生的一大樂事──這一點,老先生當然不會略過──不過,芭蕾之於老先生,更是極其嚴肅的人生大事,不可等閒視之。
不過,將我帶進職業舞者一途的老師,卻是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物理博士的一名研究生。他以前當過職業舞者,我便是由他帶領,方才領悟芭蕾的一整套動作組成之精密、複雜不下於任何語言。芭蕾一如拉丁文或古希臘文,有其規則,有其詞性變化,有其詞尾變化。不止,舞蹈的法則更不是隨隨便便就訂下來的;舞蹈的法則一樣要符合自然律。跳得「對」,不是由誰的看法或喜好在指揮的。芭蕾也算是一門「硬科學」(hard science),有實際存在的物理現象作憑證。芭蕾另也富含感受和情緒,隨音樂和動作自然流瀉,扣人心弦。芭蕾還像默讀,有幸毋須出聲即可表情達意。不過,萬事俱備、配合無間之時,芭蕾洋溢的超脫欣快之感,說不定更是無與倫比。斯時,動作的協調和音樂的感受搭配天衣無縫,肌肉的爆發力和掌握節奏的技巧同聲相契──至此,人身便是一切的主宰。這時,「我」,就可以放手不管。而「放手不管」之於舞蹈,像是萬事皆休:大腦,軀體,心靈,一概放下,無所罣礙。我想,也就是因此,才有那麼多舞者都說,儘管芭蕾規矩多、限制多,舞動之際,卻像掙脫自我的束縛──澈底自由!
而接下來我又再有幸管窺芭蕾的奧妙,便是得力於喬治.巴蘭欽(George Balanchine, 1904-1983)於紐約創立的「美國芭蕾學校」(School of American Ballet)。我在那裡師事的前輩,全都是俄國人,全都是出身另一年代、另一國度、丰姿萬千的芭蕾伶娜。菲莉雅.杜布蘿芙絲卡,十九世紀末生於俄國,「俄國大革命」(Russian Revolution, 1917)之前在帝俄首都聖彼得堡的「馬林斯基劇場」(Maryinsky﹝Mariinsky﹞ Theater)芭蕾舞團跳舞。後來加入歐洲的「俄羅斯芭蕾舞團」(Ballets Russes),最後落腳美國紐約,以教舞維生。只是,我們學生都看得出來,她身上有一部分始終留在別的地方,留在離我們很遠、很遠的世界。她全身上下怎麼看,就是跟別人不一樣。濃妝,長長的假睫毛,氣味甜膩的香水。我記得她總是一身華麗的珠寶,深濃的藍紫色緊身舞衣搭配同色系的圍巾,雪紡裙外加粉紅色的舞襪;一雙非比尋常的修長美腿依然結實矯健,驚鴻一瞥,永世難忘。就算沒在跳舞,她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無不雍容透著華貴,優雅的儀態遠非美國少女所能企及於萬一。
此外還有:妙麗兒.史都華,英國舞者,有幸和安娜.帕芙洛娃(Anna Povlova, 1881-1931)同台共舞;安東妮娜.屯科夫斯基和海倫.杜汀,兩人都出身基輔(Kiev),也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移民美國。杜汀還瘸了雙腿,據說是在蘇聯被打斷的。不過,丰華最為耀眼的,或許還是首推雅麗珊德拉.丹尼洛娃。她於一九二四年和巴蘭欽一起從列寧格勒出亡。丹尼洛娃和杜布蘿芙絲卡很像,都曾是帝俄時代的舞者,都愛粉彩的雪紡紗,都戴蜘蛛腳一樣的特長假睫毛,都搽很濃的香水。她在俄國是父母早早雙亡的孤女,我們這些學生卻人人深信她系出貴冑名門,片刻也不曾懷疑。我們的儀態、我們的舉止,由她負責指導,不僅限於舞蹈課,日常生活也在內──不要穿T恤!不要彎腰駝背!不要吃路邊攤!她諄諄告誡我們:舞者所學、所選的行當,就是與常人不同;舞者的樣子,就是要和「其他人」不一樣。這些話,當時在我覺得十分正常,卻也十分怪異。說是「正常」,是因為我知道我們這些老師都是名家,傳授的一定是很重要的學問。而且,站得筆直,行動優雅,專心致志奉獻於舞蹈,不管怎樣,確實襯得我們和其他人不太一樣。我們真的像是「天之驕子」,或,自以為是「天之驕子」吧。
不過,感覺卻還是很怪:沒有誰會好好把其中的道理講給你聽,教學法都很專橫,專橫到很討厭。在他們面前,我們作學生的本分就只在模倣、吸收,尤其要乖乖聽話。我們這些俄國老師講話再客氣,也只擠得出「麻煩你」幾個字。一聽有人問起「為什麼」,不是輕蔑苦笑,就是乾脆當作耳邊風。我們還不准到別的地方學舞(有的規定我們這些學生還是懶得去管,這一條便是)。這樣的作風在那時候實在格格不入。我們都是一九六○年代長大的孩子,聽人滿嘴權威、責任、忠誠,感覺像是遇到了天大的老古板,時地一概不宜。只是,我對這些俄國老師教的東西興趣太濃,捨不得放棄或是跑掉。最後,學了多年,看了多年,終於領悟我們這些老師不僅在教舞步,不僅在傳授舞蹈的技法。其實,他們也在向我們傳授他們身負的文化和傳統。「為什麼」,根本不是重點。舞步不僅是舞步。他們的人生、他們的呼吸,都是活生生的明證,展現的是(在我們看來)失落的過去──不僅關乎他們的舞蹈,也關乎他們身為舞蹈家、他們所屬的民族心中常懷的信念。
而芭蕾也不像是我們這紅塵俗世所有。以前我會(和我母親)排隊去看「波修瓦」(Bolshoi)、「基洛夫」(Kirov)芭蕾舞團的演出,跑到「大都會歌劇院」跟大家擠在水洩不通的站位席最後面,伸長脖子看「美國芭蕾舞團」(American Ballet Theatre)和米海伊爾.巴瑞辛尼可夫(Mikhail Baryshnikov, 1948-),或是擠在教室看魯道夫.紐瑞耶夫(Rudolf Nureyev, 1938-1993)示範芭蕾把杆練習。不僅芭蕾。那時候的紐約是舞蹈的活力中樞,什麼都看得到,什麼都學得到:瑪莎.葛蘭姆(Martha Graham, 1894-1991)、摩斯.康寧漢(Merce Cunningham, 1919-2009).保羅.泰勒(Paul Taylor, 1930-);爵士舞、佛朗明哥、踢踏舞;市中心還有小型實驗舞團在工作坊、倉庫演出。但在我,跳舞的首要理由,僅此唯一:「紐約市立芭蕾舞團」(New York City Ballet)。那時,巴蘭欽開疆拓土的舞蹈生涯已近蓋棺論定,所帶的舞團以藝術和知性的活力,在在震撼眾人耳目。我們學芭蕾的人,也都知道巴蘭欽在做的事很重要,從來未曾質疑過芭蕾凌駕一切的地位。所以,芭蕾才不會老;芭蕾才不「古典」;芭蕾才沒過時。還相反,舞蹈蓬勃的活力遠甚於以往;所展現者,遠非我們所知、所能想像。舞蹈填滿我們的日常生活,不管什麼舞步、風格都要拿來分析,不管什麼規則、作法都要拿來辯論。我們對舞蹈的熱忱,直逼宗教信仰。
接下來幾年,我轉為職業舞者,追隨過好幾支舞團和編舞家,也發現舞蹈王國不是只有俄國人而已。我和丹麥舞者共事、同台演出,也和法國、義大利舞者一起粉墨登台,還試過古義大利派芭蕾名師發明的「切凱蒂教學法」(Cecchetti method),一度企圖拆解英國「皇家舞蹈學院」(Royal Academy of Dance)制訂的複雜課程。至於俄國舞者,這時期也不再局限於先前認識的那些老師而已。蘇聯舞者的技法,和杜布蘿芙絲卡那一輩的帝俄舞者南轅北轍。所以,情況就變得很妙了:芭蕾的語彙和技法看起來十全十美、普世通用,各國的派別卻又各自分立,獨樹一幟。例如美國這邊由巴蘭欽教出來的舞者,做「阿拉伯姿」(arabesque)的時候,臀部會跟著腿部上揚,也愛利用旋轉來加強速度,強調延伸和跳躍的線條。英國舞者看了可會面如土色,覺得這樣的旋轉「不雅」;英國舞者偏好含蓄內歛的風格。丹麥舞者則以乾淨、俐落的足下工夫(footwork)和敏捷、輕盈的跳躍見長。這和他們跳舞的重心是放在腳掌的前半部,腳步不會拖泥帶水有部分關係。但是,腳跟不放下來,就永遠做不到蘇聯舞者特有的優雅飛躍和彈跳。
此間的差別,不僅在美感而已:感覺就是不會一樣。舞者選擇這樣子跳而不那樣子跳,當下,就會像是變了個人。《天鵝湖》和《競技》(Agon)同為芭蕾,卻天差地別。沒有人有辦法將各國的變體全都一手掌握。身為舞者,就必須作出抉擇,而且,事情還沒這麼簡單。每一派別又各有其離經叛道的異端:總會有舞者覺得另有更好的方法來組織肢體動作,而帶著一幫人離開,自立門戶。所學者何,也就是追隨哪一位宗師或哪一門派,決定你是怎樣的舞者,決定你想當怎樣的舞者。整理各方的爭論,抽析其中狡辯和夾纏不清的詮釋(暨個人之)兩難,每每教我愈罷不能,但也極為費力。所以,我還要再等一陣子,才開始懂得要問:這些國家流派的差別是怎麼出現的?又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有其歷史淵源嗎?若有,又是怎樣的呢?
那些年,我從沒想過芭蕾未必是當代的藝術,未必是「此時此刻」的藝術。芭蕾的歷史再古老,演出時,不交給年輕的舞者去跳也不行,因此,免不了會染上年輕舞者特屬年代的色彩。此外,芭蕾不像戲劇或是音樂,芭蕾沒有文本,沒有統一的記譜法,沒有腳本,沒有樂譜,僅有的文獻紀錄也極其零散。芭蕾不以傳統、歷史為限。巴蘭欽就鼓吹這樣的看法。巴蘭欽生前於無數訪問即一再解釋,芭蕾來了又去,像花開花謝或濤生雲滅,舞蹈是存在於當下的「瞬時藝術」(ephemeral art);也就是之說,舞蹈純粹「活在當下」──我們說不定明天就不在人世了呢。巴蘭欽言下之意,似乎是發霉的老舞碼,例如《天鵝湖》,就不要再翻出來演了,而是要「日新又新」。不過,這樣的訓誨用在舞者身上卻顯得矛盾:舞者隨目所見不盡皆是歷史?何新之有?在老師身上、在舞者身上,連巴蘭欽自己編的芭蕾,也可見斑斑盡是歷史,寫的全是對往昔的回憶和浪漫的遺風。只是,我們舞者卻以「永不回頭」為信仰的圭臬在膜拜,堅決將目光鎖定在眼前的當下。
之所以如此,便在於芭蕾沒有固定的文本可依循,便在於芭蕾是以口述和肢體動作傳世,像荷馬的史詩,是口耳相傳的敘事藝術,植根於往昔者,只會多,不會少。舞蹈其實也不是一無所本,只是未曾形諸文字:舞者習舞,不一直就是練習再練習,把舞步、變化、儀式、作法練得滾瓜爛熟嗎?這些,確實有可能隨時間而改變或是替換;只是,舞蹈的學習、演出、傳世,作法一直極為守舊。舞蹈前輩向後生晚輩示範舞步或是變化,依舞蹈這一行的倫理要求,後學只能嚴格遵守、敬謹奉行。兩方自然也都認為,老、少兩代傳承的知識經過千錘百煉,當然出類拔萃。以我自己為例,丹尼洛娃教我們《睡美人》的變化組合時,我就絕想不到要質疑她傳授的舞步和風格。她的每個動作,我們一概緊跟不捨。大師教的一切,確實因為有其美感和邏輯,才會備受後輩尊崇。但也因為大師所教的一切是後輩和過去歷史唯一的聯繫,因而不得不奉為圭臬──丹尼洛娃當然清楚這一點。這樣的關係,便是前輩大師和後生晚輩牢不可破的紐帶,銜接起數百年的流變,為芭蕾在過往歷史找到牢固的根基。
所以,芭蕾其實是存在記憶而非歷史的藝術。也難怪舞者一個個像著魔一樣,什麼都要去背:舞步、手勢、組合、變化、一整支芭蕾舞碼。絕非誇大。記憶確實是芭蕾藝術傳遞的中樞。舞者的訓練,便像芭蕾伶娜娜塔麗雅.瑪卡洛娃(Natalia Makarova, 1940-)說的,就是要把舞碼「吃下肚去」,也就是要將之消化吸收,然後長在自己身上。這樣的記憶叫作「身體記憶」(physical memory),亦即舞者會跳的舞碼,是牢牢記在身上的肌肉、骨骼裡的。舞者的回憶訴諸官能,就像法國作家普魯斯特對瑪德蓮蛋糕的回憶,不僅勾起學過的舞步,也勾起手勢和動作,也就是丹尼洛娃說的:舞蹈的「幽香」(perfume)──還有舞蹈的前輩。也因此,舞碼的資料庫不在書頁,不在圖書館,而是在舞者身上。芭蕾舞團大多還會特別指派幾人擔任「記憶庫」(memorizer)──有的舞者擁有非凡的舞碼記憶力,凌駕同儕──負責背下舞團推出的舞碼。這類舞者就像芭蕾的書記(兼學究),將全套舞碼記在四肢、身軀,(往往)還和音樂配合同步,音樂一響,就會觸動肌肉,將舞碼從記憶庫裡抓出來。不過,舞者的記憶力再好,生命也有終了的一天。所以,每消逝一世代的舞者,芭蕾就失去一段歷史。
也因此,芭蕾舞碼的資料庫人盡皆知:少得可憐。「古典舞碼」少之又少,「經典文獻」寥寥無幾。目前我們擁有的古代芭蕾舞碼屈指可數,大多出自十九世紀的法國或是帝俄末年。其他的時代就比較近了: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的作品。於後文可知,十七世紀的宮廷舞蹈是留下了些許記載,但是,這類舞譜使用的符號,十八世紀便已失傳,爾後也一直未見換新。以至這類宮廷舞蹈像是切出來的快照,前、後都找不到。其餘,也只剩斑駁的星星點點,滿是漏洞。有人可能以為法國芭蕾應該還保存得不錯:因為,古典芭蕾的基本規則於十七世紀的法國已經編有定制,之後,芭蕾藝術於法國的傳統也始終流傳不輟,迄至今日。不過,真說有,也跟沒有差不了多少。例如《仙女》(La Sylphide)一劇,一八三二年於巴黎首演,但是,首演的版本很快就湮滅無存。我們現在的版本是一八三六年於丹麥推出的新舞碼。《吉賽兒》(Giselle)也一樣,一八四一年於巴黎首演,但是,我們現在看的版本是一八八四年的俄羅斯新編版本。再如一八七○年問世的《柯佩莉亞》(Coppélia),十九世紀的法國芭蕾至今演出依然(多少)沿襲原始舊製的,其實僅此唯一,就這一齣而已。
就是因為這樣,大多數人才會以為芭蕾是俄羅斯人的舞蹈。馬呂斯.佩提帕(Marius Petipa, 1818-1910)這一位法國芭蕾宗師,一八四七年起就在帝俄宮廷任職,直到一九一○年辭世。他在聖彼得堡推出一支又一支新創的芭蕾舞碼。一八七七年有《神廟舞姬》(La Bayadère);一八九○年是《睡美人》;《胡桃鉗》和《天鵝湖》則分別於一八九二年和一八九五年首演,後二者同都和列夫.伊凡諾夫(Lev Ivanov, 1834-1901)合作。米海伊爾.福金(Mikhail Fokine, 1880-1942)的舞作,《仙女們》(Les Sylphides),也是現在依然常見演出的舞碼,首演就是在一九○七年的聖彼得堡。馬林斯基芭蕾舞團調教出來的法斯拉夫.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y, 1890-1950),一九一二年於巴黎推出他的創作:《牧神的午后》(L’après-miodi d’un faune)。再如巴蘭欽,也是出生於聖彼得堡,雖然名下諸多偉大的芭蕾作品都是在巴黎或紐約創作出來的,但是,追究起巴蘭欽舞蹈的根源和訓練,還是要回溯到俄國。以至我們說的芭蕾經典文獻,描寫的傳統一面倒向俄國,而且,論起源,再早也只追得到十九世紀末年。因此,以西方音樂來作比擬,這樣的情況就很像是西方的音樂經典從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 1840-1893)才算開始,一待寫到史特拉汶斯基(Igor Fyodorovich Stravinsky, 1882-1971),就戛然而止。
不過,芭蕾的相關文獻即使不多,芭蕾於西方文化史的位置卻不容置疑。芭蕾確實是古典藝術。沒錯,古希臘人是不知道有芭蕾這樣的舞蹈。但是,芭蕾一如諸多西方文化、藝術,其源頭,都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時期,也都和西歐重新挖掘古代希臘、羅馬文物有直接的關聯。在那以後,歐洲各地的舞者和芭蕾名家便將芭蕾看作是復興古典的藝術,致力要將芭蕾的審美理想──暨名望──重新植根於五世紀的雅典。阿波羅(Apollo)於此,便占有一席特殊之地。阿波羅是主掌文明、醫療、預言、音樂的神祇。不同於牧神潘(Pan)和酒神戴奧尼修斯(Dionysus)手中喧鬧的排笛和鈴鼓,阿波羅演奏的樂器是古希臘小豎琴「里拉」(lyre),以溫婉、清幽的樂音撫慰人心。阿波羅高貴的儀表、完美的比例,代表人類的一大理想:節制沉穩、盡善盡美,體現了「人是萬物的尺度」。不止,阿波羅出身高貴,是眾神之神的天神宙斯之子,統帥眾家繆思(Muse)女神的主神。此輩繆思女神,也非等閒,一個個都是文化涵養深厚的美女,同為宙斯所出。還有,她們同為記憶女神倪瑪莎妮(Mnemosyne)之女也非偶然。繆思女神分別主掌詩歌、美術、音樂、滑稽啞劇(mime)、舞蹈(女神泰琵西克蕊﹝Terpsichore﹞)。
不止,阿波羅之於舞者,不僅是理想的典型。阿波羅之於舞者,是具體、有形的實在。舞者每天苦練,不論明知還是無意,為的都是要將自己改造成阿波羅的模樣。不只經由模倣,也不單靠先天條件傲人,另還要發自內心,由衷形之於外。每一位舞者於內在的心眼,都深深烙著阿波羅的英姿,常懷一心追求的優雅、勻稱和雍容,念念不忘。優秀的舞者全都明瞭,單單展現繪畫、雕像裡的阿波羅英姿或是模樣,還不算數。肢體的位置若要煥發萬鈞劇力,舞者就要想辦法變得開化,有文化涵養。所以,肢體的問題,從來就不僅止於賣力鍛鍊而已,還包含品行的陶冶。也就是因此,舞者每天早上在把杆旁邊站好,將雙腳擺出第一位置(first position),神情才會那麼專注。
從法國的凡爾賽宮到俄國的聖彼得堡,迄至二十世紀,阿波羅的英姿始終雄踞芭蕾世界,睥睨一切。阿波羅代表的理想,深植於芭蕾的核心。各地芭蕾名家創作的主題、所思所想,慣常皆以阿波羅為中心,絕非偶然。阿波羅的形象確實是芭蕾歷史的骨架。文藝復興時代的王公、法國的國王,就喜歡把自己扮成阿波羅,身邊還要安排成群繆思簇擁隨行。一支又一支芭蕾舞碼,常見阿波羅身披羽飾、一身金碧輝煌,完美的體態和非凡的比例,在在是芭蕾大師的昂揚身姿和傲人成就的反映。所以,芭蕾這一門藝術從問世之初,就深植阿波羅的英姿。待走到了另一頭,時隔約四百年,巴蘭欽於兩次大戰期間,也在巴黎創作出《繆思主神阿波羅》(Apollon Musagète),日後這一支舞碼他還一改再改,直到辭世方休。於今,舞者依然在跳《繆思主神阿波羅》,阿波羅也依然在將芭蕾往回推到古代的古典淵源。
至於天使呢?芭蕾一樣從一開始就將兩大世界:「古典世界」和「異教徒–基督徒世界」,兼容並蓄於一體。無以計數的輕盈、縹緲、大大小小的精靈、仙子,有的長有翅膀、有的淘氣搗蛋,優游於大自然的空中、林間。這些精靈、仙子,無一不像芭蕾,空靈,飄忽,瞬息即逝,宛如西方世界想像的夢中國度。於此,重點在翅膀。蘇格拉底說過,「翅膀的功用,在於將重物往上抬到空中,而空中便是眾神的所在。所以,凡屬軀體所有的一切,就以翅膀和神的關係最近」。因此,會飛的精靈、仙子當中,就屬天使與眾不同:天使和上帝的關係最近。夾在凡、神之間傳遞訊息的天使,便是連接凡、神、天、地的紐帶。這樣的天使,當然是芭蕾的一切,始終縈繞芭蕾舞台不去,始終是芭蕾的參照點,橫跨不同時代、不同風格,始終是芭蕾藝術追求的境界。阿波羅若是完美的肢體和人類文明、藝術的代表,那麼,天使便是舞者渴望飛翔,尤其是渴望昇華的代表──渴望凌駕凡塵俗世,超脫飛向上帝。
只是,古典芭蕾傳達的難道僅僅是心靈和昇華?古典芭蕾不也是凡塵的藝術,有性、有欲,而且,這一面比心靈、昇華還更明顯,昭然在目?天使於此,一樣是我們最好的嚮導:天使本身沒有性,沒有欲,卻可以(也往往)撩撥起情欲和渴望。芭蕾舞者很少會從他們的藝術感受得到情欲:縱使肢體交纏或是熱切擁抱,芭蕾卻因為脫離現實、扭捏造作、純屬人工製造,但又太費力氣、需要全神貫注,以至舞者涉身其中,很難真的撩起情欲。總之,芭蕾是純淨的藝術:每一動作都要琢磨到精簡之至,純粹之至,不沾一絲冗贅或雜質。芭蕾,就叫作「優雅」。但若芭蕾先天就摒除了情欲,芭蕾往往還是透著濃烈的感性和情色:舞者向來需要公然裸露大片肢體。只不過,這中間若真有絲毫「靈、肉」和「神、俗」兩端拉扯的張力,也很容易化解。芭蕾的舞蹈再放浪形骸,也還是美化過的藝術。
想當初,我決定為芭蕾寫一部舞蹈史,原本是要為我於舞蹈生涯遇上的諸多疑問尋求解答,但卻發現,我的疑問沒辦法單從舞蹈的觀點就求得答案。因為,芭蕾舞劇本身迷離又縹緲,因為,芭蕾沒有歷史的延遞,所以,芭蕾的歷史沒有辦法限定在芭蕾本身來作敘述,而要放進更廣闊的脈絡。只是,什麼脈絡呢?音樂?文學?美術?這些原本就是芭蕾內含的元素,只是於不同時代的分量未必相等罷了。所以,從任一角度切入去談芭蕾的歷史,都有其道理。也因此,我做的便是力求不以僵化的解釋模型為限。例如唯物論,也就是以經濟、政治、社會關係作為藝術主要(或是獨有)的塑造力。或是相反的唯心論,以藝術作品的意義純粹存在於其文本,因而舞蹈應該以其舞步和形式規則來作了解,毋須訴諸舞者的生平或是舞蹈的歷史。二者,我皆不取。
另外,有人主張舞蹈尚未呈現觀眾眼前之前,不算真的存在,這一點我也未能苟同。因為,這樣的看法等於是以藝術作品所引發的觀者回應,而非作品本身之創作,來決定作品的意義。若是循此看法,那麼,全天下的藝術一概難有定論,一概變動不居。因為,這樣一來,作品的價值端看觀者是怎樣的人,而和舞蹈家原本(有意或無意)的意圖無關,和舞蹈家得以運用的語彙和理念無關。走到「觀者獨裁」這一步,依我的看法,徒然益增僵化、時代錯亂的困擾罷了。這樣的情形,和我們這時代執迷於變動和相對的觀點,脫不了關係。只是,即使我們不願率爾反對,勉與同意所有觀點都有其道理,但到頭來,卻只會放任思辨淪為虛妄而已──也就是不管作怎樣的批判和評價,一概變成「純屬個人意見」。所以,我在書裡是在講芭蕾的歷史,但也會拉開一點距離,對舞蹈作客觀的評價。這可不怎麼容易,因為,失傳的芭蕾舞碼太多,總不能拿這樣的舞步、那樣的舞步或舞句(phrase)來作論證就算了。不過,終歸要奮力一試。所以,我的原則便是常懷信心,以開放的心態,一秉所得的證據,建立批判的觀點,試行評論這一支芭蕾舞碼比那一支出色、又何以比較出色等等。若不如此,我們的歷史只會淪為一堆名字、日期和演出的集合體而已,根本稱不上歷史。
不過,我興趣最濃的,終究是芭蕾的形式,這也是當初吸引我一頭栽進芭蕾世界的主因。為什麼這樣的舞步要那樣跳?是哪些人發明芭蕾這般做作又泥古的藝術?於其背後推動的生命泉源又是什麼?法國人這樣子跳,俄國人那樣子跳,又是麼回事?芭蕾這一門藝術又是怎樣體現理想、民族或是時代的?芭蕾是怎麼演變成今天這模樣的呢?
這些問題,我認為可以循兩條途徑來處理。第一條途徑,狹窄而且集中:就是死守身體的動作,投身舞蹈藝術,盡力從舞者的觀點去看這一門藝術。縱使原始資料少得可憐,舞碼又大半皆已亡迭,但也應該未能嚇阻我們吧?於今,以古代和中古為主題的歷史著作,那麼豐富、那麼精采,所根據的原始資料不是還要更少?所勾畫的時代不是還更古老?即使是最稀疏的斷簡殘編,像是有人把芭蕾課上過的一段動作以草書信筆寫下,或是潦草塗寫的舞步組合,都是一盞盞明燈,照亮芭蕾的形式、理念和信念,讓歷史重新活了過來。因此,本書每寫到一階段,我就會重回舞蹈教室,重溫所知的舞蹈──自己跳,也看別人跳,力求對舞者認為他們在做什麼、又為什麼要這樣子做,有所分析和理解。芭蕾的技法和形式發展,是芭蕾歷史的核心。
芭蕾或許沒有連續不斷的歷史記載,卻未必等於芭蕾沒有歷史。還相反:世人跳芭蕾、表演芭蕾,至少有四百年的歷史了。古典芭蕾起自歐洲宮廷,於其濫觴,除了是藝術,也是貴族的禮儀兼政治活動。其實,芭蕾的歷史和國王、宮廷、國家命運的牽連,可能遠大於其他表演藝術。歐洲貴族從文藝復興時代開始的世道流變,芭蕾一體概括承受,而且,糾葛還十分複雜。芭蕾的舞步從來就不僅是舞步;芭蕾的舞步也是一套信念,芭蕾的舞步於一靜一動當中,流露當時貴族階級為自我勾勒的形象。芭蕾和外界的廣大關聯,在我看,便是了解芭蕾藝術的根源:若欲了解芭蕾的源起、了解芭蕾的流變,最好的門道,就是從過去三百年的政治和思想的動盪劇變來作觀照。芭蕾,是由歐洲的文藝復興和法國的古典主義,由各國的革命和浪漫主義,由表現派(Expressionism)和俄國的布爾什維克(Bolshevism),由現代主義(modernism)和冷戰,塑造而成的。芭蕾的歷史,確實是更宏大、更壯闊的歷史之流。
芭蕾的歷史進程,當然也有走到日薄西山的一天。於今,世人普遍視芭蕾為老派、過時的舞蹈;在當今步調愈來愈快、紛擾混亂的世界,芭蕾確實顯得格格不入,扭捏侷促。前一偉大世代走到強弩之末,既恭逢其盛,也親眼目睹其日益衰頹,這樣的變局,在我們不可不謂巨大。我第一次見到杜布蘿芙絲卡,是約三十五年前的事。芭蕾那時還有天時、人和,生氣勃勃一如以往,現在卻大不如前了。不過還有零星幾處地方,有人始終熱愛芭蕾未減,也有幾處地方始終看重芭蕾不輟,所以,芭蕾說不定終有一天能夠重新站回文化旗手的位置。但是,過去三十年,世界各地的芭蕾無一不從高峰墜落卻也是不爭的事實。這樣的事實容或遺憾,也不是有害無益:至少芭蕾不再身陷藝術創作的颱風眼。或許有所失落吧,但起碼目前的失落,也因此給了我們時間回顧過往,思索過往。這樣,我們反而能把芭蕾的歷史看得更透徹,而有辦法真的開始講述芭蕾的歷史。
【摘文2】
法國國王亨利二世(Henri II, 1519-99),一五三三年迎娶佛羅倫斯貴冑凱瑟琳.德梅迪奇(Catherine de Medici, 1519-1589)為后,法、義兩地的文化也像締結了緊密、正式的盟約,芭蕾的歷史,於焉開展。法國宮廷耽溺逸樂,歷有年所。馬上比武、長槍競技、化妝舞會等等,樂此不疲。不過,法式娛樂縱使刺激、豪華,比起米蘭、威尼斯、佛羅倫斯貴族擺出來的排場,可就望塵莫及,像是火炬舞、繁複的馬術芭蕾(horse ballet),數百名騎士策馬排出圖形,還會穿插幕間短劇,由臉戴面具的演員演出英雄、寓言或是異國主題的故事。
當時便有遊走義大利大城的芭蕾名師,古列摩.埃伯雷歐(Guglielmo Ebreo, c.1420-c.1481),一四六三年於米蘭描寫他見過的慶典盛會,計有燦爛煙火、走索特技、魔術等表演,外加二十道大菜,一道道菜全由純金餐盤奉送上桌,桌邊散布多隻孔雀四下游走助興。一四九○年,另一場盛宴,還有文藝復興美術大師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出手相助,在米蘭將《天堂盛宴》(Festa de paradise)搬上舞台演出,主角是七大行星外加眾神信使墨丘利(Mercury)、美慧三女神(three Graces)、七大美德(seven Virtues)、寧芙(nymph)、阿波羅。義大利人也愛跳簡單卻優雅的社交舞,時稱「芭里」(balli)或「芭蕾蒂」(balletti),舞蹈的走動步伐雍容高雅、講究韻律,一般見於正式的舞會和儀典,偶爾也穿插在動作程式化的「默劇」(pantomime)當中演出。這樣的舞蹈,由義大利傳到了法國,便叫作「芭蕾」(Ballet)。
凱瑟琳.德梅迪奇(嫁進法國王室的時候,年方十四),於法王亨利二世一五五九年駕崩之後,在法國宮廷聽政多年,義大利的品味隨之移植到了法國宮廷,朝臣爭相效尤,連國王也未能免俗。凱瑟琳的兩個兒子,先後繼任大統的法國國王查理九世(Charles IX, 1550-1574)和亨利三世(Henri III, 1551-1589),追隨他們母后的腳步,同樣愛看米蘭、那不勒斯舉行的花車、戰車、寓言故事大遊行,也和他們母后一樣熱中儀典和戲劇活動。法國在兩位國王任內,連純粹天主教的遊行,都變形為多采多姿的假面舞會。兩位君主也都以愛在夜間漫步街頭出名,還偏好「反串」(en travesti),披戴金絲、銀線的面紗,搭配「威尼斯面具」(Venetian mask),身邊簇擁的群臣也作同式樣裝束。歌、舞表演多以騎士的俠義事蹟作主題,連馬上展技也以生動的戲劇情節作穿插拼貼,例如一五六四年在楓丹白露(Fontainebleau)就有一場長槍比試,編排成全本的圍城劇碼,由妖魔、鬼怪、巨人、侏儒代表六位受俘的美麗寧芙出戰。
這樣的節日慶典,豪華絢爛的排場看似歡樂無限,卻絕對不是無聊隨便的餘興、消遣而已。法國於十六世紀長陷連年的內患和宗教衝突,難以化解又兇殘野蠻。所以,幾位法國國王借鑑義大利文藝復興思潮和王公貴族贊助藝文的深厚傳統,認為這樣的壯觀盛典(spectacle)可以安撫人民的激情,消弭派系的動亂。然而,凱瑟琳.德梅迪奇本人絕非開明包容的典範。一五七二年,巴黎「聖巴托羅繆節」(St. Bartholomew’s Day)胡格諾(Huguenots)信徒遭屠殺的慘案,她便脫不了關係。不過,慘案再兇殘,也遮掩不了凱瑟琳和凱瑟琳先後登基的二子還有諸多時人,都衷心希望戲劇活動發揮政治效能,化解緊張對峙的情勢,綏靖交戰之各方的事實。
查理九世就是秉承這樣的精神,於一五七○年取法佛羅倫斯文藝復興時期著名的「柏拉圖學院」(Platonic Academy),支持創建「詩歌音樂學院」(Académie de Poésie et de Musique),從法國詩壇徵召名家入駐,尚–安東.德巴伊夫(Jean-Antoine de Baîf, 1532-1539)、尚.多哈(Jean Dorat, 1508-1588)、皮耶.德宏薩德(Pierre de Ronsard, 1524-1585)等人便都在列。這一批詩人奉行「新柏拉圖主義」(Neo-platonism),深信分崩離析的政治動盪,於表相之下,潛藏神聖的和諧和秩序──這是由理性和數學關係交織成的網絡,體現宇宙的自然律和上帝的神祕權柄。人世於可知的世界之外,另有神祕、完美的境界存在。他們將自身虔誠的宗教信仰和這類柏拉圖理念融會一氣,致力改造基督教會,且不循天主教儀的路線,而改以戲劇和藝術的途徑,尤其訴諸古代異教世界的古典傳統,廣邀演員、詩人、音樂家合作,希望為盛典打造嶄新的氣象,藉由古典希臘詩歌雄壯的節奏,將舞蹈、音樂、語言融會為頓挫有致、抑揚有節的一體。他們認為數字、比例、設計,可以照亮宇宙晦暗不明的秩序,從而彰顯上帝。
新創的學院將祕教神學、玄奧法術、嚴謹的古典格律融於一爐,淬鍊出堅實的體系,展現獨樹一幟的理想:音樂和藝術可以召喚世人發揮最大的能力,追求至高的目標。而這中間的關鍵,便在於將精神和學習轉化為具體的戲劇效果。所以,詩歌音樂學院提出廣納百科的求知道路,自然哲學、語言、數學、音樂、繪畫、軍事,盡皆包含在內。有擁護者後來說明,這樣的道路通往的目的地,在淬鍊凡人「身、心俱得完美」。音樂──「數學美麗的一面」──於此占有特別的一席之地,因為,音樂有天體和弦(celestial harmonies)、畢達哥拉斯的邏輯、濃烈情緒的穿透力,在他們眼中,具有無與倫比的感染力。所以,當時才有言曰(套用柏拉圖的思路),「詩歌,便是靈魂的魔咒」。或如詩歌音樂學院本身的規章所言,「音樂失去章法,道德便會淪喪,音樂條理有序,世人即能知法守法」。
舞蹈亦復如是。詩歌音樂學院視芭蕾為軀策凡人騷亂情感、肉欲,朝上帝超越、將大愛昇華的機會。凡人的肉身,長久以來一直為人看作是人類墮落的源頭,導致人類為了滿足物欲而犧牲崇高的精神。「存在的巨鏈」將所有生命從最低的植物、礦物往上排到天使。天使所在的位階最高,離上帝最近。人類則被分配在中間,顫巍巍掛在野獸和天使之間。人類再高尚的精神嚮往也會受限凡人於塵世的覊絆,和肉身鄙陋的機能。
但若凡人懂得跳舞呢?詩歌音樂學院諸公認為,那麼,人類很可能就可以打破這樣的塵世覊絆,而將自己往上昇華,離天使更近一點。人身的動作有詩歌的節奏和格律作節制,輔以音樂、數學的原理作調和,應該可望和天體和弦同聲相契。法國的教士龐杜斯.德蒂亞赫(Pontus de Tyard, c.1521-1605),是當時和詩歌音樂學院來往相善的詩人,便曾以人文主義特有的用語為這樣的主張尋找支持的邏輯:「兩隻手臂平展,兩腿拉到最開,便是一人的高度,頭長乘以八或九或十,依該人身材,也正是一人的高度。」當時縱橫藝文界的梅仙神父(Abbé Mersenne, 1588-1648),一六三六年就是因為有感於這般完美的數學比例,而將「宇宙造物主」形容成「絕妙的芭蕾大師」。
詩歌音樂學院的藝術家為了將他們崇高的理想注入戲劇,殫精竭慮要將當時的詩歌、音樂,套進希臘詩歌的格律。他們依照一套長短音節和音符,為舞步標出格律,據此訓練舞者的手勢、行走、跳躍等動作,一概依循音樂和詩歌的節奏來進行。演員每逢星期天即出動,為國王和其他主顧演出。當時的宮廷表演,都是熱鬧的社交場合,吃喝、喧嘩司空見慣。詩歌音樂學院裡的音樂會可就大異其趣:全場鴉雀無聲,音樂、舞蹈表演一旦開始,就不准任何人再進場入座。因為有此虔敬的氣氛,後世天主教思想家才會那麼欣賞詩歌音樂學院諸公,奉之為「眾基督教奧菲斯」,因為,他們以身體力行,證明音樂訓練是可以讓「全高盧(Gaul),其實應該說是全世界,都和上帝至高的榮耀遙相應和,每一顆心,都有神聖的愛火熊熊怒燃」。
一五八一年,學院的研究終於開花結果,推出了《王后喜劇芭蕾》(Ballet comique de la Reine)。這一齣芭蕾是為了慶祝當時法國王后的妹妹瑪格麗特.德佛特蒙(Marguerite de Vaudémont, 1564-1624),下嫁權傾一時的重臣喬尤斯公爵(Duc de Joyeuse, 1560-1587)而作公演。公爵本人也大力支持學院。這一齣《王后喜劇芭蕾》是當時婚宴七大慶典之一。其他慶典包括武術表演、馬術芭蕾、煙火施放等等。學院的詩人以古代的風格籌備皇室大婚的慶典,揉和詩歌吟唱、音樂、舞蹈。芭蕾於巴黎的「小波旁劇院」(Petit-Bourbon)大廳演出,只限「顯要名流」入場觀賞。不過,華麗的盛典免不了招徠數以千計的群眾蜂擁朝皇宮前進,爭睹盛典。表演的時間是晚上十點開始,這在當時並不特別;而且,一旦開始就幾近六小時,直至夜深久矣方休。
盛典的排場十分豪華,卻不失親切。那時還沒有挑高的舞台,所以,《王后喜劇芭蕾》的演員就雜處在觀眾當中演出。故事講的是一則寓言,女妖瑟西(Circe)最終為威力強大的古羅馬女神蜜娜娃(Minerva)和天神朱彼特(Jupiter)聯手所敗。當時的芭蕾編導和畫家一樣,創作時多半一本神話大全在手。厚厚的一大本參考書,詳列男女眾神的寓言和象徵。芭蕾裡的故事,因此交疊出複雜的層次,但都不會超出當時觀眾心領神會的範疇:感性臣服於理性和信仰的故事(明顯直指當時的宗教狂熱,毫不避諱),國王和王后收服敵人,化解紛爭,最終是和解與和平稱勝(此劇芭蕾首演之時,距離「聖巴托羅繆節大屠殺」,年僅九年)。當時的義大利舞蹈名家巴特扎.德博喬瓦(Balthasar de Beaujoyeulx, ?-c.1587),為這一齣芭蕾寫序,「如今,歷經諸多動盪不安……芭蕾勢必昂然矗立,成為貴國國力和團結的象徵……血色終於重返各位的法蘭西」。
《王后喜劇芭蕾》的目的,也就在證明這一點。德博喬瓦負責編舞(當時有人奉他為「創意獨一無二的幾何學家」),舞者循測量精準的舞步編排,在地板勾畫造型完美的圖案:圓形、正方形、三角形。每一圖案都在證明數字、幾何、理性何以能將宇宙和人類的靈魂組織有序。表演到最後,女妖瑟西終於低頭,向國王獻出她的魔杖,接著是「豪華芭蕾」(grande ballet)上場,由十二位「水仙」(naiad)身著白色舞衣,四位「樹精」(dryad)身著綠色舞衣,和王后還有幾位公主一起排出長條隊形和圖案再作重組。「一個個舞者動作皆極靈巧,位置始終不亂,節拍也始終準確,」德博喬瓦寫道,「看得觀眾直呼阿基米德再世所展現的幾何比例,也不脫此等景況。」德博喬瓦希望看過此齣芭蕾的人,「知所敬畏」。
許多人確實是敬畏有加沒錯。《王后喜劇芭蕾》於當時備受讚揚,後來還深烙法國大眾的記憶,成為新類型舞蹈的濫觴,也就是所謂的「宮廷芭蕾」(ballet de cour)。中古的盛典於當時依然盛行不輟,不過,不受拘束的作風因為此劇問世,而如一名學者所說,加上了「強固、嚴謹的古典精神」。《王后喜劇芭蕾》問世之前,法國宮廷演出的舞蹈,比較像以漂亮瀟灑的姿態在走路,稱不上是芭蕾。反之,《王后喜劇芭蕾》既有形式格律,也有設計構想,顯然在以舞蹈和音樂作為宇宙秩序的度量。此劇作者做出具體可見的精準形式,一心要將每一舞步的幅度、節拍、格律、幾何,全都搭配完美,再加上心靈嚮往的境界遼闊浩瀚,而為現今世人所知的古典舞蹈技法奠下了基礎。近一世紀後,幾位芭蕾宗師於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的時代,秉承此一基礎,再度循嚴格的幾何原則,將芭蕾的舞步組織成系統,編成定制。
《王后喜劇芭蕾》問世,宮廷芭蕾崛起,像是一道分水嶺,將之前、之後的舞蹈作了分流。新式的舞蹈類型因此蒙上嚴肅、甚至宗教的理想,而踏入法國知識和政治的領域。起自文藝復興人文精神的強烈理想主義,因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而益發壯大,促使詩歌音樂學院一派藝文涵養深厚的文人,相信舞蹈、音樂、詩歌若是融會一氣,創作出搭配無間的盛典,那麼,塵世情欲和精神超越二者之間的深壑巨壘,可能真的可以因此搭起一座橋梁,將兩邊聯繫起來。這樣的嚮往,是極為艱鉅的工程,卻始終未曾真正消減,即使在懷疑論盛行的年代,這樣的看法有時會遭遺忘或是反駁,但卻從未真的根除。創作出《王后喜劇芭蕾》的藝術家,衷心期望提升人類的生命境界,將凡人從「存在巨鏈」的位階,往上拉抬到更接近天使和上帝的地方。
不過,那時代倒也不是人人都懂得《王后喜劇芭蕾》有何重要意義。有的觀眾容或敬畏有加,有的觀眾卻是氣憤有餘。他們質疑法國正逢內亂頻仍、杌隉不安的多事之秋,國王怎麼反而浪費鉅資在豪華的娛樂?當時,法國亨利三世已經因為耽溺詩歌音樂學院的事務,荒廢其他,備受抨擊也有不短的時間了。還有人在學院詩人和國王見面的房間釘了一張告示,指控「法蘭西無處不因內亂而遭重擊,已漸傾頹,吾王卻還大作文法練習」。告示罵的不是沒有道理;亨利三世當朝期間,法國鮮有寧日,此仆彼起的動亂未幾便將詩歌音樂學院諸公高蹈、熱切的嚮往沖垮。亨利三世注定不得善終的統治,也終告結束。亨利三世被親西班牙的反動「天主教聯盟」(Catholic League)逼得從巴黎出亡,雖然想辦法派人殺了聯盟的領袖,自己卻也在一五八九年命喪一名修士之手。
不過,《王后喜劇芭蕾》首度淬鍊出來的理念,於後世卻投下深遠的影響。進入十七世紀之後,著名的科學家、詩人、作家回顧起詩歌音樂學院於前一世紀的成績,依然不勝欽羨,尤其是歐洲當時又掀起了一波新的動亂:「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 1618-48)。梅仙神父位於巴黎「皇家廣場」(Place Royale)米寧修道院(Le Couvent des Minimes)的居所,在十七世紀前半葉,也成為歐洲知識界的「辦公室」(Bureau de poste)。不僅梅仙本人為宮廷芭蕾提筆為文,他的交遊圈也有多人愛討論宮廷芭蕾這一門藝術,例如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69-1650)。有一些人甚至下海寫芭蕾。笛卡兒一六四九年就向瑞典王后呈獻過一齣芭蕾,《和平誕生》(Ballet de la Naissance de la Paix),當時他已不久人世。芭蕾於宮中依然占有一席中心之地。當時的法王亨利四世(Henri IV, 1553-1610)之后,瑪麗.德梅迪奇(Marie de Medici, 1571-1642),出身義大利的佛羅倫斯,不僅每逢週日就在她的宮中舉行芭蕾演出,還增加場次。瑪麗所生之子,法王路易十三(Louis XIII, 1601-1643),本人甚至還是相當優異的舞者,極愛表演。
只是,今昔到底無法相提並論。路易十三朝中,詩歌音樂學院標榜的新柏拉圖理想,就算陰魂不散,較諸工具價值更高的「國家利益」(raison d’état),當然就黯然失色。路易十三和朝中權傾一時、人人敬畏的首相,樞機主教黎希留(Cardinal de Richelieu, 1581-1642),聯手要將派系紛雜、內鬥不休的法國再度團結在國家強化的鐵腕之下,因而將國王的權柄拉高,雄踞在「絕對王權」的巔峰。這樣一來,芭蕾的意義和特性連帶就不同於以往──不止,衡諸情勢,也不得不然。路易十三和黎希留關心的,權力多過上帝。所以,宮廷芭蕾不再以彰顯宇宙秩序為主,改以擴張君王的聲威為要。也因此,《王后喜劇芭蕾》展現的嚴肅知性,也改由空泛、諂媚的風格取代。這樣的風格,此後深深烙在芭蕾之上,長久未得以褪去。
路易十三本人親自為芭蕾寫腳本,設計舞衣,常常還會下海在宮中芭蕾製作群中挑大梁。他喜歡演太陽,演阿波羅,將自己刻畫成人間的神,子民的君父。不過,路易十三朝中的芭蕾,卻絲毫不見沉悶呆板或自鳴得意,還不時穿插滑稽、色情、特技的場面作調劑,連奇奇怪怪的淫穢情節或是含沙射影遙指宮中的流言,也不忌諱。結果反而更為風靡,效果更為宏大。當時就有觀眾抱怨,有一場演出竟然出現四千人都想擠進羅浮宮大廳的亂象。也曾聽說為了爭睹國王本人粉墨登場的人潮太過洶湧,反而把國王的去路擋得水洩不通,大廳還要固定安排弓箭手站崗,免得觀眾硬擠。王后有一次更因為擠不進去,氣得火冒三丈,拂袖而去。
現今常見的劇院,那時還沒問世。所以,芭蕾一般安排在宮殿、公園之類的大型場地,臨時搭建座位和布景,進行演出。那時還沒有後人說的「舞台」,也沒有「舞台鏡框」(proscenium arch)將演員托高或是圍住。演員於當時就是直接夾在大批群眾當中演出,等於和大型社交盛宴融為一體。觀眾席的座位一般是層疊往上堆(很像現在大型球場的露天看台)。所以,觀眾一般是從上往下俯視,這樣才有最好的視野,才看得清楚演員於演出場地刻畫的眾神、群仙,欣賞得到精心編排的圖形。那時沒有固定的天幕(backdrops),也沒有藏在觀眾視線之外的翼幕(wings)。布景反而是由台車推進來,擺在演員附近或是身後。不過,這樣的作法到了路易十三當朝的時候,也逐漸有所演變。義大利的布景設計師率先發難(他們有不少人都有工程師的背景),舞台開始從地面往上挑高幾吋,其他如翼幕、大幕、暗門、天幕,把雲朵、馬車拉到空中的起重機械,也陸續裝配就位。黎希留對豪華盛典有興趣,連帶也自己動筆寫起劇本,一六四一年,甚至在他自己住的宮殿蓋了一座劇場;日後又再經過改裝,就成了現在的「巴黎歌劇院」(Paris Opera)。
法國的戲劇連番出現創新,背後的想法其實很簡單:製造錯覺。那時,製造更壯觀、更神奇的舞台效果,像是違反物理定律或是理性邏輯的效果,已非難事。而把演員籠罩在一層蠱惑迷離的氛圍裡,尤其重要,特別是國王其人。這一點,關係極為重大。的確,黎希留既然一心要拉高國王的威權,國王的形象、國王其人,就變得益發重要。當時早就有政治學者主張法國的政府只存在於國王其人身上,國王的人身既無可分割,也神聖不可侵犯。時人認為國王的人身,內含他的國度──依當時一名大作家的說法,國王是國家的頭,教士是國家的腦,貴族是國家的心臟,「第三階級」(也就是平民階級)是國家的肝臟。這樣的說法,不僅是理論或比喻:國王一旦駕崩,國王身上的一些器官,像是心臟、腸子,一般還要摘取下來,存放在幾座與皇權關係密切的教堂,奉作聖髑。王室應該建立在血緣關係而非王位繼承的主張,隨十七世紀推進已經喊得愈來愈大聲;國王的人身於政治、宗教成為膜拜供奉對象的情勢,也變得愈來愈認真。進而有政治學家認為國王其人之所以身為人君,統治萬民,乃是出自「君權神授」(Divine Right):國王依其血緣和出身,比眾人更接近天使和上帝。
而強調崇拜國王人身的君主,沒人比得過法王路易十三的兒子,也就是繼位的太子,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小路易會那麼熱愛舞蹈,也非偶然──此前、此後都找不到第二位君主可以與之相提並論。一六五一年,路易十四以十三歲的稚齡首度亮相演出,此後總計於近四十部大型製作參與演出,直到十八年後,一六六九年,才以《植物誌》(Ballet de Flore)一劇告別舞台。路易十四天生就有比例優雅的體型,一頭纖細的金髮,被他的私人教師喻為「幾近乎神的儀表和舉止」,當時甚至有一些人視他為「上帝」化身的標誌(路易十四本人也作如是想)。但他還懂得要用功勤練,才能發揮他的肢體天賦。每天早晨起床的儀式過後,他會到一間大廳開始練習跳躍、擊劍、舞蹈。他有個人專屬的芭蕾老師,皮耶.波尚(Pierre Beauchamps, 1631-1705),為他作專門的指導。波尚每天指導國王,長達二十多年。路易十四為芭蕾進行排演,可以長達數小時不歇,甚至晚上還會回頭再作練習,直到午夜方休。
路易十四熱愛芭蕾,絕非年少輕狂而已。這是國家大事。路易十四日後也說過,想當年國王粉墨登台,朝臣與有榮焉,民心瘋狂擁戴,其效果「說不定遠甚於致贈厚禮或是博施濟眾」。路易十四遇到嘉年華會或是宮中有娛樂節目,甚至降尊紆貴,犧牲國王的色相,演出滑稽、小丑的角色,例如潑婦或是醉漢(反而益增國王的聲威)。不過,路易十四身上的極度信心和無窮野心,還是以崇高、尊貴的舞蹈表達得最為透澈;例如《時間》(Ballet du Temps, 1655)一劇,古往今來的時間一概匯聚於他當朝治下。他還扮過戰爭、歐洲、太陽,但最出名的,當然就是阿波羅了──一身羅馬長袍加上羽飾,象徵權柄和帝國。後來,路易十四連番出現高燒、暈眩的病症,當時認為是練習過度,逼得他不得不從舞台謝幕,不再演出。儘管如此,路易十四對於宮廷盛典的興趣始終未曾衰退。例如一六八一年初,《愛之勝利》(Le Triomphe de l’Amour)一劇,氣勢恢宏、服裝華麗,路易十四就出席至少六次排演和二十九場演出。
路易十四為什麼鍾情芭蕾到如此地步?法國於路易十四治下,專制趨於極致,古典芭蕾於此同時亦演進為體系完備的戲劇藝術,二者之間的關係──二者確實有關係──若要說得清楚,那就要回頭去看路易十四早年的生平,回頭去看他治下的法國宮廷獨具的特色。舞蹈於路易十四治下,不再是供作展示皇家威儀、權勢的招搖工具。路易十四將舞蹈融入宮廷生活,將舞蹈變成貴族身分的符號和條件,牢不可破,根深柢固。芭蕾藝術以至和路易十四一朝,永遠綁在一起。法國的皇室盛典和貴族的社交舞蹈,便是在路易十四朝中淬鍊得備加精緻、細膩。古典芭蕾的法則和常規,就是因為有路易十四青睞,而告孕生。
【摘文3】
瑪麗.塔格里雍尼,一八○四年生於非凡的義大利舞蹈世家。斯時,藝術正逢劇變,動盪難安。瑪麗的父親,菲利波.塔格里雍尼(Filippo Taglioni, 1777-1871),是義大利舞蹈家,家族有一長串先人都是所謂的「怪誕」藝人。若說塔格里雍尼家族專精的是特技和滑稽舞蹈,那麼,塔格里雍尼家族對於法國的老派高貴風格向來也忠心不貳。菲利波的父親,卡羅.塔格里雍尼(Carlo Taglioni, 1755-1835?),是出身義大利杜林的舞者;杜林於卡羅生前是義大利的法語區,居民向來傾心法國。一七九九年,菲利波本人還親自到法國首都朝聖,隨尚–馮蘇瓦.庫隆專攻古老的「高貴風格」。菲利波有一弟、一妹也都是舞者,和他一樣曾赴巴黎學舞。菲利波曾短暫供職於巴黎歌劇院,和皮耶.葛代爾合作推出《舞蹈狂》一劇。不過,菲利波於一八○二年就離開巴黎,周遊瑞典斯德哥爾摩、奧地利維也納等大城市,後於日耳曼和奧地利、義大利一帶巡迴演出,開創事業。菲利波居停巴黎的時間不長,卻正好是法國大革命過後的重要關頭。「高貴風格」於當時雖然支離破碎,不復原貌,但在老派的衛道人士手中,例如皮耶.葛代爾、庫隆一輩的大舞蹈家,卻多少還算安然無恙;菲利波因而有幸親炙大師的高貴風格。皮耶.葛代爾、庫隆一輩大師既然奉行前朝舊制的美學,菲利波也就像是這一系血脈的末代宗師。這一點十分重要,因為,菲利波日後教導女兒,便堅持女兒的舞蹈再離經叛道,也要保留一絲老派的雍容典雅。
瑪麗.塔格里雍尼生於瑞典的首都斯德哥爾摩,當時她父親正在瑞典國王宮中擔任芭蕾編導。瑪麗的母親,蘇菲.卡斯登(Sophie Hedwige Karsten),是瑞典著名歌劇演員之女。只是,芭蕾當時在斯德哥爾摩已經不見往日盛況。歐洲政治動盪,舞蹈身處其間當然不得倖免,斯德哥爾摩的狀況便是明證之一。芭蕾在瑞典原本有長遠的歷史,可以回溯到十七世紀。那時一連幾位瑞典國王皆以法國的極權政治為師,因而引進法國的宮廷芭蕾以為效尤。只是,到了一七九二年,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三世(Gustav III, 1746-1792)遇刺身亡,刺激瑞典民族自尊心高漲,商人階級和布爾喬亞聲勢鵲起,逼得貴族的特權一步步削弱。芭蕾因而頻遭時人抨擊為奢侈、放蕩,敗壞社會風氣,帶領民眾怠忽宗教、社會的職守,而宗教、社會的職守可是重要得多了。菲利波當然也感受到芭蕾在瑞典已經困入死巷,因而毅然轉進他國。
自此而後,塔格里雍尼家步上了到處奔波、巡迴演出的道路,每每一家子人四處星散。一八一三年,菲利波在義大利演出,蘇菲帶著瑪麗和瑪麗的弟弟保羅(Paul Taglioni, 1808-1883)待在日耳曼的卡薩爾(Kassel),卻遇到拿破崙遠征俄羅斯落敗,哥薩克人(Cossacks)強攻西進,鐵蹄到了日耳曼。蘇菲向來足智多謀,兵荒馬亂之際假扮成法國將軍的妻子,帶著兩個孩子和撤退的法軍一起「逃回」巴黎。母子三人在巴黎租了小公寓住下,拮据度日,一度還住在雜貨店樓上,不過,終歸算是安穩下來。遇到菲利波沒辦法寄錢養家,蘇菲也教一教豎琴、做一做女紅,貼補家用。瑪麗承襲舞蹈家業,也一樣拜師庫隆學習舞蹈。只是,瑪麗並非天生就是跳舞的料兒。她的身材比例不佳,還彎腰駝背,兩腿骨瘦如柴,算是以「醜」知名,備受同學揶揄,笨拙、難看的外形始終是別人取笑的目標。即使日後出師,登台獻藝,遇上的苛評也沒好到哪裡去,有人就說她「怎麼長得那麼難看……說是畸形也差不多,看不出來哪裡漂亮,要在舞台揚名立萬,一般外形多少要有亮眼的優點──在她身上,卻遍尋不著」。
一八二一年,菲利波受命出任維也納宮廷歌劇院的芭蕾編導,興奮之餘,馬上安排女兒瑪麗到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作生平第一次登台演出。只是,一待女兒從巴黎抵達維也納,作父親的卻嚇得不知如何是好:瑪麗雖然師事庫隆,技巧卻火候不足,絕對逃不過維也納觀眾的法眼,維也納的芭蕾觀眾可是看慣了絢麗奪目的舞蹈技巧。不止,那時的維也納也今非昔比,早已不復當年瑪麗亞.德瑞莎坐鎮宮中的繁華。以前舊制度時代的親法宮廷,可是自負又自滿,稱賞的也是諾維爾一輩的芭蕾大師。到了十九世紀初年,維也納卻已經兩度被拿破崙的大軍拿下,民眾過的是淪陷區仰人鼻息的屈辱歲月,通貨膨脹嚴重,民生困苦,帝國幾近土崩瓦解。哈布斯堡王權旁落梅特涅親王(Klemens Wenzel Lothar Metternich, 1773-1859)之手,王朝因而改頭換面,化身為歐洲保守勢力的典範和堡壘。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風潮搞得歐洲翻天覆地之前,哈布斯堡王朝倒還始終有辦法節制(兼鎮壓)社會、政治日漸高升的緊張對立,暫時帶領帝國避開傾頹的危機。
不過,穩健持重、備受節制的光鮮表相,其實暗藏凶險,正蠢蠢欲動;文化活動因之也如暗潮洶湧,蓄積了萬般的緊張和焦慮,無路可去,結果一股腦兒宣洩在舞蹈當中。在這樣的年代,維也納居民迷上了社交舞,蜂擁擠進豪華舞廳和娛樂場所跳舞。例如著名的「阿波羅宮」(Apollo-Palast),一口氣可以擠進四千名舞客。當時廣建這類舞廳和娛樂廳,原因之一,便是要對民眾焦躁不安的活力施行「教化」和管制。維也納居民和巴黎人一樣,迷的是華爾滋。這一類型的流行舞蹈,起源自奧地利和日耳曼的民間舞,發展到這時候已經登上亢奮、騷動的浪漫思潮浪頭,宛如浪漫思潮的圖徽。日耳曼大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寫的的小說,《少年維特的煩惱》(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主角少年維特就曾和心上人在舞會共舞一曲華爾滋,後來卻因得不到佳人傾心而自殺身亡。日耳曼音樂家韋伯(Carl Maria von Weber, 1786-1826),一八一九年寫下如夢似幻的《邀舞》(Aufforderung zum Tanz),也將華爾滋拱成音樂殿堂的藝術精品。十九世紀初年,維也納流行的華爾滋還未褪去粗糙的重踏步,雖然漸漸修得圓滑柔順一點了(像以滑步取代跳躍),但是,肢體的律動和情欲的挑逗卻始終飽漲能量──滑步雖然優雅,但是,速度一樣會愈來愈快,跳得人頭暈。
維也納宮中的情況大同小異,舞蹈傳統的重擔早已從巴黎朝米蘭外移。怪誕派的義大利藝人以無畏奔放的特技和煽情的舞蹈主宰芭蕾舞台。而且,不限男性;女性炫技之大膽豪放一樣教人看得兩眼發直。當時的舞者已經發展出一門精采絕活,一般歸之於當時的著名舞者阿瑪莉亞.布魯諾麗(Amalia Brugnoli, 1802-1892)名下。也就是腳尖輕盈一踮,讓大家看看一整個人踮在腳尖上面跳舞,當時叫作「足尖舞」(toe dancing)。這一門新的絕活,在周遊日耳曼暨奧地利–義大利巡迴演出的義大利舞者當中就成了必備的工夫。所以,我們現在說的「踮立」(pointe work),並不像一般所想的發源於輕盈縹緲的詩情想像,而是原本相當粗糙的特技,幾經瑪麗.塔格里雍尼等多位舞蹈家精心琢磨,才變得優美、高雅的。而這樣的「足尖舞」當然不是義大利通俗舞蹈的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助芭蕾一臂之力或是扯芭蕾後腿,將芭蕾朝意想不到的新方向推了過去。
無論如何,瑪麗.塔格里雍尼的命運就此倏地一變。眼看有布魯諾麗這一幫炫技舞者擋在跟前,再加上自己先天的外形不足、後天的技巧不良,激得塔格里雍尼發憤圖強,決心從頭打造全新的自己。一連六個月的密集訓練,便是她舞藝的轉捩點,日後,她在未發表的回憶錄筆記也寫過這一段苦練的時光。菲利波在維也納繁華的高級地段葛拉本(Graben)有一戶公寓,父女倆兒便在那裡閉門苦練。菲利波找人搭起斜面的練舞教室,監督女兒日日苦練。早上兩小時,專門練習一連串艱難的動作,兩條腿各練多次。下午則是(依她自述)「古式的」慢板組合,以希臘雕像的線條和比例為準,細細雕琢芭蕾的姿勢和神態。為了脫穎而出,瑪麗對於當時芭蕾伶娜流行的勾魂淺笑、挑逗風騷棄如敝屣,只肯穿素雅的戲服,只願意泛起平靜、知足、嫻雅的表情。她苦練的方向,似乎分朝兩條方向幾近乎相反的道路同時並進:一是簡潔俐落,一是技驚四座。百年歷史的貴族虛矯習氣被她剝除盡淨;而她和父親一起從義大利舞者那裡摭拾來的超凡絕技,也由她精雕細琢。
不過──很重要的「不過」──瑪麗.塔格里雍尼還是有先天體格的弱點需要克服。微駝的背,害她的姿勢顯得略往前傾(她父親一度甚至苦苦求她站姿要挺拔一點),由傳世的石版畫可見她把自己這樣的姿勢融入舞蹈技巧,巧妙轉移身體的重心,調整四肢的排列,以之掩飾先天笨拙不雅的比例和不算挺拔的體態。只是,她的姿勢雖然始終沒辦法真的挺直,卻反而為她添加了莫大的魅力:先天不太協調的比例,加上後天為了掩飾而作的調整,兩相結合,反而為她的舞蹈注入壓縮凝聚的能量,和法國畫家安格爾(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 1780-1867)筆下的女性幾無二致。不止,瑪麗.塔格里雍尼為了把缺點再遮掩得多一點,還鍛鍊出特別強的肌力,好把動作的幅度再放大許多。她練舞時,每一姿勢沒數到一百下不會結束;這在當今,可是連肌力最強的舞者也嫌痛苦的呢。一待固定向前的舞姿做得很嫻熟了,她便把同樣的舞姿改為一邊轉體一邊做(通常還用半踮立的),就像自轉的希臘雕像。
最後,她上床前還要多練兩小時(也就是一天練功總計六小時),這時練的全是跳躍。她以「大蹲」(grand plié)開始:背脊要挺直,屈膝到毋須前傾雙手也可以觸地,然後,一口氣伸直兩腿,將自己推升到全踮立(full pointe)的姿勢站定──這動作需要背部和腿部都有極強的力量。之後,重覆此一動作,但是繼續推升成跳躍。不過,她做的是屈膝跳躍(有別於當今舞者),用腳尖、小腿、大腿、臀部的力量往上推舉,把全身推上空中。舞者往上跳躍,膝蓋若是打得太直,在她那時代可是期期以為不可,痛斥為跳得「像癩蝦蟆」。她認為跳躍的重點,在於做得輕鬆、輕盈、圓滑、柔美──絕對不可以看起來僵硬又費力。這樣的動作,她當然一做就要重覆許多次,此後多年,也一直是她練舞的基本功。
苦練若此,自然練出了奇效。從早至一八二○、三○年代所留下來的繪畫、版畫,看得出來瑪麗.塔格里雍尼的體型絕對稱不上輕盈或是纖細,反而肌肉相當發達、精壯,可見她的肌力和耐力特別強大。塔格里雍尼日後也自述,別的舞者覺得很吃力的姿勢在她根本就像休息。體力強大到這樣的地步,並非前無古人。如前所述,奧古斯特.維斯特里和十九世紀初年活躍巴黎的男性舞者,練功的課程一樣十分辛苦,練出來的體型一樣精壯、結實。不過,兩邊的相似處也到此為止。奧古斯特.維斯特里的新派舞蹈,堂而皇之以譁眾取寵的炫技花招為重,尤其是單足旋轉。不止,這一輩男性舞者的動作一般視為陽剛、雄健的技巧。瑪麗.塔格里雍尼卻不是,她反而努力要把精壯的體能罩在陰柔、優雅的光暈之下。她專心琢磨肢體的線條和型態,對於單足旋轉的技巧沒有興趣:於她,不論是練舞還是演出,多圈旋轉都難登大雅之堂。她要的,是在奧古斯特.維斯特里、安東.保羅的矯捷強健,注入淑女的素雅嫻靜。
而她精雕細琢的秀雅推到極致,就在她腳上的踮立工夫了。瑪麗.塔格里雍尼認為布魯諾麗挺起身軀頂在腳尖上的作法,其實動作粗魯,還是以避之為宜。但是,這一新創的動作也有其魅力,所以,瑪麗.塔格里雍尼捨其粗魯而就其魅力,苦練多時,練就了輕盈優雅即能踮立腳尖舞蹈的工夫,不必舉手,不必撐得臉部表情扭曲。總之,她把這樣的工夫練到輕輕一踮,看似不費吹灰之力便能起舞。不過,我們知道,瑪麗.塔格里雍尼的踮立,不像現在的舞者做的「全踮立」。現在還看得到她傳世的舞鞋,和她那時代女性一般愛穿的時髦出門鞋其實沒多大差別。由輕軟的綢緞做成,加上皮製的鞋跟,圓形或是方形的鞋頭,腳弓處有秀氣的緞帶綁在腳踝。鞋尖不像現在的芭蕾硬鞋(pointe shoe)做成硬硬的、方方的,而是輕軟的圓形,只在蹠骨和腳趾下方多縫幾道線加強支撐力。
瑪麗.塔格里雍尼留下來的古老舞鞋,鞋底在蹠骨一帶磨損得特別明顯,可見,塔格里雍尼的踮立其實只是踮得較高的「半踮」,依現在舞者的標準,應該算是踮在半踮到全踮之間:也就是比「半踮」要高,但不到完全「踮立」的程度。這樣的站姿其實是很吃力的,所以,十九世紀的舞者常將腳趾綁緊,硬擠進太小的舞鞋(當時以小腳為美,瑪麗.塔格里雍尼的舞鞋就比現今舞者平均的鞋碼少了至少兩號),蹠骨的部位隨之束緊、繃住,這樣的站姿也才不會太吃力──但也容易害骨頭移位、脫臼。當時的舞鞋質地輕軟、織線綿密,穿在腳上還要支撐不小的重量,惡果之一,就是縫線常會繃裂。所以,塔格里雍尼一場演出,通常要換兩到三雙舞鞋。
由此可見,瑪麗.塔格里雍尼的舞蹈是前所未見的新合成體:雖有濃烈的法國貴族氣質,但又融入了奔放的義大利炫技風格,外加她為了克服先天不足而發展出來的特色作為調劑。前者和後者的路線,本來就扞格矛盾。塔格里雍尼卻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找到了銜接兩邊的疆界。而她是在維也納而不是別的地方找到會通的契機,衡諸當時的大環境也實非意外。諾維爾之後的年代,歐洲的情勢雖然大變,但是,維也納還是歐洲地理、歷史的重要文化輻湊點。新與舊的傳統在此交會頡頏,出身義大利、日耳曼、法蘭西的人等也在此交會頡頏──有的時候,當然也會打散、重組。話說回來,既然是輻湊點,塔格里雍尼在維也納落腳的時間也就不長,而和當時諸多四處巡迴演出的藝人一樣,沒多久就離開維也納另覓舞台。塔格里雍尼離開維也納時,既然已經打響名號,她的童年世界,也就是芭蕾之都巴黎,自然對她發出了召喚。
瑪麗.塔格里雍尼的舞蹈風格,若說是在維也納塑造成的,那麼,她這樣的風格有何內蘊,就有賴法國人細數道來。一八二七年,塔格里雍尼首度於巴黎歌劇院登台獻藝,觀眾為之轟動瘋狂。往後三年,瑪麗.塔格里雍尼一有演出,各方佳評便如潮水一波接著一波不斷迴盪,每每興奮得連珠炮一般吐出連番讚美的頌辭,恍若搜索枯腸也找不到貼切的評語,配得上她出神入化的舞蹈:「劃時代」,「古典芭蕾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四朝舞蹈元老,從卡瑪歌小姐到葛代爾夫人全被一筆塗銷」。一篇又一篇時論,無不像是苦旱喜逢甘霖,盛讚沒有品味只有「蠻力」的舞蹈終於壽終正寢。他們認為這一類沒有格調只有蠻力的舞蹈,只見大汗淋漓、氣喘噓噓的舞者(也就是奧古斯特.維斯特里帶起來的那一批男性舞者),不是瘋也似的大作單足旋轉,就是撲身飛躍舞台,再要不然單腳孤伶伶的站定在台上,空出另一隻腳「劃來劃去」,把複雜的舞步「做」給你看。當時的論者眼見有瑪麗.塔格里雍尼如此新秀出現,一致認為維斯特里他們那一派的恐怖舞蹈終於走到了盡頭!總算有不凡如瑪麗.塔格里雍尼者,重拾以往貴族遺留的優雅和細膩,注入嶄新、空靈的氣韻──她啊,有論者盛讚這一位舞者,誠乃法國「復辟」(Restoration)年代完美的芭蕾伶娜。
如此的美譽可不是等閒之輩扛得起來的。法國「波旁王朝」(Bourbons)復辟(一八一五至三○年),是法國「正統派」(legitimist)的釜底抽薪之策,希望以之澈底了結法國大革命,而能改以中古哥德的基督教為基礎,將法國重新打造為保守勢力的重鎮。瑪麗.塔格里雍尼的舞蹈,看似正好呼應了當時法國民心普遍的渴望──渴望和解,渴望法國社會、政治的激烈對立和分裂終於可以彌合。這樣子來看,瑪麗.塔格里雍尼苦心琢磨出來的法國丰華,確實有助於她站上不敗之地。她的氣質,儀態,在在呼應舊世界講究的含蓄內歛。不過,瑪麗.塔格里雍尼當時席捲歐洲的魅力可不僅止於此。當時的文學、藝術已遭錯綜矛盾的浪漫思潮攻陷。那時的浪漫思潮,大膽前衛卻深藏思古幽情。芭蕾追趕這一潮流的腳步算是落後不少,於當時還在和自家的貴族遺緒纏鬥,身陷泥淖無法自拔,以至在大文化的環境益愈退處邊緣。瑪麗.塔格里雍尼這時躍上芭蕾的舞台中心,簡直像是天降的神啟,超越了炫技,為芭蕾打開另一條康莊大道,直通肢體動作、理念思想的嶄新天地。所以,當時才有論者熱切歎道,好不容易啊,終於有一名舞者,「將浪漫思想用於舞蹈」。他說的沒錯,只是,這樣一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還有待往後數年政治又陷入動盪,才會清楚透析出來。
【摘文4】
一九一二年,尼金斯基以法國作曲家克勞德.德布西(Claude Debussy, 1862-1918)的音樂編出《牧神的午后》(L’apres-midi d’un faune)。德布西的樂曲靈感來自法國詩人史蒂芬.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 1842-1898)的同名詩作。馬拉美此詩的繫年是一八六五,德布西的樂曲則是寫於一八九四年。不論詩作或是樂曲,同都瀰漫印象派的深思冥想,如夢似幻。尼金斯基編的芭蕾,刻畫牧神巧遇溪畔有寧芙正在寬衣,被眼前所見撩起了情欲,寧芙受驚逃走,但是留下了紗巾。牧神撿起紗巾攤在石塊上面,自己再躺在紗巾上面,頂起臀部於幻想中達到性高潮。芭蕾的長度很短,約十一分鐘就告結束。雖然世人對《牧神的午后》的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大舞蹈家尼金斯基在台上公然自慰。但這一齣芭蕾卻也是嚴肅的創作,尼金斯基要以此創作為舞蹈的動作開創新的語言。尼金斯基從一九一○年便開始和妹妹布蘿妮思拉娃一起創作這一支舞碼。兩人一起排練舞步、不停實驗,往往一連數小時不停。尼金斯基那時迷上了古希臘的美術,不過,不是佩里克里斯(Pericles, c.495-429 B.C.)時代雅典講求的阿波羅式完美,而是還要在那之前的「遠古」(Archaic, 800 B.C.-480 B.C.)時期樸素又原始的希臘美術。他對法國當世畫家高更筆下平板、散發原始氣味的畫作也很著迷,曾經讚歎,「看那力量啊!」
等到《牧神的午后》編好,進入排練,就變得很磨人了:舞者全都討厭尼金斯基編的動作,線條凹凹凸凸都是稜角,只有二度空間,像建築物中楣的雕刻裝飾,突兀、緊繃的動作還要練出極強的肌力才做得到。舞者也不喜歡尼金斯基不容絲毫炫技污染的風格,因為,這樣的風格逼得他們必須放下譁眾取寵的花招和姿勢,改作尼金斯基自己說是「山羊」的跳躍、蹲伏,還有短促、急停的舞步和軸轉(pivot)。尤有甚者,為了強調舞步簡潔俐落的強度,舞者還要改穿硬梆梆的繫帶涼鞋上場,而不穿芭蕾舞鞋。尼金斯基還嚴格禁止舞者出現絲毫演戲或是臉部表情──這就更氣人了。例如當時有女舞者想將她的角色刻畫得再鮮明一點,便遭尼金斯基斥責,「已經全都編在舞蹈裡了」。連狄亞吉列夫本人也惴惴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擔心尼金斯基簡約素淨宛如苦行的舞蹈,會嚇得巴黎的觀眾退避三舍,畢竟巴黎人已經習慣繽紛華麗的俄羅斯舞碼。
《牧神的午后》刻畫的是內向、凝神、冷冰冰的生理本能。不以性感撩撥情欲,而是拿性欲來作白描──也就是冷眼旁觀直接描繪人性的本能欲望。尼金斯基原先在芭蕾舞台據以成名的性感、異國丰采,在《牧神的午后》像是遇到了犀利的反駁。《天方夜譚》一類淫欲飽滿的芭蕾,《玫瑰花魂》裡的美麗挑逗,在《牧神的午后》也都橫遭叛變。尼金斯基把這些一股腦兒全丟到身後,另闢蹊徑,創作出縮小版的「反芭蕾」──精密,嚴格,把尼金斯基鄙棄之至的「甜膩」(excessive sweetness)全數剔除。
接下來便是《春之祭》(Le Sacre du Printemps, 1913)。這一支芭蕾最早的構想出自狄亞吉列夫、史特拉汶斯基,還有俄羅斯藝術家尼可萊.羅埃列赫(Nikolai Roerich, 1874-1947)。羅埃列赫是畫家、建築師,終身的興趣都在基督教外的異教信仰、在俄羅斯農民的性靈傳統、在俄羅斯文化深植於古賽昔亞(Scythia)文化──野蠻原始、桀驁難馴、位處亞洲──的根。他和「塔拉希園」藝術村有深厚的淵源。其實,《春之祭》的劇本就是他和史特拉汶斯基埋首在瑪麗亞.泰尼謝娃公主收藏的大批農民美術、工藝作品之餘,創作出來的。他們以民俗學者和音樂學者的研究為基礎,將這一齣新芭蕾想像成一幕儀式,搬演虛構的異教祭典,以少女為犧牲,獻祭與豐收和太陽之神,而於春臨大地之時舉行祭典。羅埃列赫以俄羅斯農民的工藝、服飾為藍本,勾畫舞台布景。史特拉汶斯基研究民俗主題(他在一段樂譜上面寫過,「一名老婦身披松鼠毛皮的樣子,始終牢牢嵌在我的腦中。我作曲時,她始終就在我目前」)。不過,《春之祭》沒有《火鳥》富麗的的東方情調。羅埃列赫的舞台設計,是荒涼、崎嶇的詭異風景,有好幾個鹿頭插在長竿頂端,矗立在外圍。史特拉汶斯基譜寫的樂曲,粗獷嘈雜,滯澀,不和諧的和弦加上強勁、急促的切分音(管弦樂部的編制要擴大,打擊樂部也要加多),縈繞不去的旋律衝到極度的音域,倒還是和《火鳥》一樣粗暴慘烈,聽得人暈頭轉向。
尼金斯基極為欽慕史特拉汶斯基和羅埃列赫。《春之祭》的犧牲少女一角,一開始是尼金斯基和妹妹布蘿妮思拉娃聯手創作的。創作期間,尼金斯基曾經寫信給布蘿妮思拉娃,談及羅埃列赫的畫作《太陽的召喚》(The Call of the Sun, 1919):「妳記得嗎?布蘿妮亞?……黎明前的黑暗,廣袤的荒涼大地,映現強烈的藍紫、紅紫,一道旭日的金光打在一批人群身上,人群僻處山丘頂端,迎接春臨大地。羅埃列赫跟我詳細解說過他這一系列的畫作,說他這一系列的畫作,表達的是原始人類精神之甦醒。我在《春之祭》,就是要趕上史前斯拉夫民族這般的精神。」史特拉汶斯基一樣曾和年輕編舞家詳細討論過他寫的音樂,尼金斯基也說他希望《春之祭》可以「拓展新的境界」,「前所未見,意想不到,美麗萬千」。
沒想到一語成讖。尼金斯基的《春之祭》只演出了八場──前後加起來只有八場──所編的舞蹈便告湮滅於歷史。不過,由流傳下來的相片和筆記,還是看得出來,尼金斯基的《春之祭》芭蕾之「不像芭蕾」,確實教人啞然失笑。彎腰駝背的人影在台上拖著腳划來划去、重踏步,腳尖朝內擺出難看的內八字腳,手臂蜷曲,頭還歪一邊。動作急促突兀,曲折凹凸,舞者聚攏,擠成一團、彎腰、顫抖、相互偎依,或者像在跳俄羅斯傳統的圓環舞,卻在台上狂亂繞行,然後又像是不由自主一般,猛然從圓環飛出去或縱身做出狂野的騰躍。尼金斯基設計了不少很礙眼的不協調動作;手臂是一種節奏,腿部是另一種節奏。還有一名舞者回想起《春之祭》,說劇中有跳躍動作要他們故意把雙腳打平了落地,害得「我們身上的每一個器官」都震個不停。
史特拉汶斯基譜出來的曲子也一樣是教人膽寒的艱鉅挑戰。尼金斯基其他幾件寥寥可數的芭蕾舞作,《牧神的午后》和較不出色的《遊戲》(Juex,描繪運動和休閒活動,在《春之祭》推出之前兩星期於巴黎首演),都是以德布西的音樂為本而創作出來的。只是,《春之祭》的音樂沒有《牧神的午后》流瀉如浩瀚汪洋的安詳、平靜。史特拉汶斯基怪異的新樂音,複雜的節奏和調性結構,都有賴尼金斯基費心琢磨,才有辦法烘托出其中的奧妙。只是,都已經到了排練的時候,鋼琴家竟然還抓不準曲子的精髓。所以,有一次,史特拉汶斯基就氣得把鋼琴家一把推開,自己上陣彈將起來,還把速度加快一倍,嘴裡又喊、又唱,雙腳用力踩踏地板,甚至揮拳帶動節奏,傳達打擊樂激昂高亢、盡情爆發的活力和樂音震撼的聲量(舞者要等到最後彩排的時候,才聽得到完整的管弦樂曲)。狄亞吉列夫想幫忙,便雇了一名年輕的波蘭舞者瑪麗.阮伯特(Marie Rambert, 1888-1982)來協助尼金斯基,負責帶領團員排練。瑪麗.阮伯特原名席薇亞.阮龐(Cyvia Rambam),專精「優律詩美」舞蹈的達克羅士教學法。尼金斯基有她在身邊,就可以用波蘭語暢所欲言。她對尼金斯基的舞蹈出現極端創新的動作,也大有共鳴。只是,事與願違:舞者都覺得樂曲含糊不清、幾乎抓不到拍子,教他們不知如何是好。他們也很討厭尼金斯基編的舞步精密又複雜,動作也像圖樣。只是,舞者的抗拒心理說不定正好切中《春之祭》之所需:不得不屈從於《春之祭》的音樂、動作邏輯,便是《春之祭》舞蹈奧妙之所在。
《春之祭》不是傳統所說的芭蕾。既沒有簡單明瞭的敘事推演,也沒有空間供個人多作自由發揮,更沒有慣見的舞台標記可供拿捏情節。《春之祭》反而是以反覆、累積、幾近電影蒙太奇的手法,醞釀效果:一幕幕停滯的場景和畫面並置,由儀式和音樂往前推動,而非單純敘事的邏輯。舞台上有用力踏步的部落舞蹈,有程式化的強暴場面,有儀式一般將雀屏中選的犧牲少女強行擄走的場面,有白鬍鬚的大祭司領隊遊行,以少女痛苦狂舞至死推到高潮。少女倒地身亡之後,有六名男子抬起她癱軟無力的身軀,高舉過頭,沒有洶湧澎湃的絕望、悲傷,或是情感作憤怒的渲洩,僅有聽天由命的順從,教人不寒而慄。
時至今日,已經難以描述《春之祭》問世之初,激進、震撼的程度。尼金斯基和佩提帕、福金之間拉開的距離,難以度量;連《牧神的午后》與之相較,也顯得沉悶。若說《牧神的午后》是以博學深思營造自戀孤僻的情境,《春之祭》便是堂而皇之宣告個體已死的先聲,是淒厲、激昂的頌辭,禮讚集體意志。從頭到尾只作赤裸裸的呈現:舞蹈律動的美感,精雕細琢的技巧,在台上一概遍尋不著。只見尼金斯基所編的舞蹈,一下要舞動的舞者忽然頓住、拉回、改路線或是換方向,打斷動作或是衝力,恍若要釋放體內蓄積久矣的能量。不過,控制、技巧、秩序、理性、禮儀,也未必全遭《春之祭》揚棄。尼金斯基的芭蕾,從來就不狂放也不雜亂,他的創作,是在對非理性力量鼓脹翻騰的原始世界,作冷冰冰的理性描繪。
《春之祭》推上舞台,也是芭蕾歷史轉捩的一刻。此前的芭蕾創作再怎樣離經叛道,始終以高貴作為基底,緊守結構明晰和崇高理想的原則。《春之祭》於此,不復如是:芭蕾於尼金斯基手中脫胎換骨,變得醜陋又晦澀,展現了現代化的新貌。尼金斯基自己便曾自豪說過:「大家可是指責我犯下破壞優雅的重罪呢。」史特拉汶斯基反而因此特別欣賞尼金斯基。大作曲家寫信給朋友說,《春之祭》的舞蹈「正合我意」,但又追加一句,「只是,若要社會大眾習慣我們創造出來的新語言,絕對還要等上好長一段時間才辦得到」。史特拉汶斯基說中了《春之祭》的處境:《春之祭》既隱晦難懂,又太過新異。尼金斯基使盡全力,以滿腹的才華打破過往的桎梏。尼金斯基燃燒的創作激情,證明他(和史特拉汶斯基一樣)是以狂熱的意志在創發嶄新的舞蹈語言。這是他創作動力的根源,也是《春之祭》之所以是史上首見真正堪稱「現代」的芭蕾,癥結之所在。
【摘文1】
導言 名家和傳統
我的父母都在芝加哥大學任教,所以,我是在學術氣味濃厚的環境長大的。我不曉得當初我母親送我去學跳舞究竟是為了什麼,只知我母親愛看表演。說不定依她出身美國南方、注重禮節儀態的性子,芭蕾正合她的脾胃;而我家那一帶,也正好開了一所舞蹈學校,我母親自然送我過去學舞。那所舞蹈學校是一對老夫婦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有好幾支俄羅斯人的芭蕾舞團來到美國各地巡迴演出,他們便在其中一支舞團跳舞,順勢就留在美國。不過,老夫婦開的舞蹈學校跟一般常見的不同;沒有一年一度的《胡桃鉗》成果發...
目錄
致謝
導言 名家和傳統
PART ONE 法蘭西和芭蕾於古典的源起
CHAPTER 1 君王的舞蹈
CHAPTER 2 啟蒙運動和故事芭蕾
CHAPTER 3 芭蕾的法國大革命
CHAPTER 4 浪漫派的幻想世界:芭蕾伶娜崛起
CHAPTER 5 斯堪地那維亞的正統派:丹麥風格
CHAPTER 6 義大利的異端:默劇、炫技、義大利芭蕾
PART TWO 東方的光輝:俄羅斯的藝術世界
CHAPTER 7 沙皇旗下的舞蹈:帝俄的古典派芭蕾
CHAPTER 8 東風西漸:俄羅斯的現代風格和狄亞吉列夫的「俄羅斯芭蕾舞團」
CHAPTER 9 獨留斯地憔悴?史達林到布里茲涅夫的共產黨芭蕾
CHAPTER 10 傲視歐洲群倫:英國芭蕾的榮光
CHAPTER 11 美利堅世紀(一):由俄國人啟動
CHAPTER 12 美利堅世紀(二):紐約的繁榮風華
跋 前賢已逝、大師漸渺
註釋
參考書目
索引
圖版出處
致謝
導言 名家和傳統
PART ONE 法蘭西和芭蕾於古典的源起
CHAPTER 1 君王的舞蹈
CHAPTER 2 啟蒙運動和故事芭蕾
CHAPTER 3 芭蕾的法國大革命
CHAPTER 4 浪漫派的幻想世界:芭蕾伶娜崛起
CHAPTER 5 斯堪地那維亞的正統派:丹麥風格
CHAPTER 6 義大利的異端:默劇、炫技、義大利芭蕾
PART TWO 東方的光輝:俄羅斯的藝術世界
CHAPTER 7 沙皇旗下的舞蹈:帝俄的古典派芭蕾
CHAPTER 8 東風西漸:俄羅斯的現代風格和狄亞吉列夫的「俄羅斯芭蕾舞團」
CHAPTER 9 獨留斯地憔悴?史達林到布里茲涅夫的共產黨芭蕾
CHAPTER 10 傲視歐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