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封印的開啟
◎1
腳步聲近了,就在門前
那蒼白似骨的手已扣在門環之上
不再耽延,祂用著愁苦憂煩的聲音說,就是這一天了……
祂披著件黑色斗蓬,袖中藏著冊子
就是那本記載那過去、未來一切的冊子——
喪鐘已經響起,冊子即將掀開
不再耽延,祂在我耳邊輕聲問說,你可準備好了?
喪鐘已經響起,就在門前
那就開始吧!願仁慈的上帝保佑我們……
這已經是四天前的事了。
我是個簡單的網頁設計師,每天龜縮在十五吋的小小電腦螢幕空間裡玩著DreamWeaver、PhotoShop等等玩意。未婚,二十八歲,沒有女友,獨居在台北圓環附近一間出租小套房裡。我不是個愛說話的人,平日很少與人往來,也就是說——我幾乎是沒有任何朋友……或是敵人。
除了看電視外,我幾乎沒有什麼特別良或不良的嗜好,只是這樣渾渾噩噩的過著日子……就算看電視我也是迷迷糊糊的看,沒特別喜歡的節目,也沒特別不喜歡的節目,無論是連續劇、綜藝、新聞、甚至於廣告都照單全收。之所以會遠離屏東鄉下老家來到台北,完全與叛逆或什麼想出人頭地的偉大志向無關,單純就只因為台北工作機會較多,如此而已。
從小我的健康情況就差,常犯胸悶、偏頭痛、暈眩、腹瀉等等,我猜這是種先天性的疾病,在出生那瞬間,我的胃、心臟、肝或其他我所不知道的器官就出了某種嚴重病變。我深信自己遲早有天會突然地死掉,可能是在上班上到一半,或街上行走途中,甚至可能在睡眠中突然停止呼吸。在做過幾次全身健康檢查後……他們把我送到精神科,一個戴著眼鏡面無表情的中年醫生說我得的是恐懼症,一種對自身健康沒來由恐懼的精神官能症。
直接說吧!就是怕死,我對死亡有著種病態的恐懼。
因此,隔週我會到林口長庚醫院精神科去拿一次藥,若時間允許就順便跟那些無聊的心理分析師們玩玩愚蠢的問答遊戲,然後一天三次按指示服用那看來挺可愛的粉紅色小藥丸。我並不覺得精神分析師或粉紅色小藥丸對我有什麼幫助,不過我喜歡去醫院,喜歡看到一堆醫生護士圍繞在我身邊。
我認為自己算是個正常到不能再正常的普通人,比如偶爾會做些不切實際的夢,像是當個拯救世界的偉人之類的,等死後被人塑成銅像放在公園裡當成約會地標。我猜每個人多少都會有這種想做點什麼大事的願望,然後將這願望留在小學校時的作文簿裡……只有白痴才會相信這世上真有『努力就會成功』這回事情——我雖不算聰明,但也絕不是個連這樣簡單道理都不懂的白痴。
總而言之,我就是滿街都是的那種簡單、枯燥、無聊但又無害的傢伙。凡是流行的事情我都要插上一手,像是精神官能症、流行性感冒、網路……
事情是發生在那天晚上八點多。平日我大多得忙到晚上八點左右才能下班,反正幹我這行的人也多半是這樣沒日沒夜的,況且就算提早回家我也是看電視而已。那晚,在吃完晚飯時我無意識地瞄了眼手錶,應該是七點五十多分將近八點……老實說,這時間只是依著某種模糊印象推論而出,你知道,有時看錶就只是看錶,一種沒什麼道理的奇怪習慣。
我另外還記得的是,當我走進大門時,大樓管理員阿吉仔不在位置上。這沒什麼好奇怪的,要是阿吉仔會乖乖坐在他管理員寶座上那才叫怪——我們這棟大樓就只有他一個管理員,基於人道的考量,你無法要求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分每秒都坐在那兒。這大樓聽說也曾有過三個管理員輪班值勤,隨著時光流逝,隨著大樓日漸破舊,現在就只剩下他一個人在這苦撐了……但不管怎說,我們畢竟是棟擁有管理員的大樓,我個人是滿喜歡這感覺的。
當我在電梯前呆呆瞪著樓層燈號變換時……我想我被攻擊了。那個人身材必然高我許多,他用一條帶著無法描述刺鼻味道的手帕自背後矇住我的嘴鼻。我試圖想要呼救,但卻是喊不出半點聲音,隨即感覺自己如坐雲霄飛車般騰空被人扛了起來。
接著所有一切都模糊了……也不知道昏迷了多久,等恢復知覺時發現有道強光直直地打在我的臉上,刺得我張不開雙眼。那是種相當模糊的感覺,身邊有許多白色影子靜悄悄地來往忙碌著,卻不知道他們在忙些什麼。
或許這只是夢,我想應該是夢,清晰與模糊同時存在於我腦海之中,我似乎清楚知道身邊的每一件事,但又無法確定真的知道。
有個聲音用命令口吻對著我說……我猜是對我說的,因為那聲音是這樣的近,近到這聲音好似發自於我腦子內部。
『放輕鬆、放輕鬆些……嗯——慢慢吞下去,像嚥口水那樣……』
這時我才發現自己口中正咬著一個不知是什麼玩意的鬼東西,一根管狀的東西在我喉嚨裡探觸著。我突然想到胃鏡!應該是胃鏡沒錯,上回在做健康檢查時就曾受過這種慘無人道的酷刑,後來害得我好些天吃什麼都怪怪的。
出於本能的我想要掙扎,想逃脫那正伸向喉嚨的異物,卻發現全身都被某種不知名的東西給牢牢綑住絲毫無法動彈,甚至連轉個頭都沒有辦法。管子一吋吋進到我身體裡,我可以清楚感覺出那玩意緩緩通過喉嚨、食道然後進到胃、十二指腸,接著我聽到一些金屬器具碰撞的聲音,非常輕微,輕微的鏗鏗聲在我空蕩知覺裡迴響著……
危機感浮了上來,無論是聲音還是影像都越來越清楚,我所有感官都慢慢在恢復當中……然後我想起稍早時在電梯前遭遇的攻擊事件。沒意外的話,此時我正在醫院裡,那毫無道理的暴力行為可能讓我受了重傷,而這些白色影子們正幫我動著某種緊急外科手術,試圖想要搶救我即將消失的生命。
我就快死了嗎?或許我現在所感覺到的一切,是人家所說的靈魂出竅?
『血壓,給我血壓!』一個蒼老沙啞的聲音說。
某個女人一旁應道:『九十七、五十二,還算不錯……』
我感覺那根管子正從我胃中被抽出來,緩緩的……
『脈搏?』
『八十五……』
『心電圖?』
『正常,沒問題。』
『請最後一次確認樣品身分!』
『實驗代號XM56,樣品身分確認無誤……』
『好了,讓我們再確定一次,還有哪個部門對樣品有疑問?這是我最後一次詢問了……』還是剛剛那蒼老聲音。在一陣短暫的寂靜後,那聲音再次響起,『OK!如果大家都沒問題——那就開始吧!願仁慈的上帝保佑我們。』
樣品?他們是在替我開刀,還是正解剖我的屍體?沒等到我弄懂那聲音在說些什麼時,意識又慢慢趨於模糊——原本已經開始清晰的影子逐漸暈染開來,像是置入水中的油彩,所有的顏色、線條、形狀、聲音都慢慢溶化、混合著……
時間是早上七點五十分整,那該死的鬧鐘準時響起,它盡責的響了至少有五百聲以上,一聲比一聲急促。我大字形安穩地躺在床上,全身酸痛得像是剛經歷過一場世紀摔角大賽……我試著想要伸手關掉那發了瘋似的混蛋機器,但手臂卻惡意的背叛了我。
想起昨晚,一場詭異的惡夢,這夢是如此之清晰就像是真發生過一樣——矇住嘴鼻的刺鼻味道依然存留,然後我如坐雲霄飛車般騰空被人扛了起來,最後則是那個蒼老的聲音不停對著我說:『那就開始吧!願仁慈的上帝保佑我們……』
我向來是記不住夢內容的。在剛醒來、還躺在床上時或許還能憶起夢裡的某些片段,但一離開床就消失了,我的夢就如蒲公英種子般隨風飄散消失的無影無蹤。我一直認為夢跟床鋪間有著某種不可告人的勾結,它們背著我私自簽訂了惡劣的秘密條約,在我起身瞬間床便吃掉了我所有的夢,作為背負我一整夜辛勞的代價。
我就是如此的一個笨蛋,常會有這些不切實際的無聊幻想。
但昨晚那夢與以往都不一樣,它清晰的像是可觸摸到,完全真實,鼻腔裡現在還可感受的到某種藥物的怪異味道……不過現在我還躺著,沒意外的話,等等當我起床雙腳踏地的剎那,這夢就會消失——我腦容量小到甚至裝不下個夢。
聽著鬧鐘鈴聲我突然起了一個疑問:非假日時我約莫會在十一點半整上床,至於從上床到睡著需要多少時間則無法確定。不過我是個相當好睡的人,幾乎是一接觸到床立即就會不省人事。只是此刻我卻是完全無法想起,昨晚八點到十一點半,這中間三個半小時我到底幹了些什麼?這段時間是完全空白的,什麼都想不起來,難道說,昨夜……
我努力想要憶起昨晚睡前到底做了些什麼——好像是看了電視影集《慾望城市》?喔!不,《慾望城市》是週二晚上演的,那已經是前晚的事了……那昨晚我到底看了些什麼節目?
越是想要兜攏起一切,所有事情就越像亂掉的毛線球般糾纏著。
鼓足了力氣我奮然起身,左側太陽穴一陣劇痛襲來……我像個溺水的人掙扎坐了起來,眼前隨即冒出了無數黑蚊,暈眩伴隨著反胃讓我又倒了下去。那無所不在的死亡恐懼籠罩著我,喘著氣,我想我就要死了,馬上就要死了。
我常頭痛,只要是略略睡眠不足、或心煩,便會引發某種不明原因的偏頭痛;只是以往從沒如此嚴重痛過,痛得就像是有人正用電鑽對著我腦袋打洞。
隨著倒下的震動,鬧鐘從床頭滾到我的臉前,時間一分一秒在我眼前不斷消逝著。八點零六分,再不起床上班就要遲到了。我想到了副理那張晚娘面孔……我幾乎是用爬的進到浴室裡面,跪在馬桶前卻什麼也吐不出來,除了一些胃酸。
我半趴在浴室地板上,低著頭想要適應那種天旋地轉,讓這頭痛成為我身體裡的一部份。每個人在面對痛苦時都有他獨特的應付哲學,有的人是越挫越勇,也有人是哭天喊地四處求援,而我在遭遇到痛苦時的哲學則是——既然打不贏,那就無條件投降,加入敵人陣營溶入其中成為一體……
『那就開始吧!願仁慈的上帝保佑我們……』夢裡那蒼老聲音在我腦海中不停迴響著,『那就開始吧!願仁慈的上帝保佑我們……那就開始吧!願仁慈的上帝保佑我們……』
夢並沒因我的起床而被遺忘,反倒益發清晰起來……難道那不是夢?不可能的,我告訴自己,那是夢,百分之百的是夢,一場沒來由的惡夢!
仰過身子,冰涼的馬賽克磁磚讓我冷靜下來。頭還是一樣痛,但反胃則好多了,我再次想起副總罵起人來的刻薄模樣。就在此時,我看到那個青紫色的瘀血小點,就在我左手的手背上面——那是個相當細微的疤痕,細微到一不小心就會忽略……如果我沒猜錯的話,那該是靜脈注射後留下的痕跡。
一陣恐懼自我內心升起,我望著那靜脈注射留下的小小疤痕全身顫抖個不停,是誰在我不知情的狀態下幫我做了靜脈注射,昨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是遇到了鬼嗎?
在熱水下我感覺舒服多了。我的精神科醫生告訴我說:所有生命都源自於水,要是感覺緊張的話,就狠狠地沖個熱水澡!我把自己給丟在蓮蓬頭下,將水量開到最大,想像自己正捲曲在老媽的子宮裡……然後我發現了第二個證據。
當頭淋下的熱水緩解了我快爆裂的頭,只是我感覺到有些不對,說不上來的不對。然後我發現頭皮上缺了一小片頭髮。
從浴室化妝鏡上可看到那道小小傷口,就像是手背上靜脈注射後所留下的瘀傷般,那是個不小心檢查絕對不會被發現的細微傷口,被埋藏在周圍頭髮覆蓋之下。我想要不是因為淋浴的關係,這輩子我都不會發現曾有過這樣一道傷口……這傷口約略只有半公分不到,被剃除的頭髮範圍差不多也是這樣。
這些都已經是四天前的事了。在發現頭上傷痕後我立刻請了兩天的假,加上週末、週日我足足在床上躺了四天。我不知道是因為怕而疲倦,還是真生病了,總之就是感覺到累,非常之累,全身連一點勁都提不起來。
免除恐懼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讓生活回到正常且又一成不變的單調軌道當中,用上班、下班、看電視、吃飯、睡覺來證明自己依舊活著。
在浴室刮鬍子時,我面對鏡子告訴自己:『你該放棄追查這件事了,這事是屬於不可知的靈異事件,是屬於上帝的秘密。你沒病,就像醫生說的一樣,你健康的像條小豬,你什麼問題都沒,所有一切全都是因害怕死亡而生出的潛意識幻覺。』接著我對著鏡子裡的自己擺出了三種不同微笑,這讓我感覺一切都沒有這樣難過了。
然後我步出了浴室,就在這時我看到了貓……
我住在十二樓,套房的窗台是獨立且懸空的,與隔鄰毫無任何連接之處,且從我搬進來後那窗子就緊緊閉著沒打開來過。而現在有一隻貓兒正安安穩穩坐在我窗台外悠閒地舔著腳掌,然後伸了個懶腰瞄了我一眼。這貓是在怎樣情況下才會出現在那?
『一隻會飛的貓?』我告訴自己,『我眼前有隻會飛的暹羅貓。』
◎2
司芬克斯在尼羅河谷無邊風沙中嘶吼著:
是誰,早上用四隻腳走路
中午用兩隻腳走路,晚上用三隻腳走路!
神蹟降臨我身——
我聽是聽見,卻不明白;看是看見,卻不曉得
誰能指引我路,我眼所見是否為真,幻覺又是從何而來?
司芬克斯在尼羅河谷無邊風沙中嘶吼著:
我看到了,這所有一切經過我全都看到了……
我討厭目前的狀況,在第一個謎還沒解開時,又出現第二個謎,再這樣繼續下去,我遲早會被這些毫無根源的莫名其妙狗屁事情給活活逼死。如果需要用什麼來證明我發瘋了,那麼單是出現被人攻擊的偏執幻想就綽綽有餘了。
跟貓這樣對看了約有一分鐘吧!我相信眼前的一切,全出於我躺太久以致於產生的幻覺——我或許是個瘋子,但卻還沒瘋到失去理智,所以這隻貓兒是不應該存在的。於是我閉上了眼睛,用力吸了口氣後從一數到十……我確信當我睜開眼時,這貓兒就會自動乖乖的消失。
這是心理醫生告訴我的法子,閉上眼睛深呼吸從一數到十,然後所有一切問題都會得到解決,包括我幻想出來的糖尿病、心肌梗塞、各種奇奇怪怪的癌症等等。只是,等我睜開眼時,那隻該死的貓兒仍用著那雙炯炯有神的碧綠眼睛緊盯著我……然後牠低下頭開始舔毛,那身深咖啡色光亮的毛。
對動物我一向是沒什麼概念,這世界上或許有黑貓、白貓、大狗、小狗之分,但在我眼裡貓就是貓,狗就是狗,這就像我對車子沒概念是一樣的。從來我就分不出車與車在廠牌、年份、型號甚或是汽缸容量間有什麼差異,對我來說車就是車,最多只是大車與小車間的差別而已。
我猜這世上貓的品種少說有個幾百上千……嗯——或許上萬、上億種?但我唯一能認出來的就只有暹羅貓了——因為很久以前老媽曾養過隻暹羅貓,且愛牠勝過愛我千倍。我百分百的相信,如果發生什麼重大事件必須作一抉擇時,老媽會選擇那隻貓而忍痛放棄掉我……
關於這點我絲毫沒怨恨過老媽,雖說身處於被放棄的一方讓人有點難堪,但這是個相當正確的抉擇;換作是我,我想我也會選擇留下貓而放棄自己。
暹羅貓是種極為特殊的貓,雖說是被人飼養的寵物,卻不同於一般家貓的溫柔馴服,牠們堅持保留著自古遺傳下來如黑豹般的狂野因子,對進化這玩意絲毫不肯退讓。老媽平日都是用一條極細的鍊子像狗一樣把牠栓著,說是一放就會跑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暹羅貓都是如此,但起碼我家那隻就是這樣。
後來老媽那隻該死的暹羅貓還是跑了,害她哭了一整個星期。
現在這隻貓兒正用著一種獨立超然、一種懷疑的哲學眼神打量著我,這讓我感到全身赤裸裸的,一種不舒服的感覺冒了上來……
不!我突然發現自己能完全體會出這傢伙想表達的,就像心電感應一樣——那貓兒此刻正跟我一樣在納悶著:『這個只有兩隻腳的傢伙是從哪冒出來的?』或許我的出現才是種不正常狀態,就像牠的出現對我來說是如此之不合理。
既然深呼吸這種行為治療對我無效,找出醫生開的粉紅色小藥丸後,我迫不及待的吞下一顆,然後強迫自己去洗個冷水臉,越冷越好的冷水臉。
或許我正在夢遊,又或許是因為思鄉,我承認自己最近有點想家,想念嘮叨個不停的老媽。最近第四台不停地重複播出部恐怖片——有個傢伙因為過度思念他過世的妻子,居然在自己潛意識裡製造出他妻子的形象,每天依舊過著兩個人的生活……
那是部爛電影,比爛電影還爛的爛電影,每次看到一半時我都會打起瞌睡,以致於到現在我還是搞不清楚那中間的過程。不過這不是重點,重點在於——我可不想跟那男主角一樣,最後被自己所創造出來的幻覺妻子給逼到跳樓自殺。
洗完臉後那隻怪貓果真消失了,憑空的消失了,像是從未出現過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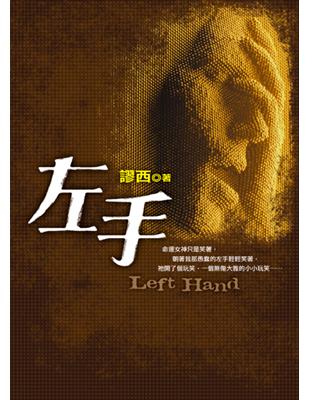




 收藏
收藏

 二手徵求有驚喜
二手徵求有驚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