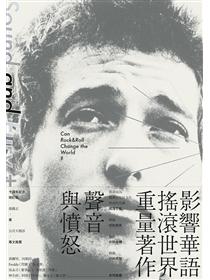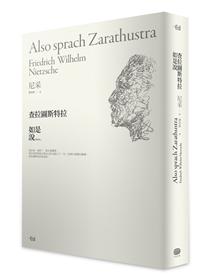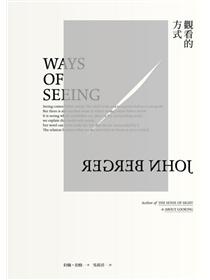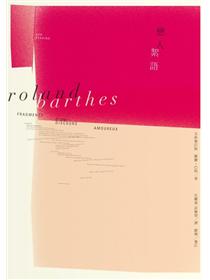五月天瑪莎 專文推薦
黃耀明、何韻詩、Freddy(閃靈)、吳志寧、吳永吉(董事長)、吳柏蒼(回聲)、林生祥、阿凱(1976)、楊大正(滅火器)共同推薦
影響華語搖滾世界重量著作!
搖滾成為整個青年反文化革命的先鋒,
因為它能挑起你的欲望,鼓動你的身體,刺激你的思想。
搖滾樂或許從來不能掀起革命,但當搖滾樂抓到了時代的噪音,這些音樂將不斷在被壓迫的人們的腦袋中迴響,將不斷在反抗的場景中被高唱。
尤其,任何政治行動、遊說或抗爭,都必須來自群眾的參與,而搖滾樂——不論是一首歌或一場表演,都可能改變個人的信念與價值,鼓勵他們參與行動。
當搖滾樂去感動人心、改變意識,並結合起草根組織的持久戰,世界就能被一點一滴地改變。
歡迎你加入抗爭行列
只要穿上抗爭標語的T恤
你便參與了革命等待大躍進的來臨
搖滾改變了我,也改變了你,而當每一個個人被改變時,世界也就被改變了。
--- ---
2004年,張鐵志用《聲音與憤怒》開啟中文世界的讀者對於搖滾與社會關係的新視野,成為中文搖滾書寫的經典,是每個世代搖滾青年的必讀之書。這本書讓純粹的音樂青年開始關心政治與社運,讓搖滾樂手更相信音樂的力量。
十年過去,那些憤怒的光影與聲音,又會與這個時代產生怎樣的新連結?
2007年,在《反叛的凝視》中,反思當代西方政治和文化反抗行動。
2010年,《時代的噪音:從狄倫到U2的抗議之聲》結合了搖滾與反抗精神,進一步書寫關於西方重要的抗議歌手以及他們所處時代。
2014年,時值時代最劇烈變遷的關鍵,全新改版的《聲音與憤怒:十週年紀念版》嘗試與這個島嶼的聲音與憤怒對話。本書除了對原先內容──從六○年代至今音樂對於社會各種不同的介入與連結,挖掘音樂作為一種反叛能量的可能性和侷限外──的增添與改寫,更增加了從捷克、東德、俄羅斯到拉丁美洲的抗議音樂。
作者簡介:
張鐵志
知名文化與政治評論人,在台灣與中港主要媒體撰寫多年專欄,關注主題包括國際政經、台灣政治、搖滾與文化。現任香港《號外》雜誌主編、文藝復興基金會副理事長,曾任台灣音樂環境推動者協會、台北當代藝術中心協會、台灣民主平台等NGO理事。台大政治系、政治研究所畢業,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曾任教於清華大學、台北藝術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著作包括《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反叛的凝視》、《時代的噪音》;合編有《愛上噪音》、《文藝如何復興我地》。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音樂人的推薦】
社會運動需要音樂嗎?占領運動期間,一個我們經常討論的議題。對於創作音樂的我與評論音樂的鐵志,答案明顯不過:音樂從來沒有在社會運動中缺席。尤其是對我這個害怕公開演說或喊口號的人,音樂是最佳的表達工具,因為音樂最容易感召人心。
金鐘清場後的週末,我在台北華山區聽著滅火器唱起〈島嶼天光〉,然後他們用粵語唱起〈海闊天空〉,突然我領悟到我們追逐自由之路是需要跨越占領區的。
聖誕後的週末,在九龍官塘聽着來自台東的巴奈,巴奈帶著台灣獨立樂手們灌錄的台版〈撐起雨傘〉來為香港打氣,當中夾雜著各地的方言和台東原住民的歌詠,令我覺得我們並不孤單,最後巴奈與家人更在台上用不算標準的廣東話唱起〈問誰未發聲〉(即〈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我已被感動得我淚流滿面。
這兩個場合,其實鐵志都與我一起在現場。無論是音樂人或寫作人,我們都用口,手與筆(或者鍵盤)去推動與見證時代的改變。——黃耀明
「音樂歸音樂,政治歸政治?」這是網路口水戰的陳年主題,但因為鐵志,讓這場陳年辯論遠超過口水戰的層次。音樂人的客觀創作背景、主觀創作理念,乃至於投入社會運動、參與政治改革的行動力,透過各種資料的分析、整理與呈現,鐵志讓音樂變得更立體,也讓音樂人更易於親近了。其實,身為音樂人,看到鐵志這種作者,會有點害怕的哩!——Freddy,閃靈樂團主唱
流行音樂是時代的切片,也驅動著時代,在網路之前,搖滾樂或者搖滾樂團幾乎是唯一的型式,搭載著憤怒、青春、公平、正義的普世價值,將所有反抗者團結在一起。《聲音與憤怒》是華文出版第一本以社會學角度出發的音樂書寫,將一個樂團或者一首歌作為case,對應一個運動、一個革命……至今仍無人出其右,十週年將屆,鐵志的增修讓人期待。——阿凱,1976樂團主唱
很開心鐵志老師的大作《聲音與憤怒》要發行十週年的增訂版了,這真是讓人感動的事。回想起第一次認識鐵志老師這個人,就是透過這本書,那時候光看到書名,就讓我們這群抱著搖滾夢的玩團青年感到興奮,因為台灣鮮少有這樣的書,可以從自己的觀點與角度,深度去論述西洋搖滾樂背後精神與跟社會運動,政治還有經濟的影響與連動關係。
更重要的是,在《聲音與憤怒》出版以後,鐵志老師更是投身台灣本土獨立創作音樂的觀察與書寫,讓這些取經自西洋搖滾的精神與概念,和在地玩團的台灣青年有了更直接的連結,鐵志老師偶爾會書寫我身為創作歌手參與社運的一些故事,但其實我才是因為他的文字與為人,讓我在參與任何的社運事物,感到有信心,感到被支持,感到驕傲!!
謝謝你,鐵志老師!希望《聲音與憤怒》一直長長久久地發行下去,持續帶給每一代新的音樂人,多元與深度的想像空間。——吳志寧
轉眼間,鐵志的《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已經發行了十年。經過這風風雨雨的十年,當初看來煽動的標題如今看來似乎不再需要為其背書。我們都知道音樂當然可以撫慰人心,但我認為沒有一種音樂能像搖滾樂這樣可以形而上的改變世界。
現在的青年不但對音樂的興趣更深厚;對政治也更加有感,所以很開心看到鐵志這本書即將要發行十週年紀念版,希望年輕的一代能藉由這本書更加理解他們未曾經歷過的和即將要面對的未來。——吳永吉,董事長樂團主唱
世界從來都不是在一夕間改變的。
從前,搖滾是對西方的鄉愁,對家鄉的盼望。大學時的我們,在春天吶喊遙想著伍茲塔克 Jimi Hendrix 那把燃燒的吉他;在地下社會尋找著 CBGB 裡 The Ramones 和 Patti Smith 的身影;期待屬於我們自己的 Bono,我們的搖滾英雄;然後,反覆聽著從 Napster 上搶先抓下的《Kid A》mp3,為了成為 Radiohead 而努力著。
十多年後,春天吶喊讓我追憶的是六福山莊舞台上,濁水溪公社那支暴走的乾粉滅火器;地下社會和 CBGB 一樣成為歷史,但記憶早已被賽璐璐阿義蒼涼的 slide 吉他聲占據;台灣的獨立音樂百花齊放著,不再活在巨人的影子下;而社群媒體和公民運動,則讓那些對英雄的遐想顯得幼稚無比。搖滾已不只是對陌生國度的憧憬,也是土地與世代的共同記憶,在渾然未覺中,它徹底改變了我們身處的世界。而在這過程裡,《聲音與憤怒》不僅闡述改變,更是參與了改變本身的重要著作。
搖滾樂改變世界?也許更應該說:改變世界的,都很搖滾。——柏蒼,回聲樂團 Echo
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
這個問題依然時常出現在我腦中,多數的時候我仍覺得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又有些時候,我會感受到搖滾樂正在改變些什麼,甚至覺得,就這樣繼續下去也許真的能把世界翻轉過來。
十年了,這問題存在腦中十年了,我還是沒有找到答案。
《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張鐵志十年前出版了這本書,拋下了這個問題,並在當年那個二十歲的搖滾少年心中搭建了一座橋,橋的彼端是音樂人的社會參與,我隨著書裡的章節,把每個年代的場景走了一遍,也推翻了心中曾存在的「音樂歸音樂政治歸政治」這種說法。
於是我告訴自己,要把音樂做好是可以慢慢去努力,去累積的,但是身體裡絕不能繼續住著對於這個世界袖手旁觀的靈魂。
熱切的參與這個時代吧!去探索,去思考,並且發出自己的聲音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
我會繼續努力,而且希望他可以。——楊大正,滅火器樂團主唱
名人推薦:【音樂人的推薦】
社會運動需要音樂嗎?占領運動期間,一個我們經常討論的議題。對於創作音樂的我與評論音樂的鐵志,答案明顯不過:音樂從來沒有在社會運動中缺席。尤其是對我這個害怕公開演說或喊口號的人,音樂是最佳的表達工具,因為音樂最容易感召人心。
金鐘清場後的週末,我在台北華山區聽著滅火器唱起〈島嶼天光〉,然後他們用粵語唱起〈海闊天空〉,突然我領悟到我們追逐自由之路是需要跨越占領區的。
聖誕後的週末,在九龍官塘聽着來自台東的巴奈,巴奈帶著台灣獨立樂手們灌錄的台版〈撐起雨傘〉來為香港打氣,...
章節試閱
16. 宇宙塑膠人的時空之旅──從布拉格、紐約到台北
多年前,我在台北讀著遠在捷克的宇宙塑膠人和哈維爾的革命故事,關於他們和紐約與布拉格兩座城市的故事。然後我去了布拉格尋找他們的痕跡。
沒有想到2006年,我會在紐約與他們相遇,以一種不遠也不近的距離。
更沒想到的是,繼哈維爾之後,宇宙塑膠人會在2007年來到台北。
1968年,布拉格
六○年代初,西方的搖滾狂風往東穿透了鐵幕,披頭四天真的歌聲來到了捷克。而爵士樂,不論是美國的還是捷克傳統的爵士,正在布拉格街頭的啤酒杯上起舞。
1965年,美國敲打的一代詩人、反文化的精神領袖艾倫金斯堡,受邀來到布拉格的查爾斯大學誦讀他的詩。一如他的「嚎叫」震動了西方文明,他的叫聲也在這個共產主義社會製造出無數個嬉皮。
這是六○年代捷克的反文化風潮,是布拉格的早春。長髮嬉皮在街上游晃,搖滾樂在收音機裡高唱,pub中本地的搖滾爵士樂隊也開始浮現。
1968年一月,捷克共產黨改革派領袖上台,開始鼓吹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放鬆言論管制,釋放獄中的藝術家和思想犯。這是所謂的「布拉格之春」。
但做為老大哥的蘇聯共產黨無法忍受春天的光亮。這一年八月,蘇聯派出坦克和十八萬部隊入侵捷克,狠狠地用黑幕把布拉格之春強行關上。人們激烈的抗議,一名哲學系大學生Jan Palach在Wencelas廣場自焚。
相比於自焚,比較沒那麼激烈的抗議方式,是成立一支搖滾樂隊。蘇聯入侵布拉格之後的一個月,宇宙塑膠人(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樂隊成立。他們的團名來自美國一個鬼才搖滾樂手Frank Zappa的歌名〈Plastic People〉,而他們也以翻唱美國樂隊The Doors和Captain Beefheart的歌曲為主。很快地,他們成為布拉格最讓人激動的迷幻搖滾樂隊。
1968年六月,紐約
就在坦克進入布拉格的美麗而古老的石板道之前,捷克劇作家哈維爾正在紐約參加莎士比亞戲劇節。他在東村的Fillmore East看到Frank Zappa的表演,在哥倫比亞大學看到佔領學校與警察激烈衝突的學生運動,並買了一張號稱後世另類音樂始祖的紐約樂隊地下天鵝絨(Velvet Underground)的專輯。
1976年二月,捷克
宇宙塑膠人誕生於一個險惡的時代。在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後,獨裁政府關閉搖滾表演場所,打壓言論自由、毫不容忍藝術自由。宇宙塑膠人的表演執照也被撤銷。兩年後他們重新申請卻被打回,因為他們的音樂太「灰暗」,並有「不良社會影響」,因此他們只能地下化。
1973年,宇宙塑膠人在一個城堡中錄製了他們第一張專輯《Egon Bondy's Happy Hearts Club Banned》,結合了迷幻搖滾、爵士、傳統捷克民謠等。同時,布拉格的地下文化圍繞著宇宙塑膠人展開,詩人們、藝術家們和搖滾樂隊們在郊區的波希迷亞村莊進行著屬於他們的藝術活動。他們有意識地把這種不同於官方文化的活動成為「第二文化」,並舉辦了「第一屆第二文化音樂祭」。宇宙塑膠人相信,搖滾樂乃是第二文化的領頭文化,是反叛文化的救贖。
但是威權的暴力機器當然不會放過他們。警察騷擾演唱會,毆打樂迷和表演者;76年的第二屆音樂祭,警察逮捕二十七人,包括宇宙塑膠人團員。
六個月後,國家開始了對宇宙塑膠人及其他人的審判。這是搖滾樂與獨裁統治的終極對抗。統治者控訴他們的歌詞反社會,會腐化捷克青年──這是搖滾樂從一開始就面臨的可笑指控,並將他們判刑。
但宇宙塑膠人其實不是支「抗議樂隊」,他們只是想玩搖滾樂,而不是要用音樂批判政治。他們最政治的歌曲是〈我們到底爲什麽要怕他們〉:
他們害怕明天的早上/他們害怕明天的晚上/他們害怕明天/他們害怕未來
他們害怕電吉他/害怕電吉他/他們害怕搖滾樂
他怎麽回事?連搖滾樂隊都怕?連搖滾樂隊都怕?
1977年,布拉格
1976年1月,宇宙塑料人的成員伊萬‧西羅斯(Ivan Jirous)認識了劇作家哈維爾。西羅斯放他們的歌給哈維爾聽,哈維爾說:「在他們的音樂中,有一種令人不安的魔力;有一種嚴肅和真誠。突然間,我了解了,不論這些人使用多麽粗俗的語言,或者留著多麽長的頭發,真理是在他們那邊的。」
對哈維爾來說,必須聲援這群搖滾青年,否則體制可能逮捕任何只是想獨立思考的人。為了聲援宇宙塑膠人和其他藝術家,哈維爾和其他知識分子在1977年一月一號發表聲明,並把援救組織取為「七七憲章」。在他們的聲明中說,「宇宙塑膠人是要用一種最真誠而自主的方式,來捍衛生命自由表達的慾望。」而這正是搖滾樂的精神。
後來,七七憲章就成為捷克最重要的民主運動組織。
1989年十一月,捷克的絲絨革命開始,不到一個月,共產黨就狼狽下台。
這是搖滾樂從被鎮壓,到激發起一場二十年的反對運動的最偉大的故事。
1990年,布拉格
兩個六零年代美國搖滾樂最具開創性的人物來到布拉格。
剛當選總統的哈維爾,邀請Frank Zappa去布拉格做座上賓。
這一年稍晚,地下天鵝絨樂隊的主唱Lou Reed來訪問哈維爾,哈維爾告訴他下天鵝絨的搖滾如何影響了捷克革命。晚上,Lou Reed和宇宙塑膠人改組後的樂隊一起演出他們的歌曲。
1998年七月,紐約
1987年,共黨政府說,如果宇宙塑膠人可以改名,他們就可以演出。對改名的內部分歧,導致了宇宙塑膠人的分裂。部分團員成立一個新的樂隊Pulnoc。1989年,Pulnoc第一次踏上美國土地,在紐約及其他城市舉行演唱會。
而1998年的夏天,在前一年正式復合後,宇宙塑膠人終於來到紐約這個搖滾的精神原鄉表演,在受到這個城市所誕生的音樂啟發的三十年後。
2004年5月,布拉格
我來到這個人們說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我走過那個哲學青年為了反抗蘇聯而自焚,89年時有成千上萬青年再度在此抗議的廣場;我在哈維爾和其他異議份子飲酒密談的小酒館中,遙想威權體制下的勇氣與理想;我走進一個位在三樓(二樓是賭場)、陳舊的革命博物館,看到了威權體制如何扭曲人們生活的展示,看到了抗議者的鮮血,以及宇宙塑膠人和哈維爾的勇敢微笑…..
當然,我只能在這裡進行對歷史的追溯與對昔日影像的哀悼。
2006年秋天,紐約
沒有想到,哈維爾會來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駐校八週,我在廣大的禮堂去聽了他的演講。
但更讓我興奮不是他,而是宇宙塑膠人的演唱會。那個我以為只屬於小說般歷史情節,那個屬於捷克森林中、留著波希迷亞血液的神秘樂隊,竟然真的在這個摩天大樓的城市出現!
就在城中的一個小小club中,三個六十幾歲的老傢伙(和一名美麗的女團員),專注而激烈地拉著小提琴、吹奏著撒克斯風,我身邊的捷克人瘋狂地唱著、跳著。
我知道他們的激動心情,因為我也來自一個有同樣歷史的國家。我們同樣艱辛地從威權體制步履闌珊前進到一個民主體制,同樣具有一個黑暗而冷酷的獨裁體制,也同樣有熱情和理想的反抗者。
2007年2月28日,台北
更沒想到的是,半年之後,宇宙塑膠人更在台北現身,在一場關於轉於正義的搖滾演唱會上演出。這個日子是二月二十八日。
他們會為了曾被噤聲的搖滾,為了歷史的正義,也為了人性尊嚴而唱。
17. 龐克暴女與政治反抗:俄羅斯的陰部暴動
2014年2月,俄羅斯政府正在索契熱鬧地舉辦冬季奧運,這是普京的燦爛時刻,或者本來應該是。
在一塊奧運看板前,幾名穿著色彩鮮豔、帶著毛絨頭罩的女孩拿著吉他唱歌跳舞──唱著「索契被封鎖,奧運被嚴密監控」。很快地,保安衝上來,用鞭子抽打和驅趕他們。
這個衝突畫面上了全球新聞,不僅是因為鞭子的粗暴,也因為他們是俄國最全球知名的異議藝術/音樂團體:「陰部暴動」(Pussy Riot)。這是他們一貫的行動方式:在特殊場所進行快閃式的演出,歌唱抗議歌曲,然後拍成影片上網。
這段被毆打的經過正凸顯了他們要表達的主題:俄羅斯異議聲音是如何被打壓的。
2012年2月,他們因為在東正教教堂演出而被逮捕,其中兩人到2013年12月才因為普京要在冬奧前改善形象而被釋放。
但黑牢並沒有嚇阻這群勇敢的女孩(她們在獄中也進行過絕食抗議)。他們又回來了。
…….
「陰部暴動」(Pussy Riot)樂隊成立於2011年8月,正好是俄國的新反對運動浪潮的開端;或者說,他們的故事正體現了普京時期俄國反抗青年的歷程。
2007年左右,上台七年的普京徹底鞏固他的權力,且飆升的石油價格讓他可以收買民眾。彼時陰部暴動的主要成員如Nadya正在大學念書,他們關注藝術,並開始參與各種抗議行動──但那時抗議運動還是微弱的。Nadya和其他朋友組成了一個團體叫「Voina」(戰爭),以行為藝術來表達反抗理念。
2008年開始,一個母親伊芙吉妮娃發起運動要拯救她所居住的森林不被公路計畫摧毀,吸引了許多中產階級和年輕人參加。2010年夏天,運動達到高潮,Nadya和她的朋友當然也參加了。但隨之受到嚴重打壓。
然後是2011年初的阿拉伯之春,俄羅斯的年輕人被深深震撼:為什麼連埃及都起來革命了?!
Nadya個人也越來越受女性主義和酷兒理論影響,尤其是美國藝術史上「游擊女孩」(Guerrilla Girls)和具有龐克精神的「暴女」(Riot Grrrl)的思想和行動深深啟發了她。她說,如果在二十世紀俄羅斯沒有激進女性主義的文化遺產,她們就只能自己幹,自己去生產女性主義的、龐克的、激進的、反抗的、獨立的文化。
在2011年,Nadya和好友 Kat成立新團體叫做The Pisya Riot──Pisya是俄羅斯小孩對於無論男女生殖器的可愛說法。他們的第一首歌是借用一支英國龐克樂隊的曲並填上了詞,歌名叫做「殺死性別歧視者」(Kiss the Sexist):
成為一個女性主義者,成為一個女性主義者
讓世界擁有和平,讓男人都去死
成為一個女性主義者,殺死性別歧視主義者
殺死性別歧視主義者,洗乾淨他的鮮血
他們又邀請會搞音樂的朋友,並且決定他們需要一套特殊裝扮,因為「如果我們只是去那裡開始尖叫,人家會覺得我們是白痴」。他們戴上彩色絨毛頭罩,並且改了名字:「陰部暴動」(Pussy Riot)。
團名「Pussy Riot」的意思是「陰部作為女性性器官,本來是被動的、沒有形狀的,現在突然要開始一場激進的革命來對抗定義她和決定她的位置的文化秩序。性別歧視主義者對於女人該如何生活有一套想法,正如普京對於俄羅斯人該怎麼生活也有他的想法。陰部暴動就是要挑戰這一切壓迫。」她們在後來解釋。
2011年11月,陰部暴動發表了第一支音樂MV,歌名叫做「釋放鵝卵石」(free the cobblestones)。這首歌中,他們批判俄國政治以及俄國女性的被壓迫處境,也談及埃及革命,唱著「讓紅場變成解放廣場」。這個視頻很快地被大量轉發,並被媒體報導。
三週後的12月1日,他們發表第二首歌曲批判普京的奢華。這首歌的MV記錄了他們衝進奢侈時裝品店演出而被安全人員趕走,他們甚至衝進一場服裝秀。歌詞依然結合了政治與性別的批判:Fuck the sexist fucking putinists。
而此時的俄國政治正進入一頁新的歷史。2011年9月時,時任總理的普京和總統梅德維傑夫宣布將要交換位置,普京要重新競選總統(普京在2000-2008年擔任總統,因為任期屆滿而下來擔任總理)。對於他們如此把總統權位當個人玩物,俄國人民深感不滿,而事實上,2009年的金融風暴已經對俄國經濟造成了嚴重打擊,油價也不斷下滑,導致經濟惡化。再加上,社交媒體的新時代已經展開,年輕一代早已有不同的訊息傳播渠道和批判空間。
12月4日舉行俄羅斯國會大選。
這場選舉原本就在執政黨的操弄下排除真正的政治競爭,國營電視也不斷為執政黨宣傳,普京和執政黨更是到處發錢來籠絡民眾。但結果,人民的嚴重不滿讓執政的「統一俄羅斯黨」的得票率大為下降,在首都莫斯科尤其如此。網路上流傳了許多政府做票的畫面,以及各種離譜的得票數據(如在車臣,統一俄羅斯黨的得票率是99.5%)。
憤怒的莫斯科人在寒冬大雪中走上了街頭,高喊「普京滾蛋」、「俄羅斯不需要普京」,震撼世界。這個多年來最大的抗議行動被稱為「大雪革命」(snow revolution),並掀起此後半年一波又一波的抗議行動。
陰部暴動的女孩們當然也參加了這些抗議行動,而那天,他們也被逮捕了,在警察局過了一夜。但遊行越來越大,就在2012年2月4日這個俄國幾年來最冷的日子,超過五萬人上街抗議。
2月下旬,陰部暴動前往俄羅斯東正教最受尊崇的「救世主大教堂」進行他們所謂的「龐克祈禱」,演出新歌〈聖母瑪利亞,把普京趕走〉。
在這首歌中,他們不但批評普京,也批評東正教對普京的支持和政府對同志遊行的禁止,高喊讓聖母瑪利亞成為女性主義者。這再一次反映他們反威權與反性歧視的立場。
在1917年革命之前,俄國本來就是政教合一,俄國人有三分之二自認是東正教徒。當普京政權的正當性開始岌岌可危以後,他為了鞏固政權,更積極強調宗教要為俄羅斯民族團結的核心,以討好廣大的東正教教徒。在2月4日的大遊行前夕,和普京關係密切的東正教大主教說:「東正教教徒知道不應該參加遊行。」他並提醒教徒九零年代俄國是多麼混亂,是普京穩定了俄國秩序。
在後來審判的證詞上,陰部暴動的兩名成員說,普京政府是要把宗教當做新的政治計畫,「這個計畫絕對不是真誠地要保存東正教的歷史和文化。而東正教教會由於在歷史上總是和權力有各種神祕的關係,所以最適合來執行這個概念。」而他們在教堂演出就是要摧毀這個連結,揭露權力如何利用宗教。他們要證明:東正教文化不是只屬於教會和普京,也可能是屬於市民抵抗的傳統。
演出的幾週後,三個女生被逮捕,七月底審判,成為全球注目焦點, 瑪丹娜等西方音樂人都為他們的自由疾呼。主要成員Nadya和Maria被判刑兩年,罪名是屬於「危害公共安全犯罪」。這個罪名顯然太過牽強,顯示這個判決的高度政治性:這既是普京政府對異議份子的打壓,同時也討好保守的東正教選民。
陰部暴動三人各自發表精采的長篇證詞。他們說:「陰部暴動生產反對的藝術,或者你可以說這是以藝術為外衣的政治。無論如何,這是一種公民行動,是對國家侵犯人權的回應。」
「在這裡被審判的不是暴動小貓,而是俄國的國家體制。」
「這是對整個俄國政治體系的審判,展現他們對個人的殘酷,對於榮譽與尊嚴的無視。如果這個政治體系要懲罰這三個女孩,那麼只是表示這個體系害怕真理。」
「我們要尋找真正的美和誠實,然後我們在龐克音樂中發現了。我們要進行龐克演出因為俄國的政治體系是一個階級體系、一個封閉體系,而政治只是為特殊利益所服務,這讓我們連呼吸俄羅斯的空氣都覺得噁心。」
「我們已經勝利了。因為這場對我們的審判是編造的,並且讓國家機器的司法過程中的壓迫本質無所遁形。」
其他成員又發表新歌「普京正在燃起革命的火花!」。
事實上,隨著2011年底的反抗運動增強,普京對反對力量的鎮壓也強化,逮捕更多人。2013年6月,政府更立法打壓同志權利,包括禁止青少年及兒童接觸同性戀資訊,壓制同志遊行等,目的也就是要討好保守宗教選。於是道德保守主義、威權主義,和強調俄羅斯榮耀的民族主義,成為普京政權的基礎,而索契冬奧就是一種要建立富強俄羅斯形象的計畫——一如此前許多舉辦奧運的威權國家。
Nadya和Maria在12月被釋放出來後,去紐約參加國際特赦組織的人權音樂會。Maria在紐約時報寫文章說:「用超過五百億美金用來建造奧運場館──巨大的、沒意義的、異形般的建築,其意義就是要滿足普京的自我,讓他成為一個帝王。索契已經成為一個封閉的軍事設施。」
「這些奧運活動的面貌是欺瞞的,一如整個威權體制。首先,掌權者不會直接驅逐你,而是有系統地要讓你採取他們認為適當的姿勢,也就是透過整套後蘇維埃的體制,從小學到墳墓,去消極地、去政治地行動。」
的確,普京就是要人們如此愛國。
而陰部暴動在索契被保安鞭打的演出,歌名就叫做:〈普京會教你如何愛祖國〉。
只是,這群女孩不會聽話,而是會展現另一種愛祖國的方式:政治異議與反抗 。
兩年多前,在法庭審判時,陰部暴動的年輕女子們說:
「我們比在法庭上我們對面的那些起訴者更加自由,因為我們可以說我們想要說的話,而他們只能說統治者允許他們說的話……他們的嘴巴被縫起來了,因為他們只是傀儡。」
是的,他們害怕搖滾樂,因為他們害怕自由。
16. 宇宙塑膠人的時空之旅──從布拉格、紐約到台北
多年前,我在台北讀著遠在捷克的宇宙塑膠人和哈維爾的革命故事,關於他們和紐約與布拉格兩座城市的故事。然後我去了布拉格尋找他們的痕跡。
沒有想到2006年,我會在紐約與他們相遇,以一種不遠也不近的距離。
更沒想到的是,繼哈維爾之後,宇宙塑膠人會在2007年來到台北。
1968年,布拉格
六○年代初,西方的搖滾狂風往東穿透了鐵幕,披頭四天真的歌聲來到了捷克。而爵士樂,不論是美國的還是捷克傳統的爵士,正在布拉格街頭的啤酒杯上起舞。
1965年,美國敲打的一代詩人...
推薦序
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
瑪莎
幾個月前,鐵志哥在臉書上捎來了個訊息,問我《聲音與憤怒》即將要出版增訂的十週年版本,是否可以為他寫幾句話?
沒有多加考慮,我便回覆答應。一方面因為鐵志哥在各媒體出沒的評論文字一直是我追逐拜讀的對象,而另一方面,《聲音與憤怒》是我音樂歷程中讓我停下腳步重要的書本之一。在心裡混亂盲目的時候回頭想想初衷,在旁人喧譁指責的時候抬頭看看前頭。
十年了,我都還記得第一次閱讀這本書的那個年代和自己:
二十七歲,我們在日本已經結束營業的「河口湖錄音室」準備第五張專輯,同時也看著那一年在雅典舉辦的奧運正在發生,2008才輪到北京奧運。台灣剛經歷完一場戲劇性的總統大選,當選的是那年在選前一天遭到槍擊的陳水扁。那時候臉書還沒有發生,Yahoo仍然是當時台灣最大的入口網站,最大的通訊軟體是MSN,Nokia是當時市占率最高的手機。蘋果的ipod最大只有到30G,仍然使用firewire。印尼那一年因為印度洋的大地震引發了大海嘯,造成了一萬多人的喪生和失蹤。
也許是因為終於從那個禁錮著男人的兵役中離開沒多久,也因為網路正在革命性地起飛,一切似乎都是如此地自由而且充滿可能性。我們不需要特別強調就可以心甘情願地相信,我們不需要證明就可以毫無保留地確定。評論的一言一語張揚著自由的權利,吶喊的一字一句單純地飄散理想的藍圖。不用擔心陰謀論的揣測猜疑,無需提防喧囂四起的人言可畏。在那個年代,除了本來就沒停過的藍綠撕扯之外,至少還能簡單地覺得未來還可以更好,努力可以有些回報,不滿能夠被溝通,憤怒能夠被尊重體諒。
也許是因為大學讀的也是社會學系的關係,讀著這本書的時候,想著書中提及的運動,思考著音樂的內涵和造成的風潮,我回起許多大學時所學的社會學理論和觀察。讀著讀著,血液仍然感覺滾燙,心裡也覺得激動而昂揚。你會深信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或乾脆誇張地說,別寄望政治或政客了,只有搖滾樂才能拯救這個世界。
只是回過神來,那已經是十年前了。
接到鐵志哥的邀請之時,是選舉剛結束一個月左右的十二月初。槍林彈雨的大選剛過,腥風血雨的評論未歇。除了電視和報紙媒體空穴來風但卻刀刀見血的新聞道德之外,網路上百家爭鳴的論戰也沒間斷過。2014甲午年年底將至,這是個令人迷惘的一年,也是個令人沮喪的一年。是讓人憤怒絕望的一年,也是讓人失去希望和信心且無所適從的一年。
十年了,我們相信的搖滾樂改變了這個世界嗎?就算不要只看台灣,看看那些我們相信的搖滾樂發源地,看看這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搖滾樂是不是真的改變了這個世界?搖滾樂讓這個世界有變好那麼一點嗎?又或者我們只是在搖滾樂的世界裡頭逃避,不願意去面對這個無動於衷且令人沮喪的真實世界?
在動筆寫下這篇文章前,我從書架上把它拿下,重新讀了一次。
讀著的時候,我仍然會因為Dylan或是U2的某些歌詞覺得感動且受到鼓舞。我仍然敬佩Velvet Underground雖然不是市場上成功的樂團,但卻吸引了一大票玩音樂的熱血青年開始拿起電吉他唱起了自己的歌。Sex Pistols和The Clash用他們的龐克反叛了音樂本身,也反叛了體制和整個保守的社會文化。David Bowie和T. Rex打破了先天生理上的性別分野,挑戰了世界文化對於性別看法的傳統觀念。
我們沒有辦法得知這些搖滾樂是否改變了曾經的世界而來到了今天的這個模樣,這是個假設性的問題,也沒有辦法獲得確切肯定的回答。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些人的音樂曾經引起如此深植人心,一直到今天,我們仍然循著他們的步伐軌跡唱著我們今天的憂心、苦痛、憤怒,還有看似微不足道的理想和希望。我們被這些音樂安慰和啟發,我們在這些歌曲中找到寄託和憤怒的解答,然後我們學著去獨立思考,用我們的角度觀察。直到有一天我們終於捲起衣袖,用世故冷酷的眼睛看透,用天真熱情的態度衝撞。不管為的是公平正義或是天氣的惡化,不管敵人是冷漠的世界或是僵化的思想。也許是領導者,也許是支持者,也許是非政府組織,也許只是為了自己的理想。不管怎樣,是那些搖滾樂感動了我們,教我們要秉持著那樣的信念往那個應許之地飛翔,是那些搖滾樂啟發了我們,教我們即使未來如漫畫《二十世紀少年》那樣操控在未知的「朋友」手中,都要哼唱著那段熟悉的旋律相信著最簡單的信念,去挑戰明知不可為的阻擋。
搖滾樂不需要特別好聽,只需要真實和誠懇的力量。搖滾樂不需要特別技巧,只需要勇敢和堅定的信仰。聲音是翅膀,憤怒是燃料,音樂一下,搖滾樂會帶著我們的信念去到很遠的地方。
搖滾樂有沒有可能改變這個世界,我想這從來都是個難以解答的問題。但對自己來說,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單憑搖滾樂本身,也許改變不了這個世界,真正改變這個世界的是,那些聽著也相信著搖滾樂,熱情天真瘋狂衝動,並且尚未被這個殘破沮喪的世界擊敗的人們。
.本文作者瑪莎,知名樂團五月天貝斯手
搖滾樂可能改變世界嗎?瑪莎
幾個月前,鐵志哥在臉書上捎來了個訊息,問我《聲音與憤怒》即將要出版增訂的十週年版本,是否可以為他寫幾句話?
沒有多加考慮,我便回覆答應。一方面因為鐵志哥在各媒體出沒的評論文字一直是我追逐拜讀的對象,而另一方面,《聲音與憤怒》是我音樂歷程中讓我停下腳步重要的書本之一。在心裡混亂盲目的時候回頭想想初衷,在旁人喧譁指責的時候抬頭看看前頭。
十年了,我都還記得第一次閱讀這本書的那個年代和自己:
二十七歲,我們在日本已經結束營業的「河口湖錄音室」準備第五張專輯,同時也看著...
作者序
自序:那些憤怒的光影與聲音
十年前(2004)的初夏,我出版了第一本書《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十年來,有許多多多朋友跟我說這本書如何改變了他們:有些音樂青年開始關心政治與社運,有些搖滾樂手更相信音樂的力量。然而,這本書改變最大的,是我自己的生命方向。
剛出版這本書時,我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剛進入第二個夏天。本來希望這本書可以在出國之前完成──我出國讀書那年正好是三十歲,所以或許這本書的出版作為我青春搖滾歲月的一場告別,從此專心進入學術生涯。
在本書之前,我只有零星公開發表過一些文章,不論是政治評論、音樂評論,或音樂政治。沒想的是,「聲音與憤怒」出版的第二個月,我開始同時在兩個主要報紙寫專欄。此後,我的軌道越來越從學術往寫作傾斜,並從一個單純樂迷越來越多介入音樂與社運的聯繫。
這十年來,台灣出現劇烈的變動。約莫就是十年前開始,台灣的音樂開始和青年抗議更多地結合,之後我們看到台灣獨立音樂更深地影響青年文化,也看到熱愛小確幸的年輕人如何轉變為憤怒的一代,而在去年爆發了太陽花占領運動。這是台灣新世代所展現出的「聲音與憤怒」。
2008年,《聲音與憤怒》在中國出版,又把我的人生軌道帶入一個新世界。我開始在中國許許多多媒體上寫專欄,結識中國的音樂人、文化人和異議者,進入中國的公共領域。我抱著巨大好奇心進入這個陌生又熟悉的國度,嘗試用寫作去參與此地的社會改變,當然也遭到被打壓的滋味,成為敏感人士。
2012年底因為《號外》雜誌邀請擔任主編,我搬來香港,見證這個島嶼的美麗與哀傷,並且看到一批音樂人如何如何透過他們的音樂,以及他們作為公民的力量,去捍衛這座城市。也許這個體制沒有一時之間被打倒、被轉變,但在這個過程中,人心已經不同,而世界不就是一個個真實的人所組成的?我們改變,世界也就隨之改變。
這就是這本書要講的故事。
2014.12 香港
1.
從來沒想到這本書的完成會在紐約,一個我少年音樂旅程的完美終點。
2002年到2007年,我生活在紐約——這個二十世紀西方文明中前衛與頹廢文化的源泉、華麗與腐敗的肉身呈現,以及六○年代以來民謠與搖滾反叛烈焰的火源。
在這裡,我走過了Woody Guthrie、Bob Dylan、Velvet Underground徘徊過的格林威治村,行過了許多搖滾人棲息過的Chelsea Hotel、約翰‧藍儂被槍殺的達科塔(Dakota)公寓門前,以及不遠處紀念他的「草莓園」(Strawberry Fields),並且和許多樂迷一起守望著龐克運動的傳奇酒吧CBGB的最後一夜。
我也親眼目睹了本書中許多搖滾反叛前鋒的表演,不論是改寫音樂史的紐約本地英雄:Dylan、路瑞德(Lou Reed)、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音速青春(Sonic Youth)、約翰‧藍儂的妻子小野洋子(Yoko Ono)和兒子西恩‧列儂(Sean Lennon),尼爾楊(Neil Young)、R.E.M.、湯姆‧莫瑞羅(Tom Morello),或是從英國、愛爾蘭來傳遞憤怒的比利‧布雷格(Billy Bragg)、原始呐喊(Primal Scream)、電台司令(Radiohead)和U2。
有些演唱會我無緣到場聆聽,只能在瞥見他們的廣告安靜地躺在報紙角落:Pete Seeger、Iggy Pop、性手槍(Sex Pistols)、大衛‧鮑伊(David Bowie),彷彿證明他們確實存在於這個時代。他們在我生活中就如走馬燈般鮮明卻一閃即逝。但無論如何,這個城市讓我確認本書的文字終究不是一場浪漫的虛構,而是真實人物輪番上演的歷史與現實。
在我眼前重現的不只是音樂表演,還有各種社會反抗。二十一世紀初的美國,正爆發美國繼六○年代以後最大的反戰運動,人們對六○年代的所有浪漫想像得以再度現身。當小野洋子在紐約另類雜誌《村聲》(Village Voice)刊登全版廣告,在全白版面正中寫著「想像和平」(Imagine Peace)時,我幾乎以為我手中翻閱的是三十年前的報紙;而當比利‧布雷格在狹小的舞台上呼籲聽眾參加反戰遊行時,我知道這不是已經泛黃的夢境,反抗就是現在!
2.
如果在紐約完成本書是一大意外,那麼人生更大的意外就是這本書的出版。
大學時期,我以為音樂僅會是一生的嗜好,攻讀政治學且以知識作為社會實踐的武器才是人生的志業。沒想到有機會把這兩者結合起來。
青春時期剛開始聽搖滾時,心中深處當然有著成為歌手的夢想:少年願望是做個在舞臺上翻來滾去砸吉他踢音箱的搖滾巨星,青年時期的想像則是蓄長髮留鬍渣背著吉他走唱街頭的抗議歌手。
因為沒有音樂天賦,歌手沒有做成,只能寫音樂文章這條路。
許多成長的回憶只有零碎而朦朧的片段,但是當時聆聽的音樂卻異常清晰,因為音樂終究是不會消逝的,彷彿電影結束時鏡頭突然停格,配樂卻驟然響起,對影片的最終記憶遂濃縮於這首歌和最後一個鏡頭。於是,這一首首歌曲拼湊起我生命旅程中那些過度曝光而模糊的聲音與光影,以及後青春期的聲音與憤怒。
3.
八○年代前期,小學五年級,我和叔叔去南京東路的「中華體育館」聽日後成為最常來台灣的「空中補給」(Air Supply)演唱會,聽到一半莫名腹痛(不是因為聽了歌),以至於演唱會未結束便狼狽逃出。不久後「中華體育館」被燒掉,也燒毀了我的「空中補給」啟蒙階段。
國中時的鏡頭是陽光燦爛的熱天午後,躺在叔叔的小房間床上,散落一地的是他的黑膠;封面是前衛搖滾的精緻插畫,或者重金屬性意味濃厚的美女封面。房中間則矗立著齊柏林飛船樂隊(Led Zeppelin)「通往天堂的梯子」,讓我可以慢慢地爬上去,逃逸到一個遠離升學體制壓迫的音樂世界。
到了高中,在放學與回家的空檔中,背著書包在台北街頭追趕上個時代的音樂,撿拾前人遺落的精采:在西門町佳佳唱片行搜尋以前本土的搖滾刊物(《搖滾生活》、《小雅》……),或是在大安路巷中沉醉於發行老搖滾錄音帶的「翰江」唱片,或者是在公館「宇宙城」唱片行認真研讀中文側標來進修音樂知識。
在這些文字中,他們說「搖滾是一種生活態度」——但也懵懵懂懂說不清這到底是什麼態度,只知道彷佛是一種不同於流行、一種抗拒主流體制的反叛姿勢。
進入大學後,我的熱情也從音樂轉向另一個世界:學生運動以及各種抵抗世界的知識。這讓我走入六○年代的西方學運史,然後發現在那個狂暴年代中,燃起熊熊烈火的正是民謠和搖滾。於是,我對搖滾樂的反叛有了更深一層認識,並開始好奇於音樂與反叛之關係。但彼時尚未想過會走上音樂寫作之路。
一個偶然機會改變了我的生涯。從1995年開始讀研究所時我就應邀在時事新聞週刊《新新聞》寫些東西,英國戴安娜王妃過世時,文化版主編希望我寫一篇關於艾爾頓‧約翰(Elton John)的文章。我試著把他放在搖滾文化中來書寫這下我開始嘗到駕馭文字的快感與探索搖滾樂豐富文化的樂趣,此後又繼續在《新新聞》和「淘兒」(Tower)唱片出版的雜誌《Pass》寫稿。我開始和所謂的「樂評圈」沾上邊。
1999年,《新新聞》與MTV音樂台合作一個節目,試圖參考美國MTV的「Rock the Vote」(詳見本書第十章),鼓勵音樂青年關心政治,我當仁不讓加入。案子結束後,又參與另一檔MTV的音樂節目「音樂百年紀事:在世紀末回顧西洋音樂史。彼時我正在撰寫關於台灣民主化與政商關係的碩士論文,於是一邊跑圖書館找台灣研究資料,一邊去充滿俊男美女時尚尖端的MTV電視台做節目,日子在人格分裂的生活中逐漸流逝。
4.
除了文字工作,也因緣際會地從事一些接合音樂和政治的戰鬥。
1995年,一位從事政治工作的學長找了我們幾個朋友幫當時在野黨總統初選候選人策劃一些吸引年輕人的活動。我們雖然不見得支持這位候選人,但有人支持我們做一些酷的事,何樂而不為?彼時春天的吶喊剛在南方出現,音樂祭還是島嶼上陌生的想像,我們決定舉辦一場「轟炸台北——青年文化藝術季」。
活動三部曲是:夜晚在大安公園舉辦一場新舊非主流串聯的搖滾音樂會,下午是從中正廟出發到大安公園沿街進行卡車搖滾表演,在卡車搖滾後和演唱會開場前是台灣電子音樂先驅者DJ @llen的trance party。台北雖然沒有被炸成廢墟,搖滾與電音卻首次用狂歡的姿態攻佔大安公園和台北街頭。
更值得驕傲的是,當時受邀表演的樂隊「觀子音樂坑」後來成為台灣最重要的樂隊「交工」,通過試唱帶甄選參與卡車搖滾的「瓢蟲」則成為台灣九○年代末最閃亮的女子搖滾樂隊。
當然,這場文化藝術季終究未讓候選人初選過關,更無法帶來政權轉移。但是就在那一年,台北的音樂地景卻真正地逐漸出現一場革命:許多另類樂隊開始一起「轟炸」台北(北大專搖滾聯盟、台大酒神祭、在台灣沃克的「自己搞歌」、當時地下文化高潮的破爛藝術節……);在城市的中心,反對黨市長推動空間解嚴,讓年輕人在曾經肅殺冰冷的「總統府」前狂歡熱舞;在城市邊緣則有是剛興起的rave party;而另類青年文化刊物《破報》也是從這一年創刊,成為這些音樂地景轉變的關鍵記錄者與推動者。
而我唯一一次從寫作者成為「演唱者」,是1996年誠品在敦化南路舉辦了一場「夏日嬉戲」活動,《破報》邀請了香港老牌左翼樂隊「黑鳥」來演唱。在那個因為過於悶熱以至如今回想起來竟被蒸發的汗氣搞得有點模糊的夜晚,「黑鳥」在表演最後演唱了〈國際歌〉,並邀請台下觀眾一起上去唱。於是在一些朋友的推擁下,我也激動地跳上狹小的舞台,一起唱著: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2008年,受黑鳥郭達年之邀,我和農村武裝青年去香港參加他所策劃的自由文化音樂節,大家再次一起在台上合唱!)
5.
如果借用政治資源進行的音樂政治行動,證明了這種實踐方式的局限,我也有機會嘗試從社運出發結合音樂。
1999年到2002年,我先後參與兩個台灣重要社運團體出版音樂專輯的策劃。首先是由「勞工陣線」出版、王明輝製作,通過廣泛向民眾徵求歌曲的方式所完成的專輯《勞工搖籃曲》。第二張是由「台灣人權促進會」出版,由朱約信(豬頭皮)邀歌、製作的專輯《美麗之島人之島》。這兩位製作人也是台灣從八○年代走來少數始終堅持社會理想的音樂人,這兩張專輯也某程度上總結了九十年代台灣零星的抗議之聲。
除了沒有直接音樂創作這條路以外,我算是嘗試了從政治介入、從社運介入,乃至從音樂媒體介入音樂與反抗,也開始思考各種介入方式的可能和局限。不過,對我個人能力而言,更有效的、更能影響大眾的或許還是文字。
對我而言,持續寫下去的動力只有一個,一如我曾經歷的不同戰鬥位置——不論是學術工作、媒體工作或者其他社會政治運動——目標都是要推動這個社會往更理想的方向前進。我聽到這麼多音樂、看到這麼多音樂工作者,是如此奮力地為改變世界而努力,所以抱著一份感動與大家分享這些音樂與他們的努力,並且激勵更多人對改變世界也抱持著希望。
於是有了這本書。
6.
這本書最基本目的能書寫搖滾樂中政治與社會實踐的歷史,並檢視從六○年代至今各種不同的介入策略和實踐可能,來挖掘音樂作為一種反叛能量的可能性和局限。
因為每個年代音樂政治的面貌並不相同(請見導論篇),且越早期的歷史,既有的書寫也越多,所以每個年代的寫作方式和分量有所不同,本書許多有關九○年代至今的搖滾反叛故事和分析,相信是首次出現在中文世界。
(2010年出版的《時代的噪音》補上了更多六○年代與之前的重要音樂人的故事。)
本書的主要限制是集中於「白人、男性、英美」。在其他國家有更多可歌可泣的音樂反抗故事,而不同音樂類型也深富激進政治的內涵,然而,本書以英美主流音樂體制中的創作者為主,除了個人視野的侷限,也更可以突顯這些有反叛意圖的音樂如何與主流商業體制之間的矛盾關係。
7.
這本書的誕生,最要感謝十多年前邀我出書的何穎怡,她在寫作與編輯過程中給予我很多意見,也感謝第一版的商周出版社編輯賴譽夫。王志弘的設計更讓這本書獲得了很大注目,很高興這本十週年紀念版能再邀請他設計封面。
本書出版後,獲得許多人的鼓勵與肯定,包括《聯合報‧讀書人》(現已沒這個版)頒發的年度十大好書,以及如許多音樂人和樂迷的喜愛與支持,讓這本書每年持續有人購買。是你們讓我認識到文字與理念的力量。
也因為這書仍然有新的讀者,所以我一直希望可以增訂。這本十週年紀念版是全新增訂版,舊文章經過重新潤飾、增加資料,最後一部分「更多聲音、更多憤怒」則新加入了文章,並且主要是在英美之外的地區:從冷戰時期時期的捷克、東德,當前普丁時代的「陰部暴動」,到軍事威權時期的智利和巴西。也因為2010年我出版了另一本書《時代的噪音》,所以本書也調整了部分內容,減少兩者重複。現在兩本書是高度互補的:《聲音與憤怒》是以事件和現象為主,《時代的噪音》則是講述不同時代的音樂人故事,讀者可以參照看。
我曾說過,我最想書寫的當然是台灣版、甚至華語世界的「聲音與憤怒」,而相信那本書已經在不遠處,我會繼續努力。
感謝推薦本書的音樂朋友,是你們的音樂啟發、感動著我們,讓我們可以勇敢地抵抗這世界的貧乏與不義。
最後,我要將這本書獻給我的妻子 Amy,謝謝她讓我在對世界憤怒的時候,能擁有一個不只是小確幸的美好人生。未來每一本書都會寫著妳的名字。
初版於2004,紐約
修改版2014,香港
自序:那些憤怒的光影與聲音
十年前(2004)的初夏,我出版了第一本書《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十年來,有許多多多朋友跟我說這本書如何改變了他們:有些音樂青年開始關心政治與社運,有些搖滾樂手更相信音樂的力量。然而,這本書改變最大的,是我自己的生命方向。
剛出版這本書時,我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剛進入第二個夏天。本來希望這本書可以在出國之前完成──我出國讀書那年正好是三十歲,所以或許這本書的出版作為我青春搖滾歲月的一場告別,從此專心進入學術生涯。
在本書之前,我只有零星公開發...
目錄
自序 那些憤怒的光影與聲音
導論 搖滾樂:是革命的號角還是伴奏?
輯一 一九六○年代
1. 六○年代:搖滾革命的原鄉
2. 在街上起舞
3. Woodstock:從反叛的烏托邦到烏托邦的反叛
輯二 一九七○年代
4. 華麗搖滾:一場豔美暧昧的情欲革命
5. 龐克搖滾:底層青年的憤怒呐喊
Extra|衝擊樂隊的永恆衝擊
輯三 一九八○年代
6. 當搖滾與政黨掛鈎:從「搖滾對抗種族主義」到 「紅楔」
7. 從「Live Aid」到釋放曼德拉:良心搖滾的政治學
8. 「警告父母」:流行樂的言論自由戰爭
Extra|是自由化還是壓制自由?美國音樂界新寡頭的爭議
輯四 一九九○年代至今
9 走向黎明:如何歌唱生命之歌?
10. 愉悅的政治:瑞舞時代的反叛之舞
11.「搖動選票」:以音樂進行組織動員
12. Britpop與第三條路的背叛
Extra|碼頭工人站起來:「撼動碼頭」
13. War Is Over?沒有停止的反戰歌聲
14. 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全球化與新世紀的搖滾行動主義
15. 告訴我們真相!
更多聲音、更多憤怒
16.宇宙塑膠人的時空之旅——從布拉格、紐約到台北
17.普京為什麼害怕陰部暴動(Pussy Riot)
18. 自由之鐘:一場搖滾音樂會與柏林圍牆的倒塌
19. Tropicália:巴西的音樂、文化與反抗
20. Victor Jara:革命不能沒有歌曲!
自序 那些憤怒的光影與聲音
導論 搖滾樂:是革命的號角還是伴奏?
輯一 一九六○年代
1. 六○年代:搖滾革命的原鄉
2. 在街上起舞
3. Woodstock:從反叛的烏托邦到烏托邦的反叛
輯二 一九七○年代
4. 華麗搖滾:一場豔美暧昧的情欲革命
5. 龐克搖滾:底層青年的憤怒呐喊
Extra|衝擊樂隊的永恆衝擊
輯三 一九八○年代
6. 當搖滾與政黨掛鈎:從「搖滾對抗種族主義」到 「紅楔」
7. 從「Live Aid」到釋放曼德拉:良心搖滾的政治學
8. 「警告父母」:流行樂的言論自由戰爭
Extra|是自由化還是壓制自由?美國音...
購物須知
關於二手書說明:
商品建檔資料為新書及二手書共用,因是二手商品,實際狀況可能已與建檔資料有差異,購買二手書時,請務必檢視商品書況、備註說明及書況影片,收到商品將以書況影片內呈現為準。若有差異時僅可提供退貨處理,無法換貨或再補寄。
商品版權法律說明:
TAAZE 單純提供網路二手書託售平台予消費者,並不涉入書本作者與原出版商間之任何糾紛;敬請各界鑒察。
退換貨說明:
二手書籍商品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二手影音商品(例如CD、DVD等),恕不提供10天猶豫期退貨。
二手商品無法提供換貨服務,僅能辦理退貨。如須退貨,請保持該商品及其附件的完整性(包含書籍封底之TAAZE物流條碼)。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
退換貨原則、
二手CD、DVD退換貨說明。